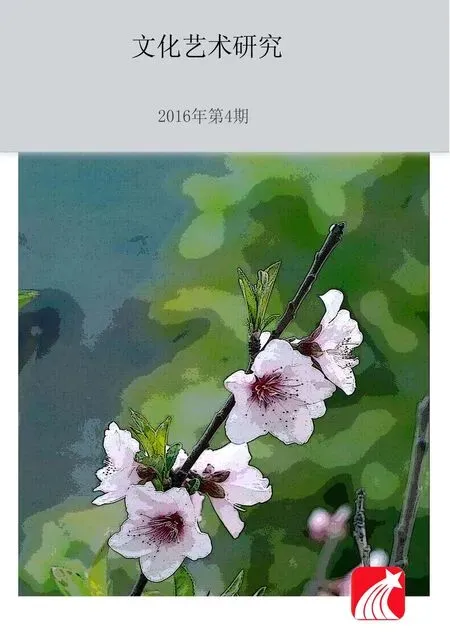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空间与环境法因应*
陈真亮 连燕华
(浙江农林大学 法政学院,临安 311300)
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空间与环境法因应*
陈真亮 连燕华
(浙江农林大学 法政学院,临安 311300)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更是环境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加强文化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和治理,是文化生态自觉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危机、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在整体的“生态人文主义”导向下,对环境法律价值、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进行发展完善。环境法的代际发展也亟须从“生物多样性”迈向“文化多样性”保护,需要迈向“文化国家”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保护。
文化多样性;碎片化;文化国家;适应性变革
《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将“文化多样性”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更是将“文化”和“文化多样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当前,我国文化保护工作存在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破坏性“保护”或“建设”,甚至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确定了生态空间管制政策,这要求环境法从环境要素的保护转向各环境要素构成的整体性生态文化空间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本质是保护多样性文化生态格局,因此要正确处理好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也更要协调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等若干关系。反思是进步的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背后的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关注与反思,首先应当是制度上尤其是法律制度上的反思与检讨[1]。
一、我国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立法现状
文化多样性是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的条件,是制度创新的条件,也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条件[2]。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颁布实施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有的地方为挤进文化遗产名录,采取了“建设性破坏”的做法。甚至在还没有得到全面充分的保护之前,就将其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这实际上是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各取所需。诚如乌丙安所言:“如果不按科学规律进行保护,搞不好,这是在打着保护的旗子进行最后一次彻底的文化破坏。”尽管从国家层面到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对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与政策,但总体来看,我国当前的文化法律体系仍然不完备,无力为文化多样性提供充分有效的全面保护。
(一)政策现状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精神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要求,文化部开展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就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要求“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从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7年6月文化部批准)设立至今,我国已经有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自此,我国开启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综合整体保护,环境法也进入一个新的保护和发展阶段。
一般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如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区域及环境中,使之成为“活文化”,是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文化生态保护区不同于自然保护区的范畴,是文化多样性保护和建设的核心内容,更是我国第一代环境法向第二代环境法甚至第三代环境法迈进与转型的重要体现。
(二)法律现状
1982年《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在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决定》修正,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根据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二条明确规定受国家保护的文物有以下五种:⑴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和壁画;⑵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⑶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⑷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文献资料等;⑸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文物保护法》在保护有形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国于2011年6月1日开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至此,我国已经有了“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标志”等。此前,我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初步完成了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转化义务,开启了我国文化多样性保护法制的新里程。
我国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都是环境法的保护对象。可见,包括人文遗迹在内的文化多样性保护是未来环境法的重要研究内容和实践命题。
(三)地方相关立法典型
在地方层面,比如《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是浙江省首部以保护畲族民间文化为主体的地方立法。此外,浙江省还出台了《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将对历史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2000年5月26日,《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云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确定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概念,内涵亦侧重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传承价值等。2002年制定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基本上与云南地方性法规规定的相同,在范围上扩展到“保存比较完整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区域”。《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具有重要价值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特定区域可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这意味着,“文化生态保护区”概念首次进入中国法律体系。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加强文化生态的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我国一些地区和城市,还出现对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进行单独立法保护,如《安徽省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等,就以单项艺术表现形式为保护对象专门制定地方性法规。
从上述政策与法律法规来看,随着2003年联合国《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实施,我国开始重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体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保护从过去的分散、不集中到现今的集中保护;其次,从过去以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保护为主,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得到提升;第三,从过去没有权威性法律法规的统领到现今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其概念、内涵、范围作为法律界定和共同性规定;第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结合国际化趋势,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概念,使法律具有更强的统一性和适应性;第五,我国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应对与保障路径主要有立法保护、开发性保护、创新性保护等,初步确立了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化框架。
二、环境法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一)文化多样性保护契合环境法的代际发展与转型
文化多样性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各民族文化特性也都与特定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保护文化遗产不单单是文化遗产自身的单一保护,目前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导向是在利用中保护,生态旅游刺激经济发展,所得经费反之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3]。实际上,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单是一个概念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4]。因此,作为人为环境要素的文化遗产,在环境法上作出必要的保护,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同时可行性也强。文化多样性要求法律不仅应当重视现代文化目标,也应当重视传统文化目标,法律的文化目标开始呈现多样性[5]。因此,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该条款可以理解为也可以解释出“文化多样性”“文化权”“文化国家”的保护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属于“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范畴。
因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本质上就是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多样性文化,常常是和生物多样性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再者,从“环境”和“环境问题”内涵的动态发展来看,环境法学研究不应只关注环境科学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还应关注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等文化生态的法律保护问题。[6]文化多样性特别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亟需引起环境法理论研究和实务部门的重视。
(二)文化多样性保护契合环境法的价值理念与法理
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要实现环境法的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必须克服观念上、法律制度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障碍。
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系统论和综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为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视角。现代生态学表明,世界是由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具有能量转换、物质循环代谢和信息传递功能的整体[7]。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
(三)多样性文化是环境法的“人类共同遗产”与“人类共同关切”
“人类共同遗产”具有主要的固有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因此“依据事实本身”是“人类共同遗产”;同时它又面临诸多威胁,急需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因而是“人类共同关切”。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不否定其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需加强国际合作,在国家间进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分配,并充分考虑代际公平。
当多样性脱离文化,失去文化深度的研究,多样性即失去了价值,因此以往多样性研究大多被赋予前缀,如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给予承认和肯定。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用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确保保护和为后代传递文化的义务也可见于文化保护的相关国际条约。比如在挪威的环境法律中,就有“将保护土地和文化景观作为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健康和福利的基础”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8]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类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各样,存在诸多方式,因此需要对多样性的保护进行国际标准化。“人类共同遗产”和“人类共同关切”应该共同作用于全球公共领域下的国际管理指导,明确其权利,义务、责任的标尺。同时,保护文化多样性,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国家间的任务分配应遵从“共同且有差异性”原则,国家间相互合作,保护文化多样性,共同捍卫人类共同家园。
三、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环境法回应与调适
(一)“生态人文主义”导向下的环境法价值之转型与重构
生态人文主义是具有多元文化内涵的一种新人文主义,它既保留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又汲取了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人文情怀向自然界延伸的产物。生态人文主义主张人与自然互相包含的辩证思想,是脱胎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新型人文主义,不否定工业化,同时也不倡导非理性,更加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对人类进步的意义,主张弘扬科学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快速增长。
环境法是保障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律,生态文明的理念对环境法的价值取向有深刻的影响和导向。研究环境法如何保障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当其冲的应该研究环境法的价值追求。环境法的价值追求应该是由多个价值构成的动态价值体系[9]。新世纪,探索人类如何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寻求社会文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就要重视各民族的生态经验和意识[10]。如果以自由看待发展,那么经济发展也好,环境保护无疑是要以民生主义为主要原则和导向的。
在环境法价值重构中,通过对传统环境法的价值基础和体系的反思分析出局限性,进一步提出以生态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新价值观。在构建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环境法转型理论无疑是对环境法治理论的推进,也是对实践方面生态维护法治进化的一个推动。生态人文主义认为,人类只有在改变工业文明条件下的主客体关系原则和人类中心论的态度,只有在转向有利于自然整体的稳定、完整和健康,只有在有助于自然事物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促进自然进化的趋势下,才能找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道路[11]。所以,生态人文主义是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和解、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人文主义形态。环境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关切就是权利的培育,权利至上理念的造就,而终极关怀则是人文自由、理性精神的承认和尊重。
(二)“环境”内涵的扩张与环境法的代际发展
2014年的新环保法所规定的“环境”采取的是非广义上的环境概念*广义上的环境概念一般是指由人类与一切社会、文化、政治、设施、制度所形成之整体空间。如此高度概括的环境概念,对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并无实际效用,恐怕无法构建出一个可与其他公共任务相区别的特有的环境保护任务,因此不足为取。,环境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上的概念,也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上的概念。*当然,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有必要从自然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人文人类学、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来对环境进行多维度的认识。实际上,人类对环境概念的认识也恰好体现了一个对环境法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即经历了环境法律观的泛化到规范化研究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对各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出现了很多学科之间的整合与交叉性的综合性研究。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包括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要素,它强调与“人”相关联的环境内涵,从人的生活与生存基础出发,来说明所要保护的环境概念,指出了环境保护最核心的任务在于确保人类之生活与生存。这种以人为基础,兼顾生态环境的环境概念虽然在学界不无批评之词,但相对而言还是较为科学的,就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文明法治时代,“环境法所保护的法益已不再仅仅是交易安全与社会安全,而是人在生态系统上的利益,包括环境本身,确保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的健康与安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良性循环,以及维护当代和未来世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与生态的可持续性。”[12]由于人类对环境内涵认知的进步与发展,环境法也产生了第一代环境法、第二代环境法、第三代环境法等划分。虽然学界对何谓第一代环境法、第二代环境法、第三代环境法尚未达成共识*据中国知网统计显示,在国内,万劲波、周艳芳等最早提出了第一代环境法、第二代环境法、第三代环境法这个提法。参阅万劲波、周艳芳:《试论比较环境法的概念及其特征》,载《贵州环保科技》2001年第3期,第10页。,但这不妨碍对我国未来环境法典的前瞻性问题进行整体定位和把握。
再者,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和文化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观之,既要重视生态健康问题也更要重视公众健康问题,甚至在有的时空条件下要体现“健康权优位”的保护原则和规制。因为,环境法特别强调“综合管理的对象是人类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活动,管理的客体是人与自然复合的而不是割裂的有机系统;综合生态系统方式承认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是构成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3]。也就是说,第二代和第三代环境法要“见物见人”,应以“生态人文主义”为导向和指引,坚持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问题进行整体性保护。因此,从环境法的代际发展来看,我国正在向第二代和第三代环境法迈进与转型。[14]
(三)文化多样性的环境法保护应坚持整体性原则
1989年颁布施行的《环境保护法》在我国环境保护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内外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保护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我国在2014年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了系统性修订与完善,成为环境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基本法。新环保法确立环境权中的各项权利,同时着重强调了环境法保护的公众参与原则。新环保法第五条新增规定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即“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此外,还应该从人类的作用、需求和价值(包括文化方面),生物多样性管理的保护,环境质量、环境整体性和生命力等方面加深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及功能内在关系的全面理解。
再者,应通过对环境、文化、经济等遵循生态友好型发展的理念,确立综合生态文化管理的原则或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要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因此,文化多样性保护内在要求环境政策与法律对其采取综合性的一体保护。也就是说,要采取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特别是要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当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时间和空间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所谓整体性,就是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也包括传承人和生态环境。[15]具体来说,对文化多样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一是要进行文化整体性保护,二是要进行生态整体性保护,三是要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进行并重保护。
总之,文化多样性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注重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样性文化应在其所属的社区及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中进行一体化保护,强调不离本土及民众的文化延续,强调可持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强调必须将遗产与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完整保护,是一种文化生态整体主义意义上的一体化保护。比如,当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坚持文化整体性和生态整体性的双重一体化保护,有助于促进整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生态、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环境法从“生物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转型
生物多样性既是生物物种及群落存在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得以生态性生存的基础和前提。生命既是生物多样性的现实存在,也是我们认识、把握及体验生物多样性的核心问题。对人类存在来说,生物多样性首先直视人的生命,它使人能够在复合且复杂生态系统中生存与发展。生物多样性还提供了一种认识与思维的方法,描述了一个思维的进程。形成了“联系的联系”的自组织结构,也使文化多样性的组织系统成为复杂结构。文化多样性作为思维转向应该是这种自组织结构演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同时也呈现一种全息性结构[16]。生物多样性是生命体、生物物种、生物群落存在的根本条件,是生态系统结构性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类生态性生存的基础和前提。简单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自然生物与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程度,并且是系统整体性的存在及关系化的复杂程度、多样化程度。
因此,人类要体验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构建文化多样性。*《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指出:“生物多样性的加速损失不仅意味着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损失,而且还破坏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的结构。这种文化多样性依赖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持续性而存在,并且与它们协同进化。”这是有关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协同进化关系的最早论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环境法的核心构成要素;而文化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精神升华,保护文化内涵,人类灵魂得以传承。从生物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既凸现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也昭示出人类在新世纪摆脱危机的前景。生物多样性对于物种的保存和人类生存具有前提意义;同样地,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说,工业化时代危害的主要是生物多样性的话,那么,信息时代危害的主要是文化多样性。为了实现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来保护文化多样性,如在不同文化之间确立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本土化进程、在21世纪建立多极化的国际关系格局等[17]。
不过,从濒危物种保护等角度来看,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法律保护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有待协调。但从总体上而言,文化多样性保护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一些特定领域或地区和民族,保护文化多样性有时候会牺牲一部分生态利益,不一定有利于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包容一些少数民族或原住民基于生存需要或者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行为,有必要正视特定民族享有的基于习惯的狩猎权利,灵活采取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政策。对政府而言,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要重视和正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在冲突及其根源。国家应当通过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问题。
环境法珍惜文化建设,这点主要体现在环境法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继承和保护上。 特别是从环境法的法律渊源上来说,特殊区域保护法的设置,重点表达了环境法对于文化的珍惜。通过对于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遗产、文物古迹等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具备特定价值的区域和要素进行特殊的保护,环境法践行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传承和维护。[18]
四、迈向“文化国家”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保护(代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多样性所蕴涵的独特价值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还体现在同一种文化的内部。“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特征、物质特征、智力特征、情感特征的总和。它不仅包含艺术、文学,还有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信仰等,是文化赋予人类反思的能力”[19]。文化多元的民族国家需要在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寻找平衡点[20],应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格局,尊重、肯定多元化的民间信仰等大众文化、草根文化、乡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本体性地位及重要意义;要避免走“改、破、建、立、禁”等发展死循环。在多元文化生态体系构建和发展完善中,需要渗透和发挥好多元文化的作用,而保存和有效利用多元文化是国家、社会和公民等主体的“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21]
文化生态保护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紧密相连,是民族身份自豪感和归属感的基础。文化多样性可以激发民族感情,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造就了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使其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奠定了强大的文化基石。从“文化国家”(cultural state)的角度看,其内在的需要环境法走向生态自觉与文化自觉。这意味着文化主体和生态文化保护区将通过自己的价值追求去发现地方性知识,去创造尊严与幸福,也意味着教师基于批判反思、对话理解,打破旧的惯习,以创造性的教育实践推动教育文化的变革,重建教育的文化生态场域。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要求“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长远来看,这是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长期予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第1条所言:“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现今,我国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理解,尊重和拯救文化多样性事关人类发展的未来,人类向何处去及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这一深层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外可以通过立法等措施为文化贸易设置适当的“文化例外”原则,筑牢文化多样性的“护堤”;对内可以通过适度开发、鼓励创新以及相应的资助、扶持等措施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发展空间,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22]。费孝通先生倡导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心理生态相结合的“三态合一”思想,实际上刚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环境健康、公共健康等问题是高度契合的,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也给文化多样性的法律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这意味着环境法不能仅仅关注生态保护,还要研究文化多样性保护;既要见人又要见物,要以生态人文主义为指导,既要保护生态平衡与健康也要保护公众健康。如此,环境法才能做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三态合一”,才能做到文化生态自觉,并自觉构建文化生态格局。
[1] 费安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6(5).
[2] 刘国利,吴镝飞.略论文化多样性与法律价值体系的完善[J].法学评论,2013(6).
[3] 胡佳.试析我国文化产业遗产的环境法保护[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1).
[4] 戴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惑[J].新闻瞭望周刊,2007(30).
[5] 刘国利,李鹏飞.文化多样性对民生法律的启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6).
[6] 陈真亮.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7] 朱祥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价值理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3).
[8] The Norwegian Act No.23 of 12 May 1995 Relating to Land [Z] .Oslo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Oslo , 2001.
[9] 吴贤静.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的价值追求[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10] 李军.傣族生态文化及其法律保护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1.
[11] 徐国栋.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44-147.
[12] 柯坚.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13] 杜群.规范语境下综合生态管理的概念和基本原则[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14] 李明华,陈真亮.环境法典立法研究:理念与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23-127.
[15] 周小璞.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个问题[N].中国文化报2014-11-21(7).
[16] 盖光.从生物多样性走向文化多样性[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2).
[17] 何中华.从生物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J].东岳论坛,1999(4)。
[18] 张忠民.“五位一体”的环境法审视——兼谈《环境保护法》的修订[J].绿叶, 2015(1).
[19] 路易斯·奥尔蒂斯·莫纳斯泰里奥.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文化权的保护[J].人权,2012(5).
[20] James A.Banks.多元文化国家的多样性及公民教育[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3).
[21] 陈真亮.环境保护的国家义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22] 任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危机和出路[J].理论学刊,2011(8).
Ecological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sponse to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CHEN Zhen-liang,LIAN Yan-hua
Cultural diversity is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but also an important value target of environmental law.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cultural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view of the crisis of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legislative status and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nd perfect th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law, the basic principles, the basic systems and so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is also an urgent transformation need from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towards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towards the needs of cultural diversity protection in the era of “Cultural State”.
cultural diversity; fragmentation; Cultural State; adaptive change
2016-12-08
陈真亮(1983— ),男,浙江台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多样性保护政策和法律、环境法研究。连燕华(1983— ),女,河南商丘人,讲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法治研究。
本文系2015年度浙江省文化厅项目“浙江省新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2016年度浙江省教育厅项目“新常态下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困境与路径选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674-3180(2016)04-0022-08
G120
A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