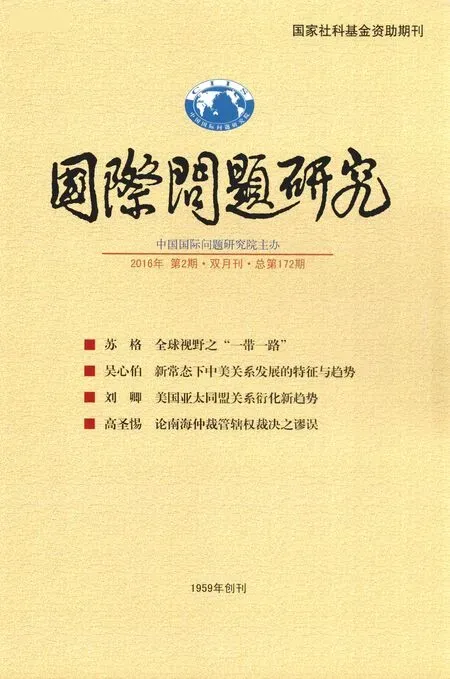航行自由制度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袁发强
航行自由制度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袁发强
〔提要〕“航行自由”在当代国际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其他公约和国际习惯法为补充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现出从关注“自由”转变为规范“航行”的权利义务、从强调航行不受干涉转变为协调航行权与沿海国利益、从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转向博弈与共同治理并存的特点。与此同时,若干新问题需要国际立法作出澄清和协调,如专属经济区内资源利用开发及海洋环境保护与航行自由的冲突、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与沿海国安全利益的冲突等。充分利用航行自由制度,积极参与该制度的后续国际立法完善将是中国适应角色转变后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航行自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
*本文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海洋自由航行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4YJA820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航行自由”是国际法上有关海上航行的一项重要原则。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下文简称《公约》。《公约》全文详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生效以来,国际法上的航行自由制度通过成文国际立法得以体系化。[1]在《公约》生效以前,“航行自由”只是作为“海洋自由”原则的一项内容存在于国际法中,主要含义为一国船舶(包括军事船舶)的航行活动只受船旗国法律管辖,可以自由航行。《公约》则通过划分不同海域的法律地位确定不同海域航行活动的内容范围。但是,由于《公约》并未全面规范海上航行活动,在个别领域仍然存在模糊的空间,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新的争议不断出现。近年来,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攻击为妨碍航行自由;中国日益“走出去”,亦需要航行自由制度的维护。因此,有必要对航行自由制度和中国的政策取向进行新的审视。
一、当代航行自由制度的特点
“航行自由”最早包含在“公海自由”的范畴中。直到1958年的《公海公约》,“航行自由”都是“公海自由”的组成部分。《公海公约》首次明文确定了“公海自由”的法律原则,规定“公海自由”包括四方面内容,“航行自由”被放在第一位。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广泛性,[2]《公约》现有167个缔约国,有关数据参见http://www.un.org/Depts/los/reference_ files/chronological_lists_of_ratifications.htm。(上网时间:2015年11月30日)以及个别海洋强国虽然没有加入该公约,但接受该公约创设的大部分国际立法(如美国),可以说,航行自由原则被广泛接受为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从海上航行视角看,《公约》不仅规定了公海的航行问题,而且全面规范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各种海域中航行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航行自由”在该公约中实现了从原则落实到具体制度的转变。在《公约》有关领海、毗连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专属经济区以及公海等各个部分,都有关于航行自由的法律规范,涉及船舶航行的权利、航道、船旗国管辖权、沿海国管辖权等诸多事项。从该制度的发展看,其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以《公约》为中心,成文国际法为主,习惯国际法为辅
虽然《公约》全面规范了海洋航行问题,对不同海域航行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范,但它并不是唯一调整海上航行的国际立法,其他国际公约也对航行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着有效的调整。[1]张小奕:“试论航行自由的历史演进”,《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4期,第31页。实际上,对海上航行的法律限制越来越多,即使是在公海上的航行,也越来越受到诸多国际法律的规范和限制。总体上看,以《公约》为中心,其他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国际公约相应展开有关航行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制,“航行自由”在国际法中已经形成一个制度体系。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全面规范各类海域的航行之外,其他国际公约,如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约》、1972年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等,都从不同方面对船舶航行进行了规范和限制,也是航行自由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
当然,有关航行自由的国际法律并没有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公约的通过而完全成文化。例如,有关军事船舶和政府公务船舶在公海上的活动,《公约》里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国际立法讨论时存在多方利益博弈,[2]Dale Stephens,“The Legal Efficacy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sertions,”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Vol.80,pp.239-240.另一方面,国际条约只对缔约国有约束力,这就为习惯国际法继续发挥作用保留了空间。不过,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变化是缓慢的,其内容的形成需要国际社会反复实践才能确认,同时内容的改变也极其艰难。除非国际立法的条文明确改变了某一习惯,该习惯的效力就仍然保留。[3][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第1卷第1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国际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时,也总是会在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中寻求平衡,引用国际习惯解释国际立法条文的含义,确立国际条约的效力边界。[4][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上卷第1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8页。
在航行自由的制度体系中,对什么是国际法中的“航行”,“航行”的主体包括哪些类型的船舶,所有国际公约都没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这就是属于习惯国际法范畴的问题。[5]不论是《公海公约》,还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没有对“航行”进行法律上的界定。从实践角度看,与“航行自由”相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包括了各种不为法律明文禁止的海上活动,“航行自由”的主体也并不排斥军事船舶和政府公务船舶。正因为如此,在《公约》生效后,有关习惯国际法在航行自由制度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二)从关注“自由”到规范“航行”的权利义务
在“航行自由”作为一种理念、一种国际法思想而存在的时期,对“航行自由”的关注集中在“自由”上,如何航行却不是重点,这是1958年《公海公约》的缺陷,但也是此后国际立法规制的发展方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航行自由的立法不仅体现在重申航行自由原则,更在于为不同海域的航行都对应地规定了船舶和沿海国的权利与义务。[1]在《公约》的立法体例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对应性的立法体例。在不同水域中,船舶的航行权利与沿海国的义务、沿海国的管理权力与航行船舶需要遵守的义务都是对应地规定在邻近条文中。例如,对于船舶在一国领海的航行,《公约》一方面赋予航行船舶无害通过权,另一方面又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外国船舶在领海内不得进行的12种活动;[2]参见《公约》第19条2款。在规定沿海国可就9种事项制定关于无害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同时,也规定了沿海国不应妨碍外国船舶无害通过领海的义务。[3]《公约》第24条。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和专属经济区等,《公约》也采取了同样的立法模式。即便是在公海这个航行自由度最高的海域,《公约》也采取了对应性立法,规范航行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在规定船舶受其船旗国法律管辖的同时,要求船舶与所悬国旗国家之间具有真正的联系;[4]《公约》第91条1款。要求船旗国为保证海上安全而对所属船舶进行严格管理,并承担共同打击海盗与海上犯罪的义务。
抽象地谈论“自由”,不过是在强调“权利”,但权利从来都伴随着义务。义务不明确,权利也就无从谈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约都在明确不同海域的航行义务,似乎是在限制航行的权利,其实是在明确权利的边界范围,界定“航行自由”的内涵。从总体上看,根据《公约》对不同海域的划分,航行自由的权利从公海到领海呈递减之势,义务的范围随之增多。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对航行自由的限制性国际立法内容越来越多,但实际上保护性立法规定也在加强。例如,要求沿海国妥为公布关于无害通过的法律和规章、[1]《公约》第21条3款。公布其所知的在其领海内危及航行安全的情况、[2]《公约》第24条2款。在专属经济区内建设人工岛屿并在其周围设置安全地带时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航行安全等。[3]《公约》第60条4款。
(三)从强调航行不受干涉转变为规范航行权与诸多因素的协调
《公海公约》及此前的习惯国际法主要强调航行的“自由”不受沿海国和其他国家的干涉与阻碍。此后,诸多新的形势和因素对航行产生了影响,存在一定的内在价值取向冲突。这主要表现为航行权与经济资源开发权之间的冲突、航行权与沿海国安全利益之间的冲突、航行权与海洋环境保护利益之间的冲突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这些可能存在冲突的利益进行了协调和规范。
例如,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需要制定避免船舶碰撞的国际立法;“自由”不应包含国际公认的海上违法犯罪活动,如海盗犯罪、海上恐怖活动等;[4]《公约》第99、100条,另见国际海事组织1974年通过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2002年通过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附则修正案等。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建设人工岛屿或规定渔区可能会与航行安全发生冲突,需要在航行船舶和沿海国商业利用开发之间取得平衡;[5]《公约》第60、62条。航行事故可能造成船舶燃油和所载原油的泄露,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造成损害,需要对船舶安全航行提出更高要求等。[6]例如,1954年《国际防止海洋油污染公约》、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2001年《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国际公约》、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2009年《国际安全与无害环境拆船公约》等。
航行自由的主体也不再笼统包含一切性质的船舶。虽然军事船舶和政府公务船舶仍然享有管辖豁免,但《公约》在许多条文中都单列了军舰和其他军事船舶、政府公务船舶在航行中应尽的义务。例如,一国军舰在无害通过另一国领海时,不得对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得以任何种类的武器进行任何操练或演习,不得出于任何目的搜集情报使沿海国的防务或安全受损害;[1]《公约》第19条2款。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须在海面上航行并展示其旗帜。[2]《公约》第20条。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一国领海之外的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军事船舶同样可以展示武力,对沿海国的主权安全产生威胁。因此,围绕军事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与活动是否享有完全的自由,海洋强权国家与沿海国之间存在争议,而《公约》对此规定甚少,这成为今后有关航行自由国际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热点之一。[3]外国军事船舶是否可以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情报收集、海洋测量等活动在《公约》中并无明确规定。各国学者分别从习惯国际法和海洋法公约的宗旨等不同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四)从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转向博弈与共同治理并存
虽然国家间利益博弈仍然是围绕航行自由国际规制的主要因素,但基于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国际社会也开始合作立法,谋求海洋航行自由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海洋环境保护开始成为规范航行的重要因素,被《公约》提高到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迅速成为国际海洋法的一条基本原则。[4]《公约》第193条。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存在于各种不同法律地位的水域类型中,即使在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公海上,国际立法也对环境保护进行了规范。这些法律和规章对航行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5]Jeanine B.Womble,“Freedom of Navig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Compulsory Pilotage in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Naval Law Review,Vol.61,2012,p.134-135.相对于气候变化议题上各国就减排义务展开的激烈博弈,在海洋环境保护与航行的问题上,各国开展合作、共同治理的色彩更浓厚一些。
在谁也无法完全控制和占有海洋的时代,航行自由的范围和界限主要表现为海洋强国与沿海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公海基本处于无法律规范调节的“自由”状态。随着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严格意义上的公海范围大幅度缩小。全球气候变化与海洋环境灾难要求各国采取协调行动,而国际海上恐怖主义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更要求国际社会统一管理海上航行。“海洋共同治理”的理念成为新的驱动力,促进航行活动国际立法的发展。[1]William T.Burke,“State Practice,New Ocean Uses,and Ocean Governance under UNCLOS,”in Thomas A.Mensah,Ocean Governance: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for the 21st Century,1996,p.219.
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海洋国际立法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不分国界的组织通过呼吁和行动,把民间的呼声和舆论转化为国际社会共同治理的决心。有关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海洋守护者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限制向海洋倾倒垃圾、规范核动力船舶的使用与限制、为减少船舶碳排放而提高船舶制造与航行标准等方面,都能看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子。这些非政府组织常常呼吁各国在国际立法中开展合作,抑制国家间利益冲突的烈度。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法律争议
尽管以《公约》为代表的海上航行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现有国际立法在规范航行自由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或者说,《公约》在协调航行权与其他利益冲突方面还存在模糊区域。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属经济区内资源的利用开发与航行自由
鉴于《公约》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自然资源开发拥有主权性权利,[2]《公约》第56条1款(a)项。当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开发风力发电、海底石油资源,或设置渔业圈养设施时,有关设施设备可能对现有航道及其安全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当渔业养殖场区域与航道交叉重叠时,应当通过什么措施避免航行安全事故发生?又如,在海上石油开采区与航道和渔区交叉重叠时,应如何划定石油设施安全区和航道、渔区的界限?[3]Geir Ulfstein,“The Conflict between Petroleum Production,Navigation and Fisheries in International Law,”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19,1988,pp.229-232.
虽然《公约》要求沿海国在行使权利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应以符合本公约规定的方式行事”,[1]《公约》第56条2款。但这只是原则性规定。《公约》本身并未具体规定“适当顾及其他国家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方式和具体程序。例如,沿海国如何向国际社会提前通报航道附近的渔业养殖场具体区域?沿海国在采取上述方式开发专属经济区的自然资源时不需要事先取得外国同意,也不需要向国际海事组织报备。沿海国的开发利用权与他国船舶的航行自由权在现实中存在冲突的可能性。
(二)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与航行自由
围绕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自由,同样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方面,海洋强国认为,军事船舶的航行包括在航行自由之中,传统习惯国际法并没有禁止军事船舶在公海上的活动内容与范围,而且《公约》将“公海航行自由”延伸到专属经济区,且无具体条文限制有关活动,因此外国军事船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航行、开展军事演习、收集情报和军事测量等都是合法的。[2]John C.Meyer,“The Impact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n Naval Operations,”Naval Law Review,Vol.40,1992,p.241;Stephen Rose,“Naval Activity in the EEZ Troubled Waters Ahead?”Naval Law Review,Vol.39,1990,pp.68-72.另一方面,沿海国基于国家主权与安全考虑,依据《公约》第88条认为,外国军事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不得违反和平的目的,而军事演习、收集情报和军事测量等与和平利用海洋无关,应该事先取得沿海国同意。[3]Zedalis,“Military Uses of Ocean Space and the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An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Peacetime ASW,”San Diego Law Review,Vol.16,No.3,1975,p.625;Stuart Kaye,“Freedom of Navigation,Surveillance and Security: Legal Issues Surrounding the Collection of Intelligence from beyond the Littoral,”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4,No.93,2005,pp.100-102.
这种分歧和争论也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海洋强国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在领海之外对一国的独立与安全构成威胁,例如卫星侦察、中远程导弹、远程大炮等军事技术已使传统的领海屏障无法起到保护国家安全作用,沿海国不得不考虑12海里领海之外的国家安全利益。《公约》将公海航行自由延伸到专属经济区的规定无法解决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以2014年为例,美国打着“维护航行自由”的旗号挑战了中国、印度、厄瓜多尔等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测量和侦察活动。[1]U.S.Department of Defense,“Freedom of Navigation: FY 2014 Operational Assertions,”March 23,2015,http://policy.defense.gov/OUSDPOffices/FON.aspx.(上网时间:2015年11月15日)中国、印度等国提出了抗议。
事实上,由于《公约》承认沿海国享有的各项合法利益,同时也确认了其他国家航行自由的权利,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平衡点,各方常常向利己的一面解读《公约》。不过,这或许正是《公约》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照顾到了各国的关切,从国际法上肯定各项权益。但是,这种做法也留下了模糊空间,导致沿海国国防安全利益与他国航行利益的冲突。[2]袁发强:“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9-200页。
(三)海洋环境保护与航行自由
同样基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沿海国可能会为保护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生态环境而试图限制船舶航道、要求强制引航、[3]Daniel Bodansky,“Protect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Vessel-Source Pollution: UNCLOS III and Beyond,”Ecology Law Quarterly,Vol.18,No.4,1991,p.738.要求提高航行船舶的安全技术标准和污染排放标准[4]Chelsea Purvis,“Coastal State Jurisdiction under UNCLOS: The Shen Neng 1 Grounding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6,No.1,2011,p.207等。例如,澳大利亚为了保护大堡礁的生态环境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虽然不具有歧视性,但过高的船舶技术标准可能会限制发展中国家船舶的通过,导致其他国家对航行自由的担忧,引起了国际海事组织的关注。[5]Julian Roberts,“Compulsory Pilotage in International Straits: The Torres Strait PSSA Proposal,”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37,No.1,2006,p.93.航行自由与海洋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遭遇海难事故时,船舶可以驶往就近海域避难,这在习惯国际法中被视为一项合法的权利。然而,生态环境保护也使得在发生海难事故时,相关国家可能会拒绝因遭遇事故而存在原油或燃油泄漏污染的船舶进入本国港口、港湾或专属经济区内避难,[6]Christopher F.Murray,“Any Port in a Storm? The Right of Entry for Reasons of Force Majeure or Distress in the Wake of the Erika and the Castor,”Ohio State Law Journal,Vol.63,No.5,2002,p.1467.避难权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冲突。例如1999年和2002 年,公海遇难油轮“Erika”号和“Prestige”号都因未被准许进入沿岸水域避难而最终沉没,导致国际独立油船船东协会(INTERTANKO)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呼吁达成全球性协议,明确遭难船舶应该被提供安全的避难所。另一方面,沿海国则认为,在不涉及海上人命安全的情况下,一国不可能以严重牺牲本国沿海和港口环境为代价准许遇难油轮进入本国管辖范围。
一些国家出于对核动力船舶安全性的怀疑,拒绝该类型船舶进入本国一般商业港口,或者限制核动力船舶通过某段航道。[1]Steven D.Poulin,“Is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aching Critical Mass for Nuclear Cargoes?”Federal Lawyer,Vol.42,No.16,1995,pp.17-18.船舶所有国则依据航行自由,主张在沿海国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根据《公约》第22和23条的规定,沿海国可以要求外国油轮、核动力船舶、运输原油和核材料的船舶在通过沿海国海域时,只能在规定的航道中航行。但在专属经济区,《公约》并没有赋予沿海国拒绝和阻止上述类型船舶通过的权利。《公约》仅要求沿海国在行使管辖权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以符合本公约规定的方式行事”。[2]《公约》第56条2款。这样就会产生沿海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与其他国家航行利益的冲突。
(四)人类集体安全与航行自由
从习惯国际法看,航行船舶在一国领海外航行,只受船旗国法律管辖,没有义务向船旗国以外的国家报告自己的位置、船员信息与基本货物信息。然而,不少国家实行开放船舶登记制度,“方便旗”船舶能够为海上不法活动提供掩护。在航行自由、船舶只受船旗国法律管辖的借口下,走私毒品、军火、非法贩运偷渡移民等犯罪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管制。[3]Michael A.Becker,“The Shifting Public Order of the Oceans: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Interdiction of Ships at Sea,”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6,No.1,2005,p.131.
海上犯罪与海上恐怖活动的影响不再局限于个别地区或国家。例如,索马里海盗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多国派遣军舰参与该地区海上安全维护活动,但目前各国以保护本国商船为主,还没有形成集体机制。《公约》本身并没有赋予他国进入一国领海打击海盗的权利,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索马里政府公开表态同意,各国才得以在索马里海域开展行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情况同样猖獗。周边国家虽然自身能力有限,却又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名义不同意国际社会直接介入。在该地区,保护航行自由与维护国家主权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美国出于自身反恐的需要,不仅加强了对沿海航运船舶的监测,而且要求在12海里领海外驶向美国港口的船只提供海域位置信息。[1]2005年,美国公布了《海洋安全国家战略》,主张“阻止任何可能威胁美国或其航运海域的人或物是一项必要的安全措施”。参见“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September 2005,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homeland/maritime-security.html.(上网时间:2015年9月27日)美国还与国际海事组织加强合作,试图推广使用船载远程识别和跟踪(LRIT)系统。澳大利亚似乎走得更远。2005年,澳大利亚推出了海事识别制度(Australian Maritime Identification System,简称AMIS),要求驶往澳大利亚港口的船舶在距离该国海岸线1000海里处或48小时航程时主动提供船籍、船员、货物、停靠港口等信息;经过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或其领海的船舶需在距离该国海岸线500海里或24小时航程处自愿提供相关航程信息以备查验。[2]王海波:“澳大利亚海事识别制度:法律视角及其前景”,《学术界》2009年第1期,第292-293页。这种要求远远超过了《公约》的规定,“公海自由”正被以“反恐”与“国家安全”为由而颁布的国内法侵蚀。
一些国家担心,这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成为大国干涉或阻止个别国家海上贸易的借口。[3]Jason M.Krajewski,“Out of Sight,Out of Mind? A Case for Long Range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of Vessels on the High Seas,”Naval Law Review,Vol.56,2008,p.219.它们质疑,国际海事组织是否有权发布强制性规定,要求所有商船配备识别设备?这是否会危及船旗国的安全利益?对于不配合的船舶,一国是否可以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内以此为借口随意行使登临检查权?集体安全保障应当如何行使才不会被海洋强国用作阻碍他国船舶航行自由的工具?这些问题都是《公约》没有明文规定的,存在一国安全利益与他国安全利益的冲突,以及一国安全利益与他国航行自由利益的冲突。
(五)沿海国管辖权与北极水域的航行自由
全球变暖的一个结果是,靠近俄罗斯和加拿大领海附近的北极海域正在成为一条“北方航线”,具有现实的航行价值。通过北极航道进行亚洲和欧洲之间、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商业运输,不仅可以缩短几千海里的路程,更可以节省燃油。不过,受地理条件限制,可航水域常常过于靠近北极附近的国家领土,甚至在部分地区需要通过领海。[1]R.R.Roth,“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ver Arctic Waters,”Alberta Law Review,Vol.28,No.4,1990,p.865.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国可能基于扩张的主权要求而对商业航行施以不合理的限制,并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禁止外国军事船舶的通过。[2]R.R.Churchill and A.V.Lowe,The Law of the Sea,2nd ed.,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p.83.另外,外国油轮和核动力商船的航行也引起沿海国对本国海洋环境的担忧,沿海国可能会基于现实的环保利益而拒绝或施加高标准的航行限制,[3]例如,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70年通过了《北极水域污染防治法案》(Arctic Waters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简称AWPPA)。根据该法案,加拿大政府建立了航运安全区(shipping safety control zones)。该法案的第12条规定了可航行于北极水域的船舶标准,涉及船体和油箱的设计和建造、导航设备的建造标准、船员资格条件等。参见Schedules V,VI and VII,Arctic Shipping 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C.R.C.,c.353.甚至要求强制引航。[4]20世纪80年代,苏联曾颁布法律要求通过其北极水域的船舶必须接受强制引航。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就澳大利亚大堡礁海域的环境保护设立了自愿引航制度,但沿海国是否有权要求强制引航仍然是一个争论话题。
维护北极航道的自由航行对于非北极周边国家同样具有重要的商业和国家安全利益。从北极特殊的航行条件看,北极周边国家当然具有比一般沿海国更强烈的管辖利益,也有更实际的控制权,《公约》的规定恐难以直接推广到北极地区。北极地区的航行或许需要制定一套特别的航行规则,在沿海国利益和航行国利益之间重新平衡。[5]这并非是要抛弃《公约》,而是要以《公约》的法律制度为基础,结合北极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特征,以及北极沿海国与其他航运国利益的平衡,设计出有别于一般海洋航道的航行规则和条件。事实上,国际海事组织也正在加紧制定《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安全规则》。
三、中国的政策选择
过去,中国维护海洋主权能力有限,且经济发展重点在陆地,因此在参与国际海洋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利益和视角的焦点放在领海、专属经济区的权益保障方面。与上述背景相适应,中国有关海洋航行的法制规范工作主要集中在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内,法学界的研究重点也放在避免外国干涉的问题上,从国际海洋法制中寻找依据以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随着中国实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对海洋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不论是远洋贸易和能源通道都亟需获得切实保障。与此同时,中国近海防御能力得到很大改观。从发展的眼光看,对待航行自由问题,中国应当更具有前瞻性,尤其要注意保持维护海洋权益和保护海外利益的有机统一。
(一)领土主权维护与航行自由
近年来,美国打着“维护航行自由”的旗号,插手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南海岛礁主权争端。2015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多次派遣军用舰机硬闯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空域,对中国岛礁及岛上人员安全构成威胁。其实,美国政府所主张的“航行自由”不过是美国军用舰机在他国近海肆意收集情报、以军事演习恐吓他国的自由,[1]曲升:“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初探”,《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4页。与国际法中的航行自由制度不存在内在联系。事实上,民用船舶在南海地区的航行活动不会受到中国限制,至于在中国管辖海域非法捕捞、开发利用资源的行为则另当别论。即使是外国军事船舶,只要遵守中国相关法律,中国也并未阻止其正常通行。目前,针对《公约》所规定的领海无害通过权,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主张需要事先征得沿海国同意。因此,在维护领土主权与安全利益问题上,一方面应毫不犹豫坚守底线,反击任何打着“航行自由”幌子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之实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注意在维护领土主权过程中,切实维护外国船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航行自由,避免不合规范地扩大海域管辖权影响正常的航行自由。
(二)重新审视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法律规制
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在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享有主权权利。因此,中国应加大这方面的国内立法活动,这既能充分体现主权,又能为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创造有利的法制环境,促进对专属经济区的充分利用。同时也应看到,《公约》对专属经济区的军事船舶航行并无具体限制性规定,过于强调禁止外国军事船舶不得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军事测量和情报收集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1]关于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能否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军事测量和情报收集活动,中国过去的研究一概主张这不符合《公约》有关“和平利用海洋”的宗旨和目的。随着中国军舰开始“走出去”,特别是在2014年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中国除参与军演外,还派遣了军事船舶在夏威夷演习海域附近观测,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中国海外航行安全的需要。因此,中国不必笼统地反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军事活动,而应该以外国军事船舶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是否危害中国国防安全为考量因素,采取恰当、与外国军事活动危害程度成比例的警告和阻止措施,保卫国家安全。
从根本上讲,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维护要靠国家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他国顾及中国军事实力的对抗而减少或放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侦察和军事测量活动。以美国在中国南海海域的军事侦察和测量活动为例,美国在拥有卫星高空侦察技术的情况下,在南海海域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有些是为了获得军事情报,有些则是为了挑衅中国反对外国可以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军事侦察和测量活动的主张。因此,对两者有必要区别对待。借口“航行自由”的挑衅活动,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并非只针对中国,过去也经常挑衅与中国主张相似的印度和其他国家。[2]2000年,美国和英国军舰在印度专属经济区从事军事测量活动遭到印度政府外交抗议。不过,为配合“重返亚洲”战略,美国海空军明显加大了在南海的现实军事存在。
当外国军事船舶的挑衅性侦察活动有害于中国国防安全时,中国军事力量当然有权采取阻止措施。[3]邹立刚:“论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规制权”,《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第53-54页。这也是《公约》和一般习惯国际法所允许或无明文禁止的。例如,美国军事船舶和飞机在中国海南潜艇基地附近进行侦察和情报收集活动危害到中国国防军事安全,中国采取阻止措施是符合国际法的,因为这种活动是危害沿海国安全和利益的行动,也是不符合和平目的的海洋用途。同时,中国还应加强对阻止行动和措施的法律问题研究。[4]不应当简单地将阻止措施和行动归类到国际法上的“自卫”,然后以自卫需以面临武力威胁为前提条件而自我限制。这是中国国际法学者应当特别注意避免的。
随着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洋实力的增强,军事船舶也需要加大远距离的航行活动。中国海军已经开始出现在阿留申群岛、夏威夷、日本宫古海峡等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或外国专属经济区。为了军舰自身安全航行需要,中国军事船舶也需要收集水下航道信息。这并没有构成对沿海国的军事威胁,也未遭到外国的反对和抗议。[1]2014年8月,中国军舰在美国夏威夷附近航行时,美国国防部就认为中国的航行活动符合国际法。另外,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海域附近保护本国商船的行动,也牵涉到外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和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航行通过问题。应该看到的是,外国军事船舶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并不总是危害沿海国国防安全。这取决于军事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军事活动的内容等多方面因素。

中美海军舰艇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练
(三)重视对和平时期海上军事活动的国际法保障研究
要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就要放弃部分传统保守的国际法认识。虽然《公约》提出了将海洋用于和平的目的,但这并不完全排斥海上军事活动。[2]袁发强:“对航行自由,中国可持更开放立场”,《社会观察》2015年第9期,第13页。客观上看,海上军事活动也会增强海上和平,关键在于中国自己要加强利用海上军事力量参与维护海洋和平的行动,例如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的检查。为此,中国应加强对和平时期海上军事活动的法律问题研究,参照国外军事活动的实践经验,为本国军事活动提供规范性意见。
例如,对于美国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应当加强研究在联合国体制内实现防扩散安全的可能性,坚决反对可能违反《公约》的单边强制措施;坚持国际社会合作与共同行动原则,倡导建立联合国体系内的合作机构;实现情报共享和行动授权机制,反对滥用登临检查权和打击措施,以及妨碍自由航行和贸易的不当措施和行为。[1]2004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对防扩散决议投了赞成票。围绕美国的“防扩散安全倡议”,中国国内存在不同的学术主张。有的认为不宜加入,有的认为应当有条件加入。参见顾国良:“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评析”,《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第38-43页;余民才:“对我国关于《防扩散安全倡议》立场之重新审视”,《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第52-56页。
(四)积极主张北极地区的航行自由
中国虽然对北极地区无主权主张,但北极航道对于中国未来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即将“极地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32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增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北极地区对于中国不仅具有安全上的利益,也具有重要的交通通道利益。[3]王丹、李振福、张燕:“北方航道开通对我国航运业发展的影响”,《中国海事》2014年第1期,第141-150页;邹支强:“北极航道对全球能源贸易格局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75-77页。在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之后,中国应当利用这个平台提出符合本国对外政策的法律立场,积极参与北极航道有关航行法律制度的立法活动。
中国应依《公约》规定,否定个别国家过分宽泛地主张相关海域的管辖权,提倡航行自由。这涉及到北极沿海国家领海基线的划法、内水的定位、有关岛屿与大陆之间的海峡是否构成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等。[4]贾宇:“北极地区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探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页。由于不同法律性质的水域决定了航行自由的权利范围,因此这些问题与国际社会的航行利益密切相关。
同时,在北极地区,应当主张借鉴南极地区保护的经验和《南极条约》中的积极成果,对待北极地区的军事航行主张有别于一般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规则,以回应北极地区国家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担忧。
此外,要积极倡导对普通商船航行自由的支持,避免沿海国以安全和环保为借口的过分控制。[1]如前所述,加拿大和原苏联都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出台了有关北极地区航行的一些限制性条件。虽然《公约》要求沿海国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得歧视,但这些限制性条件中所隐含的技术性要求实质上可能会妨碍北极航线的商业航行。另外,由于北极地区航道的气候条件限制,部分航段可能需要穿越这些北极地区国家的领海,为此有必要坚持和捍卫无害通过的航行权。过高的船舶建造技术标准和强制引航可能会形成技术壁垒,妨碍一般国家商船参与北极航行。
(五)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环境保护措施对航行自由的影响
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气候变化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开始寻求降低船舶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2]2011年,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了以强制性技术和业务措施减少航运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法案,该法案适用于所有总吨位在400吨及以上的船舶。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新船能效设计指数(EEDI)成为硬性规定,对新船设计提出了更高的排放要求。但是,西方一些在船舶建造技术方面占优势的国家以减少船舶燃油排放污染为借口,企图单方面限制过往船舶经停该国港口,对航行自由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某些国家单方面限制进出港口的船舶类型,以是否达到标准作为允许进出港口的条件,严重妨碍了中国商船的经营活动,构成妨碍自由竞争的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对此,中国应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反对单方面限制航行自由的国内和区域立法,主张通过有关国际组织,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制定恰当的排放标准。[3]中国、沙特阿拉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对2011年国际海事组织关于新船能源效率的法案投了反对票,要求给予发展中国家6年的宽限期。参见“IMO通过新船能源效率指标,减低船舶碳排放”,2011年7月18日,http://www.100allin.com/news/1/2/51114.html。(上网时间:2015年8月3日)
同时,随着海洋生物资源和多样性保护的发展,国际社会出现了划定生态保护区的呼声。[4]例如,澳大利亚要求将大堡礁保护区延伸到珊瑚海海域。这种呼声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如同上述限制船舶污染的情形一样,不恰当和不合理的海洋生物保护区,以及对船舶类型和航行条件的不合理限制,也会对中国商业航行造成不利影响。如何消除不利影响,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需要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立法活动,反对沿海国采取单方面措施妨碍和限制航行自由。
四、结语
航行自由制度在成为一个国际成文立法的过程中,已经基本建立了框架体系,但航行自由与其他国际法制度之间的协调与衔接却未必完全解决。同时,随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地球村”,新发生的问题也驱使各国在维护航行自由方面表现出多元的价值追求和利益主张。这些价值追求和利益主张的交互作用又推动海上航行法律制度不断变化和发展。
航行自由法律制度的主体、范围和权利义务内容都已经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主体上,普通商船与军事船舶、公务船舶在“自由”的内涵方面差异越来越大;范围上,“自由”的地理范围随着不同海域法律制度的形成而逐渐减小;内容上,沿海国对周边海域的管理权限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共同规范航行权利义务的内容越来越多。航行自由制度正显现出体系化特征,成为海洋法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同时,航行自由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国家主权与安全、海洋环境保护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协调将成为今后相关国际立法的重心。区分普通商业航行与军事活动分别明确立法将是未来国际立法的任务和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实力增强,国家利益的重心不再局限于以陆地为中心的近海。中国对待航行自由法律制度的态度也应当有所转变,因应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格局的变化而适时跟进。中国应综合考虑国家领土安全、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因素,建立与国家整体安全观相适应的航行自由法律立场,[1]袁发强:“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5页。丰富航行自由制度的内容,明确相应的责任义务。
【完稿日期:2016-2-17】
【责任编辑:吴劭杰】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6)2期0082-1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F935
〔作者简介〕袁发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