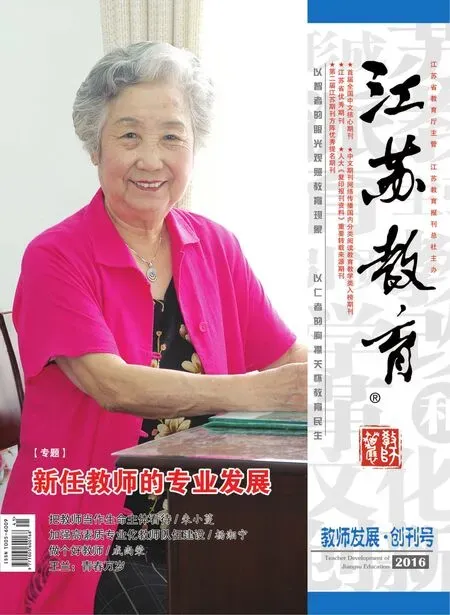做一个有点“争议”的教师
冯卫东
·冯卫东专栏:一线教师如何做教科研·
做一个有点“争议”的教师
冯卫东
做一个有点“争议”的教师,并不是在人品和师德上引起争议,而是在教师的教育理解、教学个性和创新举措等专业领域上。从个人的经历来看,教师的确需要时常提醒自己走出平庸,不惧“争议”。不可将“淡泊明志”理解为惰于作为、不思进取,应理解为建功立业却不汲汲于名利;不必主动趋向于“争议”,但也不惮于招致他人“争议”。优秀教师的教学主张通常是有“争议”的,恰恰是这样的“争议”才能有发展。
教师发展;职业情怀;学科专业
《江苏教育》将推出“教师发展版”,邀我就“一线教师如何做教科研”写一年的专栏文章。这里是开篇之作,思来想去,酌定这个标题。它或许会引发一点小小“争议”。倘能如此,则写有所值,因为,文字的价值常常在于赢得关注。看似跑题,其实不然,至少不全是题外话:教科研是一种“技术活儿”,谈“技术”之前谈谈与此有关的心志、心态,就是动力机制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技术”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与通道。
一
“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人生一辈子,倘若为人处事从无“争议”,该多么荣耀与幸福。然而,如柏拉图所说“美是难的”,毫无争议的人生也是“难的”,即便是“桃源中人”也不行,因为那里已是一处群居地,有人群的地方必然会有蜚短流长。我曾说过我的父母是目不识丁、素面朝天、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现代闰土”,也许只有这类人不会引起“争议”,然而仔细想却不然,邻里之间也会有罅隙,几个子女对他们有些做法亦有“不同看法”……看来,人世原本即为“是非之地”,社会注定就是“争议之源”。
我曾立志做一个没有争议的好人。初为人师,便写下“淡泊明志”四个大字作为座右铭,不愿执着追求任何高远的目标,常常“标榜”自己是一个“散淡人”,愿以一种低至尘埃的卑微心态做点小事、实事,平平淡淡过一生;宁可放弃一些可以提升与发展自己的机会,只为大家一团和气;有些怠惰,不够勤勉,更遑论刻苦;满足于按部就班晋级升职,从未想过先人一步,攀高履新。还记得,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做课题,我无动于衷。潜意识里觉得凭自己慢慢积累下来的经验就可以把教学做得差强人意,何必做虚头巴脑、于事无补的研究;还记得,越来越多的同龄人开始谋划自己的事业发展前景,有几个同事更是冲击着“骨干——带头人——特级”的“三级跳”。我竟在他们侧旁酣睡不醒,年届不惑几乎未曾获得一点专业荣誉……我就像“温水煮蛙”,优哉游哉地过惬意日子,不曾记得有哪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必须奋然跃起,迎头赶上。
这样的心境、性格和行事风格应该不会惹人注意,引人争议吧?的确,我一度以“好人”之名“著称”于不大的交往圈中,以至一位老资格的同事人前人后夸我人好。“口碑”成了我的人生鹄的,也是我仅存的一点“骄傲资本”。可后来一件事惊醒我的“好人梦”:我调离该校,学科同仁为我饯行,唯独这位老教师没来参加,席间有人告诉我,他很生我的气,因为上学期我申报县骨干教师,他认为我不该“争”这份荣誉,甚至给我“不学无术”的评价。我真的懵了:今后,我还要执意去做“有口皆碑”的“好人”吗?
二
当然,我还不至于让自己的品格、风格等出现“断崖式陡变”,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人格基因”很难改变,即便过了知命之年,乃至今后更长一段人生,“善”的道德根基都“厚植”我心,我自然不会不管“闾阎话短长”,“义无反顾”地去做一个“有争议的人”。
我只是渐渐变得不刻意追求做人人心目中、口口相传的“好人”,不刻意弭平他人善心或恶意的“争议”。话虽如此,把专业上长期碌碌无为都归咎于怕有“争议”的心理,也有失公允。不过,大致还是可以厘清其间的一些逻辑关联:怕有“争议”,甘愿平淡,堕入平庸,少有作为……法国著名牧师内德·兰塞姆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能成为伟人。”“伟人”做不了,但倘若心里装入一点“浩然连广宇”的“心事”,那么,自我教育的人生必定变得充实丰盈,甚至有点辉煌。这其实何止是一己幸事,最受益的当是我的学生们。
三
还好,我一直喜欢写作,素以“文人”暗中自许,不时鼓捣出一些东西来,是这些文字无形中为我今后的职场行走准备了一些必要的“盘缠”,为专业生活的“崛起”打下一点基础,挽回一点尊严。
2004年,我调至南通市教科所,成为一名专职研究人员,“上车伊始”便产生强烈的“本领恐慌”,心知“再也不能这样活”,新岗位、新角色、新工作、新要求“倒逼”我“绝地反击”。这是一方“人才高地”,不进则退,自然会失去话语权。人到中年在许多人开始萌生退意时,我却鼓满生命风帆,向着自己其实也不甚明晰的前方进发。这些年来,我读了五六百本书,啃了很多艰深的专业理论;作为课题主持人,完成省级和国家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以我为主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区域微型课题研究推进“运动”,在省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先是四面出击,边学边研,就各种感兴趣的现实问题进行散状思考与探究,后来则聚焦于若干“城墙口”,攻坚克难,取得一些成果;还慢慢建构、渐渐悟得、最终总结出一些独特而又适宜于一线教师的草根研究方法,使他们学以致用;让我倍感个人生命价值的是,“未有金针亦度人”,带出一支富有生机和创造活力的优秀教师队伍,其中以“倾听教育”课题为平台,“催生”四位特级教师、一位省名师、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我不断生成、升华与优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策略等,深深影响了他们,又通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儿童的生活及生命状态;我以坚实的步履朝着“成事成人”的纵深处走去,先后获市学科带头人、市科技拔尖人才、省“333”人才培养工程首批科学技术带头人、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等头衔,还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获省第三、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常说自己 “小器晚成”,但在这十二年四千多个日子里,“浴火重生”,少有人能赶上我的“加速度”,赶上我的“续航力”。我提出教师“终身成长”命题,著名学者肖川专门发文呼应以支持我的观点,我愿意成为这一命题的切实践行者,实现我最向往的愿景——当我满鬓银丝、步履蹒跚时,还能听到自我生命清脆的拔节声。
比起“淡泊明志”的青年时代,在已然消逝的那段中年时光中,我渐渐成为一个有点“争议”的人:有人赞赏我后来居上,在短短几年里,发愤努力,实现由一名普通教师向一位“草根教科研专家”的“蜕变”,并通过引领更多教师为地方教育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有人不满我俨然专家;有人在我评“正高”之际以匿名信列数我的若干“问题”;有人则挺我助我,使我获得“评特”所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票(年度评优)……我坦言远没能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化境”,但也愈发清醒:其一,有人非议,说明自己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特别是书生气重,处事有不妥,处世须改善;其二,其间一些“木秀于林”的因素,倘要不让“风摧”,只需也只能“放低身段”,混迹庸常。平心而论,我非顽劣之人,有错愿改,但倘若确实有人不无嫉恨,我不会因为这些而改变自己矢志投身教科研的“初心”,我会努力变得更为优秀。
“优秀是卓越的敌人”,我自知能走向卓越殊属不易,我能做的是,让它们“化敌为友”,让自己走在通往卓越的路上。
四
“淡泊明志”之人常无功利之心。无心功利好不好,这要两说,倘若理解为惰于作为,不图上进,自然不好;而如果解读为建功立业却不汲汲于名利,那应该予以无上礼赞。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翻译家杨绛将英国诗人兰德的句子作为暮年心声,我们很难找到与此媲美的“淡泊”范例,而往深处想,也只有杨绛和像她一样的人才有资格“淡泊明志”,因为她有斐然的成就,也因为她“走在人生的边上”;易言之,年纪轻轻、了无成绩者,没有理由奢谈“淡泊”,犹如有足够资本的人才有底气藐视金钱,视为身外之物。
在一定程度上,淡泊是平庸的代名词。我曾对“拒绝平庸”的高考作文题不以为然:罗素说,“参差多变乃幸福之源”,应该允许一部分人较为平庸,不能剥夺他的“平庸权”。但以育人为己任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却要努力“拒绝平庸”:作为个人,你似乎有平庸的权利;但你的平庸几乎必然贻误学生,耽搁他们的前途,从而“制造”出更多平庸者,这却不是你的权利,它甚至还是另一种“平庸的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后来成为一个著名概念。她以纳粹分子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表现为不去思考,任由他人的权力或权威主宰自我的思想)。这样说或许会被人们讥为高调,但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注定有相当多教育者是平庸之辈,一方面却要人们追求高尚,向往卓越——教育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收录“平庸”的词条,我们又岂能在事业之翼尚未完全展开之际,就让平庸的钝剑斫断双翼?
教师确有必要时时提醒自己走出平庸的沼泽地,进而优秀起来。这时你自然不必主动趋向于“争议”,但也不要惮于言行不甚“合群”招致他人“争议”。譬如,在读书空气非常稀薄的当下,众人快乐刷屏,你却捧出一本厚书,旁若无人地啃将起来;譬如,在课堂变革依然春风难度的今天,众人陈陈相因,你却标新立异,尝试创新教学方法;再譬如,在凭经验行事已成常态的“生境”,众人“跟着感觉走”,你却深入研究,透过现象悟本质……长此以往,你将不再平庸,而同时,必将收获更多关注、谈论抑或“争议”。较为豁达的做法是,悄悄拎起,轻轻放下,这时你会有一种轻舞飞扬的感觉,它也是一份有所超越的享受。
五
我没有进行实证,但可以凭经验做出一个“差不离”的判定,相比于不研究或少研究的教师,惯于研究者或研究型教师会有更多的“争议率”。我想原因可能有几个:一是唯研究者能优异,而在世俗社会里,优异者引发议论的可能性更大,子贡曰“君子之过也……人皆见之”,见之而议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二是研究者常有异思,常走新路,虽然现在的中国不再是鲁迅笔下搬动一张桌子也会弄得头破血流的社会,但对于异思和新路,评头论足的人总不会少;其三(这与第二点也有关联),研究者头脑中常会有一种“片面的深刻”,它区别于“全面的肤浅”,彰显出不“骑墙”、不“和稀泥”的风骨与锋芒,往往会打破原有人际、观点等的静态平衡,有时还会伤及他人——不招谁惹谁时尚且有“争议”,又何况现在?臧否不一、人言人殊或许是这些“片面的深刻”者必然要面对的局面。
优秀教师的教学主张恰恰是 “片面的深刻”之“集大成者”。我不太主张大家都弄出“某某语文”“某某数学”之类“树旗式”的教学主张,却主张“主张”是要有的。名师黄厚江在《教学主张的来与去》一文中说,“万金油式的主张,其实就是没有主张”,意思是,舍“全面的肤浅”而取“片面的深刻”。它们自然不应是优秀教师“拍脑而出”的,而是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所积淀的智慧逻辑发展之必然。倘若如此,即便也以“树旗式”语言加以概括和呈现,亦未尝不可,因为名号只有形式的意义,实际内容才有本质的意蕴和生命的价值。很巧的是,我所认识的祝禧、张齐华两位名师,都是我们南通海门人,他们不约而同先后提出“文化语文”“文化数学”的教学主张。实话说,他们的主张是有“争议”的,但在别人的“争议”声中,他们却把“文化语文”“文化数学”做得扎扎实实,风生水起。这也应了我的一句大白话:行不行取决于“行不行”(即做不做,怎样做)。“争议”不同于掌声,更有别于鲜花;掌声与鲜花都是“人赋”与外在的,而成长和收获才是师生共享和“自在”的,相形之下,后者更为重要。
六
有“争议”才有意义,有“争议”才能发展,倘若不愿与“争议”相向而行,也没有必要不顾实际情况远它而去。做一个有点“争议”的教师。当然,“争议点”理应不在人品和师德中,更不在核心价值处,而在教育理解、教学个性和创新举措等之上。这是一个“规则”,恪守了这个“规则”,便可尽享“规则之内的自由”,也可以在别人的“争议”声中,“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际云卷云舒”。
G451
B
1005-6009(2016)41-0049-03
冯卫东,江苏省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通,226001)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