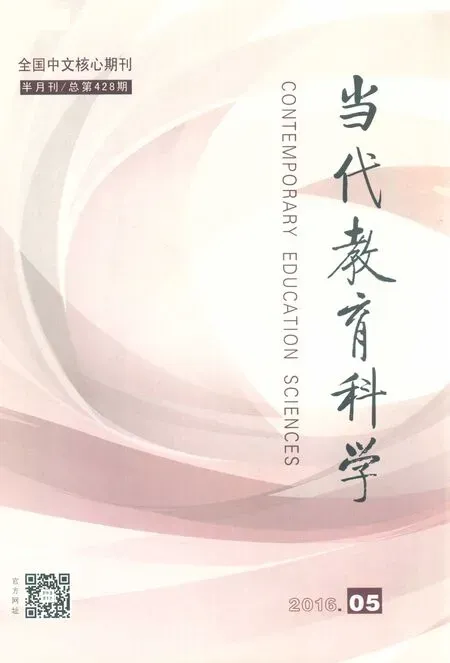从抵制到赋权:论西方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吴文涛 张舒予
从抵制到赋权:论西方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吴文涛 张舒予
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教育的组织者基于自身需要和对媒介价值的认识,在开展教育活动时的价值倾向。分析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时,应把握其内涵的三个基本要义:教育组织者的自身需要;教育组织者对于媒介价值的认识;开展教育活动时组织者的行为倾向。西方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印刷时代、电子时代、数字时代,其价值取向先后经历了“阶层化取向”、“人本化取向”及“民主化取向”的演变。
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阶层化;人本化;民主化
就教育的价值问题而言,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具有其特殊价值的,本质上蕴含着教育主体的价值取向。本文试着站在价值哲学层面,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西方媒介素养教育价值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着重探讨西方社会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期望能为当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特别是教育实践提供一种参照的视角。
关于价值取向的内涵,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界定,现有研究中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标准论”,即价值取向就是价值标准,如有学者指出价值取向是指一个人所信奉的,而且对其行为有影响的价值标准。[1]二是“选择论”,即价值取向就是某种价值选择,如有学者认为价值取向是在价值选择过程中决定采取的方向。价值取向是人们按照自行的价值观念,对不同价值目标所作出的行为方向的选择。[2]三是“倾向论”,即价值取向是某种价值倾向。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定的倾向性。[3]价值取向就是指主体基于自身的需要与对客体的认识,采取一定行为的价值倾向。[4]应该说,以上界定各有其合理性与适用性,本文正是基于“倾向论”的观点进行论述。具体而言,对于价值取向的认识,必须把握三个基本要义:一是主体的自身需要;二是客体的价值认识;三是行为的价值倾向。以此观之,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就是指教育主体,即媒介素养教育的组织者基于自身需要和对媒介价值的认识,在开展教育活动时的价值倾向。分析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时,关键在于明晰其内涵的三个基本要义:一是教育组织者的自身需要;二是教育组织者对于媒介价值的认识;三是教育组织者开展教育活动时的行为倾向。
任何主体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主体,其价值取向与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密不可分。随着社会的变迁,价值取向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体现为一种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5]因此,倘若要准确分析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必须先对其发展历程做合理划分。回顾历史,西方的媒介素养教育始终与媒介的形态特征密不可分,其发展历程依据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可划分为印刷时代阶段、电子时代阶段以及数字时代阶段。下文的探讨正是基于此类划分进行的。
一、批判与抵制:印刷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阶层化取向
20世纪30至50年代,印刷术的革新使得英国大众报业飞速发展,各类报纸层出不穷,其中,最令在英国精英学派担心的莫过于通俗化报纸的出现。精英阶层视其为“低劣”的大众媒介,认为其所传播的通俗内容与蕴含的价值意识对于精英阶层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形成了极大的冲击。1933年,学者利维斯(F.R.Leavis)和他的学生汤普森(Denys Thompson)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山之作《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极力强调大众媒介的负面效应,认为这会影响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在利维斯及其追随者们看来,大众媒介及其传播的内容,全是一种商业化、低俗化的文化,不能与传统的精英文化相提并论,“那些在学校刚刚接受文化品味教育的年轻人,在校外却陷入赚取最廉价感情的竞争中,电影、报纸以及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和追求商业利润的媒介故事,所有这些都只是迎合低级趣味,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用最少的精力,获取最直接的快感。”[6]同一时期的法兰克福派的学者们也是精英阶层的代表,他们对待大众媒介的态度与利维斯们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大众媒介的制造者为了获取最大可能的商业利润常常过分宣传媒介的感官欲望和刺激,致使人们会沉迷失在媒介提供的美好的但又不存在的世界中。正是在对大众媒介深刻批判的背景下,利维斯在其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媒介素养教育应如何开展,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学校的媒介素养教学提出一系列建议。例如,他建议教学中的课堂习题应针对不同形式的大众媒介的危害进行设计,其隐含意图就是教授民众站在精英阶层的立场批判与抵制大众媒介。[7]
在此背景下,印刷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三大基本要义大体上呈现特征为:一是教育组织者的自身需要集中体现为保护精英阶层的文化领地。有学者认为早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然而,我们要认清的是,这种“保护主义”表面上声称要保护大众不受媒介所传播的低俗化的内容的影响,实质上是在批判与抵制大众媒介的基础上实现对精英文化的保护,是一种利己的、狭隘的自我保护主义;二是对于媒介价值的认识表现为媒介的负价值被放大,正价值被忽视。在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中,价值可表现为正价值与负价值,客体对于主体的正效应,就是正价值;客体对于主体的负效应,就是负价值。[8]印刷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过分夸大了媒介的负价值,媒介被贴上了“低劣”、“低水平的满足”、“文化堕落”等一系列负面的标签。精英学者们沉醉于对大众媒介的一味批判,完全忽视了媒介在的积极价值,即媒介对于人的正价值;三是开展媒介教育活动时忽视大众的话语权。这一时期,媒介素养教育中精英文化的高级与大众媒介的低俗自然地转化成教育主体和被教育客体的关系。在这样一个新兴的教育实践中,社会民众还没来得及去做出自己的判断就已经被安排的“井然有序”,他们的话语权被扼杀,自主选择的权利荡然无存。
印刷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最初是为满足精英阶层保护自身的需要,其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阶层化倾向。这里所说的阶层化倾向是指其精英阶层作为教育的组织者与实施者,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秉承利己主义思想,一味地维护精英阶级的文化利益,过分放大大众媒介的负面效应,给大众媒介贴上错误的标签,忽视社会民众自主选择的权利。此种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究其实质,实为精英阶级担心自己的文化领地被大众的媒介文化所占领,因而采取的是反对媒介的教育。
二、理性与甄辨:电子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人本化取向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电子技术的日趋完善,以电视为首的电子媒介开始成为媒介舞台的主角,人类社会从繁荣的印刷时代逐步走向成熟的电子时代。伴随电子媒介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加剧,媒介素养教育出现了一次关键的转向,这次转向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崛起息息相关。
文化研究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9]在出生工薪阶层的威廉斯看来,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全部,不仅包括上流阶层的精英文化,还应包括工薪阶层的大众文化。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引发人们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与承载大众文化的电子媒介。电子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由印刷时代的反媒介走向对媒介的理性认识。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虽仍旧强调大众媒介的负面效应,但同时肯定其有促进大众身心发展的作用。因此,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任务应是教授民众如何甄辨大众媒介所传播内容的好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文化研究的后期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73年发表文章 《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他把传播过程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四个阶段,视其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以之取代了传统大众传播研究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模式。[10]“编码-解码”理论强调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地位,认为受众与传者是平等的关系。受众的“解码”会因人而异,其重要性等同于传者的“编码”。受此理论影响,媒介素养教育理念进一步转变,从最初认同大众文化的价值到后期开始强调大众的主体性地位,保证大众的主体性利益。
相比较印刷时代,电子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要义已有所转变:首先,教育组织者的自身需要体现为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平等价值。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肯定大众媒介所蕴含的大众文化的价值,认为其与精英文化具有同等地位,大众文化中也有对民众有益的作品,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次,媒介的价值得到理性的认识。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倡导对于媒介所传播内容的区分教育,即什么是正价值,什么是负价值。对于价值的质可以有两个层次的理解:一是正与负,二是正什么与负什么。[11]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客观地认识到媒介的正价值与负价值,并由对于媒介的价值的质的一般层次(即正与负)转变为更深的层次(即正什么与负什么)的认识;再者,教育活动中开始注意到大众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内涵主要有两点:第一,对于客观事物的能动认识;第二,对于客观事物的能动改造。[12]依霍尔分析,受众能够“解码”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分配-消费”,这是大众能动的认识媒介内容;其二是“再生产”,这是大众能动的改造媒介内容。这一时期媒介素养教育的主旨在于培养大众主动意识,使得大众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学会甄辨媒介及其传播内容的正价值与负价值。
通过以上对于电子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具有初步的人本化倾向。这种人本化倾向部分程度上也得到了同期发展到鼎盛时期的西方人本化教育思想的佐证。人本化教育强调教育应以人的“主观性”为出发点,它强调人的主体性与个体性,强调人在困境中的自由和主动。[13]同样,人本化倾向的媒介素养教育强调要培养受众的内在分析、思辨和批判的能力,以使其在面对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媒介内容时,能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辨别出大众媒介中的“正”与“负”,做出符合其自身需要的判断与理解。
三、融合与赋权:数字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民主化取向
20世纪80年代后期,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媒介成为引领时代浪潮的主力军。曾经的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非但风光不再,反而开始以其自身的数字化向数字媒介转型。越来越多的事物被打上数字的烙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数字媒介。从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媒介传播由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传播,人的个性与主动性在其中得到进一步显现,这一点在媒介素养教育界对于媒介素养内涵界定的转变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媒介学者罗伯特·卡比(Robert kubey)曾经坦率的指出:“美国在媒介教育这一重要领域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14]然而,到了数字时代,美国媒介素养教育取得了跨越式进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于媒介素养的定义就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定义指出“媒介素养是21世纪的教育之路,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用来使用、分析、评估、创制讯息,不拘媒介形式……从印刷到影视到电脑网络,民众的媒介素养是基础,在于了解媒介的社会角色,并拥有民主社会公民所需的质疑和自我表达的基本能力。”[15]2005年,该研究中心再次提出了媒介素养的五条核心概念,其中就强调:媒介被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益或权利。[16]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一整套的能力,它赋权于公民……以便于参与和从事个人的、职业的、社会的活动。[17]“民主”、“权利”、“赋权”……成为数字时代媒介的新标签。
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各国深入开展,其价值取向也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一,教育组织者的自身需要与大众需要相融合。从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最核心的转变是从以往的以传播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大众开始扮演着“演员”与“观众”双重角色。媒介素养教育的组织者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需要与大众的需要已经融为一体,难以区分,因而他们开始“鼓励发展一种更加开放的、民主的教学方法”;[18]第二,媒介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挥。数字时代的大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消费者,而是主动的媒介建构者。大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媒介中,通过创作媒介内容、增强媒介交往、传播媒介信息等方式,创造出的一种自由、平等与共享的数字媒介文化样式。当媒介的价值随着其数字化的进程被进一步发挥后,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也从传统的教授转向新型的引导,引导大众去充分发挥媒介的正价值而非负价值,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媒介传播中;第三,教育活动中强调民众的权利与利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强调,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享受其基本人权,它向公民提供了得以充分寻求和享受此项基本人权的能力,它是数字世界的一项基本人权,促进着各个国家的社会包容性……有了这项权利公民不仅可以了解信息的生产,更能了解信息的定位,并最终享受信息资源以参与到社会的各项活动中去。”[19]
综上分析,在数字时代,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呈现出鲜明的民主化倾向。这种民主化倾向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是关系的民主化。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重塑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关系。施教者不再是绝对的权威,他们只是受教者认识媒介过程中的引路人与辅助者;受教者也不再是毫无“抗体”,他们不仅具备“免疫”的能力,而且能够自己去重新建构媒介。二是活动的民主化。“媒介素养教育更多的是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论说来展开自己的调查研究。”“对话”这一形式成为西方学者最为推崇的媒介素养教育教学方式。[20]三是评价的民主化。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强调对于受教者的“发展性评价”以及受教者的“自我评价”,评价方式的改变不但反映了教育理念的转变,也体现出教育活动中受教者地位的提升。
总的说来,西方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先后经历了“阶层化取向”、“人本化取向”与“民主化取向”的演变,而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人们对大众媒介的认识与态度。每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必然有其背后的社会原因,每一种价值取向都是社会意识的集中反映。从“阶层化取向”到“人本化取向”,再到“民主化取向”,反映的是大众从被动安排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彰显的是从虚伪的“他人保护主义”到真实的“自我保护主义”的飞跃,体现的是从反媒介的教育到真正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认清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的同时,还应了解两点:第一,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历史必然性。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无论是印刷时代的精英阶层以保护大众之名来维护阶级利益,还是电子时代的工人阶级为大众文化的价值正名,抑或是数字时代媒介民主的来临,这都是历史发展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媒介素养教育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第二,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的演变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每一时期都不是一味的否定前一时期,而是对前者的“扬弃”基础上融入符合时代要求的积极元素,形成更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直至今天,早期的“保护主义”仍对今后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出警示,保护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不受媒介所传播的负面内容的腐蚀,仍然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放眼未来,媒介技术的发展会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对大众媒介的研究也将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媒介素养教育也会在沿着“民主化”的路径纵深变革。
[1]汝信.社会科学新词典[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401.
[2]徐玲.价值取向本质之探究[J].探索,2000,(02).
[3]李德顺.价值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46.
[4]袁贵仁.价值学引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50.
[5]易显飞.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47-48.
[6]F·R·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 [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33.23.
[7]大卫·帕金翰,宋小卫.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02).
[8]王玉樑.价值哲学新探[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40.
[9]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256.
[10]蔡骐,谢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传媒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03).
[11]刘永富.价值哲学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5.
[12]百度百科:主观能动性[EB/OL].http://www.baike.com/wiki/.
[13]胡继渊.浅述西方人本化教育思想及其借鉴[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2,(02).
[14]陈国明,J·Z·爱门森.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上)[J].中国传媒报告,2008,(01).
[15]周典芳,陈国明.媒介素养概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213.
[16]宫淑红,张洁.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29.
[17][19]吴文涛,张舒予.“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多视角解读[J].新闻战线,2015,(02).
[18][20]宋小卫.西方学者论媒介素养教育[J].国际新闻界,2000,(04).
吴文涛/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舒予/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从共享到共生:基于专题学习网站的知识建构转型研究”(12YJA880161)、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冯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