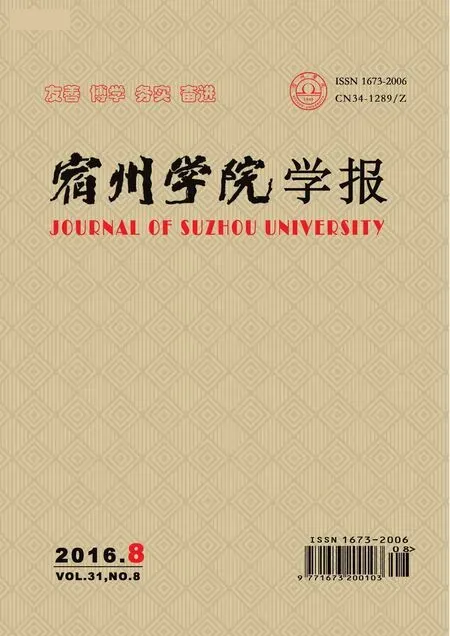《四灵魂》中印第安人的寻根之路
陈召娟,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四灵魂》中印第安人的寻根之路
陈召娟,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美国印第安裔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在其《四灵魂》中,描写了印第安人如何在多元文化之中完成寻根之路。分析了土地对主人公弗勒的重要性以及印第安传统文化对其生存的意义:土地实质上是她生存的根,印第安传统文化则是她生存的强大武器;探讨了药裙对其灵魂重塑的帮助:为了净化被主流文化削弱的灵魂,弗勒穿上了药裙,重新构建了与印第安部族的精神联系,得到了土地的认可。厄德里克以此书写了弗勒的寻根之旅,探索了印第安人在多元文化之中新的生存模式,强调了印第安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神奇。
厄德里克;《四灵魂》;弗勒;土地;药裙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本土裔文艺复兴以来,一大批优秀的美国本土裔作家展露头角,受到了国内外批评家和学者的关注和肯定。其中,当代最重要的美国本土裔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就曾先后获得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奖、艾尼斯菲尔德·伍尔夫图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四灵魂》是厄德里克在2004年创作的小说,该作品不仅真实地呈现出北达科他齐佩瓦保留地内几代印第安人的生活,而且还展示出厄德里克对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强调和对部族历史问题的关怀。
目前,国外批评家和学者主要从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批评这两个角度对《四灵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帕特里克·本顿从叙事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弗勒、毛瑟和纳纳普什这三个人物来突出恶作剧者形象的文化特色[1];艾梅·伯杰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探讨了弗勒和女儿关系破裂的本质原因,强调了白人同化政策给印第安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2]。国内学者张琼从本土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亲和、背离和偏移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研究了该小说[3]。很少有学者从主人公弗勒·皮拉杰的寻根之路这个视角来研究《四灵魂》,为此,本文尝试探索弗勒如何跨越文化边界、完成寻根之路。
2 土地——生存的根
美国著名本土裔作家波拉·甘·艾伦提出,土地在美国印第安小说中占有核心地位[4]。路易丝·厄德里克就曾在多部小说中突出土地对于印第安人的重要意义。但当代印第安部落的土地正在不断流失,四分五裂。1887年,美国政府颁布了《道斯法案》,规定了印第安部落共有土地的分配权。然而该法案实质上剥夺了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在《道斯法案》颁布以前,1.39亿公顷土地由政府替印第安人托管;到了1934年,土地分配法几乎被正式取消时,部落只剩下4800万公顷的土地。”[5]这表明白人政府剥夺了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并从中索取利益。土地的流失打破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和谐,击碎了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甚至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存。
厄德里克笔下的《四个灵魂》则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描述了印第安人弗勒离开部落后,如何与白人斡旋并最终寻回自己土地的过程。在小说的开篇,弗勒离开部族群体,并非是由于厌倦保留地的生活,而是为了寻根——土地[6],因为她认为离开印第安部族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弗勒一直跟踪那个窃取她土地的白人毛瑟。他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擅自闯入了别人的狩猎领地,只知道贪婪地往地下挖得越来越深[7]7。很显然,白人的贪婪玷污了部落的土地。土地买卖的交易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益,而他们只是把印第安人的土地视作赚钱的资本。
祖先的土地和树木是印第安人的财产,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的根基。印第安人推崇宇宙的和谐,“把万事万物视作亲属……视作我们母亲的孩子”[8]。印第安人这种独特的宇宙观表达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爱和崇拜,而土地又是其中的核心元素。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白人侵占了他们大片土地,印第安部落世代维护的神圣性遭到破坏。弗勒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家园,失去了精神核心,失去了自己的根。当代印第安裔作家西蒙·欧提兹强调,土地和印第安人互为依存,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命[9]。土地已成为弗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土地被白人掠夺使得她的生命不再完整,她发誓一定要寻回她赖以生存的根——土地。
3 传统——生存的武器
在探索本土裔文学的过程中,厄德里克不仅书写了印第安人土地丧失的历史,还像许多优秀的美国本土裔作家一样,“超越了自身的族裔背景和疆域的局限,深入涉及更为深远的思考,如文化身份、生存模式、生命本质等”[10]。厄德里克在小说中探索了印第安人在多元文化之中的生存模式。著名学者朱立元指出,第三世界的学者如果身处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他们“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改变困境以及群体的命运[11]419。显而易见,在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在宗主国面前处于弱势地位,而个体经验是其生存和把握命运的强大武器。弗勒从印第安部落来到白人世界,个体经验对她而言,意味着她所传承和敬仰的印第安文化。在白人波莉·伊丽莎白的眼中,弗勒不仅愚蠢,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习惯上与白人有巨大差距,就像野狼与家养猎狗之间的明显区别一样[7]14。显然,弗勒被看成是一个毫无教养的下等人,这种处境对弗勒夺回土地而言丝毫没有优势。但是,很快弗勒便抓住机会,依靠印第安传统治疗手段,获得话语权。弗勒发现毛瑟患上一种疾病,四肢抽搐,像触电一样猛烈地抽动,白人医生建议服用少量鸦片,但病情依旧恶化。弗勒开始秘密地用印第安部族的方法治疗毛瑟,她不仅燃烧香甜的禾草和鼠尾草,使他房间里的空气变得清新,还给他喝清热解毒的“大叶桉叶茶和印第安药酒”[7]24。在弗勒的治愈下,毛瑟的病情渐渐好转。而前后两种不同的治疗效果引起了毛瑟对弗勒的兴趣,这种变化正是弗勒所期待的。
朱立元进一步提出,虽然西方文化在发展上比其他文化更快地进入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就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的”[11]429。弗勒用印第安传统的治疗方法改善了毛瑟的病情,而白人医生却认为毛瑟的疾病是个谜,无法医治。在先进的医学技术面前,齐佩瓦族的传统治疗方法并没有被淘汰,相反,弗勒向白人显示了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神奇和神秘,而这也是弗勒所选择的个体经验,即坚持个体的特殊性,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迅速发展的西方文化不是唯一能体现优越性的文化,其他文化也有其值得骄傲的特殊性。处在主流文化语境中的弗勒,虽然一开始处境困难,但是后来通过彰显齐佩瓦族的文化习俗,不仅缓解了毛瑟的病情,吸引了他的注意,还成为了他的妻子。由此,弗勒的寻根之路跨越了文化边界,完成了重要的一步,然而,她停下了脚步。随着身份的变化,她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
弗勒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沉浸在白人的文化价值观中,无法脱身。作为毛瑟的妻子,弗勒开始体验白人的生活,富足的生活让她暂时晕头转向。弗勒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虽然她依然相信可以用其他途径来夺回自己的土地,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像很多离开部族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深陷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崇尚物质文化,不可自拔。更糟糕的是,弗勒迷上了白人的酒精,她的意识开始混乱,主流文化和自己一直坚守的印第安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酒精象征着白人文化,弗勒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被白人主流文化所控制和愚弄,让她误以为这是自己的意愿,实则却是威士忌的[7]75。弗勒强大的灵魂已然被酒精所削弱。她的寻根旅程踏入了巨大的泥潭,越陷越深,幸运的是,部族的长者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4 药裙——灵魂的重生
“本土裔文学创作大多更具有向心力,不倾向于外化扩张,主人公最终会回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的回归,溯源成为小说人物探寻知识的基本模式。”[12]厄德里克在小说中也采用了溯源的手法。弗勒重新回到保留地后,得知土地已经被转卖给其他人,这意味着弗勒的寻根之路还没有完成。弗勒再一次利用印第安皮拉杰部族祖先赋予的能力,在纸牌赌博中赢得了土地。在寻根的旅程中,弗勒总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借助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力量,但她的灵魂受到了诱惑,已不再纯净,失去了与印第安土地的精神联系。为了让灵魂得到净化,回归家园,弗勒选择接受印第安长者的帮助。
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药裙的力量神圣而强大。穿上药裙的人能够治愈心灵创伤,了解以前未知的事情。但药裙的缝制要求却极其苛刻,缝制者需要用灵魂和裙子交流,将药裙视作心灵的沟通者,并倾诉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如此,药裙才能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净化伤者的灵魂。在小说的最后,弗勒寻回了土地,却失去了灵魂,她决定求助养母玛格丽特,进行灵魂的洗礼。玛格丽特是一名药师。印第安人普遍认为,药师不但可以帮助病患者缓解和治疗身体上的疼痛, 而且还可以指引迷失的印第安人重新建立与部族的精神联系[13]。在净化的过程中,玛格丽特引领着弗勒回归家园,为她唱起了歌,一首回家的歌、古老的摇篮曲、湖泊的歌[7]203。这首歌能唤醒大自然万事万物,使它们重新接受弗勒的灵魂。最后弗勒穿上了药裙,需要在湖边的岩石上斋戒八天八夜。
在斋戒仪式中,弗勒在药裙的启发下加强了自己与印第安部落文化的联系和作为部落群体一员的认同。在遭受太阳烘烤、苍蝇叮咬和冷风吞噬的同时,穿上药裙的弗勒想起了自己已经死去的亲人,看到了他们为了坚守土地所作出的牺牲。弗勒深刻感受到了自己族裔身份所代表的意义和责任。她必须舍弃对白人物质观的依赖,重新构建与部落群体的联系,进而“构筑被殖民统治所破坏了的一种文化属性……寻根、寻源、寻找原初的神话和祖先”,获得他们对自己族裔身份的认同[14]。渐渐地,在所有看似微小灵魂的折磨下,弗勒彻底摆脱了灵魂的空虚、愤怒、迷惘和贪婪[7]206,得到了保留地居民的认可。弗勒在寻根之路中,沉迷在白人社会的物欲主义,抛弃了自己的灵魂,而药裙赋予了她灵魂的重生,使她最终被这片土地所接纳。
5 结 语
美国本土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土地这一重要元素。土地是所有印第安人心中强大的精神支柱和信仰核心,同时也是他们生存的家园,是每个人心中的根。而当代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本土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在《四灵魂》中就强调了土地对于印第安人的生存意义。本文以《四灵魂》中的印第安女性弗勒为例,探索了印第安人的寻根之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弗勒坚定地追寻着自己被掠夺的土地——信仰、家园和根,开始了寻根之旅。她在以白人为尊的主流社会中,依靠印第安传统文化习俗,改善了自己的生存处境。然而,在和白人展开对话的过程中,她迷上了威士忌,逐渐背弃了曾经一直坚守的印第安传统文化,寻根之路也因此陷入了迷雾中。但她在印第安长者的帮助下,接受了药裙的净化,重新获得了印第安土地对她的认可,寻根之路也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厄德里克以此展现了印第安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神奇,突出了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本文虽然涉及了《四灵魂》中印第安人的生存模式,但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深入解析印第安人的其他生存模式,由此来丰富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
[1]Patrick B Benton.Agent of Change:Trickster in Ojibwa Oral Narratives and in the Works of Louise Erdrich[J].Honors Theses,2007(3):260-270
[2]Aimee E Berger.The Voice of the Maternal in Louise Erdrich's Fiction and Memoirs[C]//Andrea O'Reill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89-106
[3]张琼.《四灵魂》中族裔价值与经典传统的结合、背离与偏移[J].外国文学评论,2009(6):122-126
[4]Paula Gunn Allen.Iyani:It Goes This Way[C]//The Remembered Earth: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Albuquerque:U of New Mexico P,1980:191-194
[5]王建平.后殖民语境下的美国土著文学:路易斯·厄德里齐的《痕迹》[J].外国文学评论,2005(2):42-50
[6]邹惠玲.继承与改写:厄德里克的《爱药》与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归家模式[J]. 当代外语研究,2010(8):8-11
[7]Louise Erdrich.Four Souls:A Novel[M].New York:HarperCollins,2004
[8]Paula Gunn Allen.The Sacred Hoop: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C]//Nothing But the Truth.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2001:62-81
[9]Simon J Ortiz.Speaking for the Generations[M].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8:9
[10]张冲,张琼.从边缘到经典: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源与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228
[1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2]William Bevis.Native American Novels:Homing in[C]//Critical Perspective on Native American Fiction.Washington:Three Continents Press,1993:15-45
[13]M Dimitrijevic.Shaman’s Circle:Circularity in Native American Culture[J].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2005(2):185-192
[14]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09-212
(责任编辑:胡永近)
10.3969/j.issn.1673-2006.2016.08.021
2016-02-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11BWW054);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一般项目“印第安人的寻根之路——以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四灵魂》为例”(2015YYB138)。
陈召娟(1991-),女,江苏盐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4
A
1673-2006(2016)08-008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