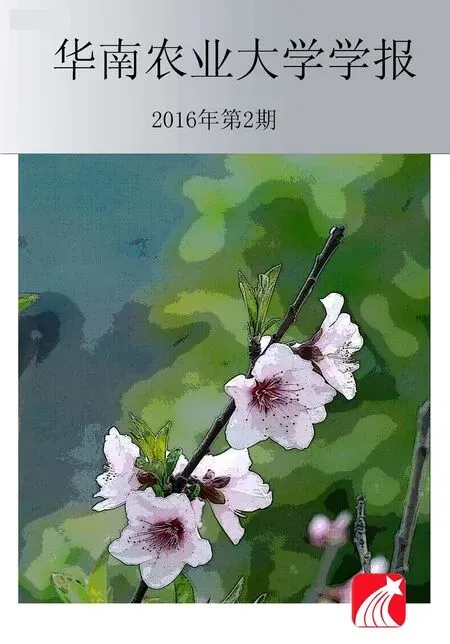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
耿达(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
耿达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20世纪3、40年代,梁漱溟和费孝通相继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并付诸实践。梁漱溟从文化改造着手,试图通过建立新礼俗、乡学和村学来教育民众,以最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费孝通则从经济建设出发,通过发展分散的乡土工业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以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两者的视角一个是“由外而内”,一个是“自内而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既有相似又有明显差异,代表了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
关键词:梁漱溟;费孝通;乡村改造;乡土重建;新农村建设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涌入,“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社会构造逐渐解体。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内忧外患:国内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西方列强加紧入侵,掀起瓜分中国狂潮。进入2 0世纪30年代,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九一八事件”更使民族危亡进一步迫近。加之天灾人祸频发,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破坏力连环影响加速了中国传统农村秩序的破坏[1]10。“近代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被剥离的地位,却又受到这个过程的吞噬”,这一过程导致农村“社会结构恶化”和农民“普遍贫困化”[2]。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使“改造乡村,改造中国”成为近代知识分子重构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共识。在近代中国农村重建的思想资源中,“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最为典型和突出。学界对梁漱溟和费孝通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两人的比较研究则相对缺乏①对梁漱溟与费孝通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徐勇:《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及其比较》,《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卫春梅:《农村三人行——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思想对于当前农村问题的借鉴意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时武喜:《20世纪30年代前后梁漱溟、费孝通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而在近代乡村社会改造的历程中,梁漱溟和费孝通无疑是两位无法绕开的人物,二者对中国农村重建有着独到的认识,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以理论指导实践进行了相关实验,在当时即产生重大反响,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乡村重建的进路。以梁漱溟的文化路向和费孝通的经济路向为代表,形成了农村重建的两条不同路向,凸显了近代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时代境遇中对中国发展路径的探索。要解决农村问题、寻找中国路径,须要认识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我们于中可以有反省、有自觉、有料度,因其大势之所趋,从而为之所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要不外如是而已,”即要本着历史的眼光去观察认识,“要从其来历背景而有以测其前途将要如何才行。”[1]8重新认识和发掘这两条路向的思想资源,对于当代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依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梁漱溟与“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的文化路向
20世纪2、30年代,全国兴起了一场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3]据统计,当时全国各地有600多个团体和机构,1000余处实验区[4]。梁漱溟指出:“现在乡村建设运动已为国人所注意,有很多人都在那里争着谈乡村建设。”它们的来历背景各有不同,有社会团体、政府机关、教育机关[5]。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参见表1),其中,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方案。梁漱溟主笔了《村治》月刊,主编了《乡村建设》半月刊,创办了“乡村书店”,在领导乡村建设实验之余,进行理论创作和宣传,先后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1932)、《乡村建设论文集》( 1934)、《乡村建设大意》( 1935)、《乡村建设理论》( 1937)等著作,在当时即产生了广泛影响,当仁不让地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

表1 20世纪2、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模式
(一)乡村建设的认识论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首先从中国社会构造剖析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制度创建多“为乡村而设”[1]10。而近百年中国史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救济乡村”并展开“乡村自救”。梁漱溟的着眼点并不仅在于建设乡村,而是探寻“中国民族之前途”,“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1]19。梁漱溟认识到中国社会已陷于严重的“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饥荒。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不同于“个人本位、阶级分立”的西方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济上“共产”,在分际关系上注重“情理”的伸缩。在这种社会中,尽管贫富悬殊,等级分明,但贵贱沉浮无定,流转相通,并不存在突出的阶级矛盾,所以“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1]30。旧社会构造崩溃之由在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表现在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中国文化“理性早熟”,教化、礼俗皆开发较早。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最显著的短处,“一是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一是短于对自然界的分析认识,不能控制自然,转而有时受制于自然。”[1]50中国文化的衰老性和幼稚性使其缺乏现代化极其重要的两大元素: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梁漱溟非常看重团体组织的作用,认为“中国社会病在散漫,救之之道,在于团体组织”[1]58。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的乙部“解决问题”中首要强调的就是“乡村组织”。梁漱溟认为乡村组织可以解决中国眼前的几个大问题、可以开出中国民族的出路,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乡村组织是一切制度的端倪,无“团体组织”的精神则教育、政治、经济等制度皆无法合理建立起来。所以,梁漱溟号召“我们乡村运动者要联成一大文化运动团体系统,由此系统领导推进大社会”[1]241。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梁漱溟认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文化失调”,而解决之道在于以“文化改造”为基础重建社会构造。这并不是说梁漱溟不重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说文化建设是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根本和内核。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也重视政治问题和经济建设,认为“成功的社会”须有“乡村组织的培养”、“经济问题的解决”和“适宜的政治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建设才能促进民族的复兴。但当时“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经济破产”,精神方面亦“动摇摧毁”。一句话,就是旧社会构造已崩溃而新社会构造“没有产生树立”[1]242。
实际上,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从儒家文化出发,结合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6]。早在1921年五四文化论争时,梁漱溟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明自己的文化哲学观。“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借鉴吸收西方文化到如何建构新文化”[7]成为梁漱溟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遵循着“意欲——态度——根本精神——生活样法——文化差异”的逻辑轨迹[8]42,认为“现在之中国问题”是由西洋文化“外面引发”。他比较了东西文化的不同,认定中西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路径,而中国文化在未来必将复兴;对于西方文化要加以吸收,并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9]。“中国问题起于中西文化之异,中国问题的解决,在于中国文化改造。”梁漱溟文化改造的目标是“阐发中国固有精神、吸收西洋文化长处。”[10]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决定了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传统的方式来实现他的“新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追求,“乡村建设”不过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现实途径。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必须面对转变,只有“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中国才能得救,而新文化必须来源于乡村[11]。乡村是中国文化“有形的根”,新的社会组织与新文化须从乡村产生。因此,梁漱溟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埋头苦干”,以达到“救活农村”和拯救中国文化的目的。
(二)乡村建设的方法论
在经历了广东乡治教育( 1927.5~1929.2)和河南村治实验( 1929.11~1930.10)的初步尝试后,1931年3月,梁漱溟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专门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到1937年底日本侵占山东结束),梁漱溟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倡导“新礼俗”
梁漱溟十分强调传统文化元素的主体作用,认为中国过去社会秩序的维持多靠礼俗,中国将来的新社会组织仍要靠礼俗。他把“新的社会组织”概括为“教育化的组织”[1]146,即通过“补充改造乡约”来教化民众。乡约在古代中国源远流长,一直为乡民所自觉遵守。乡约是本着彼此相爱惜、相规劝、相勉励的本意。梁漱溟所谓的乡约,一方面是教育,一方面是自治,即建立文化运动团体组织。梁漱溟认为乡约是农民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运动”,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在农村“乡约”具备“法律”的效用,能够促成农民的自觉[12]。
以3种运动规律分别搭配Clothoid曲线,各运动规律下的相对能耗最小轨迹,其参数都为e=25,d=44。由此得出经验性结论:以Clothoid为过渡,配合3种运动规律,获得的Adept Cycle拾放轨迹,最优参数均为e=25,d=44。
2、兴建乡学、村学
梁漱溟改革邹平县原有的行政组织,建立了乡校组织,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实行“政教合一”。村学是乡村改革的最基层组织,村学就是一个乡村学校,由校董会和教员与辅导员组成。乡农学校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产生的机关,乡农学校的目的“就是让乡村人发生自觉”。在《村学乡学须知》中,梁漱溟将教员的工作分为提引问题、商讨办法、鼓舞实行三项,以引导乡民“齐心合作解决问题”。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中,梁漱溟主张把教育从课堂搬出来,打破学校化的传统教育,代之以社会式的教育,其具体体现形式就是乡学和村学。
3、促进合作组织
梁漱溟认为合作能够调和“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分际[13],合作组织能够增加生产、减少剥削、降低成本并共同支配和享有资源。梁漱溟特别推崇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为推动合作社发展,1935年7月实验县政府还成立了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集中力量推进合作事业,并利用乡学、村学对民众实施合作教育,还设立农村金融流通处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支持。到1935年底,合作社数目达到336所,入社社员增加到14939人[8]57。合作社有各种类型,包括美棉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信用、购买等。邹平的合作社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最为活跃,棉花销路很好,农民踊跃加入。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是他的文化哲学的具体实验,主要通过“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两个途径来进行。但是,梁漱溟的中国农村重建的文化路向并没有满足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看不到“眼前利益”。梁漱溟也总结道乡村建设运动的难处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他们村外人瞎嚷嚷”,且因为“我们动”反而使乡人觉得“不合适”。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得到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因为产销棉花能够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梁漱溟所主张的建设新礼俗、兴建乡学、村学等文化措施,农民得不到实惠,反而觉得是“浪费时间”,“与他无关”。因此,梁漱溟所倡导的中国农村重建的文化路向在当时政治权力四分五裂经济基础残破的条件下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彭一湖在《乡村建设的难题》中指出:“乡村建设之有无前途,就全看经济建设之有无结果,如其经济建设而没有结果,那所谓乡村建设,也不过是昙花一现,”[14]可谓切中要害。
二、费孝通与“乡土重建”:乡村改造的经济路向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表明其农村重建的文化路向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时人指出:乡村建设对于教育之推广,第一目的空泛,乡村教育乃一种基础教育,如能使人人识字,进而团结爱国,已属难能可贵,若欲以之为建设新农村之基础则欲望未免过奢。第二,课程不切实际,各级乡村学校改用课本,除自编者外,仍用普通学校之课本,殊不适合乡村之需要。第三,方式太多,于乡村学校外,有补习学校、成人学校、妇女学校、民众教育馆等等组织,更有家庭式、学校式及社会式等变化,其实均为表面文章,不堪深究。晋生:《乡村建设运动之我见》,《新建设》1936年第3卷第17期,第2~5页。。20世纪40年代前后,费孝通从社会学领域出发,转换近代中国农村重建的问题视角,沿着“乡土中国”的认识开辟了近代中国农村重建的经济路向。
(一)“乡土中国”的文化社会学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在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出现了重大转变。梁漱溟将其总结为“乡村破坏”和“社会崩溃”,归根结底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也不断地受到一种被损蚀和冲洗的作用,结果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15]353。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化症结正在于“处境已变”:东方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无法适应西洋工业化的时代趋势[15]307-308。但是,费孝通认为:“小农经济不会崩溃只会瘫痪。瘫痪是慢性的,逐渐加深的。……崩溃、危机等字都是用来形容现代化的经济现象的。”[15]327据此,费孝通将其分析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经济问题上,极力提倡利用现代技术同时建立一个和现代技术相配的社会结构。费孝通与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同认识和分析,为他们农村重建的不同路向奠定了基本的“内在理路”。
(二)“乡土重建”的经济方案
费孝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路向有着理性的批判。费孝通认为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偏重于“文字教育”,其开展的各种事业是“消费性的”,“并不直接增加农家收入”,并且这些事业需要“外力来资助”,否则“就不易继续”[15]438-439。以此为鉴,费孝通本着“自力更新的原则”从经济建设出发,提出了以“乡土工业”为核心内容的农村重建方案。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费孝通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 1936年江村调查、1938年禄村调查),初步形成了这样的假定:假定现代化、工业化不可避免,中国的各个地方都会走向工商业时代;假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一个过程,不同的地区就会由于地处不同位置而处于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过程会对农村的社会结构、组织与关系甚至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意味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方向与路径[17]。费孝通发现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制度束缚了农村人口的全部活力,使整个文化陷于僵化。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和《乡土重建》等著作中多次讨论土地问题以及乡土经济结构。他指出“农民的收入”低下才是“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农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农民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18]199-200。因此,“增加农民的收入”才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而“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恢复和发展“农村企业”[18]201。费孝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发展起能够惠及农村的工业。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农村经济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经济。费孝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乡土工业发展的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因此提出了“工业下乡与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即乡土工业以合作社为组织形态,以落实农民利益为基本目的,进而以农民为主体自动完成乡土重建。他认为美国或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欧美的工业发展模式“只会更加剧农村人口的悲惨境地。因为它将冲击到村庄里所有的庭院工业,从而进一步减少农民的收入”而且“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中国的更进一步的工业化将只意味着工业所集中的财富将落入中外工业家的手里——这一变化并不能改变中国农民的经济情况”。因此,“为了任何一种形式的工业发展的成功,我们必须以提高普通人民——农民是其中最大多数的一群——的生活水准的能力为标准来找到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18]。费孝通提出的办法就是乡土工业“分散化”和“合作化”。因为动力、技术、社会关系、经济组织各方面都是可以变的,在现代工业技术下乡背景下乡土工业的分散发展是可能的和可行的;而发展乡土工业的形式应该是“合作性质”,因为“合作社的方式保证了生产者获得全部利益的权利,取消了剥削成分”。乡土工业包括“手工的”与“机器的”、“家庭性的”与“工厂性的”。费孝通认为乡土工业的规模可大可小,随技术的应用程度而具有伸缩性:“在技术的需要之下,可以在合作基础上成立服务工厂,把那一部分不宜分散在农家的集中到村单位的小型工厂里,再把不宜分散在村子里的,集中到中心村里为一个区域中的原料生产者服务。”[18]“家——村——中心村——区域”是乡土工业由分散化到聚集化的大致路径。乡土工业不是原始的和保守的,而是重视引进技术和提倡合作。既要通过引进机器改进手工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提倡经济组织的合作。新技术只有同新的分配方式相配合,才能嘉惠于广大人民的生活[19]。总之,费孝通时时处处总在为农民的利益着想,增加农民收入是费孝通最基本的着眼点和最根本的落脚点。
三、评价与反思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费孝通的乡土重建代表着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呈现出前后相续的历史逻辑。他们所开辟的近代中国农村重建的道路,对当代新农村的建设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当中国工业化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了30多年后,城乡关系的“马太效应”更加凸显,在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农村呈现出“空心化”和“格式化”的窘境。梁漱溟和费孝通关于农村重建的思想资源对于现代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历史的启示作用。
梁漱溟所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努力与实践,以建设乡村组织为中心,“借乡学、村学,推进社会,如农事改良,办理合作社、识字运动、社会风俗习惯的改良、禁缠足、禁赌博等等,悉皆包括在内,改革不良、提倡新的两方面事业,咸由村学、乡学推进,一方为教育机关而另一方则又属自治组织,站在教育立场,扶助领导,进行不懈。”[20]虽以救济农村挽救中国民族前途为目的,以建设新礼俗、实行村学、乡学为工具,其实质在于重建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梁漱溟所发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却无法“使乡村动起来”,闵挽澜认为像邹平那样的“村学”、“乡学”的乡村建设组织,并不是农民的自动组织,而且因为村长乡长都是乡绅地主,当然也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农民对于这种“没大关系”的建设组织,自然会“漠不关心”。事实上,农民不是有了这种组织就可以免除苛捐杂税、高率田租及高利贷的种种剥削;也不是有了这种组织就可以不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蹂躏,而且因为农民要求这些切身的关切,促使他们还会施以种种的政权压迫。这样,农民经济地位未得改善,他们自然“不动”了。又如定县的四大民教,也诚如张季鸾先生所说:“受过这样识字训练以后,他还要求下文,下文是他收的粮食不够吃;老婆小孩子,光着身子要穿衣服,没有钱去买布。如果在他的这种经济生活上,不能给以增进,那就不能解决他的痛苦,反而增加他的烦闷,增加他的焦虑、疑团。”这样的教育工作,自然是“隔靴搔痒”。而对于农民的生活,却还依然的是一天一天的破坏下去。其他如县政改革,如合作运动,也莫不是有这同样的苦闷。这可见“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未能与乡村打成一片”。这种“不以农民作基础的力量”的乡村运动,“那还有什么前途呢?”[21]
费孝通乡土重建的经济路向的开辟,分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针对中国“人多地少”、农民“饥饿”的实际状况,提出了以“乡土工业”为核心内容的农村重建方案,重在解决农民的“生活水准”。费孝通的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重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江南发展模式”备受瞩目,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基于乡土工业的发展路线,费孝通还提出了“小城镇化”的建设思想,即使城镇与乡村互为补充共同协调发展。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大城市化”的发展路线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农村成为了城市的附庸和边缘地带,农村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裹挟下呈现出急剧的空心化现象:土地被城市征用、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农田大量荒芜、农村传统文化濒临灭绝。因此重新评价和反思梁漱溟和费孝通的农村重建思想具有时代意义。
梁漱溟与费孝通对农村重建的理解和追求既有相似又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其一,都从分析社会结构出发,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无论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还是费孝通的乡土重建,都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出发,对文化、经济和政治都做了全盘的分析和考察,这就决定了他们农村重建的“中国路径”,而不是盲目跟风和屈从西方发展模式。其二,都对农村、农民、农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反思。他们都认为农村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都希望农民能够“积极向上”、“生活富足”,认为农业能够引发工业,农业能与工业相互补充。所以,他们的落脚点是一致的,就是使农村充满活力、富有生机。其三,都强调要走合作化道路。近代中国农村在经历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后破坏、瘫痪,农民力量薄弱,经济分散,建立合作组织有利于实现集体利益和保证生产者的权利,减少剥削成分。集体农庄和家庭工业的合作社都是他们所推崇和寄予厚望的组织,也是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现实途径。
由于历史境遇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两人的思路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一,对“文化”根本性的认识不同。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终极宗旨是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当前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锋中败下阵来,但是未来终将复兴,因此要利用西方文化的长处改造中国文化的短处,在文化上进行突破。可以说梁漱溟是“文化决定论”者。而费孝通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文化位育”进行了一套分析,认为“文化是一种手段”,价值在于让人生活得更好[22]。可以说费孝通是“文化功能主义”者。其二,改造乡村的方式不同。两者对文化根本性的认识不同导致改造乡村的方式不同。梁漱溟是从教育出发,通过建立新礼俗、乡学和村学来教化民众,视角是“由外而内”的,所以要努力想办法让乡村“动起来”,与“乡民打成一片”。而费孝通是从生活需求出发,通过发展分散的乡村工业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视角是“自内而外”的,能够为农民所接受和积极拥护。其三,对中国问题的诊断不同。虽然两者都用社会结构的分析,但分析的重点不同。梁漱溟将社会结构分析的重点落到乡村组织方面,建构出以乡学村学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建设理论,而费孝通将社会结构分析的重心落到经济建设方面,建构出以发展乡土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乡土重建理论。
比较梁漱溟和费孝通“乡村改造”的不同路径,重在考察二者在历史过程中所处的背景和所产生的效果,并反思两人的“思想资源”能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我所用”。时人晋生认为乡村建设若要生效,必须遵守四项条件:一是必须认清时代之需要,即科学化与机械化的发展途径;二是明了国家之环境;三是必须考查自己之力量,乡村建设成效之关键,不仅在理论之是否健全,而政治力经济力与人力之是否充实;四是必须估量农民之能力。乡村建设工作实举不胜举,但何者符合农民积极的需要何者适应农民接受之能力,并如何使之感觉某事之重要与需要,如何使之敬然接受,欣然同情,均须斟酌再三,而后始可推行[23]。这四项条件仍然是当今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遵守的。农村是承载“乡愁”的地方,要留得住“乡愁”就要留得住农村,留得住农村就要留得下农民,留得下农民就要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人”才是一切的核心和关键,所以“三农”的中心和重心应该是农民,以农民为主体,“殖产兴业”、“致富育文”。当今新农村建设必须要综合梁漱溟和费孝通的“思想资源”,既要重视经济建设又不能忽视文化建设,在满足“吃喝不愁”的同时有文化精神;要全面协调发展,把经济和文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才可能是有活力有内涵和可持续发展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张鸣.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近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J].浙江社会科学,1999( 4) : 124-132.
[3]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J].安徽史学,2006( 4) : 69-80.
[4]瞿韶华.中华民国史事纪要[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3: 19.
[5]梁漱溟.北游所见略记[M]∥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1) : 115-120.
[7]耿达.五四文化论争视域中的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J].华中人文论丛,2014,5( 2) : 154-157.
[8]左克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与实践的哲学评析[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528.
[10]高国舫.文化改造——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着眼点[J].理论界,2004( 2) : 155-158.
[11]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M]∥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610.
[12]熊吕茂.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文化诠释[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5) : 66-71.
[1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416.
[14]彭一湖.乡村建设的难题[J].民间,1934,( 1) : 16: 5-6.
[1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1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五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36.
[17]李友梅.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18]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二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19]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M].北京:清华出版社,2004.
[20]记者.乡村建设运动[J].农村经济,1934,1( 7) : 8-9.
[21]闵挽澜.如何使乡村“动起来”——致梁漱溟先生兼论目前乡村工作的动向[J].中国农村,1937,3( 6) : 25-31.
[22]费孝通.对于各家批判的总答复:后记[M]∥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66.
[23]晋生.乡村建设运动之我见[J].新建设,1936,3( 17) : 2-5.
Two Approaches to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a
GENG Da
( The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In the 1930’s and 1940’s,Liang Shuming and Fei Xiaotong studied the Chinese rural problems theoretically and put into practice.Liang Shuming started with cultural transformation,tried to establish new customs,township and village school to educate people and to reviv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Fei Xiaotong started fro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tried to improve farmers’living standard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local industry,in order to meet the vital interests of farmers.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scholars has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One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outside-in”,the other“the inside out,”representing two approaches to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Liang Shuming; Fei Xiaotong; rural tranformation; rural r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耿达( 1988—),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公共文化政策。E-mail:603474617@ qq.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13ZD04)
收稿日期:2015-12-14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2.014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 2016) 02-013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