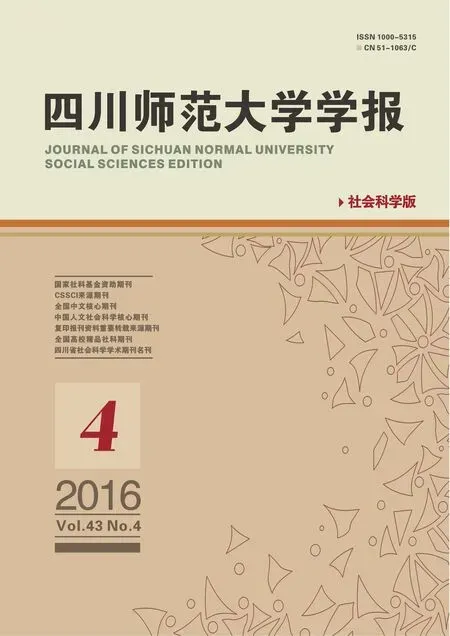论人格尊严的刑法保护
——以尖端医疗为视角
杨 丹
(暨南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论人格尊严的刑法保护
——以尖端医疗为视角
杨丹
(暨南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摘要:人格尊严具有宪法最高价值,刑法以最明确的禁止规范和最强烈的惩罚措施,为人格尊严提供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保护。尖端医疗的不当实施会严重损害人格尊严,此乃刑法介入尖端医疗的实质根据和终极理由。运用刑法规制尖端医疗领域及其关联行为,是风险社会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尖端医疗;人格尊严;刑法保护;风险社会
人格尊严①经历了从古典观念到现代价值的变迁。曾经作为理念而存在的人格尊严,现今获得了宪法的确认,并成为宪法上的最高价值。作为宪法最高价值的人格尊严,只有投射于部门法体现为具体法益,才能获得实定法规范的切实保护。然而,人格尊严概念本身是抽象的。本文以尖端医疗②为视角,揭示人格尊严的具体内涵,探讨尖端医疗领域因为严重侵犯人格尊严而应当予以刑事禁止的行为,为实现刑法对人格尊严进行“最高等级的法律保护”[1]1奠定理论基础。
一人格尊严在现行刑法中的体现
(一)人格尊严的宪法价值及其部门法投射
人格尊严理念发端于古希腊,历经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改造、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变革,最终由康德阐明其哲学内涵,进而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宪法和法律。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人格尊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1款作为第三款,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上述规定反映了人格尊严是我国宪法的价值基础,人权是保护、实现人格尊严的手段。
人格尊严作为宪法的最高价值,其本身并不是法益,而是法益赖以建立的基础[2]。因此,“人格尊严”不是刑法(乃至于一切部门法)直接保护的法益,它作为宪法的核心价值,通过投射于部门法之中,具体化为部门法所保护的法益。例如,为了充分全面维护人的“自在目的性”,私法在立法技术上将人格尊严的内容化作“权利”加以保护,谓之“人格权”。人格进一步具体化为各项人格要素,例如生命、健康、名誉、隐私等,在各项要素上成立的权利,被称为具体人格权[3]391。在德国,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通过其放射性功能渗透于部门法中,民法、刑法、社会法中随处可见人格尊严的影子。部门法打开了迎接人格尊严条款的天窗,宪法与部门法形成了完美的互动,二者的融合共同维护了宪法秩序,发展了宪法法理,我国学者誉其为“德国宪法对于世界的贡献”[4]。
宪法和部门法既需要在肯定的方向上维护人格尊严,也需要在否定的方向上惩治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作为手段的行为。国家承担保护人格尊严的积极义务,其直接方式是通过设立并贯彻具体的刑法条款来确证和细化宪法上的禁止性规定,宣示并落实违反宪法禁止性规定的法律后果。刑法以其最明确的禁止和最高强度的保护,为人格尊严提供了最现实和最有效的保障。
(二)我国现行刑法保障人格尊严的具体进路
我国刑法通过如下三条进路实现对人格尊严的保障。
1.树立了“罪刑法定”的核心价值。罪刑法定是各国刑法普遍规定的最高原则,在有的国家(例如法国)甚至成为宪法原则。我国1997年《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通过罪刑法定显现行为法律效果的预测可能性,既保障公民的行动自由,也保护犯罪人获得公正的刑罚。自由是人格尊严的最高价值,公正是人格尊严的内在要求。
2.确认了“被害人承诺”等基本制度。在我国刑法总则中,通过确认“被害人承诺”等正当化事由,从一般制度层面对自主和自我决定给予了最高强度的刑法尊重。自治是人格尊严的核心,自我决定权是人格尊严中与一般人格权联系最为密切的权利,若权利人基于自主决定允许他人实施损害本人权益的行为并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则排除该行为的犯罪性,这是各国刑法立法或者刑法理论普遍认可的正当化事由。被害人放弃自己的相关利益,正是行使其人格自由权利的表现,因为与放弃的利益相比,人格自由权利本身才是最高的利益。
3.设置了保护人格尊严的具体个罪规范。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对于人格尊严的保护主要体现为规定了侵犯人身法益和精神法益的犯罪③。相关罪名集中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所保护的人格尊严具体表现为生命权(由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侵犯)、健康权(由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所侵犯)、性自主权(由强奸罪所侵犯)、婚姻自主权(由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所侵犯)、人身自由权(由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所侵犯)、人身不可买卖权(由拐卖妇女、儿童罪所侵犯)、名誉权(由侮辱罪、诽谤罪所侵犯)、隐私权(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由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所侵犯)、通信自由权(由侵犯通信自由罪所侵犯)、选举权(由破坏选举罪所侵犯)等等。
二人格尊严是刑法介入尖端医疗的实质根据
现代医学的发展不仅为民事立法带来了人格权保护的新课题,更是给刑事立法提供了新的规制领域。生殖性克隆人、器官移植等尖端医疗技术从不同角度涉及和影响人格尊严,在相当范围内和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刑法介入尖端医疗的需求。从德国医疗刑法一百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医疗刑法的核心正在从传统的医疗行为不断延伸到尖端医疗领域,尖端医疗研究和运用中的刑事规制成为关注的重心[5]。
(一)学说争议
关于刑法介入尖端医疗的实质根据,理论界仍然存在相当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权益保障”是生命科技刑法的基本理念,但是,保障的仅是“人身权益”,且限于“基本生命权益”,具体包括生命健康权、人身完整性和人的自主权[6]108-110。笔者认为,该观点没有阐明“权益”的本质和范围,所列举的具体权利表现极为有限,既不能反映出新兴生命科技的特性,也无法解决其所引发的权利冲突和伦理困境。同时,该观点将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禁止商业化人体构件只是视作风险预防理念的产物,没有真正认识行为的实质危害和法益侵害。
有学者提出了“医事刑法法益”这一概念,认为现代医事刑法法益的核心指向是人格尊严和医事秩序,人格尊严涵盖了个体人格尊严和人类尊严,医事秩序是指对新型医疗技术进行刑事法规制所形成的秩序[7]48-53。笔者赞同该观点对人格尊严的理解,但是,人格尊严应当是刑法介入尖端医疗的深层理由和实质根据,而不是刑法所直接保护的法益。因为人格尊严是法益建立的基础,只有转化为具体权利才能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此外,医事秩序也不能与人格尊严相提并论,因为人格尊严是构建医事秩序的基础,医事秩序的目的就是维护人格尊严。尽管我国传统医疗犯罪将医事秩序作为首要法益,但是,在尖端医疗领域,医事秩序不能作为立法论上论证刑法介入的根据。
甲斐克则教授认为,医事刑法直接保护的法益,以国民的生命、身体和健康为中心,但是,医事刑法还包含了很多超越个人而成为人类共通问题的内容,在根本上涉及“人类尊严”这一本质命题;而且,“人类尊严”不是与人格(权)尊重相提并论的同一层次的问题[8]。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还将进一步论证,人类尊严和人格(权)尊重具有何种关系?
首先,“人类尊严”基本等同于“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人的尊严、人性尊严)在本体意义上侧重“个体”的价值,“人类尊严”则属于“集体”的范畴,但由于尊严本身在价值上蕴涵了整体权利的属性,所以二者不存在实质差异。在尖端医疗领域,有的行为(例如生殖性克隆人)表面上仅针对具体个人,但实质上最终将侵害人类全体。
其次,人类尊严是具体人格权利的上位概念。在制度层面,历经“人格尊严的宪法确认—宪法上的基本人权—部门法中的具体人格权利”这样一个渐次具体化和实定化的推演逻辑,人格尊严显然比人格权利更抽象、更基础,具有更高的价值。
最后,除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具体人格权利以外,还存在其他人格权利。私法上的人格权体系包含了各项具体人格权,尖端医疗还可能侵犯具体人格权以外的其他一般人格权④,例如自我决定权、人的独特性、人体器官的不可买卖性等。这些新型人格权随着尖端医疗技术的兴起而被人们发现和重视,与传统的具体人格权居于并列地位,作为医疗刑法的法益共同隶属于人格(类)尊严这一核心价值之下。
(二)尖端医疗中的人格尊严
尖端医疗的本来目的是延长寿命和改善生活质量,但是,它以迥异于传统医疗的方式深度侵袭人的身体甚至改变了人的产生方式,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刑法介入尖端医疗是对其带来的利益和引起的风险进行权衡取舍的结果,其权衡取舍的标准就是是否贬损了人格尊严。刑法将尖端医疗领域的相关行为入罪化,透过对具体法益的保护最终保障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证立新型法益的价值源泉,是解决法益冲突的终极理由,是将相关行为入罪化的最高标准。刑法以保护人格尊严作为介入尖端医疗的实质根据,人格尊严是尖端医疗刑法保护的最高价值。
各类尖端医疗技术研究和运用中的不当行为,可能从不同角度否定和贬损人格尊严。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将“人”设计出来,侵害了人固有的独特性、唯一性、偶然性;出售或者出租人体器官是将人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利用,侵害了人的主体性;辅助生殖中对胚胎等人体组织的损害,侵害了生命的潜在可能性;滥用基因技术和基因信息,侵害了人类的物种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和基因多态性。在这些具体法益中,独特性和偶然性是人格尊严的来源,生命是人格尊严的前提和基础,自由和自治是人格尊严的核心,身体是人格尊严的载体和依托。尖端医疗技术的不当运用对这些法益造成实质且重大损害时,刑法必须介入;否则,会造成刑法的保护不足,违背法治国家的基本原理。因此,立法论上首先需要对具体尖端医疗技术涉及的法益进行充分研究。
下面以生殖性克隆人和商业化人体器官为例展开论证。
(三)生殖性克隆人的科学研究
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尚处于研究阶段,对该行为的禁止实质上涉及科研自由这一基本权利。一种观点认为,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原因之一是不成熟的克隆人技术会产生具有根本缺陷的人[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即使技术成熟也不能克隆人,因为这本质上违背了人格尊严[10]110。尽管同样持禁止态度,但这两种观点所潜藏的深层动因和最终结论是不同的。前者着眼于技术层面,禁止应用的是不成熟的技术。易言之,技术成熟以后则是可以应用的,先期研究是技术得以成熟的必经之途,因而不应当禁止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的科学研究。后者则着眼于克隆人的本质,认为生殖性克隆人技术违背了人格尊严,无论该技术成熟与否均不得应用,因而一开始就应当禁止实施这样的研究。因此,生殖性克隆人技术与其他尖端医疗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于其他医疗技术的规制通常只及于应用阶段,而对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的规制则可能需要前置于该技术的研究阶段,这就引发了科学研究自由与刑法禁止的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在尊重科研自由的前提下,倘若科学研究与人格尊严发生了冲突,则产生了刑法规制科学研究的可能性。
首先,科研自由不是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应当符合自然法则和社会规范。一方面,科学研究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主要通过技术规范来实现;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也要遵守人类社会的基本规范,通常体现为科技伦理对科研人员的自律性要求,在必要时,法律也要做出有力的外部约束。例如,日本立法者基于对研究自由的尊重,很少在法律中直接将科学研究本身作为规制的对象,专业人士的良心和判断优先于政治和行政的判断与要求。但是,若重要的研究领域涉及到宪法保障的人格尊严和人类存亡,影响的层面和强度已经非一般研究可比拟,日本则会采取严格立法的方式来规制。因此,日本制定了《人类复制技术规制法》(ヒトに関するクローン技術等規制法),限制了克隆人研究的范围,从刑事上明令禁止研究人员逾越界限。
其次,生殖性克隆人研究因否定了人格尊严而受到限制。生殖性克隆人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因彻底改变了人的产生方式而使其丧失了固有的偶然性和独特性。独特性正是人区别于非人的、不能被改变的东西。在独特性的基础上,人格尊严还包括个体成员之间的对等和平等个体的相互敬重。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剥夺了人内心的独特性,破坏了人作为自在目的的地位,损害了人之间的对等性,先天地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格尊严,单纯靠伦理规范不足以宣示对该行为的反对态度,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予以禁止⑤。
最后,生殖性克隆人研究产生的巨大风险和诱惑需要强力的刑法限制。传统的科学研究往往是对已存事物的探索,主要是为克服各种有害于人类的风险服务。生殖性克隆人的研究则主要是对未存事物的创造,属于创设高风险的行为,它本身包含了有害于人类的无法估量的巨大风险,已经远远脱逸了人类可控的范围。与此同时,该技术能够带来重大的科学利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筹码,对于科研人员和国家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在这种情形下,其他规范的禁止均不足以阻止相关人员去冒险,只能通过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来威慑和预防此类高风险行为。
总之,科研自由是人的自由的一部分,也是研究者尊严的体现。但是,生殖性克隆人的研究,贬损和否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在地位,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主体的对等性,因而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人格尊严。正如《世界生命伦理和人权宣言》第3(2)条阐明的:“在科学和社会利益方面,个人利益和个人健康享有优先权。”生殖性克隆人研究因其颠覆性、风险性和利益驱动性,必须通过刑事立法明确予以绝对禁止,从而达到威慑和预防的目的。
(四)人体器官的商业化出售(出租)
器官⑥所有人基于本人的所谓“意愿”而出售(出租)自己身体器官的行为,一直被国际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为非法行为而加以禁止。关于禁止出售(出租)身体器官的理由,道德上通常采取如下两条论证路径。
第一条论证路径是,所谓器官所有人出售(出租)身体器官的“意愿”并非是自我决定权的体现。人基于金钱的理由出售(出租)本人身体器官,只是表面上的自愿,而不是真正的意志自由。认为人可以基于自愿出售(出租)自己的身体,是自由至上主义的自我所有权观点,即只要我拥有自己的身体,就能够自由地、如我所愿地出售我的身体器官[11]78。但是,若彻底贯彻该自由市场逻辑,则居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者在急需金钱时就只能出售(出租)身体器官,还不具备公平的议价能力,这样的选择并非真正的自由,这样的市场是对贫困者的掠夺。
第二条论证路径是,自愿出售(出租)器官的行为在客观上贬损了人格尊严。该观点承认出售(出租)器官的人是基于自愿做出的自我决定,但是,这种自愿行为将人贬低为、客体化为器官的集合体[12]120。无论对于出卖(出租)者还是购买(承租)者而言,都是将器官所有者视为工具,侵犯了本应作为目的的“人”的尊严。人的器官不能用金钱来交换,必须排除市场机制和商业规范的调整,出售(出租)者即使行使了自我决定权,也是无效的,不能成为使其行为正当化的理由。
上述两条论证路径反映了不同的道德理想,前者强调市场的完全自由性和公平性,后者则关注相关物品的道德重要性。笔者基于刑法学研究的视角,以尊重人格尊严为起点,在被害人承诺的制度框架下,从如下层面论证刑法禁止出售(出租)身体器官的理由。
首先,从根本上看,出售(出租)器官的行为是对人格尊严的贬损。德国学者Günter Dürig将人格尊严与意识、自决等概念一并加以探讨,并从反面阐述了人格尊严:“当具体的个人,被贬抑为物体、仅是手段或可替代之数值时,人性尊严已受伤害。”[13]719-720出售(租)器官的行为根本上违背了人永远是目的这一尊严的内核,侵犯了蕴含于身体之中的人格自由权利,不具有积极的现实社会价值。
其次,即使出售(出租)器官者行使的是自我决定权,也因为超出了可处分事项的范围而使得决定无效。自我决定权只适用于本人能够决定的事项,若对超出处分权范围的事项进行承诺,则构成自我决定权的滥用。权利人行使自我决定权体现了自由的意志,人的身体受到保护也是因为其中存在人格自由权利,但是,“只有在具有的积极的社会价值时,人格自由权利才能受到肯定,人格自由权利总是只存在于历史地形成的积极的现实社会价值中”[14]157。生命、重大健康等是个人进行自我发展的基础,是个人承诺不可放弃的法益,出卖(出租)者不能进行有效的承诺,从而无法排除其违法性。
最后,出售(租)器官的行为损害了公序良俗。器官作为人格载体具有道德重要性,本不应当进入市场,然而,器官交易却用一定数额的金钱来标示本当“无价”的器官。一旦器官成为在市场上买卖的对象,商业化就会排挤重要的、非市场的道德规范,直接冲击伦理上鼓励的、善的无偿器官捐赠。因此,器官交易不再只是单纯的买卖双方的私人合意,交易行为的存在会侵蚀捐赠者的义务感,削减人们的利他精神,降低捐赠意愿,破坏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器官交易的市场化将导致器官捐献减少,不但不能缓解反倒会加重器官短缺危机,甚至影响到器官交易以外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影响到他人和共同体的利益⑦。因此,商业化出售(出租)器官的行为已经不再纯然属于私的领域,由于进入了公共范畴而使得刑法规制必须介入。
综上所述,人出售(出租)自己的身体器官本质上贬损了人格尊严,其自愿的决定由于损害了自我发展的基础而超出了可处分事项的范围,并且损害了公序良俗。因此,出售(出租)者的“自我决定”是无效的,不能构成确立其行为正当性的根据。国家应当按照该行为侵蚀人自我发展和破坏公序良俗的程度,决定是否动用刑法手段予以规制。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增设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仅仅处罚“组织性”的器官交易行为,非组织性的“自愿”器官买卖,目前在我国不构成犯罪⑧。
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均将器官交易及其关联行为(包括买卖、中介、组织、帮助等)作为犯罪处理,并且多数立法将买卖器官罪规定为器官犯罪的首个罪名(例如德国、法国)。笔者坚持认为,基于器官的重要性和我国当前器官交易肆虐的现实,立法者有必要通过刑事制裁来有力地确认禁止器官交易之规范的效力,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出卖、购买人体器官罪”,同时,针对以牟利为目的的代孕(出租子宫)行为,有必要增设“商业性代孕罪”。
三风险社会中尖端医疗的刑法规制
“风险社会”概念由社会学界率先提出并且已经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为了应对“风险”而产生的“风险刑法”理论成为我国近年刑法学研究的“显学”。但是,在刑法理论界,对于何为“风险社会”之“风险”,“风险社会”如何转换到“风险刑法”的逻辑路径,“风险刑法”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对于刑法的基础理念和基本原则将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本文仅以“尖端医疗”为视角,论证其属于现代生命科技进步带来的、与人格尊严密切关联的新型风险,刑法既应当也能够规制这一具体领域。
(一)尖端医疗技术产生的风险均属于“风险社会”中“风险”的范畴
由于现代性的断裂,人类从古典工业社会突变至风险社会,其“风险”超越了传统的“事故”范畴,具有特定含义。贝克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导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15]19现代风险与古典工业社会风险的区别在于其“异质性”和“不可控性”,包括核技术、基因技术、恐怖主义等等。显然,不论现代风险的范围如何划定,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尖端医疗均具有现代风险的一切重要特征,是现代风险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尖端医疗的现代风险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主张构建风险刑法理论体系的论者,多从价值重心、保护法益、行为要素、主观要素、因果关系、归责原则等一般理论展开论述[16]。反对者则认为,风险的全球性、未知性、系统性和两面性均与古典工业社会的刑法存在对立,风险刑法理论无论如何颠覆传统,因为受制于古典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所以无法化解风险社会的风险,因而刑法应当反思,而且在科学和政治层面的反思完成之前,刑法的反思无法转化为具体的立法或者司法主张[17]。笔者既不同意“风险刑法理论”体系的一般构建,也不主张刑法只停留于意识层面的“反思”,理由如下。
第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倡导者围绕价值重心等一般要素建构所谓的“风险”刑法体系,不能成为与“传统”刑法并存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使作为原则的例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刑法理论体系内部本身就是原则和例外并存。当然,在面对新型风险时,可以围绕其特点形成刑法学研究的专门议题,但是,产生的理论和立法对策仍然必须恪守刑法和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否则“刑法的干涉就必须停止”[18]19。
第二,刑法已经超越了“反思”风险的阶段而开始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现代社会的风险虽然与古典工业社会刑法存在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已经有了相当的缓和。刑法具备的国际性、预防性、综合性和权衡性特征,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风险的全球性、未知性、系统性和两面性。实践证明,各国刑法和国际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了有力的规制,很多国家将生殖性克隆人、滥用基因技术等规定为犯罪。因此,对风险规制的讨论不能泛泛而谈抽象的风险,而是应当就各个具体的风险领域展开专门研究。并且,刑法的反思并不必然以科学和政治的反思为前提,相反,不同学科、不同层面的反思在很多时候是同步的,彼此促进并相互启发。例如,伴随尖端医疗技术的研究和运用,科学家、生命伦理学家、法学家以及公众会从各自的立场展开思考,观点不断碰撞和融合。科学和政治的反思不是必然有一个鲜明的“完成”标志,科学和政治很多时候始终存在歧异,更需要刑法以其“决断性”和“形式性”提供一条确定的规范标准。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尖端医疗,带来了“异质化”和“不可控”的现代风险,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尽管技术和风险是新型的,但是,其所触及的“人格尊严”却是根本和永恒的,这是刑法必须应对的重要议题。刑法的任务不是化解风险,也无法化解风险,即使规定了刑事禁止规范,也必然会继续存在“禁而不止”的行为。但是,刑法能够以最明确的姿态划定尖端医疗技术的边界,推动公众形成一致的价值判断;同时,刑法通过对尖端医疗犯罪处以最有力的刑罚,确认规范的效力,引导医疗参与者各方建立正确的行为模式。
注释:
①在国际公约和各国宪法中,相关用语有“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类尊严”等。有学者作了术语辨析,认为上述用语的意蕴基本一致,存在本质联系。参见:郑贤君著《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辨》,《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
②本文所称“尖端医疗”,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医学进步和医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深度介入身体和生命、乃至于颠覆生命创制方式,对人类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带来重要影响的医疗技术,具体包括人类辅助生殖、生殖性克隆人、人体基因技术、器官移植、变性手术等。
③对人格的尊重同样也意味着对他人财产的尊重,但是,现代法律更加关注人格权独立于财产权而存在的价值。因此,结合对人格尊严本质的理解和我国人格权法的规定,人格尊严的核心内容是个人的人身性权利和精神性权利。
④在人格权体系中,除了明确列举的具体人格权以外,还有体现了人格尊严的其他方面但未明确列举的人格权利,该类权利被称为“一般人格权”,已经获得了司法解释的确认。笔者认为,一般人格权理念对于理解尖端医疗刑法应当保护人的自主性、独特性、不可买卖性、性别的自我决定权等非传统法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⑤日本众议院关于《人类复制技术规制法》(ヒトに関するクローン技術等規制法)的立法资料阐明了“以保障人的尊严作为《人类复制技术规制法》的基本立场被认为是正当的”。参见:衆議院憲法調査会事務局.「科学技術の進歩と憲法」に関する基礎的資料.衆憲資第48号.2004-4-15.21.
⑥本文所称“器官”,原则上是指与人体健康具有重大关联的不可再生器官,具体包括内脏系统的肾脏、肝脏、胰脏、心脏、肺脏、骨骼、肢体,以及眼角膜、视网膜,等等,不包括血液、精子、卵子等可再生的组织和细胞。出售人体器官,主要是指器官交易;出租人体器官,主要是指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代孕。
⑦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的经典实例,是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比较英国和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所做的一项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血液采集全部来自无偿献血,美国则部分来自无偿献血、部分是血液银行从愿意卖血的人那里买来的。大量数据表明,英国的血液采集系统比美国运转得好。参见:Richard M. Titmuss. 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 NY:Pantheon,1971,pp.233-255.
⑧有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仅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说明立法者有意识地克服了对供/受体直接交易行为的犯罪化冲动。参见:董桂文著《人体器官犯罪的刑法规制——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分析解读》,《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M].王世洲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王晖.论人的尊严之理念与制度化[J].中国法学,2014,(4).
[3]朱庆育.民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郑贤君.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辨[J].中国法学,2012,(2).
[5]杨丹.医疗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刘长秋.生命科技犯罪与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7]刘维新.医事刑法初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8]〔日〕甲斐克则.医事刑法的基础理论[J].刘建利译.法律科学,2012,(2).
[9]刘长秋.刑法学视域下的克隆人及其立法[J].现代法学,2010,(4).
[10]〔法〕戴尔玛斯·玛尔蒂.克隆人:法律与社会(第三卷建议)[M].张乃根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1]〔美〕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是好?[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2]〔美〕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M].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3]李震山.论资讯自决权[C]//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
[14]冯军.被害人承诺的刑法含义[C]//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5]〔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16]魏东,何为.风险刑法理论研究综述[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5).
[17]南连伟.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J].法学研究,2012,(4).
[18]〔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苏雪梅]
Human Dignity’s Criminal Protec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ced Medical Treatment
YANG Dan
(Humanities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519070, China)
Abstract:Human dign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of constitution, and criminal law can provide the clearest prohibitions and most powerful punishments to protect human dignity directly and effectively. If advanced medicine is implemented improperly, it will be in contradiction with human dignity, which becomes the essential base and ultimate reason for criminal law’s regulating.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isky society that how to apply criminal law to regulate advanced medicine and its related actions.
Key words:advanced medicine; human dignity; criminal protection; risky society
收稿日期:2016-02-11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尖端医疗领域的刑法理论及立法对策研究”(10CFX025)和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丹(1978—),女,贵州安顺人,法学博士,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比较刑法学、医疗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F6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0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