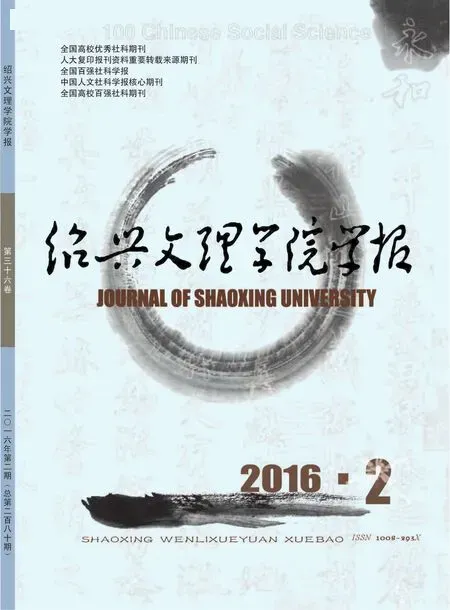贺知章的价值:对《回乡偶书》的再思考
张东华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与设计艺术学院,浙江 绍兴321000)
贺知章的价值:对《回乡偶书》的再思考
张东华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设计艺术学院,浙江绍兴321000)
摘要:在中国文化史上,贺知章以一首《回乡偶书》为世人所称颂,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同时代的诗人。本文试图透过诗文内容从社会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贺知章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原因,即此诗描述了传统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传达了一种普遍观念;而贺知章的成功之处在于用诗化的语言对常识理性的描述,这也是唐代诗人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贺知章;《回乡偶书》;游学;常识理性;佛道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贺知章(659—744)既不是一位著名的儒生,谈不上显赫的官位和政绩,也不是如李白、杜甫那样引领时代诗风的大诗人。贺知章在《全唐诗》中只有19首,远无其他诗人传世诗作之多。那么,为什么贺知章的名字如李、杜那样一直被后世所称颂,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同时代的诗人呢?笔者认为,贺知章之所以有如此长盛不衰的影响,完全是因为他的《回乡偶书》。
《回乡偶书》第一首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第二首云:“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然而,此诗文句浅显易懂,历代笺注家对其注述不多,现代学者也极少研究[1]。那么,凭什么此诗能产生如此经久不衰的影响?难道仅仅是因为浅显易懂吗?可见,此诗的价值远未被充分挖掘。本文试图从社会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探讨。
贺知章《回乡偶书》第一首从表面上看,非常容易理解:写诗人久客他乡,垂老回家而无人相识,这是一种对人生经历的事实描写。即此诗是对人之常情的描写,加上措辞的浅近,在历史上多作为幼儿识字的启蒙教材。然而,此诗的内涵意蕴由于时代的变迁而沉淀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多数现代学者只是从现代观念出发解读此诗,有人从诗文的“笑问客从何处来”中读出了贺知章爱玩爱闹的秉性;有人根据诗的背景知识:37岁前离乡,86岁回乡,回乡不到一年即驾鹤仙去,而认为此诗传达了一种悲苦情节。种种解读,意味着此诗可以为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经历的人理解和感慨。
然而,从深层的思想史层面考察,此诗描述了传统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传达了一种观念,而这种现象和观念引起了历代文人的共鸣,一直持续到现代。
一、少小离家老大回:儒生的游学、宦游生涯
作为一个儒生,从“少小”(37岁前)离家到“老大”(86岁)回,长长50多年离家,诗人用短短的七个字来描写他一生的经历,充满想象的空间。那么,诗人在外做什么呢?
那就是古代儒生游学、宦游的人生历程,即儒学八条目中的“治国平天下”对古代儒生的要求。这是古代儒生的普遍行为,是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体制下的普遍现象,因为维系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国家的组织力量就是儒生(士)阶层。
在古代中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马克思对欧洲小农经济的分析时指出:“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往。”[2]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古代农民的分析:一种社会制度,如果只有自耕农、农奴、地主、商贩、皇室、贵族等阶级,只能组织成一个割据性质的封建小国,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就是这种形式的呈现。如果古代中国与中世纪欧洲一样,除了自耕农、佃农、地主、商贩、皇室、贵族等阶级外没有其他社会成分,那么,中国的小农经济形态也将由一个个互不来往的、分散的宗法村社组成,秦始皇建立统一帝国前的中国社会就是这种分裂割据状态下的社会结构。然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口频繁流动;政治结构中也出现了以郡县制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士”这样的一个特殊阶层[3]——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有少数来自于农民)为核心的“游士”阶层。从文献史料看,“士”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活跃,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就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描述。“士”是一个以受教育服务社会为主要特色的知识分子集团,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不那么强调身份等级。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和此后的延续,与“士”这个特殊的阶层的存在关系密切。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执行着主要社会联络功能的就是“士”这个特殊阶层,通常称为儒生。由于地主阶级优越的经济条件为他们提供了游学、宦游的资本,使他们可以从小饱读诗书,熟习儒家经典,或游山玩水、千里迢迢求师访友,或苦读于深山书院,与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虽然这个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他们的流动性极大,组织能力也极强。一旦他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就有可能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成为国家官员。需要强调的是,他们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学问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的[4]。历代王朝就是依靠这个官僚(儒生)阶层组成的巨大官僚机构,上令下达,维护封建大国的统一。贺知章的游学、宦游生涯,正是这些特点的反映。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唐武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中进士,时年37岁。景云二年(711)至先天二年(713)间,得族姑之子陆象先的引荐,授国子四门博士,后迁太常博士。开元十年(722),因宰相张说举荐,与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同入丽正殿修撰《六典》及《文纂》等书,后转太常少卿。开元十三年(725),升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开元十四年(726)改为工部侍郎;开元二十六年(737),李亨立为皇太子,贺知章迁太子宾客,授秘书监。天宝二年(743)冬,因病上表请为道士,求还乡里。天宝三年(744)还乡,不久离世。
由于史料缺载,贺知章具体的游学、宦游经历不是很清晰。然而,以“清官”著称于世的明代海瑞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以举人出身进入仕途。至万历十五年(1587)卒于任上[5],前后34年,迁13次之多。贺知章、海瑞的游学、游宦生涯就是《回乡偶书》中所描写“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情境,这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此诗生动地描写了古代知识分子(儒生)因游学和宦游从小离家远行,老年荣回归故里的复杂心理。这不但是贺知章个人游宦生涯的写照,更是古代儒生阶层的内心独白,能不引起古代儒生阶层的共鸣吗!
二、乡音无改鬓毛衰:唐代士人的佛道思想
众所周知,自从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后,魏晋时通过玄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合流而成为传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佛教出现入世转向,其标志是禅宗成为佛学流派的主流。禅宗教义表明成佛不一定要出家修行,日常生活也可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经过入世转向的佛学在唐代的大发展,成为唐代士大夫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一时期,儒生多在寺庙里念书,儒生对僧侣的关注十分普遍。如著名的“推敲”典故虽然讲的是诗人贾岛应试前借居京师时与韩愈的故事,但诗中描写的却是僧侣的生活情状,可见儒、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如《续高僧传·释慧荣传》载:“十五辞邻故,五十还故邻。少年不识我,长老无一人。”*释道宣《续高僧传·释慧荣传》卷八,载《大藏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87页。此偈语与《回乡偶书》第一首的内容,无论是诗文结构,还是思维方式都十分相似。“十五辞邻故,五十还故邻”与“少小离家老大回”所表达的内容几近同一。而“少年不识我”与“儿童相见不相识”,二者的诗意更为接近。根据文献推断,慧荣是贺知章的前辈,而且是同乡。《旧唐书》说贺知章是“会稽永兴人”,《新唐书》说他是“越州永兴人”。而《续高僧传·释慧荣传》说慧荣是“会稽山阴人”。隋唐时,越州包括会稽、句章、剡和、诸暨四县,而会稽县又由南朝时期的会稽四县即山阴、永兴、上虞和始宁组成。另据《续高僧传》载:“(慧荣)梁高祖大通年,辞亲出听……年至五十,门人亦尔。乃大弘法席,广延缁素……后与诸徒还归故邑。”在唐代佛学大繁荣的时期,慧荣“与诸徒还归故邑”也必定“大弘法席”,同乡高僧对他的影响也是情理中的事。即使不是同乡,随着慧荣讲悟的范围扩大和门弟子的宣传,后世受其影响也属正常。慧荣的这首偈语贺知章可能熟知。《回乡偶书》所包含的佛学思想也可以用另一个佛教故事来求证。后秦释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说:“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邻人皆愕然。”*释僧肇《物不迁论》云:“是以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虽静而常往,故往而弗迁。……是以观圣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见得也。何者?人则谓少壮同体,百龄一质。”见释僧肇《肇论》卷一,载《大藏新修大藏经》第45册,第151页。这里的“白首而归”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叙述方法和写作思维模式十分相似。而“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与“乡音无改鬓毛衰”所传达的思想意识完全一致,这就是佛教义理中“变”与“常”的观念,即《物不迁论》中所说的“少壮同体,百龄一质”和“徒知年往,不觉形随”的观念。贺知章通过对身体外貌特征的改变和“乡音无改”的事实描写在不经意中传达出了“变”与“常”的关系,抒发了人事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这是佛道笼罩下的唐代士大夫的普遍思想。而这种思想直指唐代士人的人生观:“外无物,内无我,一是归于涅槃”[6]的佛学境界。《回乡偶书》很可能是受佛家偈语的影响而发的感慨。
其实,对于一个僧侣来说,讨论肉体的“归”与“不归”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佛学的时间观念是由主体意向性建构而成的,时间只是心识活动的体现,与现实的时间概念无关。但对于一个儒生来说,则意义重大,“少小离家”是儒生践履“治平天下”的开始,而“老大回”意味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是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下的特殊产物,对于普通地主或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意义特别重大。
三、笑问客从何处来:唐诗中的常识理性思维
在轴心文明中,与西方的工具理性不同,中国文明以常识理性为正当性依据。常识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经历、感受或时时见闻的,以至于熟视无睹的现象,或约定俗成的规范。常识理性可分为人之常情和自然现象常识两个出发点。人之常情是指那些与人的行为有关、人人知晓并普遍遵行的行为方式。在古代中国,人之常情合理就是符合道德规范。而自然现象常识是指不必追溯一存在或现象背后的原因,把常识看作本来如此,天然合理,不需要解释的东西。如中国人不可能像牛顿那样去问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这样的问题,不大可能去追问自然现象背后隐藏的自然之谜。如果把这种思维方法推广到整个常识领域,即是视常识为天然合理的精神。虽然早在先秦道家和儒家中已具备视常识和人之常情为合理的因素。但是在道家思想中,“自然”与“无为”是不可分离。而孔孟对宇宙论不感兴趣,先秦儒家尚未建立天人合一结构,人之常情合理和常识合理尚未成熟为论证万物的理性精神。“只有到隋唐以后,中国士大夫才真正找到对抗迷信的思想武器”,而“儒学的复兴使得中国社会又一次获得整合辽阔农业社会、建立大一统帝国的组织力量。随之而来的是隋唐盛世,常识理性正是在这一时期成长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金观涛说:“隋唐之后,每当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过分迷信或丧失常识理性时,就会有一些儒生用常识合理对意识形态批判和重构,遏止迷信的泛滥。”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6、67页。。
从整首诗看,诗人就是通过对常识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垂老回乡的复杂心理。第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描写的是少年外出游学、游宦,年老还乡,表现的是一种时间的流逝。第二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描写的是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老去的状态,毫不虚设夸张。第三句“儿童相见不相识”意为由于长年游学游宦在外,以至于老年荣归故里时却无人相识,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状态。第四句“笑问客从何处来”,承前一句,表达的是特定状态下人的行为模式——“笑问”。全诗非常理性且合乎自然,如从心底中流出,从诗中我们感受不到迷信色彩的存在。赵明华在《唐诗原来可以这样读》中说:“全诗二十八个字中无一生僻字,不用一个典故,都是家常话。”[7]明代唐汝询《唐诗解》亦云:“模写久客之感,最为真切”。虽然《回乡偶书》的内容言如家常,但可以层层追索,字字补充,而且句句都在人之常情(常识理性)之中。
在唐诗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表面看就是作者傍晚登楼时所见之景的事实描写。全诗二十个字,也无一生僻字,不用一个典故,但是诗中所传达的意境却是让人回味无穷。骆宾王七岁时的《咏鹅》也是如此。然而,重要的不是诗人们写了此诗,而是人们对诗的认可和传唱,可见唐代常识理性已深入人心。唐诗中流传最广、最为久远的多为对常识的描写和抒发,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常识理性为主要思维方式的社会。
四、近来人事半消磨:唐代士人的儒佛两面性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从《回乡偶书》第一首可以看出唐代士大夫的佛道思想(道家思想在唐代与佛学相似)。而唐儒佛道两面性的人格在《回乡偶书》第二首中非常突出。
《回乡偶书》第二首前二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承前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描写了诗人从离乡别久和自身的衰老,联想到世事的变迁。几十年的宦游生涯,抵挡不住家乡人事的“消磨”变迁。其意与上文分析的后秦释僧肇《物不迁论》的观点十分相似。而“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则更进一步点明了佛教教义中“变”与“常”的玄理,更是贺知章思想的体现。这里的“春风”表示时序的更替和时光的流逝,年年春风,四季循环,而湖波依旧。“波”的运动,加上时间的流逝(“旧时”),却无法改变“门前镜湖水”的永恒。在诗人流动的时间意识里,萌生永恒不朽的意念,由此而感慨人世沧桑,岁月,人生如梦。即年轻时的宦游,所谓的建功立业到头来只是人事的“半消磨”,还不是归去“修道”,忘却世事的纷争,寄身自然。这样就可以与自然永恒同在,从而又回复到唐人惯有的“涅槃”之境,或道家的“逍遥”之境。白居易晚年散尽家财、遍造净土也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贺知章晚年因病上表请为道士,即是佛道人生观“归于涅槃”的确证。而这种人生观,投射到社会生活中,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这种消极人生观的产生,其根源是在常识理性和佛道人生观的影响下,“儒家道德变得世俗化。儒生除了追求事功(为帝王服务)之外,别无他途来实现道德理想。”*同第16页注①。大多数唐代儒生在为帝王服务时是儒家,考进士、做官需要读五经;“他们只要一谈到修身,其内容几乎只是重复佛教的论述。”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很形象地描绘了唐代士人儒佛两面人的心态,“……投牒自试,以图出身。不中则寄食僧寺,取径终南;中式则上书权门,苦求官禄。盖此辈将伫进之事纯视为谋生之途。对国政民生之利病,并无主张,且多未用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在唐代即为极罕见之事”[8]54。我们很难从现有资料判断贺知章是否是这种唐代典型的知识分子,但贺知章《回乡偶书》第二首也多少反映了唐儒的这种中仕“苦求官禄”、不中(逆境)则“取径终南”的、消极的人生态度。在这里,儒家倡导的、儒生所具有“治国平天下”和“教化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荡然无存。难怪劳思光批评唐代士人的道德品质低下。
而宋代的儒生在诗文中却表现出极高的道德风尚,与贺知章同乡的宋代诗人陆游在临终前所作的《示儿》诗中表现出何等的社会责任意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至死都不忘家国大事,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与贺知章所表现的“近来人事半消磨”有着天壤之别。故劳思光在评论唐代知识分子道德普遍堕落的同时盛赞宋人的责任意识。宋代知识分子“未登仕籍,已忧天下,既入政府,则有所主张,……知识分子之责任感,在唐代即为罕见之事,在宋代则为寻常之事也。”[8]54这可能就是更多地传达常识理性而很少涉及人生观的《回乡偶书》第一首为人熟知,而表明其消极人生观的第二首则少有人知的原因。纵观唐代诗文,对于大多数唐代诗人来说,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是那些较少反映其人生观(价值观)的诗文,一涉及价值观,就马上表现出其儒佛两面性的特点,也就是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
然而,就诗而论,在佛教“冥想”思维的作用下,诗人是在悠远开阔的时间和空间的遐想中,形成了一种美丽深邃的艺术境界。这就是唐人的诗文为什么“心中有天机,笔下有造化”的真正原因。
五、打油诗:“境界”的缺失对现代诗歌的影响
“意境”或“境界”是诗的灵魂。没有境界就没有诗。纵观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从诗经、汉赋(严格地说赋不是诗歌),一直到唐诗、宋词,从此就一步步走向衰落,而到现时代只剩下打油诗。据传2014年的鲁迅文学奖诗歌类评奖,获奖的作品与打油诗相类,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究其原因,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在当下的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中越来越缺乏“境界”这个形而上的层面。先秦诗歌(诗经)得益于周代文化中族群传统与宇宙法则和价值的融合。而周代文化中的这种融合正是中国文明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源头,因此,先秦时的一部地方民歌和官方乐歌组成的诗歌总集——《诗经》,西汉时就被尊为儒家经典。而诗经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和宇宙变化法则正是其可以想象的境界之所在。汉赋恢宏的气势实与汉代宇宙论儒学——天人感应学说相对应。如扬雄的《甘泉赋》:“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文意诡异,诘屈难懂,但给人以天马行空、气势磅礴而又耐人寻味之感。其实这是由于汉人处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论的境界之中造就的。如果撇开此一境界层,扬雄此赋描写的就是皇帝出行时的场景。而从汉末起,伴随着佛学的传入,佛学的冥想思维也慢慢深入人心。由于唐时佛教的入世转向,使得常识理性趋于成熟。我认为唐诗的境界是由“冥想”思维和常识理性共同作用下的产生,如前述王之焕的《登鹳雀楼》,一方面是对事实(常识)的描写,另一方面又境界开阔。如果没有“冥想”的思维模式,是不可能出现“欲穷千里目”这样的境界。但是,唐诗与汉赋的表达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唐诗给人的感觉是贴近生活(常识)。贺知章的这首《回乡偶书》就是对常识的记录。与唐代佛学的偈所表达的内容十分相似,但与追求空无之境的佛学偈言是完全不同的。与前述释慧荣偈语相比,贺知章的诗更自然,更接近生活,意境更优美,这是常识理性在儒生思维中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儒释已出现融合。宋代(程朱理学)是儒道释三家思想合一的时代,孔孟儒学得以复兴。而天理世界的存在和朱熹“半天静坐,半天读书”的修身方式,使得通过“冥想”的形而上的“境界”得以突显。宋人的这种思想意识使得宋词在“大江东去,浪涛尽”的豪迈中多了一分忧国忧民的思想。而随着清代实学(考据之学)的兴起,清儒在反思宋明理学中,否定儒生修身对天理世界的冥想,境界层面被破除,中国的诗歌也随着境界的缺失而走向生活化。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的冲击,各种思潮在五四时期激荡,诗歌也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诗在五四后广泛涌现。五四以后的诗人们正是怀着忧国忧民的道德理想而抒发创造理想社会的热情,诗之境界也十分高远,影响深远。我们只要看看那一时期的诗词就可以知道诗歌的境界。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泛滥,境界层开始缺失。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出版的自由化,一方面带来诗歌的繁荣,网络诗歌流行,好像谁都能凑上两句,谁都能出版诗文集;另一方面却在成千上万的网络诗歌和无序的出版热中湮灭了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这是现阶段造成把打油诗看作优秀诗歌的重要原因。这是文艺界非常痛心和无奈的事。
但是,现阶段,随着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梦”的提倡,势必为诗歌的重新繁荣营造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理想环境。何为“梦”,《说文解字》云:“梦,不明也”。梦的本义指睡眠时局部大脑皮质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而引起的脑中的表象活动,如《墨子·经上》:“梦,卧而以为然也。”汉王充《论衡·死伪》:“且梦,象也。”也指“想象、空想和幻想等”。杨倞注:“梦,想象也。”想象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思维方式。当然,想象可以指向善,也可以指向恶。而指向善的想象,就是境界。这就是习主席在提“中国梦”时要附加“传递正能量”一个限定条件的真正原因,这样又可以重新找回诗歌所需要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郭预衡.诗歌精品[M].徐俊,曲江,评注.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119-120;金霞,李传军.从《回乡偶书》谈贺知章的信仰问题[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1):76-8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3.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25.
[5]海瑞年表[M]//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257-268.
[6]钱穆.理学与艺术[M]//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37.
[7]赵明华.唐诗原来可以这样读[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87.
[8]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三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林东明)
The Value of He Zhizhang: Rethinking about Poem On My Returning Home
Zhang Donghua
(Shaox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In th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e Zhizhang has been compliment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because of his poem: On My Returning Home, his influence surpassing the other poets of his time. From the soci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 paper means to discuss the causes for his ever-lasting influence: the poem describe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conveys a universal concept. His success lies in the poetic language utilized to convey common sense and rationality. This is a mode of thinking typical of the poets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He Zhizhang; On My Returning Home; study tour; common sense and rationality; Buddhist and Taoist thought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2-0014-05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2.003
收稿日期:2015-12-16
作者简介:张东华(1967-),男,浙江嵊州人,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与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