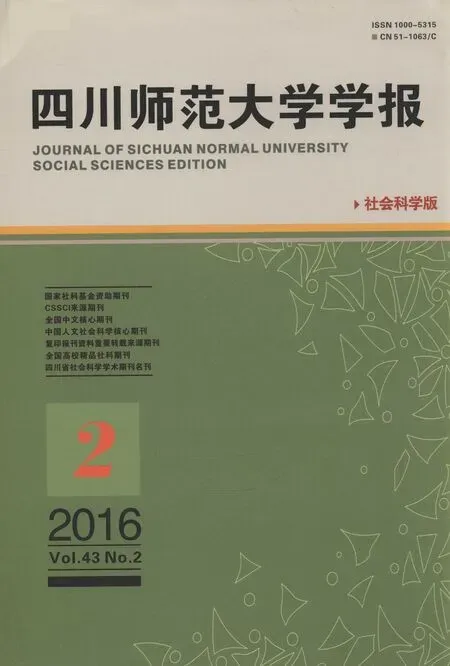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
曹 鹏 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成都 610071)
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
曹鹏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成都 610071)
摘要:北宋初期,蜀地动乱频仍,以致给人“易动难安”的印象。进入北宋中期,蜀地政局长期稳定,时人对蜀地的观感有所改善。北宋末年,赵谂之乱事发后,蜀地再次遭到宋廷的猜忌和防范。时至南宋,随着蜀地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蜀士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稳步提升,“蜀人好乱”之说逐渐沉寂,蜀地形象彻底改观。蜀地形象的嬗变过程,堪称中国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发育过程的缩影。
关键词:宋代;蜀地形象;易动难安;蜀人好乱;嬗变过程
两宋时期的四川地区,虽然行政机构名目不一,辖区分合不定,但总的趋势是一个位于川峡四路之上的开始走向实体化的一级行政建制,“四川”之名也逐渐固定下来[1-3]。与之相应,宋人往往把四川地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单元,并习惯性地在这一层面考虑相关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宋廷在四川地区实施的特殊政策,而这些针对蜀地的特殊政策与时人对蜀地的认知又不无关系[4-7]。由于北宋初年一系列动乱的刺激,朝野上下一度认定蜀人好乱[8-10]。此后,随着时局的发展,蜀地的形象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本文①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集中考察蜀地在两宋时期的形象,力求勾勒出其动态发展的轨迹,以期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时期政治中心与边缘地区的互动与融合过程。
一“易动难安”:北宋时期的蜀地形象
北宋平蜀之后的30多年间,蜀地变乱频生,各类反宋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乾德二年(964),宋廷兴师伐蜀;次年正月,后蜀皇帝孟昶奉表请降。但由于入蜀宋军军纪不整,次月即有后蜀军校上官进“啸聚亡命三千余众,劫村民数万,夜攻州城”[11]148,其后更是爆发了以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为首的兵变,蜀地再罹兵祸。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宋廷拟伐北汉,宰相卢多逊即指出:“西蜀险远多虞,若车驾亲征,当先以心腹重臣镇抚之,则无后忧。”[11]458淳化二年(991),宋廷准备增加蜀地赋税,监察御史张观则以“远民易动难安”[11]711为由上疏反对。事实似乎也证实了他的忧虑。三年之后,即淳化五年(994),李顺破成都,称大蜀王;至道二年(996),王鸬鹚起事,称邛南王;咸平三年(1000),王均发动兵变,占据成都,称帝建元。时人吕陶谓之“七年三乱”[12]144。这一时期,蜀地动乱规模之大,绵延之久,远非其他地区可比。面对蜀中动荡不安的局势,即便是治蜀名臣张咏(946—1015)也不得不感叹“从来蜀地称难制”[13]24。
何以变乱屡生于蜀地?对于这一问题,当时舆论多归咎于蜀地民风。梁周翰(929—1009)即认为蜀民“多犷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13]80。而在宋祁(998—1061)、欧阳修(1007—1072)等人的笔下,蜀人“喜乱易摇”[14]804或“轻而喜乱”[15]463,则进一步成为各类循吏们做出卓著政绩的背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史事: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十一月,镇守益州的梁武陵王萧纪准备率兵东下,平定侯景之乱,其兄湘东王萧绎以书止之,书云:“蜀人勇悍,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16]5056其中的“蜀人勇悍”,不见于此前史籍。揆诸《南史·梁武帝诸子传》之记载,“蜀人勇悍”原作“蜀中斗绝”②。从“蜀中斗绝”到“蜀人勇悍”,其着眼点从地理形势转向社会风习,所指大不相同。身为宋人的司马光,大概有见于北宋前期蜀地动荡不安的形势,并深受彼时舆论的影响,产生了“蜀人好乱”的印象,于是就将这一主观认知投射到了历史记载中。《资治通鉴》中“蜀人勇悍”的说法,虽然未必是历史实相,却准确地反映了时人对蜀地民风的整体观感。关于这一问题,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1048—1125)与苏轼(1037—1101)之间的一段交涉也值得玩味。元祐初年,刘安世与苏轼两人同朝共事。当时,“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身为蜀人的苏轼(1037—1101)听到这一说法后自然大不乐意,“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刘安世应声答道:“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苏轼居然闻之“默然”[17]159。两人的争执牵涉到当时的党争,可暂置不论。但刘安世的言论并非逞一时口舌之快,他一贯认为“两川之俗,易动难安”[18]201,这是他所谓中人以下易受土习熏染的前提所在,也代表了朝野上下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以言辞敏捷著称的苏轼,也感到难以辩驳,不得不为之气短。
朝野上下既然对蜀中民风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其应对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事实上,北宋朝廷确实采取了不少针对四川的特殊政策,如禁止蜀人及宗室子弟在本地任职,禁止入蜀官员携带家眷同行,守蜀官员有便宜行事之权等[5]154-164。名臣张咏最早获得便宜行事之权。他首次知益州,临行面奉宋太宗谕意:“西川经贼后,民颇伤残,不聊生,卿去到后,可便宜行事,钦哉!”入蜀之后,张咏果断行使了这一权力,“其有从权而合义者,先行后奏”[19]71。此后,赋予蜀帅便宜行事之权的政策就一直延续下来。如蜀人文同所言:“国初以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20]622而“便宜行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典治蜀。据范纯仁等人的记载:“蜀经王均、李顺之乱,人易动。先是,许守将以便宜,多专杀立威,虽小罪,或并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路,丁壮逃而为盗者甚众。”③[21]709范镇也注意到:蜀中“为政者务为威猛击搏以操切之,民有轻犯则移乡,甚者或配徙内地,终身不复还”[22]161。官长以杀伐果决为能事,难免会酿成冤案。天圣年间,知益州程琳将祭灌口神的表演当作民众造反,于是,“捕其首斩之,配其社人于内地,道路或以为冤”[11]2547,即为显例。
对于朝廷的特殊化政策,蜀中士人颇有微词,但彼时朝野上下“蜀人好乱”之说甚嚣尘上,不便直接反驳。于是,部分蜀士退而求其次,一方面承认蜀地民风确实不佳,另一方面则强调并非蜀人天性如此,而是牧守施政不善的结果。郫县人张俞(1001—1065)就曾指出:“益为西南之都会,外戎内华,地险物侈,俗悍巧劲,机发文诋,窥变怙动,湍涌焱驰。岂其性哉?守之者非其道也。”[23]452又云:蜀地向来被认为“其俗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骄,吏袭而奸,民伺而暴”,然而“穷焉察焉,得非吏师之过乎”[24]455?双流人宋右仁亦云:“蜀始以僻陋险隘,人民夸诳,古谓难治”,虽然如此,但“地有常形,民无常性,繇上之化,所从而正”[25]929-930。也就是说,蜀地多乱的症结在上而不在下。
也有蜀士声称蜀人天性良善,蜀中多乱与蜀人无关。早在五代时期,因孟知祥据蜀不臣,后唐明宗“颇以蜀人为疑,凡高赀有力者,尽令东徙”[26]788,蜀中隐士张立因此赋诗以讽,云:“朝廷不用忧巴俗,称霸何曾是蜀人!”[27]261就表达了这一看法。张唐英是张立的后人,他继承了祖上的观点,在其《蜀梼杌序》中指出:“……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下于蜀者。”[26]787-788前文提到的那位张俞,面对外人时尚且承认蜀地民风确有可议之处,但在为乡党杨钧送行时,口气却大不相同,称:“谈者谓蜀之地岩险,其民峭急剽速,治不可恩,宜一中以刑,且无事。……为吏者不去邪以自讼,而反咎之于民,无乃暴己之狠而怒彼羊之斗乎?古人谓,上失其道而民散,予犹过之,今乃信然。”[28]453其中“暴己之狠而怒彼羊之斗”一语,充分表露出蜀中士人面对朝廷猜忌的愤懑之情。关于这一点,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所见略同。嘉祐四年(1059),苏轼向时任成都知府王素进言,认为长期以来守蜀者治以重典,导致“民怯而不敢诉,其诉者又不见省,幸而获省者,指目以为凶民,阴中其祸”[29]5222,以致民怨郁积,亟待纾解。而在苏辙看来,蜀人平素“畏吏奉法,俯首听命”,受辱则含垢忍耻,积怨一旦爆发,则“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怨愈深,祸愈大,故蜀地之乱其实是朝廷措置不当有以激之,并非蜀人天生“有好乱难制之气”[30]1619-1620。元丰元年(1078),苏轼还曾为其故里眉州的民风辩解道:“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如果牧守既明且能,则州人循规蹈矩,终日寂然,若牧守为政无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究其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问题的关键在于施政得当与否[29]1112。苏氏兄弟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对朝廷治蜀政策的不满,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言论,正是对彼时流行的“蜀人好乱”之说的回应。
上述认识不仅限于蜀士,一些入蜀任职的官员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至和元年(1054),出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就说:“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在任期间,张方平“以齐鲁待蜀人”,政声颇著[31]354。川峡四路幅员辽阔,内部差异也非常明显,成都、眉州、嘉州等地向来人文荟萃,而夔州路则属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32]98-101。绍圣三年(1096),青州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市)人王辟之(1031—?)知忠州,发现当地“民情尤为倔强,白香山所谓‘吏人生硬都如鹿,城市萧疏只抵村’,迄今犹相延未化也”,但他对于移风易俗显得信心十足,认为:“牧者更刻程以课,计月以稽,讵浇漓者不能使之厚,乔野者不能使之文,穷乡僻壤不能化民成俗,进于声名文物之邦耶?”[33]卷十二中,1-2值得注意的是,王辟之此前在《渑水燕谈录》④中谈及蜀地时尝谓:世人皆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历史上割据蜀地者多为外人,至于本朝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实因官府需索无度,亦不宜归咎于蜀人[34]105。王辟之在忠州期间拊养良善,锄治奸猾,治声翕然[35]954,与他对蜀地的认识不无关系。
自北宋中期以来,蜀地政局长期稳定,似乎也从另一方面印证着张方平等人的看法。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往的特殊治蜀政策开始松动。张咏和赵抃同为治蜀名臣,前者“严明为政”,后者则“简易临民”[36]921。赵抃能以宽治蜀,显然与蜀地承平日久的局面有关[37]477-478。神宗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诏川峡四路不得将家属赴任法,其除之”[11]7985。至此,宋廷明确允许入蜀官员携带家属同行。对蜀地而言,这一政策意味着能够获得与其他地区同样的待遇,无疑是蜀人形象改善的积极信号。
然而,上述局面却被一个偶发事件猝然打破。建中靖国元年(1101)九月,渝州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人、太学博士赵谂谋反事发。对于这一事件,宋廷的处置十分严厉。时任谏议大夫的彭汝霖,“鞫赵谂反狱,穷其党与”[38]10976。近年新出的《王蘧墓志》也透露了朝廷处置该案的若干细节:赵谂被告发后,时任夔州路转运判官的王蘧驰诣渝州;在此之前,赵谂及其同党已被擒获,而夔州路提点刑狱杨挺“乃一切宽假”;王蘧查明赵谂谋反情状,“乃并其党钳锢讯治,狱既具,槛送谂等京师,下御史阅实”;最终,赵谂被诛杀,而“杨挺卒死制狱,前后两路官吏亦坐不觉察,而独公(王蘧)有旨原罪”[39]43。王蘧从严治狱,颇受朝廷赏识,他因此得以免遭杨挺等人的厄运。
赵谂谋反事件令朝廷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宋史·席旦传》载,“自赵谂以狂谋诛后,蜀数有妖言,议者遂言蜀土习乱”[38]11016,刚刚沉寂下去的“蜀人好乱”之说又被频频提及。据《夷坚志》记载:“崇宁三年(1104),成都人凌戡诣阙告言:‘蜀州新津县瑞应乡民程遇家葬父母,其坟山上常有火光紫气。’诏下本郡,令速徙它处。仍命掘其穴成池,环山三里内,自今不许墓域,郡每次季月差邑官检视。”[40]397事情看来并不是洪迈的杜撰。因为当年这位凌戡确曾入京,他的同乡张商英(1043—1121)还有一篇《送凌戡归蜀记》传世[41]415。而凌戡带来的消息,可能就是《宋史·席旦传》文所谓“妖言”之一。对于凌戡的上言,宋廷显然没有等闲视之,其应对措施可谓雷厉风行。同样,在崇宁三年,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命其子李倞代为点检州学学生答策。李倞在代为点检策卷时,发现邛州士人费乂策卷中“言多诽谤,至不忍闻”,“虑蜀中狂人复生”,于是将此事告知其父李孝广,孝广随即上奏朝廷,“始以为不过重罚屏斥不齿,足以劝励。既而勅下,窜乂海外。视之,乃一村邑陋儒,不识时忌,所以然耳”⑤[42]196。朝廷既然有从严处置的倾向,这类冤案也就在所难免。
官至太学博士的赵谂,居然阴谋造反,影响所及,朝野上下再次以异样的眼光打量来自蜀地的士人。如眉州人王腾所言:“自赵谂狂图,好事者类指以疵蜀人,蜀之衣冠,含笑强颜,无与辨之者。”[43]12可见彼时蜀士的尴尬处境。王腾又述及当时朝野流言:“谓贼谂以来,朝廷至疑蜀人,故取之与天下同,用之与天下异,众口相扇,互同一说。”⑥[44]98这样的氛围,不仅使普通士子备受猜忌,即使身居高位的蜀士也感觉到了压力。崇宁三年(1104)三月,官居尚书左丞的张商英就发牢骚说:“……赵谂不轨,以辱乡邦,吾何敢怀土哉!”他假借梦境中的青城丈人之口回顾历史,认为:蜀中向来忠义辈出,至于本朝李顺、赵谂之乱,前者为孟昶后裔,后者出身獠人,皆与蜀人无涉;然后指出:“吾三川之灵,何负于世,而公见弃之速耶?”[41]415曲折表达了对朝廷猜忌蜀士态度的不满。眉山人唐庚(1070—1120)在《辨蜀论》⑦中也曾感叹:自赵谂之乱后,“诸公论议,多以蜀人为疑,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为矣”;在他看来,蜀人喜为动乱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主政者欲防患于未然,采取预防措施未尝不可,但“独施于蜀,则吾不知也”[45]卷七,1-2。而另外一位眉山人苏辙,晚年卜居颍滨,有蜀人来访时避之,不与相见,据说也是因为受赵谂案牵连,不得不收敛形迹以避嫌疑[46]82。
在赵谂之前,蜀地动乱多由底层民众发动,故“蜀人好乱”之说多指向这一群体[9];至于蜀士,除了不能在家乡任职,尚未受到大的影响;虽然不断有人为蜀地发出不平之鸣,也多出于护惜乡邦的心理。但赵谂之乱的发生,却使蜀士无论在朝在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波及范围如此深远,可能是蜀地形象问题在南宋朝受到持续关注的原因之一。
二“德守者固”:南宋时期的蜀地形象
宋室南渡后,不少人囿于思维定势,依旧保持着北宋以来的蜀地印象。绍兴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针对蜀士发表了一番感言,语云:“蜀中人多能文,然士人当以德行为先,文章乃其余事。”[47]3257大概就与此有关。而王之望、赵汝愚等人在其奏议中一再提及蜀人“易动难安”[47]3875[48]3245,也显示出这一主观认知仍在部分人心目中顽强延续。
但时势毕竟不同于北宋,中原业已沦陷,蜀地在半壁江山中的战略地位骤然凸显。此前,论者谈及蜀中多乱,往往归因于其地之“险”且“富”;然而,时移势易,丰饶的物产和雄奇的山川固然容易成为割据之资,但如果措置得当,也可以成为抵御外侮的坚固屏障。易言之,“天下之险在蜀”[49]900[50]445,就意味着“天下之势在蜀”[51]186或“天下根本在蜀”[36]1227。生于蜀中的著名史学家李焘,曾撰《六朝通鉴博议》一书,其中对四川的战略地位再三致意,如谓:“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独论兵为然。而因地势以行兵者,盖亦似之。”[51]186这些言论不能简单地视为夸示乡邦之语。事实上,当时蜀地以外的士人也多持同样的看法。温州平阳(今浙江省平阳县)人朱黼即云:“蜀之难平而不易取,前事可验也。况天下分裂之际,蜀实据天下三分之一,……一举足,南北遂有轻重。”[52]518他们虽然是针对南北朝形势立论,但宋室南渡之后面临的形势与南朝相去不远,故两人的言论无疑是在借古喻今。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人李文子对此亦有同感,他在《〈蜀鉴〉序》中说:“蜀之在宇,九之一尔,得之则安,失之则亡。”[53]2-3隆兴丰城(今属江西)人徐鹿卿(1189—1249)也说:“东南立国,倚蜀为重。”[54]831类似的论调在这一时期不胜枚举,蜀地战略地位之重要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随着四川战略地位的上升,蜀地士人的心态也在悄然变化,以往为蜀人辩解时的隐约其辞,至此一变而为理直气壮。淳熙五年(1178),蜀州(今四川省崇州市)人张縯就断言:“蜀视天下,其亦可谓敦厚而易治矣。”[55]649简州(今四川省简阳市)人刘光祖(1142—1222)亦谓:“维蜀慕王化,通中国,最为古远,载籍之传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书之曰‘庸、蜀、羌、髦、微、卢、彭、濮人’,则其附声教,识仁暴,概见于经矣。”[56]515庆元年间(1195—1200),李焘之子李埴(1161—1238)出知夔州,在任期间作《鱼复扞关铭并序》⑧,称:“自古言,蜀人嗜乱喜祸,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尽其术。呜呼!何其过也!”他接着指出,自公孙述以下至五代孟知祥等人,自古以来乱蜀者多非蜀人,惟东晋时期的谯纵,本宕渠人,但原情察迹,可知谯纵“初无异志,劫于群叛,不能自还”;蜀地险要的形势固然易生割据,但相对于地形,人心之向背才是治乱的关键,“一定而不易者,地形也;难保而易变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化”[57]1333-1334,要求为政者消除地域歧视,一视同仁,以王道政治化民成俗,则风行草偃,国家自然有磐石之安。西晋人张载曾在《剑阁铭》中称蜀地“世浊则逆,道清斯顺”[58]1516,李埴显然注意到了这一措辞,他说:“鱼复与剑阁,埒险角壮,并为西南镇,昔有铭剑阁者,独此缺诸?”故其文颇有与张载观点针锋相对的意味:“……西方之人,王化所达,宁甘嗜乱?实首攸胁。岂富是怙?忍上之觖。惟此山川,重阻复叠。德守者固,兵据者蹶。惟此黔庶,嶷嶷业业,力制则离,道怀乃协。”[57]1334
在这种心态下,昔日盖棺论定的史实,如今也被重新审查。两晋之际,蜀郡成都人杜弢遭逢李特之乱,流寓荆、湘一带,后被巴蜀流民推举为首领,《晋书》将其与王弥、苏峻、孙恩、卢循、谯纵等人置于同卷,称其“纵兵肆暴,伪降于山简,简以为广汉太守”[58]2622。但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县)人郭允蹈却在《蜀鉴》中指出,杜弢并非诈降,只是适逢山简病卒,事遂中辍,其后,杜弢致书应詹,向司马睿乞降,获准后被任命为巴东监军,不料“诸将徇功者攻之不已”,杜弢不胜愤怒,再次举兵反叛,最终被陶侃、应詹等人击败;郭允蹈以为,“此乃陶侃心惮王敦,规模不大,不能招纳弢等,欲讨杀以论功耳”,《晋书》的记载是“以成败论人”,并说:“《晋史·应詹传》称贼中金宝溢目,应詹但取图书。岂有贼而载图书者乎?此皆梁、益流徙之衣冠也。悲夫!”[59]178-189显然,《蜀鉴》中的杜弢是一个屡遭冤屈而又求告无门的悲剧性人物,与《晋书》本传迥乎不同。郭允蹈在《蜀鉴》中尝谓:“议者谓蜀民喜乱,不为过乎?”[59]340为蜀人正名的用意至为明显。他不惜篇幅为杜弢辩诬,显然出于同样的动机。
蜀地战略地位的崛起,也引起了东南论者对蜀地民风的重新认识。绍兴二十九年(1159),兴国(今湖北阳新)军人王质(1135—1189)著论指出,蜀人“柔忍而朴厚”,惟其如此,故易为奸雄所用,唐之崔宁、韦皋,梁之王建,后唐之孟知祥,都曾以此为基地拥兵自重[60]366-367[61]180。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历史事实,前人多归咎于蜀人好乱,王质则认为原因在于蜀人柔弱朴实的天性,王十朋也有类似王质的认识。乾道(1165-1173)初年,王十朋出知夔州,州宅内原有堂名“整暇”,王十朋乃易其名为“易治堂”,并赋诗云:“风俗无难易,治之端在人。古夔尤易治,风俗本来淳。”[62]396自夔州离任时,王十朋再次感叹:“峡民淳狱讼稀”[62]434。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的《太平寰宇记》,谈及夔州时,认为当地民风“剽悍巧猾”[63]2961。王十朋的夔州印象,显然与此截然相反。至于曾在蜀地长期游历的大诗人陆游,在离蜀多年之后,仍然对这里的民风淳厚印象深刻[64]35。
关于蜀地民风,宋人还有“闽蜀同风”之说。持此论者,往往带着主流政治文化对南方后进地区的傲慢与偏见,视闽、蜀两地为异类[65]414-440[66]54-59[9]。然而,到了南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闽蜀同风”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绍兴二十一年(1151),莆田人黄公度(1109—1156)为文曰:“闽、蜀相望,各在西、南一隅,而习俗好尚,实有东州齐鲁遗风。蜀由汉以来,号为文物善地,闽又其最后显者。”[67]55颇以闽、蜀两地的习俗自豪。无独有偶,咸淳八年(1272),眉州人宋日隆为新修《连江县志》作序,亦称:“闽、蜀风马牛不相及,前辈乃以为同风,每窃疑之。三载兹邑,目文物之盛,科馌之勤,习俗之俭,真与吾眉同。”[68]1437前文述及,苏轼一闻“闽蜀同风”之说,即勃然变色;而黄、宋二人在提及“闽蜀同风”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负面内涵,而津津乐道于两地的文物之备、科举之盛。这一鲜明的对比,正是蜀地形象在两宋时期改观的真实写照。
蜀道之难,古今同慨。西晋张载在《剑阁铭》中称,此地“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58]1516,对蜀人的戒惧溢于言表。其后,李白《蜀道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69]199的说法,更是万口传诵。于是乎,“蜀道难”这一文学题材,就与蜀地易乱的意象产生了关联。时至南宋,随着蜀地形象的改善,昔人视若畏途的蜀道,似乎也不那么险恶了,甚至不少人反其意而用之,用“蜀道易”来表达他们对蜀地的观感。绍熙五年(1194),赵彦逾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明州鄞县(今属浙江省宁波市)人楼钥(1137—1213)制旨勉励赵彦逾力行仁政:“蜀道,天下之极险也,然以为难则难于上青天,以为易则易于履平地,是在人尔。”[70]卷四十二,10在送友人入蜀诗中,楼钥又重申此意[70]卷一,24。祖籍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市)的李曾伯(1198—1268),也有“昔蜀道难,今蜀道易”之语[71]414。正如合州人(今重庆市铜梁县)度正(1166—1235)所言:“昔李太白赋《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后人反而赓之,作《蜀道易》。蜀道岂有难易哉?特存乎此心而已,心险则难,平则易,此古今不易之路也。”[72]242的确,蜀道山形依旧,但不同时期的观察者却有着迥乎不同的感受,适足以反映他们心目中不同的蜀地形象。
另外一组事实的对比,也有助于观察蜀地形象的转变。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吴曦叛于四川,不久被李好义、杨巨源等人诛杀,叛乱平息。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而言,这次叛乱都远远超过百年前的赵谂事件。赵谂谋反事发后,群情耸动,蜀士备受指摘;而吴曦之叛敉平后,却鲜见针对蜀人的批评,相反朝论以为蜀士在朝者过少,于是“又特召四人”[73]662。两相对比,反差不可谓不大。朝廷的这一举措,固然有笼络人心的动机,但如果不是基于对蜀士的信任,那么这样的动机自然无从谈起。蒲江人魏了翁(1178—1237)还指出,吴曦初叛时,“元帅既遁,王人继逐,东归之士蔽江而下,至是所望以反正者,惟蜀人耳”[74]卷四十,13。不仅魏了翁有这样的体会,其后《续编两朝纲目备要》⑨在述及吴曦之叛时也如是说:
自昔乱蜀者非蜀人,如张鲁、李特、刘辟、王建、孟知祥之类,皆北人也。本朝王均、张信,东京人,王孝忠,蔡州人。中间惟饥民王小波以岁荒盗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吴曦兄弟与其谋主姚淮源、米修之皆德顺军人,董镇,饶州人。方是时,东人有为元帅者、为奉使者、榷牧者、护漕者、详刑者,皆方舟而去,而纠合忠义,克清大憝,挈六十州之地以还天子者,又西人也。曦既死,凡前日东人之任,悉西人为之。[75]178-179
这番议论不但坐实了魏了翁的观点,而且再次回顾历史为蜀人正名。其中又提到,吴曦之叛后,蜀中官职率由蜀人充任,也反映出朝廷对蜀士态度的转变。
由是观之,蜀地形象在南宋时期出现了明显改观,往昔“易动难安”的色彩逐渐淡化。北宋时期,不少蜀士对于加诸蜀地的偏见与歧视耿耿于怀,群起而为之辩白。关于这一问题,魏了翁的一番感言值得重视,兹移录如下:
后唐张(不)[丕]立尝为诗曰:朝廷不用忧巴俗,称霸何曾是蜀人。人以为名言。至本朝张次公(张唐英——引者注)序《蜀梼杌》,天觉(张商英)《送凌戡归蜀》,大抵亦皆为蜀人辩。数者也,忠义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节表表在人,亦岂狂图者之所能溷?三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东溪(王腾号东溪先生——引者注)《辩蜀都赋》,盖不专为蜀辩,将以发左思抑蜀黜吴、借魏谀晋之罪,真有功于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爱重,毋使后人辩今犹今辩昔焉。[74]卷五十九,7
在他看来,蜀人的节义世所共知,毋庸多辩,张丕立(即张立)以下诸人汲汲于自辩,反而显得器量不弘;而王腾的《辩蜀都赋》将着眼点转移到魏蜀正闰之辨,值得效法;蜀士应自爱自重,面对外人的质疑,置之不辨可也。从魏了翁的议论可以看出,他所处的时代,一度令蜀士颇为尴尬的蜀地形象问题已在若有若无间,笼罩在蜀士心头的阴影也趋于消散,所以魏了翁才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如此自信和超脱。
三余论:蜀地形象在南宋得以改观之原因
为什么蜀地的形象在南宋得以改观?前文的论述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南宋时期蜀地战略地位的提升,无疑是首要原因。如前所述,南宋时期的王质和王十朋都认为蜀地民风淳朴,这样的认识固然与其自身阅历有关,但针对现实政治的考量,可能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王质在同一奏疏中建议朝廷厚恤蜀人,收拾人心,以防吴氏家族势力在蜀地坐大,“盖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过于江、淮、闽、浙、湖、广之民,而后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则缓急之际斯有不忍负朝廷之意”[60]367,他对蜀地的认知无疑与此有关。而王十朋也曾于乾道三年(1167)提醒宋孝宗:“国家全有吴、蜀之地,蜀去行在万里,远而易忘”,然而“今日之所以立国者,正赖蜀以为重”,不惟一日不可忘,而且还要倚之以恢复中原;蜀有天险,故外患尚不足忧,当此之时,“正恐民心或离,衅由内起,为可忧尔,抚绥固结,在今日为尤急”[62]640-642。可见,王十朋对蜀地的重要性也有深刻体认,是以他能对此地民风刮目相看。
面对大敌当前的局面,南宋持此论者不在少数。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陈傅良(1137—1203)曾赋诗感叹,吴、蜀士人向来互相轻薄,在昔有“眉山(苏氏父子)与金陵(王安石),奈何不相容?大雅如关、洛,亦复互诋攻,朋分文字间,祸起师友中”,一时意气之争终致神州陆沉;当今之世,理应抛弃畛域之见,使“西人不为西,东人不为东”,同舟共济,共赴时艰[76]67。宋室南渡后,蜀地的战略地位有目共睹,朝廷注意收拾蜀人之心,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蜀人好乱”的论调趋于沉寂,为蜀人辩护的观点声势渐壮,北宋以来对蜀地的偏见最终被克服。
另一方面,蜀士群体的扩大及其影响力的提升,无疑也有助于蜀地形象的转变。据统计,有宋一代,四川和江南的进士人数已经占了全国的80%左右[77],而蜀士中官至宰辅者达27人,也大大超过前代[78]292-298。大量蜀士进入仕途,特别是进入政治中枢,自然会给彼时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带来冲击。北宋时期,包括蜀士在内的南方士人群体崛起于政坛,影响到长期占据要津的北方士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后者的反弹,以至蜀地一度名声不佳,这与中原主流文化的打压有关[9]。到了南宋,蜀中科举之盛更上一层楼,四川进士数在北宋时位居全国第八,南宋则跃居全国第四位[79]。从宰辅人数来看,两宋蜀籍宰辅27人中,有18人出仕于南宋[78]292-298。宜乎宋高宗有言:“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47]2089政坛之外,蜀士的表现也颇为突出。如《宋史·地理志》所云,自宋平孟蜀后,川峡四路“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南宋时,苏轼文章风行于世,士人竞相模仿,以致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咬菜根”之语[64]100。如果说蜀地战略地位的崛起,使南宋君臣逐渐修正他们对蜀地的认知,从而推动了蜀地形象的转变,那么,蜀士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稳步提升,则使他们得以从正面引领蜀地形象的重构,前述李埴、魏了翁等人的呼声正是其中之荦荦大者。
从更宽的视野来看,宋朝结束五代分裂局面后,政治虽归于一统,但认同意识的形成尚需时日,在各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激荡的过程中,畛域之见日趋淡化,包括蜀地在内的地方精英被主流文化接纳,一个凝聚了士大夫阶层认同意识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不断扩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融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过程在蜀地显得有些曲折和漫长。惟其如此,两宋时期蜀地形象的嬗变,堪称边缘与中心地区文化互动的典型片段,也是中国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发育过程的缩影。
注释:
①本文曾提交2015年10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中心宋史研究工作坊主办的“宋代的巴蜀”学术论坛,承蒙与会专家们的指点,投稿时又获匿名评审专家指瑕,在此一并致谢!
②马宗霍先生已经发现了《资治通鉴》中的这段异文,惟未论及原因。参见:马宗霍《南史·校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页。
③王安石为田况撰写的墓志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参见:《王安石全集》卷八八《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99页)。范、王两文当同出于田况的行状或家传。
④据王辟之自序,《渑水燕谈录》成书于绍圣二年(1095)。
⑤据王明清《投辖录》记载,李孝广时任州路提举学事,费乂为忠州士人。但后来王明清在《挥麈录·后录》卷一一中再次提及此事,李孝广为“成都漕”,费乂为邛州士人,并说同时涉案的还有韦直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三的记载及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三的考证,当以《挥麈录·后录》所载为是。但《长编拾补》《旧闻证误》《挥麈后录》均缺乏关于此案细节的记载。而据王明清在《投辖录》中的自述,此事由李倞亲口告知其父王铚,而且王明清后来“因阅宣徽宗皇帝诏旨,备见费乂削章”,故《投辖录》透露出的案情细节,当属事实。
⑥王腾,字天长,一作庆长,号东溪先生,眉州人,生卒年不详(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五《跋眉人王庆长〈辨蜀都赋〉》,四部丛刊本,第7叶;《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附《二百名贤世次》,《宋集珍本丛刊》第9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14页)。其文《上翟提学书》中有“方今天下一家”之语,当作于北宋。《代上邵宪书》(见佚名《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九二,《宋集珍本丛刊》第94册,第100页)中又自称“前任恭州某官”,渝州改名恭州,在赵谂之乱后;邵宪,当指邵伯温,建炎初年官至提点成都路刑狱,是知王腾其人生当两宋之交。
⑦《辨蜀论》中有“甘陵之围,难拔于均、顺;江津之谋,易败于逢、育”一语。所谓“甘陵之围”,是指发生于贝州(甘陵为贝州清河县旧称)的王则兵变,事在庆历七年(1047);“均、顺”所指两事,分别是指咸平三年(1000)的王均兵变和淳化五年(994)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均爆发于蜀地;“江津之谋”即指此前不久的赵谂之乱(赵谂为江津人);“逢、育”则是指李逢、刘育,因涉及宗室赵世居之狱被凌迟处死,事在熙宁八年(1075)(见:《宋史》卷二〇〇《刑法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98页)。故《辨蜀论》当作于赵谂之乱后。
⑧据清光绪十九年《奉节县志》所录《鱼复扞关铭并序》,李埴时“知夔州”(参见:杨德坤《光绪奉节县志》,四川省奉节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重印,第241页)。清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544页)卷一五〇引旧《通志》:“李埴,庆元中知夔州,爱民诲士。”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李埴名列庆元党籍,时为校书郎,盖于此时出知夔州。
⑨据点校者汝企和先生考证,该书成书年代极有可能就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至景定五年(1264)之间,见是书《前言》。
参考文献:
[1]张至皋.“四川”的名称由来和辖区演变[J].社会科学研究,1979,(5).
[2]胡昭曦.四川省省名考析[C]∥蜀学:第7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
[3]刘复生.由虚到实:关于“四川”的概念史[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2).
[4]林天蔚.南宋时强干弱枝政策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C]∥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5]林文勋.北宋四川特殊化政策考析[C]∥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6]余蔚,任海平.北宋川峡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C]∥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粟品孝.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8]张邦炜.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9]黄博.制造边缘:宋代的“闽蜀同风”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10]黄博.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G].北京:中华书局,2004.
[12]吕陶.净德集[G]∥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3]张咏.张乖崖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4]宋祁.景文集[G]∥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6]司马光.资治通鉴[G].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17]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刘安世.尽言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0]文同.丹渊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1]范纯仁.范忠宣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2]范镇.吕惠穆公公弼神道碑[G]∥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香港:龙门书局,1977.
[23]张俞.送益牧王密学朝觐序[G]∥袁说友.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24]张俞.送明运使赴职益州序[G]∥袁说友.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25]宋右仁.石室铭[G]∥袁说友.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26]张唐英.蜀梼杌序[G]∥杨慎.全蜀艺文志.北京:线装书局,2003.
[27]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8]张俞.送杨钧廷评赴治温江序[G]∥袁说友.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29]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30]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曾枣庄.嘉祐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2]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3]王辟之.重修夫子庙记[M]∥同治忠州直隶州志.1873.
[3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5]黄庭坚.四贤阁记[G]∥杨慎.全蜀艺文志.北京:线装书局,2003.
[36]祝穆,祝洙.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7]张邦炜.关于赵抃治蜀[C]//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38]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9]蒋静.王蘧墓志铭[G]∥谢飞,张志忠,杨超.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40]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1]吴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2]王明清.投辖录[M].上海:上海书店,1990.
[43]王腾.辩蜀都赋[G]∥杨慎.全蜀艺文志.北京:线装书局,2003.
[44]王腾.上翟提学书[G]∥佚名.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北京:线装书局,2004.
[45]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G]∥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86.
[46]庞石帚.养晴室笔记[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
[4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8]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9]邵博.代成都帅檄[G]∥袁说友.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50]王咨.上汪制置书[G]∥袁说友.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51]李焘.六朝通鉴博议[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52]朱黼.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G]∥四库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53]李文子.《蜀鉴》序[C]∥郭允蹈.蜀鉴.成都:巴蜀书社,1984.
[54]徐鹿卿.清正存稿[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5]张縯.南康郡王庙记[G]∥袁说友.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56]刘光祖.万里桥记[C]∥袁说友.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57]李埴.鱼复扞关铭并序[G]∥杨慎.全蜀艺文志.北京:线装书局,2003.
[58]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9]郭允蹈.蜀鉴[M].成都:巴蜀书社,1984.
[60]王质.雪山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1]王兆鹏,王可喜,方星移.两宋词人丛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62]王十朋.王十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3]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4]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5]吴天墀.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C]∥邓广铬,等.宋史研究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66]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67]黄公度.知稼翁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8]宋日隆.宋咸淳八年《连江县志》序[C]∥连江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
[69]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0]楼钥.攻媿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71]李曾伯.可斋杂稿[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2]度正.性善堂稿[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4]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75]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6]郁震宏.陈傅良诗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77]肖忠华.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3).
[78]《历史知识》编辑部.四川古代名人[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79]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比较研究[J].教育研究,1991,(1).
[责任编辑:凌兴珍]
The Image of Sichuan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Evolution
CAO Peng-c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71, China)
Abstract: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military unrest broke out so frequently in Sichuan that the region was impressed by its preference for rebellion to obedience. And the following decades saw gradual improvement of Sichuan’s image because of its political stability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this process was interrupted by the incident of Zhaoshen’s rebellion, which promoted the authorities to treat Sichuan with suspicion and precaution.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of Sichuan, and the steady promotion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scholars from Sichuan, the preconception that Sichuan people inclined to rebel was changed, and the image of Sichuan was ultimately reversed. The evolution of Sichuan’s image, therefore, can be regarded as an exemplary case of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Key words:the Song dynasty; image of Sichuan; preference for rebellion to obedience; Sichuan people inclined to rebel; evolution process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2-0143-09
作者简介:曹鹏程(1982—),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5-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