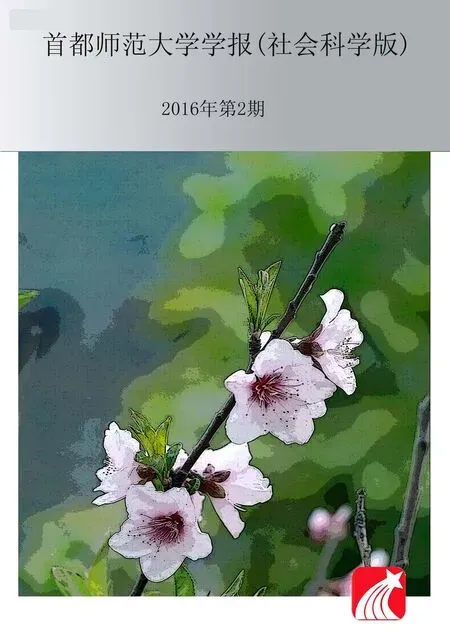儒、道论“和”之两系三义及其当代意义
杨 杰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和”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有争议的,这当然与其本身的特性有关。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阴阳和合”、“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等说法表明了“和”字具有抽象性、根本性的含义;而与“气”的概念相关,“和”字又具有形而下的具象性的含义。比如“和气”一词,在哲学史上一般指阴阳二气激荡而生的和谐之气①高亨注曰“‘冲气以为和’者,言阴阳二气涌摇交荡已成和气也”。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7页。,而人们也用其指人所具有的温和的态度或和睦融洽的氛围,比如“面色和气”、“一团和气”或者“和气生财”;同时“和气”又指人体内的生命原动力,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养气》有云:“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②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这里的“和气”即是人的“元气”、“中气”。“和”的这种贯通形上形下的性质,使之在传统哲学范畴中的位置长期以来未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①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张立文主编《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葛荣晋著《中国哲学范畴通论》这三部较有代表性的以概念或者范畴评述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和”都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行讨论的,最多是作为与“气”相关的概念进行讨论。。而随着“兼和”(张岱年)、“和合”(张立文)等理论的提出,以及政治层面“和谐社会”理念的强调,“和”字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与文化范畴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和道家那里的本真含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比如陈鼓应先生通过分析《庄子》中的天和、人和、心和等观念考察道家的和谐观②陈鼓应:《道家的和谐观》,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但是,如果深入儒道思想内部,会发现老子讲“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庄子讲“游心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与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概念层次与面向是不同的:老庄在宇宙论和境界论上讲“和”,孔子在人间伦理上说“和”。这分别可用“天和”、“心和”与“人和”加以概括。因而“和”在儒、道两家呈现出两系三义的概念格局,其当代意义也可由此分而述之。
一、道家所论之宇宙论视域中的“天和”
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是由道家特别是老子开创的。所谓“宇宙生成论”,王葆玹认为它“分为宇宙发生论和宇宙构成论两部分。前者是从时间上推究宇宙的发生发展过程,这种推究常常会推出一个最早的起源;后者是从空间上考察、推算宇宙的结构,结果往往变成主观规划,设置一个结构中心”③王葆玹:《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84页。。可见宇宙生成论,是指探讨宇宙万物的产生来源、生成过程、构成元素和宇宙结构的问题。这种主观建构的理论是一种气化宇宙观,即“气”是贯彻宇宙形成前后的动态质素,而“和”保证了这种动态过程的稳定与平衡。《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有一个“道→一→二→三→万物”的生成序列,说完这个生成序列之后,老子讲万物的内在状态是“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也就是说生成后的万物包含阴阳两个方面,二者相互激荡而成为一个“和谐体”,这个“和谐体”就是成型的“物”本身;之所以称之为“和”,乃是因为只有阴阳两个方面和谐平衡了,一个物才能完整地产生与维持存在。因此,“和”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和气”,万物内部保有了这种“和气”(也称为“元气”、“精气”)才能长久存在;其二是指一种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保证了万物的产生与存在。
“和”的这两层含义在老子之后的道家学派里得到了进一步显题。《黄帝四经·道原》认为“道”与“和”的关系是体用关系:“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一者”即道,“和其用也”,意指和合是道的作用;这个“和”既指道本身(先天之气)内部阴阳之气保持和合状态才能生成万物,也指万物资于道的和合状态才能保持存在。《淮南子·泛论训》指出“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这里的“和”既指和气,也指和谐状态,“和气”实现了阴阳二气的调和,这种和谐状态实现了天地万物包括时间的生成与存在。庄子则指出空间即“天地”与阴阳二气的关系,《庄子·田子方》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即指天地所生的阴阳二气氤氲和合才能生成万物,这里的天地当然也是道所生的,气在道时是阴阳氤氲而未分的,已有天地后则分为阴阳,继而生万物。这种宇宙论视域中的“和”《庄子》将之称为“天和”,书中凡三处四见:
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
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居,一汝度,神将来舍。(《庄子·知北游》)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庄子·庚桑楚》
第二处的“天和”,陈鼓应注曰“天然和气”,并引林希夷说“天和者,元气也”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53页。,又如《淮南子·主术训》“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高诱注“天和,气也”①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2页。。可见,“天和”一词的意义与道家所主张的气化宇宙生成论直接相关,既指元气,也指这种元气所体现的和谐状态。不过,宇宙生成论不是道家道教关注“天和”的最终目的,讲述天道的目的还是指向人间。第一、三处的“天和”意指“与天相和”,“天”即“天地之德”,也即自然而然和谐运行的天道;所谓“明白于天地之德”或者“同乎天和”,意指人道要与天道同体,行为处事遵循天道,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
“天和”意义上的“和”在当代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元气”意义上的“和”要求我们要保持天地自然之元气的和谐状态。这要求我们在开发利用自然时要尊重自然,人道要尊重天道。道家认为宇宙自有其和谐的生生之道,因此人们利用自然的行动不应当是戕害自然,而是辅助自然和谐运行的同时实现人类的目的与结果。庄子认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纥草饮水,翘足而陆”,就是说马有其自我存在与行动的自然而然的和谐的方式,但是人们却“烧之剔之,刻之络之,连之以羁络,编之以皂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荚之威”(《庄子·马蹄》),企图改变马的本性而造成马的死亡。因此,庄子主张要顺应马的本性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道家的这种顺应自然和谐本性的观点,在当代尤其受到环境生态学者的重视,认为其尊重自然的观念是我们现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其二,天地自然的和谐状态是人类的榜样,因此“人道”要效法“天道”,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都应遵循自然而然的原则。这种“自然”,是就天道运行的和谐有序而言的,在道家看来,天地自然所体现的和谐精神,在人间社会也是应该如此的,天的和谐原则是人间社会必须要遵循的原则。不仅如此,在道家那里,这种“天和”更下贯到人的内在心灵之和,也即境界意义上的“心和”。
二、道家所论之境界论视域中的“心和”
在道家看来,人是禀自天地之气而来的,也因存有此气而维持生存。如《管子·枢言》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文子·道原》说“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文子·守弱》说“气者,生之元也”。《庄子·知北游》所谓我们的身体是“天地之委形”、生命是“天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顺”而来的。因此宇宙论意义上的“天和”下贯到个人身上,则要求人也要保持一种“和”的状态。上引的《庄子·天道》“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意指运用天地自然而然的特性治理天下的叫做“与人相和”,“人”即禀自自然之天道而来的无为之人道。此处虽然用的词是“人和”,但实际上首先指向的是“心和”;因为在道家那里,首先要人心保持一种平和和谐状态,也即“心和”,才能实现天下人人皆和睦相处的目的,从而接近天道实现“天和”的境界。达到“心和”状态的人可称之为真人:“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庄子·徐无鬼》),即怀抱无为之德保养平和之气来顺应天下的人才是“真人”,这是要经过一定工夫修养才能达到的崇高人格。
“心和”一词最早出于《庄子·人间世》: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此处讲述的是颜阖傅残暴的卫灵公太子的故事。蘧伯玉建议颜阖对太子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自己的心灵因循太子,但又不能顺应太子或表现出来,如此将太子引向正途,由此可见人间世中人与人相处的艰难。庄子的理想则是“与物为春”(《庄子·德充符》),即以虚无之心平和之境应接事务,这实际上是一种因循事务并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
在道家那里,“心和”与“天和”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人禀自天地之气而来,人之性情亦源于天地之气,因而“心和”禀自“天和”;因此“心和”既是一种应然状态,也是一种本然状态。即人心本然是和谐的,也应该是和谐的;但由于大道沦丧,人心被各种欲望、思虑控制而呈现异化状态,这种异化需要经过一定的修炼工夫才能回到其本然状态与应然之境。为了达到个体心境的和谐,既要“吹煦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庄子·刻意》),经过修炼形体保养平和之气,更要杜绝欲望抛却思虑,经由“心斋”、“坐忘”的修炼达到以虚无之心应接万物的身心兼养的过程。前者在后世的道教那里具体展开为各种繁杂的养生术,后者从心灵上入手提升人的境界。庄子详细描述了心灵修炼的过程:抛却“蓬心”、“成心”,经过“朝彻”“见独”的“外”(排除)(《庄子·大宗师》)的过程以达到“虚室生白”(《庄子·人间世》)的境界,从而应接外物时是一种“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的“游”的状态,即达到顺应外物的自然发展的同时保持自我心灵的自由与逍遥的境界。
另一方面,经过一番修养工夫达到的“心和”境界也可称为“天和”,这里的“天”意指天然、自然而然。庄子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就是说顺应天地自然之德的,叫做“天和”,具备这种境界的人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称为“同乎天和”的“天人”(《庄子·天下》),也即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
“心和”的提出在当代社会尤其有着积极意义。其一,在物质至上、欲望张扬的当今时代,人心的混乱、迷茫、烦躁、焦虑等负面情绪需要和谐的力量进行调整,这就需要人们回到老庄所强调的少私寡欲、抱德炀和的修养工夫,回到自我性情的本真平和状态上来。庄子及后来的道教为本真性情的复归提供了很多修养方法,既有外在的排除欲望,又有内在的元气充盈,这在消费主义、个性主义盛行的当代受到很多人的鄙薄。但是,道家尤其是庄子注重的是个体精神生命的自由与价值,既摆脱政治的束缚,又杜绝欲望的控制,只追求自我性情的自然发显。而道家的自我性情不是元康名士“无德而折巾”①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式的任诞作达,而是有着“和”的要求的,此即庄子所谓“游心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德”即自然无为之德,“德”的内容就是“和”,要心灵与德相和,也要心灵超越于人间的是非欲望,在无心无意中遨游。因此,“心和”要求身处物质丰盛、科技发达时代的我们更要抛却名利外物的异化,追求自我心灵的成长。其二,“心和”考虑的实际上是现实境遇中的个体如何安顿理想境界中的生命的问题。在道家人格论里,现实中的个人与“真人”的差别与其说是形体上的,不如说是心态上的,也即对个体来说,以平和之心、虚无之境应接世界,就是实现了个体生命的最大自由与崇高境界。因此,“心和”提供了一种在物质力量十分强大的当今时代我们如何因应的问题,就是说不必刻意地与外在物质抗争,而是遵循王弼的主旨因任其存在但“有情而无累”,也即应接外物而不被其牵累,自己是外物的主人而不是被外物所异化,更多地复归到自己的内在性情,回到“心和”的本然之体与应然之境上,追求自己内在的生命价值。这在追求功利主义、为名利异化的当代社会,无疑有着积极的警醒价值。
三、儒家所论之伦理世界中的人和
“人和”概念最早仍然是庄子提出来的,就是上引“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在庄子那里“人和”最终还是指向“心和”,因为庄子讲“和”主要是就心灵境界而言的。事实上,“人和”概念在儒家那里得到更为详细和全面的阐释。与道家从宇宙论、境界论讲“和”不同,儒家从人伦出发,试图为人间塑造一个良善的社会结构;其讲“和”,实际上是一种人伦之和。这在儒家的核心概念“仁”字的结构上得到两个方面的呈现。
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字,许慎解为“从人从二”,段玉裁注曰“按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因此阮元说“仁之意即人之也”③阮元:《研经室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6-179页。,其“仁”指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在儒家所提出的众多伦理观念中,比如“十义”以及后来整合出的“三纲五常”,关注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现实中的人际相处需要用礼进行规范,而“礼之用,和为贵”。也就是说,用来区别人类等级名分的礼(《荀子·乐论》:“乐合同,礼别异”)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种温情脉脉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伦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社会,就是要求整个社会乃至天下各国达到和谐状态(《尚书·尧典》:“协和万邦”),这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儒家渊源。这是“人和”的第一层含义。
早期儒家讲“人和”并不只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也关注人身心之和。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博简》中的“仁”字写作“上身下心”的结构,而从身从心的结构,说明早期儒家对“仁”的理解是从身、心两方面着手的。孔子以“爱人”为仁,又说“中心惨怛,爱人之仁也”(《礼记·表记》)。孟子也以心中萌发的“恻隐之心”作为“仁”之发端处。可见在孔孟看来,“仁”首先是从内心发出的个人情感。《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这个个人内心情感的发显有一个“中节”的要求,这就是要达到“和”。而不“中节”的发显,孔子称之为狂狷:“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在这个意义上,“中”与“和”是相关的,即是通过符合“中道”的行为,在儒家那里就是通过礼的节制与乐的引导实现身心“和”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层次的身心之和与道家的“心和”有内在的不同。儒家的心有一个仁德的内容,道家的心则是空灵的。这点区别尤其体现在人格境界上。孟子评价柳下惠为“圣之和者也”,这个“和”,是就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孟子·万章下》),因而使得受其影响的百姓能够“变弼狭而为宽博,变浅薄而为敦厚”(《孟子注疏》)而言的。这里柳下惠浑身散发着儒家所追求的仁德的道德力量,并且力图将这种仁德观念推及他人,由此才获得殊荣。而道家的真人则是关尹、老聃似的“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庄子·天下》)的“能体纯素”(《庄子·刻意》)之人,即非但自身保持纯粹素朴不受任何物质及价值观念束缚,亦不将自己所坚持的观念施及他人,而是对整个世界采取自然而然的态度。
从外在礼制和内在仁德上讲“和”是儒家和谐观在现当代能给我们的积极价值。道家所强调的遵循自然的要求显然不是每一个现实中的个体都能做到的,因此需要外在仪式、规则的规范;拒绝欲望抛却思虑也不是多数身患现代病的人所能所愿做的,因此需要内在德性的约束。从外在来看,儒家要求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遵循一定规范,才能形成一个有条理的、和谐的社会。在古代这种规范是礼教,在当代是法制。中国古代传统中礼法皆是缘人情而设的,也就是要先有内在德性对仁的崇尚,再由此制定外在的礼法,最终内外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和谐的大同社会。这种由内而外的逻辑对当今法治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启示,这就是我们要避免建立一个“法令滋章”的法治社会或者仅仅以道德、礼节规范人的行为,而是要人从心理上接受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法治、道德及礼节的共同作用,如此才能发显于外在行为,才能有真正的效果。不过,传统的礼制与道德观念需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这不仅需要去粗存精的取舍,更需要在中西文化相较融合中进行综合创新式的现代转型;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四、儒、道论“和”的殊途与同归
儒、道分别从“人和”、“天和”与“心和”两系三方面论述“和”的意义,不过这种区别并不是截然两分的。这种解析的方法只是为了说明儒道两家的不同精神旨趣,并不是说道家不讲“人和”,儒家不讲“天和”与“心和”,而是说他们对“和”的侧重点有不同的理解,认为实现“和”的方法也有异。
儒家讲“人和”的同时,也涉及到“天和”与“心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指天地自然运行的和谐有序是不需要天自己去“说明”的,它自己就呈现在那里;对于人来说,人也应当注重自己行为的适当性,而不是“巧言令色”,所以人要“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和道家主张以人道模拟天道、人要效法自然是一致的,言天道的最终指向都是人伦事理。孔子亦赞颂颜回之乐与曾点乐处、孟子评价柳下惠为“圣之和”,说明儒家在理论上也强调不能局限于人伦人际关系的和睦祥和,而要将仁义礼节内在化为本己的需求与自然的发显,此境界的“和”与道家的“心和”境界在层次上无别,但内容上有异。儒家始终不能忘怀内在仁义的自我限制与外在礼法的节度;而道家则主张要通过“心斋”“坐忘”即抛却形体的限制与思虑的引诱达到“朝彻”“见独”的状态,从而实现逍遥的精神境界。
而道家在论述“天和”、“心和”时,其最终目的与当然结果也与儒家的“人和”是一致的。不过这个“人和”不是儒家意义上的试图以礼法规范人们行为的“和”,而是只要社会个体都保持“心和”的境界,整个社会也就自然而然达到“和”的地步了。老子所倡导的“小国寡民”社会以及庄子的“至德之世”,其实都是这样的理想社会。因为在道家看来,人的本真性情是自足的,是不喜干涉的,外在的礼乐仁义或者政治势力的干涉对人的本性都是一种戕害。因此道家特别是庄子主张个体性情的自洽自适,反对他者的干预,每个个体都遵循自身的性情,不干涉他人,特别是君主要采取无为的方式治理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会达到更高的和谐境地。也就是说,以无为作为一种“政治策略”①梅珍生:《论道家的政治和谐思想》,《江汉论坛》2012年第11期。,依靠百姓的自化自为实现社会群体的和谐与天下的大治。
值得注意的是儒、道两家对音乐与山水自然的观点也是异中有同。儒家的“乐和同”,其目的是通过“和乐”来实现人伦关系的和谐和睦。而道家则更看重“天籁”也就是未经人们音律调整后的清和之音,认为这才是“至和之声”。魏晋时的嵇康从“音声有自然之和”的立论出发,指出首先必须有人内在身心的平和,和声对人才能起正面作用,从而实现移风易俗的乐教目的。对于山水,儒家看重“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比德观念,而道家特别是从魏晋时起,沉醉于山水自然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境与生活就成为具有道家意识的士人或道教徒的一种精神寄托、生活理想或者精神境界。但是这种不同也不能极端分判。孔子曾指出礼乐并不仅仅是钟鼓玉帛,而是有其背后的“礼之意”即仁德精神存在的,这种仁德在“圣人”身上达到了非刻意为之的境地,也就与道家的“真人”境界相差无几,因此持庄学精神的嵇康非常称颂尧舜之为人,认为其是采取无为之道治理国家的。对于山水也是如此,无论是陶潜还是王维,其身上具备的不只是抛却俗务享受自然的精神意境,也具有悲天悯人的淑世情怀,只是后者遭遇困境时他们往往回归自然,对世界终究未能忘怀。这是因为儒、道两家在汉唐逐渐走向互补与融合,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精神信仰;游走于山水与俗世之间的士人从“心和”入手,体会“天和”“人和”贯通的个体之精神自由境界。
因此,虽然儒、道之“和”的内涵不同,但其目的是一致的,最终都是回到人与社会上,主张个体与社会达到一种合理合情和谐的关系,从而既实现个人的自由,也实现社会的安定乃至天下大同。这种和谐观是全面而深刻的,对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积极意义。这要求我们不必局限于儒家还是道家,而是从个体与自然(天和)、个体与社会(人和)、个体与自我心灵(心和)三个方面入手建构一个和谐社会。具体而言,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天和”、德治法治相结合建设法治社会以实现“人和”、节制欲望追求内在生命的自我成长以实现“心和”。其中“心和”的实现是根本的,由内在的“心和”扩展到外在的“天和”与“人和”才能实现更彻底的人我皆和、天下大和,如此才是在更深程度上实现中国传统中“和”的哲学诉求与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