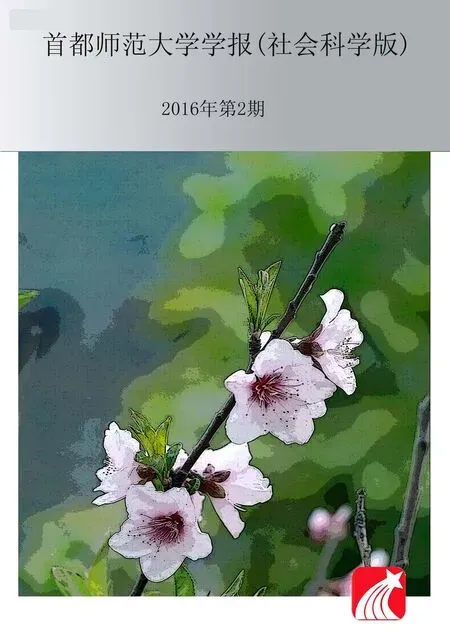试论宋代社会的赌场与赌风
纪昌兰
柜坊,《辞海》的解释:“唐宋都市中代客保管金银财物的商铺。其保管柜称‘僦柜’。唐时商业繁荣,城市中的富商巨贾,为了财物的安全或避免搬运麻烦,常将钱物储存柜坊。存户需用时,可出帖或用信物向之支领。到宋代,柜坊成为游手无赖销熔铜钱和赌博的场所,官府常加取缔,柜坊业务逐渐衰落。到元代已不存在。”①《辞海》经济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不难看出唐代兴起的柜坊,起初用于寄存钱物,是为适应日渐繁盛的商业活动而产生。随着时代变迁商业发展呈现新形式和特点,柜坊的这种功能遭到淘汰,最终演变成专门的赌博场所。
学界对柜坊早有研究,着眼点大都是唐代社会寄存钱物的金融机构,对宋代社会演变成赌场的柜坊并未着意探讨,②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认为,柜坊一种营业,亘唐宋二代皆流行。唐宋时代有柜坊一行受人委托,收受保管费,代人保管钱货;同时接收存户支票,支付现钱或现金银为主业,且以受人委托,代人售卖贵重品为副业(加藤繁著、王桐龄译《唐宋柜坊考》,《师大月刊》1933年第2期),并未对宋代社会变成赌场的柜坊探索。曹健民先生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赌博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其新特点之一就是出现了专门的赌博组织,但未深入探讨(曹健民主编《中国全史·赌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秦晖先生对唐代柜坊有所研究,参见秦晖:《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兼论封建后期金融市场的形成机制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尤其是赌场内部的运营、国家的管制及效果、唐宋时期赌博和赌场的不同时代特征等更是乏人问津。因此,本文的研究或可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
一、赌场的经营
宋代赌博非常普遍,尤其在节庆日更是烘托喜庆气氛必不可少的活动。北宋时期,“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①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6《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4页。宣和七年(1125)春,“开金明池,有旨令从官于清明日恣意游宴,是夜不扃郭门,贵人竞携妓女,朱轮宝马骈闐西城之外。诸公仍群聚赌博,达旦方归”。②曾慥:《高斋漫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京师人以端午日“为解粽节。又解粽为献,以叶长者胜,叶短者输,或赌博,或赌酒”。③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1《解粽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7页。到南宋更盛行,杭州地区除夕“小儿女终夕博戏不寐,谓之‘守岁’”。④周密:《武林旧事》卷3《岁晚节物》,杭州:西湖书社,1981年版,第47页。四川一带也如此,陆游就有诗曰:“呼卢院落哗新岁,卖困儿童起五更。”且在诗后注释“乡俗岁夕聚博,谓之试年庚”。⑤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38《岁首书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91页。为庆祝新年,老少皆参与其中,充满节日气息。冬至日都人“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遝于九街……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⑥周密:《武林旧事》卷3《冬至》,第45-46页。一般朝廷会在特定节日“纵民赌博”,“凡诸节序唯冬至寒食,虽小巷亦喧喧然者,以许士庶赌博,小人竞利喜为之”。⑦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5《重九中·无饮宴》,第390页。元旦,“天子受朝贺……三日,放士庶赌博”,⑧金盈之:《醉翁谈录》卷3《正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京师每遇冬至寒节假日,许士庶赌博”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七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736页。等。除节日外,平时人们也嗜赌成风。袁采披露当时社会风气:“士大夫之家,有夜间男女群聚而呼卢至于达旦”⑩袁采:《袁氏世范》卷3《赌博非闺门所宜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1页。,范成大诗“酒垆博簺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⑪范成大:《范石湖集》卷30《灯市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0页。将宋人的赌博热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嘉祐中,京西转运使陈希亮奏请河清知县著作郎王元规留任,理由是军民歌咏其任职期间境内有十奇,第七奇“不敢赌钱怕官知”。⑫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2《知县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01页。宋初,张咏为金陵守,殿直范延贵押兵路过,张便问范,沿路是否见到好官?范答:“袁州萍乡县邑宰张希颜著作者,虽不识之,知其好官员也”,只因“自入萍乡县境……及至邑则廛肆无赌博”。⑬魏泰:《东轩笔录》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5页。判断一个官员政绩好坏的重要标准是其境内有无赌博现象,恰恰说明一般情况下社会上赌风之盛。
赌博的盛行催生出专门的赌博场所——柜坊,供人们聚集赌博。由于赌博活动的群聚特性,对赌场位置的选择有特别要求,即一般设置在人员密集的商业区或交易往来频繁的市镇。北宋时期,都城开封繁华地带东角楼街巷就有“探搏饮食”⑭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东角楼街巷》,第145页。之类的活动。定州为重要的军事要冲,扼守河北和京师重地,宋人有“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⑮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86页。的说法,此处交易频繁,人员往来密集。元祐年间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⑯苏轼:《苏轼文集》卷36《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1页。透露出赌场位置较之一般场所需要人员密集、商业活动频繁的特性。
宋代赌场大多与酒楼、茶肆、妓馆等消遣地方兼营,或者可以说消遣的地方大都难以绕过赌场这个“销金窟”。嘉祐年间,苏颂“尹开封颇严……比方试进士,有博于肆楼者”。⑰苏颂:《苏魏公文集·谭训》卷5《政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7页。平民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⑱《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因赌博自缢》,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0页。池州东流县村墟,有少年数辈,“相聚于酒店赌博,各赍钱二三千,被酒战酣”。⑲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9《东流道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92页。南宋初,洪皓出使金朝,见到“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棋具也”。①洪皓:《松漠纪闻》续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反映出赌场与其他消遣场所兼营的时代特征,赌场经营的这种特色与现代社会各种“一条龙”服务有很大相似性。当然,这种特色也与国家禁止开办柜坊有一定关系,以开酒楼、茶肆等为幌子,开办赌场更容易掩人耳目。
赌场以金钱直接进行博弈,必须拥有雄厚的资本完成正常运转,加之内部鱼龙混杂,对开办者的资格有更高限制,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一定的政治资源,否则难以胜任。宣和六年(1124),有臣僚上言:“伏睹宣和二年御笔:‘在京官司辄置柜坊收禁罪人,乞取钱物,害及无辜,已降指挥,并令去拆,及已重立法禁,又访闻外路,尚有沿袭置柜坊去处,为民之害尤甚,限一日去拆’……然豪吏擅私,贪夫求利,覆出为恶,无所畏忌……欲望特降处分,在京选强明郎官一员,遍诣捉事使臣家,毁拆禁房……在外委监司,各据分界,岁巡州县,亲诣点检、毁拆,私置柜坊、禁房,见有拘留人户去处按劾以闻。”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九一,第6541页。天子脚下官吏们堂而皇之的开办柜坊,官官相护,禁令已然成一纸空文。赌场主本身是官场中人,又豢养豪吏作为爪牙,在利益的诱惑下,所谓“致君济民”的担当意识荡然无存。街市牙侩不良子弟黄松,“开置柜坊,停著赌博,势所必有”。③《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县尉受词》,第41页。赌场主黄松代表一股黑帮势力,拥有雄厚的资财,实力不凡。如果官吏开办赌场还有一定顾虑,那么宗室成员就肆无忌惮了。绍兴三年(1133)三月,诏书有言:“宗室及有荫不肖子弟多是酤私酒,开柜坊,遇夜将带不逞,杀打平人,夺取沿身财物。”④(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八,第6569页。其行为之猖獗甚至惊动朝廷。另外还有打着宗室招牌开办赌场者:赵汝佛冒充宗室成员,“开置柜坊,宰杀耕牛,奸夺妻女,骗诈店户”,⑤《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假宗室冒官爵》,第400页。宗室成员被冒充,说明这一身份对不法活动的庇护作用。这些真真假假的宗室成员以柜坊为依托,打杀劫掠,无恶不作,俨然是独霸一方的黑恶势力。
对赌场主而言,面对国家法律的打击,维持赌场运转单凭雄厚的资产和相当的管理能力远远不够,还需一定的社会关系维系这种高风险“产业”。勾结官吏和黑恶势力是其常用手段,也是宋代国家对开办柜坊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宋光宗时期,朱熹知漳州,发布约束榜文:“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赏钱三十贯文,禁止百姓及军人赌博,仍拆毁柜坊,并告报诸营寨厢官及遍牒在城诸官,听常切觉察钤束,非不严切,今来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开柜坊,停止军兵,百姓公然赌博,全无忌惮,厢巡容纵,兵官亦不钤束,深属不便出榜。”⑥朱熹:《朱熹集》卷100《约束榜》,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22页。朱熹注意到赌场主勾结官吏,诱使兵民赌博的行径,并指出当地兵官“容纵”开柜坊的现象,说明赌场开办者与兵官狼狈为奸,逃避国家法律制裁。《名公书判清明集》宗室犯罪的判词:“赵若陋者,专置譁局,把持饶州一州公事,与胥吏为党伍,以恶少为爪牙,以至开柜坊,霸娼妓,骗胁欺诈,无所不有。然亦官司有以纵之,今不暇尽述其过恶”。⑦《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宗室作过押送外司拘管爪牙并从编配》,第398页。赌场主赵若陋“与胥吏为党伍,以恶少为爪牙”、“骗胁欺诈,无所不有”,可谓恶贯满盈,官司却“纵之”,究其原因无非是赵若陋平日勾结官吏和黑恶势力,使赌场在夹缝中生存下来。以上种种,说明在宋代柜坊的生存和运作充满“技巧”。
具体到柜坊内部的运行与管理,更是机关重重。出入赌场的人员三教九流,赌博本身又是投机冒险行为,赌徒们心存侥幸,幻想通过赌博改变命运。参赌过程中稍有不顺就会引发冲突,加之赌场是直接与金钱打交道的场所,更要严加防护,须专门人员维持赌场秩序。因此赌场大多会雇佣打手作为“保安”,其在维护赌场内外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史载:“京师升平之久,无知之民,游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居外,皆在火房、浴堂、柜坊杂居。”⑧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2页。这些游手好闲的流动人口杂居在各种“公共”场所,大都靠打杂维持生存,寄居在赌场内者无非是赌徒或赌场伙计,成为赌场伙计,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维持赌场秩序的职责。宝庆年间,婺州“城中则有开柜坊停者,赌博者,其风甚盛,多是十数为党,倚骄惰之卒,无藉之胥为之持局”,①曾枣庄主编:《全宋文》卷7803,王柏《述民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册第297页。本该维护地方治安的卒与吏人俨然成了赌场的保护神,正是依靠他们赌场才得以正常运转。
为赚足腰包赌场主更是想尽办法榨取赌徒的钱财。元祐八年(1093)十月,苏轼上奏朝廷,指出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牓,召军民赌博”,②苏轼:《苏轼文集》卷36《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第1021页。利用广告宣传手法招徕顾客,与正常营销手段没有区别,但赌场运作仅凭这种手段难达“销金”目的。临安就有所谓“柜坊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赚财物。③(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3页。据载,“无赖辈以赌博为名,诱陷良家子生生至破产,俗呼松子量……在处有之,而杭繁盛,故特甚,入其中者,初不自觉,计所得随手分散,以钤众口而把持之,号分子钱”,④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19《故朝请郎直秘阁淮南江淛荆湖制置发运副使赠徽猷阁待制胡公行状》,《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7册第203页。宝庆年间,婺州城中开柜坊赌博者,“引诱良民,欺骗博脱合分财物”。⑤曾枣庄主编:《全宋文》卷7803,王柏《述民志》,第338册第297页。至于欺诈手段,以下记载或许能窥见一斑:
照得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徐庆三、何曾一、王寿、余济皆与踰滥,与以钱物,群聚赌博,实为欺骗渊薮……支乙与郑厨司、杨排军商量,遂出赌博具下场赌,有余济、陈通者闻风而至,亦与赌博。一时余济等能将骰子两只,当留六两面大采靠掷,或下枚人喝跷,不与陆震龙理赢下枚,遂致陆震龙输过带来旧会二百五十贯,其陈暹等赢过之数各有差,支乙等取过头熟亦各有数。及既二鼓,陆震龙又自家中办到旧会一百五十六贯,复与余济等赌博,支乙再出赌具在旁下枚。其余济等常留五六靠掷,共骗赢陆震龙一人钱物。陆震龙既输带来之钱,又以汗衫褐袄典当赌博,得官会三十五贯。既输之余,又多输官会二十贯,遂剥皂褙抛当于余济边,其余济等骗赢陆震龙官会亦各有差,支乙等讨取头熟各有其数。陆震龙前后共输旧会四百六十一贯……陆震龙深夜欲归,无衣可着……夫药骰子骗人,出于一人之手,而众人为之犄角,今余济等数辈,各能留五留六靠掷,欺骗赢钱,则与用药骰子何异。⑥《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因赌博自缢》,第530-532页。
以上详细勾画出了赌场的欺诈手法,其“药骰子骗人,出于一人之手,而众人为之犄角”。大致看来,赌场中的“托儿”都是扮演各种诈骗角色的好手,应当时场合的需要,使出浑身解数,运用各种卑劣手段,只为骗取赌徒的钱财。赌徒们赢钱心切,不知不觉陷入圈套中,往往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柜坊则“日进斗金”,成为名副其实的“销金窟”。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一般不把赌场称柜坊。元和年间,有牛黑子者“带了钱到赌坊里去赌”。⑦(明)凌濛初:《拍案惊奇》卷36《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梦粱录》更有“穷富赌钱社”⑧吴自牧:《梦粱录》卷19《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的说法,大概柜坊是官方的书面叫法,与当代口语“赌博”及官方语言“博彩”属同种事物却不同称呼一致。
二、官方对柜坊的管制及实效
早在建国初,宋廷即下令禁赌,对开场招赌更是严加管制。淳化二年(991)诏:“京城无赖辈相聚蒱博,开柜坊……令开封府戒坊市,谨捕之,犯者斩,匿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同罪”。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13页。可见,宋初对开办柜坊招人赌博行为判罚相当严厉,直接处以死刑,不过这是对京师重地的区域性规定,存在树立天子威严的目的,有相当的威慑成分。也有适于全国范围的法律,明道二年(1033)敕文明确指出:“禁民间诱聚兵民赌博之家,官司严行捕捉,人得告言犯者,具狱当议投配恶地,告言有赏,纵而不察,有司论罪”。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四,第6944页。对开赌场聚众赌博的判罚是投配到“恶地”。康定二年(1041),开坊赌博规定有变化:知仪州、礼宾副使曹僖言:“应开柜坊停留军伍樗博之人,乞依法决讫刺配清边弩手”。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二〇,第6631页。得到朝廷批准。关于“清边弩手”,《宋史》中记载,大将明镐“尝阅同州厢军,得材武者三百余人,教以强弩,奏为清边军,号最骁悍。其后陕西、河东颇仿置之”。③(元)脱脱:《宋史》卷292《明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769页。可见清边弩手是宋代国家的一类兵种,可以说康定年间对开坊赌博的判罚较明道年间有一定松弛(虽然诱惑赌博的对象“兵民”和“军伍”范围有所不同,但毕竟都是开坊聚赌的性质),因为无论如何,刺配做清边弩手总比发配到“恶地”接受管制遭遇要好些。
南宋时期,对开坊赌博的判罚有变化。《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开柜坊停止博戏、赌财物者,邻州编管。于出军营内停止者,配本城并许人告。厢耆巡察看营,入宿提举人失觉察者,杖八十。”这条敕文对柜坊开办者、失察者、赌博者的判罚都有明确规定。对告密者也有相应奖赏:“诸告获开柜坊或出军营内,停止博戏赌财物者,在席及停止、出九、和合人所得之物悉给之。”另外“诸色人,告获开柜坊停止博戏财物或于出军营内停止者,钱一十贯”。④《庆元条法事类》卷80《杂敕.博戏财物》,燕京大学图书馆1948年影印刻本,第1-2页。这些条款对赌博的各个环节都有严密规定,可见朝廷对禁止开坊赌博行为的决心。对比两宋法规,南宋的判罚力度已呈现减弱趋势,逐渐由北宋的处斩、编管恶地、刺配为兵转变为邻州编管。这一变化或许是对社会上开坊赌博行为普遍化的一种被动调整。
国家在法律上对开坊赌博严密规定,不代表此类行为的禁绝,法律效力的生成还需看其执行效果。元祐八年(1093)十月,苏轼状奏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牓,召军民赌博”,最终“开柜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陈首改业,其余并走出州界。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⑤苏轼:《苏轼文集》卷36《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第1021页。可见,苏轼对开坊赌博的基本处罚是改业,并未按照此前法律规定的发配边远恶地或做清边弩手,且他对这种判罚及所获效果颇自负,透露出当时社会普遍存在官员对开坊赌博行为的纵容。宋光宗时期,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发布约束榜文:“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赏钱三十贯文,禁止百姓及军人赌博,仍拆毁柜坊,并告报诸营寨厢官及遍牒在城诸官,听常切觉察钤束”。⑥朱熹:《朱熹集》卷100《约束榜》,第5122页。对开坊赌博没有具体规定,拆毁了事。《名公书判清明集》相关判罚更清晰:“本府严赌博之禁……袁六二系开柜坊停止赌博之人,杖一百,编管邻州,仍诉毁停止去处”。⑦《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自首博人支给一半赏钱》,第533页。罗友诚“开张质库,且有文约可凭,今已越八年矣……所谓开库,系是柜坊……罗友诚勘下杖一百,锢身押下县”,⑧《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领库本钱人既贫斟酌监还》,第335页。对开坊赌博的判罚主要是“杖一百,编管邻州”,但开坊者身份不同判罚也有差别。宗室成员赵若陋,其“专置譁局,把持饶州一州公事……以至开柜坊,霸娼妓,骗胁欺诈,无所不有……申省及宗司,将若陋押送外宗拘管,并移其家。所有陈念三、陈万三并系其爪牙,亦自有司置柜坊本罪……陈万三追上杖一百,送邻州编管”。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宗室作过押送外司拘管爪牙并从编配》,第398-399页。犯开坊等罪名的赵若陋是宗室成员,受到“押送外宗拘管,并移其家”的处罚,同伙陈万三则“杖一百,送邻州编管”。可见,宗室成员的特殊身份起到了保护作用,较之平民,所受处罚要轻很多。这些判罚案例透露出开坊聚赌禁令在执行过程中松、严参差不齐,但总体是有收效的,至少对肆意开办赌场有震慑作用。宋人王栐对淳化二年(991)朝廷颁布的关于开柜坊赌博者处斩的诏令评价道:“所以塞祸乱之源,驱斯民纳之善也。其后刑名寝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尝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视此三者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尝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是开盗贼之门也,毋乃不思之甚乎”。①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严禁蒲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说明官员中普遍存在视而不见的包庇行为,枉法者、疏于执法者大有人在,且呈风靡之势。南宋绍定四年(1231),李宗勉(文靖公)知台州,“与陈文逸民饮玉霄亭上,良久,忽移过君子堂。陈文告曰:‘此间不如玉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掷骰赌博,争注喧哗,姑避之。’”②车若水:《脚气集》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作为台州的主管官员,面对聚赌喧扰行为,并非像想象中依法纠治,而是“避之”了事,对散布在境内各处开坊赌博行为的整治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可以想见其他地区官员类似做法的普遍性,否则,不会出现前面所述军民歌咏王元规任职期间境内有十奇,第七奇“不敢赌钱怕官知”的现象,透露出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种种弊端。当然,从制度层面来看,宋朝政府禁赌决心是坚决的。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今律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宋制之严如此,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刑乱国用重典,固当如此”。③(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8《赌博》,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01-1002页。言语间对宋朝政府厉行打击赌博的做法充满赞许,只是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效力大打折扣,开坊聚赌行为禁而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三、从宋代赌场的盛行看唐宋社会的变化
“唐宋变革”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变革的种种表现更是不胜枚举。单就开坊聚赌现象本身来说,唐宋社会就有很大不同。从法律层面来看,《唐律疏议》针对当时社会赌博行为有如下规定:“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己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九,若和合者,各如之。赌饮食者,不坐。【疏】议曰:‘停止主人’,谓停止博戏赌物者主人,‘及出玖之人’,亦举九为例,不限取利多少。若和合人令戏者:不得财,杖一百;若得利入己,并计账准盗论”。④(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26《杂律十四博戏赌财物》,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4册,第34—35页。以上,唐代律法对赌博参与者、组织者都有着严格的法律规范,但缺乏明确的关于开办赌场的规定,是否说明那个时代这种行为不多见?或法制体系不健全?这些疑问或许能从以下的分析中得到解答。
在唐代赌博行为并非罕见。咸亨中,贝州潘彦好赌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⑤(唐)张鷟:《朝野佥载》补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8页。永昌年间,监察御史张东之揭露姚州官属“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蒲博,一掷累万”。⑥(五代)刘昫:《旧唐书》卷91《张东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40页。言语间透露出当时这些官僚聚会赌博似乎没有固定场所,只是聚集时的一种消遣,这种推测从以下的记载得到了印证。天宝年间,万年尉韦黄裳、长安尉贾季隣“常于厅事贮钱数百绳,名倡珍馔,常有备拟,以候准(官僚王鉷之子)所适。又于宅侧自有追欢之所”。⑦(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05《王鉷传》,第3230页。在官署或宅子准备赌资,营造赌博场所,行赌博之便。唐玄宗时期盛行叶子格赌博法,“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⑧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6页。揭示出士大夫喜好在宴集时赌博,这种现象在唐代非常普遍。咸通末年,卢澄任淮南节度使李蔚的从事,“因酒席请一舞妓解籍,公不许,澄怒,词多不逊……澄索彩具,蔚与赌贵兆”。⑨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9页。冯衮做苏州郡守时,“优游暇日,辄纵饮博,因会宾僚,掷卢,冯大胜,以所得均遗一座”。⑩范成大:《吴郡志》卷11《牧守》,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6页。唐人薛恁《戏樗蒲头赋》:“招邯郸少年,命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樽举酒。犹贤博弈,将取适于解颐;乃贵先鸣,故决争于游手。终日莫闲,连宵战酣。”⑪李昉:《文苑英华》卷100,薛恁:《戏樗蒲头赋》,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60页。都反映唐时人们有在宴集时赌博的喜好。大概宴集时赌博更能尽兴,逐渐变成这种场合不可缺少的助兴活动。关于当时的赌博,史载:“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甚……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食,闾里用之,于是强名争胜……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①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8,第683页。透露出唐代王公大人赌博热情高涨,只是这种赌博发生在“闾里”间,未扩展开来。以上,唐代社会聚集赌博现象虽不少,但规模不大,未形成专门、固定的赌博场所,且参与者多是王公大人,与宋代社会全民皆赌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别恰恰说明“唐宋变革”确实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影响。钱穆先生曾指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②钱穆:《理学与艺术》,《故宫季刊》1974年第4期。张邦炜先生在《“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一文中认为:“称宋代为平民社会,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平民化趋势。”(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平民社会”与“贵族社会”的区分具体到赌博中就是唐宋社会参与赌博群体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又导致两个时期赌博特点的截然不同,其中就包括赌场专门化、固定化。
赌场专门化、固定化根本上应归因于经济的繁兴。宋代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史学前辈的一致肯定,而何以在唐代用来储存钱物的机构——柜坊,发展到宋代却成为专门的赌博场所?有学者认为恰恰是唐末至宋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坊市壁垒的打破,“日中为市”的时间限制取消,柜坊原有职能逐渐消失。③秦晖:《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兼论封建后期金融市场的形成机制问题》,《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关于柜坊功能转变的原因,陈明光先生认为主要当是社会需求的变化。纸币解决了铜铁钱携运和交易的不便;盐引、茶引等有价证券取代现钱而流行,消除了以往用铜铁钱交易的不便。总之,笨重的钱币大量退出流通领域,使代人保管钱币的柜坊失去服务对象,衰败势在必然(陈明光《钱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在于道出了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发生改变,柜坊储钱存物功能被淘汰。事实上,这种变化在唐代后期就已露端倪。会昌三年(843)五月,京兆府奏:“‘两坊市闲行不事家业,黥刺身上,屠宰猪狗,酗酒斗打,及僦构关节,下脱钱物,摴蒱赌钱人等。伏乞今后如有犯者,许臣追捉。若是百姓,当时处置,如属诸军诸使禁司,奏闻。’从之”。④王溥:《唐会要》卷67《京兆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88页。说明唐末柜坊职能的转变势所必然,发展到宋代变为赌场在情理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坊市制度打破,人们的活动空间变得广阔,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赌博。当赌博演变成一种社会风尚时,就需要为大众提供专门的活动场所,赌场应运而生,加之柜坊长期以来与金钱有密切关联,使其得以顺利演变为另外一种金钱快速流通场所——赌场。
“唐宋变革”另一显著影响是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受到挑战。宋代实行土地私有,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已不甘于躬耕田亩,一旦获得机会就选择离开田地另谋生路,整个社会弥漫着“轻农”的思想氛围,这种转变在宋代社会非常明显。早在北宋中期,苏轼就指出:“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则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居而乐之”。⑤苏轼:《苏轼文集》卷8《策别安万民三》,第259页。刘挚也注意到这种现象:“无悦而愿为农者……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惰游”。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第5447页。这种趋向令司马光十分忧心,元丰八年(1085)八月他在奏疏中写道:“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至使世俗俳谐,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9,元丰八年八月乙丑,第8590页。社会上这种“舍本逐末”的趋向发展到南宋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农商的传统看法,叶适就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⑧叶适《习学记言》卷19《平准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3页。正是彼时舆情的真实写照。离开土地的农民,四处寻找谋生机会,冲击着传统社会的分工格局,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促使整个社会变得开放。①冻国栋先生指出:“在唐宋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的职业结构所发生的某些变化是引人注目的,最主要的变化乃在于‘四民分业’界限的相对模糊以至混杂,此外则是城市居民职业的广泛性,已远非‘四民’所可涵盖。”冻国栋:《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暨南史学》第3辑。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也认为:“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唐研究》第11卷。有学者就敏锐指出:“宋代失去土地的流动人口,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可以比较自由地探寻生活之道。这是唐宋变革的产物。”②程民生:《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而在唐代均田制束缚下的人们无法自由迁徙。随着人口流动性加强,闲散人员增多,赌博这种充满投机的活动为其谋生提供捷径,短期内改变命运成为可能,从而促进赌博和赌场的兴盛,也成为令当政者十分头疼的问题。北宋时期,四川井研县制作井盐的家庭作坊“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譁譟,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③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5-16页。此外“镇市乡村有行止不明、无图运作过之人,并开柜坊”,④李元弼:《作邑自箴》卷6《劝谕民庶榜》,四部丛刊续编本,第64页。“荆土市廛子弟,多因挟赀在手,饮博浪游”⑤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1《江陵村侩》,第883页。等等,可以说社会流动性加强⑥张邦炜先生同样认为:“宋代与前代相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与赌场的盛行都诞生于“唐宋变革”这个母体中,只是社会流动加强后,赌博活动更加猖獗,赌场变得“兴旺发达”起来。
结语
在宋代赌博是违法的,受到国家管制。从道德层面上讲,亦属“大逆不道”行为,遭到社会的谴责和批判。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宗法——伦理三位一体的文化格局中,由于赌博从本质上与‘重义贱利’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相悖,因此其文化本质实属于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⑦涂文学:《赌博纵横》,北京:中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事实上,赌博不仅与“重义贱利”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相悖,还与长期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树立起来的中国传统道德观背道而驰。也正因此,赌博在宋代受到广泛批判。吴泳认为:“饱暖则生逸乐,逸乐则生慢易惰,弃农桑,崇纵饮博,入不能孝养父母,出不能顺事长”。⑧吴泳:《鹤林集》卷39《宁国府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第382页。朱熹说:“只如今赌钱吃酒等人,正在无礼,你却将《礼记》去他边读,如何不致他恶!”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3《孔孟周程张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60页。真德秀有言:“非法之事莫妄做,如聚众斗殴、开坊赌博……如此之类,皆系非法无理之事,莫妄兴”。⑩真德秀:《政经》之《谕俗榜文》,《中华百科经典全书》,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册第287页。喻汝砺也指出:“处约者道必远,嗜利者毒必厚。郤至居赌而亡……甚矣哉,利之溺人也!”⑪袁说友:《成都文类》卷44《义勝轩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49页。吕公著“尤不喜人博,有‘胜则伤仁,败则伤俭’之语”。⑫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9《善博曰胜》,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8页。以上种种,宋人从各个角度对赌博行为进行谴责,包括赌博“不孝”、“无礼”、“非法”、“重利轻义”、“伤仁”、“不俭”等,从这些理由可以看出赌博是对传统道德的一种颠覆,严重违背社会礼法规范,势必受到舆论的批判。但任何一种行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存在的道理,不会因为社会舆论和道德的约束而止步不前或消亡。清朝时期,人们“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将不知所底矣”⑬(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3《赌符》,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30-131页。之类认识恰是对社会上难以遏制的赌博现象的一种强烈挞伐和深刻反思。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社会赌博风气根深蒂固,试图利用舆论力量从道德层面予以制止难达目的,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国家法律的规范和制裁,关键在于执行力度的掌控,只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赌博行为的蔓延。社会舆论和道德约束只是法律的辅助工具而已,永远无法取代法律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