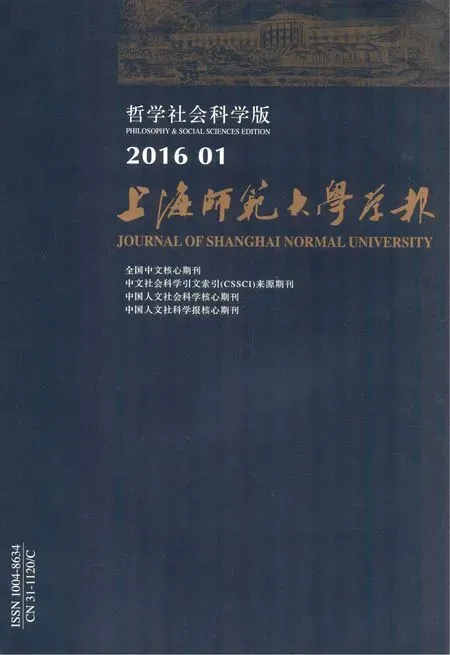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及影响
俞 钢,薛璞喆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三部有着继承关系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章氏的《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做了最为全面的总结阐释,堪称集大成者。回眸历来围绕章氏《文史通义》的研究,学者们往往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角度展开论析,而少有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视野探究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价值和意义的成果。笔者认为,尽管章氏用《文史通义》名其著作,但他的精辟论述实际上已超越了文学与史学通义的范畴,所谓“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1](卷6,P655)故非常有必要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视野重新加以阐析。本文试就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和影响展开讨论,以期揭示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的主旨。
一、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形成
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学术成果重新梳理和汇通明义基础上的,也理应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一脉相承至晚清的时代产物。相对于近代留学西洋的学者所带来的学术观念,章氏的学术观念明显打上了传承与演进的烙印,这主要体现在他依然从传统的文、史角度去找寻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的轨迹和蕴含其中的思想精义,试图成为经世致用的着力点。因此,探析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形成,就有必要考察他对传统四部之学、已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学术风气的认识。
首先,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形成,源自他对传统四部之学的梳理辨析。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学术史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体,源远流长,分支众多,其绵延积累的学术成果基本著录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就四部之学的重要性而言,历来首推神圣的经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源头,逐渐演变成九经、十三经等,建构起了儒家经典理论体系。正如章氏所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1](卷1,P94)史学仅次于经学,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史官制度和精神一直传承有绪,其源头甚至早于经学,而其成长则更是枝繁叶茂。对于史学的演变,章氏做了精辟的梳析: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退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卷1,P50~51)
显见,章氏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史学纪传体之祖,而其又是经典《尚书》和左氏《春秋》之流变,故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至于子部和集部之学,前者属于诸子百家言,从先秦儒家学说开始,逐渐形成了墨、道、名、法等诸子百家学说,其后佛学、理学等入流,由于诸子百家探讨人类和自然的专门问题,乃私家之思想和智慧宝库,也就足备四部之一的学术地位;后者大致归属于文学,虽源出《诗经》,但在四部之学中最迟形成,由此以诗文、戏曲、小说等构成的总集和别集蔚为大观。对于集部之学的形成,章氏评论曰:
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也。[1](卷1,P61)
由此可知,章氏视集部为“辞章之学”,应属文学的概念。从章氏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认识来看,他特别强调史学在经学之前,又多得经学之遗,所谓“六经三史,学术之源”,[1](卷4,P355)而“后世集部,即古代子部之流变”,[2](P5)因此考镜四部之学的源流,大致可以缕析为史学和文学两大学术体系。
其次,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形成,明显深受刘勰《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这两部学术理论著作的影响。章氏在《与严冬友侍读》一文中指出:
日月悠乎,得过多日,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马班,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3](卷29,P333)
这里,所谓“下该《雕龙》、《史通》”,而作《文史通义》,明显反映出章氏的学术观点与已有学术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和帝年间,不仅系统梳理了以往的学术成果,而且以经制文,初创了文学理论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章氏论及《文心雕龙》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六艺(义)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而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者,亦于是而益广也。[1](卷1,P79)
又曰:
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1](卷3,P278)
可见,章氏是将《文心雕龙》置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进步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他对《文心雕龙》学术贡献的清晰认识必然影响其学术观念的形成。刘知几的《史通》,撰成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内涵极为丰富,几对唐以前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尤其侧重于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而使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有了第一部理论著作,恰如学者们所言:“《史通》的出现,标志着《史记》、《汉书》以来主要在编纂实践上一支独秀的史学,产生了从学科内容和形态上进行全面自我检讨的重大转折。”[4](P291)就章氏《文史通义》内容来看,笔者发现,章氏对刘知几《史通》的观点多有直接评论,如《书教·中》曰:
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亦知《尚书》折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和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后人讫莫之行也。[1](卷1,P40)
又如《说林》曰:
唐世修书置馆局,馆局则各效所长也。其弊则漫无统纪,而失之乱。刘知几《史通》,扬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准焉,所以治散乱之瘴历也。[1](卷4,P355)
显然,章氏学术观念的形成也是受到《史通》影响的。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刘知几的《史通》,再到章氏的《文史通义》,无疑存在着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更反映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由偏文和偏史走向成熟全面的演变规律。
其三,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形成,还应与他身处的清代乾嘉学术风气有关。我们知道,自清初开始的考据学,至乾嘉时期而称极盛,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以惠栋、戴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潜心于音韵训诂、文字校勘、名物辨伪、版本鉴定等,试图通过回归“汉学”的实证努力,从治音韵文字中明白义理,以改变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学术风气。应该说,乾嘉学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一些名师大家,不仅考据学功力深厚,著作丰赡,还由此进一步阐发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学术思想,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2](P232)但是,乾嘉考据学主流学风“征实过多,发挥过少”的弊端,[3](卷9,P82)也确实造成了负面影响,尤其是注重考据方法、轻视析理明道的学术引领,使许多人埋首于故纸堆中,迷失了治学的宗旨和方向。章氏身处这一时代,却并不趋时徇风,而是继承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深刻反思乾嘉考据学的得失,并从学理上对乾嘉考据学的弊端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所谓“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也”,[1](卷2,P154)由此发出了与时异趋的强音。在章氏针对时弊而发的诸多论议中,笔者认为,其倡发“六经皆史”说,强调汇通明义,应该是他“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
章氏的《文史通义》,首篇《易教·上》第一语就说:“六经皆史。”[1](卷1,P1)在他看来,原本只有六艺的说法,而无六经的尊称,其后诸子立说,才由孔门弟子改称六经,并逐渐演化为不可触犯的经典。其实,经为史所包,“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3](卷9,P86)由此,他指出: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纠大道也。[1](卷2,P138)
很明显,章氏“六经皆史”说的倡发,是对考据学通训诂可明义理主张的批评。既然六经并非神圣的经典,后世有“六经不能言”者,就可以“约六经之旨”而随时进行史学的撰述,由此也就动摇了考据学的学理基础。
章氏的独到之处,并不仅仅在于狭隘地固守史学天地,而是在于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强调学术的汇通明义。笔者注意到,在《文史通义》中就有《释通》《横通》等篇专论“通”,又有《原道》《原学》等篇专明“义”,充分体现了章氏所言“通”和“义”的含义。其曰: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至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1](卷4,P372)
又曰:
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去圣久远,于事固无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1](卷2,P138)
从中显知,一方面章氏特别注重治学的通达,有此境界可以“通天下之不通”;另一方面他在批评考据学“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的同时,提出了“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非可限于隅曲”的观点,并以为如此才能达到“独见天地之高深”之学术道义。
简而言之,章学诚通过梳理传统四部之学的渊源,特别强调史学在经学之前,又多得经学之遗,而集部之学则是子部之流变,大致可以缕析为史学和文学两大学术体系;通过考察刘勰《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这两部学术理论著作,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发展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反映了传统学术思想由偏文和偏史走向成熟全面的演变规律;通过评析清代乾嘉学术风气,不仅抨击乾嘉考据学的弊端,还提出了“六经皆史”、汇通明义等重要的学术主张。笔者认为,章氏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应该是他“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
二、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
章学诚提出的“交相裨益”学术观念是他汇通明义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主要是指他所认为的传统文学和史学两大类之间的互证通义、交相裨益。章氏著《文史通义》的用意,正是试图把包括一切文字的文史之学加以汇通,并揭示出学术的道义,恰如刘咸炘所云:“书(《文史通义》)本通论四部,乃舍经、子、集而但言史,又加文于史上者,盖谓凡书皆文,文之原则史。”又云:“此篇(《释通》——笔者按)专论史法,乃先生之大计。不可通者各归其分,可通者归于大原;不可通者勿强通,可通者勿自蔽;乃先生学术之大本,亦即此书所以名‘通义’也。”[5](P1057~1058)
章氏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说:
故左氏论次《国语》,未尝不引谚证谣;而十五《国风》,亦未尝不别为一编,均隶太史。此文选、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验也。[1](卷8,P828)
这里,章氏明确提出了“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在他看来,左丘明编撰《国语》时就曾“引谚证谣”以裨益于史,而《诗经》中的《国风》则出自于史官之手,颇裨益于文,这就是文史交相裨益的明证。笔者发现,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在他的《文史通义》等论著中多有反映,并具体延伸出以文证史、以史裨文等学术方法论,由此构成了丰富的学术内涵。
章氏认为,文学和史学是春华和秋实的关系,诸如诗赋、古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不可能脱离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质,因此它们可以辅证记载重大事件、人物和崇尚求实、求真的史学,也即可以用文学来辅证史学。他在《书教·中》中指出:
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1](卷1,P40)
在他看来,魏晋以后文学成果丰硕,但“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故《文选》《文苑》等汇次铨括一代之文学著述,其后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想要“包括全代”、“与史相辅”,实质上乃“言事分书”,可以补史之阙。又章氏《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云:
文有关于士风、人事者,其类颇夥,史固不得而尽收之。以故昭明以来,括代为选,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明有《文选》,广为铨次,巨细毕收,其可证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1](卷8,P792)
可见,章氏认为,《文选》《文苑》《文鉴》《文类》等“文有关于士风、人事者”,“巨细毕收”,“史固不得而尽收之”,由此“可证史之不逮”。章氏还以《文鉴》为例加以说明:
《文鉴》之并收制科,则广昭明之未登,亦犹班固《地志》之兼采《职方》、《禹贡》。[1](卷8,P837)
宋吕祖谦的《文鉴》记载了有关宋代制举的内容,笔者细检《宋史·选举志》,确实没有专论宋代制举的内容,显然《文鉴》的记载可以补证宋代制举资料之阙失。
章氏从史学的角度,认识到诗赋、小说等与政事的关系,并通过考究诗赋、小说等的文辞典故和现实背景,指出这些资料可以用来辅证当时的社会生活。他的《永清县文征序例》云: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于司乐,篇什叙于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于是声诗之道,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1](卷7,P643)
所谓“汉魏而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强调的正是通过“指事类情”的诗赋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信息,具有“证其时事”的作用。以小说证史,章氏在《乙卯札记》一文中曰:
近世尊官称大人,卑者为老爷。赵耘菘谓:“大人本父母。”而以为尊者称,起于汉世中官。后世因为达官之称。爷,本父之称谓,自高力士承恩日久,中外畏之,驸马辈直呼为爷。后世王爷、公爷、老爷之名称,亦自此始。然观明人所为《金瓶梅》,小说于尊者称为老爹,老爹即老爷也,以称太师、提督、抚按诸官,如知县、千户等官,则以大人呼之,疑明时称谓与今互异。[3](外编,P365)
这里,章氏考察了“大人”、“老爷”称谓的变化,并以小说《金瓶梅》的描述作为依据,特别指出明、清两朝在“大人”、“老爷”称谓上是“互异”的。按章氏之意,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小说对背景的描写则应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样可以用来辅证史实。
当然,章氏并不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证史,对于那些“文采斐然”而“不知本事始末”的文学作品,他指出:“论文有余,证史不足,后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1](卷6,P594)笔者细究章氏以文证史的学术观念,发现他多从指事类情、事类相通的角度论证文学作品辅证史学的功用,并由此出发,强调通过考辨不同时期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事类,可以补证史学之不足。客观地说,章氏的这种学术观念指明了以文证史的学术意义,较之于只重文字训诂的考据之学更为高明。
文可证史,史亦可裨益于文。章氏认为,以史裨文集中体现在文人以史例为参照对象从事文学创作、史学求真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正史为小说提供叙事基础等方面。章氏《答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云:
辱示《文选》义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复。夫踵事增华,后来易为力,括代总选,须以史例观之。昭明草刨,与马迁略同。[1](卷8,P594)
可见,章氏认为,《史记》与《文选》在义例上有相通之处,《文选》的文例深受《史记》的史例影响。在章氏看来,南朝以后的文学创作大多以史例为模仿对象,其《文理》篇云:
归(有光)氏之于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顺之)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1](卷3,P286)
又《古文公式》篇云:
此碑(《表忠观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时奏议上陈、诏旨下达之体。而苏氏意中,揣摩《秦本纪》“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语太熟。[1](卷5,P497)
显知,明代归有光的时文创作是描摹《史记》而成的,而苏轼《表忠观碑》同样模仿了《史记》的史例,史学的体例裨益于古文的创作。
章氏认为,史学求真的精神对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文德》篇云: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卷3,P279)
这里,他以《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两部史著为例,着重指出了两点:其一,后世文人不知古人所处之时代,“不可妄论古人文辞”。其二,后世文人仅知古人之世而不知古人身之所处,“不可以遽论其文”。笔者以为,章氏所强调的正是史学求真的精神,这对于后世文人论古人文辞多有启发意义。
至于正史为小说提供叙事基础,章氏在《丙辰札记》一文中云:
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其所惑乱,如桃园等事情,学士大夫真作故事用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诫,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3](外编,P385)
他把小说划分为纪实、虚构、虚实相间三类。纪实类小说,通常以正史的记载为基础,将其转换成文学作品,以史裨文的作用显而易见。虚构类小说,无伤大雅,可供阅读,但故事情节相对偏离史实。虚实相间类小说,如《三国演义》,七分实三分虚,往往难辨虚实,易使读者“为其惑乱”。尽管章氏认为虚实相间类小说“实有益于劝诫”,但他主张“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明确反对虚实错杂,由此可观章氏以史裨文的学术观念。
此外,笔者注意到,章氏在阐述以文证史、以史裨文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同时,还敏锐地提出了姓纂、氏族志类文献具有证史功用的看法。章氏《与汪龙庄简》一文云:
大著以史为主而类其姓,仍当以姓为主而证其史,则彼此互通又可得许多增益。如《元和姓纂》、邓名世《姓氏书辨证》、郑樵《氏族略》等书,大抵以韵分编,若将诸书购集,与《万姓统谱》、《姓苑》诸编一体采取,反证史书,可以得往复交推之益。[3](卷29,P334)
章氏的这一主张,是专门针对传统史学排拒姓纂、氏族志类文献而提出的,他在《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一文中就指出:“至郑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叙例之文,发明谱学所系,推原史家不得师承之故,盖尝慨切言之。而后人修史,不师其法,是亦史部之阙典也。”[1](卷6,P631)我们知道,姓纂、氏族志等原本的功能是奠世系、辨昭穆、明门第等;至宋代以后,由于著录氏族谱系多为地方大姓自己修撰,故姓纂、氏族志类文献也就被排拒在正史之外。对此,章氏认为,正史“以史为主而类其姓”,姓纂、氏族志类文献则“以姓为主而证其史”,如果两者“彼此互通”,可以得到“许多增益”。具体而言,如果将大抵按韵分编的姓纂、氏族志类文献与《万姓统谱》、《姓苑》等一体考察,用以“反证史书”,还可收到“往复交推之益”。可见,章氏特别注重姓纂、氏族志类文献是很有见识的,这也为他取得编修地方志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综观上述,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在他的《文史通义》等论著中多所反映,并通过具体阐析以文证史、以史裨文等学术方法论,形成了丰富的学术内涵。他所提出的以文证史,就是将文学和史学视为春华和秋实的关系,强调文学可以辅证史学。他所提出的以史裨文,则在文人以史例为参照对象从事文学创作、史学求真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正史为小说提供叙事基础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强调文、史之间的汇通可以“交相裨益”。笔者认为,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多有与前人之说“不相袭”的创新;[3](卷9,P86)特别是他倡导文、史之学汇通和明义的观念,不仅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另辟了学术研究之蹊径,而且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增添了难能可贵的色彩。
三、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影响
章学诚“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章氏《文史通义》等论著的问世和流传,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和认同,并对近现代学者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最早肯定章氏《文史通义》学术价值的学者,他在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学术史演变的过程中对章氏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如梁氏在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指出:“实斋为《文史通义》,批评导窾,虽刘子元蔑以过也。”[6](P53)他认为章氏《文史通义》的学术贡献在刘知几《史通》之上。又如梁氏在1920年撰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7](P69)可见,梁氏对章氏《文史通义》阐发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其自身也受到了“开拓心胸”的影响。
梁启超兼通中西学,他在寻找中西学“冥契”点时,注意到了章氏的学术思想。他在1921年撰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云:
章氏生于刘(知几)郑(樵)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此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学家言多有冥契。[8](P27)
在梁氏看来,章氏学术思想“特别见地”之处就是“融会贯通”,而这源自于传统学术的新思想,又与近代西学多有“冥契”,自然具有了开启后学的价值。对于章氏提出的“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和方法,梁氏在继承的基础上还自觉运用。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就阐述了以文证史的功用:
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实事。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以度牒即可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知。[8](P61~62)
梁氏以《水浒传》和《儒林外史》两部小说为例,认为小说的情节“并非事实”,但其中对当时社会制度文化的具体描述则为事实,往往无法从他书中求得,而只能从小说中得知。笔者以为,梁氏的小说证史学术观念和方法,与前述章氏以小说《金瓶梅》的叙写来辨析明清两代“大人”、“老爷”称谓的“互异”,可谓一脉相承,而后者应受到前者的影响。
胡适是我国第一位为章氏作年谱的学者。他编撰章氏年谱的目的,是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于1920年所作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基础上,“决计作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9](P164)可见,胡氏对章氏的学术思想是推崇的。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序》云:
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一位讲史学的人,不应该在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文献征存录》里确有几行小传,但把他的姓改成了张字!所以《耆献类征》里只有张学诚而没有章学诚。谭献确曾给他做了一篇传,但谭献的文章既不大通,见解更不高明,他只懂得章实斋的课蒙论!因此,我那时很替章实斋抱不平。[9](P163)
在胡适的观念中,章氏作为一个在史学方面有卓著贡献的学者,应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居然没有人为他作一部详实的传记或年谱,胡适表达了“不平”的感叹。
胡氏撰成的《章实斋年谱》,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印发行,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章氏的学术思想也由此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所谓“旦夕间变为中国史学炙手可热的人物”。[10](P74)笔者认为,从胡氏的学术成果来看,在撰作年谱和传记方面均明显受到章氏学术思想的影响。如他深有体会地说“章实斋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9](P165)并在《章实斋年谱序》中大段引用了章氏《韩柳年谱书后》有关年谱的见解;又如他本着“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意图,[11](P6)撰作了《吴敬梓传》《李超传》《顾咸卿》《丁文江传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等多种“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传承了章氏文、史之学“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诚如学者所言:“在近代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有力倡导传记史学的,不能不首推胡适。”[12](P481)
在近现代学者中,受章学诚学术思想影响较深的还有钱穆,他在全面考察和梳析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过程中明显借鉴了章氏的见解。钱氏《中国史学名著·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云:
章实斋讲历史有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章实斋眼光卓特处。我也可以说,我同诸位讲了一年的史学名著,我自己也不是站在史学的地位上来讲史学。若如此,这就会像刘知几。而我是站在一般性的学术地位上讲史学,所以我要特别欣赏章实斋。[13](P253)
由此显见,钱氏对章氏的学术思想“特别欣赏”。在他看来,章氏“眼光卓特”之处,是因为其能够站在整个学术史的立场上关照文学和史学,所以他仿效章氏的治学方法,“自己也不是站在史学的地位上讲史学”,而是“站在一般性的学术地位上讲史学”。可以说,钱氏的专著《中国学术通义》,从篇章结构到论述内容,无不深受章氏学术思想的影响。
钱氏借鉴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同样主张学术通义。《中国学术通义·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文学》云:
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是如一本剧。中国文学重在诗,西洋文学重在剧。诗须能吐出真心话,戏则在表演世上事。中国文学重心,西洋文学重事。此处便见中国文学与历史合一……尤要者,即在诗人自道一己之日常人生,亲切经验,乃使作家与作品,合成一体。每一人之诗集,即不啻是其一生之自传。魏、晋后大诗人,如陶渊明,如杜甫,如苏轼……文学不在想像,乃在写实,而且所写即是作家自身之现实人生。[2](P169~170)
可见,通过类比中西文学的差异,钱氏指出了“中国文学与历史合一”的特征。
钱氏还以杜甫之诗详加说明,其《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云:
中国人向来推尊杜诗,称之为“诗史”,因杜甫诗不仅仅是杜甫一人私生活过程之全部写照,而且在其私生活过程中,反映出当时历史过程的全部……杜甫一人之心,即可表现出当时人人所同具之心。所有杜甫诗可称之为当时之“时代心声”。后人把杜甫诗分年编排,杜甫一生自幼到老的生活行历、家庭、亲族、交游,以致当时种种政治动态、社会情况,无不跃然如在目前。[2](P54)
显然,钱氏认为,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唐玄宗执政时期的“全部”历史过程,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杜甫个人的现实生活,而且可以读出当时的“政治动态”,为我们研究安史之乱提供了可资辅证的资料。钱氏于杜甫的诗歌中窥见其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动态,强调的正是文学与史学的合一,也就是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
据上可见,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前辈学者都深受章氏学术观念与方法的影响,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梁启超是最早肯定章氏《文史通义》学术价值的学者,他指出章氏“融会贯通”的学术观念是源自于传统学术的新思想,并延承了章氏以演义小说辅证正史的“裨益”观念,进行了小说证史的学术实践,具有开启后学的意义。胡适是中国第一位为章氏作年谱的学者,他本着“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宗旨,极力倡导创作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中同样传承了章氏文、史之学“交相裨益”的学术主张。钱穆则在全面考察和梳析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过程中借鉴了章氏的学术观念与方法,他用文学和史学合一汇通的学术思想来审视中国学术史,进而另辟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途径。
四、结论
归纳全文,笔者认为,章学诚通过梳理传统四部之学的渊源,考察刘勰《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这两部学术理论著作,评析清代乾嘉学术风气,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有着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这是他“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在他的《文史通义》等论著中多有反映,具有与前人之说“不相袭”的创新;特别是他倡导文、史之学汇通和明义的观念,不仅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另辟了学术研究之蹊径,而且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增添了难能可贵的色彩,其丰富的学术内涵更有待深入挖掘。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还对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开启了梁启超的小说证史、胡适的创作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史学、钱穆的文学与史学合一汇通等学术思想,进而另辟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途径。
[1]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钱穆. 中国学术通义[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 章学诚.章氏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 张国刚,乔治忠. 中国学术史 [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
[5] 刘咸炘. 推十论 [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
[7]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9] 胡适. 章实斋先生年谱[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 姚名达.姚名达文存[M]. 南京: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胡适. 四十自述[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
[12] 朱文华. 胡适与近代中国传记文学[A].解析胡适[C].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3]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