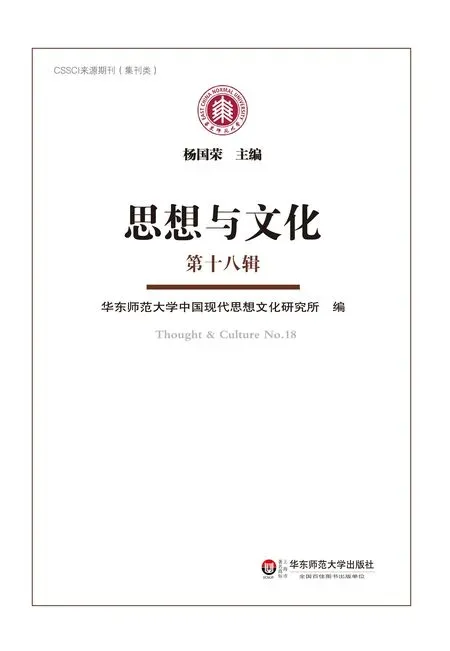一个唯情主义者的发明
——朱谦之的“我”兼论现代性的“内转”
肖铁
上世纪二十年代,吴稚晖曾将朱谦之(1899—1972)看作“最近中国思想界的四位代表人物”之一——其他三位是胡适、梁漱溟和梁启超。*吴稚晖: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梁冰絃编: 《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 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第24页。那时,二十出头的朱谦之“任情而行”,崇尚“不思之知”,一面写《现代思潮批判》(1920,新中国杂志社)和《革命哲学》(1921,泰东),批判杜威(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和罗素(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访华讲学前后流行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一面为他自己“这个浪漫的人呀”记下《回忆》(1928,上海现代书局)。不过,现在作思想史的学者多重视他的学术研究(比如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和音律、日本古学、或西方历史哲学的研介),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又常常忽视他以“真情”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对20世纪初期浪漫主义作家的影响(比如文学史会提及著名的《创造社丛书》,往往不提丛书在郭沫若的《女神》和郁达夫的《沉沦》之间曾推出过朱的《革命哲学》)。他的“唯情论”和记述“狂热勇敢常为自己的真情燃烧的青年”的自白远没有其他“浪漫的一代”的作品(比如他的好友郭沫若的自传)那样受到关注。自封为“唯情主义者”,朱谦之将情感与理性相对立,认为“真情”不能被社会道德和理性化的习俗所桎梏,而是流转运行,冲破一切道德、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的限制。他20年代的写作凸显了“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界中关于理性与情感/直觉之间的紧张。当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号召读者不要沉溺于情感之中,而应坚持理性的怀疑主义立场时,朱谦之一面把情感和直觉重新引入政治运动话语之中,高歌情感和直觉是产生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的根本要素,一面把他的唯情论融入对自我的书写。
本文把朱谦之的哲学写作和自述性文字作互文性阅读,通过他20年代的“唯情论"来看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史的上“真我"“无我"“大我"之间的辩证。一边是情感作为主体性基础的内在空间在现代中国的发明,一边是新兴的心理学理论和反理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朱谦之的“情"这一概念的历史特殊性正处于这两个事件的交叉点上,而这两方面都可以放到一个关于现代性“内转"问题的框架下来讨论。所以在讨论朱谦之提出的“反知复情"说前,我想先绕道谈一谈现代文学、思想内向性的旅程,以及把这种内转作为解读现代性的线索的局限。
“内转”的现代性和“去个人”的渴望
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把“内转”(inward turn)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这样的解读把对内在真实自我的发现与一些文类(比如日记、自传、成长小说)的流行以及一些特定叙述方式(比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并把现代心理学视为这种”内转”的理论动因和表现之一。艾伦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在其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著作中认为心理学内转的核心是“无意识的发现”,从沙门巫术,经过梅兹梅尔动物电磁学和催眠术,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他所谓的“动力精神医学”(dynamic psychiatry)一步步向内挖掘的过程。*Henri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London: Allen Lane, 1970.这种向内挖掘的结论是自十七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被推崇的理性自我——那个从教堂里走出来以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为目的的个人,那个《少年维特之烦恼》或《鲁滨逊漂流记》里的主角,那个自由主义和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背后的行为主体——原来不过是一层脆弱的面纱,它背后被压抑的无意识才是自我最真实的面孔。如果法国生理学家Jules Hericourt在1889年还需要把自我的双层结构作为新的发现报告给读者——“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有意识的思想也一直受无意识的指挥”*转引自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p.315.——到了1935年,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杜博(Leonard Doob)只不过是陈述一个流行的共识: 人是被“冲动、本能、趋力(drive)、欲望、需要、力比多驾驭的生物……一个充满变数的、复杂的、常常受无意识鼓动的存在”。*Leonard Doob, Propaganda: Its Psychology and Technique, New York: H. Holt, 1935, p.18.人的行为和情绪原来是受那些我们无所意识的力量控制,它们说着和理性不同的语言,似乎是无序而狂乱的,需要新的科学解读和记录方式才能被自我把握。
这种“内转”不仅以新兴心理学为动力或借口体现在文学、电影、摄影、美术中(乔伊斯、布努埃尔、达利、曼雷是耳熟能详的例子),而且更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学、政治理论,甚至室内设计上。比如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 Durkheim)通过“集体兴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概念,把宗教生活或社会变革与情绪的激烈、肉体的刺激连在一起: 比如他把法国大革命解释成了特定情境下心理变化的过程(当然他也因此常被后来的受行为主义理论影响的社会学家批判为走了社会学心理学化的歧路)。*É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 Joseph Ward Swai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15, p.211.意大利犯罪学家西盖勒(Scipio Sighele)、法国历史学家塔德(Gabriel Tarde)、法国学者和畅销书作家勒庞(Gustave Le Bon)等用催眠、暗示力、模仿、幻觉等心理学的观念,解释从手淫到暴动,从节庆狂欢到自杀和犯罪等各种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参见Christian Borch, The Politics of Crowds: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Soci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而在中国,“五四”前后在北大教授社会心理学的陶孟和则旁征博引——从勒庞、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华拉斯(Graham Wallas),到克里斯登森(Arthur Christensen),福来德(M.P. Follett),兰普列西(Karl Gotthard Lamprecht)——论说伦理、经济、政治、历史都“要心理的解释”: “心理学近来的进步就是所研究的对象不限于意识、研究的方法不限于内省。心理学要包括精神活动的各方面、大部分要应用客观的方法。这就是现代的‘动的心理学’或‘机能的心理学’……我们要藉动的心理学所研究的结果考察人类精神在社会生活上的表现。”*陶孟和: 《社会心理学(续)》,《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4日。革命心理、民族心理、教育心理、犯罪心理、社会心理、战争心理,不仅成了流行的学术语汇,更是很多畅销书的题目。*比如勒庞的关于心理学的著作,大部分都在民国时期翻译成中文。这种内转也体现在新的对室内空间的理解与追求中: 比如戴伯·西维尔曼(Debora L. Silverman)在其《新艺术与世纪末的法国: 政治、心理和风格》一书中分析了心理的“内景”(interiority)和新的室内风景风格的出现之间的联系,法国现代神经病学之父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把住所设计为自己的梦与记忆的外延就是一例。*Debora L. Silverman, Art Nouveau in Fin-de-siècle France: Politics, Psychology, and Sty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泽维·斯坦贺尔(Zeev Sternhell)指出,从16世纪开始,对世界进行理性主义的、机械论的解释主导了欧洲思想,但到了19世纪末,这样的解释让位给了一种“有机”的解释。这些反实证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强调“非理性价值的复兴、对本能和情感的崇拜、对生命与情感力量的绝对主导地位的肯定”。*Zeev Sternhell, Neither Right Nor Left: Fascist Ideology in France, trans. David Mais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3.与这种作为现代性标尺的“内转”紧密纠缠的是一种叙述自我的方式: “我”摆脱了各种羁绊(传统、教堂、宫廷等等),一步步解放、挖掘、表现、实现自己。从对理性的崇拜到对非理性的充满焦虑的发现,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的晚近阶段,它不是一个从秩序到无序的蜕变,而是更进一步对内在自我的承认与理解。在西方的语境下,这个关于“我”的故事经常被浓缩成从中世纪虔诚的教徒,到文艺复兴时“我思故我在”的思考者,到20世纪大都市人群中孤独、自恋、神经质的漫游者,再到贝克特“我痛苦,所以我可能存在”的充满焦虑的存在主义者的变化。*原话是“I suffer, therefore I may be”。见Samuel Beckett, The Complete Dramatic Work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p.117.这种叙述当然有其真实的成分,但正如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其主编的《重写自我》(Rewriting the Self)的文集前言里指出的,“这个故事也有着神话的感觉,甚至肥皂剧的气味,特别是当它被像史诗一般讲述出来: 一个英雄的自我克服千难万阻,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了完美的巅峰。这是一个讨好我们自己的故事。”*Roy Porter, ed., Rewriting the Self: Historie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ge, 1919, p.8.
一方面,这种叙述忽略了在意识与无意识纠葛中寻找平衡的“我”不仅是内转的现代性所研究和再现的对象,同时也是在这个内转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用尼卡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话说,现代内在自我的出现——也就是这种为本能、冲动、欲望、力比多等等非理性意识所能掌控的力量所主导的自我——成为可以被分析、被言说的对象,是和“心理‘真实效果’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psychological ‘truth effects’)分不开的。这个“生产”的过程把“心理可视性”(psychological visibility)投射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带来了他所谓的“20世纪的经验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 of exper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ikolas Rose, Inventing Our Selves: Psychology, Power, and Personhoo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0. “20世纪的经验心理化” 一词引自Nikolas Rose, “Assembling the Modern Self,” in Rewriting the Self: Histori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ed. Roy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1997, p.232.也就是说,现代性内转的叙述常常预设的真实的深层自我,那个从前现代种种束缚和遮蔽中释放出的自我,恰恰是在其被发现的过程中通过特定现代学科的语言而变得可视可见的。罗斯的观点和一些同样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坎古兰(Georges Canguilhem)、克龙比(Alistair Crombie)影响的学者相呼应。那个内向的、孤独的、压抑的、真诚的、狂乱的,甚至变态的自我,他们强调那个被内转的现代性发现和表现的“我”,并不是火山下的熔浆,沸腾在地表之下等待发现;它的涌现不是压抑已久后自然的迸发(Porter所谓的肥皂剧),而本身就是被发掘它的工具不断规训的过程。
另一方面,这种关于内转的叙述往往把现代性的主体定义为内向的、孤独的、压抑的、真诚的、狂乱的,甚至变态的个体自我,并把这个自我与社会/大众对立起来。远离人群,或借用威尔治(Jobst Welge)的话说,“孤独在文学中的表演”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Jobst Welge, “Far from the Crowd: Individuation, Solitude, and ‘Society’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in Crowds, ed., Jeffrey T. Schnapp and Matthew Tiew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35.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启发了很多现代中国文学里的独行客的。比如郁达夫的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这样写道: “几日来我那独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里的腐浊的空气,同蒸笼里的蒸气一样,蒸得人头昏欲晕,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发的神经衰弱的重症,遇了这样的气候,就要使我变成半狂。所以我这几天来到了晚上,等马路上人静之后,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个人在马路上从狭隘的深蓝天空里看看群星,慢慢地向前行走,一边作些漫无涯涘的空想,倒是于我的身体很有利益。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张均编辑: 《郁达夫代表作》,上海: 全球书店,1937年,176—177页。这样的段落让人想起郁达夫自己翻译过的卢梭的话: “我的余生只想清清静静一个人孤独地来过,因为我只在我自身之内才寻得到慰安希望与和平,我不该再,也不愿意再和别的相周旋了,除了我自己自身之外”。*转引自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75页。因此李欧梵教授在他关于“五四”作家“内向性的旅程”的重要研究中,指出“自我和社会间充满纠纷、对立的关系”是新文学中自我的形象的标志。*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4—65页。
很多学者(大至可追溯到卢卡契)把现实主义与现代派对立起来,将内省、超脱和对社会现实的冷漠视为后者的标志。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学者质疑这种解读。麦克·特拉特纳(Michael Tratner)对乔伊斯、伍尔夫、艾略特和叶芝的研究就是这样。与那些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逆向而行,特拉特纳把现代派文学和当时的大众政治以及各种群众心理学连在一起,论争说现代主义恰恰是要突破19世纪个人主义惯例的限制,现代派的各种尝试,包括像“意识流”这样实验,不是向内的收缩,而是“对个人的拆卸”(The dismantling of the individual),“以释放被资本主义所隐藏或压抑的社会秩序和精神”。他发现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夫的《海浪》,甚至艾略特这样高度抽象、程式化的现代派经典文本里,也“充满了集体团结的时刻: 他们试图展示不需要暴力或独裁领袖也同样能有同心同德的喜悦。”*Michael Tratner, Modernism and Mass Politics: Joyce, Woolf, Eliot, Yea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 p.15.乔尔·尼克尔斯(Joel Nickels)2012年出版的关于现代派诗歌的专著沿着特拉特纳的思路更进一步。通过对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罗拉·莱汀(Laura Riding)等诗人的阅读,尼克尔斯争论说“现代主义幻想”(modernist fantasy)的主体不是远离群众的孤独者,而是把自己想象为“置身于诸众(multitude)之中一个自然而然的力量”: “作者把自己表现成走在大街、拱廊、公园或其他的公共场所,以求建立与诸众的联系并象征性地展现他们的潜能。”*Joel Nickels, The Poetry of the Possible: Spontaneity, Modernism, and the Multitud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p.21.
这样的研究大多发端于詹姆逊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单一的现代性》(A Singular Modernity, 2002)一书中,詹姆逊质疑把“内转”作为现代性的阐释线索、把局外人和孤傲的叛逆者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典型的传统观点。与之相反,他强调现代性的核心不是孤独的内省,而是一种“去个人化的渴望”(longing for depersonalization)。这是一种“对超越自我的新存在的渴望”,这种渴望背后是“一种在自我中无法满足的动力,这种动力必须通过对现实世界本身的乌托邦式的革命转变才能得以完成。”*Fredric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 Verso, 2002, p.136.詹姆逊因此重新思考了革命与现代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强调了二者背后共同的对个体自我超越的欲望。
也就是说在现代性内转的背后,恰恰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超越个体限制、突破孤寂的欲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史背景和理论考虑下,我们可重新考量朱谦之的唯情说、革命哲学和自我书写之间的关系。
反知复情
二三十年代朱谦之思想的中心是真实自存的自我。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置身于上节提到的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反实证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思潮中,歌颂本能、冲动、直觉和真情,希望恢复被掩盖在理性表皮下深层的内在自我。另一方面,朱谦之对“真情”的渴望与“五四”前后出现的情感化人格和内心模式密不可分。对自我的解放和表现是大家讨论五四新文艺和思想耳熟能详的一条线索: 普实克把“主观主义”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得以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标志之一,李欧梵强调“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个性的出现”,而王德威最新的专著更把“自我的抒情”视为中国现代性的核心问题。*Jaroslav Prus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95页;David Der-wei Wang,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朱谦之的唯我主义就是在这国际国内互相缠绕的双重语境中提出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面孤独的夜行者不同,朱谦之对“我”的思考却是在对群众革命的畅想里展开的,展示了唯我主义和“去个人的渴望”之间吊诡的联系。
朱谦之反对与“五四”时期流行的以发展和进步为历史主线的进化史观,提出了“虚无主义进化论”的历史循环模式,也即他所谓的“‘自无而有,自有而无’永远的流行。”*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24页。在朱看来,从无向有的进化是一个把尘世减化成被理性技术宰制的冰冷客体、消泯人性的过程。他因此号召进行一场“消灭现在”的虚无主义革命。这场“向着‘无’的路上跑”的革命,将荡涤一切阻碍情感发扬的障碍阻塞,因为唯有“‘情’就是本体,就是真实,就是个性自存的实体。”*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54页。朱谦之不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自然选择理论或其他认为进化反映的是自然的外在机械过程的理论——在这点上,他和大多数的五四学者不同,但和很多20世纪初的西方思想家相似。*Peter Bowler, The Eclipse of Darwinism: Anti-Darwinian Evolution Theories in the Decades around 1900,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比如柏格森,他不满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提出了自己的“创化论”。他认为进化的动力在于élanvital——一种潜在而有目的性的内驱力,凭借这一驱力,生命反抗充满惰性的物质限制。与适者生存的机械性进化论不同,柏格森试图证明: 作为一种有机而连续的现象,进化过程实际上是生物内在驱力的作用。*见Henri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trans. Arthur Mitchell, New York: Henry Hold and Company, 1911. 关于柏格森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见 Bowler, The Eclipse of Darwinism, pp.56-57, 116-17; Leszek Kolakowski, Bergson,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00, pp.53-70.朱谦之一面受伯格森的创化论影响,一面又吸收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的情感理论,并融入禅宗思想和阳明心学,进而提出了他的“反知复情”的革命说。朱谦之认为,进化/革命(他说革命就是一种进化)并非受外在环境影响而做出的改变/适应,而是根源于人类内在力量的消长变化。趋向“无”的虚无主义革命进化,正是对这种自身内在驱力的复返,其驱力就是“真情”。
在冯特看来,人类首先是情感动物,人们原初的情绪状态是他们行动和心智的源头。情感过程为主动行为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基础;在冯特的理论体系中,单纯的理性选择不可能存在,只有情感驱动的过程才能解释人类意识的统一性。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史家科特·单奇格(Kurt Danziger)所述,对冯特来说,“只有情感状态才无处不在,而正是这样,意识才能呈现出它独特的统一性”。*Kurt Danziger, “Wundt and the Temptations of Psychology,” in Wilhelm Wundt in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ed. Robert W. Rieber and David K. Robinson, New York: 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1, p.80.阿瑟·布鲁门塔尔(Arthur Blumenthal)指出,在冯特看来: 情绪先于认知,因此“理性思考不过是覆在更为基本的情感驱动过程上面脆弱的装饰。”*Arthur Blumenthal, “A Wundt Primer — Th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nsciousness,” in Wilhelm Wundt in History, p.135.在19世纪晚期,冯特带领他的莱比锡实验室,通过分析实验者面对能激发情绪的暗示或经验时的心跳频率,来研究情绪和意志行为的关系。冯特认为,人的一切心理状态是不断变换的情绪引起的波动场域的各种变形,意志是情感的一种加强形式。*见Kurt Danziger, “Wundt’s Theory of Behavior and Volition,” in Wilhelm Wundt and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ed., R. W. Rieber, in collaboration with Arthur L. Blumenthal, Kurt Danziger, Solomon Diamond, New York: Plenum, 1980, pp.89-115; C. Wassmann, “Physiological Optics, Cognition and Emotion: A Novel Look at the Early Work of Wilhelm Wund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4, no. 2 (April, 2009): 213-249.朱谦之借用了冯特的两个观点: 首先,在意志活动中,情感占据首要地位;其次,相对于认知和智力,情感相对来说具有优先性。朱谦之和同时代大多数思想家将情绪看作理性机制的断裂不同,他认为: “鉴于情的发动,在‘知’之先,知识是附属于情的第二段作用,故知识是情的派生”,是它“涣散下来的东西”。*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45页。朱谦之扩展了冯特的看法,他断言,一旦意志被施压或被强化,“便是意依于情的时候”,可是,“当意志弛缓的时候”,就“趋向了‘知’”,成为“不进化的死的迷妄颠倒,丝毫不得自由。”*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46页。这是因为,意志低于情感,意志“里面有理知分子,还没有涤除净尽,至于知识这个东西,不但不是革命的心的要素,而且简直是‘革命之敌’。”他还补充道: “所以革命的好处,正在于用真情来激励行为,以至于利害关系如何,那就管不了那么许多。”*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49页。他断言: “当知理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朱谦之看来,革命需要的不是理性分析,而是一颗革命之心: “组成革命心理的要素,只有情意,没有知识的”,而“革命的行动,也正是真‘情’的流行罢了”。*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53页,第52页,第57页。
朱谦之认为真情的流行需要靠直觉和冲动,是本性中的原动力激发了革命行动,人心中由内向外的冲击焕发为革命意志。他将柏格森的活力论融入他自己的激进革命理论,非但没有像同时期的冯友兰或方珣那样试图调和柏格森反智思想与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关于五四知识分子对伯格森的误读,见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61-63.反而将创造性冲动和直觉这两个柏格森学说中的反理性观念推向了极致,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关革命行动和革命方略的激进学说。对柏格森来说,真正的生命之流不可能被分割,更不可能被分析。理性的分析过程,仅仅将我们置于“停滞而僵死的处境”,因此理性“自然无法理解生命真谛”。*Henri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trans. Arthur Mitchell, New York: Henry Hold and Company, 1911,p.165.想要洞穿自然科学包裹在真实世界的扭曲表象,人们必须依靠直觉。直觉才是“以生命本身的形式塑形”,凭借它,人们才能直接把握真实。通过直觉和本能,“人们让自己沉浸于客体之中,与它独一无二、无以言表的本质融为一体”。*Henri Bergson,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T. E. Hulme, New York: Putnam’s Sons, 1912, p.7.朱谦之把柏格森的直觉观念移植到他的革命理论,并将柏格森“创造冲动”这一概念与进化过程中的抵抗性强力联系在一起(柏格森仅仅稍稍提及了后者)。*例如,柏格森认为在特定情况下,伴随着“爆炸性的力量”,“创造冲动”可以转化为“强烈的冲击”,“可以战胜一切抵抗,清除那些最强大的障碍”。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p.98, p.271.朱认为直觉法对革命的真价值在于“直觉能亲证本体……这正是科学方法的没奈何”,*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82页。并把“创造冲动”视为革命的原初动力。这种动力是植根于“情”之中的一股本质能量,在真情展开的历程中,这股能量不断与外在障碍争斗角逐。朱谦之断言: “革命是创造冲动,故此也是自然的冲动,不能排除,而且应该任他自由做去,非何等势力所能强制他的。”*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35页。
他将内在的情感直觉和非理性冲动看作革命的驱动力,反对经济决定论,嘲笑唯物史观“把理想那样东西,也看作不过物质的影子”。*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133页。朱谦之把革命中共同的感情解释为自觉的个体之间的心心相印,并把这种心心相印浪漫化为一种和谐共鸣。对他来说,革命群众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之中,每个人的真情都同时汇入深沉的情感链接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潜在的真情实感,从而获得新生: “人人感情思想的一致,也只是‘真情’的自然一致。”*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125页。
用本能、直觉、冲动解释革命行为,将内在真情自我的自然展示视为革命情绪的表达和最终目的——朱谦之的革命哲学体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内转的现代性。他批判“保守主义者极力排斥神秘的情感的论理”,强调“其实神秘的情感的论理正是革命的福音”。*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175页。“不受理知的束缚,除真情外,没有什么的。真情!真情!试看翻山倒海的革命运动,那不是由真情发动?”*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127页。这不仅是对“五四”时期知识和政治语境的回应,更从跨国流行的反理性、反决定论思潮中吸取到灵感,将他所谓的先于理智的内在性视为个体实存和欲望的源泉。
革命成了内转的方式: 通过革命,自我“恢复了他元来的心理,所以极其活泼,而且真诚的很”。*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59页。而“热血”则成了这种内转的载体。朱谦之挑战那些让人们坚持理性怀疑主义、而不放任于情绪行动的知识分子: “我是受了本性自然性的冲动,也可见比那做知识奴隶的强得多了。呀,我的血已经沸了!我已叫着我去破坏去了!你呢?你没有血?你没有真情?”*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53页。这种表述生动地呼应了《革命哲学》的四首序诗中沸腾之血的形象。郭沫若的《宇宙革命底狂歌》幻想: “我渡过血涛滔滔的黄海/你们吐出浑身底血液来/把海水都染红了——快在这血河中添一点血哟!/快在这血海中添一点血哟!/教那血涛滔滔的黄海/把全球底海水和盘染红!”而郭沫若的创造社同仁郑伯奇延续了“黄海”的意象: “我们准备着血来洗污浊的黄海哟!我们拿着火轮般的爆弹去欢迎光明的太阳哟!”郑振铎的诗《微光》写道: “青年之血——沸啊,沸啊,/神圣之泪——流啊,流啊/把撒旦的宝座烧掉吧,/把撒旦的宝座漂掉吧!”袁家骅则这样写道: “嘡——嘡——嘡!——/血钟响了!血钟鸣了!/澎湃——澎湃——澎湃!——/血潮起了!血潮涌上来了!/光明钟啊!/光明潮啊!”这些诗连同朱谦之的书都以放肆而近乎迷狂的呼号,表明他们对某种内在的、非理性的、拯救性的情感强烈的信仰。对于朱谦之和他的同道来说,革命就是遵循“真情的命令”。*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122页。
在朱谦之看来,这种反知复情的内转不仅仅是个性的重新发现和任情发泄,也同时是超越个体的唯一途径。在主流知识分子盛赞批判理性的20世纪20年代,朱谦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评价政治行为的另一种标准。在瞿秋白和陈独秀等人呼吁人们警惕非理性的迷狂时,朱谦之却高调赞扬未经过反思的意识,并认为它具有无与伦比的革命价值。他认为,这样一种未经过反思的意识来自于所谓的“反知的群众”,通过情感冲动和内心直觉得以爆发。“群众运动正是社会上各个人普遍的自觉,这种自觉,是本能的,不是理知的——‘无知’的‘知’才是无上的,普遍的‘知慧’”,而知识分子们“所认为智慧的部分,则不外虚伪的差别的理知而已。”*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泰东,1921年,第124页。对朱谦之来说: “群众运动的好处,即在于他把‘情’的个性,尽量发挥,也唯有这‘情’的个性——无意识的个性——才是真实的个性。把真实的个性来代替皮相的个性——意识的个性。”*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126—127页。正因如此,那个反知复情的“我”(朱谦之称之为“理想者”)才能“代表群众,[因为他]是代表群众的真情,却不是代表那组成各个人心理的‘理性。’原来理性是差别的,是不能代表的,而真情则自然一致。故此理想者的真情,也就是群众的真情,他不过能认识自家的真情,同时知道‘群众的真情,皆备于我’”。唤醒群众的“我”与群众一样至情至性、血气方刚;事实上,群众与理想者合二为一: “他真情之单独实现,也等于群众的真情的总和——因为群众的特征就在已构成了单独的‘真情’,而为‘群众心意一致律’所支配,而理想者则完全具备这个要素,他的好处,就在多情,多情就和群众心理密合无间了。”朱谦之以理想家的口吻写道: “我就是群众;群众就是我!我的一举一动,莫不和群众合德了。”*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121页。
反知复情、回归个性自存的实体恰恰为了超越个体;推动朱谦之唯情主义的不是自我剖析的理性内省或纳西瑟斯式的自我陶醉,而是(再次引用詹姆逊的话)“一种在自我中无法满足的动力,这种动力必须通过对现实世界本身的乌托邦式的革命转变才能得以完成”。*Fredric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 Verso, 2002, p.136.对正处于激进的虚无主义时期的朱谦之来说,这种革命须经历四个阶段: 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的革命)、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无政府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对所有政治机构),以及最后的虚无主义革命,以求最终达到“无物即是万物,无身即是万身”的境界。*朱谦之: 《革命哲学》,上海: 泰东,1921年,第221页。朱谦之的宇宙革命论与章太炎、毛泽东等人的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参见王远义: 《宇宙革命论: 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许纪霖、宋宏编: 《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70—685页。
“浪漫的人呀”
如果说新的心理学语言和反理性主义为朱谦之的激进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回忆录则把他的唯情主义变成了一种书写自我的方式。在他的早期自叙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五四“浪漫一代”(特别是他的创造社同人)的影子: 热忱、骄傲,更有些疯癫地要“平沉大地,粉碎虚空”的叛逆者。比如他1921年的自叙就这样写道: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老实说吧!我来不是要建设,乃是要打破,一旦天翻地覆,把宇宙的组织都推翻了,那时烟消云散,我才撒手归去。我是谁?是个破坏、反逆、奋斗的虚无主义着,也是狂热勇敢常为自己的真情燃烧的青年,总之行为偏僻,不肖无双,把一切最大的诅咒来诅咒我,不辞的——我么?我么?有人说我是“爱的真神”“情的主宰”,有些是;有人说我疯,有些是;有人说我是痴,有些是;疯呵!痴呵!我都直接承当——而且过去种种,现在种种,我何者不是直觉的进行,而为一种纯粹真情的努力活动,虽有时直觉消失、间断,好似坠落了些,然我的信心,总能使我摆落了理性的牵制,而实现那遗世而独立的真我。*朱谦之: 《朱谦之文集》,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39—40页。
这里能看到禅宗《高峰语录》的影响(朱说,“这本体上的‘我’无始本来,性自清净,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尽未来际,常住不灭”)。而他自我夸大的狂热(“我比宇宙还大,宁可为我而牺牲宇宙”;“我的存在,比宇宙还早,宇宙尽管生灭,我却是独立不改”)似乎直接源自他的好友郭沫若的《天狗》(初发于1920年2月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比朱的自叙早了一年): “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但就像上节所述,对“我么?我么?”的痴迷背后是超越个体的欲望,在朱谦之的狂想中,融入革命成了实现这种欲望的方式。写这篇自叙的朱谦之也是同时正在写《革命哲学》的那个自命“狂热勇敢常为自己的真情燃烧的青年”。“实现那遗世而独立的真我”和“我就是群众;群众就是我”非但不是对立矛盾,反而是互为表里的: “我就是无我,就是大我。”*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第40页。
朱谦之1928的《回忆》更着意描述自己“轰轰烈烈的壮气,如焰如潮的热血”: “天马行空,不受羁勒,如一片狂热,不可炙手;英雄之事业,或出于无意识,彼唯知满足自己之情热,发挥自己之本我而已。”他出生于福州的一个精英家庭。1917年,他移居北京,就学于北京大学,先读法学预科,后主修哲学,进入他自称的“革命思想时代”。他这样描述自己对实证主义(杜威、罗素)、新庶民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批判: “这时的我,为着真理的向上努力,竟敢破坏一切,否认一切,而成个空前绝后的虚无主义者了!虚无主义是根本反对现代的任何制度,由着否定的方法,批判一切,打破了种种偶像,扫除了种种迷想。”*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44—45页。
在他的“革命实行时代”,朱谦之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这一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刊物工作,号召学生罢考,恳请蒋梦麟校长停止颁发学位,因为朱认为学位把知识变成了“赃物”(他对“我觉悟的朋友”说,“请诸君把考试的‘笔’抛去”)。五四运动后,1920年10月9日,他和互助团的人在正阳门周围散发革命传单。他的朋友毕瑞生因为夹带“中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计划书”这份朱谦之主笔的文章而被捕后,他去警察局自首,以换得朋友的开释。他特意记下了公庭审讯时,他跟审讯人讲直觉,讲本体,说“我就是宇宙,所以不能不为宇宙做事,眼见宇宙间的痛苦,不能不亲自出来,做革命的事业”;他说胡适,“我从前曾劝他出来革命,他不敢。他还不能脱杜威的圈套”;他说教授,“国立学校的教授,是不能教我的”。当他被讥笑为“神经病的小孩子”时,他答曰: “不错!哲学者大半都是疯子。”朱谦之被判三月徒刑,在服刑期间,他试图绝食自杀,并写下这样字句: “我有头颅,要他干么?我的心灵,不如早些归去!”*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47—48页。
对朱谦之来说,记录下这一切,就是为了证明“我这个浪漫的人呀!实在把一切身外,绝不经心,只凭着活泼流通的‘真情之流’,任运流转,舍次以外,我便不知什么了!”*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第52页。但如此对自我的英雄式浪漫书写,在朱看来,却不是以探索、记录,或暴露内在自我为目的。这里不妨把朱谦之的《回忆》和梁启超的《三十自述》(1902)做一比较,看各自书写自我的理由。梁说: “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拦镜据鞍,能无悲惭?擎一既结集其文,复欲为作小传。余谢之曰: 若某之行谊经历,曾何足有记载之一值?若必不获已者,则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上海: 中华书局,1936年,第四册,第15页。梁的《三十自述》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个人传记的早期典范之一,他把对自我的了解作为最根本的缘由。这里当然有自谦的考量,但对“自知”的强调无疑和后来郁达夫所讲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有亲密的联系。
而在朱谦之的自述里,“‘个人’的发见”却和“与天地同流”的狂想缠绕一处:
真情之流荡漾着我的心,使我一面不能不和现象世界悲惨的战斗着,一面不能不顺着爱潮创造一个绝对自由的美世界。我鼓舞着,挣扎着,好像沉溺在水中的时候,竭力和逆流拼命推破一重重的波涛险阻,即一重重地回复了真我本体的自由……活泼泼地自从狭窄的兽性里拔身而出,而与天地同流也……我就是这个人生的象征,我的活泼泼的“真情之流”,并不是我个人所能占有的,我的快活就是一切人们的快活,我的悲哀也就是一切人们的悲哀哩!我必须决定我是和宇宙间公共的,我在生里艰辛努力所发出来的一种哀歌,或我从无量情流跳出来的一种不能言的欢唱,这都不单是“我”的,是一切人们的。那么我为什么不应该把我全整的一首情歌,通通给你们歌唱,让你们把这首情歌,收纳在你们的心中呢?写到这里,我实在畅快极了!觉着我所有的活泼流通的“真情之流”,和我一切亲爱的读者们,都是共鸣共感似的了!*朱谦之: 《朱谦之文集》,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41—42页。
朱谦之用来讲述自己的词汇让人想起同时期大量出现的自白性文学,但在他看来,这样的自白并非出于背离社会而无处表达的苦闷,记录自己的“真情燃烧”恰恰因为真我即是大我: “浪漫的人”才能唱出超出自我、“去个人化”的情歌;活泼泼的独白才能引起共鸣。
结论
阅读朱谦之以唯情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与自我书写,并非要证明他天性不羁,有“如焰如潮的热血”,天生“一片狂热”,以此显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个人的解放;更无意像陈独秀那样嘲笑朱谦之激进主义的幼稚,“想不笑实在忍不住”(当然朱谦之对陈也不客气,说他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陈独秀: 《独秀文存》,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0页。这样的解读和批判自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本文想强调的是这类对个人“情热”的狂热肯定,以及将革命解说为“真情之流”的浪漫主义,与其说是某种压抑已久的内心在现代的迸发,不如说这种迸发本身就是在内转的现代性语境下才成为可能的。
朱谦之把《诚斋易传》、《高峰语录》、王阳明《传习录》、谭嗣同《仁学》连着《孙文学说》、汪精卫《革命英雄小传》,还有伯格森的创化论、冯特的心理学和勒庞的政治理论一起看。他对“真情命令”的信仰有王阳明心学的影子,也延续了帝国晚期对“情”的膜拜,它认为个人自发的感情是主体性和道德权威的基础。朱在《论语》“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字句里,找到“真情洋溢胸次悠然”之妙,在《周易》“见天地之心”里看到“随感而应,一切都听任真情”的复情说。*朱谦之: 《一个唯情主义者的人生观(二)》,《民铎》,第五卷,第二号,第2页,第5页。关于朱谦之的唯情论与传统的性情之辩以及朱的《周易》研究的关系,见方用: 《朱谦之“唯情哲学”批判》,《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第35卷第4期,47—51页,57页。可是,如前所示,朱谦之借以定位其哲学思想,并衍生其“情”之含义的语义网络,不仅包括这些传统,更将19世纪晚期产生的、在20世纪初跨国流行的关于心智的心理—生理学话语涵纳了进来,放在一个反理性的现代思潮中,糅合成自己的唯情论。
朱谦之激进的革命哲学和对自我英雄式的浪漫叙述,将现代心理学和伯格森的活力论嫁接到中国传统思想对“心”和“己”这两个范畴的构想之上。他对于本能和直觉的颂扬,受柏格森的影响,更与牟宗三所说中“能够自己去形成一内在的道德决断之超越的、实体性的、本体论的‘智的觉情’”这一新儒家观念一脉相承。*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三册,第254页。而他对自身与集体融合无碍的论断,也内含了儒家宇宙论的核心关切: “即通过实现一种世界整合,化解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区别,达到(个体与整体)的连结。”*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243.邓腾克(Kirk A.Denton)在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中自我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在五四运动对作为现代个人主体的自主这一颠覆传统的想象背后,存在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痛苦”的焦虑,害怕“失去联结自我与世界的超越性的许诺”,而这种联系是传统的自我观念中一直存在的。现代的自我因此“纠结于两种同等重要的欲望: 一种欲望试图让自我获得自觉自治,另一种欲望则试图将自我置入某种强大的宇宙他者之中,后者在当时被指认为民族、革命、大众或历史”。历史、革命被神圣化为个人意志无法左右的必然运动,而自我在激进的唯我主义和历史、革命这无法抵抗的力量之间进退维谷。*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63.
朱谦之的唯情论,既源于这一痛苦的自我观念,也是对其的反应。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朱谦之强调理想者的“我”与集体之间的共鸣,以求坚持自我在革命中的作用,从而构造个体内心空间和大众之间的联系,进而超越政治介导和自生自发之间的刻板对立。*朱谦之在《革命哲学》中强调群众的自发性,批判列宁主义的精英政治,但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也有自己的局限,请参见Tie Xiao, “The Lure of the Irrational: Zhu Qianzhi’s Vision of Qunzhong in the ‘Era of Crow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4. 2 (Fall 2012): 1-51.而他对自我的书写同样源自这样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超越的紧张。舒衡哲、余英时、王汎森等教授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自我形象转变的重要研究,讨论了文化、政治环境变革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 在对自身位置的界定和想象中,知识分子从“四民之首”的“士”自我贬低为社会的一“分子”,在革命和历史的暴力行进间,质疑自身存在的正当性。*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45-194;Ying-shih Yü,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e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 122, no. 2 (Spring, 1993): 125-150;王汎森: 《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 联经,2003年,275—302页。这种自我边缘化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类感伤颓废的作品里,在那些苦闷哀伤的独行客身上得到了文学的体现。20年代朱谦之对“我”的自信,似乎是这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过程中的一个特例,但也可以把他自我肯定的唯情论看做是对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的边缘化的一种不乏浮夸妄想的自我补偿。当然这种“我比宇宙还大”的狂热自信只是朱谦之思想的一个早期阶段。20年代末,他成了黄埔军校的教员,后留学日本,三四十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这二十年间,他从一个信奉直觉、冲动的虚无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推崇蒋介石的“厉行哲学”。朱谦之自我认识的转变,可以在他1946年出版的回忆录《奋斗廿年》(中山大学史学会)里找到,不过那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