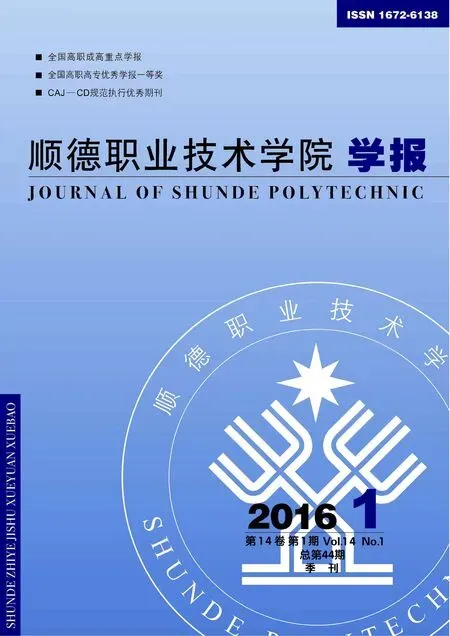论余华《古典爱情》的先锋表征
韩兵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论余华《古典爱情》的先锋表征
韩兵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在自身长久的艺术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创作理念和叙事模式。在作为才子佳人小说模仿之作的《古典爱情》中,余华通过人物描摹的符号化、语言运用的陌生化、情节设置的戏仿化实现了对才子佳人小说传统范式的颠覆,体现出鲜明的先锋表征,带来了新颖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古典爱情》;符号化;陌生化;戏仿化;先锋表征
《古典爱情》发表于《北京文学》1988年第12期,是先锋文学的创作佳绩。才子佳人小说“从题材内容上说,是描写有才华的读书人与美貌多才的官宦富室小姐的爱情婚姻故事的。”[1]2在这个模仿古典才子佳人小说故事模式的文本中,作为先锋作家群体先驱与旗手的余华对封闭的、拘囿想象力的、僵化的传统创作范式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解构。他通过人物描摹的符号化、语言运用的陌生化、情节设置的戏仿化实现了对叙事传统的毅然放弃和决然逃离,在消解了文学传统所赋予的秩序和逻辑、建构起鲜明的先锋性表征的同时,也“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2]9。
1 人物描摹的符号化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文本书写的基本构成。在对待人物塑造的问题上,传统的小说与先锋小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创作进路。
传统创作观念推崇的是“心理型”人物观。“心理型”人物观注重人物内心活动,强调人物性格的一种认识倾向。刘再复先生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以各种形式组合的差别和变动显示出不可重复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写实传统认为虽然小说人物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层面的虚拟建构,但是,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丝毫不亚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人物形象塑造的美学价值在于性格的审美显示,性格不仅是产生美感力量的原动力,也是构成典型形象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也是被誉为小说黄金时代的19世纪的一个主流观点。例如,普洛普提出,小说艺术的伟大之处在于小说家通过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感动读者、“引发泪水”,最终揭示“关于人的真理”[3]68。在这种观念的经年浸染下,自觉地追求人物形象的逼真性与典型性,着力雕琢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人物的性格成长或变动中寄寓、传达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或道德说教已然嵌入传统作家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他们奉为圭臬的审美指针与创作追求。
与传统叙事高举的“心理型”人物观相左,先锋文学把“功能性”人物观当作自身叙事实验的法宝。“功能性”人物观追求在小说的建构过程中,把人物的行动视为一个叙事功能而对人物进行抽象化,只关注人物的行动在情节安排中的作用,完全不考虑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普洛普提出,无论故事中的人物如何变化,人物在抽象的结构层面承担的功能是相同的。“将人物抽象为‘角色’,关注人物行动在故事发展自然时序中的功能,这是普洛普分析模式的基本特点。”[4]47在人物的塑造上,余华遵循的就是这种观念。在他的笔下,人物被抽象化为一种叙事的符码,他们没有具体可感的外在形貌,没有清晰鲜明的性格特征。他们在文本中只不过起推动叙事发展的功能,他们的存在,只是要让故事得以继续发展,作家看重的是事件的延伸,而不是他们的形象塑造。
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对才子和佳人的家庭背景、音容笑貌、才气横溢和娇美动人的描写既是完整塑造人物形象的必须,也是为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埋下的根苗。如《兰花梦奇转》中的松宝珠,从小男扮女装,但丽色难掩:“瘦瘦的身子,长长的脸儿,春山横黛,秋水含情,杏靥桃腮,柳腰莲步,犹如海棠带雨,杨柳迎风。”[5]6一个天资国色、动人心魄的美娇娘让人印象深刻。又如《莺莺传》,一开篇就交代了张生“性温茂,美风容”,一个形貌俊朗、才华高茂的书生形象立马在眼前清晰显现出来。其后又叙写了在普救寺凭借自己的一身才气,作诗向自己心仪的莺莺发动心理攻势,结果就有了西厢那温情绵绵的场景。但是在《古典爱情》中,余华对柳生的勾勒仅仅是“身穿一件青色布衣,下截打着密褶,头戴一顶褪色小帽,腰束一条青丝织,带恍若一棵暗翠的树行走在黄色的大道上”[6]20。从“青色布衣”、“褪色小帽”隐约可见柳生并不是名贾贵胄的富家公子,没有高头大马,没有伶俐的书童,有的只是肩上背着的一个“灰色的包袱”,一路上陪伴他的也只有“投在黄色大道上的身影”和“笔杆敲打砚台的孤单声响”[6]21。柳生相貌描写的缺失,也使其面貌朦胧难辨。文本中没有安排柳生为祈见佳人而作求谒诗,也没有挥就铭记两人矢志不渝的定情诗,这也从侧面交代了柳生诗才的匮乏。余华笔下的柳生既没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书生所拥有的显赫家世,也没有傲人独立的俊美仪容,更没有才子所通有的玲珑诗才,甚至在文本中没有自己的声音,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指代书生意义、模糊不明的叙事符号。余华笔下的小姐惠身穿“霞裙月披”,“樱桃小口笑意盈盈”,“一双秋水微漾的眼睛飘忽游荡”[6]25。只是“霞裙月披”、“樱桃小口”、“秋水微漾”是描写佳人容貌的惯用语词,小姐惠给读者留下的仅是一个指称佳人生命存在的形象符号,其具体容貌仍是朦胧的雾中之花、水中之月。
人物性格是一个有着“具体各种属性”的艺术整体,唯有各具特征的性格塑造,艺术形象才能获得美的价值,产生美感力量。传统叙事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着力在人物的气质、心理、习性、行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展现人物的心灵特征和性格蕴涵。如《玉娇梨》中的苏友白,执意退亲、不惜断送功名表现了他的孤高傲岸;赠银打发承差反映了他仗义疏财的一面;把无艳当成无娇又表现了他谨慎中不乏武断,这样一个傲岸、讲义气又有些冒失的苏友白就血肉丰满地站在读者面前了。再看《古典爱情》中的柳生和惠,不仅他们的外在形貌模糊不清,性格蕴涵亦是朦胧不明。
柳生为了光耀祖宗踏上黄色大道赴京赶考,为了激励儿子全力以赴,柳母剪断了全家赖以生计的织布。按说作为贫寒子弟的读书人,在这么一个可以转变自己人生运势的机会面前应该目标明确、信念坚定、踌躇满志地去博取功名,可余华偏偏让他“爱读邪书”并且“生疏了八股”,并没有赋予他积极上进的意识。与小姐惠在花园初次相见时,柳生并没有像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那样对心上人倾心不已,他所做的只是“仰视绣楼的双眼纹丝未动”,在遭到丫环的呵斥后,他“仍然看着窗户目不斜视”,在突遭的大雨中,他很晚才发觉落在自己身上的雨点,可仍呆呆站着,不肯离去。他也没有像司马相如那样弹唱《凤求凰》向美人示爱,也没有像张生那样作诗求见,他只是静静地站着,像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丧失了感知意识和行动能力。在菜人市场,余华是借柳生的眼睛来描绘所看到的一切,虽然通过柳生的视角观察到的肢解人体的场景尽管是血腥的、残酷的,可代表柳生主观态度的文字叙述并没有任何恐惧、紧张的情绪浸染。柳生的形象在这里被简化为一架忠实记录的摄像机,它并不准备对眼前发生的非人间场景“表示点儿属于人世间的态度”[2]99。在给小姐惠擦拭尸体时,腿断处七零八落的、稀烂的皮肉在柳生眼里成了“一片断井颓垣”,被刺穿的胸部也“恰似一朵盛开的桃花”。面对小姐惠的尸体,柳生没有常见的悲痛,“脑中却是空空无物”,有的只是“茫茫无知无觉”,在这里,柳生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尺被余华无情地剥蚀了,他就像一个没有任何情感依附的人物符号,只剩下冷漠和虚空。
小姐惠与柳生从相遇到相爱没有遭到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常出现的父母的反对、豪门贵胄的逼婚或是生死的阻隔,因此,在作者笔下,她的心理活动和情感起伏并不明朗,性格特征也随之隐匿。既没有表现出传统叙事中佳人常有的初遇爱情时的欲拒还休,也没有表现出在封建礼教禁锢下的痛苦与挣扎,更没有显现出蔑视纲常伦理、大胆追求真爱的决绝与反叛。小姐惠在这个仿才子佳人文本中的功能只是传统叙事中“富家小姐”这一负载大量社会文化属性形象的象征性存在和情节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叙事成分。她的性格特征并不是作家关心的对象,她的行为只不过是在柳生这一人物形象总体性暗淡的情状下,使情节得以继续发展的推动力。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有着鲜活具体的音容笑貌,繁富驳杂情感世界的佳人形象被余华执意消解了。
余华认为“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7]175,因此,他“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在他的文本世界中,“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7]175。《古典爱情》中,柳生和惠告别了性格发展的线性轨迹,也没有丰沛的情感活动方式;《世事如烟》中,余华只给极少数人赋予了身份特征,其他人均用数字来替代,摒弃了传统叙事应有的性别和名字;《鲜血梅花》中,丧失了主体性意识的阮海阔在“复仇”的名义下准的无依,随处飘荡;《往事与刑罚》中,余华的运笔所重显然不在人物塑造,而在往昔的历史与记忆……在余华的笔下,不考虑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背景,不注重人物形象的丰实度和可信度,拒绝将人物还原到欲望化、人格化的生命层面上来,人物只有动作没有心理,只有身体没有灵魂,人物作为抽空的生命符号只是作家进行文字游戏的工具而已,而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符号化的人物可以避免现实逻辑、文化、性格上的羁绊,不仅使人物果断地抛弃了他所必须负载的大量的社会文化身份(如职业特征、时代气息、文化背景),直接展示生命自身的本原性的生存图景,而且让叙事话语挣脱了传统的写实化的创作律令,逃离了真实性、典型性的拘囿,通过对故事本身的单纯营构达到了表意上的畅通无阻,从而开辟了新的理想通路让创作主体无所牵制地表达对真实的人类生存本相的独特思考。这种对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勾勒消弥了人物在文本中的人格特征,使他们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成为余华表情达意的非人性符码,只能按照作家的意图行事,朝着作家努力的意义方向前进。人物符号化所导致的结果,不只是有效地剔除了那些紧裹在人物身上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使以往的典型化叙事法则彻底地破产,还使先锋性“功能型”人物观在当代文坛有了一席之地,进而导致了叙事传统中人物塑造真实化、典型化艺术观念的分崩瓦解。
2 语言运用的陌生化
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主体多为士子文人,他们多有诗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富于诗赋之才的小说家将他们的诗性思维融注到小说创作中,使其小说语言具有了精炼简洁、严谨准确的特色,文风也随之纤丽婉约。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写龙宫之富丽堂皇:“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9]258这种多以四字句式的华词丽藻、骈词俪句来铺排场景的赋体文风在卷帙浩繁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屡见不鲜。另外,才子佳人小说在记叙事件发展和人物言行时,也常常使用平正典雅、含蓄精炼的文言语词。语言的诗化追求有着韵律、字数、形式等方面的严格约束,这就在无形中妨碍了作家对人物、事件、场景进行尽情传达。此外,经年的历史积淀使这种表意规范里的语词负载了相对稳定的形象特征和意义归属,语词的搭配与句子的整合也已嵌入作家以及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一种僵化的无意识文化规约,读者在面对这种存袭已久、有着固定意义指向的语汇时,已经丧失了对之进行深度感知的兴趣和耐心,这就不利于读者对语词意涵进行深入解读。
“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8]33为了实现叙事的通达,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余华在部分继承传统用语规范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尝试。他运用灵活多变的现代语词,调动多种写作技法,对文本语言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在不破坏基本句法规律的前提下,在语义内容和逻辑范畴内对严谨准确的文言语词做了最大可能的颠覆和发挥。
余华往往在一个词上赋予通感色彩,调动读者的多种感觉去体悟语词所涵蕴的更多的表意信息。如“一片喧哗声从城门蜂拥而出,城中繁荣的景象立刻清晰在目”[6]32。“喧哗声”一词本身是用来形容声音的嘈杂,带有听觉色彩,但在这里“喧哗声”竟然可以“蜂拥而出”,余华对它进行了跨感觉组合,赋予了它视觉色彩,我们仿佛看见喧闹声通过城门时的拥挤与杂乱,这就从侧面形象地写出了城中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余华还善于借喻指和喻体跨度较大的奇譬妙喻来对事物进行形象化的传达。如“被利刀捅过的创口皮肉四翻,里面依然通红,恰似一朵盛开的桃花”[6]47。余华把利刃捅过的伤口比作盛开的桃花,不可谓不颠覆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在人们的习惯思维里,花是美好、祥和的象征,血是残酷、暴力的所在,两者是界限分明、不可调和的。余华用桃花来喻指跨度较大的伤口,使人们在两者的鲜明对比中惊异于他超群的想象力,同时也领略到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暴力美。
此外,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作家往往在叙写人世间的悲剧、苦难时寄寓深沉,有着鲜明的爱憎臧否倾向,其叙事话语也因此浸染着作家清晰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说教,如《霍小玉传》中作家借霍小玉之口对李益出于私利背弃与霍小玉的海誓山盟和八年之约的薄情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李君李君,今当永觉!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10]35同样是写苦难,余华摒弃了对生活中悲惨事件的摹写,却对血腥场面的展现情有独钟。如《现实一种》写的是亲人之间的血腥杀戮;《一九八六年》对疯子的疯狂自戕场面进行了浓墨泼彩般地细致描绘等。嗜血的余华在展现这些血腥场景时摒弃了传统叙事中叙写苦难、残酷事件时常用的情感宣泄和道德评判,作家往往采用一种“无我式”的零度情感语言,只是将叙事景观原原本本的忠实记录,并不掺杂任何阐释性的话语,并不流露自己的任何态度和见解。这种冷漠书写在对暴力、肢解、凶杀进行全方位视觉呈现的同时,使读者对这种毫无掩饰的残酷场景产生一种陌生之感,自身业已钝化的感受力被强烈的视觉映像瞬间激发,给自己留下的只有难言的恐惧和彻骨的寒冷。
在《古典爱情》中,柳生眼睁睁地看着店主的利斧砍向幼女,斧头落下后,按说余华该将笔触转到痛苦的哀嚎、肆流的泪水上,但笔锋偏偏转向了幼女,将她在骨肉分离时的身体反应写得真真切切,让人心生怜悯,不忍直视。“幼女在‘咔嚓’声里身子晃动了一下”,这是利斧猛劈的力道所致,读者甚至能在头脑中织构出幼女瘦弱的身子猛地晃动的场景。“然后她才扭回头来看个究竟”,这个时候的幼女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断臂的痛楚,可见斧头的锋利无比,也更突出了幼女的可怜与店主的残忍。“看到自己的手臂躺在树桩上,一时间目瞪口呆。”一边是血肉模糊的身体,一边是静置在树桩上的自己的手臂,这一静态画面的充分延展给人以极大的视觉震撼,被暴力肢解的幼女一时间也被眼前的残酷景象惊吓得不知所措。但余华并没有偃旗息鼓,他的笔继续写着,“半晌,才长嚎几声”,一个“长嚎”可见幼女被剖骨剔肌后的钻心之痛是何等的销魂蚀骨。然后是“哭喊不止,声音十分刺耳”,这里的“刺耳”显然让读者觉得十分“刺目”。拒斥任何道德包装和情感宣泄,让零度情感式的叙事话语无所阻隔地诉诸读者所感同身受的切身感受性,这正是余华想要的叙事通衢。
“看着”一词,强调了文本的视觉特性,并成为观察视角结构性内嵌的外在表征。画面虽是血腥残酷的,但作家并没有对这一令人发指的血腥行为进行常见的道德指责和血泪控诉,也没有对饱受摧残的幼女表示出惯常的悲悯情怀,一切都在冷漠的叙述中进行,一切阐释和感受都消融在这无声的画面里。冷漠地书写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加掩蔽的直观呈示方式,也就是在苦难画面的呈现过程中羁勒叙事主体的评说权力,拆除现实主义叙事传统中存袭的那道理智和道德防线,让苦难以苦难本来的面目来照面,而不是以经过政治、道德等解释性话语文饰过的形态来示人。通过话语的裸露与暴力悬搁人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进而激发无所依傍的切身感受性,理性判断就失去了至高的权威,丑恶和苦难也就得以实现了自身的本原性在场。读者对这种叙写方式的陌生之感源于余华残酷地剥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领悟苦难的方式,让人们毫无依托地直面人性之恶和生之苦难。但是,在这种方式中呈现的丑恶和苦难往往更为真实与纯粹,读者产生的审美体验也比往常更为强烈与持久,进而让读者“在超道德超文化超人道主义的超理性主义超习俗的本原存在的层次上,唤起对苦难与罪恶的一种‘畏’”[2]105。
余华的小说对叙事语言的陌生化处理,打破了传统追求平正典雅的传统叙事的语言规范,拓展了汉语语词的所指空间,凸显了语言的张力与活力。这种有力的语言冲击有效增加了人们认知事物的难度,延宕了审美感受的时间,激活了业已萎顿的感受能力,推动人们摆脱审美疲劳,对习以为常的事物进行重新审视、认真开掘,以获得更为真实、更为深刻的意义和价值。余华陌生化的语言追求“不是诱使人们走到叙事话语之外,而是让人们卷入写作的语词运作之中。某些时候,语词本身即是最终目的。”[11]208这种言说方式不仅建构了先锋文学的语用法则,彰显了余华丰实的创作实力和面向现实的大胆突击,还完成了小说叙事从传统的“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根本性转变。
3 情节设置的戏仿化
爱情作为人类生活中的永恒话题,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根深源长的脉流,才子佳人小说在自身的发展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情节模式。将郭昌鹤《才子佳人小说研究》对才子佳人小说情节设置的归纳概而述之,就成了“一见钟情→小人(权臣)拨乱→才子高中→终得团圆”,或者称为“定情→磨难→团圆的三部曲”[4]101,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定情人》等小说就采用了这种故事模式。作为常数,这种叙事模式在情节设置上通过磨难来考验定情男女的爱情,以团圆来奖掖他们的忠诚,对早期作家来说,不失为一种能给读者带来美感的“有意味的形式”。但是,随着后人创作的亦步亦趋,把它当作生成新作的模本,那么这种情节模式就成了令人生厌的旧窠。
先锋的余华致力于打破传统的陈陈相因的故事模式,他在创作中多次使用戏仿手法“把原本正经的、严肃的事物、文本等,进行一次反其意而道之的书写,从而解构原来的意义和价值”[12]25,实现了对文学成规和人们惯常思想观念的彻底清算:《鲜血梅花》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戏仿,余华用非典型化的武林环境、病态化的主人公形象、无限延宕的复仇过程和令人啼笑皆非的复仇结局消解了传统武侠故事中为父报仇的严肃主题;《河边的错误》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凶手、作案动机、作案过程三个关键要素统统没有出现,此外,作为案件真相主要探查者的马哲没有穿透重重迷雾看清真相的洞察力,反而在案件调查中陷入迷惘,小说的结尾也不是真相的终极展露而是调查人变成疯子的荒诞收场;《爱情故事》是对“青梅竹马”式爱情小说的戏仿,主人公忆起的初恋没有甜蜜温馨,结婚后的生活更是索然无味,在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里,传统的爱情叙事不见了踪影……
作为古典才子佳人小说的戏仿之作,《古典爱情》也拥有这类作品的鲜明特征:赴京赶考的贫寒书生、闺楼伤春的富家小姐、热心牵线的丫环、幽深旖旎的后花园、心旌摇荡的一见钟情、温柔缱绻的私人相会、难解难分的伤感别离。但这仅仅是余华为读者设下的一个叙事圈套,反叛的先锋的余华自然不会去重复那业已存在千年的套路化的叙事模式,随着戏仿化的情节逐渐延伸,余华不动声色地开始了对古典爱情的解构。余华选取三个时间点为叙事的启端,分别讲述了柳生的三次出行经历,三次出行都可以看作是三个独立的故事,但余华在本应是三个故事的高潮处悉心设置了三个崩塌式的情节,在效仿传统的前提下,实现了对传统故事模式的叛离和嘲弄。
第一次出行,柳生在后花园偶遇伤春的富家小姐惠,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带着小姐惠“不管榜上有无功名,还请早去早回”的深情嘱托,柳生挥泪而别进京赴考。按照传统的故事模式,肯定会出现父母因两人身份悬殊而严禁两人的爱情进一步发展,或者会出现达官贵人因看中小姐惠的容貌而进行逼婚,结果是柳生状元及第,冲决这些外在的阻隔和小姐惠终获圆满。但是,余华并没有让柳生高中状元,这就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发生了悖逆。草木尚有荣枯的转换,而柳生却不能锦衣荣归,落榜的境地让柳生深感耻辱,但是想到小姐惠倚窗而望的情形使柳生的心中对两人的再次相见满怀期待:“重逢的情形是黯然无语,也可能是鲜艳的”[6]32小姐惠如何与落榜而归的柳生相见以及如何继续他们的爱情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阅读期待里。但是,余华在这时却突然扭转笔锋,拒绝讲述故事的任何按照常规经验可能出现的情节,而是没有任何征兆地展现出了令人错愕不已的画面:小姐惠已经无迹可寻,只剩满眼的废墟和朽木烂石,昔日威严气派的府邸已经没有缘由地败落了。赶考归来的柳生与小姐惠没有温暖的重逢,没有爱情的继续,世事的无常让人感到诧异万分,这一崩塌式情节的设置,使作品远离了传统的古典爱情叙事模式。
在柳生的第二次出行中仿照传统模式安排了柳生与小姐惠的重逢。按照常规故事模式,久未相见的才子佳人的相逢肯定是倾吐相思、互诉衷肠,其画面肯定是催人泪下的,气氛一定是哀婉中透露着甜蜜的,如果进一步发展,还有可能是两人缔结良缘,厮守终老。但余华把两人的相逢安排在了令人始料未及的菜人酒店,血腥冷酷的菜人酒店代替了两人初次相见时的玲珑精致的后花园,小姐惠已沦落为菜人,此时她的一条腿已经被商人买去,柳生用昔日小姐所赠的纹银赎回了那条已经被割得支离破碎的腿后,在小姐惠的哀求下又亲自将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惠刺死。两人的重逢没有出现读者预料中的温情脉脉的场景和共结欢好的结局,只有沦为盘中之菜的奄奄一息的佳人,柳生亲手结束爱人的生命,又将读者期待两人团圆的愿望付诸流水。故事情节在本应是高潮处又一次出现了崩塌,这种充满了极度血腥的故事演进和情节描写在让读者体会到了余华血液中“冰渣子”的冷酷的同时,也让读者彻底将余华的古典爱情与常规经验中的古典爱情划清了界限。
在古典才子佳人叙事传统中,以悲剧结尾的爱情故事常常用一种幻想的方式对两人生前的悲剧作圆满式的补偿。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双双殉情后,两人化为“连理枝”、“比翼鸟”永远在一起,又如《牡丹亭》中葬身梅花庵观的杜丽娘为柳梦梅还魂再生,二人终成眷属。为了实现颠覆传统的决绝性和彻底性,余华毫不留情地对这种补偿式的圆满进行了戏仿和嘲弄。第三次出行,柳生决定为小姐守坟。这时小姐惠却返回人世与柳生相会,两人共宿一夜之后小姐却又神秘消失,满心狐疑的柳生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挖开了小姐的坟,并发现了小姐惠死而复生的迹象。次夜,小姐惠神色悲戚地对柳生道:“小女本来生还,只因被公子发现,此事不成了”[6]60。小说至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唏嘘、感叹。如前所述,小姐惠死而复返与情郎相会是对传统“死而复生”模式的仿作,但是接下来余华对《古典爱情》结局的崩塌式处理,无疑再一次地解构了这种模式:小姐本可以复活的,但这种可能性却被柳生亲手毁灭。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小姐有死而复生的希望时被重新唤起,认为故事将向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发展,但结局的崩塌式情节的设置却再一次使读者的愿望落空。戏仿手法对古典爱情造成的嘲弄使读者所有关于古典爱情的浪漫想象、心理期待都被余华驱遣殆尽。
余华对传统的故事模式和叙写规范进行的戏仿,其最终结果是颠覆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和思维方式。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之际)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的才子佳人小说,根源在于作家们的合理诉求与这个诉求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矛盾、冲突。正是现实的残酷与命运的悲哀,才使得对现实不平的文人靠才子佳人的文学表达来获得精神慰藉和心灵补偿。既是外在于现实世界的心灵避难所,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世界也就成了经过作家精心营造、粉饰过的理想世界:不同于纷繁杂乱甚至有些荒诞的现实,作家为了消解人间现世的苦难与丑恶,拒绝爱情的波折与残缺,往往刻意夸大人物的主体力量,他们往往凭一己之力便可轻易蹈破现实的藩篱,达成自身的既定理想。他们不仅形貌俊美,而且还才华横溢,不用干谒权门,不必因缘攀附,完全靠自己的才学就能金榜题名,独占鳌头,不仅受到皇上的重用,还能赢得佳人的青睐,最终功成名就、幸福完满。他们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的理想,却在艺术世界里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事实。正是在人物主体力量的强力弥漫中,现实丧失了原有的自足性、残酷性和无常性,变得秩序井然、温顺可测,显得理想化色彩过于浓厚,崇高但不厚重、纯美但不真实。经过这种传统情节模式的反复浸染,读者很容易在这种文学成规下对这种理想化的世界形成固定的接受心理和对之深信不疑的思想观念,很容易把这种失真化的世界当成实际存在的现实,从而忽略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与荒诞性,甚至误判自身本真的生活状态。
在余华的眼中,“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2]11。余华认为世界并非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描绘的那么美好,他“意识到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2]8。从本质上说,理想化的才子佳人小说,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思想游戏和白日梦境,是回避现实社会的消极态度。为了看清现实世界的真实面目,余华认为“只有摆脱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背离公众共识的秩序和逻辑的方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2]6所以,他运用“戏仿”这种“虚伪的形式”,让柳生失去改变命运的
能力,让两人无法实现圆满,在理想化的世界中加入了冷酷的现实因子,从而展现了读者早已忽略但却实际存在着的现实生活中冷酷、荒诞的一面。让读者在一连串的惊诧声中激发他们日趋颓靡的哲学思考和审美感受能力,促使他们抛弃头脑中虚美的、不切实际的现实乌托邦,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真假纷呈、浮沉不定的复杂现实世界,重新衡估一切价值,正视人生的本真状态。在《古典爱情》中,余华用人物的符号化颠覆了传统文学中的“心理型”人物塑造法则,用语言的陌生化打破了才子佳人小说中叙事话语平正典雅、婉约纤丽的用语风格,又通过情节设置的戏仿化消解了传统书写中固定的故事框架和结局指向。小说在解构了创作成规、给读者带来“震惊式”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建构起独异于当代文坛的先锋表征。这种新奇大胆的文学实践使小说这种“过去的形式”贴近了现实、贴近了苍生,既给传统文学注入了创新求变的活力,也掀开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华章。
参考文献:
[1]苗壮.才子佳人小说史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2]吴义勤,王金胜,胡建玲.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美)Miriam Allott,Movelists on the Novel[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5.
[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吟梅山人.兰花梦奇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0.
[6]余华.古典爱情/鲜血梅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7]余华.虚伪的作品[M]//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8](苏)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M]//方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9]张燕瑾.中国古代小说专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0]陈大康.短篇小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11]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8.
[12]王洪岳.反讽与戏仿现代主主义小说技巧论之一[J].创作评谭,2005(4):22-26.
[责任编辑:钟艳华]
文·史·哲研究
文·史·哲研究
On Pioneering Characteristics in ClassicLoveby Yu Hua
HAN B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ng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The novels about gif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ladies in ancient China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relatively stable creation idea and narrative mode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artistic evolution. In Classic Love, a parody of novels about the gif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ladies, Yu Hua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by symbolizing character description, defamiliarizing language use and devising plot parody. At the same time, the novel fully embodies distinctive pioneering characteristics and brings new aesthetic experience.
Key words:Classic Love; symbolization; defamiliarization; plot parody; pioneering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韩兵(1990—),男,山东聊城人,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30
DOI:10.3969/j.issn.1672-6138.2016.01.013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138(2016)01-0063-08
——评杨向荣《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