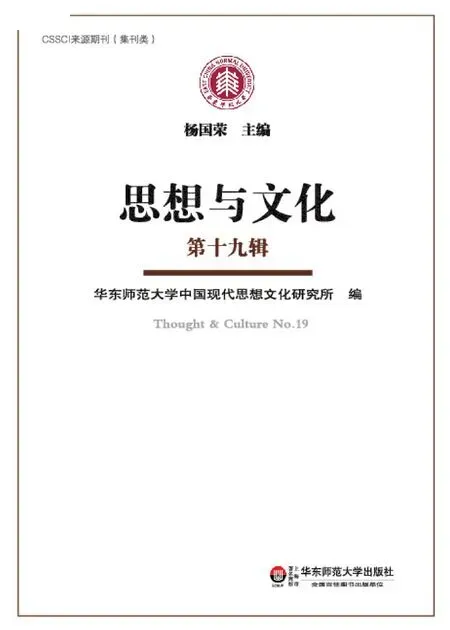〗“泛审美”视阈下的中国都市电影形态*
●杨海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急速转型,以科技化、商品化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众审美也渐由“纯审美”转换为“泛审美”,即审美的取向由深入、理性的沉思和反省转为浅显、感性的行乐和悦已,精英化、唯美化、高雅化逐渐淡出时代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化、世俗化和商业化。“一方面,‘审美’不断向普通文化领域渗透,迷漫于其各个环节;而另一方面,普通‘文化’也日益向‘审美’靠近,有意无意地把‘审美规范’当作自身的规范,这就形成了难以分辨的复杂局面。”①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泛审美”文化的兴起,使得人们将精神层面的审美诉求和物质层面的日常所需有机融合,并且相互渗透、互为影响,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互为循环的机制,即人们逐渐将审美日常化、世俗化,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审美的源泉。与此同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下,商品经济、科技发展与审美文化现实相靠拢,人们逐渐将自我的审美标准泛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和日常规范。
“泛审美”文化的盛行折射到电影艺术领域,不论是从题材、人物、主题,还是影像风格、叙事结构和镜语特点等方面,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特形态,本文将以最具代表性的世纪之交中国都市电影为观测点,阐述“泛审美”文化在电影艺术领域的深远影响。
一、题材的生活化和叙述的个人化
“泛审美”文化的广泛流行,不仅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纯审美”文化(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唯美文化)的淡出和疏离,同时也意味着日常审美(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娱乐文化)的深化和突显。在世俗文化日益成为主流文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再苛求心灵的诗意栖息,而是追求肉身的感性欢愉,审美需求转向生活化、通俗化,立足于日常的现实生活,“我的地盘我做主”,强调构建一个以自我定义为准的审美世界。
回望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电影,题材的生活化和叙述的个人化倾向与“泛审美”文化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谋而合。无论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资深导演张元、路学长、王小帅、管虎、娄烨、阿年等创作的《罪恶》(1996)、《非常夏日》(1999)、《苏州河》(2000)、《卡拉是条狗》(2001)、《我爱你》(2001)、《绿茶》(2002)、《西施眼》(2002)、《紫蝴蝶》(2003)、《蔓延》(2003)等,还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兴导演高群书、韩杰、宁浩、王笠人、杨超、金琛、施润玖、毛小睿、张杨、吴天戈、王瑞等创作的《离婚了,就别来找我》(1996)、《美丽新世界》(1998)、《洗澡》(1999)、《网络时代的爱情》(1999)、《女人的天空》(1999)、《走到底》(2000)、《暖冬》(2003)、《绿草地》(2005)、《赖小子》(2006)等,他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化、平民化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都市电影的创作题材,拓宽了中国电影的表现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些都市电影讲述的大多是发生在当下的中国故事,展现的是城市生活的真实现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导演们面向现实,讲述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生活和人生实况,日常化的题材唤起了观众对电影现实性的深层思考,大大地扩展了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广度。有些作品堪称是历史的实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断代史,比如说,贾樟柯的《站台》以发生在山西汾阳一个“文化剧团”里的故事,展开了一段史诗般的宏伟叙事,客观而真切地反映了中国整整十年的社会文化变迁;张杨的《爱情麻辣烫》以五个小故事演绎了不同年龄段人们的情感经历,展现了当代城市人的爱情画卷,尤其是以“结婚”为线索而串起的“声音”、“照片”、“玩具”、“十三香”和“麻将”五个情感片段,将表面上看似关联不大的五个故事串在一起,生动地展现了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等人生不同阶段对待爱情的态度,于细节中体现现代都市人的内心情感和伦理道德……
值得关注的是,世纪之交的都市电影在表达城市生活的时候,更倾向于表现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比如说,路学长的《长大成人》通过一本“小人书”、一个英雄故事和一位“朱赫莱”式的兄长,构筑了主人公周青从童年到青年的信仰寄托,反映了一代人成长的精神历程;路学长的另一部作品《非常夏日》也是一个关于青春成长的故事,影片以《北京晚报》的一则新闻报道为原型,讲述了一位汽车修理工的内心转变:雷海洋因为懦弱无能被女朋友抛弃,一次外出进货,他亲眼目睹一名少女惨遭强暴,在关键时候,因为性格懦弱,他没有挺身而出,可事后又陷入深深的自责,最终向警方报了案。当在逃的罪犯找到他时,他选择了捍卫自己的男性尊严,直面生死考验,完成了一场别样的成人仪式。同样的例证还有:贾樟柯的影片《任逍遥》通过两个少年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和无助,真实地记录下时代转型期年轻人的情感状态和心路历程;李欣的《谈情说爱》用一种巧妙的手法展现了都市青年对爱情的不确定性和患得患失感,等等……虽然导演们所展现的青春姿态各有不同——有的积极向上,有的躁动不安,还有的迷茫无助——但因为创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大致相同,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也颇为相似,所以电影的题材和内容也趋向统一。
“泛审美”文化影响下的都市电影较之20世纪80年代“纯审美”文化影响下的都市电影有着明显不同。80年代被观众所熟知的张泽鸣的《太阳雨》、孙周的《给咖啡加点糖》、周晓文的《疯狂的代价》、夏钢的《无人喝彩》、《大撒把》、《遭遇激情》和《与往事干杯》、谢飞的《本命年》,以及由王朔的小说改编而成的《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大喘气》等,虽然形态各异,但表达的都是人们对生活的沉重思考和深刻反省,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也有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其艺术呈现更加含蓄、婉转和唯美,突显时代精英的道德立场和行为准则,具有较强的人文主义情怀。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逐渐出现,其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新型人群的涌现,如先锋艺术家、流浪歌手、发廊妹、下岗工人、农民工、同性恋、吸毒者等,他们已经成为生活在都市里的“另一种”现实存在。导演们敏锐地关注到这些群体,并看到了其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于是,他们用影像去记录、讲述这些新人群、新现象背后的故事,而且更加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境遇,如,表现社会小流氓的《周末情人》、《任逍遥》、《赖小子》、《十七岁的单车》、《安阳婴儿》,表现逃学少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表现发廊洗头妹和大厦保安的《好奇害死猫》,表现偷渡者的《二弟》,表现吸毒者的《昨天》等……这些作品以客观、冷静的艺术姿态,呈现出转型期中国都市的种种社会实况,充满了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情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纪之交的都市电影借用一个个日常化的生命状态,表达的既不是以往影片中观众已经十分熟悉的对于传统道德观的高扬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神化,也不是对坍塌的社会秩序重建的呐喊或是对人性悲喜剧的铺垫,他们只是想再现日常生命中的真实状态和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所以,施润玖在谈到《美丽新世界》的创作感想时,不无感慨地说:“真实对我而言,它的重要程度相当于每天的必需品,没有它就会被饿死、渴死或冻死。”①施润玖:《〈美丽新世界〉启示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贾樟柯在《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中也说道:“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②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第368页。
故事叙述的个人化倾向是世纪之交中国都市电影的另一大显性特征。导演们在讲述都市故事时,往往热衷于展现个人化的成长体验和自我的生命记忆,在熟悉的日常故事中抒发对人生和世界的感悟。究其原因,都市电影导演大多都比较年轻,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也大多是都市或城镇,作为同龄人,他们对都市年轻人的生存境遇有着比较深刻的体悟,鉴于生活阅历有限,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其实就是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的客观记录,有的甚至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从路学长的处女作《长大成人》到姜文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周末情人》到《头发乱了》,包括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每一部影片表达的几乎都是导演的个人成长和心路历程。《头发乱了》中,女大学生叶彤在影片开头的一段独白,真实地反映了都市年轻人的共同心声;《周末情人》的自恋情结恰恰是这一代人的精神优越和自我流放的客观写照……当然,因为过于沉浸于这种自恋式的个人表达,世纪之交的都市电影往往摆脱不了视野的狭窄,有的作品甚至类似于创作者的喃喃自语,“导演使电影终于脱离了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所做的事情,而只想传达生活过程中的个人体验”③陈犀禾、石川:《多元语境下的新生代电影》,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44页。。但是,“他们并没有思考和追求,只不过用了年轻人独特的方式来表述,在喧嚣的摇滚中纯净心灵,从血腥的殴斗中伸张正义……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电影风格脱离了传统,但抛开了长者的偏见,这种现象在每一代新人重新登场时都有可能发生,也只有通过他们自身的经验才会有所调整”④陈犀禾、石川:《多元语境下的新生代电影》,第46页。。
这一现象的产生恰恰与“泛审美”文化的浅显化、平面化相吻合,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导演对自我的艺术化表达和内心的外向化呈现。虽然表达形式各有不同,有的直白、有的含蓄,有的直接、有的隐晦,有的比喻、有的象征,但是,这些作品都表现出对青春的描摹和记忆的重现,以此来完成对自我成长的祭奠。这种个人化的故事讲述本身就是对传统电影的一次解构和重构。
二、影像的纪实化和人物的日常化
“泛审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在实践中体现的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相互转化和相互统一。“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投射到电影艺术中,就表现为影像风格的纪实化和人物形象的日常化。
综观世纪之交的都市电影,其对纪实主义影像风格的追求并不是传统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实,而更注重通过置景、表演、对白和化妆等手段再现生活的真实。在诸多都市电影中,简约的摄影手法、生活实景拍摄、现场同期录音等频频运用,较为充分地还原了日常生活的质感,拉近了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比如说,《昨天》以纪录片的视角,完全实景拍摄,客观冷静地呈现了演员贾宏声的行为状态;《悬恋》、《邮差》、《冬春的日子》摒弃了传统的锤炼、含蓄、典型化的技巧处理,冷静地审视主人公单调、琐碎的日常生活;《小武》、《站台》、《任逍遥》、《巫山云雨》、《落叶归根》中以同期录音的方法,让片中主人公操着原汁原味的各地方言,有的演员非但没有表演性的话语和动作,甚至都没有化妆……无怪乎章明在《巫山云雨》的导演手记中说:“我们要电影的风格化,更要影像的极度自然性。不要担心画面不够丰富斑斓、题材不够刺激人心、画面不够华贵亮丽……在我们获得的条件下,我们要的是质朴。甚至不用担心将来别人指责这部电影平淡沉闷,貌不惊人。因为影像的背后自有另一种东西,一种眼睛所不能见到却可以用精神去感觉到的真实存在。”①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第33—34页。
在都市电影创作中,一直追寻纪实主义风格并将其运用到极致的当属贾樟柯。从《小山回家》到《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到明显的纪实主义痕迹。《小武》以几近纪录片的拍摄手法,真实地展现了世纪之交中国北方小城镇的社会文化生态:斑驳的城镇、贫瘠的文化生态、车水马龙的大街、喧嚣甚上的集市,县城里随处可见除旧迎新的景象,可大街上的行人却神情麻木、目光呆滞……影片真实地描绘了处于时代大潮和社会转型下的中国城镇的生活图景,色彩晦暗、基调冷峻,给人强烈的悲怆感,同样的视觉体验在《站台》、《任逍遥》等影片中也随处可见。而在《二十四城记》中,影片以类似于新闻报道现场记者采访的形式,让每一个片中角色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影片巧妙地将叙述的焦点集中在三代厂花的人生经历和五位讲述者的个人故事上,通过小人物口述历史的方式,演绎了一座国营飞机制造厂的变迁,堪称当下中国工业发展、经济改革大背景下的时代史诗。贾樟柯近年拍摄的另一部影片《海上传奇》,也采用口述历史的形式,由十七个生活在上海的受访者于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个人记忆和成长故事,写意地描绘了隐匿在大都市的每一个生命心灵深处的上海模样。在十七位受访者中,既有家世显赫的名门之后,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但是不论来自什么样的阶层,当他们安静地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成长记忆时,影像自然构成了一部生动鲜活的历史……
长镜头的使用是纪实主义影像风格的主要标志之一。就电影本体的角度而言,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可以使影片的形式与风格更加突出,因为长镜头完整地记录事件的全过程,不仅可以真实地反映事件不断推进的存在状态,同时也给观众以最大限度的思考空间,使得影片具有非常强烈的透明性和客观性,更能体现导演忠实于现实的创作态度。比如说,出生于上海、成长于苏州河畔的导演娄烨在《苏州河》一片中,以大段的长镜头表达了自己对一座城市和一条河流的复杂情感,记录下破败敝蹙的弄堂、飘着垃圾泛着白沫的苏州河、河岸废弃的房屋和工厂、横跨在河上的一座座桥梁;章明的《巫山云雨》中也随处可见独特的长镜头,斑驳的建筑、空白的墙壁和茕茕孑立的信号台……从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毫无修饰的长镜头中,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都市电影的艺术姿态:以纪实主义的影像还原生活的原貌,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和生活化的叙事模式,让摄像机穿行在现实的每一个细微处,记录下行进中的中国社会的影像历史。
“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对都市电影的投射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导演往往选择观众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作为影片的主人公,这不仅使得电影角色更加亲切、质朴,同时也容易在情感上引起观众共鸣,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如前文所述,都市电影几乎大多选择了社会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城市平民作为故事主角,他们身份普通、地位卑微,是中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但却是不可忽略的群体,《小山回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影片故事很简单:河南民工小山在北京的餐厅里打工,快过年的时候却被餐厅老板开除了,遭此变故,他突然很想家,于是决定找几个老乡一起回家过年。在他寻找的同伴中有建筑工人、贫困的大学生、票贩子、服务员、“小姐”等等。“小山找老乡的过程带出底层生活的众生相。影片的结尾是没有人跟他回家,最后他只能在街边一个理发摊上,剪去了一头凌乱的长发。其实不论是妓女也好、包二奶也罢,下层工人、进城打工者抑或小县城众生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平民。”①蓝爱国:《后好莱坞时代的中国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张杨的影片《叶落归根》也以公路片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有关人性回归的温暖故事,呈现出城市平民的群像。农民工老赵在深圳打工,工友刘全有意外死亡,为了坚守承诺,他背着工友的尸体开始了“叶落归根”的返乡之路。在返乡的途中,他遇到过坏人,但更多的是好心人,并且很多好人恰恰是传统观念中的坏人,如仗义的劫匪、粗鄙的货车司机、黑店的店主、性感的发廊洗头妹,当然也有山地自行车爱好者、养蜂人、城市拾荒者、给自己办活葬礼的老人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老赵也在影片的结尾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归宿,和城市拾荒女走到了一起。
令人可喜的是,近几年的都市电影中还出现了很多勇于追求个人生存价值、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人格尊严的正面小人物形象,他们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大流下,勇敢地直视人生的挫折和困境,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懂得如何依靠自我的力量把握人生方向,并在亲情人伦的感召下回归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既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也彰显出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文明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举例来说,阿年的《感光时代》中的主人公马一鸣,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当摄影记者,一直梦想着能开自己的影展,他从根雕老艺人的遗愿中得到启发,在生活中寻找美,去山间寻找纯朴和乡野之美,把自己影展的核心元素转到怀旧的主题上,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最后影展大获成功;张猛的《耳朵大有福》里的退休工人王大耳朵,由于妻子住院花销大,退休金又少得可怜,生活在东北小城里的他走投无路,决定再去找一份工作,影片呈现的就是其找工作的一天,他去了一元擦鞋店、去蹬人力车、在推销会上参加活动、拜访在二人转小厅里工作的朋友、在修车行和打游戏的人吵了一架,回家后又发现女儿和女婿因为第三者的介入而感情不和,年迈的父亲在弟弟家吃不到像样的饭菜……王大耳朵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如意,夹杂着生活的无奈和困厄。可是,就在片尾,舞伴约他去跳舞,他忘情地跳着,仿佛忘记了所有的不快……
为了使日常化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真实,都市电影喜欢使用非职业演员,更有甚者,部分导演甚至在影片开拍前的几小时临时到陌生的人群中去找演员。非职业演员表演的最大魅力在于:没有表演的痕迹,天然地具有原生态的生活气息,亲切、质朴、自然。“那些非专业的演员从内到外去除了一切程式化的东西,以令人惊愕的力量表现了人物。”①安德烈·巴赞,崔君衍译:《电影是什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266页。张杨的《昨天》以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人和事作为原型,让演员贾宏声及其父母、亲人和朋友在影片中扮演真实生活中的自己,完全本色表演;李扬的作品《盲山》扮演村民的都是非职业演员,有一部分就是当地的农民;章明的《巫山云雨》中的导航员麦强、服务员陈青和警察吴刚等也都是非职业演员……而王全安的影片《图雅的婚事》则采用了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混搭的方式,除了女主人公的扮演者余男是专业演员之外,其他演员都是拍摄地的普通百姓,这种混搭的方式使得专业演员和业余演员在表演中相互启发、相互影响,表演风格质朴、自然又别有情致。
从美学形态上来说,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电影所呈现的影像风格的纪实化和人物形象的日常化,带给观众生活化的审美体验和观影感受,这与“泛审美”文化的价值内核是相统一的。
三、叙事的碎片化和镜语的感觉化
关于20世纪90年代“泛审美”文化的兴起,有学者认为:“‘审美’文化这个概念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之后提出来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出现的文化现象。”②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2页。也有学者说:“‘审美文化’概念,或者是指后现代文化的审美特征;或者是用来指大众文化的感性化、媚俗化特征;或者是指技术时代造成的技术文化,如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MTV等文化的特征。”①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4页。由此可见,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泛审美”现象的产生与中国“消费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和“感官化”潮流盛行紧密相连,以此来解读中国都市电影的碎片化叙事和感觉化结构,便能梳理出极为清晰的脉络。
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电影,从情节叙事的角度而言,放弃了传统电影中“起承转合”、“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完整的情节脉络和极具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而是选择了碎片化的叙事风格,有时全片甚至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情节的层次递进,也没有前后因果逻辑,而大多由心情、感觉等人为情绪变化推动情节发展,更像是日常生活片段的自然呈现,同时,将回忆、幻觉等感觉化的元素参与到叙事当中,显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更接近于生活的原生态。《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影片的故事背景虽然是文革时期,但是导演姜文并没有对文革的“伤痕”或“苦难”进行痛彻心扉的叙述,他只是为了感怀自己已逝的青春岁月和年少时光,片中处处可见充满诗意和温情的“碎片化”记忆:年少懵懂,把父亲抽屉里的避孕套吹成气球,拍着满屋子地玩;情窦初开,故意和少年宫的女生搭讪;在浴室洗澡时,伙伴之间以生理反应相互逗乐;和活泼、开放的女生举止暧昧,接吻玩耍;在月光如水的夜晚,坐在屋顶上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偷偷地潜入部队礼堂,偷看标有“少儿不宜”字样的内部电影;在铁皮屋顶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打发无聊的时光;打群架、拍砖,闯了大祸最后又莫名其妙地摆平;在莫斯科餐厅庆功、狂欢;暗恋心中的女神米兰,创造各种机会偶遇;撬开陌生人的家门,不为盗窃,只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每一个情节都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记忆中的场景,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一群没有管束、放任自流的少年整日游荡、肆意发泄青春癫狂和欲望冲动,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是一场青春的狂歌。诚如姜文在导演手记里叙述的那样:“电影是梦,这群人已忘掉了自己融入了梦当中,我们的梦是青春的梦,那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国家中的一群危险青年的故事,他们的激情火一般四处燃烧着,火焰中有强烈的爱和恨。如今大火熄灭了,灰烬中仍噼啪作响,谁说激情已经逝去?!”②姜文:《燃烧青春梦——〈阳光灿烂的日子〉导演手记》,《当代电影》,1996年第1期。
除了对成长记忆的碎片化呈现,都市电影还因为各自主题的差异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形态,比如说,影片《湮没的青春》几乎没有故事,只是情绪、心境和内心变化的外在呈现;影片《头发乱了》的情节构成全都是生活中的琐事,是情绪的碎片式拼接和几个不连贯的事件的串联,以杂糅的方式展现出女主人公叶彤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更有甚者,张元的处女作《妈妈》,彻底地打破了故事片和纪录片的风格界限,在结构上将这两种影片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在虚构的故事行进的同时,不时地插入一段段纪录片式的现场采访,让被采访者直面镜头,讲述自己的内心感受,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体验;张杨的影片《昨天》在再现贾宏声的“昨天”过程中,穿插了贾宏声及其身边的相关人物(如爸爸、妈妈、妹妹、朋友等人)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接受采访的一系列场景,并且在画面中故意将摄影机镜头拉远,呈现出摄影棚中影片正在拍摄的状态,不断给观众以间离的效果。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谈情说爱》中采用了三段式的重叠结构讲述三个现代都市的爱情故事,《城市爱情》采用了在叙事和电影语言上逆向对比的双重时空结构等……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导演在叙事结构上的把控力和想象力,也体现出“泛审美”文化影响下的都市电影所蕴含的后现代主义特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碎片化叙事还体现于后现代主义空间优位在都市电影中的充分呈现。所谓空间优位,是指在后现代主义的时空观念上,空间的优势地位得到充分体现,而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却失去了线性的逻辑关联,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的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不再永恒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空间可以代替时间取得优势地位。“空间都被主观化的进行了精心选择和处理,处于极为重要的优先位置,它作为主人公存在的环境往往对人的存在形成排挤和威压,故事在时间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模糊不清,但这些空间却是故事中明确而刻意交待过的,给人以极深的印象。”①杨晓林:《〈2046〉:碎片式的记忆和后现代情感表达》,《电影新作》,2005年第1期。这就不难理解,在现代都市电影中,时间往往总是被分割成七零八落的碎片,叙事中的人物也不是存在于时间的线性逻辑之中,而是活在时间碎片之上,唯一能够撑起逻辑关系的是空间,空间成为了存在的依据。《阳光灿烂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中的北京城,《苏州河》、《茉莉花开》、《紫蝴蝶》等影片中的上海,《安阳婴儿》中的河南安阳,《巫山云雨》、《三峡好人》、《密语拾柒小时》中的巫山水库,《小武》、《站台》、《任逍遥》中的汾阳县城……空间被导演用各种艺术手段和表现手法反复聚焦,而故事中的时间却出现了多处切割、断裂。在《苏州河》中,马达和美美的爱情故事时断时续,但作为整个故事背景的苏州河却得到了极大的突显,充斥全片的苏州河上行船的汽笛声、机器轰鸣声、水流湍急声等融合在一起,以一种奇特的混合声效完成了生动的隐喻,象征着生活在河两岸的城市人的精神迷离、生活困厄等。贾樟柯的《小武》中,街道两旁的店铺里播放着《爱江山更爱美人》、《心雨》等流行歌曲,录像厅里传出经典香港电影的对白,广播里播放着国家扫黄严打的政策宣传,空气里弥漫着福利彩票的叫卖声……这些极具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的声音和街上行驶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拖拉机等声音交织在一起,使得观众在听觉上立即产生了一种对城镇生活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导演正是通过特殊的城市空间、无处不在的嘈杂环境声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形象而立体地表达了对城市的真切感受——虽有孤独和迷惘,有无奈和无助,但也心有所盼,期待美好的未来。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体验恰恰是这一代都市青年人所共有的,具有普遍价值和现实意义。
感觉化的镜语是世纪之交中国都市电影的另一大显著特点,导演们喜欢打破常规,运用跳跃式剪辑,以短镜头的频繁切换、频闪和晃动等,来传达创作者极力要表达的焦灼、躁动和不安,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比如说,都市电影颠覆了淡入淡出、遮挡、化入化出等传统的剪辑手法,转而采用快速剪辑的方法,在蒙太奇中随意地将镜头硬性拼接,取消任何的过渡修饰;在时空上摆脱传统的逻辑关系,将不同场面调度的镜头直接交叉衔接;热衷于触犯传统的剪辑禁忌,在没有任何的情节暗示下以大幅跳跃的画面跳接来完成场景之间的切换等……这种消解常规的跳跃式剪辑手法非常先锋,带有明显的导演个人化标签。究其根源,世纪之交的都市电影导演大多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术高校接受过造型艺术教育,甚或本来学的就是美术、摄影等专业,他们对于色彩、造型、视听语言的理解非常专业,也很注重,其中不少人还间或从事广告制作和MTV的拍摄,在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又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比一般人更擅长于把握视听语言的构成,注重影片节奏和氛围的营造。比如说,《苏州河》的片头就是以快速跳接的方式将三分钟的蒙太奇段落进行组合,使得人物和场景之间产生了跳跃式转换,彻底消解了影片的叙事中心和情节线索,而摄像机的多角度拍摄和非规则剪辑也使得画面更加精彩纷呈,充满了视觉的跳跃感和陌生感。更有甚者,有的导演还尝试在影片中运用广告和MTV的拍摄手法,以构图精致的平面化再现、快节奏的镜头切换等手段去表现纷繁复杂的情绪化场面,李欣的《谈情说爱》、《花眼》中就借鉴了MTV的剪辑手法,以类似于广告片的质感营造梦幻般的视觉效果……总之,借助于这些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表现形式,现代都市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表达力得到了明显的深化和加强。
当然,叙事的碎片化和镜语的感觉化使得部分电影作品在受众的接受愉悦度上遭遇到尴尬,很多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一头雾水,不明所以,这无疑是导演创作中的缺憾之一。但是,这恰恰也体现出探索和创新的积极意义:他们以截然不同于以往中国电影的新鲜内容和陌生方式,带给了观众一种崭新的观影体验,是一种开拓性的进步。
一言蔽之,在“泛审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想根源影响下,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电影显现出现代审美的诸多特征:以都市生活为题材,以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为叙事对象,以纪实主义的影像风格和日常化的人物形象塑造,观照当下的社会现实,关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通生命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况味,并且丝毫不粉饰人性的晦涩、阴暗和社会文化的岌岌可危,大胆地裸露社会的原生态,大大拓展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视阈。与此同时,极具后现代主义特质的碎片化叙事和感觉化镜语也给中国电影语言的变革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考。因此,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电影在创作中展现出来的先锋意识、实验精神和开拓的勇气,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带来了新希望,也带来了活力和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