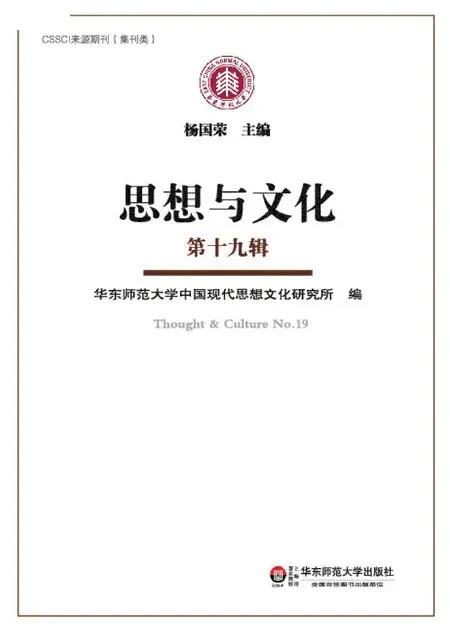〗先秦诗书文化与孔孟文化守成主义*
●杨海文
子思说过:“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①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1页。孔孟文化精神的实质是经由文化守成主义(“始于《诗》《书》”)达成道德理想主义(“终于礼乐”)。文化精神类似马克斯·韦伯说的社会学的理想类型,现实中很少存在,然而作为抽象的原则或典型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存在。文化精神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马克斯·韦伯说的历史学的理想类型有着内在的关联,亦即与具体进程中形成的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孟文化精神同样如此:道德理想主义孕育于礼乐文明传统之中,文化守成主义脱胎于作为传统资源的诗书文化。
一、诗书文化的历史重任
《史记·孔子世家》有言: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②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5—1936页。这里“礼乐废”与“《诗》《书》缺”并举,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周室衰微一般指相传由周公创制的礼乐文明在政治—伦理生态中越来越丧失统制功能,与此相比,司马迁还洞察到另一重内涵——诗书文化在思想—文化生态中越来越丧失统制功能。
在以周天子为中心的西周时期,就社会生态而言,政治—伦理生态是主要方面,思想—文化生态是次要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由前者所决定;就统制功能而言,尤其是从“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③参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2页。看,以“行同伦”为目标的礼乐文明是体,以“书同文”为目标的诗书文化是用。
礼乐文明的主体实践决定诗书文化的历史发展。诗书文化在这种关系中形成自身独特的使命,亦即保存并承传礼乐文明的实践成果。这种独特使命,首先要求把礼乐文明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知识形态。《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42页。在继往开来的主体实践中,礼乐文明通过学校教育而习得。《礼记·王制》说的礼乐、《诗》《书》各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作为知识形态,又都统一于诗书文化之中。依此,“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旨在确立诗书文化的思想—文化统制功能,而这一功能是为礼乐文明的政治—伦理功能服务的。
周室衰微结束礼乐文明与诗书文化体用一致的历史性统一之后,诗书文化与礼乐文明的逻辑性统一由此凸显。原因在于,诗书文化既具有载诸竹帛的物质属性,又具有文以载道的精神属性。即使礼乐文明的主体实践被外在因素所中断,礼乐文明的已有实践成果遭到巨大破坏,诗书文化也将因其物质属性传诸后世,因其精神属性昭示来者。春秋战国时期,诗书文化借助文以载道的运作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逻辑性统一的角度承担着经由诗书文化达成礼乐文明的历史重任!
孔子说过:
(1)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8·8②此种序号注释,参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2)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上博简《孔子诗论》)③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诗离不开志,乐离不开情,文离不开言。
(3)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616页。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亦云:“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⑤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2343页。
孔孟时代,礼乐文明再也不能现实地发挥政治—伦理统制功能,诗书文化失去自由地实现思想—文化统制功能的社会条件。尽管展示诗书文化与礼乐文明的逻辑性统一是文以载道固有的属性,但诗书文化这时处于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必然王国之中。只有经过人的反思与理解,诗书文化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并成为实践主体的知识素养与精神力量。先秦诸子出于王官之学,他们深知诗书文化作为知识要素的重要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智慧地把握诗书文化的精神本质。据《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自称研修《六经》很久了,熟悉过去的各种典章制度,老子则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①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9页。《六经》是先王留下的遗迹,而不是本原;足迹是脚踩出来的,但它并不等于脚。与老、庄的批评相反,孔、孟不独着眼于迹,而且探寻所以迹。
二、孔子:扭转诗书文化的坎坷命运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越来越消解礼乐文明固有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对于宗周礼乐文明,孔子心存“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3·14)的复古志向,因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5·15)、“入太庙,每事问”(《论语》3·15)、“诵《诗》三百”(《论语》13·5),认为书本学习比实地访问能够更快、更全面地了解知识形态的礼乐文明。在诗书文化中熟悉并把握礼乐文明,可以视为孔子“学而不厌”(《论语》7·2)的主要方式。孔子的知识十分渊博,正如《墨子·公孟》引公孟子所云:“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②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04页。
孔子不独自己努力学习诗书文化,而且在王官之学解体、学术流落民间的历史条件下,首开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以诗书文化教导青年学子。《史记·孔子世家》云:“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③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914、1938页。与前引《礼记·王制》一样,这里具有不同内涵的《诗》《书》、礼乐也统一于诗书文化之中。章太炎指出:“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①章太炎著,傅杰校订:《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页。杜国庠指出:“儒家学术是继续着西周以来世传的诗书礼乐,虽然关于谁是孔子的老师,有种种的说法,但他所学的总不出乎诗书礼乐的范围,则毫无可疑。”②杜国庠:《杜国庠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页。陈晹的《乐书》卷二《礼记训义·王制》指出:“《诗》《书》礼乐谓之四术,亦谓之四教。犹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谓之五典,亦谓之五教也。然不言《易》与《春秋》者,为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骤而语之故也。孔子之于《易》,必待五十而后学;游、夏之于《春秋》,虽一辞莫赞,其意盖可见矣。”③陈晹:《乐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34页。其中,《诗》《书》是课堂教材,礼乐是依据教材内容进行的实际训练。
《诗》《书》在孔子时代的独特性、重要性,表明它们承担了经由诗书文化达成礼乐文明的历史重任。下面两位学者的说法可资参阅:
儒家的课程原是“诗、书、礼、乐”四项。礼、乐是课堂外的实习课,只有《诗》、《书》是课堂上的两种教本。似乎一是文学课本,一是历史和政治哲学课本。(《诗》还是应排练礼乐课的需要所搜集的当时社会上行用的乐歌,同时也供儒生帮助统治者举行祭祀或外交典礼时歌诵之用。)由于这样,《诗》、《书》就成了代表儒学的两部重要典籍,因而法家运用秦王朝政权力量所要全力扑灭的也就是《诗》、《书》这两部典籍,以致下诏“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看出《书》这样的文献和《诗》篇竟都成了新政权极为害怕的东西,对它的焚禁达到这么厉害的地步。④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4—65页。按,标点符号略有改动。
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等教育的课程。又《诗》、《书》是符号(文字)的教育,《礼》、《乐》是实践(道德)的陶冶,所以《诗》、《书》列在先,《礼》、《乐》又列在其次。总之,一《诗》、《书》,二《礼》、《乐》,三《易》、《春秋》,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①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页。
司马迁说的“身通六艺”,从字面含义看,指孔门有72位弟子精通《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时代的诗书文化,果真达到了《六艺》或《六经》这种完整、全面的文本规模吗?
先看纸上的文献。一般认为,《庄子》最早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当作《六经》。《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②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第389页。郭象本《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③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页。这两条材料的文献价值历来倍受怀疑。关于《天运》,李学勤指出:“这显然是《庄子》寓言,《天运》又在《庄子》外篇,有晚出的嫌疑,因此现代著作多以为不足信。”④参见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页。上引《天下》一段位于郭象本“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和“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之间,陈鼓应认为“这二十七字为后人对上句‘《诗》《书》《礼》《乐》’的注文,误入为正文,当删除”⑤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第859页。,未把它们列入《庄子》正文。
荀子稍晚于庄子,《荀子》有《六经》这个概念吗?《劝学》云:“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⑥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2页。又云:“《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⑦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14页。《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①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133页。《大略》曰:“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②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506—507页。《劝学》《儒效》不言《易》,《大略》言《易》,但荀子没有把《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可证《六经》之称当时尚未固定下来。③蒋国保依据《庄子》《荀子》,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统称为《六经》,“决不会迟于战国中后期”。参见蒋国保:《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4期,第35页。
《诗》《书》《礼》《乐》并举,是庄、荀的共同点。《庄子》书里,《天下》有言:“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④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第855页。《徐无鬼》有言:“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⑤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第626页。《荀子》既提到《诗》《书》《礼》《乐》之归,归是归属;又提到《诗》《书》《礼》《乐》之分,分是职分。前者见《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⑥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133页。后者见《荣辱》:“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⑦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68、69页。
汉代以后,《诗》《书》《礼》《乐》四者并举,以及《五经》《六经》或《六艺》之说,则已司空见惯。譬如:
(1)……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新书》卷八《六术》)⑧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6页。
(2)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玉杯》)①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6页。
(3)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②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3197页。按,《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六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始见于太史公《滑稽列传》。”(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74—1075页)
(4)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法言·寡见》7·5)③韩敬:《法言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9页。
(5)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白虎通》卷九《五经》“右论五经象五常”条)④班固著,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47页。
(6)《五经》何谓? 《易》、《尚书》、《诗》、《礼》、《春秋》也。(《白虎通》卷九《五经》“右论五经之教”条)⑤班固著,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448页。
汉初,陆贾的《新语·道基》有云:“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⑥参见陆贾著,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页。徐复观指出:“仅《新语》五经六艺两名并列。且为两名之最早出现。以意推之,以礼乐为主,则称六艺。去乐而以诗书为主,则称五经。”⑦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再看地下的材料。郭店简有三段重要论述:
(1)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性自命出》)①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2)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六德》)②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88页。
(3)《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语丛一》第36—44简)③荆州市博物馆编: 《郭店楚墓竹简》,第194—195 页。按,廖名春由第38、39、44、36、37、40、41 简重新拼合而成:“《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参见氏著:《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第66页。学术界一般认为,郭店简的成书年代早于《孟子》,或与之同时。在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学发展史上,郭店简并举《诗》《书》《礼》《乐》和《六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思想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事件的思想史,另一种是传播的思想史。某个有意义的文化学术事件一经发生,自然而然成为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然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整个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这种思想史即是传播的思想史,也是人们日常说的思想史。文化学术事件及其文字记载很可能被后人所忽略:有时出于主观原因,人们从未意识到这个文化学术事件的特殊意义;有时出于客观原因,某个文化学术事件的文字记载被埋入地下,因而不可能为后人所注意。对于这种思想史,我们称为事件的思想史。事件的思想史指特定的文化学术事件缺席于思想史,传播的思想史指特定的文化学术事件在场于思想史。过去缺席的文化学术事件以后又变成在场,这类情形在思想史上同样屡见不鲜。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郭店简并举《诗》《书》《礼》《乐》和《六经》,既属于历史事实,又只是事件的思想史;《庄子》《荀子》并举《诗》《书》《礼》《乐》,则是传播的思想史。与事件的思想史相比,传播的思想史对于思想史的作用更大,地下的材料对于已经展开的思想史所起的实际作用比不过纸上的文献。具体到郭店简的出土将改写整个中国思想史这一论断,我们有必要意识到事件的思想史与传播的思想史之间的复杂关联,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
退一步,即便从郭店简到《庄子》《荀子》的《六经》之说以及《诗》《书》《礼》《乐》之说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它们也无法否定更早之前的历史事实:春秋时期,尤其是在孔子那里,《诗》《书》是诗书文化的核心文本。党晴梵说过:“儒家所称道的是《诗》《书》,若礼、乐仅就习惯作为律行的标准。”①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页。刘起釪指出:历史方面的《书》和文学方面的《诗》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两种读物,并称《诗》《书》②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第7页。。所以,西周以来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生态是以《诗》《书》为核心文本的诗书文化。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7·18)孔子不用方言而是用普通话给学生讲《诗》《书》,诗书文化在《论语》中即是《诗》《书》文化。孔子还超越诗书文化的知识要素,进而把握其精神实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2·2)“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17·9)孔子以“思无邪”精炼地概括《诗》的人文主题,以“兴观群怨”简约地阐释《诗》的文化作用。“思无邪”与“兴观群怨”是孔子《诗》教观的重要内涵。《十力语要》卷一《与某报》评论:“孔子论诗,是千古无两。唯孔子才能以他底理境去融会三百篇诗底理境;唯三百篇诗是具有理境的诗,才能引发孔子底理境。这两方面底条件缺一不行。”③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这首诗颂扬鲁僖公养马多,注重国家长远利益,凡四章。末章曰:“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骃有,有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610页。可今译为:“群马雄健大又高,放牧原野在远郊。请看骏马多么好:红色骃马灰白,黄脊马白眼鱼,身高体壮把车套。鲁公思虑是正道,马儿骏美能远跑。”⑤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56页。诗中,“思无×”依次表述为“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孔子独独挑出“思无邪”,并把它上升为《诗》教纲领,足见作为解《诗》者的孔子极其看重思想的纯正,期盼经由诗书文化重建礼乐文明。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8·8)孔子基于文以载道的历史学类型,意识到礼乐文明与诗书文化的历史性统一终结之后,必须与时俱进地架构诗书文化与礼乐文明逻辑性统一的未来愿景。文以载道的历史学类型是就诗书文化作用于礼乐文明而言,是经由诗书文化达成礼乐文明;文以载道的社会学类型是就文化守成主义作用于道德理想主义而言,是经由文化守成主义达成道德理想主义。两者相互关联,孔子的文化守成主义精神是从诗书文化传统中开显出来的。
就像深切地觉察到礼乐文明的现实困境一样,孔子对于诗书文化的坎坷命运也有着敏锐的感受:一方面,“文献不足故也”(《论语》3·9),诗书文化的物质载体——典籍越来越得不到有效保存,以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另一方面,“天之将丧斯文也”(《论语》9·5),诗书文化的精神本质越来越得不到积极弘扬,以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60页。。“文献不足”与“将丧斯文”釜底抽薪,致使诗书文化在新时期内的历史重任有可能落空。
孔子充盈着扭转诗书文化之坎坷命运的担当意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9·5)匡人曾受阳货的掠夺与残杀,孔子途径匡地,因貌似阳货,误被匡人囚禁。身家性命危在旦夕,一般人避害求生,孔子想的却是远远大于个体生命的文化命运——既意识到“天之将丧斯文”的命运悲怆,更以后死者(相对于文王而言)自比,朗现了“振兴周文”的历史使命。
如何具体落实这种担当意识与历史使命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7·1)③《墨子·非儒下》引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第437页)“循而不作”是“述而不作”近似的表述。就是孔子的回答。“述而不作”是针对载籍残缺提出的基本对策,可以理解为文献整理工作。孔子晚年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因而奠定《六经》规模,则如周予同所言:“这些话到现在都发生摇动而成为问题了。”①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355页。按,《毛诗正义·诗谱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唐代孔颖达正义:“《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263页。)有论者指出:“此则材料是自司马迁倡‘删诗’说以来,数百年之后的第一声异调。”(韩宏韬:《“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1期,第36页。)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四《策秀才文五道》亦云:“然考之《论语》,惟从先进似定《礼》,正《雅》《颂》似定《乐》,其余俱无明文。”②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64页。我们当以平常心看孔子的述而不作:孔子坚信“有德者必有言”(《论语》14·4),重视古代文献的整理与承传;他不仅用历代文献作为教育学生的四教之一(《论语》7·25),培养出子游、子夏两位熟悉古代文献的学生(《论语》11·3),而且把“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6·27、12·15)、“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12·24③这句话是曾子说的,可以代表孔子的思想。)作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的重要标准。“信而好古”是直面文弊道息抒发的信仰立场。在孔子看来,要完整地承传古代文献,必须具有信而好古的温情与敬意。子贡认为孔子博学多才,原因在于“多学而识之”,孔子则强调“予一以贯之”(《论语》15·3)。“一以贯之”是把信而好古的温情与敬意贯穿于述而不作的整个过程,所以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7·20)
述而不作的基本对策、信而好古的信仰立场属于具体的诠释,振兴周文的担当意识属于浓缩的表达。诗书文化在孔子时代中命运坎坷。自从礼乐文明与诗书文化的历史性统一终结之后,振兴周文的重中之重是经由诗书文化达成礼乐文明、经由文化守成主义达成道德理想主义,文以载道成为孔子振兴周文、高扬文化守成主义的内在机制。文化守成主义作为社会学的理想类型,逻辑上无处不在,但事实只是存在于对此有着高度觉悟的思想家身上。
哲学终归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且看《史记》《汉书》的描述: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史记·乐书》)①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176页。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书·艺文志》)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711—1712页。
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的边疆。周衰俱坏,郑音兴起,乐尤微眇。孔子的文化守成主义,哪里有足够的力量巩固得起诗书文化所以能够再现礼乐文明的基础本身呢?然而,文化在所有的时代中又是社会的灵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云:“遹求厥宁,遹观厥成。”③苏辙:《诗集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147页;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676页。按,此句又表述为:“遹求遹宁,遹观厥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526页)阮刻本当误,其校勘记没有说明各本差异。孔子借助诗书文化恢复礼乐文明,孜孜以求的正是文王时代那种天下安宁、大功告成的太平盛世。《经义考》卷二三一《孟子一》引欧阳修:“孔子之后,惟孟子最知道。”又引黄庭坚:“由孔子以来,求其是非趋舍与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④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等主编:《经义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65、4166页。按,《经义考》卷二三一—二三六辑录孟子学史料颇为宏富。孟子是如何被孔子的文化守成主义精神所召唤并激励的呢?
三、孟子:确立孔子与儒学的权威地位
诗书文化在《孟子》那里主要指《诗》《书》文化,《诗》《书》文化在孟子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四库全书总目·韩诗外传提要》:“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页。《孟子》不专门研究《诗》《书》,它既引《诗》《书》以证事,又引事以明《诗》《书》,两者兼容并包。对于孟子引论《诗》《书》,《东塾读书记》卷三《孟子》指出:“盖性理之学,政治之学,皆出于《诗》、《书》,是乃孟子之学也。”①陈澧著,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页。《万木草堂口说·荀子》亦云:“荀子不甚言《易》,孟子亦不言《易》,亦不言《礼》,孟子全是《诗》、《书》之学。”②康有为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3页。孟子思想体系何以与《诗》《书》文化传统如此紧密关联呢?
与孔子一样,孟子对诗书文化的坎坷命运也有着切身体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8·21③此种序号注释,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表明天子是维护诗书文化的决定性主体;“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10·2),表明诸侯是破坏诗书文化的决定性主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唤醒并展示诗书文化与礼乐文明的逻辑性统一,亦即在诗书文化中再现礼乐文明,从而恢复礼乐文明固有的、但又逐渐丧失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孟子同样依据文以载道的历史学类型,追问诗书文化的命运何以如此坎坷。
思想—文化生态的历史剧变,在孔子那里主要表现为诗书文化的命运坎坷,而在孟子这里还有“处士横议”(《孟子》6·9)。杜国庠指出:“孔子不但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教学的教育大家。他最先把古代氏族贵族所专有的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地教给民间;只要致送‘束修’,他是不问来学者出身贵贱的(所谓‘有教无类’)。这样就把官学变成了私学。也正因为有了私学,才有‘百家之学’。儒家学派就是最先成立的。”④杜国庠:《杜国庠选集》,第5页。孔子揭橥子学时代的序幕,其后诸子蜂起,百家并作,互相排斥,彼此攻讦。孟子把它称作“处士横议”,并试图整治这种思想乱局。
处士横议与《诗》《书》文化有关吗?且看墨子与孔子的关联:“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吕氏春秋·当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是否学于孔子,然后背叛儒家,且不讨论。重视《诗》《书》,则是墨子与儒家的共同点。傅斯年说过:“孔子、六艺、儒家三者的关系,我觉得是由地理造成的。邹鲁在东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六艺本是当地的风化。所以孔子与墨子同诵《诗》、《书》,同观列国《春秋》。与其谓孔子定六艺,毋宁谓六艺定孔子。所以六艺实在是鲁学。”①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8页。孔子、墨子皆鲁人,六艺又是鲁学,可为什么《孟子》《荀子》所引《诗》《书》多与今本大同小异,《墨子》所引《诗》《书》却与今本大相径庭呢?
固有之《诗》《书》与孔子之《诗》《书》实为二物,孔子之《诗》《书》也未必完全同于今本之《诗》《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谓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表明孟子因袭孔子传的《诗》《书》,同时做了某些创新。譬如,《孟子》引《书》19条②详细考证,参见杨海文:《〈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兼评陈澧〈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现代哲学》,2011年第4期,第105—107页。,《论语》引《书》仅2条。如下表所示:

《论语》引《书》一览表
《论语》引《书》少,《孟子》引《书》多,同样有其思想史意义。陈梦家认为孟子比孔子重《书》:“……春秋晚叶时,称《尚书》为‘书’。孔子答弟子问,引《书》为说,而弟子亦引《书》为问。但孔子当时,《书》似为雅言之一,其地位尚不如《诗》与《礼》、《乐》重要。”“……孟子时《尚书》或者已编成课本。孔子雅言《诗》、《书》,孟子用《书》授徒,或者是最大的分别。观于孟子屡与弟子讨论古史,可为佐证。”①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1、14页。蒋善国指出:《论语》引《书》仅2条,《墨子》引《书》多达42条,因而《书》是由墨子提倡起来的;《孟子》引《书》19条,先秦儒家中最多,这是因为墨家以《书》立说,而孟子当仁不让。②参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页。党晴梵指出:“《诗》《书》既然是周代的文献,儒家立说引以为论据的材料,墨家立说亦引以为论据的材料,但因两学派立场不同,虽用同一资料而论断就互异了。汉代统治者压迫墨家,学说中断,《诗》《书》遂为儒家专有品,更汇集《易》《礼》《春秋》而为五经。老子不引《诗》《书》是上层者予智自雄的态度,儒、墨代表中下层立说,就不得不极其谨慎,援引《诗》《书》以求其依重。”(蒋善国:《先秦思想史论略》,第40页)
罗根泽1932年发表的《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一文有言:
今观《墨子》所引《诗》《书》,率与今本不同;《尚书》阨于秦火,尚可委之残毁,《诗经》则未受秦火影响也,而亦大异。且《尚书》异者有什七八,固亦不可一委于残毁。《孟》《荀》两书,皆喜引《诗》《书》,固亦时有与今本异者,然同者多,异者极鲜(当别为《孟子引经考》、《荀子引经考》以证之),如谓火于秦,则《孟》《荀》所引,亦当如《墨子》所引之与今本大异也。今《孟》《荀》儒家书所引者,略同今本,墨家所引者,则悬殊太甚;今本举世知为儒家所传,被有浓厚之儒家色彩,则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之说,虽难遽信,而其经过儒家之修饰润色,殊有极深之嫌疑。③罗根泽:《诸子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7页。
《书》由墨子首倡,孟子又不让墨子,或为假说。《全晋文》卷一一二《陶潜二》有“八儒”条,其中说道:“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103页。孟氏是否就是孟子,本文存而不论。⑤郭沫若的《儒家八派的批判》认为《韩非子·显学》说的“孟氏之儒”即是孟子。参见氏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但是,《诗》《书》同为先秦诸子的思想财富,后来被儒家发扬光大,这是历史事实。《韩诗外传》卷六第21章引孔子曰:“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也。”①韩婴著,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页。《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②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3290页。孟子同样厥功甚伟。章太炎说:“……在荀子主礼仪,礼仪多由人为的,因此说人性本恶,经了人为,乃走上善的路。在孟子是主《诗》、《书》;《诗》是陶淑性情的,《书》是养成才气的,感情和才气都自天然,所以认定人性本善的。”③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37页。诗书文化旨在再现礼乐文明,但在迹熄《诗》亡、儒墨对峙的情形下,孟子如何整治处士横议的思想乱局、扭转诗书文化的坎坷命运呢?
扭转与整治是孟子针砭当时思想—文化生态的两种策略。为了扭转诗书文化的坎坷命运,孟子建构了“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它以“以意逆志”(《孟子》9·4)为核心,要求人们依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解读诗书文化的内在意蕴。为了整治处士横议的思想乱局,孟子凸显了“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它以“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6·9)为目标,希望人们坚守圣人之道,拒斥杨墨之徒的异端邪说。“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与“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鲜明地体现了孟子的文化守成主义,“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是这一文化基本精神的核心。
在孟子看来,一旦确立孔子与儒学的权威地位,诗书文化的坎坷命运就可扭转,处士横议的思想乱局就可整治。与扭转诗书文化的坎坷命运相对应,孟子重构了“《诗》云子曰”(亦有“《书》曰子曰”)的文化范式。这一范式在《论语》中初露端倪,但不具备形式化特征。孟子重新构建这一范式,并且使之形式化,强化了孔子思想与诗书文化的相互权威性。孟子“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正是立足于“《诗》云子曰”范式。与整治处士横议的思想乱局相对应,孟子构造了“尧、舜→汤→文王→孔子”的道统谱系(《孟子》14·38),不仅承认孔子与尧、舜、汤、文王的“道之本统”有着历史联系,更以“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10·1)、“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3·2)、“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3·2),强调孔子开辟了新的价值理想。孟子“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正是依托于这一道统谱系。
从《论语》看,孔子没有说过他是儒家,更没有说过他创立儒家。孔子之后,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充盈明确的学派归属感,以“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3·2)宣告了自己的立场①相关讨论,参见杨海文:《“儒”为学派义钩沉》,《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7日第13版。。由此立场出发,孟子强化孔子在思想背景上与诗书文化的相互权威,彰显孔子在精神方向上与古代圣人的一脉相承,从而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确立了孔子、儒家的权威地位,“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成为其文化守成主义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文化守成主义。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转折关头,巩固诗书文化所以能够再现礼乐文明的基础本身,这是孔子的主要目的;在儒墨相争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这是孟子的主要目的。孔子较多地认同作为传统资源的诗书文化,但不是只述不作,而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最早的诸子学派之一——儒家;孟子着重于确立孔子与儒学的权威地位,同样重视认同、转换诗书文化传统。文化守成主义从孔子传承到孟子,深刻地表明孟子对文以载道的社会学理想类型有着高度的觉悟。唯其拥有高度的觉悟,在诗书文化越来越丧失统制功能的战国时期,孟子才会随着思想—文化生态的不断变化,具体而又真切地弘扬文化守成主义的文化精神。
先秦以降,从传世文献看,先有《诗》《书》《礼》《乐》,四者又以《诗》《书》为核心文本,其后才出现完整的《五经》。秦汉以来,独尊儒术,经学昌盛。《礼记·经解》开篇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609页。今文经学更以《诗》为《五经》之首。从《诗》《书》到诗书文化,从诗书文化到《诗》教为先,孔孟文化守成主义代不乏人,薪火相传,宗风所及,召唤并敞开了隐藏于历史深处的道德理想主义对“其为人也”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