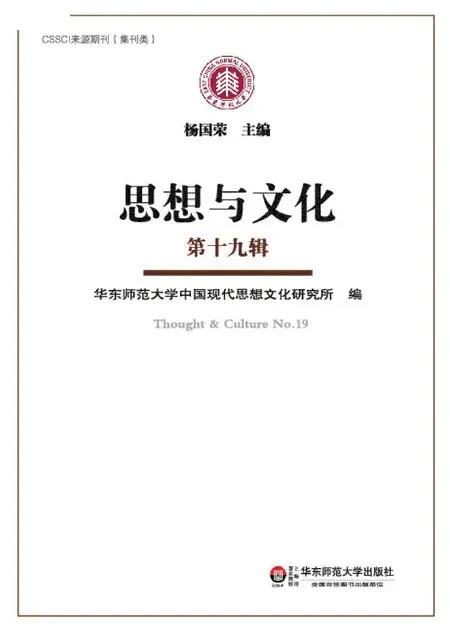〗当代中国与“儒学复兴”
●晓杰
一、儒学在当代中国存续之必要性
时至今日,尽管很多人对中国经济以及政治地位的日益提升以及“中国梦”有强烈的认同感,但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与资源分配、理想诉求,还是微观层面的民生,都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的问题,这已经很难再用单一的“经济发展”来解决。而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之复兴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似乎儒学已经不再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游魂”,而马上能“还魂”回中国了。但在这种潮流之中,也隐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行冷静的分析与梳理。
首先,赞成与推动也好,反对与质疑也好,“儒学复兴”涉及的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当然这只是求讨论之方便而已,三者之间无疑存在着大量的交叉与复合型的可能):一是当政者与相关人士;二是知识分子,更直接地说,在近代社会的框架下即大学的教授;三是非官方的民间人士。在此,本文限定的讨论范围是第二类,即知识分子的言说。这一方面是由于涉及高层政治决策的,非笔者所能得而闻之与轻议,故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乃至陈明先生的“市民宗教”等主张,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尽管民间的“儒学复兴”之背景与内涵非常重要,但笔者也没有亲身经历与考察之机会,因此只能是自我限定在知识分子同类相争的口诛笔伐之中了。
在此,本文先借用张志强先生的概括来给出本文分析的基本对象:“在最近十年来传统复兴运动与传统相关的论述中,具有理论模型意义的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传统之辩护人而自任的传统论者,还有一种是从文化政治论的角度出发的中国文明主体性的论述。”①张志强:《传统与当代中国——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传统复兴现象的社会文化脉络分析》,转引自《現代思想いまなぜ儒教か》,东京:青土社,2014年3月专刊(小野泰教翻译),第147页。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两种论述都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有密切的关系。前者在经历了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后,在当今形成了新的形式,后者则更多的是当代中国的某种文化自觉的结果,同时又与中国的经济与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即针对上述两种儒学复兴推动派的思想进行简单考察。
但在此之前,本文首先想就以下三个基本概念的混用作一简单评述:现在很多学者将“传统”、“儒学”基本等同起来,于是“传统之复兴与继承”就是“儒学之复兴与继承”,而近年来又有所谓“国学热”,“国学”之说法本身就很笼统,但无论是赞成与反对者似乎都将其大致理解为以儒学为首的学问。但是,“传统”、“儒学”与“国学”这三个词无论在内容还是涵盖范围、历史意义都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简单地说,从最广义的哲学层面上来看,任何时代之社会都必然面对界定与理解“传统”的问题,作为个人,从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被投性”来看,也必然与“传统”有最本质的关系——尽管大多数人可能是“习焉而不察,日用而不知”,此不必细说。抛开形而上学,就一般的现实理解而言,我们也基本应当同意,不是仅仅是相对于“当下”而言“过去的”东西就能称之为“传统”,无论是中文、日文或者西文的表达,“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定于“当下”对“过去”存在的一部分文化、精神乃至制度、宗教等层面的价值肯定与追认(因而肯定有尼采所说的“谱系学”的成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作为政治、社会架构的制度层面的“儒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这并不能成为“因此儒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唯一代表”的理由,此其一。与此直接相关的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是由梁启超等人从日本引进的东西,在这里姑且不论日本“国学”之本意以及流变,学界一般认为“国学”即是“一国固有之学”,而其内涵囊括了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之学问。但当我们翻看子部之收录标准,就会明白这当中不仅包含了儒学之外的“诸子百家”,还包含了“释家类”(佛教)、“道家类”、“耶教类”(基督教)以及“回教类”(伊斯兰教)等等部类,换句话说,至少从理念上来说包含了通过汉字书写而网罗到的“世界”。当然,这并不表明中国在古代即具有现代的“多元主义”之倾向,而应当说,是在“一”之层面下所可能容许的“多”,此其二。由此可见,“传统”与“国学”之所指涉之范围要远远大于“儒学”,因此当我们提到“回归传统”就想起“孝悌忠信”或者“四书五经”,这显然是有以偏概全之问题的。当然,本文也赞同学界对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即传统中国无论是政治、社会与文化,均以儒学为“正统”,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之传统或者一国固有之学就能化约为“儒学”。相对于争论焦点的儒学而言,从唐宋之际开始,中国传统社会之民众所信奉的多为杂糅了道教与佛教思想之诸神,这一点至今也没有改变,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道教”或者“(本土化之)佛教”不能成为“传统”之代表?更进一步要追问的是,如果说“儒学是传统中国之‘代表’”的话,这究竟是“谁”之“传统”?之所以要厘清上述三个概念,是因为如后文会提到的那样,将不可化约的“传统”化约为“儒学”,属于“全体性言说”之范畴,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而且如此之理解往往会导致当代政治学上所说的“多数派的暴政”的结果。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面对反封建派、欧化派的批判,儒学维护派主要采取了防御的姿态,亦即是说,面对“现代化”的强烈诉求,他们主张儒家传统不会阻碍中国之现代化,而且从儒家之思想与文化中还能够找到促进现代化的要素与资源,其一是肇端于美国学者的“东亚儒家资本主义”或者“儒教文艺复兴”(日本)的说法,即儒家文化对于经济发展能起到类似于西方新教的作用(当然这是对马克斯·韦伯的古典理论的比附与照搬),其二是力图证明儒家的政治思想中也有“自由”、“民主”之要素。前者的论证因为亚洲四小龙经济在九十年代后的停滞而不攻自破,而后者的主张在今日的传统辩护派学者的著作与言论中依然能经常看到。
对于上述诉求,事实上例如甘阳先生早在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兼论儒学与当代中国》一文中就指出,所有这些努力实际上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对儒学提出某种强弱不等的功利主义要求,尽管这些努力都主观上希望提高儒学的价值,但“恰恰是降低以至抽空了儒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其根本问题就在于,它们并不是从儒学本身的立场、原则去反观、评价、批评现代社会,而是力图使儒学去顺应、服从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和原则”①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14页。。换句话说,在这种防御性的姿态下,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要实现中国之现代化,则儒学之存亡会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对于儒学而言,现代化意味着什么”。这当中的区别非同小可。纵观欧美资本主义之发展,时至今日,除了弗朗西斯·福山这样的少数“历史终结派”论者之外,很少有学者还会相信以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为标准的“现代化”在根本上不存在很难解决的问题与困境。因此,中国一方面不能就此因噎废食而彻底拒绝“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不能“全盘西化”,故美其名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此,相对于杜维明、余英时、林毓生、李泽厚等学者所提出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甘阳借用了康德、韦伯的价值领域分割以及哈贝马斯的机能主义系统论,主张儒学应当坚守文化价值之阵地,而与其他近代体系相对区分开。熟谙西方哲学的甘阳当然不是要“反现代化”,而是将儒家界定为“非-现代”的文化价值理念,来相对化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化”的所谓“普遍性”,由此期待儒家能起到某种平衡剂的作用。但是,姑且不论康德主义式的价值领域分割在现实世界中能否成立,即便此分割能成立,儒家以及儒学研究在保持了自身的“纯粹性”的同时,却会丧失与中国社会的有机联系。儒家诚然不是功利之学,但也从不标榜自己是“无用之用”,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儒学无论是在内部批判还是对竞争对手之佛教、道教进行批判,其依据的最基本标准之一就是是否能“经世致用”或者“治国平天下”。诚如谭仁岸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不管是文化还是宗教,如果在社会中不存在人为的、物质的实践者以及媒介,则难免会成为列维森所说的‘博物馆’。”①谭仁岸:《儒学の「創造的転化」——八〇年代中国の近代化問題と関連して》,《現代思想いまなぜ儒教か》,2014年第3期,第136页。
在甘阳等学者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之“现代化”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自由、民主与科学等价值无疑是应当得到正面评价的(他们并不认为自由与民主就是绝对正确与好的),因此如果我们把问题分割为四个基本单元,即“传统中国”、“当代中国”、“传统西方社会”、“现代西方社会”的话,那么在儒学维护派之间是存在某种基本共识的,亦即:作为传统中国之代表的儒家文化和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文明”,彼此都有着值得肯定与借鉴的价值理念,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就可以采取如下的选择:
(1)在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框架的基础上,从儒家传统思想中选取符合现代理念(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等)的要素,儒家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比较被动的。
(2)西方现代化之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儒家思想与文化中的部分精华恰恰可以对治欧美资本主义之“毒素”(工具理性,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等等),因此儒家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而成为“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但是,在最根本的方向上中国还是需要工业文明、科学技术与民主体制等等。
针对第一种选择,我们很容易设想某种反驳:如果对于现代社会,儒家无法提供自由、民主等西方现代价值理念之外的东西,那么儒家文化之延续乃至复兴就缺乏必要性,因为西方已经有现成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乃至与之相符合的制度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地找自己良莠不齐的精神遗产中去寻找一鳞半爪的“自由”或者“民主”呢?
对于第二种选择,在笔者看来,可能存在着大量“似是而非”的情况:在当代中国所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其主要原因未必就是中国在按照西方之模式实现“现代化”才出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症状”。本文仅以“个人主义”为例来进行分析。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两大起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中,“个人主义”并非来自于古希腊,而是源于继承希伯来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到了近代,假定抽象的“个体”先在于“集体”乃至“社会”、“国家”,由原子式“个人”通过契约而构成社会与国家,一度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之主流。时至今日,由“个人主义”(尤其是现代美国)而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这基本是西方学界之共同认识。由此,提倡儒家价值理念之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人伦”,强调人与人之关系与网络先在于“个人”,此正可对治西方之“个人主义”。但笔者首先要问:我们都假定要解决的问题是当獉代中国(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的问题,而当代中国无疑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自私自利”以及“不顾他人与集体、社会利益”的“利己主义”①在本文作为口头报告宣读的时候,上海师范大学的王江范教授指出,“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应该区分开,笔者在此深表感谢。现象,但这个现象是否就等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假定当代中国存在的“自私自利”之价值趋向即是“个人主义”,那么这种“个人主义”是何时开始、从西方“导入”的呢?为什么说“导入”?就笔者之管见,解放后的中国政府在政治理念上从来都没有认同过西方的“个人主义”,即便儒家思想被贬低为“关系主义”或者“裙带主义”,大陆所提倡和推行的一直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理念。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但凡在海外有长期留学或者生活经历者,大致都会认同以下这种“外国人看中国”的观点——中国人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实在要远甚于欧美以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难道说这是因为中国“全盘西化”,走的比西方还要“西方”,乃至连现代化之弊病都沾染上乃至比师傅更严重?恐怕不是这样的。
更何况,西方社会从古至今都不乏反对“个人主义”的呼声,本身也有对抗“个人主义”的价值存在。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当然要放在古希腊的城邦制以及古希腊特有的民主观的脉络中来进行理解。贡斯当这样批评当时盛行的个人主义风潮:“古代人世界中的个人,尽管在公共事务上几乎都是主权者,但在个人关系上却全面的是奴隶。作为市民,古代人关于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但作为私人之个体,其全部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抑。”①Benjamin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ed.Biancamaria Fonta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11-312.即便承认抽象的个人先在于共同体与社会,作为个体也必定是在某个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中展开其生命与活动,所谓“对于民主主义而言,国境是必要的”②Seira Benhabib,Of Guests,Aliens,and citizens:Rereading Kant's Cosmopolitan Right,in Pluralism and the Pragmatic Turn,ed.Rehg and Bohman,The MIT Press,2001,p.363.,那么个体与时间上先在于他/她的共同体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成文乃至不成文的习俗(conventions)之间就必然会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在现实世界中作为共同体之一员,当然不意味着人就必须无条件地遵从共同体之意志或者习俗,因此作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之提倡者的康德才会区分“居民”(bourgeois)与“市民”(citoyen),只有后者才有参与立法的投票权,其必要资格是“自己是自身的支配者,并且在生计上拥有一定的财产”,③Kant, ber den Gemeinspruch: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taugt nicht für die Praxis,s.295,Akademie Ausgabe,Bd.无疑也是为了确保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之权利正当性(而不是抽象的“个人”之间的原初契约)。又例如,作为近代“人权宣言”的先驱之一,法国的权利宣言之标题本来是“人类与市民之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e citoyen),但在之后的历史中则被过度强调了“人权”的成分,以至于现代人很容易忘记了这一点:尽管其第一条“所有人生而自由且平等”的宣言,很显然属于西方个人主义之系谱,但与此同时,宣言也要求所有人作为“共和国之市民”,在“一般意志”之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作为一员而积极参与。(例如第六条:“法显然是作为一般意志之表现。所有市民,作为个人、或者通过其代表,拥有参与一般意志之形成的权利。”)以上仅仅是西方政治思想之一端而已,近年来出现的基于亚里士多德古典学说而建立的社群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麦金泰尔Macintyre)也好,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与国家主义之争议也罢,西方从来就不乏对于个人主义之反思与实践。
当然,从上述情况来看,西方的反省多集中在政治哲学以及公共领域上,而中国的儒学传统中强调的人伦关系,则不仅限于“君臣民”之纵轴,因此在君主制或者折衷式的君主立宪制均被否定的情况下,儒家依然能提供“父子兄弟”以及“孝悌仁爱”之价值观念与历史实践经验,这些均为西方社会所少提及(但不是“没有”或者“缺乏”)。陈来先生曾提到新加坡的“亚洲价值”,所谓“亚洲价值”,第一是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第二是国之本在家,第三是国家要尊重个人,第四是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维护秩序,第五是宗教之间应该互补与和平共处,陈来评论道:“这五项原则包含的,不仅是传统的东亚的价值,也有百年来吸收西方文明所发生的新价值……所谓亚洲价值不是追求元素上的那个差异,而是价值的结构和序列、中心有不同。”①http://zhuanlan.sina.cn/article?ch=history&id=5978&vt=4&page=2,2016-06-15.其实我们的所谓“中西之争”也是如此。提倡儒学复兴者往往认为某某为西方所无而是儒家之所独有,但很多情况下,一方面是古代之西方同样重视儒家所重视的某些核心价值(例如道德与伦理、共同体),但到了近代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此如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提出的:“中西之争”其实只是“古今之争”;另一方面,儒家重视家庭血缘之纽带以及行为规范之“礼制”,此并非西方所“无”,但西方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在其价值结构和序列上,血缘伦理和礼节规范可能都不占据中心地位。
简单总结一下本文对于“儒家价值观能对治中国当代个人主义之泛滥”这一命题的质疑:中国当代之个人主义可能并非直接源于西方个人主义,对此问题需要慎重考察与分析,此其一;西方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从未以“个人主义”为绝对,“市民”思想与近年来的社群主义等等都是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此其二;与西方侧重政治哲学与公共领域不同,儒家一方面要求“君仁臣忠”,一方面强调家庭血缘伦理之重要性与基础性(这一点徐复观先生有很好的论述),其价值序列与结构确有不同,但事实上能否运用儒家价值与实践就能对治当代中国之个人主义,则未可知,此其三。
由此可见,儒学维护派的观点与主张其实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反思与探讨。
二、作为“普世价值”之儒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来的儒学复兴思潮中,中国大陆开始逐渐出现了另一种新的主张,亦即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主体性的诉求。在这些学者看来,以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为标准的“现代化”已经破绽百出,其价值理念本身也并非具有“普遍性”,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应当在精神、价值层面上全面崛起,由此才能促进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到了这里,论者自认为已经完全摆脱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被动姿态,而转守为攻了。
从儒学复兴论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无论论者的论点如何,划分各派之基本标准都集中在“中”与“西”之比较上,换句话说,“西方”一直是我们在评价儒学时候的基本参照系。从五四时候对儒学的全面否定,到如今部分学者对儒学的全面肯定,我们都可以从其诉求中找到作为比较对象的“西方”这个大写的他者的身影。
将儒学奉为普世价值的学者(以下简称“儒学普世”),其正面主张并不容易归纳,因为各家对“普世”或者“普遍”的理解也好,当代提倡儒学的意义以及自我定位也好,都存在不少分歧,因此本文不打算从正面分析“儒学才是普世价值”的说法,而是从他们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亦即对西方“普世价值”论之否定上进行简要分析:其一,他们认为目前在中国政治中的左派即马克思主义派,右派即是欧美自由主义派,这两派其实都是西方之舶来品,不应当在中国的政治领域和价值领域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中国自有自己的传统政治主张与智慧。其二,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自称是“普世价值”,但实则一方面只是欧美社会内部才存在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而对非欧美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之输出,因此是虚伪而需要抵制的。
“普世价值”之说法当然来源于西方,亦即英文的Universal Values。但很奇怪,如果我们查阅《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的话,当中并没有收录该条目。一般西方思想中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超越时间、空间之限制的追求,被称为“普遍主义”,因此有诸如“普遍伦理”(Universal Ethics)之说法,但“普世价值”并不为西方人所常用,这一点首先应当得到澄清,反倒是中国这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08年左右达到使用的高峰,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对“普世价值”的质疑与反对。①汪亭友:《“普世价值”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页。笔者没有能力详细考证该词在中国之使用与流变情况,故下面说法仅仅是推测: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普世价值”,其主要语境是当代中国,是发生在当代中国对解决社会、文化乃至国家问题而持有不同政治立场与诉求的知识分子内部所发生的争论(因而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西方“自由”与“民主”,都或多或少是建立在大陆学者对西方“自由”、“民主”乃至“普世价值”的想象中),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对峙“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其次,在中国提倡“普世价值”、尤其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之学者,基本被视为是所谓“右派”的“自由主义”,而提倡儒学之“普世价值”的学者也承认,他们所要批判的首先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但同时又指向“西方那套深刻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这套理论指导下的美国”②陈明语,引自曾亦、郭晓东编著《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亦即是说,“儒学普世”论学者坚持,“自由主义”的弊病并不仅仅是中国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肤浅”所造成的“人弊”,而是就算自由主义再“深刻”也无可避免的“法弊”,故不得不破除。正因为如此,本文不考察中国的主张自由平等之“普世价值”论者,而直接分析作为源头的西方“普世价值”论。只有在对西方“普世价值”论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进一步评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否“肤浅”,“儒学普世”论者是否“深刻”。
英文版维基百科区分了两种“普世价值”,一种以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之说法为代表,认为“在几乎所有时代,在绝大多数地区和情形下的绝大多数人,均普遍持有此价值,不管其是有意识而明显的,或是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中”③Jahanbegloo,Ramin,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McArthur & Co.Reprinted 2007,Halban Publishers,1991,p.37。另一种则认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人都“有理由”(have reason)相信其价值,例如主导印度非暴力运动的甘地就认为,任何人都有理由将“非暴力”(non-violence)视为普世价值——即便并非当下的所有人都会如此认为。很容易就能看出,前者之主张是经验层面的,因此伯林用词很谨慎,说“几乎所有时代”而不说“所有时代”,说“绝大部分地区和情形”而不说“所有地区和情形”,这都是因为在经验意义上说“普遍性”,太容易被举反例而驳倒;而后者则是先验意义的“普遍性”,儒家说“性善”其实也是如此,都不为经验层面的所谓“反例”所能驳斥。那么回到普世派所要抗衡的西方“普世价值”问题上来,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在欧洲、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与民主几乎被认为是不容怀疑的价值理念,但毫无疑问,无论是被美国过度妖魔化的伊斯兰国家、非洲地区,或者广大亚洲地区,都未必会接受这一套价值体系。
既然在经验层面上我们很容易想象在任何时候的世界上都存在着不相信“自由”、“民主”的人或者社会,那么为什么一般的西方人还是会相信自由、民主为普世价值?显然答案只能是,普世价值被认定为先验形式的“普遍性”。普世价值是所有人都“有理由”(have reason)相信的,那么反过来说,不相信此普世价值的人,必定是“非合理的”(unreasonable)或者“蒙昧的”(barbaric,uncivilized)。这当然是典型的循环论证,但却非常有效。正如萨义德等学者所指出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种逻辑、为自己在十九世纪开始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提供意识形态的“正名”。但是,这些东西西方人自我批判就已经讲的够多了,本文不打算多作重复。西方“普世价值”说的强大之处就在于,首先,在20世纪绝大多数殖民地的人民都开始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统治,从而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但解放之后的这些国家与民族依然要面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此国际獉獉秩序或者标准当中,毋庸置疑掺杂了太多的欧美价值观与理念(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这样的国际秩序是不公正的);其次,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例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尽管各自不同,但在获得国家与民族之独立之后,都会构筑各自的“传统”与民族主义的言说,来对抗西方的价值体系与理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帝国主义之地理空间的系统性序列化与差异化,在生活空间中创造与发现属于自己的‘本有的东西’的努力”。这跟“东方主义”在本质上一样,都属于“全体化的言说”(the totalizing discourses)①姜尚中:《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批判の射程》,《岩波講座·現代思想15 脱西欧の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21页。:
欧洲大国的形象是在19世纪被支撑和塑造而成的。而这些恰恰体现在习俗、仪式和传统中。这是霍布斯鲍姆(Hobsbawm)、瑞恩杰(Ranger)和《传统的创造》(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其他作者提出的论点。当将各个前现代社会从内部连接的旧有的一线联系开始松弛时,当管理大量海外领地及国内新增人口的社会压力增加时,欧洲的统治经营明显感到有必要及时向历史汲取力量,赋予他们的权力一个只有传统和持久性才能赋予的历史合法性。
同样,在另一方也有了创造,那就是反叛的“土著”关于前殖民时期的历史创造。独立战争(1954—1962)期间的阿尔及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那时,非殖民地化运动鼓励阿尔及利亚人和穆斯林创造自己在成为法属殖民地以前所具有的形象。在殖民地世界其他地方的独立与解放战争中,许多民族诗人或文人的作品和言论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做法。①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Alfred A.Knopf,New York,1993,p.16.
正因为如此,殖民地在获得民族解放与建立独立的国民国家的同时,所采取的反抗性的言说(counter narrative)与策略,在原则上继承了帝国主义形态的价值体系的特征,可以说:这种形式的对“东方主义”的反抗,依然是“东方主义”。
当然,中国的情形不能简单地套用上述的批评,因为当代中国既不属于帝国,也没有被彻底沦为殖民地的惨痛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简单摆脱“全体化言说”的魔咒:在“普世派”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攻击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两点特征:
(A)西方之价值理念发展纷繁复杂,在近代意义的“自由”、“民主”之价值理念诞生之后,就从不缺乏对于“自由”与“民主”的批评与相关实践,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反省之早、力度之深,当前的非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无法望其项背的。在讨论“自由”与“民主”是否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时候,近三十年来(即冷战结束之后)的西方思想家都基本以“多元世界”为基本前提而进行探讨。①我们看一下美国“自由主义”的标杆人物罗尔斯的论说就很清楚了,他就明确承认“合于理但不可化约”(reasonable but incommensurable)以及“无法共存但合理”(incompatible yet reasonable)的诸价值规范之并存(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36)。事实上,在2011年11月5日复旦大学所召开的“普世价值的概念”讨论会上,白彤东先生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者是怎样的呢?他们现在很少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论证那套普世价值了,可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世界的多元性,因而承认人类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多元世界的前提下,我们能否还有一个普世价值?”(《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第7页)另外笔者在此想要补充一点:“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视为“右派”,但在西方基本都被认为是“左派”或者“左翼”(沿袭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国民议会的左右之区分),在近十多年来,美国、欧洲以及日本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坛格局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传统左派的失势与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保守主义势力乃至右翼团体的崛起,这些团体或者政党所诉求的是对各国之“传统”的复归、对移民乃至外来流动人口的敌视与排斥等等,虽然在学术上依然有不少“新左翼”(除了日本以外)学者活跃在第一线,但总体来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体“向右转”才是一个根本的趋势。而“普世派”简单地将西方社会之价值理念不分古今、不分具体情形地归结为自由民主并加以批判。
(B)西方之自由民主理念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与脉络,直到很晚,尤其是从殖民扩张的帝国主义时期,直到现代对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才与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结合在一起。“儒学普世”论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而片面强调了萨义德等西方学者早已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之侧面。
回首五四时期开始的“反封建派”、“西化派”对儒家的攻击,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找到相似的逻辑:
(A')传统中国走到清末,遭到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与压迫,几近亡国,此中之原因有很多,但反对儒家者一方面认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为统一不可分割之整体,“传统”既然已经无以强国,则必须一并革除,而“传统”又被简化为以儒学为首的价值体系与制度建构,因此“孔家店”必须被打倒。
(B')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很多问题,很多思想更被统治者所歪曲而被作为统治和奴役人民之工具,例如从孔子开始提倡君臣父子伦理纲常之重要,但到最后竟被扭曲到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以理杀人”、“礼教吃人”的地步,可见儒家思想是要不得的。
(A)和(A')都认定,某个民族或者地区的文明以及其价值主张只能是单向度的(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儒家的“孝悌忠信礼让”),(B)和(B')则认为,某种思想或者文化最终导致了非常坏的结果,那么此思想也必须负全部责任(以自由民主之“普世价值”强加于他国;以“君臣”人伦或者“礼”之名义强迫他者之服从)。一言以蔽之,都属于“全体性言说”之范畴——尽管是其主张与结论是完全倒转的。
作为对抗形态的儒家普世价值说,当然不仅仅限于本文所分析的这种形式。中国没有被殖民之历史,因而比较难与非洲、拉丁美洲等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国家产生较强的连带感。如果要提倡儒学是“普世价值”,那么儒学之价值就不局限在中国,而应当得到全世界人民之承认(至少在潜在意义上),否则就无法自称为“普世”。从策略上看,我们理所当然地会想到两个词,一是“东方”(此针对“西方”),一是“亚洲”(此针对“欧美”)或者“东亚”①“ 东亚”一词本为日文,因为日本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都使用了“大东亚共荣圈”,因而在战后日本避开了“东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東アジア(Asia)”的说法。。两个词汇都看似是地理概念,但实则是地理政治学以及区域文明论的范畴。通过论证“儒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广大亚洲地区也曾实现过“再本土化”,并影响各国之现代发展,儒学就超越了国界而成为凌驾于亚洲这一地理空间的“普世价值”。
众所周知,近年来以台大的黄俊杰教授为首的一批台湾学者提出了“东亚儒学”之主张:
所谓“东亚儒学”这个研究领域,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东亚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并不存在前近代式的“一元论”的预设,所以不存在“中心vs.边陲”或“正统 vs.异端”的问题。②黄俊杰:《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台湾: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第1—2页。
黄俊杰的界定可以说很清晰明确,但由此很自然会引发出一个问题:在东亚地区的不同国度及其文化传统中曾经存在过“普遍的”儒学价值理念吗?对此,吴震先生分析道:“他的基本观点应当是:东亚儒学拥有一种普遍价值观……一是‘(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一是‘思想结构的类似性’……无非是说东亚儒学无论是在动态的历史发展上还是在静态的思想结构上,都表现出‘同’的一面。”①吴震:《东亚儒学刍议——以普遍性、特殊性为主》,《中国学术》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页。但是,即便承认“德川儒学”、“朝鲜儒学”与“宋明儒学”在本质上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这也并不意味着黄俊杰等学者所主张的儒学之“普遍性”是以发生学意义在先的中国儒学为基准的“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子安宣邦提出对“东亚儒学”之严厉批评之后,黄俊杰反复强调其主张不是要搞某种新形式的“一元论”,也不预设“中心vs.边陲”的问题。黄俊杰版本②因为理论上说日本、韩国乃至越南都能建构各自的“东亚儒学”论,而在黄俊杰所主导的台湾版“东亚儒学”论当中,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成分可能是比较低的。的“东亚儒学”所存在的(潜在)问题恰恰不在于某种子安宣邦所担心的“中华文明帝国论”,而可能是相反——作为台湾学者而主张“东亚儒学”以及“东亚意识”,可能潜藏着“去中国化”的台湾主体性意识。③梅约翰:《东亚儒学与中华文化帝国主义:一种来自边缘的观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事实上,本文先前提到过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说,这里面无疑包含了儒学的价值理念,但新加坡也好,中国台湾也好,他们并不依据欧美的“政教分离”(这当然有宗教改革的背景在里面)原则,而是在政治上大力提倡儒学价值理念并参与相关活动,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的是“中国大陆的”儒学,而是已经被“去(中国之)脉络化”和“再本土化”之后的“(新加坡)儒学价值”、“(台湾)儒学价值”。然而问题在于,“去中国化”的倾向可能发生在当今台湾社会的诸多层面,却未必就是以黄俊杰为主导的台湾东亚儒学提倡者所主张的东西。无论从他们的相关著作还是其言行,笔者都无法认同“在台湾提倡东亚儒学的复兴就是台湾学者想要去中国化”的解释。
其实,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日本,在当年何尝不以中华文化之正统继承人自居而欲建立“东亚新秩序”?而这也正是子安宣邦所担心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日本在“西洋的冲击”(western impact)下很快整合了政局而发动“明治维新”,在经历了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之后,日本逐渐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主体意识,并开始策划对西方帝国主义之“世界旧秩序”说不,由此提出了所谓“新秩序”,即“东亚共同体”(東亜協同体)的主张,这一说法到后面就演变为“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是“以日本为首”的,包括“支那及其周边、隶属支那政治文化圈的诸国家、民族”和除此之外的“南方国的诸国家、民族”。为什么是以“日本为首”?虽然长期以来中国是亚洲甚至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政治大国和文明大国,但自从明清鼎革之后,日本逐渐认为这一“华夷变态”的事件意味着中国的衰落和日本的逐渐崛起,在19世纪之后,日本不仅吸收了西方之文化与科学,又拥有东方文化之传统精髓,只有日本才有资格成为代表整个亚洲之主要势力,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所掌控的“世界旧秩序”。对此最明确的表述当属1943年帝国日本所发表的《大东亚共同宣言》①新纪元社,1944年。,日本在此公然宣称,对于中国以及南太平洋的战争是为了使亚洲从“英美之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正义”之战争,同时更是为了“建立世界和平”与新秩序的战争。“东亚共同体”以及“大东亚共荣圈”之说法表面看起来似乎与儒学无关,实则对于自称融合了东西文明的帝国日本来说,儒学当然是“东亚”乃至“东方”传统之精髓,并为日本所发扬光大。例如作为第一批留学欧洲的精英,井上哲次郎在1890年从德国留学归来,便受当时的文部大臣委托为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撰写“衍义”,曰:“盖《欶语》之主意,在于修孝悌忠信之德行,以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1912年,他又撰写了《国民道德概论》,认为中国之家族制度是个体性的,而日本之家族则包含在以天皇家为始祖的民族大家庭之中,所以对于各自之家庭伦理的“孝”与对天皇之家族的“忠”是统一而无矛盾,日本之国体也因此优越于中国而值得万世弘扬,其用心由此可见一斑。宇野哲人以及之后的服部宇之吉则区分“孔子教”与“儒教”,以日本为继承“孔子教”而中国是没落的“儒教”。
至此,提倡“东亚儒学”或者“儒学在东亚”所可能引发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显:即便我们承认“儒学”在十六世纪开始的两百多年中,在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朝鲜以及越南等国家确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①日本和韩国的很多学者并不认同“儒学在东亚”之“普遍性”或者“同”,而强调儒学在传播途中的所产生的“变异”与再本土化之后的儒学之“特殊性”。特别是在经历了“明清鼎革”的17世纪之后,日本、朝鲜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认同明显遭到了削弱,葛兆光先生就撰文指出了这一点参见氏著《地虽近而心自远——17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台湾大学编:《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1期,2006年。对于这一“事实”的理解依然可能由提倡者之不同而呈现出声称各自之国家为“中华文明”或者“儒家价值”之正统继承人的局面,而这不用多说,都牵涉到东亚各国之间的国家、民族认同与政治利益问题。
就笔者之管见,在目前中国大陆提倡儒学复兴的学者中,还很少有人以“东亚儒学”或者“亚洲儒学”的名义来抬高儒学的“普遍性”,这一方面与大陆儒学研究的历史状况与学术积累相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尤其是日本之间的近年来的政治局势紧张有密切关系。笔者并不打算暗示,一旦大陆开始出现对于“东亚儒学”之风潮,就必然预示着某种“中华帝国”或者“中华文明一元论”的倾向。但在学界内部,有不少学者对日本儒学、韩国儒学研究颇感兴趣,而且在听到例如韩国现在还有很多诸如“家礼”的实践之时,总会由衷地感慨“礼失而求诸野”,笔者对此深表疑虑:“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正预设了过去的中华帝国之“华夷秩序”乃至“中心——边陲”之地理政治学理念。诸位不妨设想一下,当印度人在唐代来到中国,看到在印度本土逐渐衰败的佛教却得到中国朝野上下的信奉,他也感慨一下“佛法失而求诸野”,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听了会作何感想?
三、结论
以上,本文就儒学复兴论者的几种主流观点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与考察。中国发展到今天,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之成就,平心而论,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经验教训需要反省与总结。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对于自己的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否定之决绝,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都是很少见的,而在今天,尽管“儒学复兴”还无法说达到最广泛的共识,但无论是党中央政府、知识分子还是民众,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向度追求经济发展与繁荣所存在的困难,中国传统资源、尤其是儒家价值理念可能可以对治当代中国问题。但是,正如张志强先生所说,儒学也好,中国传统也罢,其对于“当代中国”(注意不是“以欧美资本主义为基准的现代化”)之意义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中国近年来对于传统之需求,与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普及、以及佛教为主的宗教复兴现象,在时间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我们不能像一部分传统辩护者那样,对于传统之复兴意气高扬,认为民众自然地选择了传统,即能证明传统之固有价值。对我们来说毋宁是这样,传统之复兴首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痛的反应,传统(笔者按:此处可加上“在当代中国”)之价值,实际上可以说必须在能否对治此时代病这一点上受到考验。”①张志强:《传统与当代中国——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传统复兴现象的社会文化脉络分析》,第145页。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所奉行的固然是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经济发展模式,还是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上,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乃至症状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问题可能就不是以中国儒家价值理念之“精华”来对治源于西方现代化的“糟粕”(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
其次,当代的部分传统儒学复兴论者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证明儒学存续之“必要性”,而开始积极地主张儒学之“普遍性”或者“普世价值”。对此,本文通过对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概念进行梳理,并指出:先验意义的“普世价值”说通过循环论证,一方面维系了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价值体系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出(官方外交或者非官方的媒体宣传等渠道),贬低不接受“普世价值”的国家与地区的价值理念,从而保持了欧美国家在心理上的巨大优越感。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文化帝国主义,就断定西方之普世价值说就是欧美资本主义之“阴谋”,因为如果把关注点集中在国别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得到解放的殖民地所各自倡导的“传统”以及价值理念也都在不自觉地情况下复制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策略。从五四时期对儒学乃至传统的彻底否定,到今日彻底否定西方、提倡中国儒学之普世价值的言论,我们固然应当肯定学者们的文化自觉与主体性意识,但与此同时,也需要警惕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实则都属于“全体化言说”的陷阱的危险。而这一点,我们从曾经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日本的近代史当中,能够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要而言之,只有经得起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批判与质疑,并努力给出相应的答案,儒学才可能继续在当代中国得到健康与持续的发展,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