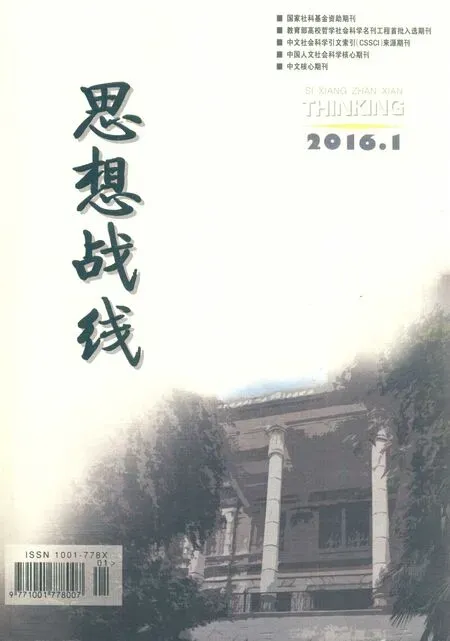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设计的反思
常士訚
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
——路径设计的反思
常士訚①
摘要:政治整合是当代多民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治整合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而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代学者在此问题上进行了不同的探讨,主要存在两大方面:制度路径和国家性路径。就前者而言,涉及威权主义政治整合和民主政治整合路径;就后者而言,主要涉及国家的合法性、治理能力和重叠共识的形成与引力作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不仅需要制度建构,更重要的是要有国家建设。也就是多民族国家在制度建构的同时,要从国家性,也即国家能力和内涵性关系建构上夯实制度存在的基础,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整合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加强国家建设,并不是否定民主建设。国家性建设只有和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性才能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制度选择;威权政治;民主政治;国家性
当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由两个或多个民族、种族或宗教集团组成的。如何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和平共存,共同生活在一起,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政治整合,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选择。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在路径选择上存在不同的设计和思考,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主张。本文主要以近些年来国外学者的观点为依据,侧重从学界普遍关注的制度选择路径和国家性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反思,在此基础上,对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路径选择的基本取向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当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政治整合是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责,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问题的成败决定着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民族的存亡。政治整合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指将民族国家内涌现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纳入一定的政治秩序的过程。政治整合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政治整合从来不是静止的,维护政治整合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深刻变革和市场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卷入全球化的大潮中。在这一变革中,不同地区和国家由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形成了中心与边缘关系。在这种模式中,中心地区集中了优厚的资本和福利,而边缘地区处在了经济上的依附和被剥削的地位上。中心与边缘地区的这种不平等,本质上带有民族和种族地区的不平等性和矛盾性。同时,由于中心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进而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话语霸权地位,意味着原殖民地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受到了发达国家的遏制或削弱,将辐射和影响到国内政治,带来国内统治合法性危机和政治整合的失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发展中国家绝不会坐以待毙。为了维护民族生存和发展,必然在国际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提高自己在国际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同时,不断促进和完善自己本国的政治整合。
就国内政治看,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内部,殖民者退去后,给这些国家留下了畸形分工的经济格局。尽管发展中国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优势民族和弱势民族的二元对立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出现了优势的民族群体居住在城市和良好的地方,并在国内经济体系中处在中心地位上,而弱小民族群体地处边缘,经济上处在贫穷和受剥削的地位上。当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沿着阶级分野而展开,阶级矛盾往往占据重要地位,如今天的拉丁美洲国家。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市场政策的调整而缓和。如果经济上的不平等沿着民族群体展开时,民族矛盾上升,不同民族群体就会以各自所居住的区域,各自所持有的资源和优势,而与其他民族或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众所周知,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生来就有不平等性。穷山恶水之地使人难以改善生活,实现富裕,投资者也不会光顾。气候宜人、资源富饶不仅带来民族的繁衍和发展,更成为人们投资和旅游向往之地。在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极度差异下,现代化会优先在那些具有资源和地理优势的地区和民族发展起来,在铸就民族经济富裕的同时,也提升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地位。据此,他们力图使那些落后的民族群体听从于自己的指挥,或者与国家分庭抗礼,如当代印度尼西亚的亚齐、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都曾经自持资源优势与中央政府对抗,从而使中央权力渗透到地方的权力有限,甚至出现有政治无整合的状况。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中央权力不出首都周围或被局限在有限的一些范围,而出了这些地区就成为了部落或反对派控制的地盘,鲜明地表现了一些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经济上的激烈竞争本质上是人的竞争、不同民族群体的竞争。竞争是一种特殊的人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不仅有个人的行为,更重要的表现为一定的群体行为。经济生活虽然按照分工将人以现代技术和组织的方式组织起来,但“现代国家的政治过程和结构似乎奖励那些以大规模集团的集体努力。比起如家庭、裙带和宗教来,族体性在实现集体利益上被视为是一种群体关系的寓所”。*S.W.R.de A.Samarasinghe and Reed Coughlan,Economic Dimensions of Ethnic Conflict,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1,p.6.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接触、比较,群体身份的建设和竞争,加大了群体认同和身份竞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族群中心主义,将这种身份认同自觉化,以此动员民族群体“为了最大可能的自治和∕或为了在与其他族群所共享的国家里拥有较大的份额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斗争”。*[美]马莎·L.科塔姆:《政治心理学》,胡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使原来一些国家或民族摆脱了大国的控制而自立为国,这为那些依然处在一个主权国家统治下的弱小民族带来希望。而跨界民族的发展,毗邻国家或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助长了一些民族群体的独立意识。政治整合需要一定的凝聚力支持,当政治凝聚力下降,人心离散时,政治整合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是建设中的国家。虽然独立后的很多国家有了现代国家的外形,如边界、主权和一定的人口,但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都处在建设和变动之中,也这就增加了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不确定性和制度的多孔性。全球化的发展,外部多元文化的影响,更使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结构方面存在着种种弊端和问题,从而使诸多的社会和民族问题暴露出来,使其不能得到有效的协调。一个较为科学完善的制度和治理可以改善公民行为,提高公民的归属感。而在一个布满漏洞的社会中,各种力量的较量和人的安全焦虑解构着政治秩序。
二、制度路径选择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
维护和实现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如何实现这一任务,涉及路径选择。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不同的路径设计,在此主要集中在威权主义政治与民主政治的选择上。
就民主路径选择而言,19世纪后半期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密尔指出:
在一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自由制度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缺乏共同感情,特别是语言不同的人民中,不可能存在实行代议制政府所必要的统一的舆论。*[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3页。
密尔的这种多民族与民主不可兼容的观点具有相当影响。然而,吊诡的是,印度、新南非都存在着严重的多民族、多种族的状况,甚至在一定的时期中还非常严重,但这些国家都推进了民主,国家并没有分裂,相反,各个不同种族能够和平共存,国家实现了政治整合。林茨讲到印度时指出:
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领导下,印度通过灵活和志愿的方式开展了大量的合作活动,在处理多民族紧张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这一过程,印度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就成为了一个民主的“国家—民族”。但是,如果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1990年代赢得了政权,而且企图把这个拥有1.1亿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变成印度民族—国家,那么毫无疑问,公共的暴力就会增加,印度的民主将受到严重的威胁。*[美]胡安·J.林茨等:《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中国学者秦晖从多元政治的角度评价了新南非的民主问题,指出:“所谓民族矛盾严重的国家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分裂”,这是一种“谬说”。无论南非、还是印度,他们实行的是一种“左右多元”的民主,这种民主并没有整垮国家,反而增进了国家认同,有利于国家巩固。*秦晖:《南非启示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84页、第586页。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亚非拉不少国家,尤其在东南亚国家表现更为突出。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曾说:“在所有的东南亚国家,族群紧张关系都是非常普遍的。”当然,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族群冲突更为严重。*David Brown,The S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1996,p.1.然而,如果与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比较,东南亚国家的民主转型并没有出现国家的崩溃,相反,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社会依然在国家的掌控之中,政治整合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研究非洲的一些学者也指出,非洲是多部落的社会,部落国家化和国家部落化几乎成为了非洲政治的典型特征。一些人也认为,在非洲这样的多部落国家,推进民主政治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崩溃、政治整合的失败,但非洲一些国家毕竟推进了民主,国家保持了稳定。
然而,不少人依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忧心忡忡。美国多头政治的代表达尔指出:
种族或宗教的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尤其危险,特别是如果他们又同地域相联系的话。由于种族和宗教的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很容易被看成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个人利益的威胁,所以敌对者很容易转变为一种邪恶的、野蛮的“非我”,他们的威胁刺激了人们的强暴和野蛮行为……并证明它们是正当的。*[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谭君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8~135页。
在这种背景下,多元的亚文化容易给民主政体带来紧张。 霍洛维茨和利普哈特关注到了族群分裂对民主稳定的影响。前者提出了一种向心性民主理论,后者试图通过一种共识民主取代运行了几个世纪的“多数人民主”。不过在制度选择上,不是收回民主,否定民主,而是修正竞争性民主或多数民主,政治整合获得巩固。
还有一些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出发,指出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不采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但至少可以采用“非自由民主”,如亚洲不少国家即为代表。加拿大学者贝淡宁以亚洲国家为案例,指出这种民主也只能是一种“非自由民主”。他指出,在这一地区的国家,道德共识重于西方的多元价值,国家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承担着更为积极的教育和规训功能。“在亚洲国家中,政治统治者习惯上主张,即使不是在生活各个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干预是合理的,目的是维护或建立一种和谐和平衡的政治。”*Daniel A.Bell,ed.Toward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5,p.14.在亚洲国家,非自由政治并不看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因为,这些因素与国家和经济管理者的集体目标是冲突的。对于民主,亚洲国家并不赞成多数人的民主。因为在多数人占优势的情势下,多数人的民主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群体权利的侵犯,并由此导致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然,在这样一种国家中,“不那么民主”倒能实现政治整合。*[加拿大]贝淡宁:《超越自由民主》,李万全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79页。由于多民族国家实施民主确实有不少相反的案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南斯拉夫国家的解体,21世纪最近几年来欧洲的分裂性公投,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多民族国家实施民主承担着巨大的政治整合风险。值此之故,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发表于2014年10月28日《联合早报》的《地缘政治变迁重塑政治秩序》一文中提出:“民主很难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力量。”“民主不足以整合多民族社会。”*郑永年:《地缘政治变迁重塑政治秩序》,《参考消息》2014年10月29日。
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比较倾向于把威权主义政治作为实现政治整合的路径选择。在这里,威权主义政治主要是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在这种政治体系中,存在着“有限的、不承担责任的政治多元化,没有精致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但具备独特的精神,且除了在发展中的某些时刻外,不存在广泛或深入的动员,由一个领导人或者有时是一个小团体行驶权力,这些权力受到正式的但不甚明了的限制,而它们事实上又是可以预测的”。*[美]胡安·J.林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威权主义政治有多种表现形式,史密斯将威权政治分为“人格化的威权制”和“制度化的威权制”。*[美]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谭道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53页前者更强调个人的强悍的统治,带有个人独裁特点,后者主要通过一定的集团,如宗教组织、政党、军人集团或寡头集团,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对国家进行统治。但这些统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效地抑制了国内出现的种族的、宗教的冲突,实现了政治整合。
蔡爱眉《起火的世界》一书以大量血的事实证明,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引进,“并不会将一个国民社区中的选民转变为思想开放的伙伴公民。相反,对选票的角逐助长了蛊惑人性的政客,他们将遭人嫉恨的少数族群当作替罪羊,煽动种族民主主义运动,提出要让‘国家的真正主人’重新获得国家的财富和民族身份”。*[美]蔡爱眉:《起火的世界》,刘怀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在蔡爱眉看来,自由市场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带来了种族仇恨,限制民主发展的威权统治倒能保证政治整合。具体而言,就是要使具有不同身份的群体,纳入一个内部团结一致的群体中,加强内部联系。在她看来,“在一个多种族的发展中国家,威权的统治是维护族群和谐的必要条件,以此便于财富的公平分配”。*Nicholas Tarling and Edmund Terence Gomez,The State,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Ethnicity,Equity and the Nation,Routledge Malaysian Studies Series,2008.p.3.
美国族群社会学家马丁·N. 麦格对发达国家、东欧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族群政治表达了一种权威主义的倾向。在他看来,一些多民族国家以为,致力于民族平等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国内的民族矛盾,实现政治整合,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
当政治和经济资源在各族群之间的分配平等达到最大化时,多族群社会中的各个族群能否相对和谐地共存,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有足够力量将族际冲突控制在可容忍范围以内的中央政府,仅仅公平不足以取得所有群体的效忠。正像伊格纳蒂夫所认为的,“在当今成功的多族群社会中,能将族群或者种族之间的紧张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的,是一个强大的足够使其权威得到尊重的政府”。
南非在此方面表现得比较成功,而南斯拉夫则是教训,在那里,一个强大政府的倒台使南斯拉夫分崩离析。*[美]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里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523页。因此,从当代正反教训中可以看到,“一旦强大的中央政府的粘合力消除,潜藏的族群仇恨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土重来”。*[美]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里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524页。
三、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
民主政治和威权政治只是从制度或权力与权利分配上,思考了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路径问题,但不少经验教训说明,政治整合更是一个国家性的问题。因为一些多民族发展中国家不是不存在制度,甚至制度层面内容还比较全面,但最终依然难逃政治整合失败。尤其苏联、东欧国家解体,“9·11”以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的战后重建,更使不少学者把国家性建设问题作为多民族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重要途径。
什么是国家性?林茨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中,以描绘的语言做了解释,指出:
在许多国家非民主政体的转型同时伴随着深刻的分歧:哪些在事实上构成了政治体(或者政治共同体),哪些民众或者民众们(大众或者大众们)应该成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地理边界的分歧的出现,以及关于谁在这个国家拥有公民权利的分歧的出现,我们称之为“国家性”问题。*[美]胡安·J.林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从林茨对国家性的解释中可以看到,国家性主要指国家对主权范围内事务的一种治理能力。就内容而言,主要涉及国家和国家建构、民族和民族建构等问题。而哈维尔·科拉莱斯更注重从客观上解释国家性,他认为,国家性是指“国家在国土内宣示权威的能力”。它是“国家制定政策并争取必要的共识——国内外的——以确保履行的一个程度上的衡量标准”。*转引自[美]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谭道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57页。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独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非常薄弱,也就是说,不少人只认自己的种族、民族、宗教或家族归属,缺少对国家的认同。如果说,西欧国家的国家建设是在战胜内部的各种地方的、家族的或宗教的力量,通过由王朝国家向人民主权或民族国家转变实现了政治整合,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更多是一种外部形式,也即是它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实质上的政治整合,如政治合法性、国家自主性、渗透性、国家能力等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就合法性而言,20世纪初,韦伯在对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分析中提出了3种合法性:即合法性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合法性统治涉及“合法授命进行统治”;传统型统治建立在“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事实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魅力型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模范样板之上”。*[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41页。上述3个方面的合法性,简言之,就是法治、德治和人治。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原生性*泽里曼认为,所谓的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是对远古时代的起源、演进和一种现实的自然状态的想象。在原生主义看来,族体性是生而具有的,不可改变的。参见Sandra Fullerton Joireman,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Continuum,2003,p.19.因素,如传统、宗教等诸多因素有着深厚的基础,因而后两者在政治整合中意义非凡。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第10章“整合的革命”中指出:
新兴国家很容易被基于原生依附的严重不满所伤害。原生依附的意思是指来自所“给定的”——或者更为精确地说,就像文化不可避免地卷入这类事务一样,它被假定是“给定的”——社会存在:主要是密切的紧邻和亲属关系,此外,给定性还源自与出生于特定的宗教团体,说特殊的语言,甚至是一种方言,还有遵循特殊的社会习俗等等。*[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07页。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就是超越这种限制,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在这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发挥国家的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对国家问题的研究也越加丰富。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斯考切波提出“找回国家”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国家是自主的,即国家既不会归于社会,也不会由社会决定。国家的作用就是促进组织和普遍利益。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国家自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的能力。在此方面,一些学者在研究亚洲的发展中发现,这一地区经济之所以得以发展,关键在于国家拥有掌控和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主要涉及政治自主、专家介入、社会镶嵌和官僚机构等。显然,这里以国家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国家自主性,既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强社会弱国家逻辑的反叛,也是对20世纪全能主义国家的修正。与斯考切波“找回国家”理论几乎相同的是,杰克曼在《不需暴力的权力》一书中,将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上。在他看来,政治能力就是政府解决冲突的能力,政权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过程,也就是权力实施与贯彻的过程。政治能力体现在两个维度,或者说,它由两部分组成,即制度与合法性。在这里,所谓的合法性是指“一定程度的默认和对政治秩序总体上的合理性的认可和接受”。*[美]罗伯特·杰克曼:《不需暴力的权力》,欧阳景根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而福山的《国家构建》,同样结合“9·11”之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问题。正如作者指出的,他的国家建构针对的是“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而国家建构的核心不是国家职能范围,而是国家政权强度。“前者涉及到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和追求的目标,后者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通常指国家能力和制度能力。”*[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米格代尔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强社会”的一面。这种局面不能不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整合程度带来影响。在他看来,在一种“强社会”的环境中,国家缺乏对社会的控制力及自主性,自然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整合。实际上,这是一种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上的政治整合。对于一个包括如家庭、宗教、多国合作、国内企业、部落、政党以及庇护组织组成的高度异质性社会,无论采取国家对社会的掠夺性整合,还是社会对国家的抵制,都不能实现政治整合的长久性。米格代尔从一种正和博弈的角度,重新论证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互相强化与建构的关系。韦思也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对于国家能力而言至关重要,并创造了“由政府控制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的概念,以描述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由“国家向社会行为者授予部分权力”的独特的制度化联系。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到,国家建设并不是国家中心主义,而是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承认、协商共治。政府通过各种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回应社会提出的问题和需要。同时通过各个环节上的政府创新,加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共治,提高公民对国家及其政策的认同。国家和社会的这种互动,正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核心。
如果说,国家建构的问题主要涉及政权合法性,民族国家建构则属于文化和价值建构,它与国家的凝聚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否成功或持久,很大程度上涉及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处理。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不同民族群体能够共存一体,首先涉及不同民族群体超越自我而认同和忠诚于国家的问题。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合适期待”,即“一个群体在面对其他群体之时的一种特殊的团结感”。*[美]胡安·J.林茨等:《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与国家相比,民族不具备任何组织性特征。它没有自主性,没有领导者,没有规则,仅仅拥有来自于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一个国家可以将其规则的外在一致性作为其存在的基础,民族则要求内在的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也即是说,没有这种想象,也就没有民族。然而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想象”,心理认同难以“一致”,又如何使这些各有自己认同的民族群体结合到一起,实现政治整合呢?林茨的解决方案涉及了公民平等。而在民主政治上采取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如联邦制、多样化的公共机构的存在,各种不同语言的存在等。与此相同的是,利普哈特提出了协商民主方式,强调个人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权利。林茨则主张,将集体权利与国家保护的个人权利结合起来是一种冲突较少的方式。*[美]胡安·J.林茨等:《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而这种方式实际上也就类似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涉及的,在个人自由权利得到保护基础上,实施承认的政治。这种模式不能不使民族国家建构颠倒过来,变为国家—民族方式。在此方面,印度即为代表。至于认同问题,林茨认为,他们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和社会性。只要国家政策得当,人们可以享有追求多样化和完整的认同的能力,这些不一定对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因为政治认同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久的,民主领导人的品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政治领导人可以培养多样化和完整的政治认同。”*[美]胡安·J.林茨等:《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四、余论
采取怎样的路径实现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上述国外学者对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路径选择的设计上,可以看到两大方面:一种是制度选择路径,另一种是国家性选择路径。在制度选择路径中,可以有威权主义政治,也可以有民主政治方式。威权主义具有权力集中的特点。在一个强差异性社会中,社会内部的多元化意味着各个组织、民族群体和宗教集团对各自偏好和权力的关注和执著。这些具有不同偏好的集团之间的排斥容易带来整个社会的分裂。为了保证社会不同集团能够和平生活下去,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将这些彼此对立的集团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应当指出,威权主义政治自有其合理之处。它通过对国内存在的多元组织和利益要求的限制和控制,通过现代化动员和组织,将分散的力量纳入发展的轨道上,通过绩效合法性改变国内的生存状态和分裂状态,其积极作用功不可没。然而,也要看到,威权主义政治也存在着局限性。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威权主义政治的主体,更多寄托在主体民族的精英身上,国内少数民族很难分享到权力。加之威权主义政治多以实现和维护主体民族的利益为重点,而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甚至一些威权主义者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外衣下,不惜以掠夺方式对待少数民族群体,以满足一己或所代表的民族群体的利益,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少数民族群体的抵制和反抗。就威权政治组织结构而言,官僚制和庇护关系结合在一起,官员与私人资本家的结合,不能不使威权政治与社会逐渐脱离开来,从而出现了国家和官员在合法性外衣下掠夺社会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情况。而社会和少数民族群体也通过各种方式躲避、抵制甚至反抗国家。国家与社会的脱节,决定了威权主义政治下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可能享受了一时的“和平”与“发展”,但内部滋生的断裂,解构着威权主义的统治效能和统治的合法性,这就决定了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整合蕴含着族际政治的危机。
而民主路径选择试图将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不同民族群体与国家结合起来,改变了威权政治所具有的被动性政治整合特点。它通过一定的政治平台和机制,将具有不同偏好的多元群体,其中也包括一定的民族群体吸纳进来,通过法治和对话等族际政治文明的方式,将不同民族群体和国家结合在一起,由此通过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统一,促进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然而,今天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民主,多是西方传播给他们的“竞争性民主”或“多数民主”。这里的“竞争”是对立主体之间的竞争,其所坚持的“胜者通吃”原则,带有零和博弈特点。即一旦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当政,人数上占少数的民族群体也就成为多数民族群体的“牺牲品”。多数与少数的竞争导致了社会内部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由此多民族国家和民主之间陷入紧张,所谓的族际政治民主也变成了一种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紧张。如果社会内部差异性比较小,政府尚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合理的利益分配,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不至于走向强烈的政治动荡,国家能够保持政治整合。一旦政府缺乏能力或能力低弱,不能有效控制民主进程,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也就走向了反面,民族分裂主义伺机而起,政治整合面临失败的危险。
对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无论选择威权主义政治路径还是选择民主政治的路径,都有其合理性方面,但都面临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由于发展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要务,往往威权主义政治具有优先地位。不过,在世界民主化浪潮面前,今天的威权主义政治也在发生着变化,一种“半民主”或“非自由民主”在亚洲一些国家发展起来。但要看到,制度路径的选择依然有其需要弥补的方面,因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的实现,仅仅使这些国家获得某种外部统一形式,作为实质性规定的国家性,即集中表现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建构这样一个全局战略性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如果与制度路径选择比较,国家性建设更侧重在了制度的内在本质上,它注重了政治整合内在机制的建设。国家建设涉及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安排和国家能力,特别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前者涉及社会成员对国家统治权威的接受程度和服从程度,国家在社会和不同民族群体成员面前的统治权威越低,国家就越难以控制和影响社会和民族群体,政治整合将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国家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地渗透到地方,不能汲取和合理分配资源,同样不能实现政治整合。而民族建构的核心涉及国家认同和国家的凝聚力。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也就是“认同问题”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碰到的棘手问题。现代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获得均质化的认同只能是一种理想。承认差异,发展重叠共识,扩大重叠共识的影响范围,建立一种稳固的共识引力场,使其能够辐射和影响周围,才能在政治整合中发挥强有力的中心引力作用,防止由于多元力量离散性而使国家走向解体。因此,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要想保证政治整合的长期性、稳定性和适应性,需要从统治的合法性、治理能力和重叠共识等“国家性”问题上寻求政治整合路径。当然,在此问题上并不是排除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是将制度建设和“国家性”建设结合起来,二者相互促进,才能保证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巩固。
有必要指出的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加强国家建设,并不是否定民主建设。实际上,今天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不少民族问题,是与本身存在的民主建设不足、扭曲或不成熟联系在一起的。不少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没有或缺少民主传统。这些国家中的“民”还停留在“臣民”文化的状态下。独立虽然使这些国家有了自己的“体”,但在“制”上往往继承的是西方的机制。这种机制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而是使这些国家获得优势地位的族群、部落或宗族的“寡头”成为了国家主人,其他族群或弱势群体依然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即使是这些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民主形式,如建立了议会和选举等,但不少机制的设计依然漏洞百出,不能起到有效地管理和整合国家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理解民主上或囿于西方的民主观念,或局限于本国的传统,或将民主视为就是“选举民主”,或将民主理解为就是“官”主。凡此种种,不能不影响到民主建设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建设上如果和民主建设脱离开或者出现畸形,则或将步入歧途。因此,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国家建设时,一方面应通过提升国家能力,为民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使民主建设获得实实在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在推进民主建设上,需要不断反思自我,总结民主建设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应从民主就是竞选,民主就是多党的排斥性民主观念中解放出来,真正将民主建立在以最广泛的人民利益实现和保证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民族群体合作共赢和民主建设之路。国家性建设只有和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性才能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廖国强)
作者简介:常士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多元文化与国家建设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天津,300387)。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选择研究”阶段性成果(13AMZ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子课题“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阶段性成果(15ZDA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