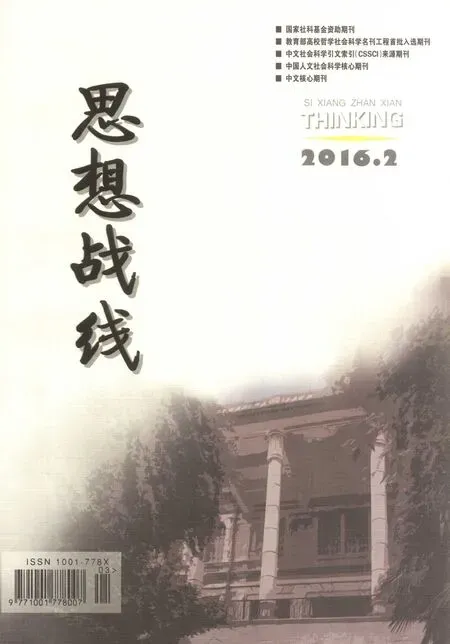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吴洪琳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吴洪琳①
摘要:由于儒士与道教的排斥及政府禁止汉人信佛的法律限制,佛教自汉代传入至西晋时期,信仰者大多为“羌胡”,佛教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成为民族边界标识的工具。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建立者因其民族身份,对“夷狄之神”佛教大力支持,以此凸显其民族身份,但汉人信仰佛教禁令的解除,形成了“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又在宗教层面上弥合胡、汉民族边界。北朝时期,太武帝与周武帝在极端反佛的方式下,也有摆脱本民族印记、认同华夏的意图。隋唐时期,困扰内迁胡族的胡、汉冲突与儒、释、道三教论争,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佛教成为胡、汉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关键词:中古;佛教;民族边界
中古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教繁荣发展的时期,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自两汉时期传入的外来宗教——佛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活动频繁的时期。在文化多元、民族多样的状况下,错居杂处的华夏民族与内迁民族之间,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生态及文化资源,总是有意、无意中寻求辨识民族边界或弥合民族边界的工具。*关于民族与边界的有关理论,可参见[挪威]弗里德里克· 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马成俊《弗雷德里克·巴斯与族群边界理论(代序言)》,《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其思想和信仰因素对个体、群体的归属感、自我意识、自尊和社会角色地位有深刻的影响,甚至有些宗教对此有直接的规定。从民族形成及发展史上看,宗教长久以来就是不同民族之间区分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在中古尤其是十六国北朝时期,无论对华夏民族还是内迁民族来说,都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新的信仰资源。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使华夏民族本能地对来自于异域的佛教产生一种拒斥心理,从而捍卫华夏文化的正统;而入主中原的内迁民族因为其“胡”“夷”之身份,对佛教却有着一种与华夏民族截然不同的亲近感,并且主动利用佛教进行民族身份的构建。面对同样的宗教资源,一个群体亲近,一个群体拒斥,两个群体的不同表现,使得在中古时期,佛教与民族边界的互动比较频繁,外来的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及一定范围内,成为内迁民族与华夏民族标识边界以及消弭民族边界的一个重要工具。本文试图就中国中古时期佛教与民族边界的互动状况加以分析。
一
佛教既是一种宗教,同时它也是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及与此相关联的宗教实践等诸方面,与中国原有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皆有冲突,因此一直受到来自于政府层面及社会层面如儒士、道士等的贬抑与排斥。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宗教信仰理念。早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政府就在法律层面,对立寺地域及信奉人群的民族身份作了限制,即只允许西域胡人立寺信仰:
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
从而抑制佛教的传播及信仰。西晋太康年间,政府仍明令“禁晋人作沙门”。*道世:《法苑珠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69页。 此处“晋人”即为与“胡”相对应的汉人,就是本文中或与“汉人”混用的华夏民族。汉人不准出家为僧的政策经汉代历曹魏、西晋一直延续到后赵。当然,禁令是一回事,实际情况也许是另一回事,当时汉人也有出家之人,但是,汉人的这种行为毕竟属于私度,从法律层面来说是不合法的。所以,“在汉、魏、西晋时期,佛教主要流传于侨居汉地都邑的胡人聚落空间内。而从文献反映的早期汉族僧人材料看,代表人物主要有魏、西晋时期朱士行、支孝龙、刘元真、竺法深等人。由于魏、西晋时期国家仍禁止汉人出家,汉人社会舆论环境也不支持汉人出家,故出家汉僧的生活空间基本上离不开奉佛的侨居胡人生活空间”。*叶德荣:《汉晋胡汉佛教论稿》,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其中作者认定为汉族僧人中的支孝龙、竺法深也应该是胡人。
除了国家或政府层面的明确禁止,传统的儒、道之士,也以佛教为“夷狄之术”加以排斥。东汉明帝时欲将派人西行获取“所图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经,缄于兰台石室”。*佚名:《汉显宗开佛化法本传》,道宣《广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年,第98页。但此行为遭到反对:
今陛下道迈义皇,德高尧舜,窃承毕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胡神,所说不参华夏。*佚名:《汉显宗开佛化法本传》,道宣《广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年,第99页。
反对者非常明确地认为佛祖是“胡神”,且指责佛教教义“不参华夏”。三国时期,儒、释、道之间主要围绕老子化胡、沙门袒服及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等问题发生争论,儒、道二家从伦理纲常上将佛教置于与“夏”相对的“夷”之地位,从而将佛教排除在华夏文化之外。对于佛教信仰,“世人学士多谤毁之”,*牟子:《理惑论》,僧祐《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年,第5页。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信奉之人自然极少。因而当迦叶摩腾“不惮疲苦,冒涉流沙”来到洛阳时,东汉明帝出于礼节虽以礼相待,并“立精舍以处之”,但时人却“未有归信者”。*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页。成书于汉末三国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梳理了时人对于佛教的误解以及儒士对佛教的非难之事,试举一例:
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牟子:《理惑论》,僧祐《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年,第3页。
也是径直将佛教当做“夷狄之术”。这种例子在《理惑论》中非常多,兹不赘举。“胡神”与“夷狄之术”成为儒生及道士排斥、反对佛教时经常使用的一种称呼。
由于国家政府层面的禁止,以及儒、道之士的排斥,一直到后赵政权正式放开汉人奉佛的禁令之前,汉人大多不奉佛,奉佛者主要为“羌胡之种”:
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桓玄:《桓玄与王令书论敬王事》,僧祐《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年,第81页。
寻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刘勰:《灭惑论》,僧祐《弘明集》卷8,《大正藏》卷52,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年,第51页。
中原人士与羌胡各有各的宗教信仰,出家为僧者大多为胡人,中原人士奉道,成为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如此一来,是否信奉佛教成为当时辨识胡人群体与汉人群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仅如此,学者通过对相关史籍记载的两汉至西晋时期的高僧进行统计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高僧传》的记载, 东汉到三国时期的传教译经高僧共有21人。这21人中,“有明确记载是来自印度及西域的僧人15人,其中天竺僧人5人,安息国僧人3人,月支3人,康居国4人,占了71%;而支曜、昙果、竺大力、帛延、竺律炎5人,文献中虽没有明确记载他们来自何国, 但从他们的支、竺、帛等姓氏以及他们同上列其他外籍僧人同行而至或合作译经的行迹来看,至少不会是汉族人,大多也是来自西域或天竺的僧人”。*尚永琪:《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不过,对于作者所说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来自何国中的支曜,其实是可以确定他的族属的:“支氏,本月支胡人,汉时来归,以国为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5页。故而可以确定支曜应为月支人,作者对于其族属的推断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学者统计的21位僧人中,胡僧有20人,所占比例非常高,高达95%强。因而,东汉至三国时期“传教僧人主要还是来自西域的胡人和印度僧人”。*尚永琪:《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因此,无论当时人的看法,还是后世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从两汉至西晋时期的佛教与胡人关系密切,其信仰者主要是胡人,传播范围比较窄,故发展比较缓慢。
二
佛教自传入以来,信仰者主要是胡人,且发展比较缓慢的状况,到十六国时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许多政权及其首领公开支持佛教,其中尤以后赵、前秦、后秦等为甚。羯人石勒尊崇西域高僧佛图澄,称其为“国之大宝”,*《晋书》卷95《佛图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87页。让其参与军国要事。氐人苻坚为了迎请鸠摩罗什,曾派吕光攻打龟兹,羌人姚兴把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迎入长安,“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2页。以至于后秦“公卿以下莫不钦附”,都城长安成为当时佛经翻译的重镇,有5 000多个僧人汇集于此,而且整个后秦的领地也是“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0页。甚至“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晋书》卷117《姚兴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5页。
在各个内迁民族政权的扶持与大力提倡下,佛教在中国的状况在十六国时期比初传入时已有了非常大的改观,至北魏时其境内佛寺与僧人数量都大幅度提高,分别达“四十千寺”“二百多万众”。*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卷50,石家庄:河北佛教协会,2005年,第640页。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内迁胡族政权对佛教的大力扶持应该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几乎是古今学界的共识,古人有“(佛教)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道林:《周祖巡邺请开佛法事》,道宣《广弘明集》卷10,《大正藏》卷52,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年,第154页。的断言,现代学者认为:“汉魏之后,西北戎狄杂居。西晋倾覆,胡人统治,外来之勤益以风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佛教的发展、兴盛与内迁胡族的密切关系,充分体现了内迁民族与佛教之间的契合感及认同感。
因民族身份产生对佛教的亲近,羯人石虎表达得非常明确。石虎曾公开宣称“佛是戎神,正所应举”,*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既标明了其民族身份,又说明了“正所应举”的原因。通过推崇、信仰佛教这种方式,标明或凸显了信奉者的民族身份,但是这种在汉人官吏反佛建议之下激发出来的民族身份的标榜,毕竟有点意气用事的意味,不仅无助于其政权获得华夏民族的支持,反而授人以“夷夏之辨”的把柄。因此,石虎坚称“佛是戎神,正所应举”的同时,还明令自此之后汉人可以公开出家,不必私度:“夷、赵、*“赵人”与前文“晋人”性质相同,即与“夷”对应的汉人或华夏民族。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大量的汉人也开始公开信奉佛教,从此“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6页。。石虎的这一政策打破了只有羌、胡之人可以信奉佛教、出家为僧的禁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府层面明令汉人可以出家”,*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此后汉人出家为僧便成为一种合法行为,佛教的势力迅速遍及后赵统治的广大北方地区。“胡晋略皆奉佛”的状况使佛教由胡人信奉的“戎神”成为“胡”“晋”两个群体之间的共同宗教信仰,佛教由两汉西晋时期民族身份的标识逐渐转化成模糊民族界线的一种工具。
虽然石虎放开了汉人信奉佛教的禁令,从宗教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胡、汉民族的界线,但是,华夏民族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内诸夏而外夷狄”“贵诸华贱夷狄”思想绵延不绝。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偏见,曾在社会上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内迁胡族已经称帝的情况下,“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晋书》卷104《石勒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仍是当时人的普遍认识。当时内迁胡族建立政权时因其民族身份都面临着政权正统性的尴尬,因此,他们必须努力寻求一种事实或理论上的根据,来解决这一问题。刘元海自我标榜:
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卷110《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49页。
北魏拓跋氏则将其祖源与黄帝联系在一起: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此外,儒家传统的五德历运也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各个政权用来论证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工具。*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总之,面对政权正统性的挑战,内迁民族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时机及工具论证其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
太武帝时期,北魏成为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的内迁民族建立的政权;周武帝时,长期处于内迁民族统治下的华夏民族,对于胡族所建政权也已经有了很强的认同感,但是鲜卑族的身份使太武帝与周武帝面临着解决政权正统性的困境和尴尬。与之并立的南方政权因是汉人所建政权,而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是天然的正统所在,而且南方的政权统治者顺理成章地在“夷夏”之别中占据“夏”的位置,并且时常理直气壮地把当时活动在北方地区的胡族斥为“虏”,视其所建政权为“僭伪”。在这种形势下,太武帝与周武帝自然对影响其政权正统性的因素拒之千里。更何况佛教在这个不适当的时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恰巧又暴露出了足以致命的窳败现象,更给伺机已久的统治者以口实。面临“正统论”的挑战,太武帝与周武帝不惜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
太平真君五年(445年),北魏太武帝两次下诏严厉打击佛教,在诏书中身为鲜卑民族的北魏太武帝坚定地把佛教指斥为“西戎虚诞”“邪伪”“鬼道”,其神祇是妖鬼、胡神,经典是胡经,承天绪的自己有责任“荡除一切胡神”*《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4~3035页。等。太武帝的诏书表明了其严厉打击佛教的态度,表达了其借此以争正统去僭伪的心理,同时也暗含其试图脱离原本的鲜卑民族印记,自我认同为“华夏”的意图。周武帝的诏书将这种意图表达得更加明确和清晰:
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佚名:《历代王臣滞惑解》,道宣《广弘明集》卷6,《大正藏》卷52,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年,第126页。
他认为佛教是生于西域的“非正教”,是“胡神”,因“朕非五胡”,故自然“废之”。周武帝非常明确地将自己的民族身份定位为非“五胡”(北方内迁民族的泛称)。太武帝与周武帝的灭佛诏书暴露出了同样的心态,反佛方式也是淡化其真实的民族身份,表明其对华夏民族认同的一个工具。
三
隋唐时期,佛教因是外来宗教而仍不时被当做夷俗受到攻击,无论是皇帝抑佛,还是士大夫反佛,皆常持夷夏之观。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在三阳宫避暑,当时有胡僧欲邀其观看葬舍利,被狄仁杰劝阻:“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主。彼胡僧诡濡,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久视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546页。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欲迎佛骨入宫供养,韩愈谏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新唐书》卷176《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9~5260页。即使此时仍有人如此前一样以“夷夏”之论排斥佛教,但此时期如何对待佛教的态度所表达的文化意义,远大于民族身份标识的意义。
隋唐时期的政治局势及民族形势与十六国北朝时期已有很大的不同。隋唐实现了“大一统”,政治上没有十六国北朝统治者所面临的中原立足的急迫感,更不会因民族身份而存在正统性的困扰,再加之,通过十六国北朝长期的混融杂处,民族融合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隋唐宗室为例,隋、唐两朝的皇室均为胡、汉混血后裔: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即隋炀帝的母亲,是匈奴人;*吴洪琳:《关于中古独孤氏的几个问题》,《唐史论丛》第20辑,2015年2月。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元贞皇后即杨坚独孤后的四姐,同样也是匈奴人;唐高祖皇后窦氏(唐太宗的母亲)、太宗皇后长孙氏(高宗母亲)、睿宗皇后窦氏(玄宗母亲)皆属鲜卑人。因此,唐朝开国之君高祖及贞观、开元盛世之主太宗、玄宗3人,皆为汉族与鲜卑族婚配的混血儿。李唐皇室是北朝民族大融合后出现的汉胡混血后裔,其核心力量又是西魏、北周、隋政权最高统治层汉、胡后裔,故胡三省说:“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资治通鉴》卷108太元二十一年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9页。唐太宗不仅是中原的皇帝,同时又是西北诸蕃的“天可汗”:*《旧唐书》卷3《太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页“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憾。”*《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240页。唐太宗成为胡、汉民族的共主,因其“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247页。困扰十六国北朝政权的胡、汉冲突至此基本消解。 而中国历史上只有民族冲突及民族矛盾比较激烈的时候,“夷夏之辨”及“夷夏之防”才是华夏民族排斥其他民族的有力思想武器,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夏金时期等,因此,在隋唐时期民族矛盾得到比较好解决的情况下,夷夏之防的必要性大大削弱。
外来的佛教,经过长期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教的冲突、排斥、磨合,三者之间的矛盾逐渐缩小,它们互相吸纳、融合,呈现出一种“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唐代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6页。的走向,儒、释、道三家都从不同程度上期盼着“三教合流”的新局面。因此,到了唐代,形成了三教合流的社会气氛,“士大夫阶层人士兼习三教或二教兼习已成为一种风气,他们热衷于与僧、道交游;而僧人、道士结交儒者、朝廷官吏,熟悉儒家学说的也大有人在。三教共处,被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所接受,成为多数人多元信仰精神生活的一大特色”。*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8页。而佛教在传入中国不久,就开始意识到需要吸收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或者借鉴道家的思想及修行方式等,经过儒、释、道三家之间的互相通融,到唐代,僧人神清认为,三教基本上实现了“各运当时之器,相资为美”*神清撰,富世平校注:《北山录校注》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 65页。的状况,僧人宗密作《原人论》进一步提出会通本末的主张:“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扬,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故有学者认为:“宗密的著作是三教从调和伦理道德的对立到融通世界观的分歧的重要标志,这足以说明隋唐时期三教的融合已进入思想文化的深层了。”*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8页。因此,隋唐时期,统治者顺应了这一趋向,采取了平衡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政策,明确了以“儒学为本、道释为辅”的官方意识形态基本结构 。*参见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而整个唐代,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政府基本上实行的“三教共存,不分先后”的政策 ,*寇养厚:《唐初三帝的三教共存与道先佛后政策》,《文史哲》1998年第4期。也有力地促进了儒、释、道三教合一。
此时佛教也已经出现中国化的趋势,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佛教有已经中国化的,有的仍然保持印度原来精神的。但无论如何,主要僧人已经多为中国人。”*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此外,佛教在宗教实践方面已经向中国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妥协,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等问题得以圆满的解决 。*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佛教中国化的实现,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佛教思想磨合的结果。宗教信仰对人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有很强的影响、支配作用。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成为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民族交流与交融的一种工具和途径,共同的宗教信仰不仅削弱了民族间的对立,同时也有力推动了民族间的整合。在共同的宗教思想体系及宗教实践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原有的民族归属意识渐趋弱化甚至消失,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一体化进程。因此,到了隋唐时期,统一王朝的确立,由民族身份而引起的困扰十六国时期内迁胡族政权的胡、汉冲突得到进一步消解,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互相妥协与和解,以及佛教中国化的趋势,使佛教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初传入时曾经的民族身份的标识作用消失,最终反而具有了促进共同民族意识产生的作用,佛教与民族边界的互动关系至此基本了结。此时,其他的外来宗教三夷教(祅教、景教、摩尼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取代了佛教原有的民族边界的标识作用。
综上所述,佛教传入中国后,自两汉至后赵,政府通过法律方式禁止汉人出家为僧,从国家层面树立了一个华夏民族与内迁胡族的边界;儒道之士以“夷夏之辨”为思想武器,以佛教为“胡神”“戎神”加以批评或排斥。由于政府及儒道之士两个层面的努力,因此,佛教在一定程度及一定范围内,成为标识华夏民族与内迁胡族边界的一个工具,即信佛教者皆为胡,反之即是华夏民族。虽然当时也有少数汉人出家为僧,但这属于私度,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些汉僧也大多活动在胡人聚落之中。到十六国时期,内迁民族统治者试图以尊崇佛教来彰显自己的民族特性,重新构建民族身份,但是民族身份的重构并不能解决来自华夏民族“夷夏之辨”的思想对抗。因此他们试图放开汉人信奉佛教的禁令,通过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努力,在一定上程度消解了胡、汉民族的边界,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形成了“中州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但是政权建立者的胡族身份使得政权的正统性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而南方政权因其统治者为汉族而具有天然的正统性优势,故而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为了显示自己亲华夏而非胡的态度与决心,借助于对“夷狄之教”和“胡神”的排斥与迫害等极端方式,试图模糊自己的胡族身份,表明其认同华夏民族的意图,促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内迁民族与华夏民族的边界。隋唐时期,实现了政权的一统,唐太宗既是中国帝王,又是天可汗,十六国北朝时期各个政权面对的正统性尴尬已不复存在,而且此时佛教也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过程,从而基本上清除了中国社会士族阶层以“夷夏之辨”反佛的障碍,儒、释、道三家相互吸收和融合,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此时仍有人以夷夏观念反佛,但其文化上意义已经远大于民族上意义,佛教已经成为胡、汉民族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责任编辑廖国强)
作者简介:吴洪琳,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陕西 西安,710062)。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13BMZ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