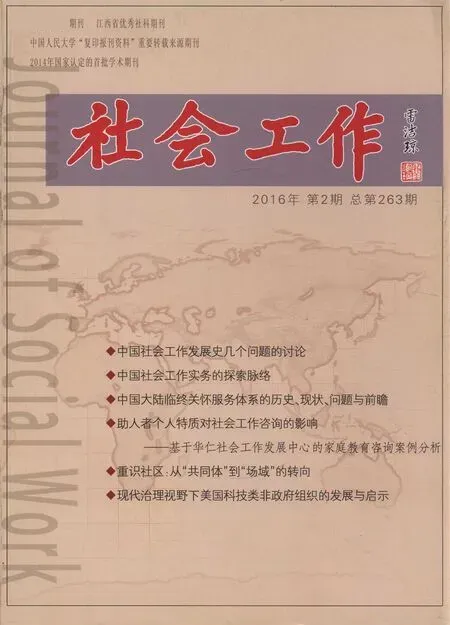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探索脉络
孟亚男 石兵营 陈静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探索脉络
孟亚男石兵营陈静
摘要:梳理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兴起与发展过程,需要明确社会工作实务的基本概念,同时明确“外来的”和“本土的”区别。通过文献整理,可以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引入和探索、源自“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和专业恢复至今社会工作实务的兴起与职业化进程加速。这三个阶段都是社会需求的客观反映,有其内在的历史脉络。
关键字: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探索脉络
孟亚男,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石兵营,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陈静,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保定102206)。
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掘都是在建构一种“现代性”的发现过程,社会工作以及其所从属的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在近现代史上的考察也是如此。在《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一书中,李怀印(2013)将这种现代化叙事的中心命题概括为5个方面:第一,传统中国因其自身文化而处于“落后”状态;第二,现代化的关键是引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现代制度;第三,开明的统治精英的努力使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可能;第四,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成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第五,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由民主。这就为我们在相对宏观的框架下分析社会工作实务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一种线性进化的分析思路。本文试图在澄清一些基本问题之后,从历史和“实务”两个维度梳理中国社会工作的两次引入和最终纳入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线索和过程。
一、需要明确的前提
书写历史本质上是一种“重构”的过程。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业内人士而言,自晚清以降,尤其是民国时期开始的那一段历史似乎与1987年之后专业恢复重建到今天社会工作的当代建设相对独立。这两个时期跨越近40年的时空,无论是概念还是实践,都已经有了差异,当我们根植于今天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和书写那一段历史或者企图建立一种“沟通”时,一些核心概念必须界定清楚,以规避片面要求合乎所谓的“专业性”而破坏历史“还原”的完整性。
(一)关于“社会工作”和“实务”的界定
首先,要探讨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必然要考虑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演进。而这主要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相关。从最初民国时期主要专业文献来看,关于社会工作的定义实际上来自西方。比如言心哲在《现代社会事业》一书中主要归纳了桂因、霍尔伯等五个定义,认为“社会事业①注:当时对“social work”一词汉译的一种。是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办理各种社会救济事业,以免除个人当前的痛苦及解决社会当前的问题,消极地减少各种社会病态。同时,注意社会生活的改进,积极地预防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其主要目标在于调整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共同关系,增进大众的福利(言心哲,2012)。”而1983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定义则是这样的:“社会工作是帮助个人、群体或社区的专业活动,这种活动能够提升或者复原社会功能的能力,并能为上述主体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社会环境(扎斯特罗,2005)。”对比二者,民国时期的言心哲概括的定义相对宽泛,而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的界定则更注重职业性和专业性。联系到1930年以前,社会服务以及对有需求的人给予经济帮助,基本上由教会和志愿机构提供的历史背景,可见,对社会工作界定的宽泛性显然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
其次,社会工作概念的界定还必须考虑本土历史的特殊性。比如,如何界定在民国时期影响广泛的“乡村建设运动”和从“苏区”、“陕甘宁边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政工作”的“专业性”,就涉及到一种“历史特殊性”的问题。从言心哲的定义来看,积极致力于拯救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无疑应该属于社会工作,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社区工作”的范畴,但从当时发起人和推行者的主体身份以及推行的主要理念和方法而言,与单纯的“社会救济”又不尽一致;肇始于“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也同样由于其较强的政治动员特征和“官办”色彩,似乎与西方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相对独立特征以及专业理念方法不相契合。但纵观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述两个部分所占地位又相当重要,不可或缺,所以这就必须使概念的界定具有本土适用性。基于这样一种考量,本文中对社会工作的界定采取一种“流动”的观点,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参照同时期国外社会工作的发展,兼顾本土特殊性,采取“从宽”的原则。
“实务”是相对于理论而言的,是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和工作技巧得以应用,专业服务得以开展的过程。但在历史分析中,实务分析必须配合上面的社会工作概念的界定,既要考虑专业的视角,也要考虑时代的局限性。社会工作实务兴起与发展的历史梳理可以有多个维度,比如:可以从工作领域进行划分,按照儿童、青少年、妇女、医院、社区等;也可以按照方法来整理,比如个案、小组、社区以及社会行政等。但必须要考虑的是,在社会工作引入本土的诸阶段中,其内涵和外延也是不断发展的。
(二)“外来的”和“本土化”
源自西方的知识体系引入本土,可能存在或者产生一种“惯性思维”,那就是对所谓“专业性”的坚持。这种坚持是保持一个专业和一个职业独立价值的重要前提,但同时也会造成在处理本土问题时的尴尬以及对本土要素的排斥和忽视。在专业恢复以来的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推展过程中,西方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在保持专业独立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工作嵌入民政系统形成了理念和工作思路上的差异与障碍。这就告诉我们,在历史文献整理中,在保持“外来的”专业性的同时,要将“本土的”传统社会福利和社会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实务兴起与发展的交互性考虑在内,在定位“乡村建设运动”和“民政工作”问题上看到本土要素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自民国以来,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务践行者所进行的“本土化”的努力。
二、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引入和探索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早期,社会福利变得越发专业化。在此之前,这种服务一般由来自中高经济群体的有良好意图但缺乏训练的志愿者(做好事的人)来提供。在那个时候,受过较正式训练的人已开始受雇于某些职位,同时,也存在着在咨询服务中发展治疗技术和方法的兴趣的增长。(扎斯特罗,2005)”而与之相对应,民国时期本土的社会福利转型也已经开始,在新型福利制度开始引入的同时,社会工作实务也随之引入并得到了本土的回应。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的引入和发展有四条主线。
(一)西方传教士和传教组织在华的社会服务
关于西方传教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定位,实际上大致是一种二分的看法:一方面这是一种带有明显殖民和渗透性质的活动属于列强入侵的固有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不可避免的侵略性和破坏性;一方面这些外来的力量确实为相对传统落后的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理念、知识和技术,并且扎扎实实开展了一些社会事工。至少在早起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先驱者步济时看来,“社会服务”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或者根本途径之一。而作为非常成功的典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部分是由于儒教的定位和中国的急切需要,部分由于青年会本身的传统,从一开始中国青年会奠基人来会理实践着‘我们不是来传教,而是来服务’的原则。(邢军,2006)”对于传教活动来说,“世俗事工”也就是所谓的带有慈善救助和社会改良特征的社会服务,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这种服务本身就是教会的信仰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社会福音”,本身就是教会功能外显的方式;第二,救济、慈善服务和带有科学普及的教会事工,更有利于改变中国人的传统和惯常思维,有利于教会信仰的普及。
西方传教士和教会传教组织的社会服务至少包括公共卫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体育活动、公共演讲和兴办宿舍等。抛开传教色彩,教会社会服务主要集中在慈善救助和社会改良两个层面。在慈善救助中具一定专业色彩的是各慈善机构开展的集“救、养、教”为一体的针对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慈善救助活动。与本土传统慈善事业相比,源自西方教会的慈善机构重救济,但更重教养,尤其注重救助对象在机构的知识和技术训练。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列举了上海圣母院育婴堂的案例,“要送进圣母院幼稚园教养一年,然后再送到圣母院孤儿院那里。从这时起,凡是女孩子就要学习刺绣、做花边、编织、缝纫等劳动,并负责勤杂事务;男孩子要学习印刷、修琴、画圣像、木工、铁工和其他杂工,同时对他们进行宗教灌输和识字教育。(顾长声,2013)”与之相对应,更专业性的案例来自教会医院的代表——北平协和医学院社会事业部的社会服务:“中国有病院社会服务,当以北平协和医学院为始。该院于1921年在所属病院内设立社会事业部,……社会事业部底职务,正如欧美各国同类机关底一样,是从病人底经济的或社会的方面搜出病底原因来,加以考察与诊断,施以社会的治疗,以与医生和护士所施的医药治疗相为辅助。(吴铎,2014)”
社会改良方面,教会的社会事工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改造上,这既是西方人基于对中国社会问题判断的一种回应,实际上也是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之一。基督教青年会在很多城市开展了世俗性事工,包括公共卫生运动、禁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体育活动、公共演讲和兴办宿舍等,直接推动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彭秀良,2010)。在青年会发起的社会改革中,劳工问题一直是重点,曾经一度得到盛赞的是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模范村”的浦东住房项目很具有代表性。这是一个为工人家庭建造清洁住房的实验……到1929年,已有24个含有起居室、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每个房子的月租金是3元至4元……为社区家庭提供社会、教育和娱乐服务,包括125个工人子女的日校和50名成人工人的夜校。由工人组织的社区自治团体经营着他们的共同利益和计划,包括戏剧和音乐俱乐部,体育游戏、宗教集会、演讲、公共教育课程、健康活动、种牛痘和健康医疗检查①《模型乡村活动》(the model village activities),未具名打印稿,1928年2月21日,青年会档案(邢军,2006)。这一早期的“廉租房”行动是将西方“俱乐部”式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教育工作理念引入到本土的直接尝试,理论意义大于其实际社会效应,尤其是体现在社区工作的专业性层面,更是如此。
(二)本土社会精英推进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
郑大华(2006)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在西方社会建设思想引领和启发下,由本土社会精英发起的带有社区发展色彩的社会改良运动。尤其是具备西方基督教青年会背景的晏阳初发起的“平民教育”,已经有着比较科学的“诊断”“计划”和“介入”的色彩。“平教会实验区成立后,经许多专家研究,认定中国社会的病根在于‘愚贫、弱、私’。‘除文盲’只能救‘愚’,此外,还要用‘生计教育’来救‘穷’,用‘卫生教育’来救‘弱’;用‘公民教育’来救‘私’。这就所谓‘四大教育’。这四种教育要用三种方式来推动,即所谓‘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何适,1948)尽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这种工作方式其所渗透出来的“西方式”科学分析和社区策划的要素,足以使其成为中国本土社区工作实务的开端。
(三)高校领办的带有试验性质的实务探索
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高校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浓墨重彩地去书写。晚清以降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特殊复杂的使命,扮演着超越高校本身的重要角色。从社会工作兴起角度上来讲,作为专业,社会工作进入高校过程中,传教士和西方知识分子是当时绝大多数社会学系(含社会工作课程)的创办者,比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等,功不可没。同时中外社会精英云集的高校,也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救亡图存,进行了一些带有实验性质的实务探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河实验区”。清河实验区始建于1936年,服务范围包括清河镇及其周边的40个村庄。其社会改良活动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经济上与华洋义赈会合作开展了五项以增强农民自立能力为目的的实验活动;二是社会服务方面,开办了幼稚园、幼女班、女子手工班、母亲会、家政训练班等,办起了图书馆和阅报室;三是在改进农村卫生上,开办了医院,推行新式助产,搞好环境卫生,等等,重点是培训农民参加儿童福利和妇女保健工作(王贺宸,1936)。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相比,尽管也存在理想性,但燕京大学的清河社会实验区直接由具备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相关知识的大学师生来运作,在专业性上是一个很好的突破,这也是高校领办社会工作实务的优势之一。
(四)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为主导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的职业化
民国后期,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以“社会部”为首,开始在官办和官民合办福利机构中推进社会工作,并开始尝试探索社会工作实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体制建设。以儿童福利为例,按照1948年《社会工作通讯》第五卷第二期熊芷女士撰写的《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报告》一文所交代的,“社会部为倡导推进社区儿童福利服务工作,实验研究技术方法,期以所得,辅导各地普遍推进(原文模糊不清),全国儿童福利事业之发展与改进起见,除在战时陪都北碚设立儿童福利实验区外,还都后复增设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熊芷,1948)。并且该文还列举了一些专业儿童服务手法,已经包括个案、儿童小组、亲职辅导和家庭辅导等项目,较之前我们提到的西方传教士社会救济机构所谓的“救养教”一体的社会福利机构服务显然更为科学和专业。
尽管蒋旨昂在《社会工作导论》一书中抱怨“深感社会工作之意义,尚未获得国学者一致的了解”(蒋旨昂,2012),但是从当时“社会部”成立后的一些举措来看,社会工作却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并且也开始在政府的有意引导下从特定领域的实务探索,走向一种职业化的发展趋势。1945年第7期社会部公报发布的“考试院公告”《特种考试社会工作人员考试规则》中已经开始将社会工作资格认证分成“甲级社会工作人员”和“乙级社会工作人员”两种。而在社会部直属的南京伤残重建院的《组织规程》中明确规定“(在职人员)必须掌理个案调查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及随访并心理测验精神病社会工作等事项”。从当时《社会工作通讯》杂志所显示的这样一系列的证据表明,政府在推进社会工作实务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态度和计划,也做了较为系统的尝试。
三、源自“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
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对应,由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民政工作”,包括优抚安置、赈灾移民、民众团体、妇女儿童、医疗卫生和宗教工作等,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政工作是一脉相承的,属于本土社会工作的范畴。民政工作脱胎于1931年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内务部”工作职能;之后历经“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陕北省苏维埃政权内务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卢谋华(1991)在《中国社会工作》一书中认为:“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中,长期存在着专业和非专业社会工作同时存在的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两种性质的专业社会工作和非专业的实际社会工作并存。在建国以后,是一种性质不同形式的专业社会工作和非专业的实际社会工作并存。”他这里所谓的“非专业的实际社会工作”指的就是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期开始,延续至今的“民政工作”。在王思斌看来,非专业性指的是“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不是一门职业,而且实际社会工作者也不是以专业身份来开展工作的,但认为“这种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是有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并且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对帮扶困难群众和缓解社会问题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王思斌,2010)。但同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转型,这样一种源自“全能政府”理念的民政工作很显然已经不适应新的工作形势。但是,也恰恰是这样一种理性认知,由民政部牵头,推动和促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和重建,拉开了社会工作第二次引入和发展的序幕。
四、专业恢复至今社会工作实务的兴起与职业化进程加速
在回顾社会工作专业恢复以来的这段时期,学界更多看到了教育先行的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特征,看到了高校的作用,也看到了上海深圳等先行试验区的贡献,民政部“政府”身份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根据王婴(2009)在《“马甸会议”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的回顾,至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民政部就开始思考专业化发展的问题,在组织了香港、美国和加拿大、北欧三次主要的外部考察之后,1987年12月,由民政部人事教育司牵头召开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论证会,制定了专业恢复的基调和专业教育后续发展的规划。可以说没有这次会议,后续所谓“教育先行”以及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实务的格局很难预期。①当然,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是以社会学专业重建为背景和前提的,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尤其是雷洁琼教授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按照不同主体推动的角度出发,专业恢复以来社会工作实务的兴起与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两条路径。
(一)民政部主导下民政系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
这一路径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外考察开始,到上海等地开始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实务探索为止,代表了社会工作实务的恢复和再次兴起。这一时期的发展包含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应急性的专业人才和师资队伍培养,比如1984年到2002年,民政部在民政系统做了多次专业人才培训,同时也和高校合作,大力培育专业师资和人才;第二个分支是上海等地开始的实务领域的探索,重点代表是上海,是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开始的。在这一试点过程中,上海市司法行政部门率先进行了理念和服务创新,尝试构建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政府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在笔者看来,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上海的动作太早太快,导致这一探索实际上与整体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显得稍有脱节。
第二个阶段是一条相对常规的实务发展路线,指的是从2000年民政部颁布《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开始,走的是一条经由基层社区建设逐步引入社会工作的发展思路,直到2007年深圳试点全面发力,率先全面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社区建设是民政系统的主要业务范围,因此这一条路线有效推动了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加速。2006年7月20日,《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暂行办法》出台,正式拉开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帷幕。这一阶段的高潮发生则是广州市在发展社会工作服务中大力引进港台经验,从局部试点到全面开花,系统推进“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过程。2009年9月28日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学习借鉴香港先进经验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先行先试的意见》,拉开了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来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帷幕。按照曾永辉在《广州蓝皮书2015》一书中提供的数据,广州市财政在购买社工服务费用方面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劲头,到2014年,达到了3.37亿元,约占市财政总支出的5%(曾永辉,2014)。以街道和社区为平台,广州市社会工作凭借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的全面开花,其工作实务已经涵盖了儿童、青少年、老年、妇女、禁毒、学校、企业、医院等几乎所有常见领域。
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是2012年11月14日,民政部、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在制度层面明确了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这一制度的出台,为各地借鉴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将社会工作纳入政府公共福利和服务供给奠定了基础,因而宣告长达30余年的探索落下帷幕,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全面铺开。
(二)专业恢复之后高等教育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实务发展
这条路径既可以作为第一条路径的辅助线,同时也有其独立发展的内在逻辑。从1988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被批准首批试办该专业起,到2014年4月底,全国已经有298个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到2014年5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MSW授权点达到了104所(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2014),近30年的发展,可谓成绩斐然。从教育角度来梳理专业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工作实务的进展,抛开实务研究不谈,主要可以分为专业实习实践和通过领办社工机构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两部分。从第一部分来讲,作为以实务为灵魂的一门专业而言,专业恢复重建之后的课程建设中实习实践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环。从调查来看,社会工作学生专业实习去向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社区居委会、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学校/医院/新闻媒体等(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2014)。而对于社会工作实务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来说,高校开办社会工作机构才使社会工作实务有了本质性进展的标志。根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截止到2014年,国内高等院校开办社会服务机构的比例为42.9%。关于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林顺利(2014)在《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能力建设的五个基本问题》中曾经谈到“从本土社会工作专业资源高度集中在教育领域的现实来看,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是必然的选择,也必须在特定阶段加以扶持和推广,但从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一模式是值得商榷的。”客观评价,在社会工作专业重建以来的社会工作实务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高校所起的作用是综合的,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提供着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高校学者大力引入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实务知识与技巧,并尝试本土化;更为重要的是,在职业化不足的现实国情基础上,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居中策应”,是社会工作实务专业化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工作逐渐走向社会化和市场化一个重要过渡。
在《略论本土社会工作历史的整合》一文中,林顺利认为:“自1987年社会工作专业在高教系统恢复以来,无论是本土教材还是学术文献,似乎都急于引进西方当代的社会工作知识和经验,而有意无意地疏忽了社会工作在19世纪初期到建国前的那一段历史”。社会工作的两次引入过程,包括在这二者之间的“民政工作”,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割裂的部分,社会工作实务的兴起和发展,是社会需求的客观反映,有其内在的历史脉络。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H·扎斯特罗著,2005,《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第七版)》,孙唐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美]李怀印著,2013,《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3][美]邢军著,2006,《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赵晓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顾长声,201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何适,1948,《晏阳初成功史》,《时事新闻》第6期。
[6]蒋旨昂,2012,《社会工作导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7]林顺利,2014,《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能力建设的五个基本问题》,《社会工作》第3期。
[8]卢谋华,1991,《中国社会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9]彭秀良,2010,《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0]社会部,1948,《社会部南京伤残重建院组织规程》。
[11]王贺宸,1936,《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社会学界》第9期。
[12]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主编,2014,《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3]王思斌,2010,《社会工作本土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4]王婴,2009,《“马甸会议”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工作》第3期。
[15]吴铎,2014,《北京协医社会事业部个案底分析》,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从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6]熊芷,1948,《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报告》,《社会工作通讯》第2期。
[17]言心哲,2012,《现代社会事业》,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8]郑大华,2006,《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第2期。
[19]曾永辉,2014,《广州市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现状与对策研究》,载张强、陈怡霓、杨秦主编:《广州蓝皮书:2014年中国广州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辑/陈建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实务研究”(15CSH067),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进展研究”(HB14SH012)。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6)02-0018-08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6.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