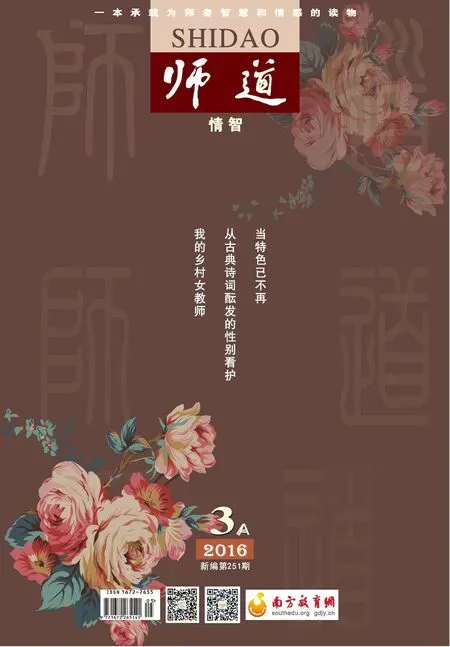从古典诗词酝发的性别看护
北 熹
从古典诗词酝发的性别看护
北熹

儿童性别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同伴交流、群体嬉戏、阅读学习、社会传播等都会从各个侧面提供点滴信息和教养,渗透、雕琢、催动性别意识的生长和成熟。作为一生人格养成的重要构成部分,性别意识是自我认知、自我接纳和自我开拓的精神基石,是社会角色的出发点。出色的性别反省力常常是在接受与怀疑、斗争与疏离,唤起与确认等多重“扰叨”中趋于灵敏的,它不单指向对性别特征认知的确立,更意味着走向内在的精神生活,拥抱更趋完整强健的身心。
有人抱持西方女性觉醒的社会运动观念,认为中国并没有丰富的性别文化和女性自身的精神经验留存,其实是粗糙的印象,虽可设想在漫长的农业形态下,女性若拥有与男性同样的话语权,中华典籍里将会呈现怎样令人绝倒的芳菲,但仍旧不应一笔抹杀以男性为写作主体的古典诗作在性别经验上的耕耘成果,而且毕竟他们不是凭空创作了那样的两性故事,只要有文学的细心,也可以在里面看到女性身心的舞蹈。更加不容错过的是,一些“雌雄共体”的诗心,以人之同情、爱情、超情,施布了一方可居可游的处所,让千载之下,我们可以带着学生到那里,领会他们通过文字展开的种种有关性别的外求与内证。本真的存在与超越的存在,是性别意识教学省思中两个内涵集,也就是说两性既可完成自身固有的使命,更要觅得超越和圆通,方不负历史中男男女女以身心的操劳所呈报之不倦的开示。
显·身体
在我们的传统诗作中,有大量关于身体的精彩摹写,诗人不动辄视身体为累赘、牵绊以及反德的存在,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论是形而上的哲学传统,还是重视义理阐述的文论传统,身体在真实环境和文本环境都在边缘化的事实愈演愈烈,西方的笛卡尔更是以“我思故我在”斩钉截铁地将身体完全排除在第一性之外,这是人类身体与心灵聚讼对峙的必经之路,可悲的是,在身体与心灵的和谈远远没有到来之前,无视、掩没、宰制、残害身体的事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幸在诗歌中,男女身体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出场,接受目光的洗沐和加冕。无论是“竹杖芒鞋轻胜马”对男性身体任真的自得,还是“彩索身轻长趁燕”对女性身体韵致的赞美,都不失为人类身体社会学里最令人慰藉的存在。特别是那些顾盼有情的少女,总是以飞跃入眼帘的出场方式,予人不尽惊喜,在这样的美好面前,古板的卫道者亦不会一点都无动于衷吧。而在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里,身体与精灵亦是交融无痕,有质有实。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无视或刻意消解文本中身体之存在和反应,并进行一套逃避的解说,是对身心的不真诚,也是对人性的阉割。
不过,任何身体的出场都不是单独的出场,它势必终究要带着强大的情力,或被它侵占,或被裹挟,身体其实并不能独自筹划自身。情爱,作为强大的性意识,可以形塑身体,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一个性别与另一个性别建立了某种深刻的因缘关联,其意蕴的透露是要表现于身体的,文本传授要坦诚面向这个生存的现实。如高中人教版必修课《邶风·静女》之“搔首踟蹰”,身体是情感自然的随动,可与《周南·关雎》辗转之态同观,两者皆为不能自已之状,真切生动,无一浮饰。
在古典诗歌中,情爱是一种缓慢的精神活动,与现代多见之速生速朽的爱情相比,古典的情境总是显得徘徊、持久。慢的历史中收获的却是关系的纵深,而浮光掠影的快速消费自是不知道骨肉般的情感为何物。今人多劝慢生活,慢自然会意味着对生活项目做减法,而在“必修”项目上做加法,反复体验、细腻感受——“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添就的便是性情的深蕴,而这必定会导致记忆的深牢——“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其“无终性”意味着存思者愿意在对方身上永久寄放他自己。而渴盼、求不得、寤寐思服不一定会令生命枯焦,也可能是滋养——
泽·情爱
辛弃疾之“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在他一贯的“壮士悲歌未彻”的咏叹调里别具风华,正是在永恒的对异性的渴盼中,不断迂回体会自己的襟怀,从而愈发深沉含韵。在古诗词史上,因为真诚传达出对另一种性别深切的期待,而赢得历史上无数女性读者特别的爱戴者,辛弃疾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曾闻有学生大胆提问,这里面有没有诗人的性饥渴,不知那位老师如何作答,我的回答是,肯定有,但是他并不局限于此——能解他千古之愁,她势必也有同样的格局能操持这深愁,她虽面容安详和美,心却能与他一同纵横捭阖,她不是一个影子,只是简单地帮他抚慰拭泪,她亦能在“谁共我,醉明月”里同醉人世,牧放性情之深壑奇峰。辛弃疾一再把对异性的渴求编织进严谨的格律里,在一次次默默的苦楚中,一次次叠加女性的形象,这个女性精神的总和在迅速地变大,最后在“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获得某种清零,轻轻便便,仿佛她从未复杂过,从未心酸过,只是美,且这种美能与时空发生一场轻盈的奇遇,从此便惊艳后世。
在辛弃疾的文本里,他以自身出发歌讴女性,女性作为他者而存在,这是跨性别的审视,但丝毫不见卑劣的玩弄、浅薄的解读,令人相信,如果两性之幸福来临,他一定以最谦卑和敬重的态度来领受。这种真挚的情爱实践在杜甫诗里得到最强的注脚,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选取了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诗人以妻子之眼写情,以心换心,体贴之状动人心扉。“清辉玉臂寒”五字最得女性之神韵,深知双臂之清寒,男子心地必是极为温厚。玉臂易寒,其知冷暖如是,是愿意把心托付出去,放心把心托付出去,他伤心高兴,却也第一时间感知对方的伤心高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紧接着的几乎与之同时的便是“却看妻子愁何在”!我们在教学中强调国难、民难,却常无视最迫切的伦理教育,一位举国上下皆公认为最伟大的诗人,他身上背负了一整个民族的苦难,却也不会被它压弯脊梁,他或许在变得伟大的同时在变得抽象,而失去了日常的和颜,若学生们能以父亲的角色审视他,以母亲看父亲的角色审视他,或者以自己性别的角色思忖他,那肯定会获得最深切的感动。若见得诗人在情爱的唱叹中展开自身,亦是开了一个“私”的视域,却丝毫无碍于“公”在心中的呼啸。因公而伟大,因私而丰满。
高中语文教材(苏教版)《江城子》(十年生死)笔墨亦真亦幻,却在情爱的纯粹上兼融为一。“小轩窗,正梳妆”,语虽简至,却是淑女品格的最佳摹写,又在朴素纯然的文字流转中,与诗人自身之君子品格相互辉映,使得这份爱而愈敬,敬而愈爱的夫妻之情显得格外坚贞不破,而竟又天人永隔,引为长泪纵横。记忆的影像越是和合谐美,生命的孤途越是大恸难忍。两性性情之醇美不自觉地流露,诗人安静地叙述了永诀的沧桑,——那样的真淑女,真君子,或受命运无情掏挖,却也永远无惧时间的攘夺,而在诗歌的长河中永远互相欣羡,被阅读和理解者铭记为恒久的精神造像。
《鹊桥仙》也是人教版的著名篇目,以“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惊世之言使得鹊桥之题别与以往情伤之叹而卓然挺立,既是对别离之爱的真诚慰藉,也是对世俗麻木之爱的一剂警醒,与其长久沉沦其间,不如短暂赏得真味,亦是对人世的珍视。
叶嘉莹曾记老师顾随评诗,他说“黄山谷不好说女性,工部、退之、山谷,一系统;义山、韩偓便不然,不但女性写得好,其诗的精神也近女性,杜、韩、黄便适当其反,是男性的。美的花,山谷也不以美女比,而比美男子,由此归纳可考察其生活范围”,令人读来莞尔,似比豪放、婉约之说更加直白。由此议发,义山的诗若是抽去女性精神之蕴藉,那光彩岂止折半?《无题》(相见时难)与《锦瑟》两首分别见于人教版初高中教材,教学时多想帮学生理清线索,但作者诗作本来就隐晦难懂,后世很多诠释都有牵强,如一味重视逻辑性的推理,即知因果而弃情味,于诗教当属大失。若是将叔原、少游、耆卿、美成、君特、容若等人情爱之作择佳者并观,便知他们虽在性别审美的向度上姿态各异,但记惦、回味着两性盛景时虽苦闷而已有所出,知道那只是回不去的美梦,以泪遥祭,以笔遥点。义山却似思无他出,他的“滞留”让他笔下境界迭生,他格外的缠绵和代入女性情怀的双视角,使其绪乱不排,意繁难解,所以落墨点笔,情又再起,“当时”“已惘然”,“追忆”更成伤,他是何时何地都不想要和时光和解似的。在精神迷狂地带,“蚕丝”“蜡灰”“月、珠、泪”等丰富意象与两性之精神征徽交错盘起,入愈深,性愈迷。诗作是作者生活里全部的失败,又是他全部的胜利——他的高明在于,竟然将繁复和剔透两种难以统一的特质都包裹在他给出的意象里,你在诵读时觉得繁复成全了他的婉曲,掩卷,又发现剔透收留了他与伊人全部的郁结。
意象,是诗人心灵框架对外在环境的摄入、裁切和品赏,它是物景,更是心景,经过历代无数绣口的吞翕,已成为民族心灵共同的“程式”。面对这些“高凝缩”的意象,要让学生们得其艺术灌注,需要适当“解套”,回到人和自然的简单关系,看到情是如何“移入”景的,“泡开”这些高度符号化的场景、物象,才能再次收获感动。性别意象的审美或者意象的性别审美,始终离不开自然的托举——
寄·自然
古典文本中性别意象的审美,总有着朴素纯真的自然的朝向,特别是代表女性之蛾眉、粉泪,鬓云、裙带、佩环,几乎都会在自然中出场,或以自然之物比拟,即便是室内空间,或限于床笫,也会以屏山、绣扇等有自然景色展现的艺术品来衬托佳人,避免因空间的窄小私密而带上促狭的气息。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脸之美以花比,“人人道,柳腰身”,腰身之美以树比;“唤起佳人,不顾清寒与攀摘”,佳人的清丽定格在梅景的清寒中更惹人怜,“有暗香盈袖”,花香之缭绕令挽袖更具妙曼;“黛娥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自然有情,芳心独孤,“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自然万古,倩影倏忽……而其中最壮阔的,莫过于山水的比附和烘托——“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简直是将山水与美好女性奇幻杂糅,而“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山水亦有女性妩媚的眉眼,可谓“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宗炳)。山水可为我助添美色,我亦清越非俗,可拟作山水之眉眼。
女性审美与自然审美有独立向度的“各美其美”,更有互相衬托的“美人之美”。至人与自然之“美美与共”,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更见天人谐和,此时性别会悄悄隐遁,只见人性的成色纯然无晦。
在男性的意象中,男性力量和男性困境同样饱蘸山水情势。山水哪有情?本来也是人情所化的结果,但人格化了的山水却能以人所无法具备的浑大与顺生,或济男性以力,或辅以仁,或抚以安。无论是激越,还是顿挫,男性诗人都在自然山水里找到寄情之所在。
“回首射雕处,千里暮云平”,遥遥之暮云,更见将军之豪阔,“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龙蛇”以云烟比,更见书家之酣畅;“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日脚光荡,其明丽若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江山纵横,其凄苦若是。这是男性朝向自然的必然表达,是作为自然之子在母亲面前毫无掩饰地宣泄娇肆、得意、乖张、苦闷和懊恼,是力的冲撞,是情义的跌宕,这无疑是相对于女性意象更加泼辣和更加自由的姿态。
若说“和羞走”与“画远山”等女性意象在自然里更多是一种蓄意,那么“马蹄催”与“拍栏杆”等男性意象则有一种不愿拘束的生命原力,有意思的是,当这种生命力遭受钳制或冰冻后,都不由自主地,兜转至蓄意来。而女性但凡也能“兴尽晚回舟”,竟悠然招展出别样的快然!所以,人们一见那些一点儿都不怕颠覆自己性别的诗作,总是过目不忘,愿意珍存里面人性的丰富。细腻的心灵,可以在诗词的性别审美中遐游,出入无碍,往复有滋味,超越刚柔的粗暴二分。性别意识,非取熟视麻木,又不必念兹在兹,未若让它坐落于分内,并让精神按其禀赋的本质发展升华。
古典心灵,招引来自然,从此,若不言它,仿佛它在。“甚时跃马归来,认得迎门轻笑”是阳者越过千山万水,阴者越过平庸琐碎后甚为宝贵的照面,两性在对方的世界里映射出最美的容颜,此时,两免跋涉,良愿合璧,引为圆满。
曾问学生,他的烽火和她的炉火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学生若有所思,这样的问题难以回答,但是好的问题可以引发人长久的思考。对学生两性意识的萌芽和拔节的看护放在古典文本中来进行,先验般别有一番珍重。这样的问题,没有对性别的遮遮掩掩,亦不会媚俗无聊,它指向词赋里横亘着的那个自然。自然之深广,可至男女皆能从中找到自身特性的对应。这个庞大者既让人无法进越,又让人们远瞩的视线有寄存之地,它既是令人伤心,又令人慰藉,并最终将意绪又指向人自身。海德格尔曾有“为什么世内存者首先在‘自然’中被发现?”之问,我想正是因为它诱导人们发现自己,净化自己,在烽火和炉火之间,苦难并没有消解,但是自然帮助人们感悟情感,思考人生,审美生活。在自然的幽敻里,无人共说,却可偶及天人之高远,落想于斯,但永秋遥夜可渡。
人子有情,诗歌并不可尽述;天道有理,文字并不能清算。唯阴阳演化不休,男女淹留,其蔓不绝。身体不是无关紧要,性灵也非虚空无凭。教书育人,正是看护人本、养性开正、诚赞天地也。
本栏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