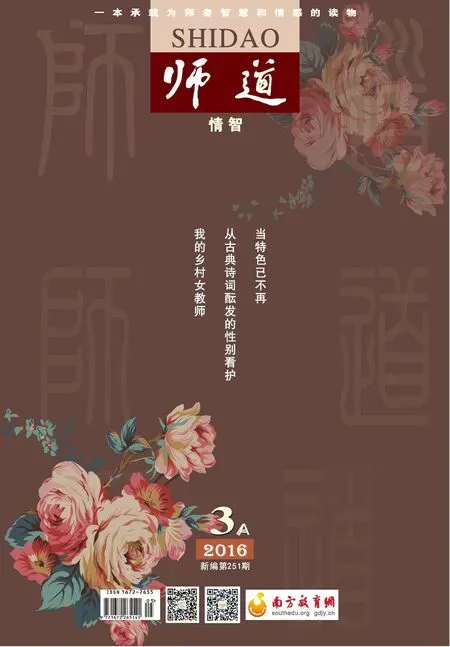我的第一位女老师
王京霞
我的第一位女老师
王京霞
去年妇女节的前几天,人民网教育版发表两会调查指出:中小学的校园几乎成了女老师的天下。而半个世纪之前,在我的家乡沂蒙山区,女老师是稀缺的,直到上了初中二年级,我才遇到我生命中的第一位女老师——丁老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教育,是朴素的,原始的,率真的。我们村的小学草檐茅舍,桌凳破陋,没有围墙的校园里五个年级总共才六十几位学生,四位老师清一色男的。家长见了老师都恭敬有加,几乎同样地嘱托:“我家的那孩子调皮,野淘,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老师多操心,不听话就打,使劲打,自家孩子,打了没事。”所有学生,不管男的女的,几乎没人不挨过老师的巴掌。我从小胆小听话,为了不挨巴掌,拼命学习,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即使这样,每次看到老师训斥没学好的女同学,暴打调皮的男生,仿佛雷公震怒,都吓得我心里哆嗦,不敢看老师的脸。
1981年那个润湿清新的初秋,我升入初中。在初中校园里我发现了两位女老师,她们穿着洁净得体的衣服,理着短发,亭亭玉立。姐姐告诉我,她们一位是丁老师,一位是刘老师,很少打骂学生。可惜,她们一个也不教我们。我远远望着她们的背影发呆,原来女人也可以当老师啊!那时候生活艰辛,我的母亲辈们总是蓬头垢面,日晒雨淋,在田里劳累,穿着破旧的衣服,天天围着磨台、碾台、锅台转,弯腰驼背,唉声叹气。看着女老师衣着整洁,优雅地抱着书,笔直地走着,我羡慕地想:要是将来我也能当上老师,吃上公家粮,风吹不着,日晒不着,雨淋不着,那该多好啊!
升入初二,刚刚进入新班级,屁股还没有坐稳,就听到有男同学大叫:“那个女老师教咱班数学——”“哪个女老师?”“笨蛋,就是教数学的那个,还有哪个?”同学们在叽叽喳喳地叫嚷。
第一节数学课,我把破旧的课桌擦得干干净净,早早地拿出课本、练习本、笔,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上,挺直了脊梁,端端正正地坐在位子上,等待我生命中的第一位女老师!同桌是一位淘气的男生,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朝前,一会儿往后,伸长了脖子往窗外瞧,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嘻嘻哈哈,闹闹喳喳。
“来了来了来了……”同桌边压低声音喊,一边屁股挨上了凳子。透过门窗,我看到了丁老师:她手里拿着两本书,不急不缓地走来了,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衣,上面印着淡淡的粉紫的丁香花儿,浅灰的西裤,笔直的折痕,更衬出她挺拔的身姿,半高跟的塑料凉鞋是晶白色的。老师登上讲台,把书放在讲桌上,我看到她漆黑的短发,仿佛现在烫过的纹理,妥帖而生动,一双大眼睛满含着笑意。看到同学们窃笑私语,丁老师微笑着说:“怎么?不认识我?今天咱们就认识了,我姓丁……”“我们早就认识你了——”一位胆大的男同学高声喊。全班同学都笑了。丁老师也笑了,接着说:“那就更好了,老相识好说话。咱们以后一起学习数学,同学们只要有不明白、不清楚、不懂、不会的问题,就大胆提问。如果同学们有什么新发现,新想法,也要大胆说出来,发现老师的错误更要积极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说不定将来的陈景润就在咱们班上。”丁老师的声音真好听,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而丁老师的这些要求更是闻所未闻,以前老师都是大声呵斥:“听好了”“记住了”“别废话”……吓得我们噤若寒蝉,丁老师却要求我们多问,发现问题,指出她的错误。我更喜欢她了。
因为很喜欢丁老师,就喜欢上了数学课,数学学得特别好,有好几次,我的数学考满分,甚至连附加题也圆满完成。丁老师经常表扬我。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教师的嘴,就是一个源泉,从那里可以涌出知识的溪流。”我想说,丁老师的嘴不仅是知识的源泉,而且是力量的源泉,她的鼓励让我探究学习的劲头更足了。我每次都赶在丁老师讲课以前就预习好教材,还把练习题也做好。
丁老师不仅在学习上教导鼓励我们,在生活上她也悉心照顾我们。那时候,我是寄宿生,冬天学校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我们住的宿舍是废弃的教室,破旧的平房。为了保暖,把所有的窗户用砖头垒严实,外面涂上泥巴,只有门可以透进光亮。整个宿舍里黑黢黢的。就是这样依然是冷。早上,我们脸盆里准备的洗脸水结了冰,只能砸开冰洗手洗脸。没有手套,没有棉鞋,没有像样的袜子,就是棉衣也是捉襟见肘。大多数同学的手脚都生了冻疮,化了脓,流着血水,从破棉袄里撕出一块棉花粘擦。丁老师常常从家里拿了药粉给我们上药。她还用小布块絮上棉花,做成二十公分长的一对对圆筒,接在棉袄袖上就是一副副暖袖。课间,丁老师把手冻得厉害的同学叫过来,一针一线把暖袖接在棉袄袖上。我是数学科代表,经常去送取作业本。我的手冻得像刚出土的生姜,又红又肿。一次,我又去交作业,丁老师抓住我的手,一边搓着,一边心疼地说:“看把这姑娘冻成什么样了。”老师修长柔滑的手,像春天的暖阳,熨帖温暖。我又感激又不好意思,抽回手就要跑,老师一把抓住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副酱红色暖袖,塞给我说:“把它缝上,就不冻手了。”我接过暖袖,边走边摩挲着,它们又柔软又暖和,颜色和我的棉袄正相配,而且又耐脏。暖袖上还细心地别上了针线。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个冬天,每次我做题想偷懒,或者遇到难题想要放弃的时候,一看到那副暖袖就想起丁老师的笑容,那笑容鼓励我坚持下去。
初三下学期,为了跳出农门,为了给艰难的家庭减轻负担,为了考上中专,为了实现当上老师的梦想,我拼命学习。春天天长,我四点就起床背书,晚上点着蜡烛学习到11点才睡觉。由于严重的睡眠不足,我整天昏昏沉沉,睡也睡不着,醒也醒不来。学习只求时间,不计效率,由此也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一天,丁老师叫住我,盯着我的脸看,心疼地说:“你这孩子,太累了,不能这么拼。离中考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样身体吃不消的。你的知识已经掌握得很扎实了,只要稳稳地完成最后的复习,正常发挥,就一定能考出好成绩。关键是保持好心态,不能过分拼体力。”我点点头,但是回到教室,几个排头的同学你追我赶,我不敢松懈,反而更努力了。终于,我病了,头疼欲裂,嗓子冒火,连唾液也不敢下咽,趴在课桌上抬不起头。那时候,出现这种小毛病总是自己扛过去,从没有想过要回家,或者告诉父母的。家离学校十几里地,没有电话,没有车,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谁去告诉呢?我迷迷糊糊趴在课桌上,上课和下课一个姿势,一种状态。上数学课,丁老师给同学们布置好作业,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准备好的药,倒上水。水凉的过程中,她让我坐到椅子上,给我的头部按摩。我滚烫的额头,感受到老师细滑微凉的手,不轻不重地摁着,太舒服了。几个月来的压力劳苦,几天来的病痛折磨,稚嫩的心灵,想家的孤独一起涌上心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丁老师问:“疼吗?”我哽咽着说:“不疼,一点都不疼。”“那你忍着点。”老师试探着,先是眉心,然后是太阳穴,仔细的,一下一下捏着,我感到病魔被老师柔滑的手一丝丝地抽去,疼痛越来越轻,感觉越来越舒服。老师给我揪了眉心和太阳穴,头已经不那么难受,睁开眼睛,清凉多了。老师给我吃了药,把余下的药放到我手心里,细心嘱咐我怎么服用。那一刻,我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是在心里想: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将来我当了老师,也要像丁老师一样,对待每一位学生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快乐!
那一年我考出了全镇第一的好成绩,可惜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没有能够上中专,而是上了县一中。但是,我当老师的梦想依然热烈。怀揣着自己的梦想,我进入了高中,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位女老师,有的博学而温婉,有的美丽而贤淑,有的活力四射,她们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和激励。但丁老师在我心中的美好从来没有逊色过。她像一轮太阳,照耀着我,激励我前行,最终走上了教师岗位。
如今,我已经当了二十多年老师了。走过青春,在校园里,在课堂上,我只有一个信念:把丁老师浸润给我的母性的仁爱,对知识的探求,对学生的鼓励,传授给我的学生们。
(作者单位:山东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中)
责任编辑黄佳锐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