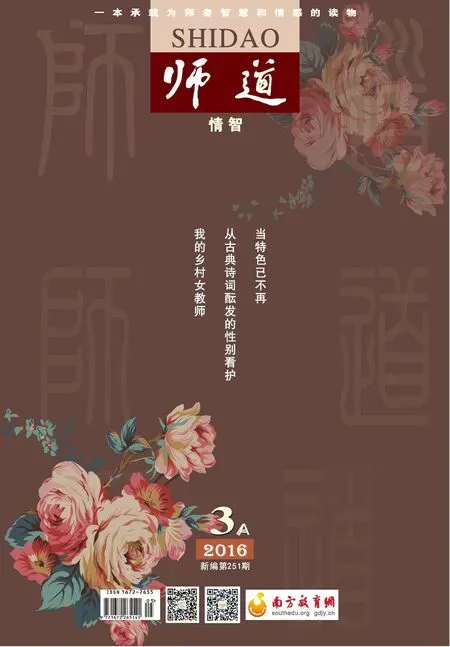我的乡村女教师
周世恩
我的乡村女教师
周世恩

我的小学在山坡上。山坡离我居住的村子,有三华里的路。
小学是名副其实的“小”学,在巴掌大的凤凰山的山坡上,像只蜗牛,还把头缩进壳里。小学叫做走马岭中心小学,据说,三国时的关公曾打马经过这里,走马岭因此得名。那时,断不会想这穷乡僻囊还会与一位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有一些关联是一种荣耀,只会天天抱怨:这学校怎么这么远,每天,要起个大早,走弯弯曲曲的田埂,爬逶迤曲折的山坡,然后才到达这里。
通往学校的路是有些野趣的。春季开学,田埂边便是一望无际的紫云英,红色的花海荡漾,有着一种无法说出的美。青草之中,刚刚冬眠了一冬的水蛇苏醒了,也会窜上田埂,碰上了,难免会尖叫一番,甚至也会失足掉到浅浅的水田中,湿了鞋袜。秋季的时候,叶草枯黄,这时调皮的我会掏出火柴来,放上一把野火,还带着水分的草“哧哧”地燃烧,小伙伴们则在一旁拍手叫好。偶尔,也会碰上一两只野兔子,卯足劲儿追上去,累得气喘吁吁,但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兔子飞一般地从眼前逃脱,窜入洞中或者灌木丛中。
只是我当时不喜欢学习,或者说不知道学习是为什么?只知道玩。我最喜欢的是上体育课,老师基本上是放羊式的管理,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站在教室门外吹响口哨,我们疯了似地跑到操场,毋须站好,等待老师叮嘱一番,便四散开来,去找自己的乐子。春季里的水田是必须去的,田里有很多的窟窿,那是泥鳅和黄鳝藏身的地方,花一点气力,一节体育课,可能会挖上半碗的荤食,上了学,还能让家人打一下牙祭。要么去爬边上的凤凰山,山上野食子不少,鲜嫩的笋,刚长出的月季花的嫩茎,都能成为一群嘴馋的娃娃的零食。语文数学课,就难免死气沉沉,不是抄,就是读,没有几个人喜欢的,但是面对长长的柳条做成的教鞭,我们也不得不正襟危坐。
五年级开学第一天,我们乱哄哄地坐在教室,猜测着今年谁上我们的语文课,她走到了我们的教室。花格子缀着小花的确良衬衣,黑色的土布裤子,平底的白色凉鞋,干净、干练、漂亮,完全没有乡村的土气。一下子,乱哄哄的教室安静了下来,几十个小脑袋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她。她不像别的老师,满脸的严肃,背着手,踱着方步,一副老学究的模样,而是嘴唇微微地翘起,扑闪着那双带着智慧的狡黠的丹凤眼,面带微笑,亲切自然。一群乡村的孩子,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教师,也没有见过这么温和的人。
她上语文课,和别的老师不同。上世纪80年代,乡村的语文教师授课多用方言,而她,却讲一口纯正标准的普通话,刚开始,我们不大习惯,甚至同校的老师还会嘲笑,说她“开洋荤”、“忘了本”,她不顾不管,顶住风言风语,坚持用普通话为我们上课。以前的语文教学是八股式样的上法,先读文章,然后学习生字词,解释词语,然后一句一句串讲,然后记一大堆笔记,她却不要求我们做笔记,上课时还让“放羊式”的让我们自学、讨论。这,也是当时乡村小学教师不敢想象的。她上课亲切、温和,不责骂学生,更不会打学生,教鞭是会备一只,但是,这教鞭多用来指点黑板,偶尔,也会指向我们这群调皮仔,但终究像初中学课本中作家魏巍笔下的蔡芸芝先生一样,即使教鞭高高扬起,也会从你的身边轻轻落下。
记得五年级下学期,江汉平原刚好下了初冬的第一场雪。那天,我们开了新课,是峻青的那篇文章——《第一场雪》,窗外,雪簌簌地下着,不一会,就把整个操场铺成了白色,连教室窗外的雪松上,也推积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她在教室里上着课,而我们却不安分地看着窗外,甚至,坐在窗口的几个同学,干脆将手伸出了破了无数个洞的窗口,用双手接起雪花来。她看见了,没有生气,干脆把课停了下来,眨巴着那双丹凤眼对我们说:“你看,这也是江汉平原上的第一场雪。要不,我们拿着课本,到操场去上这节课吧!”当然,她得到的回应是一阵欢呼雀跃。
这是一堂特殊的语文课。雪花飘扬,迷蒙而美丽,山路蜿蜒,如银带弯曲盘旋,一群孩子,就站在初冬的第一场雪中,一边欣赏着雪景,一边听老师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讲解课文,而这课文,正好是《第一场雪》。成年后,虽然我也成了一名语文教师,虽然我听过无数的试教课、示范课、公开课,虽然我也上过无数的语文课,但是没有哪一节课,让我感觉这么富有诗意,那样真实,那样触动人的心灵,甚至,在相隔小学的20多年里,我还能清晰地背诵峻青《第一场雪》的片段——这是入冬以来,胶东半岛上第一场雪。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儿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冬天的山村,到了夜里就万籁俱寂,只听得雪花簌簌地不断往下落,树木的枯枝被雪压断了,偶尔咯吱一声响。
几十个孩子,在这样漫天飘扬的雪花中,走进了语文的世界。我们觉得语文再也不枯燥无味了,而是充满着快乐、乐趣。她像一位魔术师一样,变换花样为我们上课,有时,会在冬日的阳光下,让我们围坐在一起,吟诵古诗;有时,干脆让我们爬上学校前面的凤凰山,让我们在山林里看春花,听秋叶,寻蝉蜕,寻找写作素材;为了上好“记一次劳动”的习作课,她还带领我们为学校前面的路挑土,铺石。这样贴近实际、丰富有趣的课堂,就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这一群乡村的孩子,他们怎么不会爱上学习呢。
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村子到学校三华里的路,并不远了,以前上学路上勾引我视线的野花野草,让我脚步放慢,从草丛窜出的水蛇、野兔,再也不会让我长时间逗留了。每天清晨起床,心中好像总是装着一件事,那就是赶快到我那巴掌大的“走马小学”,去见我的语文老师。
或许是爱屋及乌,我们渐渐地不怎么讨厌数学了,还爱上了读书。当时,电视里播放着金庸的武侠电视剧,我们喜欢得不得了,她花钱买来了金庸的全套小说,趁热打铁推荐给我们看。她买来了当时很流行但是乡村里根本没有的《儿童文学》杂志,让我们阅读。这一群农村的娃娃,在她的引导之下,回家之后,多数不会漫天地乱跑,而是沉浸在书香之中。而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记得那时,我看完了金庸的全套武侠小说,也迷上了看书。爸爸妈妈给的几毛零花钱,我不会像以前一样,把它花在买饼干和糖上,也不会花在买弹珠和贴纸上,而是骑着自行车,跑到十几里路外镇上的邮局,捧回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儿童文学》,细细品读,若品甘饴。现在想想,我能爱上文学,能坚持写点文章,都是受了她的启蒙和教诲。
上世纪80年代中,港台明星在内地流行。我们这一群少年懵懂的学生,自然也受到了影响。那时的小伙伴,不少人都有一本抄歌的笔记本,上面,工工整整地抄着歌词,描边勾画,还贴着明星的照片贴纸。家境殷实的小伙伴,还买回了录音机、磁带,听学邓丽君、费翔、蔡琴、小虎队的歌曲。放学的路上,课间的走廊,总能听到学生们哼唱流行音乐。我们高兴唱流行歌曲,高兴抄流行歌歌词,可学校并不高兴。校长就在晨会上三番五次教育我们,不要整天哼唱“情呀爱”的,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甚至要求老师搜我们的书包,没收我们的抄歌曲的笔记本。
我们都以为她会听校长的话,会没收我们宝贝的抄歌本,会禁止我们唱那些充斥着“情爱”字眼的流行歌曲,因为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柔弱,性格那么随和。可是,她没有。有一次晨会结束,她径直进了校长办公室,跟校长唇枪舌战。我们躲在窗外,听不到她到底讲了什么,只知道她出来的时候,脸红扑扑的,对着我们,嘴角带着笑。结果,学校没有禁止唱流行歌曲,甚至还允许她在上音乐课时,教唱一些流行歌曲。
她兼职我们的音乐老师。她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师范生,书法、绘画、音乐样样精通。在她来走马小学之前,学校的音乐课基本都是自习。她来了,我们才第一次听到手风琴里蹦出的音符,第一次看到沉睡在办公室里的风琴能流淌出美丽的旋律。在跟校长谈判之后,她公然地教我们流行歌曲,当然,歌词当中是没有情和爱的。那时流行的《黄土高坡》、《鲁冰花》、《我的中国心》等歌曲,都被她一一教过。现在想起,觉得她有中国式的智慧——既没有让校长难堪,下不了台,也保护了我们这些孩子,让我们发自内心的爱好和兴趣能持续下去。
小学毕业前夕,她还教了我们一首爱情歌曲,是邓丽君的那首《美酒加咖啡》。当她把歌词端庄秀丽地抄写在黑板时,我们一眼就看到了当时令我们脸红的两个字——“爱情”,我们有些匪夷所思。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教室里齐刷刷的几十双眼睛,缓缓地对我们说道:“是的,老师今天教你们唱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爱情并不羞耻,其实它很圣洁,有甜蜜,有辛酸,有付出,有美好。若干年后,希望你们能记住这首歌曲,幸福的时候,唱一唱,不高兴的时候,也可以唱一唱。”那一节音乐课,我们出奇地安静,也出奇地认真,一节课,就完整地记住了旋律,完全地记住了歌词。和她上《第一场雪》让我记住了文章一样,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完整地唱出这首歌,完整地记住每一句歌词。
她为什么会在毕业之际教我们唱这首歌,我不得而知。或许,是年轻的她也经历过爱情,品尝过爱情的酸甜苦涩,这首歌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或许,这只是她一次心血来潮,一次狡黠的恶作剧;或许,她是真的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正确地对待爱情。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美酒加咖啡》的旋律中,打开了一扇认识爱情的窗口,从此,我们不会觉得爱情是个龌蹉的字眼,而纯洁从此生根,美好从此发芽。这,或许是她带给我们的——乡村最原始,也是最淳朴的爱情教育课吧。
她教我们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我对她的了解也停留在那两年,当时她已经当了妈妈,两个儿子却是有着小小的残疾,一个高度近视,一个鸡胸。她上课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容,但是偶尔课后见到她,她却并不是那么地快活。她姓谭,名凤鸣,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毕业后,我到离走马小学不远的同心中学念初中,常常想去看她,却不知道找什么理由去看她,结果,当我告别羞涩和内向,找到理由去看她的时候,她却调到别的小学去教书了。像一滴掉进大海里的水,再也找不到了。
一别就是20多年,我时常惦记着她。
(作者单位: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萧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