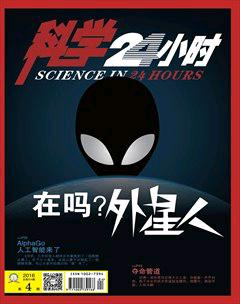在药物抗癌的征途上(上)
王震元
巴里港悲剧的启示
1943年伊始,盟军的油轮和载满军火的舰只,就不断驶往意大利东南部亚德里亚海岸的巴里市,准备为继北非和西西里胜利之后,对意大利的进攻提供支援。至当年12月2日,这座城市因海堤布满了舰只而显得拥挤不堪。控制这一地区的英国指挥官认为,此时纳粹德国在意大利的空军力量已日薄西山,因而为了加速卸货,港口没有实行灯火管制。这种低估对手实力的错误判断,导致了一场悲剧。就在当天晚上,德军迅速组织了105架容克88型轰炸机,对巴里港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轰炸。满载弹药和油料的舰只互相引爆,形成“死亡链条”,巴里港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紧急组织起来的救援队,从冰冷刺骨且满是油污的海水中救起了1000余人。治疗过程中,死亡人数仍不断攀升,更特别的是死者临终前多呈现麻木表情,而幸存者又大多出现眼部剧痛的症状,由此英国军事当局推测,德军很可能投掷了化学炸弹。于是,紧急调来当时正在阿尔及利亚空军指挥所任职的亚历山大中校负责调查。亚历山大是一位受过化学战训练的医务官。他发现伤员的皮肤都接触过化学毒素,死者肺部也都受到了毒气的损伤。而舰船分布草图进一步表明,绝大部分死者都集中在一艘名为“约翰·哈维”号的美国运输船周围。至此,英国港口官员不得不承认:这艘船上载有100吨芥子气!
1925年公布的《日内瓦协议》中虽然有严禁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的规定,但是二战前夕,美国情报部门获悉,德国和日本都在研制化学武器。为此,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8月警告说,美国“将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全面的、迅速的报复”,因此芥子气便被储藏在全球各地的战区弹药库中。
遭巴里港空袭后住院治疗的617名伤员,都是因被海水稀释的芥子气缓慢进入体内而致病的。这就为亚历山大提供了难得的观察机会。他在报告中写道:“这种毒气有较强的全身效应,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芥子气灼伤,其特点是对伤员白细胞的致命破坏……在受侵害的3~4天,体内的淋巴细胞数量大幅度下降,之后白细胞消失。”
北美化学作战部医学处的罗兹主任及时收到了这份报告。作为一位病理学家和血液病专家,罗兹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潜在价值——化学药物或可治疗癌症。
化疗时代的曙光
那时,医生们已经发现白血病和淋巴肿瘤患者的血液中,都会有过多的幼稚白细胞,它们简直充盈了患者的机体。既然持续接触芥子气的人白细胞的数量会不断减少,罗兹很自然地想到,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毒性作用对付它们。他立刻放弃休假,迅速与耶鲁大学的两位药理学家吉尔曼和古德曼进行了沟通,并邀请解剖学家多尔蒂一同攻关。他们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
多尔蒂把这种氮芥子气施用于一只移植了淋巴肿瘤的豚鼠身上。按照预期,由于肿瘤已经深度发展,其体积几乎比豚鼠本身还要大,因而豚鼠的生存期不会超过3周。但是经过两针注射后,豚鼠的肿瘤就明显软化和缩小,最后竟消失了。豚鼠又开始活蹦乱跳了。多尔蒂不禁兴奋地高呼道:“这简直是奇迹!”
但不久后,豚鼠的病情又复发了。再次用药后,豚鼠的肿瘤再次被抑制住了。不过,待豚鼠再一次病情复发时,药物已无能为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后来进行的同类实验中,再未出现过这种生命空前延长的奇迹。但氮芥子气能使病情缓解却是肯定的。
不久,一位45岁的银匠自愿接受研究小组的临床实验。他患的是晚期恶性淋巴肿瘤,放疗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患者面部和颈部的肿结,使他无法咀嚼和吞咽;腋窝处的肿结,使他无法把胳膊垂于体侧;胸部的肿结,更使他的血液不能回流心脏,造成头、颈部肿胀。经过静脉注射药物后,这些症状就逐渐消退。虽然不久后,他因病情复发而死亡,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由于这种药物对恶性淋巴瘤、淋巴肉瘤、慢性白血病等都具有缓解症状的作用,因而仍被美国默克制药公司接受,并使用商业名称——“氮芥”。1949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氮芥”上市。美国癌症学会对“氮芥”的问世作了高度评价:“癌症的化学治疗时代开始了……在巴里港惨案中意外且幸运地发现了一种具有抗癌效果的药剂!”
但是,随着“氮芥”的推广应用,这种药物的不足之处也逐步显现出来,如肿瘤的消退往往是暂时的,会引发人体恶心、呕吐等毒性反应,进一步治疗会产生抗药性等。于是科学家们又开始寻找其他替代方案,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科学家们只能通过大规模检索的方法去寻找。美国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就以1.8万只带有移植或自生恶性肿瘤的老鼠为对象进行药效检索,终于发现了一种可以明显抑制癌细胞生长的肝提取物。按照当时公认的见解,这种提取物中的主要成份是叶酸。于是,研究人员欣慰地认为发现了“新大陆”,美国立达药物实验室在儿科病理学家法柏的指导下,迅速合成了各种叶酸化合物。
“抗代谢”奏凯歌
出乎法柏的意料,迎接他的竟是灾难,而不是胜利!这类药物不仅加速了11例急性白血病患儿的死亡,而且经尸体解剖发现,死者的骨骼中形成了大量新的白细胞。这种与老鼠实验完全矛盾的现象,只有一种解释:当时从肝中提取的不是叶酸,而是叶酸的对抗物。重复鉴定证实了法柏的推断。于是,他进一步设想,如果白血病的细胞被剥夺叶酸,它的生长就应该受到抑制。1948年,法柏选择了一种叶酸对抗物——氨基蝶呤。临床运用中,16个急性白血病患儿中,有10名患儿的病情明显缓解。而1949年研制成功的甲氨蝶呤,更是第一次成功地治愈了一名女性绒膜癌患者。
但是,“氮芥”和氨基蝶呤的发现毕竟纯属偶然,或源自盲目。寻找理想的抗癌药物,应该在揭示癌细胞本质的基础上,在如何抑制其无限增值的科学思想指导下进行。于是,日后将谱写人类药物抗癌史光辉篇章的两位科学家登场了。他们就是美国的希钦斯和埃利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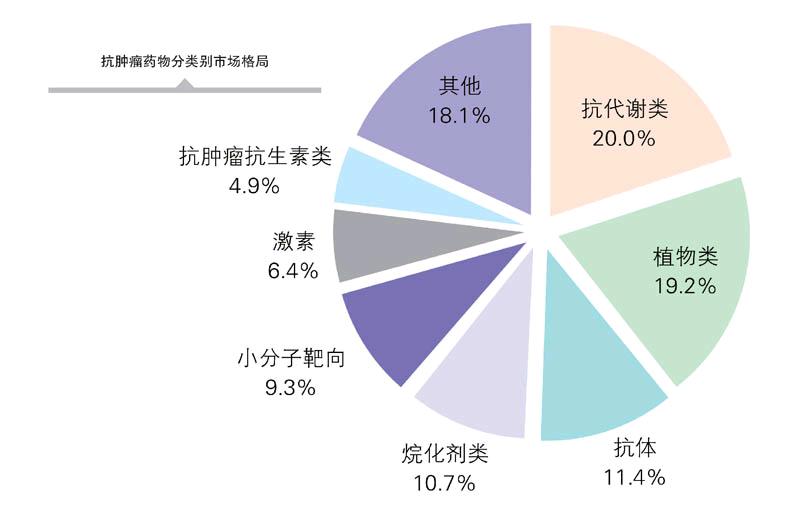
早在1940年前后,科学家们就发现磺胺类药物由于其化学结构——对氨基苯磺酰胺,与叶酸的原料——对氨基苯甲酸十分相似,细菌会不识真伪,“误食”后无法产生叶酸,更不能通过代谢进一步合成细胞中的DNA而繁殖。希钦斯从中受到启发,从1945年起,根据人体正常细胞与癌细胞之间核酸新陈代谢的不同,努力寻找能选择性地阻止癌细胞增长的方法。当时科学家们对核酸代谢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只确认嘌呤和嘧啶这两种物质是整合在核酸中的。后经进一步研究表明,嘌呤碱基(腺嘌呤、鸟嘌呤和次黄嘌呤),从简单的前体合成而来,加入糖(去氧核糖和核糖)之后,形成腺苷和鸟苷,再与磷酸根结合,就转化成了核苷酸。核苷酸参与细胞代谢,并且是DNA和RNA的合成原料。他由此推断,一种药物只要结构与腺嘌呤或鸟嘌呤相似,就有可能防止次黄嘌呤转化为腺苷酸与鸟苷酸,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合成。
埃利昂本是一位女化学家。她15岁那年,由于家族中有长辈死于白血病,促使她决心攻克癌症。1944年,因许多男性科学家都奔赴战场,她有机会应聘进入纽约的威康制药公司,并成为希钦斯的助手。他们的第一次实验突破发生在1948年,那一次,他们将老鼠胚胎的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一起放在试管中,然后加入一种“2,6-二氨基嘌呤”,结果发现癌细胞被摧毁了,正常细胞并无损伤。但令人失望的是,临床试验并不理想。一位17岁的女性白血病患者服用这种药物后,病情虽有好转,但几年后却因旧病复发,继续药物治疗无效而死亡。
埃利昂并不气馁。她继续对100多种嘌呤衍生物进行筛选,终于在1953年找到了“6-巯基嘌呤”,它不仅可使10%~40%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的症状完全缓解,而且对绒毛膜上皮癌和恶性葡萄胎也有显著疗效。“6-巯基嘌呤”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化疗药物。1988年,时年83岁的希钦斯和70岁的埃利昂由于在“抗代谢”药物指导思想下开拓性的成功实践,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然而,科学家们并没有停止继续前进的脚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