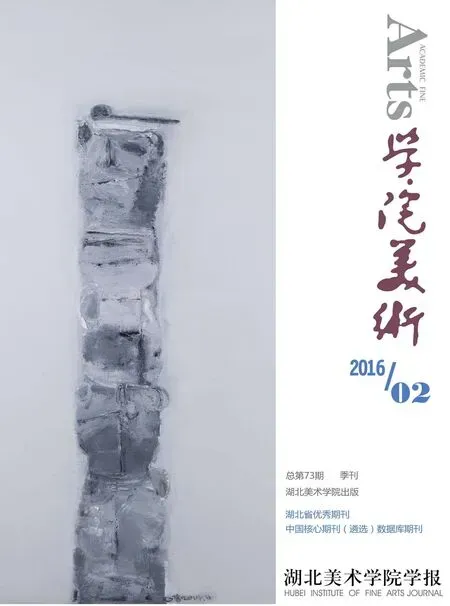当代语境下版画语言的延异性特征
张亚敏
当代语境下版画语言的延异性特征
张亚敏
摘要:版画作为传统而又现代的艺术形式,在当代各种艺术语言与艺术思潮的碰撞中,版画语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延异性特征。这种延异性主要体现在创作者在场与审美语境的延异性、创作者的主体性与审美体验的延异性,以及创作者与欣赏者移情的延异性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延异性特征,构建了当代版画艺术思维和艺术语言,推动了当代版画美学价值的重构。
关键词:版画语言;延异性;审美语境;移情
版画是一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的艺术门类,从初始形态来看,版画仅仅是作为实用性文化传播工具而出现的。随着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陆续上演,版画这种艺术门类始终以自身的艺术实践映射着时代精神。19世纪法国美学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指出:“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1]在中国,由于受到“八五”美术思潮的冲击,多元化的创作倾向和时代精神在当代版画艺术中得以迅速呈现。在当代语境下,版画艺术具有三层含义:一是时间范畴上的当代版画;二是内涵层面上具有当代艺术精神的当代版画;三是具有当代艺术语言的版画。当代版画所体现的“当代性”是版画艺术家置身于当代文化环境,直面当代现实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因此,对于当代版画艺术价值的判断,必须置身于这种当代语境中去考察,理性解读当代版画语言符号的多重特性与语义转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版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分析。当代版画艺术由于其语境的特殊性,多种哲学与文化艺术思潮的渗透融合,已经无法用某种单一的文化维度去指涉其内涵。因此,对当代版画语言的阐释应超越心理、情感、观念上的形式,要基于当代版画艺术历史文化积淀,把当代版画语言符号含混性延伸到多角度的文化空间,强调主体意识,凸显当代版画艺术语言符号的不确定性。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差异性渗透导致理性质疑与价值重构,从而使得版画艺术语言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进而推动版画艺术家去探索当代版画的美学价值以及这种美学价值的文化意义。
一、当代版画语言“在场”的审美语境
“语境”本意是指人们在说话时自身所处的主体状态和客观环境。从狭义上来讲,语境主要是指人在使用某种语言时,由该语言作为母语衍生的生活环境。从广义上来讲,语境是文化的一种特性,是指某种文化产生的特定社会背景,包含该文化产生和存在的所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当我们考察某种艺术现象时,语境对于阐释这种艺术形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英国新批评文艺理论家瑞恰兹认为,“词语意义的功能就是充当一种替代物,使我们能看到词汇的内在含义。它们的这种功能和其它符号的功能一样,只是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方式,是通过它们所在的语境来体现的。”[2]
版画是一种间接性质的绘画艺术,它的艺术呈现过程需要多种物质媒介的多次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创作“在场”的许多审美感觉经验被过滤或者强化,新的意象性符号就此产生。在版画的创作过程中,允许版画进行重复性的印制,由此版画创作具有重复性、复数性的特征。“在场性”是西方古典哲学中的重要状态名词与哲学概念,“在场”主要是指直接面对事物,把感觉经验直接、无遮蔽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中国古典哲学里面,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法国解构主义领袖人物德里达认为:“人所创造的语言符号,其主要的特征,不只是在于它本身内部和它同所表达的对象之间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语言符号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包含着当场显示和未来在不同时空中可能显示的各种特征和功能。正因为语言符号中隐含着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也就是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特征和功能,才使人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差异化运动问题。”[3]
当代版画创作实践中,作者面对各种物质材料进行绘画和印制,其最终得到的“印迹”语言符号与作者“在场”的审美感觉经验之间形成一定的延异性特征。这里的延异性不是解构主义所主张的平面化、碎片化的后现代理论倾向,而是指相对稳定的文化语境与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产生的意义不确定性的延缓,它所指向的是版画艺术语言与语境的永远相互关联、永远不能被确定为表达某种意义的存在状态。“任何欣赏活动都是在时间之域展开,都离不开历史与未来的调节,离不开视野的改换和对作品意义的重新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欣赏活动是调动欣赏者整个审美经验对作品的空白结构加以想象性补充、充实的过程,是一种融注了欣赏者感知、想象、理解、感悟等多种心理因素的一种艺术形象再创造活动。”[4]
当代版画艺术语言的“在场性”与“延异性”之间永远存在巨大的审美差异,直观体悟式的审美感觉经验只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通过版画艺术所诉诸的物质材料间接迂回实现。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认为,“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5]当代版画语言的“延异性”传达的意味是耐人寻味的,它不仅是有意味的形式显现,亦是有意味的感觉状态存在,这成为版画审美语境的价值源泉。当代版画艺术的“延异性”展现了其“印迹”语言符号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这种预先编辑的艺术感觉“信息”的解码决定于版画受众所处的文化语境。当代版画艺术家面对有限的材料和所要表达的版画审美语境空间的无限性,这才是当代版画存在的意义所在。因而,负载各种社会文化思考的版画图式语言成为版画艺术家关注当代现实社会首要研究对象,并体现为对理性生存状态的抽象性表达。从注重版画艺术观念传达到关注建立自我主体文化精神,当代版画艺术借用一切可能的视觉形式呈现其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并以实验性、理性的综合跨界艺术实践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当代版画艺术语境。如有些版画家运用现代计算机高清微喷技术进行创作,在追求对象的真实中隐含着理性的批判精神和颠覆情绪。再如版画家谭平的腐蚀铜版画作品,画面的各种语言符号随意散布而又相互依存,在蔓延的象征符号下内在的秩序被重新构建。湖北版画家张广慧的木刻版画崇尚黑白形式,作品中的都市日常生活图景被作者题名“北渚”,即彼岸之意,富于当代审美语境的哲学思考。
二、当代版画语言“非主体性”的审美体验
主体性是哲学的概念,主要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和地位,在艺术实践活动中这种主体性显现的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决定了在版画艺术实践活动中艺术家自由、自主、能动的进行版画语言符号创造的特性。同时,随着具体历史语境的改变,艺术实践的主体性也是逐步得以展现。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艺术哲学的基本倾向转向艺术回归人生活的现实世界,追寻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当代艺术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人的生命主体意义,信仰、信念、情感、价值、欲望、潜意识等都成为艺术的目标和对象。黑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被限制的、有限性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美或艺术,作为可以从压迫、危机中恢复人生命力的东西,并作为主体的自由希求,是非常重要的。”[6]人的本质决定了其生命主体意识会反抗外界自然主义理性工具的压抑,艺术成为反抗这种压抑的有效途径。当代语境下的版画艺术创作更具有这种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版画语言符号所体现的本真存在赋予作品比认知更本质性的生命激情。谭平的木刻套色版画《无题》系列作品,画面由一些形似细胞的线圈和点组成,通过多次半色彩覆盖,使得图像具有深度感和层次感,进而把创作主体的生命意识和情绪波动蕴涵于视觉语言之中。当代版画语言符号作为一种艺术主体与主体间的存在关系,是一种创作主体与受众的对话和交往关系,在这种艺术对象的主体间性存在中,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版画语言符号的话语权关联到生活世界与文化语境。当代版画“印迹”语言符号的本质就是创作主体与受众之间的理解差异,主体的创作活动反过来被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延异性所牵制。当代版画作品的创作者不再是当代版画艺术活动的“中心性”的主导者,而是版画艺术阐释的无中心、非主体性的多元化表达者。
当代社会艺术的话语权取决于“知识——权利”的运行模式,文化权利的模式会对艺术主体本身进行无形塑造,艺术创作主体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主体,艺术创作主体通过艺术作品反抗权利压抑是有限度的。当代版画艺术作为一个特定的艺术存在,这种“非主体性”的因素要求当代版画语言符号把人的存在及其审美体验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当代版画艺术家的思考从时代生活转向个人内心世界,从公众审美理想转向个人审美体验,这种主体性的艺术感应从“微观”映照着时代气息。如中央美术学院苏新平的木刻版画《干杯》系列作品,在对传统版画的批判继承基础上,逐渐放弃了自然写实主义的传统,把创作主体的个人意识凸显出来,不断超越传统的视觉经验。同时,当代版画艺术家又是在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质疑中实现自我超越,在当代版画创作的间接性、重复性中寻找和延伸“在场”的情绪体验,在对各种物质材料的试验中获得审美实践经验。又如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借用丝网版画的手段对名人头像进行的多次重复创作,引导人们关注现代艺术的多样化与互融性。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同样反感抽象艺术的即兴创作方式,转而研究创作材料的融合性,海报、商标、照片等,以及各种材料的印刷品都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并与其它材料进行拼贴,施以色彩,从而打破了各种视觉艺术之间的界限。当代版画艺术家之所以采取综合的方式进行创作,其目的是以最大化的自由表达创作意图与审美感受。
从当代版画创作主体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是版画这种艺术门类表达的目的而非手段,版画作品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互为目的,这是当代版画本质特性的理想状态。功利性是版画创作主体面临的基本价值问题,如何超越功利主义的误区是当代版画艺术家摆脱外界束缚而独立进行批判性、反思性创作的关键。不管是什么艺术门类,其价值都在于以人为终极目的,只有这样,主体才能把对自身的审美追求投射到艺术创作中,才能超越主体的感觉经验,使艺术作品上升到“非主体性”的层面,凝聚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内蕴,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精神寄托。
三、当代版画语言内心关照的移情倾向
移情是精神分析学中的术语,是指受访者在催眠法和心理联想的作用下对分析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具体表现在受访者把自己过去的情感感受经验投放到分析者上。移情分为两种情形,即正面情绪移情和负面情绪移情。成语“爱屋及乌”、杜甫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牛希济词句“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等,都是移情的具体心理表达。移情效应在艺术和美学上反映也很普遍,中国古代文人绘画题材中热衷于“梅”“兰”“竹”“菊”,就是典型的移情心理现象。“移情是主客融合,是物我合一。它不仅由我及物,把我的情感移注于物,而且由物及我,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7]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移情的根本原因在于主体把情感投射到事物上,使事物具有情感属性,达到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创作主体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外物化。德国学者沃林认为,“审美享受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就是在一个与自我不同的感性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即把自我移入到对象中去。”[8]正如《庄子·齐物论》末篇的庄周蝴蝶梦所显现的一样,移情既发生在有意识里,亦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在梦中,隐喻所意指的意义经由意象呈现出来。”[9]
当代版画艺术作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艺术存在,更多的需要创作主体投入情感体验和哲学思考,当代版画艺术的美学价值不在于客观对象而在主观情感,因而创作主体的生命感悟对当代版画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当代版画创作实践中,版画语言符号成为受众审美观照的直接对象,也是创作主体移情的主要媒介。在河北版画家袁庆禄作品中,西藏少女的形象单纯质朴、目光深邃,厚重的服饰和空灵悠远的高原背景使人产生诗意梦境般的联想,纯净的视觉物象使人精神归于短暂的永恒境界,起到关注内心体验的移情效果。同时,他的作品在再现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注重材料印痕的审美价值,用刀干脆果断,线条流畅质朴。在艺术意志决定论者看来,最终决定当代版画艺术现象的因素是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艺术审美心理需求,这也是当代版画整体向内心观照发展趋势的深层次原因。从发展趋势而言,当代版画艺术正逐渐打破对客观世界的直觉认识,用版画的多种材质形成的绘画语言和符号对外界进行整体联想,观者在这种联想中产生延异空间,从而审美需求得以满足、审美意识得以栖居。也就是说,当代版画艺术不能够走完全抽象的道路,没有生命情绪体验的纯粹抽象是没有生命力,更不具备艺术作品的移情效应。
四、结语
当代语境下,版画艺术的本质属性被重新发现和认识,表现手法上向综合材料和非图像化方向发展。社会学或哲学意义不是当代版画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当代版画艺术作为视觉艺术的组成部分,强烈的反映着时代精神特征和创作主体的生命意识。当代版画创作主体的审美感觉经验通过多种物质媒介进行拓印等规定性处理,使各种印痕组成的语言符号物化呈现出完整的视觉画面。作为间接性绘画,当代版画对语言和视觉符号意义延伸和审美价值的重视是当下版画创作的趋势。当代版画追求看似是偶尔的、不可控制的视觉符号呈现,确同时逐渐辅以各种新的物质材料和表现形式。这使得当代版画艺术越来越具有综合画种的特性,并呈现出非常广阔而令人充满期待的发展前景。
张亚敏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丹纳. 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4.
[2]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6.
[3] 高宣扬. 后现代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74.
[4] 胡经之. 文艺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72.
[5] 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4.
[6]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5.
[7] 凌继尧. 美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1.
[8] 沃林格. 抽象与移情[M]. 王才勇,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4.
[9] 张贤根. 互文性—在艺术、美学与哲学之间[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48.
中图分类号:J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016(2016)02-0097-04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版画作为艺术治疗的媒介研究》(14YJA760055)。
——论移情行为中两种现象的区分
——论移情行为中两种现象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