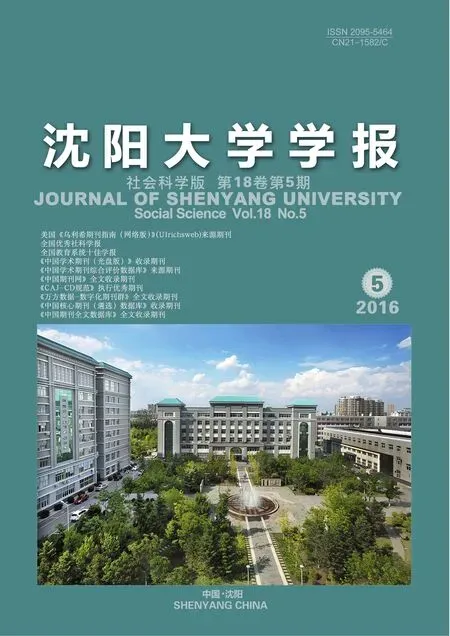从《东坡志林》看苏轼的柳宗元观
王 苑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从《东坡志林》看苏轼的柳宗元观
王 苑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以《东坡志林》中关于柳宗元的评论,探究整理了苏轼对于柳宗元其人、其诗、其文的评价,并将陶渊明与柳宗元进行比较,从中总结了苏轼其人的人生观与文学理论,认为苏轼既因袭历代文士学者的成论,在对柳宗元持身处世上的大节有亏表示憾恨痛惜的同时,也对柳氏文章的高才绝学予以推崇。
《东坡志林》; 苏轼; 柳宗元; 立身为人; 诗文创作
《东坡志林》一书,为苏轼杂感随笔之记。就所记内容而观,所历时间明确可考者,大抵自元丰三年贬黄州起,至元符三年量移廉州止。
考“志林”二字作为书名,始见于晋虞喜《志林新书》,《隋书·经籍志》录是书三十卷,今仅存一卷。以今存内容而言,虞喜所记多杂论故事,亦兼及考据,其体实与笔记杂文无异。东坡继承并拓展了《志林》的书写传统,或记人、记事、记物,或因事见理,或寓写性情,韵散兼行,庄谐并见,充分发挥了宋人“笔记体”在内容、形式、风格上突出于前人之处。
是书宋、明以来,主要版本有三:《百川学海》《东坡先生志林集》一卷本、万历二十三年赵用贤刊《东坡志林》五卷本、《稗海》所录明商浚刊《东坡志林》十二卷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十二卷本,即据商刻本而来。然《四库全书总目》改“十二”卷为“五”卷,并言此书原名《手泽》,“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1]。就此余嘉锡已辨之甚详,其《四库提要辨证》云:“其书为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观庭坚语意自明,其编次出于后人,或亦有所增补,而非零星搜辑者也。”[2]
今存商刻本十二卷凡359则,所记“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3]其中并不乏东坡个人读史心得,亦一并可见其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较具代表性者,即《东坡志林》中对中唐诗人柳宗元的评论。《志林》中述及柳宗元部分计有四则:《桃笙葵扇》《诗须要有为而后作》《评柳子厚〈瓶赋〉》《评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其中除《桃笙葵扇》一则为名物考证外,其余三则分别牵涉柳之为人、文章及诗作。综合三则评论可以看出其间差异极大,而截然有别的评价,是否与东坡个人经历有关?换言之,在不同的政治高度、时间、空间,看待如柳宗元这样因参与革新而贬死岭外的悲剧人物,其视角是否亦随之有不同?再者,就人物论的历史脉络而言,东坡的评论是否受到前人或时人的影响?凡此,均为本文欲考论的范围,故拟从东坡之论柳氏之为人、诗文两方面分论之,以见东坡此中寄托。
一、 柳氏之人
1. 信道知命而不足观
《东坡志林》中,对柳宗元行事为人有所质疑的首见于《书〈瓶赋〉后》:
或曰柳子厚《瓶赋》拾《酒箴》而作,非也。子云本以讽谏设问以见意耳。当复有答酒客语。而陈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盖补亡耳。然子云论屈原、伍子胥、晁错之流,皆以不智讥之;而子厚以瓶为智,几于信道知命者,子云不及也。子云临忧患,颠倒失据,而子厚尤不足观,二人当有愧于斯文也耶!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七日[4]127。
据东坡自署,文作于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时东坡在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此为其一生仕宦中最荣显之时。在历经何正臣、李定、舒亶等言其所作诗文谤讪朝政,并欲置之死地,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一事后,东坡对于政治人物的行事秉持着严谨的态度,其所论柳宗元之《瓶赋》,全文引录如下:
昔有智人,善学鸱夷。鸱夷蒙鸿,罍罃相追。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不如为瓶,居井之眉。钩深挹洁,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久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觊一时。子无我愚,我智如斯[5]。
所谓“鸱夷”,指皮制的革囊,以其与时张弛的特质,故能“多所容受”。扬雄即曾以盛酒的鸱夷与藏水的水瓶对比,撰成《酒箴》一文: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而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叀碍,为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讬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6]
扬雄以水瓶、鸱夷并举,以其属性不同,因而际遇有别:瓶以处高临深,酒不易入口,故不得随人左右;而鸱夷以其能随酒流转,与物张弛,反得出入宫家,成为国器。自古以来,小人之见用与君子之见斥,何尝不如是?柳宗元对此深有同感,遂进一步诠释撰成《瓶赋》。就叙述的主体或文字的运用,可看出是有意继扬雄《酒箴》脉络而下,故东坡直指子厚此文是“补亡”之作。对于子厚“以瓶为智”的识见,赞许他是“信道知命者”,可见子厚的才识,仍为东坡所赏。
《瓶赋》既属咏物之作,则咏物当自有其寓意。子厚将水瓶与鸱夷设为对立面,一正一反,一颂扬一批判,其创作意图之指向便十分明显:一方面以瓶清白淡泊的品格和利泽广大的作用,以比喻持身严正、利国利民的先圣时贤;一方面则以鸱夷皮囊随物赋形,张阖由人的性质比喻巧曲逢迎的小人。章士钊《柳文指要》云“此子厚明明为永贞之变作一解释”[7],是肯定了柳子厚与王叔文等欲“共立仁义,裨教化”的理念,故以瓶为喻的幽微隐情;而“绠绝身破”、“复于土泥”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必然宿命,故章士钊誉其辞为“正直忠悴”之言,洵为的评。
东坡此时以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身份地位,回首审视多次遭贬的自己,再看待子厚面对鸱夷谄诱,以致“昏至莫知”,而清白淡泊,终不媚私的立身原则,却招致“复于土泥”的斥逐命运,寄寓了无限痛惜,故结评子厚“有愧于斯文”。实在是有感于“文应如其人”,以子厚之高才绝学,“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的推崇,对于其不自贵重顾藉的粗疏,表达了深切的感愤。
2. 不知愚妄而欲自解
相同的标准,同样呈现在《东坡志林》中的是对子厚《伊尹五就桀赞》的评论:
元祐八年,读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终篇皆妄,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有意教诲桀而全其国耶?不然,汤之当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诛,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二王之罪也[4]172。
所谓“二王”,指的是王叔文与王伾。顺宗永贞元年,王叔文等因赏识柳宗元之才学,引内禁近,与计事,并擢为礼部员外郎。后王叔文等败,柳因附叔文等坐贬官。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即言其“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急于仕进,以致自污其身。宋祁《新唐书·柳宗元传·赞》甚而将柳宗元与王叔文等的结合,称之为“傅匪人”[8]。凡此均是着眼于附王叔文党,而忽略其利国利民的初衷。据《旧唐书·顺宗本纪》所载,王叔文执政的五六月间,即有废宫市、罢五坊小儿、出后宫并教坊女伎等举措,改革弊政,嘉惠穷民。可知叔文非夸夸其谈、擅权专事者。台静农即尝论王叔文党“尚不能算是比于利禄的集团,如其所结合的是‘当代知名之士’,其所行动又是有关国家的大计,‘内抑宦官,外制方镇’。因此,宗元自述与王叔文结合的原因是可以相信的”。[9]至于王伾为人,据《旧唐书》本传载其“不如叔文,唯招贿赂,无大志……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其上”[10]3736,如此行径则真正是“小人乘时偷国柄”。子厚在认清朝廷及其他势力“愚陋不可力强”的现实下,期许自己如伊尹“急生人”的救世襟怀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柳宗元的政治立场及“出入唱和,凡其党瞷然自得,谓天下无人”[10]3734。不能含藏的行事风格,毕竟影响了世人对他的评价。就立身大节而论,究竟算不得为纯全之姿,此历来论者视其为二王党羽之因,东坡亦未能例外。
东坡对柳宗元“欲以此自解其从二王之罪”的评断,显然着重于柳氏的人格操守上。柳不能自持自重的误判,自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之后,深深地影响了宋人评柳的视角。自刘昫以降,北宋文人如宋祁、欧阳修等均采取一贯立场,从“昵比小人,自致流离”[11],到“桡节从之,侥幸一时”[8]5132,再到欧公所谓“柳真韩门之罪人也”,均说明宋人对于君子应慎独自重、群而不党,严格的士风标准。
庆历四年,因内侍蓝元震劾奏范仲淹、欧阳修等结“朋党”营私,欧公于是撰《朋党论》,除自辩外,并直指“小人无朋,唯君子有之;……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此后时人大多承其观点,如司马光《朋党论》、刘安世《论朋党之弊》、苏轼《续朋党论》、秦观《朋党》等,或深入阐发欧公“君子有党”论,或专论小人朋比之弊,同时并对士大夫群体立出道德操守的标杆。这种群而讨论之现象却也意味着任何一人在当时都无可回避地卷进“君子党”或“小人党”的漩涡里。
苏轼早期因与新党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任,先后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并于元丰二年移知湖州。同年七月以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御史中丞李定相继弹劾,并言其诗歌毁谤朝政,遂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坐罪者牵连至广,史称“乌台诗案”。元祐元年、二年,又以两次策题遭洛党朱光庭奏为“不忠”,最后虽“未欲深罪”,但仍落得出守杭州的结果。此时的苏轼已年近六十,在经历了半生因党争所招致的奔波流离后,对于眼前的宠遇,更有谨慎戒惧的存心。因为唯有自持其身、守正不阿,才有拨云见日的一刻。故而当其看待柳宗元时,是视其为二王之“朋比”者,未必得列“君子”行中。
至于柳氏个人,在经历了永贞革新的失败,贬斥南荒后,仕宦生涯的剧变所给予情感上的冲击和生命的体悟,反倒焕发了他在文学创作中更深邃的内涵。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柳宗元从政、处世、作人、为文,不管哪样,均能保持独立精神、自然质性、纯真心灵、自由意志,宁折不屈,纵然偶有瑕疵,也绝然掩盖不了他人格的伟大。”[12]
二、 柳氏诗文
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主要包括文与诗两方面。北宋文人在关注柳集时,大抵将焦点集中于柳文,或韩、柳并举,以推崇其文。如田锡《贻宋小著书》“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论辨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为诗为文,为铭为颂,为箴为赞,为赋为歌,氤氲吻合,心与言会,任其或类于韩,或肖于柳”[13];王禹偁《寄题陕府南溪兼孙何兄弟》“篇章取李杜,古文阅韩柳”[14]、《赠朱严》“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15];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16]。而肯定柳宗元,甚而将其列于韩愈之上的则首推晏殊“韩退之扶导圣教,刬除异端,自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矣”[17],足见宋初文人对于柳文的推重,并且足以作为效法的典范之一。
苏轼对柳氏的为人虽有微词,但对于柳文却极为嗜赏。“久欲书柳子厚所作《东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净住院无量寿佛堂中”,后以与曹辅等会堂下,遂书以遗僧从本,使刻之,并为之跋[18]。据苏轼自署,文作于元祐六年二月九日,其书成时间较前述《书〈瓶赋〉后》略早。书古人之文刻于石,自然是深爱此文,方有是举,苏轼久欲书《东海若》文,则意味其浸淫柳文中已有一段时间,能知子厚“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19]坚执的心境。而苏轼对现实的热切关怀与面对朝臣攻讦的冷静思考,与子厚当年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置之佛堂”以所观者未必皆是佛门信徒,适足以作为自表心境的最好证明。
苏轼对柳氏才学的肯定,亦体现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20]423其评价固然有因袭前人之处,但从宋祁所谓“不失为明卿才大夫”到苏轼的“高才绝学”,说明了他较前人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柳宗元整体的价值。而这也是他备受扼抑、饱经忧患之后的晚年收获。
至于柳氏的诗,则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是为文名所掩的缘故。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柳河东集》所录,其今存诗共163首,除《省试观庆云图诗》《韦道安》《龟背戏》《浑鸿胪宅闻歌效白纻》四首为长安时期所作外,其余103首作于永州期间,40首作于贬柳州时。柳宗元自永贞元年九月贬邵州司马、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至元和十四年卒于柳州任上,159篇诗作是十五年曲折坎坷的生活纪实与心路历程的映照。亦因为诗作植根于个人政治生涯和情感思想的真实写照,故而发愤以抒情成为其作品的主要基调。
就现存资料考索,苏轼初言柳诗在自密州赴登州时,“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旁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20]7546,可见至少在元丰以前,东坡即已接触柳诗。晚年的东坡在先贬惠州、再贬琼州,愈转愈穷之际,重新关注柳诗,《与程全父简》:
流转海外,如逃深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21]。
许顗《彦周诗话》亦载:
东坡在海外,方盛称柳柳州诗。后尝有人得罪过海,见黎子云秀才,说海外绝无书,适渠家有柳文,东坡日夕玩味[22]。
苏轼晚年的遭遇与柳宗元极似:长期贬谪、流转岭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日夕玩味”柳宗元诗作,不仅对柳宗元的遭际也有了更深刻的同情与悲悯。换言之,即更能体会柳宗元当年幽独的情怀。此际此刻,谪处海外的东坡自然对柳宗元产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而时诵其佳句亦成为东坡窜逐生涯中,解其牢落之愁的精神慰藉。
以陶、柳二集为友,固然是辗转流离下,物质条件缺乏所致,而另一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渊海中,先哲前贤的典范里,他肯定了陶、柳二人相同的文学底蕴与深邃的精神内涵,从而作为自己安身立命、安顿心灵的依傍。
1. 温丽靖深而似陶
东坡对柳诗的首肯其来有自,究其原委,应是来源于对陶渊明的赏爱,而其于陶氏的亲近则始于熙宁外任时期。而后黄州时期,由于躬耕的生活体验,使得他在情感上进一步贴近陶“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元祐七年开始创作和陶诗[23]。晚年远贬岭南,枯槁淡泊的生活更加深了对陶氏人格的体悟,一百余首和陶之作,不仅是与抒情主题的对应与沟通,更是对陶渊明卓然独立人格的肯定。日夕玩味陶、柳二集,苏轼体味出柳诗深远的内蕴与陶潜清淡的风格有相通之处,以陶、柳二人的相通点为基础,苏轼阐述了他论诗的观点:
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4]168。
他首先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的现实功能,换言之,诗除了传统以来裨教化、补时政的社会功用外,就诗歌本身价值而言,恢复魏晋时期高古的风调,应该是更重要的。《书黄子思诗集后》: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24]285。
文学是渐进的,风格亦是逐步形成的,当一个时代新的风格建立时,也意味着它离古愈远。《艇斋诗话》就指出:“大抵一盛则一衰,后世以为盛,则古意必已衰。”[25]281虽然凌跨百代,集诗人之大成,但亦离汉魏高古之风渐远。所以“有为而作”应该是恢复汉魏诗歌高风绝尘的特质,而这也是他推崇黄子思诗的原因。
在有为而作的命题下,所谓“以故为新”,指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营造出新意。艺术上的新变,总是在历史的原典上不断地创发而形成新的典范,书法如此,诗歌亦如此。李、杜融合了苏、李、曹、刘、陶、谢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开创了唐诗独有的气象。
在诗歌的语言上,苏轼要求“以俗为雅”,俗与雅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可以转换的。俗者近人情而易明,雅者高古而温婉,以平浅近情的语言表达温婉的情致,这是他所追求诗歌的“雅”。相对的,“好奇务新”刻意求奇以新人耳目,是作诗应当避免的。
“好奇务新”的韩孟诗派的特征,苏轼《评韩柳诗》:“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则不及也。”[26]264退之诗“过奇”而不够“温丽靖深”。柳宗元晚期的诗歌由于受到山水的陶铸而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极似陶渊明”亦就意味在温丽靖深的特质下,苏轼肯定了陶、柳二人诗风的共同美感。
2. 外枯中膏,似淡实美
柳宗元从不明言自己学陶,长期的贬谪生涯中,亦不似苏轼,从无和陶之作。然细检柳诗可以发现,柳氏谪居永州后,所作《饮酒》《读书》《感遇二首》《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篇目几与陶潜诗相同,这暗示了他在人格理想、生活方式上追步渊明的存心。尤其《读书》《觉衰》二诗,秾纤合度的笔法,萧散简远的风格,更与渊明诗不相上下。苏轼因进一步地强调陶、柳二人作品实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看似清癯而实为丰腴,看似平淡而实含绮丽:“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26]264
东坡以“外”“中”“枯”“膏”“淡”“美”等形式、内容的反差以表述他的诗歌美学,简言之,就是以平淡的形式表现不平淡的内容,在枯槁的外表下,蕴藏着丰润与华美,在质朴的表象中又蕴有无限的绮丽。以“外枯”与“中膏”“似淡”与“实美”“纤秾”与“简古”“至味”与“淡泊”看似绝对的对立面,总结成为他“平淡”理论的实质。
“平淡”的美感特质是一种成熟的美,是繁华落尽而后成其实的美。苏轼曾自述其诗作是“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就说明了他的诗歌是在现实生活与生命阅历下,不断磨揉所形成的“老境美”。岭海时期的东坡,年已五十九岁,在历经多次的政治打压后,他已摆脱了对事功的追求,而多了对生命的体悟。因此在审美的角度上,亦就超越了悦人心目的层次,而上升到宁静淡泊、恬淡澄明的境界。在简淡的况味中,体会生命的本质;在耕读的形态中,遥契古人。《书柳子厚诗后》:
元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至庚辰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24]280
饮酒、读书是海外生活的重心,书柳诗以赠人则是东坡对柳宗元的认同。“淡泊而有至味”是浪尽大化后子厚全人的呈现,亦是晚年的东坡过尽千帆后的人生观与诗学观。
三、 结 语
源于诗文二者在文体上的差异,传统以来对于二者的要求亦不同。诗歌是情灵摇荡下,吟咏抒怀的产物,年寿或可有尽,但文章则应传诸百世。然而文章是否能见重于世,还系于作者的人格与操守。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一方面称道柳宗元贬谪后的文学辞章必传于后,一方面又指责柳参加政治改革是不能自持其身;此后历代的文士学者大抵沿袭这种角度:因为永贞革新的失败而忽略、漠视他的文章思想。苏轼对《瓶赋》《伊尹五就桀赞》的评论,不仅表露了宋人在“士风”要求上严苛的标准,亦代表了元祐六年至八年,东坡“身居庙堂”,始终以清白耿介面对异党深文周纳以罗织罪名的不屈操守。
至于诗歌的部分,生命情境逆转后的苏轼,“远处江湖”,透过生活实践与实际创作,表达了他对平淡之美的追求。亦从学陶、和陶的反思中,体味出柳诗靖深的特质,进而将柳宗元与陶渊明作了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提高了柳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对柳诗的推崇,苏轼可谓继司空图后北宋第一人。《艇斋诗话》:
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多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25]292。
作为一个鉴赏者,苏轼从整体上掌握了魏晋以降,书法与诗歌发展的轨迹,又从创作者敏锐的角度,提出了韦、柳、陶的同质性,亦概括了自己的体会所得,就唐诗流派的研究领域,建立了新的观点。从韦、柳、陶并称,到南宋严羽《沧浪诗话》“韦柳体”的提出,东坡的识见无疑是建构诗歌体派的一大功臣。
[ 1 ]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四)[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3107.
[ 2 ]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919.
[ 3 ] 赵用贤. 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M]∥全宋笔记:第一编卷九.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123.
[ 4 ] 苏轼. 东坡志林[M]∥全宋笔记:第一编卷九.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127,168,172.
[ 5 ] 柳宗元. 瓶赋[M]∥柳宗元. 柳河东集:卷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29.
[ 6 ] 杨雄. 酒箴(瓶赋:附)[M]∥柳宗元. 柳河东集:卷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29.
[ 7 ] 章士钊. 柳文指要:体要之部(卷二)[M]. 北京:中华书局, 1971:55.
[ 8 ]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列传九三(柳宗元传)[M]∥新唐书:第16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5:5143.
[ 9 ] 罗联添. 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台静农别集附·柳宗元[M]. 台北:学生书局, 2009:6.
[10] 刘昫. 旧唐书:列传八五(王叔文附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11):3736.
[11] 刘昫. 旧唐书:列传一一〇(柳宗元传)[M]∥旧唐书:第11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5:4214.
[12] 张维娜. 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石”与人格精神[J]. 沈阳大学学报, 2006(1):116.
[13] 田锡. 贻宋小著书[M]∥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5册卷九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217.
[14] 王禹偁. 寄题陕府南溪兼孙何兄弟[M]∥傅璇琮,倪其心,等. 全宋诗:第2册卷五九.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657.
[15] 王禹偁. 赠朱严[M]∥傅璇琮,倪其心,等. 全宋诗:第2册卷六六.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759.
[16] 穆修. 唐柳先生集后序[M]∥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16册卷三二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31.
[17] 陈善. 扪虱新话:下集[M]∥ 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三.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70.
[18] 苏轼. 题所书东海若后[M]∥张志烈,周裕锴,等. 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7864.
[19] 柳宗元. 东海若[M]∥柳宗元. 柳河东集:卷二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363.
[20] 苏轼. 续欧阳子《朋党论》[M]∥张志烈,周裕锴,等. 苏轼全集校注:第10册.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423.
[21] 苏轼. 与程全父简[M]∥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88册卷一九〇六.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132.
[22] 何文焕. 历代诗话:彦周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383.
[23] 孔凡礼. 苏轼年谱[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1042.
[24] 苏轼. 书黄子思诗集后[M]∥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89册卷一九三六.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285.
[25]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艇斋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281.
[26] 苏轼. 评韩柳诗[M]∥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89册卷一九三五.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264.
【责任编辑 李美丽】
Su Shi’s Concept of Liu Zongyuan inTheDongpoLiterarySketches
WangY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Based on the comments on Liu Zongyuan inTheDongpoLiterarySketches, Su Shi’s notions on Liu Zongyuan himself and his articles along with poetry are studied and sorted. The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eory of Su Shi are drawn from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ao Yuanming and Liu Zongyuan. It considers that, Su Shi followed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precedent scholars, criticizing and lamenting Liu Zongyuan’s political conduct, but at the same time, speaking highly of his literary articles.
TheDongpoLiterarySketches; Su Shi; Liu Zongyuan; political behavior; literary creation
2016-03-27
王 苑(1989-),女,山东济南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2095-5464(2016)05-0611-06
I 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