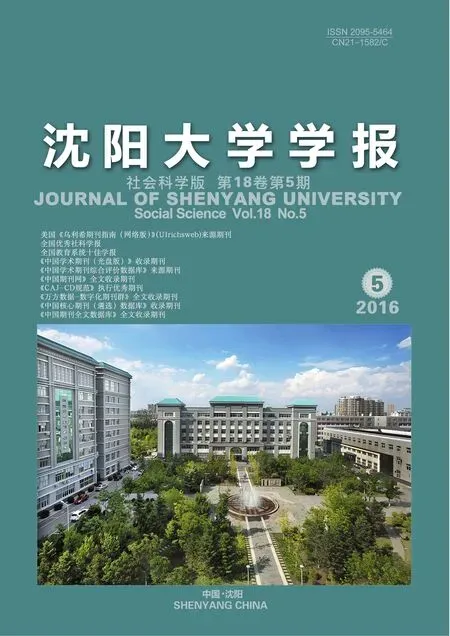虚构中的真实
——论莫言儿童视角叙事的“真实性”
赵 月 霞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37)
虚构中的真实
——论莫言儿童视角叙事的“真实性”
赵 月 霞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37)
通过对莫言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分析,探讨了莫言的儿童视角叙事在莫言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生成、表现及意义,认为莫言的儿童视角叙事在叙事者视角、作家视角,以及读者视角之间恰当地阐释了意象与精神的“真实性”。
莫言; 儿童视角; 叙述者视角; 读者视角; 虚构; 真实性
柏拉图曾以“真实”为标杆,划分出了三个世界:理式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和艺术的世界。这样的“真实”反映在文艺创作中表现为两类:一类是模仿现实的理性文艺,一类是超越现实的非理性文艺。柏拉图轻“模仿”、重“超越”,他更看重通过艺术越过现实直接进入理式世界,所以他贬斥荷马为“说谎”的艺人。
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而著称,其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也着重指出了这一创作的主要特征,可见他所关注的正是超越现实进入的理性世界,尽管在他的创作中也不乏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但是他的作品并不以“批判现实主义”而著称,他总是将故事与人物设置在现实的社会和文化批判背景之下,却并不以揭示罪恶的社会根源为鹄的,可见他的意图并不在于批判现实主义,他的内涵更为广阔。
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玄想与内蕴,而是践行在叙事话语、人物形象、情节设置等诸多方面,如他以“民间”的姿态书写历史的真相,他以“魔幻”的方式书写现实的存在,也表现在他以儿童的限制性叙事言说“意在言外”的多元复杂时空。文章想要探讨的正是儿童视角叙事在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生成、表现以及意义。
一、 儿童视角下的虚构与真实
纵观莫言的创作历程,儿童视角叙事从创作初期开始就已经成为莫言文体特征中的基本元素。从1985年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出现的那个高举晶莹剔透的红萝卜的“黑孩”开始,到《红高粱家族》中讲述“我爷爷”“我奶奶”故事的豆官,儿童视角叙事已经成为莫言叙述的重要维度,此后的《牛》《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以及《四十一炮》,莫言的儿童视角叙事最终“形成一个整体”,在不断的变化、突破与创新中,莫言以儿童视角叙事的“撤退性”叙事策略达到了叙述的极限,并且直接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洪峰的《瀚海》、方方的《风景》和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等儿童视角文本的大量涌现。
莫言的儿童视角叙事在80年代中后期初见端倪,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为代表,这种叙事视角的选择与80年代中国文学“向内转”寻求创作形式的重大变革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视角与文学形式的试验也让莫言与整个80年代以后的文学流派如“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印证与关联。他前期的儿童视角叙事更多的是一种透明的童话体风格,如《枯河》《透明的红萝卜》《大风》等作品中较多使用纯粹儿童视角叙事,以儿童的卑贱化策略来书写生活、历史之沉重。而进入90年代,莫言的儿童视角叙事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是回忆模式下儿童的“经验”视角与成人的“理性”融合下的“我”的记忆反思。以儿童视角叙事为主体,多种叙事视角杂糅并存,形成复调叙述,更加强调叙事的虚构性、传奇性和寓言性。《丰乳肥臀》中永远长不大、吊在女人的乳头上终其一生的“上官金童”,《四十一炮》中对食物特别是肉有着狂热情感的“罗小通”,《生死疲劳》中集驴、牛、猪、狗、猴轮回转世于一身,脑袋巨大、身体萎缩的“蓝千岁”,《檀香刑》中能将身边的人物幻化为惟妙惟肖的动物的赵小甲,极具魔幻、传奇色彩的“异型”儿童成为儿童视角叙事的主体。
与同时期同样热衷于儿童视角叙事的作家相比,余华关注的不是性格,而是人的欲望;王安忆关注的是童年的影响与成长的意义;迟子建关注的是健康的人性,她笔下的儿童具有“泛神”“泛灵”的神话原型的意义;苏童关注的则是儿童的文化想象,他在象征和隐喻中将孩子塑造成“人性之恶”的生命延续和客观载体。而莫言儿童视角的关注点在于“呈现”,摈弃理性、放下成规,以原初态的感性视角和直觉判断呈现遮蔽已久的“另一面”,因此,他的叙述指向的是意象、情绪、精神的“真实”。
莫言的儿童视角叙事的确创造了极具莫言个性化的叙述,但是这种陌生化叙事获得叙述可靠性的基础是什么?莫言笔下的儿童的言说力度究竟有多大?当莫言将儿童的叙述以“撤退性”“非常态”的方式言说关于历史、现实的寓言时,这种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冒险。这样的取舍和判断又凝结着作家主体怎样的文化审美价值在其中?季红真在《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一文中说道:“生理意义上的儿童、精神意义上的儿童与文化意义上的儿童,像活化石一样结构着他神话世界的主体。”[1]
显然,从叙事学角度来说,莫言借助儿童的生理意义选择了叙述视角,但是视角的交叉变化、复调同声以及视角与作家视角之间的游走与隐匿又曲折地指向了莫言的窠臼——精神的“儿童”,当读者视角介入时,儿童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在一种开放与流动、交流与悖反中抵达了叙述的“真实性”。
二、 叙事视角与文本意义的动态关系
儿童视角叙事的选择,本身就是对“虚构性”的倚重,对“真实性”的远离,莫言对此心知肚明。王富仁在研究鲁迅小说的叙事结构时提出小说的三个基本视角,即作者的视角、读者的视角和叙述者的视角。 莫言儿童视角叙述的真实性问题关涉到作家、叙述者以及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三者之间如何共同建构了叙述的“真实性”的问题。
对于“真实性”的考量,一般来说,如果从空洞的理论层面开始建构并铺张叙述,理论就会在无形中侵占真情实感的领地,也由此造成一种习惯性的错觉,只有理论的才是真实的、普遍的、合理的、有意义的,而来自感性层面的情感和细节描写往往显现出个体的、偶然的、不可信服的特征,因而在阅读中遭到控诉和打压。
以儿童视角展开叙述,要求叙述以回归儿童本体为前提。但在成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儿童由于其在思维水平、知识储备、感知能力的欠缺与不足,造成其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方面的“不足”,他们的认知和感受常被赋予感性的、零散的、偶然的、片面的、肤浅的形象特征,因此也会影响到所“传递”信息的有效性。
此外,儿童视角叙事的内在矛盾和复杂建构也直接对于叙述的“真实性”表达构成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首先,儿童视角叙事具有双重人格。儿童视角下的“我”——孩子,不仅是叙事的观察角度,也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他不仅是文本的叙述者,同时也是作品中的行动者。因此在叙事情境中,儿童叙述者便有两种“身份”:他是故事层面的一个人物,也是话语层面的一个叙述者。所以赵毅衡先生曾说: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 简言之,在儿童视角文本中,“儿童”作为叙述者和被叙述者具有互构性,具有说者和被说者的双重人格,这一双重性直接关系到“真实性”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儿童视角叙事中作者视角与叙述者视角之间存在“藏匿”与“代言”的游走形态。
儿童视角叙事,在叙事学上很大程度地避免了全知视角的武断性和霸权性,以较为全面、立体的声音恢复每个事物的真实面貌,同时这种限制性的叙事视角,也较好地隐藏了作家的思想锋芒,消解了潜在的意识形态灌输性和思想说教性。对于作家、隐含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撤退性”的叙事策略,是作家有意识地掩藏自己的主观判断与价值立场,但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又不能缺少、也不可避免地介入作家伦理判断,因此,一方面要如实还原儿童的本相,一方面又要通过儿童传输自己的观念和价值,这种表层的叙述感觉与深层的作家观念如若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叙事的虚假和艺术的失真。
另外,成人作家视角建构儿童的叙述视角话语,其内在的罅隙也是不可避免的。作家在借助语言讲述“孩子”的故事时,尽管作家竭尽全力在向儿童的本体靠拢和贴近,但这种“成人”讲述“儿童”的世界的方式,毕竟还是存在某些难以触摸到的罅隙。儿童视角叙事让童年的经历与人生理想借助回忆生成的文学模式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虚幻性。因为叙述者在成人的叙述话语和儿童的经验视角的交织中,在历史与现实的映现中,成人心态干扰对童年体验的回味,记忆将永远被回忆所改写——即便成人作家努力体察、体验儿童的情感、心理,甚至通过对自身心理底层无意识的发掘来契合孩子们的思维。 因此,儿童视角叙述在真实性方面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对童年生活取舍中的有意“彰显”和无意“回避”,也来自于回溯往事时所加入的成人的后知后觉思考与判断,还来自于还原童年的印象与还原童年的感受之间存在的差距问题。因此,成人作家在语言的编辑、逻辑的推理、心理的揣测上是否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在“叙述”的过程中又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这种真实。
对于莫言而言,这种文本背后的意义与他在叙事表层显现出来的叙述者视角构成更为异常复杂的动态关系,有时它们是相互交融、互相印证、补充完善、水乳交融的,有时它们又是背道而驰、皮毛两张,在裂隙的张力中阐释意义。这就回到了儿童视角叙述在多大程度上吻合作家自己的思想价值的问题上来,也就是儿童叙事者视角与作家视角、读者视角之间的交集是如何建构的。
三、 荒诞的叙事与精神的真实
对于莫言儿童视角叙事的“真实性”探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从作家角度来说,作家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再现了儿童的本相,而儿童的形象以及叙述又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作家的伦理道德和思想内蕴?从叙述者角度来说,在以儿童视角为主,其他视角为辅,相互转化、交叉、互补的复调叙事结构中,叙述者的价值倾向是什么?从读者视角来说,没有乡村经验的、已经是成年人的读者怎样通过儿童视角下的陌生乡村叙事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经验共鸣,而产生信任感和真实性感情?以上问题的症结点都在于儿童经验世界的呈现与作家思想、观念意识的渗透之间的内在权衡与分担,其间的分寸拿捏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莫言在对《红高粱家族》所开创的这种“如鱼得水”“水到渠成”的儿童视角赞叹之余,也指出了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叙述时空”[2]。换言之,莫言在文本的建构之初,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儿童视角叙述存在的“虚幻性”和“风险性”,那么他所着力的“真实”又是什么呢?
莫言以自我认知能力以及社会认知能力“有限”的儿童展开叙事,以“非正常”的儿童作为典型形象,意味着莫言的叙述从开始就远离对现实世界“真实”的模仿,是对叙述的虚拟性和荒诞性的极度张扬。在很多时候,他甚至直接跳出来强调这种虚构性,《四十一炮》是爱“吹牛撒谎”的“炮孩子”讲述的故事;《酒国》里的故事都是作家“李一斗”的文学虚构;《生死疲劳》中的很多情况介绍都是借助“多嘴多舌”“爱出风头”的青少年“莫言”传达的。由此可见,莫言所倚重的“真实性”并非是针对“现实的条框”来说的,而是对现实的荒诞演绎,那么就说明莫言在意的并非是现实的真实性,他追求的是意象、精神上的真实。
首先,现实主义的土壤难以安放焦灼的灵魂,莫言以超现实主义的魔幻精神触摸“真实”的纵深。纵观莫言的创作历程,其中不乏强烈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和《红树林》等,但占据更大比重的还是他的具有魔幻色彩的文本创作。莫言从创作之初就很少对于社会批判、政治介入以及道德规劝等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就被命名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借助黑孩这个感觉和想象超常的传奇人物,写出许多超现实的内容,他能看见红萝卜流淌的透明的液体,他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他能看到蓝色的阳光。他通过想象建立起来的与人物相关的传奇经历、自然景观、环境文化的虚拟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与人的日常经验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莫言总是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相信“万物有灵”的世界体认,相信想象可以抵达精神的真实,于是经验世界和虚拟世界具有了内在的互通性,正如季红真在《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一文所说,莫言的叙述连接了“经验世界”和“神话世界”[3]。
其次,“仰视”的叙述视角与扎根乡土的叙述场域,让叙述的“真实性”有了坚实的着陆点。莫言的叙述很多都来自儿童视角,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视角选取来说,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充满虚拟色彩的,然而扎根乡土、立足现实的叙事,却使得莫言在经验与现实、抽象与具象、有限与无限之间获得了有效而奇妙的沟通,这就是这个视角的神奇所在。他总是将视野投放在高密东北乡的那一片土地,总是用孩子的朴实眼光来审视众生万物,对政治领域的刻意疏离和超然自拔,使得莫言在叙述中获得一种不为外在事物所困的超脱与自由,在贴着大地行走的叙述中,有着一种热气腾腾的升华,暧昧的关系,变形的幻景,魔幻的建构,空灵的想象,造就了天马行空的艺术氛围和艺术特征。于是,以儿童的最低“仰视”姿态开始的叙述,对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把握逐渐为叙述的空间所吞没,通过一种内在的编辑、重组、错位、链接的新形式转化为一种寓言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颠倒错乱的反而正是一直被人们忽视的真实。这一历程正是从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再到后社会主义语境的历程,即碎片化的现实,自身的形式与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寄居于互相矛盾、抵触、过剩、亵渎与无意义的形式与叙述中。
最后,“童心”的原初性解密现代主义的繁复性。利用儿童这一“颠覆性”的眼光来叙述和思考,旨在与交际、再现、编码的传统理性语言与叙述策略相对抗,儿童视角下截取的世界,是与成人清醒的、理性的相对立的梦幻世界,一方面是对失去心灵方向、价值体系、精神分裂的后社会主义语境的一种投射,另一方面也是在迷雾中积极求索的一个过程,借用拉康的“无意识”理论观点,儿童的单纯视野发现了社会的野蛮、残酷、欲望、诱惑、死亡、暴力、淫荡与虚伪。社会的建构应该首先回到对于社会和人性的重新认识的起点上来,认识自我,建构自我。于是,复杂性的现象借助单纯性的视角表达,“自然史”的坍塌却遭遇了新价值体系的尚未建立,陈旧过时的与刚被创造出来的混乱,造就了叙述中的“狂欢”和“多元”。所以从儿童视角下呈现出的景象,单纯却真诚,幼稚却纯朴,模糊却依旧鲜明,奇特荒诞却又独具逻辑性,令人昏聩迷乱的不一致中深藏着清晰感和坚定性。“现代小说中对于小说形势的玩弄性颠倒以及对于语言成规的滑稽模仿”[4]是与现实主义描绘真实的方法大相径庭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总是在极力掩饰小说的虚构成分,总是通过小说即生活真实的“共鸣”情感来完成对于现实的揭露以及批判。而“现实主义执行其意识形态计划最为有效的方式,正是通过诉诸于‘真实’而将某些东西合法化,同时又将它称之为‘不真实’的东西斥为非法的。毋庸赘言,现实主义这一述行功能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它可以维系共识性和模仿性地理解语言和文学的运作方式;即,语言和文学反映现实,而不是构造现实或者大肆影响现实。”[5]
莫言儿童视角的叙述策略,借用了创作中从意识坍塌到无意识,从理性坍塌到非理性(感性)坍塌,再到一种无意识与非理性的新逻辑、新视野——这是作品寓言化得以实现的起点,同时也是“再现”“真实性”的观察角度。由此,在人物形象的建构中虚构的维度越是稀奇古怪、越是扭曲变形,越是可疑超验,在寓言的维度上就越是清晰客观、越是真实可信。
于是,在莫言的文本中从开篇就能感受到虚实相间、真假并存的叙述元素,他一面客观冷静,一面情绪肆意驰骋,他总是一面煞有介事地宣称“句句都是实话”,一面又戏谑调侃地指出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甚至是一个玩笑。
《四十一炮》主人公罗小通以“炮孩子”命名,专指吹牛撒谎的孩子,故事以罗小通在五神通庙对大和尚讲述离奇虚幻、真真假假、碎片游离的故事为脉络,小说以炮来划分叙事的单元,以四十一炮结构四十一章,罗小通的叙述真诚坦白中有着欲盖弥彰,客观冷静中有着肆意渲染,童言无忌中有着世故老成,良心叩问中隐藏着油滑轻浮,虚虚实实并置在文本中互相渗透,又互相解构。小说开篇就设定了虚构的成分和基调,然而,叙事者却一再声明:“句句都是实话”。事实上,小说以“谎言”开始,以“想象”作为结束,颇具荒诞色彩的拟真实叙述在事件发展的逻辑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虚构的,但一个灵异儿驰骋在他的想象空间中的精神心理却是真实的,这也是小说在着力营造和打磨的艺术审美本性。莫言在《后记》中也说,诉说者“煞有介事”的腔调,能让一切不真实的都变得“真实”起来。
莫言总是强调“纯属虚构”,但又极力说明“句句是真”。叙述情节的荒诞、天马行空的想象、魔幻离奇的传说和演绎以及一再以“元小说”的方式强行中断叙述,提醒读者“一切纯属虚构”的表白都使得小说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叙述氛围,你总在他煞有介事的严肃中感到诙谐、游戏式的轻松;你总在那直白、童真、无意识的调侃中感到生命至真、历史沉重的叹息。莫言的故事是传奇的、有趣的,但当你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总是介于复述和难以复述之间的尴尬,作家的意图也总是在把握和难以确定之间游离,小说的风格总在严肃和轻松甚至油滑之间。
韦勒克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幻想和虚构是返回现实的有效途径。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些试图背离现实的人,借助艺术的想象和幻想,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的艺术创造。但是,他们的幻想又往往是合理的,具有反映实际生活的价值,因此,在幻想世界搭建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现实世界。 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描述欧洲作家的作品时强调,艺术不是真理的助手,无论是特定时期的真理还是永恒的真理。他说“艺术作品自身也是一个生机盎然、充满魔力、堪称典范的物品,使他们以更开阔、更丰富的方式重返世界。”
莫言以儿童原始生命力的“单纯”与不受社会成规所禁锢与污浊的优势,获得了重新言说、评价和审视世界的另一种角度,在莫言看来,这种角度的重新选择远比墨守成规地抵达深邃来得更为真实,也更为深刻。由此,虽是孩子的稚言拙语,却具有穿透历史、文化和民族乃至人类意义的深远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莫言获得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立场的实现。也就是说,解构我们认知习惯上的“真实性”本来就是莫言写作的动机和目的之一。任何一种经历、一种认知因其表达的立场与方式不同,会有不同的叙述效应,这里不仅关涉到叙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叙述者的差异性,也关涉到叙述本身的局限性,“真实”不过是混杂着无数“虚构”的个人判断。这是莫言的创作观,也是他的历史观,更是他的世界观。莫言的小说处处暴露其虚构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真实,暴露虚构正是以更加坦诚的姿态面对真实。
四、 读者视角“真实性“的获得
从接受学角度讲,读者视角在儿童视角的引导和叙述下又经历着怎样的观察调试和精神旅行,从而接受并认可其“真实性”的表达呢?
读者的视角是指“作者从自己假想的读者的角度对小说文本进行的整体观照,他要在这样一个角度上使自己假想中的读者感到审美观照上的满足或相对的满足,这种满足是接受者的审美满足,是借助文本获得自我的乐趣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与作者在思想上发生共鸣。”[6]这样的共鸣已经不再是就小说创作技术层面的知音寻觅,而更多的是在意义和现实层面上“隐含的作者”、文本的自足意义与“隐含的读者”的交互沟通。
新时期文学的变革与繁盛,不仅是作家文体意识自觉追求的结果,也离不开大众审美方式和审美价值的改变与更新。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当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生活方式日益趋同之时,潜意识中对于“经验趋同”“欲望审美”等导致的想象力贫乏有着本能的抗拒,因此激发生命中的潜能和力量,挖掘新的审美质素成为文学发展的新方向。无疑,莫言的这种新鲜、陌生的叙述方式潜在地暗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为莫言儿童叙事可靠性的接受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莫言一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扎根乡土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写作立场,也让他的作品具有了亲民色彩。“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立场,让他从情感深处回到乡土,钟爱那里的一草一木,怀念那里的一人一事,莫言思想意识中的乡土远非长久以来被主流文化遮蔽、排挤、边缘的附属体,它有着不为人知的蓬勃生命力和生活价值意义。因此,认识乡土、理解生活的同时,读者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现代文明,需要“隐含读者”对自己既定的价值标准和取向进行清理归零,儿童视角正以这样的原初状态带领读者进入阅读。另外,莫言总是为小人物、弱势群体代言,儿童是这些人物的集中代表,也因其心智尚未成熟,其悲剧的震撼力更为深刻与鲜明,人类共同的“同情弱者”的心理情绪也让他们在“情感共鸣”“理性反思”中完成了对于“真实性”叙述的接受。
莫言利用儿童视角打开的文学之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模糊叙述中的真实与虚构成分,从内容上的传奇魔幻性到形式技法上的亦真亦幻,共同构成了文本之间特殊张力,在这种张力的牵引之下,作家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真实意图的遮掩和保护,一种花腔的形式呈现出来,模糊了评论界的视线。但是,毕竟不是儿童,也不是高密东北乡的读者,如何在这种低智化、虚幻性的叙述中保持旺盛的阅读激情乃至最终确立“故事”是“真”的呢?
莫言一泻千里、滔滔不绝的语流,以及天马行空、荒诞不羁的想象力和快意恩仇、率性而为的人生写照共同架构了莫言充溢饱满的快节奏叙述,那传奇编织的人生,那祖辈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那不回避的死亡与暴力的淋漓尽致,在叙述的强大攻势下击毁了读者在阅读中的些许质疑与思考,而在叙述洪流的裹挟下一路向前。同时对于读者来说,莫言多种声音的叙述策略总是让读者毫无招架之力就被他的叙述所裹挟,但在阅读过程中却不断地质疑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质疑文本的同时,也开始质疑自己过往的以及现在的判断。而每当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试图做出某种判断或结论之时,莫言“演讲式”的语言洪流直接裹挟读者进入下一段“解构式”的叙述。这正是莫言小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带来的无限开放性。
当读者来不及也无意于对行进中的文本提出质疑时,思考的反作用力直接反射在读者对自身存在的质疑,叙述者迂回隐秘传达给隐含读者的对于生命力退化的藐视、对于隐含读者自以为是的现代文明的嘲弄与鄙夷开始在读者身上发生反应。那个弱小、无知的儿童,正是在隐含读者毫无设防、漫不经心中带动读者与叙述者一起缅怀祖先、朝拜生命、拷问自我。其实叙述本身并没有强加给读者多少压力,读者的焦灼感完全是自己的,是“隐含作者”在文本之外赋予“隐含读者”的。
由此可以看出,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更多是“作为弱者”的写作,为以乡村、农民、孩子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这种弱者更多地针对权贵之士和城里的文明人。但是莫言的针对性并不以锋芒锐利的批判来呈现和暴露,他情感的渗透和氛围的渲染使得他的叙述很是讨巧,一方面他以弱者的立场和身份赢得了弱者的共鸣和理解,另一方面他又以传奇的故事、神秘的乡土和敢爱敢恨的率直人生吸引了那些进化发展历程中靠掩饰和人性的泯灭而成就起来的所谓“文明人”与“强者”。简言之,莫言的小说对于隐含读者来说,从表面上很容易获得“弱者”的同情和支持,而在深层却拨动了“强者”那尘封已久的真实内心,唤起了对于良知、人性、生活的追问与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莫言不仅有文学艺术上的独特创造,而且也迎合了历史消费、传奇消费的文化口味和时代潮流。
[1] 季红真. 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6):91-100.
[2] 莫言,王尧. 从《红高粱》到《檀香刑》[J]. 当代作家评论, 2002(1):10-22.
[3] 季红真. 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J]. 当代作家评论, 1988(1):80-89.
[4] 华莱士·马丁. 当代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222.
[5] 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152.
[6] 王富仁.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57.
【责任编辑 刘 洋】
Fictitious Reality: Authenticity of Mo Yan’s Children’s Perspective Narration
ZhaoYue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B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n Mo Yan’s literary works, the generation, perform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Mo Yan’s children’s perspective narration in his magic realism creation are discussed. It considers that, Mo Yan’s children’s perspective narration properly illustrates the authenticity of intention and spirit between the narrator’s perspective, the writer’s perspective and the readers’ perspective.
Mo Yan; children’s perspective; narrator’s perspective; readers’ perspective; fiction; authenticity
2016-05-12
赵月霞(1979-),女,内蒙包头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2095-5464(2016)05-0600-06
I 206.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