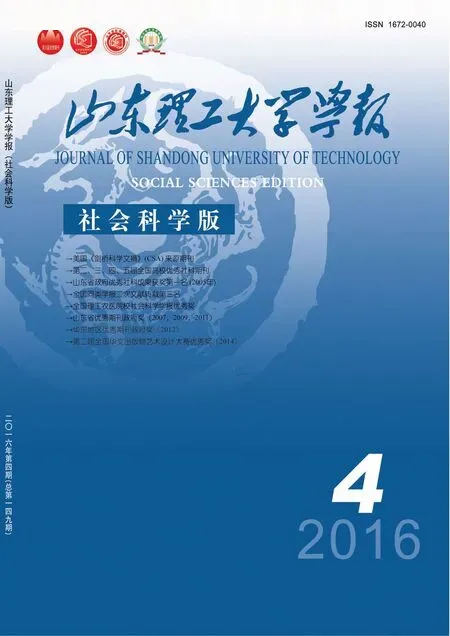《微暗的火》与“幽灵”书写
尤 丽 娜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外国语系,安徽马鞍山243000)
《微暗的火》与“幽灵”书写
尤丽娜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外国语系,安徽马鞍山243000)
[摘要]鬼魂、亡灵复活等超现实意象在纳博科夫小说中有举足重轻地位,特别在其代表作《微暗的火》中,幽灵、暗影等超现实意象频繁迭出,富有哲学思辨色彩,不仅充满了彼岸世界的召唤,而且彰显了纳博科夫独出机杼的艺术观。对纳博科夫小说《微暗的火》中幽灵意象进行诠释,为阐释小说主题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空间:哲学思辨空间、文本叙事空间、人物心理空间、文学艺术空间。通过小说多重幽灵意象书写,揭示了纳博科夫对死亡的形而上的哲学反思,而文本叙事空间、人物心理空间显示出小说人物身份多元化与纳博科夫的流亡创伤意识与飞散思维,通过小说人物命运的结局,表现出纳博科夫的向彼而生的哲学观,从而管窥火焰缘何微暗的小说主题。
[关键词]纳博科夫;《微暗的火》;幽灵;空间
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不仅以晶莹明澈的意境、瑰丽旖旎的异国气息著称,而且小说内涵晦涩难懂,由序言、诗歌、注释和索引构成的小说结构一直为学术界关注。纳博科夫运用游戏、镜像、火焰、象棋、阴影甚至幽灵等后现代主义的意象使得《微暗的火》成为他最自负的创造策略——“达到了恶魔程度的骗术,以及接近荒唐边缘的创新。”[1]227金波特古怪荒唐近乎疯狂的衍生评注使得谢德的诗歌“逐渐消失在金波特沉重评注之下,小说从预设的中心转移到边缘”[2]52。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结构与形式上,陈平和李小钧分别从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和文本叙事结构来解读《微暗的火》的主题;陈世丹从后现代主义视阈来分析纳博科夫的小说形式。相比国内研究而言,国外对《微暗的火》研究成就斐然, 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认为,小说“仿佛是个庞大的宝藏,每次探访都有新的发现”[3]21。纳博科夫对小说中的亡灵、魔鬼、灵魂、幽灵等超自然意象的处理,表现出他对死亡和彼岸世界的感知与思考。因此,通过《微暗的火》中幽灵、暗影等意象分析,其创作主题昭然若揭。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斯(Julian Wolfreys)在《21世纪批评述介》对幽灵批评(Spectral Criticism)进行系统的阐释,他认为:“许多当代的批评都是显在或是潜在地建立在文学‘幽灵’之上,即在形成文学的在场与非在场之间的神秘纠结中”[4]259。因此幽灵批评不仅是对文本中幽灵表征意象的剖析,也对具有幻象性、隐性特点的文本外因素进行探索;幽灵批评模糊了二元对立论,它用多维空间理论对线性时间结构挑战,它还“质疑生和死、有形与无形、肉体与灵魂、过去和现在、在场与缺席的明确界线”[5]19。在幽灵视阈下反观小说《微暗的火》,幽灵书写折射出纳博科夫对生存与死亡、肉体与灵魂颠覆性的哲学认知,挑战了美国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揭示出纳博科夫作为流亡美国的俄裔贵族创伤心理,他用回忆性想象来填补过去和现在、在场与缺席之间的鸿沟,最终彰显纳博科夫向彼而生的哲学思想。
一、幽灵意象表征: 跨越生存与死亡的限界
从词源学来看,幽灵(Specter)是指景象和视觉,具有光影、幻影(Phantom)的意思, 幽灵批评提供了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学作品里面怪异(Uncanny)、界限模糊、暗影等现象。幽灵意象起源于哥特文学中游荡在幽暗古堡、神秘废墟的鬼魂、幽灵形象,哥特文学中的幽灵意象重在渲染阴森恐怖的气氛。在现代、后现代文学作品中,幽灵意象则逐渐活跃于后殖民主义的历史、文本、话语中乃至延伸到弗洛伊德的“怪异”心理分析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领域。作为纳博科夫“有生以来写过最难写的小说”——《微暗的火》,通过幽灵意象的书写刻画出小说主人公在死亡、孤独中上下求索的心理状态,突破了生与死、有形与无形、肉体与灵魂的界限[6]168。
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通过谢德与逝去之人的灵魂对话和幽灵侵扰的复现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微暗的火》的主题是一首999行的诗歌,作者是虚构的诗人约翰·谢德,此外还有由精神病患者查尔斯·金波特编辑的前言、评注和索引。谢德写完第999行诗的那天,被一个越狱犯杰克·格雷枪杀,格雷误认为是戈尔德华斯法官。幽灵意象与死亡、来生主题反复出现在谢德四章长诗《微暗的火》中。
谢德借助童年时亲人鬼魂复现以及少年时病痛袭击时瞥见死后世界的经历,反思死亡与生存的界限。诗歌第一节,谢德站在自己窗前,在眼前的真实景物和幻象交织中回顾自己幼年失怙和病痛侵扰的童年经历。在诗歌开首,谢德把自己想象成飞进他窗户的连雀阴影——字面是阴影,实则暗指鬼魂,窗户上映现的碧空仿佛是天空的延续。在谢德的想象中他自己成了污迹一团的灰绒毛——地上鸟儿的尸体,同时又成了连雀鸟的灵魂,飞进那个蓝色映现的世界。从他的书房,谢德也把自己投射在书房的窗玻璃上,或者仿佛投射在外面的雪景上,这些意象渐渐融化为谢德对平静童年的回忆——“一个锡制男孩推动的独轮小车”[7]30。紧接童年的回忆之后,谢德经历了一系列的病痛发作,“蓦地,一阵阳光突现在我脑海里。接着黑夜来临。那片黑暗庄严肃穆。我觉得全身通过时空在分向四面八方”[7]30。正是幼年的疾病让谢德体验到肉体与灵魂、有形与无形的界限,顺着幼年记忆穿越时空。谢德通过幽灵意象的复现回顾童年的经历和再现疾病感受,从而反思现象与现实的哲学关系。
诗人专注思考并探讨人类是否有前生后世生命,通过他和西碧尔的相恋和相守、对女儿海斯尔的爱、对女儿自溺身亡的悼念来对死亡的神秘相抗争。在诗作中谢德艰苦的探讨死亡,与这个“肮脏的不可接受的深渊”进行搏斗[7]48。对于谢德,死亡意味着被“抛进一个无边的虚空,你的身子已经失去,你的精神被剥夺,彻底陷入孤独,你的使命未尽,你的绝望无人知晓”[7]49。爱女海斯尔的死验证了他的怀疑主义,但是海斯尔的幻影却是如谢德想象的那样升起来:在他死亡的那天,一只“漂亮、柔软、火红的蝴蝶”在夕阳中一闪而过,消失在阴影中[7]49。谢德应邀来世预备学院讲学,他解释道,“在勘察死亡深渊时,什么该不理睬”[7]49。之后,在诗歌俱乐部的讲演中,谢德的心脏病发作,在一种临床死亡状态下,在他心醉神迷的时刻看到一座白色的喷泉,似乎充满难以言喻的意义——随后他醒了过来。几个月后他在杂志上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太太在濒临死亡的体验中也看到了一座高高的白色喷泉。他驱车300英里去和她交流,发现一处误印,应该是“山峦而不是喷泉”[7]64。当他到家后这种新的洞见也失败了,甚至对西碧尔都无法表达。他在诗歌中写道:“真正的要点,在于结构;不在于梦幻,而在于颠倒混乱的巧合,不在于肤浅的胡扯,而在于整套感性”[7]64。这也是纳博科夫借助诗人谢德之口表述了他对生命中秩序和设计的见解,更是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探寻。在小说《微暗的火》中真相为类像所取代,最后无限制的消解。在谢德的诗作中,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学院却被称为“我真闹不清这地方和地狱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听见火葬场工人粗野狂笑,轻蔑哼哈,谴责那种甑式炉,大大不利于阴魂显形”[7]55。纳博科夫借助死亡、幽灵意象揭示了在时间的球形牢狱中的谢德生活状态,通过死亡,让谢德瞬间瞥见世界的意义和主宰;而谢德在诗作的结尾部分表示,“通过我的艺术,结合欢悦心情,我才能理解生存,至少可以理解我生存微小的部分”[7]74,谢德透过艺术创作企图到达永恒的生命维度和对彼岸世界的惊鸿一瞥,最后在诗作写到999句的时候被影子杀手格拉杜斯射杀。诗歌在结尾与开头遥相呼应。在诗歌开篇,谢德借助死去的连雀把自己投向碧空,接着在诗歌结尾,他又宣布会在明天醒来,最后跟着金波特走向他的死亡,完成对开头的奇妙回归。
纳博科夫借助谢德诗歌传达了他对肉体死亡的反思,他认为灵魂永生不是通过生命文本来表达,而是通过诗歌与评注,自我与非我,有形生命与无形幽灵的相互作用来表现。谢德与金波特彼此努力进入另一个灵魂,穿越生命与死亡、通过有形与无形、在场与缺席关系将死亡变成人生存在意义的探索之门。
金波特利用幽灵、微光、影子等意象折射出他多重心理世界。金波特自诩为赞巴拉国王查尔斯·金波特,被国内极端派别影子派追杀,杀手格拉杜斯自始至终仿佛影子一样紧跟着金波特从赞巴拉来到美国。金波特躲在偏僻的地方注释谢德的作品,但是其他“谢德研究家”,如赫尔利教授等到处声讨他、追查他、批驳他没有资格作为谢德临终之作的注释人。杀手格拉杜斯本是一家玻璃厂工人,他内心装着发条,如同机械一样,没有头脑,是个傀儡透明的物体,而他的名字中间也隐含着“灰色”、“阴暗”的意思,谢德是被这个影子杀手、阴暗的家伙所杀。金波特从赞巴拉王国逃亡时,天空布满幽灵般的微光,布满幻影和另一个世界的召唤。国王从赞巴拉辗转来到阿巴拉契亚的情节,小说中的象棋、迷宫的意象以及海斯尔的死亡和金波特的出逃,这些镶嵌在精彩纷呈的万花筒似的文本中,烘托出小说多重主题,如同幽灵般的微光踪迹难觅。然而结合纳博科夫的人生境遇就涣然冰释:在谢德被影子杀手误杀和纳博科夫的父亲的无故暗杀;令金波特魂牵梦绕的赞巴拉和纳博科夫故国俄罗斯,在纳博科夫努力构建出来的小说文本中无疑不言自明。
二、幽灵叙事:叙事时空断裂使得叙事主体成为漂浮的能指
幽灵批评除了揭示逝去的事物、死亡、阴影、幻象之间的错综关系,它还包括诡异感(Uncanny)、神秘感(Mysteriousness)和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幽灵” (ghost) 本身就充满悖论,具有典型多重性的特质,既在场又缺席——它游离不定,无处不在,又不受时空局限。童明称这种怪异心理为暗恐(Uncanny)心理,幽灵叙事特征导致小说叙事空间的多元化与不确定性并存。《微暗的火》的费解、矛盾、虚幻与颠覆性体现了费奥多尔启示:“一切在获得意义的同时,立刻就被遮蔽”[8]159。《微暗的火》灵感来自纳博科夫翻译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它在形式上可以说是纳博科夫把后现代游戏文本的实验运用到极致。从形式看它仿佛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按照顺序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由金波特写的序言;谢德的999行英雄对偶体长诗,最后是金波特为诗歌《微暗的火》写的详尽细致的评注和他编辑的索引。“纳博科夫刻意打破开始—发展—结局的时间线性序列的空间小说,故事中镶嵌了看似平行,实则相互印证、相互消解又相互关联的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叙事文本。”[9]75这种荒唐奇特的小说框架吸引读者经过“大量暗示的尝试和错误的迹象”来发现真相——虚无[10]79。纳博科夫在无解的矛盾和含混中表达了对现实的认知:“现实是无穷延伸的台阶,是无穷的认知层面,现实是不可满足于抵达的”[11]55。 《微暗的火》中多重叙事空间、叙事视角的不确定性使得小说主题愈发扑朔迷离。
叙事空间是个宽泛的概念,不同于数理概念中单纯的空间,福柯曾经预言“当今是空间的时代”[12]34。纳博科夫突破了多重地理空间,在从诗歌《微暗的火》到谢德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到金波特的赞巴拉、纽卫镇,以及影子杀手格拉杜斯的巴黎、日内瓦和纽约的一路追踪,各个叙事层面组成无法完全操控的“双纽线的奇观”(the miracle of lemniscates)[13]137。纳博科夫还把视角延伸到小说人物的心理微观世界以及艺术创作空间,实现了越界。如果说《微暗的火》包含着一个现实世界,那么金波特塑造的那个虚幻世界——赞巴拉王国则栩栩如生却又遥不可及。谢德的长诗里真实与虚幻并存,在诗歌开首两行谢德就奠定了《微暗的火》的虚幻性质,误会、欺骗和光学错觉奠定了颠倒混乱、错综复杂的迷宫似的小说基调。诗歌开头两行的过去时态说明谢德在诗歌未完成时就已经离世,他作为一个幽灵来回忆自己的过去经历,并且在回忆性想象中对人生存在和死亡进行探索。
除了多重地理空间和叙事时间的并置,纳博科夫还运用了叙事时空断裂。纳博科夫借金波特之口表达对艺术现实的观点:“现实既不是真正艺术的主题,也不是真正艺术的客体;真正艺术创造了自己特殊的现实,与大众眼光看到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7]10纳博科夫在小说《微暗的火》中用幽灵、鬼怪对线性时间之牢狱、碎片式空间进行越界,使得过去、现在、未来融合成一点,读者和书写者可以同时感观到过去、现在、未来蜂拥而至的顿悟,从而达到“宇宙同步”。金波特运用注释对谢德的诗歌进行“学术强奸”,直接导致他所编造的异文,引诱出相关部分,他臆想强行从不相干的部分引出他自己想说的话,即使后来他添加的索引其中依然存在着漏洞、错讹。其原因在于金波特自我沉溺蒙蔽了他自己的双眼。他自己的编辑水平、客观原因造成的索引的疏漏和错误;金波特“住在凄凉的小木屋没有书房,而又为了赶快引证,金波特是在游乐场等嘈杂环境下完成的”[7]267。更重要的原因是金波特患有自大狂精神病,不时偏头疼,他的各种幻觉,受迫害幻想和恐惧如鬼魅般缠绕着他,影响着他的心智。最后纳博科夫让谢德在诗歌没结束的时候被死神无谓的戕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波特把谢德对死亡、灵魂探索的诗歌进行恣意解读注释,对于谢德用生命换来的诗歌进行野蛮的“学术强奸”。金波特近乎疯狂的天才注释与谢德长诗的温情思辩相映成趣,无论是诗歌还是注释都是多种人格、心灵的对照,无论是部分间反差和讽刺,还是内部的多层次和谐与统一都焕发出各自迷人的风采。
叙事角度的不确定性表现在谢德和金波特叙事的身份复杂性。这部明显分裂的小说有着互相并行,充满悖论的“中国套盒”式的故事,谁是真正的作者一直是学术界旷日持久的争论。谢德在诗歌开头运用“连雀”的阴影和“蜡翅鸟”隐晦含混的意象来暗示谢德之死像“连雀”,是误会的牺牲品,那么金波特也就等同于“蜡翅鸟”,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究竟谁是被暗杀的对象——是“连雀”、“蜡翅鸟”,还是他们的阴影?也许潜在含义是那只象征着谢德的“连雀”,活跃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一带的花园里;而金波特认为的“蜡翅鸟”活动范围是在“赞巴拉”,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罗斯北部地区。如果谢德是“连雀”的影子,金波特是“蜡翅鸟”,那么可以认为谢德是金波特明亮火焰的“微暗的火”。但是还有其他可能性:金波特宣称:“谢德的第1000行诗应该是第一行的重复,完成了结构的对称,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各有500行诗的中间部分,构成一对孪生意象”[7]14-15。谢德还是金波特是这部小说的始作俑者,没有正确答案,金波特所说的孪生意象让人想起纳博科夫迷恋的蝴蝶的两翼,然而他的目的却是把读者注意力转移到他的赞巴拉王国。他蹩脚的注释、主观臆断以及接近偏执狂般解码谢德长诗都暴露他注释的虚幻成分,他对诗歌的解码增加了《微暗的火》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镜子、反射、影子、替身、字谜、双关、回文和数字等具有幽灵般后现代主义意象造成谢德诗歌的现实性被金波特诡异的评注掩盖,如同辛辛那特斯的现实性被一个超现实但是确实可感知的世界所湮没。
三、创伤的幽灵:现实与想象并置造成家与非家幻觉并存
幽灵本身也有“怪异”(Uncanny)意义,因为“它们既对人性起到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人,但同时又是对人性的否认和干扰,是非人的存在”[14]132。 “幽灵是人又非人——既衍生于生前的人,却又不是那个人,而是他的‘他者’;它既活着却同时又死了,是一个活着的死人 (1iving dead)。”[14] 241弗洛伊德认为“怪异”揭示了人的心理状态中存在着“陌生和生疏感总是侵扰人对周围熟知和安全的心境”,也就是压抑复现”(return or 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8]55。“怪异”是被童明称作的“暗恐/非家幻觉”,它在德语中 (“Das Unheimliche”) 具有“家”(homelike) 与“非家”(unhomelike) 双重悖论式因素,也就是熟悉与陌生并存、家与非家幻觉相关联,二者构成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上的“怪异”。压抑复现的体验是以延宕的、不知不觉的方式在某个时间空间产生的创伤如幽灵般的复现,怪异理论经过德里达、拉康、克里斯蒂娃发展,在后现代文学中被广泛应用于后殖民、族裔和飞散文学中。纳博科夫因俄国革命的发生,从青年时期离开俄国,旅居德国、法国、美国等地,他的小说也主要以俄国侨民生活为主要素材,小说人物大都拥有流亡飞散的创伤烙印,他们原有的生活被切断,故国的往昔已疏离,现实和梦境交织或冲突,自我错位的思绪逐渐深化为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微暗的火》中两位主人公,谢德与金波特虽然人生经历不同:谢德是通过追寻死亡背后的世界来达到他对逝去亲人的缅怀,期待他们不是彻底消失,而是去了另外世界,他还会和他们在“来世”相见,从而摆脱他如影随形的孤独与儿时创伤;金波特却是通过对谢德的长诗近乎疯狂的注释,创造出他的理想王国“赞巴拉”来治愈由于流亡异乡产生的浮夸妄想狂与精神分裂。
谢德之所以毕生执着彼岸世界是因为他一生遭遇多次亲人创伤:婴儿时期父母离世,生活唯一依靠是莫德姑妈;女儿出生姑妈逝去,而后自己女儿自溺身亡,这一系列生活变故给他沉重打击。除此之外,他本人曾经有两次跨越生死疆界却没有真正死去的经历,使他愈加笃信来世的存在,并且终其一生来证实和阐释:死亡并非生命消亡,而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谢德在家庭和社会感受到的孤独,预示了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流放,一种形而上的禁闭意识。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诗人以他特有的方式执着于死亡世界的探索,他确信自己曾经死去,确信曾经体验过,看见过另一世界。这种感觉在他女儿海斯尔死后不久,他在一所学院做演讲,突然他的老毛病再度发作,他晕厥在一位医师的脚下。失去爱女的沉重打击不仅使得谢德真切的感受到死亡,并迫切想跨过那道界限,儿时亲人纷纷离散的创伤在此刻如幽灵般复现,“我爱的一切都以消散,却没有一条主动脉能表示遗憾”,这让谢德清晰的看到自己幻觉“在那黑暗的背景衬托下,清晰可见一座喷泉那向上高喷的白色水柱”[7]16。之后,他还特意驱车前往“见过死后世界”的女士去获取证据,结果令谢德大失所望,陷入绝望的深渊,“这里有一处误印,是山峦,不是喷泉”[7]18。从这次经历,谢德真正理解了生命中的秩序和设计,真正令他愉悦的生命奥秘,他终极一生都在死亡包围的世界中寻找意义之所在。直到谢德生命最后一刻,他宣称自己找到理解生存的真谛和坚持来世的存在,“我确信无疑我们会继续存在,我们的宝贝儿也会生存在某处,正像我确信无疑我会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二日醒过来”[7]24。写完这几行诗歌不久,谢德就死在突如其来的枪口下,并没有见到次日清晨的事实,这里面包含着明显的讽刺意味。但是在联系到谢德的人生境遇就有种悲凉的感受,在走过漫长的探索死亡历程,他领略到可以通过艺术而治愈自己伤痛,借助艺术可以达到永恒,女儿短暂痛苦的生命同样也会在自己的缅怀长诗中永生。正如纳博科夫曾经说过,“不朽只是一种油滑的诡辩,一种语言游戏,死也是一种风格问题”[15]241。
金波特错乱的思想和自私狭隘与谢德的善良敏感形成鲜明对照,但是金波特同样深陷在孤独与流亡创伤的泥潭里,唯一不同的是,谢德是采取诗歌创作来抒发胸臆和探索死亡与彼岸世界;而金波特是通过虚构代偿性的赞巴拉王国来缓解他的流亡伤痛。凯西·卡露丝在《无名的体验: 创伤、叙事与历史》中指出,创伤“是对一个或几个重要事件的反应,时间上通常滞后,表现为重复、幻想、梦幻或事件促成的思想和行为等形式”[16]32。和谢德一样同为大学老师,金波特虽然和谢德处在对立的两极,金波特疯狂,谢德清醒;金波特在身份上是流亡者,谢德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地方;他们的人生境遇也截然不同:如果说谢德是由于幼年失怙和疾病导致他陷入孤独的深渊,那么金波特则是由于他的俄裔流亡身份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而导致的边缘化,渴望融入美国社会和日益的孤独感蚕食着他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妄想狂(paranoia)。妄想症一般患者会呈现两种状态:自大狂(grandeur)和受迫害狂(persecution)。金波特的自大表现在他把自己当成国王,他营造出一个遥远的国度——赞巴拉来逃避现实空间的压抑。在金波特的幻想中,赞巴拉拥有漫长的历史,有真切的自然气候与山川地理环境,那里还有宫廷生活、乡野风情,甚至还有精神分析学。其中宏阔、真实的场面设计堪比“约克纳帕塔法县,或巴切斯特大教堂的院落,或者霍比特人的世界”,而这一切的中心就是查尔斯国王二世——查尔斯·金波特[17]102。虽然金波特总是隐藏自己真实身份,他的自大狂为他和周围除了谢德之外的所有人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陷入自我孤独的深渊。“一旦一个心智失衡的人高估了自己的价值,那么通常他把别人看作潜在的敌人就不远了。”[18]575他痛恨那些学者同事,把他们想象成赞巴拉推翻他统治的“影子派成员”,让金波特感到最深的恐怖是影子杀手格拉杜斯,“一辆汽车飞快的奔驰声犹如生命美好的解脱或死亡可怕的阴影古怪相混的到来,那阴影会出现我门前吗?那些幽灵般的杀手会来杀害我吗?”[7]326。影子杀手是金波特对周围蔑视目光的压抑和被日益边缘化的恐惧心理的化身,这种恐惧也是他自己所作所为——同性恋,这种恐惧感犹如幽灵般挥之不去,游离不定,他企图用构建赞巴拉王国来满足自大狂病症。在这虚构的王国里,查尔斯·金波特统治时期,众人投其所好,同性恋变成赞巴拉男人普遍的癖好,后来由于他的堕落引发国内革命迫使他离开故土来到美国华兹斯密斯大学,他依然遭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小说结尾,金波特在肉体上逃过影子杀手的暗杀,但是惶恐不安情绪如幽灵般抓住他的心灵,他真切感受到“孤独寂寞是撒旦的游乐场,我那种孤独和痛苦的深度无法形容”[7]16。在痛苦绝望中他已经靠寄生在谢德的诗作中让赞巴拉不朽,但是孤注一掷也彻底暴露他身份。虽然金波特表示希望还能继续存在,以别的方式存在下去,但是他流亡创伤导致妄想狂病症无法消除,自杀是使他最终解脱的方式。
小说《微暗的火》中谢德、海斯尔、金波特甚至格拉杜斯的结局都是死亡,这使得小说陷入恶魔般的黑暗,虽然小说主人公谢德与金波特处于截然不同的两极,但是他们的部分性格代表了纳博科夫的两面:谢德的渊博、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深陷孤独依然热爱生命是纳博科夫外在表现;金波特的自大与被边缘化的孤独、冷酷以及对艺术的接近天才的疯狂则是纳博科夫的内在。这样谢德如此容忍金波特怪癖和癫狂的谜团就迎刃而解了。其实纳博科夫的原型就潜藏在谢德和金波特的身上,时常借助他们之口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他原来是俄罗斯贵族,因为他父亲被误杀身亡和被俄罗斯其他政党迫害让纳博科夫被迫离开故土,过着流亡生活;准备定居德国时又因为妻子薇拉的身份遭到德国纳粹迫害再次陷入流亡生活中,他居无定所,被迫逃离柏林,辗转西欧,最后来到美国。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下他和谢德甚至金波特一样迫切想要发现生命的逻辑、主题,寻找并留住“我存在过的决定性证据”,而只有艺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19]31。纳博科夫把“赞巴拉”这个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王国作为自大狂妄的恶魔金波特的故国,纳博科夫运用精妙的艺术构思和良苦用心把黑暗、邪恶隐藏在光明、真理之下,道德与伦理的追求掩藏在这个狂欢、怪诞的虚幻世界的最深处。
四、结语
《微暗的火》是后现代的特技表演,是对生命与死亡、清醒与疯狂、希望与绝望、爱与孤独、隐私与分享、善良与自私、创造与寄生、天才与疯狂并存的视觉盛宴,也是灵魂震撼的发现之旅。幽灵意象的反复出现使得连接小说主题的虚构层次犹如中国套盒,追求真相成为幽灵般漂浮的能指,无限地被消解。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最终结局都是死亡,围绕着人物鬼魂意象内涵,揭示了纳博科夫对于艺术创作的理解,对于流亡生涯和失去亲人的伤痛,在小说《微暗的火》中都有对位性体现。小说中每个事实真相都闪耀着幽灵般的微光,拥有多重意义,蕴含着纳博科夫对生命与死亡的哲学思辨和真知灼见。纳博科夫正是通过对小说中“幽灵”的书写,以小说无序、混乱、不确定性来揭示出他生命在荒谬与悲剧、理想与现实、死亡与重生的越界中实现了对人生主题与文学主题的新书写。
[参考文献]
[1]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M].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89.
[2]Prescilla Meyer, Find What the Sailor Has Hidden:Nabokov’s Pale Fire[M].Middletown,Connecticu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3]Brian Boyd, Nabokov’s Pale Fire: The Magic of Artistic Discovery[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4]Wolfreys Julian.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5]张琼. 幽灵批评之洞察:重读爱伦·坡[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22(11).
[6]Nabokov Vladimir.Strong Opinions[M].USA:Penguin, 2013.
[7]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微暗的火[M].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8]Buse, Peter and A. Scott. Ghost Deconstruction Psychoanalysts History[M].New York: Macmillian Press Ltd. 1999.
[9]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天资[M].王家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0]王安.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空间叙事[J].俄罗斯文艺, 2012, (10).
[11]Friedman,Susan S.Spatial Poetics and Arundhati Roy’S T he God of Small Things,in Phelan,J. and P.J.Rabinowitz.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M].Malden and Oxford:Blackwell,2007,(12).
[12]何庆吉,吕凤仪. 幽灵、记忆与双重性:解读《献给爱丽丝的玫瑰》的怪异[J].外国文学研究, 2012, (6).
[13]Henri L. Michael J. E.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J].Antipode, London: Methuen, 1976,5 (2)
[14]Bennett, Andrew and Nicholas Royle,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ory[M].Harlow,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1999 .
[15]Vladimir Nabokov, Bend Sinister[M].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0.
[16]Herman, Judith Lewis.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Basic Books,1992.
[17]Périssé R. B. Solitude and the Quest for Happiness in Vladimir Nabokov’s American Works and Tahar Ben Jelloun’s Novel[J].Comparative cultures and literatures, 2003,19(1).
[18]Pekka Tami, Pale Fire in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M]. Great Britain: Routledge, 1995
[19]Derrida,Jacque.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M].trans.Peggy Kamuf.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 ledge.1994.
(责任编辑鲁守博)
[收稿日期]2016-04-2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重点项目“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异质空间研究”(SK2016A0469)。
[作者简介]尤丽娜,女,安徽淮南人,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外国语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16)04-00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