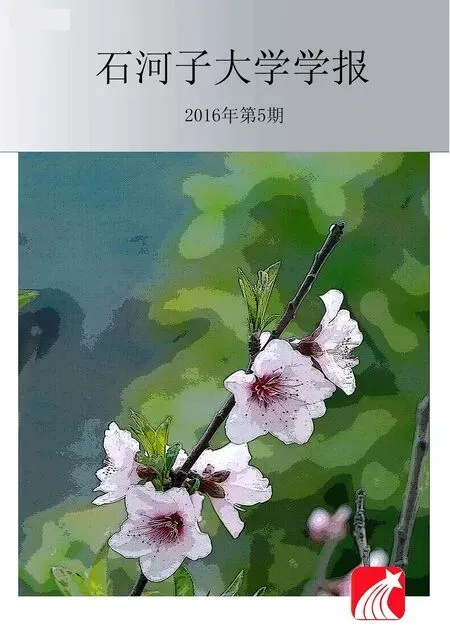不可译性:西方现代哲学的四个传统阐释
陈家晃,刘成萍
(四川民族学院英语系,四川 康定,626001)
不可译性:西方现代哲学的四个传统阐释
陈家晃,刘成萍
(四川民族学院英语系,四川 康定,626001)
不可译性不仅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西方现代哲学关注的对象之一。20世纪西方哲学的四大传统:解释学、分析哲学、解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对不可译性作了探讨。该文基于西方现代哲学的这四大传统,对《渡荆门送别》的汉语版本及三个英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指出这首汉语诗歌在进行英语转换时存在的不可译之处,进而表明不可译性在语言之间客观存在。
不可译性;解释学;分析哲学;解构主义;意识形态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61019.0139.032.html
可译性/不可译性是翻译研究中著名的悖论之一,任何翻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能的,与此同时,任何翻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不可能的,“可能/不可能同时存在”[1]9,可译性/不可译性这一悖论其实反映了“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2]18这一矛盾。需要指出的是,在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这一矛盾体中,不可译性往往受到忽视甚至否认。其实,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都是相对的,“不可译性绝非意指术语、表达、句法或者语法形式等,不译或者不能译,它揭示了翻译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有时只是表现为创造一个新词(neologism)或者把新义强加到旧词身上,这表明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任何词和概念系统都不能进行简单的叠加(superimpose)”[3]xvii。简言之,不可译性并非指翻译的绝对不可能性,它其实揭示了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表面上,这种差异性表现为语言形式本身的差异,但深层次上,却反映了不同民族借助语言来认识(认知)世界的差异。因此,不可译性绝非仅是语言学或者翻译学的研究内容,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其实,哲学与翻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转向”,哲学对不可译性的研究愈加关注,“哪里有不可译,哪里就有哲学,哲学对不可译性的回应,证明哲学日益进入翻译的研究领域。”[4]54本文拟对西方现代哲学关于不可译性的阐述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一首汉语诗歌的英译版本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指出不可译性在英汉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客观存在这一事实。
一、西方现代哲学对不可译性的阐述
单继刚认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主要包括四大传统:解释学、分析哲学、解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5]5。本文基于这四大西方现代哲学传统,对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进行理论梳理。
(一)解释学与不可译性
解释学(hermeneutics)源自古希腊神话人物赫尔墨斯(Hermes),他是宙斯的儿子,也是众神的信使。赫尔墨斯负责把宙斯及其他诸神的口信传达给人类。由于人和神的语言存在差异,因此,赫尔墨斯必须对神的旨意进行解释和翻译。源于此,hermeneutics本身就含有“释义、解释、阐释”等意思,也常被称为“阐释学”“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传释学”等。
解释和翻译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解释学的基础上,解释学翻译观也得以形成和发展。解释学翻译观的核心之一就是“翻译即解释”这一论断。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就解释和翻译的等同关系进行了多次论述,“每一个翻译,甚至是所谓的直译也是一种解释”[6]61,“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7]496。解释学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Gorge Steiner)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和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专门用第一章来论述“翻译即理解”这一观点[8]。解释学把解释等同于翻译的观点确有不妥之处。阿克塞尔·布赫勒把阐释的种类细分为12种,然而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阐释都与翻译活动的目标相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翻译不能被认为是任何一种阐释活动”[9]312。霍华德·桑基(Howard Sankey)也认为,解释不应该视为翻译,解释必须和翻译区分开来,不能翻译的语言表达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解释[10]6-7。笔者也曾例举了和合本《圣经》(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Bible)里的一些中文译名,比如吗哪(mana)、基路伯(Cherub)、没药(Myrrh)、中保(Mediation)等,来说明解释并不等同于翻译,能够解释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能够翻译[11]85。
此外,解释不能消弭语言间的差异,因此,解释无法避免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实际上,解释学非常重视语言间的差异性,认为正是差异使事物得以彼此区分并显得有趣甚至具有审美的魅力,而且,理解也正是开始于解释学上的差异。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一切解释的对象,始终是某种生命的表达,如果这一生命表达完全是陌生的,解释就根本不可能,如果这一生命表达中没有任何一点陌生的东西,解释就完全不必要[12]31。解释学的翻译观重视不同语言之间的语际翻译。伽达默尔曾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解释学这一名称的起源,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在此处理一种语言的事件,处理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翻译,由此也要处理两种语言的关系。”[13]476而斯坦纳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和翻译的诸多方面》更是强调语言差异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而“通天塔”(Babel,又译巴别塔)一词源于《圣经·创世纪》,意为“(语言的)变乱”。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尤其是语言之间存在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往往会导致不可译性的发生,正如王宾所言,“只要人不升格为神,只要人类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净化为‘纯语言’,那么,‘不可译性’的难题就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展示自己的存在”[14]87。
最后,解释具有局限性,而解释的局限必然导致翻译的困顿。解释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神圣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柏拉图以来,诗歌被认为是天才的非自觉创作,是未曾预谋的、自动发生的和非关理性的,即一种并不按照诗人意图和自觉思考而发出的“天籁”,因此,诗歌就需要解释者来阐明诗人们的意思[12]4。因此,解释学被看作是一种有法可循、被用来探索和阐明作者在写作活动中懵然不懂的东西的理解艺术[12]13。解释学既要理解和阐释文本再现的意思,又要搞清和体悟作者的思想和意图。为了使解释学“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15]244,并“随时随地地进行(正确的)解释,从而消除误解”[16]110,解释学者提倡利用“(文本)语法”“历史”“成见(传统和权威)”“心理”等主客观因素,然而,这些因素恰恰表明人的理解和解释能力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人的解释能力毕竟有限,“所有的解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实现其使命,因为所有的理解都始终是局部的,永无止境的,个别甚至是无法言喻的。”[15]243解释的局限性也让解释学陷入循环论的深渊,因为所有解释者认为对文本意思或者作者意图的“正确”解释,都不过是解释者自己的解释而已,结果,“当我们追问真理的时候,我们必然已经陷入解释学境遇的樊篱之中。成见、传统、权威、效果历史、理解的应用结构,使得我们往往对文本意义的认识达不到一致”[5]53。当理解和解释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制约而陷入困境时,解释学者视为等同关系的翻译肯定也会陷入迷失的境地。大卫·伊文斯(David Evans)也曾就解释学的翻译观提出疑问,“如果我们缺乏理解,我们又如何翻译呢?如果不能翻译,我们又如何明白呢?”[17]231
(二)分析哲学与不可译
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的语言转向,英美分析哲学(Anglo-American analytic philosophy)得以孕育而生,并成为与欧洲大陆学派(Continental School)并驾齐驱的两大哲学流派之一[18]335。
分析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次变革,这种变革的标志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y),并用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语言。因此,分析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研究方法是分析,研究目标是通过分析语言来认识世界(存在)。20世纪中期以来,分析哲学家开始更加关注指称、命题、真值、言语行为、意图等问题,开始从自然语言出发,分析语言的表现形式,进而揭示语言本质及其语言所反映的世界(存在)[19]26。
哲学与翻译历来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析哲学也不例外。分析哲学代表人物马蒂尼奇认为,分析哲学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语义学、语形学和语用学[20]2,然而,一旦分析哲学把翻译纳入其研究范畴时,“众多分析哲学家,比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罗素(Russell)、奥斯汀(Austin)、奎因(Quine)、卡维尔(Cavell),试图对欧洲哲学词汇进行确切解释和翻译……(但最终)却陷入文化和语言不可译的深渊”[21]588。
其实,分析哲学如果仅仅是通过研究某一门语言来研究世界(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那无可厚非,然而,语言、翻译、哲学这三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旦分析哲学把翻译也纳入其研究范畴时,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甚至不可通约性),尤其是语义、语形、语用差异,必然给语际翻译带来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不可译也就在所难免。
语义一直是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语义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分析哲学关于语义研究也取得诸多成果,提出“指称论”“真值论”“图像论”“用途论”“行为论”等语义理论,而这些理论恰恰也证明语义的复杂性。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奎因在其著作《词与物》(Word and Object)就干脆提出“语义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meaning)观点,并宣称“语义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翻译的不确定性”[22]。此外,不同语言之间的语义存在不对等,势必也会导致翻译困境,甚至不可译,就英汉两种语言来说,汉语中的“阴阳”“八卦”“道”“风水”等在英语中都找不到语义完全相对等的词。
如果说语义差异导致的不可译性往往是相对的话,那么,语形差异导致的不可译性就通常是绝对的。语形包括语音和字形,它们都是人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语音中的“双关”“头韵”“尾韵”等,以及语形中的“颠倒字面顺序而构成的词(anagram,如desperation:a rope ends it)”“藏头诗(acrostic poetry)”“回文(Palindrome,如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等往往只能翻译意思,而不能兼顾语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汉语中的象形字“山”和“月”,分别翻译为英语的“mountain/hill”和“moon”,只能译出部分意思,而语形却完全无法译出。
语言之间的语用差异也会往往导致不可译。语用研究使用中的语言,与语境和含义紧密相联,语境涉及语言交际发生的时间、地点、交际双方、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而含义除了基本的语义之外,还涉及言外之意(implicature)及意图(intention)等因素。比如“关系”一词,美国的《侨报》和《纽约时报》都译为“Guanxi”,而不是“relationship”,在西方媒体看来,“关系”指“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带有“拉关系、走后门”等贬义色彩,其批贬的语用含义不言而喻。
(三)解构主义与不可译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它是在结构主义阵营内部并以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和拆解开始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保罗·德曼(Paul de Man)、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解构并不是摧毁,而是颠覆,是一种对规范化、模式化的抵制,是对中心和权威的反叛,尤其是对西方传统哲学一直倡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颠覆。结构主义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往往把意义和实在的法则视为不变之物,并将其作为思想和认识的中心,而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并不像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透明的、清晰的,包含着明确的二元对立的稳定结构,它更像一个意义之网,无限展开,无限变化,无限循环,任何东西都不会由语言符号清楚地表现出来[23]427-429。
解构主义反对文本的完整性及意义的稳定性,认为文本是开放的,意义是流动、丰富的,因此,也反对传统翻译的“等值论”和“二元对立论”:译文不是原文的附属物,也不是简单忠实地对原文的复制物。因此,解构主义认为,翻译绝不是实现译文对原文忠实的再现或者复制,而是“有调节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24]4。由于翻译的调节转换,以前静态、封闭的文本变成动态、开放的,原文经过翻译转换之后,意义能够推陈出新,原文也能够实现投胎转世,并在新的语境中成长和再生。
解构主义其实解构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语言的差异性。德里达创造性地提出“异延(différence)”一词,它既指差异和区分,又指延期或推迟,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一种异延行为,上帝创造意义本身,也创造了多义的名词,同时播撒了语言,使文本陷入多义解释的困境[25]4;福柯反对结构主义重语言轻话语的研究,他认为话语具有更丰富复杂的意义,而话语又与权力密切相关,权力是各种力的关系,它使话语形成系列或系统,抑或彼此独立的差距与矛盾[26]345;而罗兰·巴特更是以《作者之死》为文章名,来宣告读者的诞生以及作者的死亡,进而表明文本意义的多变性及不确定性[27]。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及语言的差异性,这必然给不可译埋下伏笔。德里达曾经说过:“事实上,我相信任何东西都是可译的,同时,也是不可译的。”[28]在解构主义视角下,“不可译性不意味着译者不应该翻译,而意味着在遵守‘数量’法则下,在译文中创造原文本的多样性是不可能的。”[29]537因为,首先,在解构主义看来,任何语言和文本的意义都在延异和变化,因此是不确定的,而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解读也是无穷尽的。其次,语言之间巨大的差异性也使译文不可能穷尽原文中的多样性,德里达甚至用巴别塔来喻指翻译的矛盾性,他认为巴别塔的故事讲述了“语言混乱的起源,习语不可简约的多元性,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作为不可能性的必要性”[2]18,显示了上帝“既强行翻译又禁止翻译”[2]17矛盾心态。
(四)意识形态与不可译
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而意识形态(ideology)是这门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三种:最广义的意识形态,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观念、思想的总称;以认识论为标准加以辨析的狭义的意识形态;以历史观为标准加以辨析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某个阶级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向大众灌输的具有引导性的思想、观点等[5]211-212。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阶级密不可分,不同的社会、历史、阶级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会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之中,从而深刻地影响甚至操纵翻译。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Erich Fromm)把意识形态学看作是“社会过滤器”(social filter),“社会过滤器决定哪些思想和感情能达到意识的水平,哪些则只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的层次”[30]93。语言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作为语言转换的翻译,理应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制约,甚至操纵。基于意识形态与翻译存在的紧密联系,Fawcett率先直接提出翻译意识形态(translational ideology),后经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等英美学者的发展,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理论最终得以形成[31]149-152。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及操纵,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不可译。美国著名学者艾米丽·埃普特(Emily Apter)曾把不可译归因于世界观认知的差异,她认为不同民族的世界观(意识形态)的差异会导致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解读差异,从而会导致不可译性现象的产生,比如,Pravda一词,因其曾作为前苏联政府掌控的官方报纸的名字(《真理报》),从而烙上了鲜明的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印迹,因此,Pravda这一词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是不可译的[22]581-598。
二、个案分析:《渡荆门送别》汉英译本对比
《渡荆门送别》是李白年轻出蜀时所作,本文所选此诗的三个英文译本分别来自许渊冲[32]26,叶维廉(Wai-limYip)[33]239和大卫·欣坦(David Hinton)[34]9,下文分别简称为“许译本”“Yip译本”和“Hinton译本”。笔者拟结合上文四个西方现代哲学传统,具体分析此诗中的不可译因素。
《渡荆门送别》
李白
渡远荆门外,
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
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Farewell beyond the Thorn-Gate Gorge
Leaving Mount Thorn-Gate far away,
My boat pursues its eastward way.
Where mountains end begins the plain;
The river rolls to boundless main.
The moon,celestial mirror,flies;
The clouds like miraged towers rise.
The water that from homeland flows
Will follow me where my boat goes.
(许渊冲译)
Crossing Ching-Men Ferry to See a Friend Off
We cross over the distant Ching-men
To travel in the land of Ch’u.
Mountains end with vast plains.
River flows into the great beyond.
Moon falls,a mirror flying across the sky.
Clouds grow,weaving terraces above the sea.
Deep love of hometown waters;
A million miles to see your boat go.
(Wai-lim Yip译)
At Ching-Men Ferry,a Farewell
Crossing into distances beyond Ching-men,
I set out through ancient southlands.Here,
mountains fall away into wide-open plains,
and the river flows into boundless space.
The moon setting,heaven’s mirror in flight,
clouds build,spreading to seascape towers.
Poor waters of home.I know how it feels:
ten thousand miles of farewell on this boat.
(David Hinton译)
(一)语义不可译
王宾认为,应该重视汉语的聚合关系,汉语中调位的(tonemic)和表意的(ideographic)特征是区别汉语与其他语言的主要因素,这两个因素往往会导致汉语译为其他语言的不可能性。汉语中的调位不同于英语中的音位(phoneme),英语中的音位具有区分意义的功能,而汉语中的调位虽没有表意功能,但会决定汉语的平仄和韵律,并使汉语的几乎每个词成为同音异义词,比如,《渡荆门送别》中的“渡”,就蕴含“穿过”“渡河”“渡船”“摆渡”“渡口”等义。此外,汉语中的每个词不受人称、时态、语态、性别、数、词缀、语气等约束,这一表意特征使汉语词语承担了词位(一般含义)和语素(特殊含义)的双重功能。“其后果之一,是每个词(语素)在组合段的词性/词义,不像英语那样受到来自聚合段的较严格的逻辑约束,常常可以在不变词序的前提下,改变词性/词义,从而读出不同的句段含义来”[1]11。
在这首诗歌中,由于汉语聚合关系中的调位和表意特征,词语含义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表露无遗,这里仅以此诗歌的标题为例进行分析。这首诗歌标题有三个词(语素),即“渡”“荆门”和“送别”,这三个词语义丰富,“渡”,蕴含“穿过”“渡船”“摆渡”“渡河”“渡口”等义;“荆门”,是指“湖北荆州汉水以西50公里之外的古荆门城”,还是“包括古荆门城和汉水及其支流、孕育楚文化的广阔之域”,抑或“楚蜀咽喉之称的荆门山(今湖北宜都县西北,长江南岸)”;而“送别”一般含有“与(友人等)……送行告别”之意,但“诗中并无送别朋友的离情别绪,诗中无送别之意,题中二字可删”[35]303。此外,这三个词(语素)构成的标题,又可以看作是多种可能关系的组合,具体如下:
1.“渡”视为动词,“荆门”视为名词,“送别”视为动词,做“渡荆门”的目的状语,因此组合成:渡荆门(动宾)+送别(目的状语)。Yip译本偏向此关系组合,“渡”意为“渡过,越过”,而“荆门”只是音译,未指明具体含义,“送别”意为“与友人的送行告别”。
2.“渡”视为动词,“荆门”视为名词,“送别”视为名词,只不过“渡荆门”相当于形容词词组,修饰“送别”,因此组合成:渡荆门(定语)+送别(名词)。许译本偏向此关系组合,“渡”意为“渡过,穿越”。不过,许渊冲先生用英语介词“beyond”来译汉语动词“渡”,“荆门”意指“荆门峡”,“送别”意为“道别,再见”。
3.“渡”视为名词,“荆门”视为名词,“送别”视为名词,只不过“荆门”修饰“渡”“渡荆门”相当于一个介词词组,修饰“送别”,因此组合成:渡荆门(地点状语)+送别(名词)。Hinton译本偏向此关系组合,“渡”意为“渡口”,而“荆门”只是音译,未指明具体含义,“送别”意为“道别,再见”。
4.“渡”视为动词,意为“穿越”,“荆门”视为名词,意为“荆门山”,“送别”视为动词或名词,只不过“送别”在标题中并无实际意义。因此,这种关系组合为:渡(动词)+荆门(宾语),题目可译为“Crossing Jingmen Mountain”。
显然,“渡荆门送别”的汉语语义远丰富于三个译本的英语语义,三个译本的英语题目不能完全表达汉语题目意思,不可译性表露无遗。首先,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汉英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及汉语语义的不确定性在这首汉语诗歌的题目上得以体现:汉语独特的聚合关系,尤其汉语独特的调位和表意特征,完全有别于英语,加之汉语诗歌语言的高度凝练,必然造成汉语诗歌词语以及由词语构成的语段的“语义不确定性”,而且,随着对汉语古诗歌进行更深刻的解构分析,词句意义往往能推陈出新,汉语古诗歌语义的不确定性就愈发明显,这使汉语与其他语言进行等同的语义转换几乎变得不可能。其次,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无论解释学的学者怎么充分利用“(文本)语法”“历史”“成见(传统和权威)”“心理”等主客观因素,都无法消除汉语诗歌的“语义不确定性”,也无法用英语完全译出汉语诗歌词句的丰富含义。最后,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此诗歌汉语标题除了上文分析的语义之外,是否还蕴涵特殊的语用含义或者“言外之意”,诗歌题目是否蕴涵作者首次出川远游的兴奋之情,或是对“楚国故地”的向往之情,抑或远离故乡的伤感之情?毕竟“渡”“荆门”“送别”等字眼承载太多中国文化与意象。
(二)语形不可译
语形包括语音和字形,是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语形的差异往往也会导致不可译性。《渡荆门送别》是一首五言律诗,即诗歌每行五字,且遵循一定的韵律格式。全诗韵律结构如下: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而全诗的押韵遵循“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原则,押韵格式可标注为:abcbdefe。
汉语的五言律诗无论韵律还是押韵格式都有别于英语诗歌,这让汉语五言律诗的英译变得困难重重,而且五言律诗的语形往往是不可译的。从《渡荆门送别》的三个英译本来看,英译诗都无法体现汉语诗歌的语形特点:许译本想尽量反映原诗的一些音韵特征,但差异还是很大——原诗每行五个字,许译本每行差不多六个字,原诗第二行和第四行押同一尾韵,第六行和第八行押同一尾韵,而许译本是相邻两行押同一个韵;Yip译本和Hinton译本无论是字数还是押韵都比较自由;此外,这三首英译本都没有采用固定的韵律和节奏来体现原诗的韵律。
显而易见,这首汉语诗歌的语形特点完全不能在英语译文中得以体现,这说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差异性,而无论是解释学、分析哲学,还是解构主义都承认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汉英两种语言当然也不例外;而且,这三种西方现代哲学传统为分析英汉语形差异的表现及原因提供了更深和更广的视角,进而揭示英汉语言转换过程中,语言语形不可译的客观存在。
(三)意识形态不可译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是对世界存在的认知和反映,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有所不同,意识形态也有所差异。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差异,必然体现在语言表达上,而作为高度凝练语言艺术的诗歌也必然承载民族不同的意识形态。
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重感性和悟性,语言表达与分析重意不重形。语句不拘泥于形式结构,语法呈隐性,注重心理意会。语句表达时抛弃了可有可无的形式束缚,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比如时态、语态、性数、连词等,有时甚至省略主语,这些语言形式在表达中往往“不在场”。而西方人认知世界重理性,语言注意形态的外露,拘谨于结构成形、形式完整,语句拘泥于形式结构,语法呈显性,比较刻板,注重以形达意,主语、时态、语态、性数等语言形式不可或缺,这些语言形式在表达中必须“在场”。
中西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渡荆门送别》的中文版本和英文译本上表露无遗。原诗中主语、时态、语态等都不在场,“谁渡荆门?”“送别谁?”“何时渡荆门送别?”等诸多问题在原诗中并没有直接表明。然而,《渡荆门送别》的三个英译本都有明确的主语和时态,具体指明送别的主体及时空:三个英译本都采用一般现在时态,而送别的主体都是第一人称,只不过许译本和Hinton译本是第一人称单数,而Yip译本是第一人称复数。
《渡荆门送别》的汉语版本与英译本存在主语和时态“不在场”和“在场”的巨大差异,这种语言表达的差异体现了中西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反映中英两种语言存在着不可译性。无论解释学如何解释,解构主义如何解构,都无法弥合中西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比如,就《渡荆门送别》英译本中的送别主体而言,许译本和Hinton译本采用第一人称单数,而Yip译本采用第一人称复数,这反映了译者对原诗中“不在场”主语的不同解释和解构,原诗与英译本的差异表露无遗,不可译也可见一斑。
不可译性是翻译研究与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反映了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已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哲学思考。本文通过《渡荆门送别》的汉语版本与三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分析,揭示了英汉诗歌(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汉语诗歌(语言)中的一些语义、语形、及诗歌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都无法在英语译本中得到相对应的体现。英汉两种语言存在的不可通约的差异,往往会导致英汉转换的不可能。虽然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解释学、解构主义、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都积极地介入不可译的研究,但他们都无法解决不可译性这一难题,相反,他们从不同的哲学视角论述或证明着不可译性的存在。
[1]王宾.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J].中国翻译,2001,(3).
[2]雅克·德里达.巴别塔[M]//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Cassin,Barbara,translation edited by Emily Apter et.al.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A Philosophical Lexicon[M].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4]Apter,Emily.PhilosophicalTranslationandUntranslatability:Translation as Critical Pedagogy[J]MLA Journals Profession,2010:50-63
[5]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伽达默尔.文本与解释[M]//严平.伽达默尔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8]Steiner,Gorge.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9]阿克塞尔·布赫勒.作为阐释的翻译[M]//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Sankey,Howard.In defence of untranslatability[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0(1).
[11]陈家晃,周心悦.解释学视域下的不可译性[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6).
[12]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3]伽达默尔.美学与解释学[M]//严平.伽达默尔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14]王宾.“不可译性”面面观[J].现代哲学,2004,(1).
[15]Dilthey,Wilhelm,Hermeneutic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M]. Eds.R.A.Makkreel and F.Rodi.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1996.
[16]Schleiermacher,Friedrich.Hermeneutics.TheHandwrittenManuscripts.[M].Ed.Heinz Kimmerle.Trans.James Duke and J-ack Forstman.Montana:Scholars Press,1977.
[17]Evans,David.Semantic Antipluralism:How to Translate Terms in Philosophy[J].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08(16).
[18]Dasenbrock,ReedWay.PhilosophyAfterJoyce:Derridaand Davidson[J].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2006,(2).
[19]陈家晃.分析哲学视角下的不可译性[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5,(1).
[20]A.P.马蒂尼奇.语言哲学[M].牟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1]Apter,Emily.Untranslatables:A World System[J].New Literary History,2008,(3).
[22]Quine,Willard.WordandObject[M].Cambridge:TheMIT Press,1960.
[23]董学文,西方文论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4]Derrida,Jacques.Positions[M].Trans.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25]刘军平,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六个维度及其特点[J].法国研究,2009,(3).
[26]米歇尔·福柯:求知之志[M]//杜小真.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
[27]Barthes,Roland.The Death of the Author[A]Richard Howard,TheRustleofLanguage,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1989.
[28]Derrida,Jacques.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Trans.Lawrence Venuti[J]Critical Inquiry 27,2001.
[29]金敬红.解构“不可译性”[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30]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1]孙志祥.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证[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32]许渊冲.李白诗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33]Yip,Wai-lim.ChinesePoetry:MajorModesandGenre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6.
[34]Hinton,David.The Selected Poems of Li Po[M].New York:New Directions Books,1996.
[35]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李登叶)
On Untranslatability:A Study from Perspectives of Four Western Mod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and a Case Study
CHEN Jia-huang,LIU Cheng-ping
(English Department of Sichuan Minzu College,Kangding 626001,Sichuan,China)
Untranslatabilityisthefocusforbothtranslationstudyandwesternmodernphilosophy. Untranslatability has been profoundly studied by four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20th century,namely,Hermeneutics,AnalyticPhilosophy,Deconstructionism,andMarxism(Ideology).Thepaper,basedon these four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makes a contras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version and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Du Jingmen Songbie”,explicitly exhibiting untranslatability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untranslatability;hermeneutics;analytic philosophy;deconstructionism;ideology
H059
A
1671-0304(2016)04-0112-08
2016-06-20
时间]2016-10-19 1:39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不可译性探究:西方现代哲学视角”(14SB0274)。
陈家晃,男,福建邵武人,四川民族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与翻译研究。
——以山顶度假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