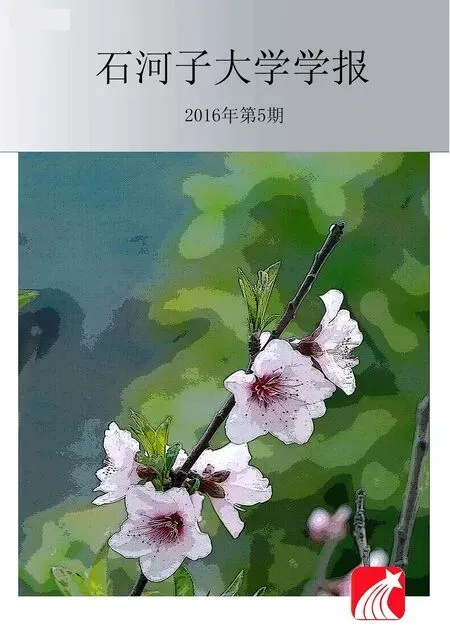论新疆生态批评的可能性
胡新华,马小慧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新疆当代文学论坛】
论新疆生态批评的可能性
胡新华,马小慧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新疆生态批评的建构,旨在针对新疆文学创作中所表达的生态意识,提炼出新疆各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形成一套属于多元文化视域下的生态批评话语。大体而言,新疆生态批评的可能性,可以从生态批评理论形成的现代性思潮、新疆生态客观环境的现实变化、各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及新疆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生态批评;生态;新疆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61019.0117.016.html
论及新疆生态批评的可能性,事实上是在学理层面补建一个生态批评的框架,对新疆而言,生态意识的形成是与客观自然环境的脆弱性紧密相关的,即在干旱与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生态保护意识是天然而生,若非如此,人类只能面临着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最终导致现有绿洲的退化,成为荒原。正是这种客观性,就决定了新疆各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存有大量的关于生态保护或者反思生态的作品,无论自发与自觉,均是对自身居住环境的关注与焦虑,也是面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反思,实属现代与前现代的博弈。也就是说,具体到新疆生态文学可能性建构上,现代性的反思,环境及现实条件下的生态变化,多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作家的作品创作及批评,是纳入考察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基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作为世界性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按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自17世纪以来一直发挥着作用,就其表现上讲,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发达,政治民主自由是它的主要方面,在这些要素中,现代性的核心要义就是人类自身主体性的发现,并进而在时间观念,政治诉求(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人类主体的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上提出了具有启蒙性质的要求。因此,现代性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在人类主体性的主导下势必涉及到脚下位置的拓展,在空间里更广更深地发掘资源,提升技术,攫取物质,满足自我在生活方面的需求。我国的现代性发展尽管晚于西方,但在价值取向上没有变化,是在摆脱封建社会束缚后的个性发展。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的诉求一直在现代性精神的指引下发展,且变得愈发强烈,很明显地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辩证地讲,现代性发展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人类自身的解放意义重大,但从生态学的角度讲,人类自身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向现代模式改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另一套逻各斯中心主义,摆脱束缚而发展的另一面则使人类居住的环境,自然资源面临着破坏与枯竭,是社会迈向进步的表征,也是生态系统遭受重要改变且无法规避的因素。正如S·N·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一书中明确指出的“人的自主性相应地受到了强调,这构成了这一方案的深层核心。这是他的或她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是指,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断扩展个人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扩展人的活动创造性与自主性”[1]70。在这里,S·N·艾森斯塔特强调的是能动性开放层面上的积极性与潜在破坏性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对现代性发展中的反思需要予以重视的内容也是S·N·艾森斯塔特所关注的核心部分,即反思人类自身的探索意识和对自然控制及人类精神生态的处理。实际上,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的“合目的性”开始,人类把外在自然就作为了满足自我生存与发展的攫取对象。经济、生存、科技发展甚至美学都是自然必须担负的中心圈价值。在这些功利性目的之下,导致的是人类欲望的膨胀和自然的祛魅。“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2]48。韦伯说的这种价值莫过于自然的破坏与人性的异化。这种态势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里,均在不同程度上发展。针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也正在努力纠正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自身价值或主体性诉求的实现同自然的和谐共存,如何协调、合理地利用自然成为焦点问题,究其实质,仍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下的权宜调整,这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采取的策略。重要依据是恩格斯的经典论断:“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3]518
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历史来看,世界上目前的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都有一个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自工业文明出现之初,这个矛盾就一直存在,高度的发达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诸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我国也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经济与政治文明的建设已经具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家从现实出发,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自然资源肆意攫取、环境严重恶化的代价有了重要认识。
具体落实到新疆,则必须重新审视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政策,孰轻孰重,或者将二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需要从客观情况中出发予以考量。新疆因地处西北,地缘不占优势,在国家改革开放发展以来的宏观设计中,“率先发展东部”与推进中西部开放策略使新疆处在前现代与现代交融的状态中,生态环境尚处在可控范围之内,人文精神也未有大的改变,但随着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疆作为重要的资源产地受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矿产的开发与冶炼,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人心愈发浮躁,忽视了生态与人同为有机圈层这一概念的认识。新疆的生态在现代化建设中也走上了某些发达地区“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这对生态脆弱的新疆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因此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笔者以为在理论层面,占据第一要位的则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的发展无可厚非带来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的高速发展,但“人类中心主义”方面的人类特权或优先权利也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于此,现代性的反思应该不断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使自然与人类不断达成圆融状态。我们相信,具有批判意义的现代性精神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势必会找到更好的途径。生态批评的任务也在提醒着现代性理论批判精神发挥作用。
二、基于新疆生态环境的客观状况
在地缘的角度上,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部,西南方向有帕米尔高原,南与青藏高原相邻,东北方向是蒙古高原,与内地接连的东部是同样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甘肃,遍布戈壁荒漠。这种地理位置,使新疆的地形、地貌,土壤水文,气候条件等形成了多样化的特点。地形地貌中的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即所谓的“三山夹两盆”。这些地貌夹缝中,冰山、草原、绿洲、沙丘、荒漠、戈壁造就了绮丽多姿的风景,也形成了迥异的生活情形,但需要指出的是“三山夹两盆”的地貌构型指向另外一个关乎切身实际的问题,那就是生存与生活中如何处理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毕竟夹缝的形态是较为封闭的,高山环列的雄伟背后是湿润的隔离——海洋性气候被阻隔在外,“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大体就是这种情形。那么因地理位置、地形形成的大陆性气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夏季炎热,冬季酷冷,尤其是降水极少,干燥难耐。那么在这种气候条件影响下,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想而知,并且以不断恶化的趋势发展,“根据国家遥感普查统计资料,到20世纪末,新疆土地沙化面积以每年近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许多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河流和湖泊,已经基本断流或干涸,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流动沙丘每年以5米左右的速度向绿洲推进,沙漠面积一直呈现不断扩展的趋势,风沙危害日益严重,以塔里木盆地为例,沙漠面积33.7万平方公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扩展83平方公里”①新疆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四分之一[EB/OL].中国新闻网,http://news.sina.com#cn/c/306036.html,2001-07-19.。可以说,新疆生态环境的现状不容乐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碱地扩大,草地不断缩小,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等。其中,有自然的客观原因,但人为因素也占据了很大比例,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对新疆资源的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又造成了水土、大气、植被的破坏。2002年,李新琪在其研究中曾将新疆生态环境质量划分为五个等级并作综合评价。“Ⅰ级区”,指的是生态质量为优的地县,其中主要在新疆北部,计10个县市,如布尔津县、巩留县、新源县、特克斯县、霍城县、哈巴河县、昭苏县、尼勒克县、伊宁县、阿勒泰市,在新疆的县市单元中占据约12%的比例,面积占约4.85%;“Ⅱ级区”中的县市为环境良好地区,有11个县市,其中面积占据7.57%,主要的县市是察布查尔县、裕民县、乌鲁木齐市、额敏县、和静县、乌苏市、呼图壁县、昌吉市、库车县等;在“Ⅲ级区”中,环境质量的评估为一般,有23个县市,占全疆面积的16.06%,其中有被联合国誉为“人居环境改善良好城市”的石河子市;“Ⅳ级区”是生态环境质量差的地区,主要为新疆东部、南部的各大县市,如莎车县、库尔勒市、疏勒县、乌什县、岳普湖县、和硕县、阿图什市、阿克苏市、巴楚县、福海县、皮山县、疏附县、和布克赛尔县、阿瓦提县、和田市、麦盖提县、吐鲁番市、沙雅县等29个县市,占全疆面积的32.74%;“Ⅴ级区”为环境恶劣地区,包括英吉沙县、策勒县、尉犁县、伊吾县、若羌县、托克逊县、且末县、洛浦县、柯坪县、墨玉县、鄯善县、哈密市,共计12个县市,占全疆面积的38.78%。以上数据表明,在新疆,环境质量评估差与恶劣的Ⅳ、Ⅴ级区中包括县市有41个,占全疆县市总数的48.24%,“表现为林地、草地生态覆盖率较低;水域、湿地面积较小,各种荒漠化土地面积大,生态恶劣区比例较高,景观多样性中等,耕地、草地有一定程度的退化,综合评价等级为差。”[4]85
时隔多年,新疆生态环境建设尽管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任重道远,“十二五”规划期间:
“全区森林覆盖率由‘十五’期间的2.94%提高到4.02%,绿洲森林覆盖率由14.9%提高到23.5%。沙化土地年扩展速度由‘十五’期间的104平方公里减少到82.8平方公里。退牧草原达876万公顷,草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各类型湿地面积达148万公顷。继续实施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累计向下游输送生态水24亿多立方米,下游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缓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等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区域开展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生态修复示范面积达到2.4万公顷”①新疆环境保护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保护“十二五”规划[EB/OL].http://www.dowater.com/info/2012-09-03/101346.html。。
这种严峻的形势也提示我们,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相互博弈,既是经济发展的悖论,也是对根深蒂固的“人定胜天”思想的突破,实现一个生态学意义黄金分割式的完美、和谐建设与发展,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在生态十分脆弱的新疆:“我们不仅一定要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而且也一定要作为整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仅与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国人和我们的文明社会具有某种形式的同一性,而且我们也应对自然的和人为的共同体一道给予某种尊敬。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通常字面意义上所讲的‘一个世界’,它也是‘一个地球’。没有对这种事实的了解,拒绝承认文明世界各个部分之间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就无法更成功地生活。”[5]389-390
三、基于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生态思想
众所周知,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塔塔尔族等,各民族均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交汇、交融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生态建设的共性文化。汉民族的生态思想源远流长,儒家、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影响深远,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古代的生态思想被当成生态理论建构的资源被重新挖掘整理。如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刘青汉主编的《生态文学》及《论生态文学的价值系统》等,都将研究的视野回归古代传统文化,包括季羡林、汤一介、张岱年等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也均对中国思想中占据主要位置的儒道两家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了深度阐释,为生态理论提供可供借鉴的线索,尽管儒家与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点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达成自然和谐、平等对待人与非人物种的生态伦理境界,实现万物和谐统一。
作为世居新疆的主要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在传统文化中也同样具有富有实践意义的生态伦理,稍有不同的是维吾尔族的生态思想还体现在宗教信仰中,与汉民族的哲学体系更具有广泛意义,并在心灵世界中形成一种敬畏感:“崇尚自然、敬畏生命,以绿洲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前提,承认大自然的完整与多样性,以道德力量减少或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与自然共生共存。”[6]“建立在绿洲文化基础上的维吾尔传统文化,在祖国西北新疆地区对人类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人与绿洲耦合关系的绿洲民俗文化模式。……应该说人与绿洲的自然共生关系是维吾尔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6]。要而言之,维吾尔族所在的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他们整个生存与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讲,维吾尔族的生态思想比纯粹的学理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在维吾尔族的历史中,先民的自然崇拜,回鹘时期的宗教信仰(佛教、摩尼教、祆教、萨满教等),10世纪左右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具体的生活实践是其生态思想的根源,并保留在历史典籍中或经书中,如《乌古斯传》《回鹘医学文献》《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等,逐步形成一套具有民族特征和地域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
而主要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族更是对生态有着深刻体验,既有着宗教的因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之也具有了生态保护的处身性认知。游牧主要是“人类对于干旱或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主要在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一条以植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人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在畜牧生产中,人类虽然没有对生态系统进行根本上的改造,却能巧妙地对之加以积极地利用,牧民们可以在尽量长的时间里,通过有规律的‘转场’把畜群牧放在生态系统的能源输出口——青草地上,从而达到以较大的活动空间来换取植被系统自我修复所需时间的目的。在人、牧畜、草场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牲畜—草场—人。人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在协调三者关系上人的生态观念、生态意识发挥着主导作用”[7]。哈萨克族牧民的转场根据四季气候变化和生态特征,有效地实现生态平衡,游牧生活的这种流动性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哈萨克族流传着这样的俗语:“草场是牲畜的母亲,牲畜是草场的子孙”,“草肥则牲畜壮”。其实,“牲畜”一词是可以置换的,草场也是哈萨克族人的母亲,哈萨克人也是草场的子孙。这种血缘关系的比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草场/草原与人的切身关系。另外在哈萨克族万物有灵,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马牛羊狗等都有专门的守护神,草亦有青草神,显现的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渗透着宏厚的宗教情感,哈萨克族与维吾尔族在宗教信仰上稍有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除了伊斯兰教外,萨满教也是他们文化中重要的宗教信仰,其中重要的教义也指向着万物有灵,两者有着共同的旨归:“在谋求基本生存条件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过程中为有效地协调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价值,满足心灵寄托,形成牢固的关于家庭关系、社会交往、从业思想以及以积极的态度合理地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等一系列重要的规范性要求。”[8]
同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与哈萨克族在传统文化中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即萨满教),关于草原与人、万物有灵的生态思想,再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蒙古族的典籍中关于生态保护的规定,如《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阿拉善蒙古法则》等,根据自身的实际,制定了一些保护草原的律令,尤其是对草原失火、违反狩猎期的规定及偷猎行为有着严格的惩罚措施,如《卫拉特法典》规定:“失放草原荒火者,罚一五。荒火致死人命,以人命案惩处”,“因报复而放草原荒火,以大法处理”。《阿勒坦法典》规定:“偷猎野驴、野马者,以马首罚五畜:偷猎黄羊、雌雄狍子者,罚绵羊等五畜;偷猎雌雄鹿、野猪者,罚牛等五畜”[9],如此等等,说明蒙古族对生态保护已经上升到了制度层面。此外,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也有关于天父、地母的说法。总之,蒙古族的生态文化是生产方式、居住环境基础上形成了在物质、精神(宗教)与制度层面的一套实效准则。
至于新疆其他民族,柯尔克孜族、回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塔塔尔族等,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大同小异,或环绿洲农耕定居,或逐水草流动迁徙,也就具有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蒙古族类似的生态思想。因此可以说,共性民族文化的形成是共同生态特征的环境下的一种产物,也是各民族立足于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经营策略,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操作性。
四、基于国内外生态文学研究与新疆生态文学创作现状
如果说新疆生态环境的客观情况和各民族传统文化是新疆生态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来源的话,那么可以说,国内外生态文学创作与研究则是推动、实现新疆生态文学创作、研究的本土化、民族化值得借鉴的摹本。
生态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如火如荼地发展,归根到底是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博弈的结果。生态文学也据此被定义为“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10],从本质上看,仍然没有打破自然/人类二元对立的定势,只是将其统摄在整体利益的框架内。因为我们还没找到发展的合理方案——罗马俱乐部提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式的诘问仍困扰着我们: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发展对生存的利弊,发展的可持续性,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国内外生态主义共同面对的难题。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带来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哪一国、哪一地区,具有了全球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在工业污染、温室效应、土壤沙化、资源减少的现实条件下还需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就催生了生态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反思、批判、和谐、平衡,责任、义务、可持续发展等一时成为高频词汇。
在生态文学研究上,国外生态文学的发生、发展的情状,主要是以译介的形式介绍到国内,首先是作品的译介,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卢梭作品《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爱默生的《自然沉思录》、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艾比的《珍贵的沙漠》、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莫厄特的《被捕杀的鲸鱼》及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等等,这些作品中主要体现的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然返魅,在我国影响较大。其次是生态批评研究理论著作的译介,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史怀泽的《敬畏生命》、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莫斯科维奇的《还自然之魅》、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洛夫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马尔腾的《人类生态学》、贾丁斯的《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布依尔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等,为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发展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基础。其中,“首倡生态思想的核心精神——生态整体主义的人,是生态文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掀起世界生态思潮的始作俑者,是生态文学家蕾切尔·卡森”[10]。
在译介的过程中,王宁、王诺、朱新福、刘蓓、韦清琦、胡志红、陈晓兰、李美华、杨素梅等一批青年学者成为国内引介和积极探索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主将,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欧美生态批评》(2007)、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杨素梅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2006)等均是第一次系统研究欧美(国别)的生态文学研究专著,尤其是王诺定义了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对我国生态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且由他主持成立了我国高校最早的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从事生态文学研究。2011年,山东大学成立“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研究中心”,南北两所高校由此成为生态文学研究的“重镇”,使之具有了学院派的特点。事实上,我国从事生态文学研究和批评同国外几乎同步,并注重理论的建构,像余谋昌、佘正荣、蔡正邦、陈望衡、徐恒醇、曾繁仁、张皓、赵白生、曾永成、鲁枢元、刘青汉等都是资深的生态批评研究者,从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哲学等角度阐述了生态批评的可操作性。
在生态文学创作上,新疆作家对时代变化、社会转型中的生态环境变化在作品中充分予以了体现:文学的介入带来了对生态建设的重要反思,注意到了“整个共同体”的重要性,比如李娟对阿勒泰哈萨克族牧民与牲畜转场的书写、叶尔克西对塔城地区草原上牧民精神生态的描绘、刘亮程对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周边乡村的描写,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小说中对社会变迁中环境与人物关系的关注,帕蒂古丽(维吾尔族)的“混血的村庄”,朱玛拜·比拉勒(哈萨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族文化表达,买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哈丽旦·依斯热依勒(维吾尔族)、哈依霞·塔巴热克(哈萨克族)、夏木斯·胡玛尔(哈萨克族)、吐尔干拜·克力奇别克(柯尔克孜族)、艾斯别克·奥罕(柯尔克孜族)关于所属民族生态文化的表达,周涛的散文与诗歌创作,沈苇对西域文化的痴迷与吟唱,如此等等。这些作家的创作都在表明新疆作家对发生着变化的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关注,不论是属于浅层生态还是深层生态文学意义上的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已经构成了新疆生态文学独有的魅力,即在多民族生态文化、多区域生态特点、跨语际表达等因素影响下共存的文学价值系统焕发的多元性,汉族作家如周涛、刘亮程与李娟等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关注即是一个例证。但从生态文学研究或生态批评角度来说,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批评仍在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研究系统。
五、结语
总的说来,当前生态批评理论与运用的蔚然成风,它的发生与趋于全球化的特点,在于当今人们面对现实形成的危机意识,这层危机意识的现实基础主要是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在社会属性上的人类精神生态危机。尤其是后者使人类步入到了精神痼疾的圈围中不能自拔。本质上讲,这两种形态的危机来自于以张扬主体性的现代社会,现代性带来了无以比拟的发展与进步,但其双刃剑的特点同样造成了恶果。对新疆而言,生态批评的建构是在生态批评理论与运用在全球化基础上的区域化,新疆作为中国西部偏北的重要省份,地理位置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均衡,不同于中部、东部的快速发展,在整个国土版图中,现代性样态的层梯状分布,使得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较慢于中部、东部地区。而在特殊的地表生态系统中,生态批评的空间却又是其他地区无法达到的。在生态文化的资源上同样如此,多民族的生态思想将促使新疆生态批评更富有内涵,外延更为宽广。因此可以说新疆生态批评,尤其是建构具有丰富生态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系统有着较大的空间,充分挖掘新疆文学中的生态思想,也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要义。
[1]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2]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李新琪,等.新疆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研究[J].干旱环境监测,2003,(2).
[5]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艾娣雅·买买提.文化与自然——维吾尔传统生态伦理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3.
[7]白保莉.中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8]阿利·阿布塔里普,汪玺,张德罡,师尚礼.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1)——哈萨克族的形成、分布及宗教信仰[J]. Grasslaand And Turf,2012.
[9]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M].台湾:中华书局,1970.
[10]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任屹立)
The Possibility of Xinjiang Eco-criticism
HU Xin-hua,MA Xiao-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s,Shehezi University,Shehezi 832003,Xinjiang,China)
TheconstructionofXinjiangEco-criticism,aimedatecologicalconsciousnessexpressedin Xinjiang literary creation,extracting the ecological thought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culture,forms a part of eco-critical discourse from the multicultural one.In general,the possibility of Xinjiang Eco-criticism could be elaborated from four aspects:the reflection of modernity,realistic changes of objective environment,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in Xinjiang ecological thoughts,and ecological status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eco-criticism;ecology;Xinjiang
I207
A
1671-0304(2016)05-0099-07
2016-06-10
时间]2016-10-19 1: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批评视野下新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12XW036)。
胡新华,男,湖南双峰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生态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