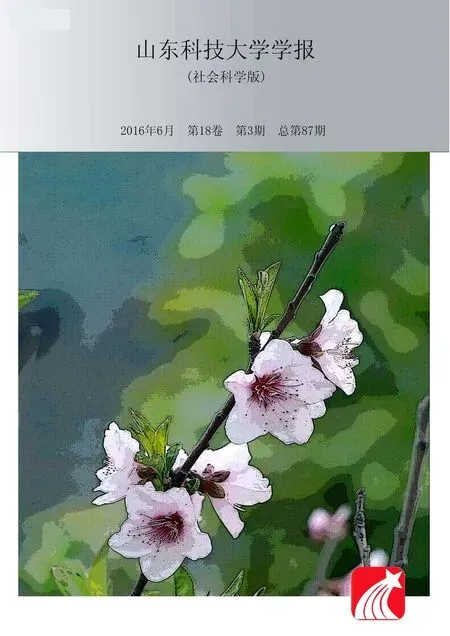自救的无力与他救的无望
——论徐坤《厨房》中枝子的回归失败
任现品,姜晓梅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自救的无力与他救的无望
——论徐坤《厨房》中枝子的回归失败
任现品,姜晓梅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与《伤逝》对“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回答相呼应,《厨房》则展示了经济独立女性渴望回归家庭而不得的处境,从男权文化观念和市场经济浪潮两方面探究其根源:受男权文化观念的制约,枝子将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和自身价值的寻求混同为一,使其回归家庭的自救行为徒劳而无力;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使枝子和松泽的需求相背离,前者渴望家庭,后者逃避婚姻,枝子的他救处于无望状态;自救的无力和他救的无望共同造成了枝子的回归失败。
关键词:《厨房》;自救;他救;男权文化;市场经济
1925年鲁迅创作《伤逝》,借助子君的离家出走及其结局,推演了女性意识觉醒而没有经济权的“娜拉”的命运逻辑,揭示出经济独立在女性解放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当代小说对女性生存状态的透析也日益精深化,徐坤的《厨房》就是其中不可忽略的文本。与《伤逝》对“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回答相呼应,《厨房》则展示了经济独立女性渴望回归家庭而不得的处境。因此,经济依赖情况下的出走悲剧和经济独立条件下的回归失败,构成了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女性存在的想象和言说,二者既前后相继又遥相对照。作为经济独立、事业有成的女性,枝子想回归家庭,获得归宿感,却在与男人松泽的情爱追逐中败得溃不成军,从而使自己的回归之路变得渺茫,感慨之余不禁追问:枝子回归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论文意在从男权文化观念和市场经济浪潮两方面探求枝子回归家庭失败的根源,以期丰富对它的解读。
一、自救的无力:男权文化观念的制约
与《伤逝》中的子君相比,枝子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自由度和发展空间扩大了很多。当时的社会条件,连涓生找工作都很困难,更何况子君,所以子君虽然读了书,却没有工作,只能做家庭主妇;而同为知识女性的枝子则幸运得多,几年前,她为了追求自我能力的发挥和自我生命的实现,毅然走出束缚自己的家庭,最终获取了事业的成功,现在她已成为冉冉升起的商界新秀,拥有不一般的经济资本,这和子君出走的悲剧结局构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枝子所承受的生存压力也成倍增加。当下女性的生存处境更多地受制于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双重要求,即女性既要向男性的标准看齐,显示出一定的能力和才华,又要保有女性角色,履行女性性别角色规范的要求,女性主义者将现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体验到的性别认同的内在紧张表述为“分裂的意识”,[1]这种双重要求其实是男权文化观念在当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如果说枝子先前的离家是展示自己的才能以向男性看齐的话,那么枝子现在的回归家庭,则是她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规范的一种认同;因此,无论是当初的离开还是现在的回来,都是对这种双重要求的一种回应。但对枝子自身而言,她的出走与回归,都是她对女性身份价值的寻求,是特定生存处境下的一种自我拯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受男权文化观念的影响。枝子自身观念的模糊不清,即不自觉地将男权文化观念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和自身价值寻求混为一谈,造成其自救的无力。
首先,枝子对厨房和女性价值之间的定位暧昧不清。厨房之于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小说开头就说:“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2]在中国传统社会,因性别差异而带来的社会分工,使得“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权文化观念日益盛行,“主外”的男人以修身为本,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因而,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思考领域从来不局囿于家,更不在厨房;而“主内”的女人则只能守在家里,照管全家人的生活起居,男人不屑于踏足的厨房就成了女性们的专属领地。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碌不停而又自得其乐,厨房成为了既禁锢女性自由又显示女性价值的一个尴尬处所。这是男权文化对女性和厨房的关系定位。
尽管厨房禁锢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生命活力,但由于社会分工的稳固和男权文化的强大,这些隐藏着性别歧视的传统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已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成为难以撼动的信条,即厨房是属于女人们的领地,不管资质多么聪慧的女人,都难以彻底摆脱其影响。“厨房里色香味俱全的一切,无不在悄声记述着女人一生的漫长。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厨房里。”[2]女性走进厨房已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行为。作为有着高等学历的当代女性,枝子对厨房这个隐秘的所在有一定的警觉,婚后她更认识到厨房的单调乏味及其对自身生命的束缚,于是她毅然地选择了逃离。逃离厨房是枝子逃离男权文化藩篱、追求自我价值的第一步。走出厨房后的枝子,犹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见识到了外面有别于厨房的广阔天地,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能量和光彩。
但由于男权文化的深层制约,具体体现为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双重要求,也由于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给女性带来的疲惫无奈,随着事业的成功,厨房对枝子的吸引力逐渐强烈,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枝子,还是想要回归到厨房,以获取自身价值。其实男人也很疲惫,但他们从不会把厨房作为退路;在此枝子将自身价值和厨房联系起来,“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她愿意一天无数次地悠闲地待在自家的厨房里头,……慢慢料理这些的时候,她的心情定会像水一样沉稳,绝对不会再以为这是在空耗时间和生命。……她希望她的心情就那样像水一样,温吞、空泛,温吞、空泛地在厨房里消磨时光,什么外面争斗的事情都不去想。她愿意看见有一两个食客,当然是丈夫和孩子吃着她亲手烧的好菜,连好吃都顾不上说,只顾低头吃得满嘴流油,脑满肠肥。”[2]枝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将厨房和自我生命价值相联系的同时,已不自觉地美化了厨房,先前那个禁锢她、让她郁闷的厨房,现在又成了她获得自身价值的所在。她对厨房的这种定位,即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认同,是变相地承认女性的价值不在商界、学界,也不在其他领域,而是在这狭小的弹丸之地——厨房。于是她处心积虑地想掌管松泽的厨房,甚至不惜以厨房献艺的方式来激发松泽对自己的爱意。至于厨房和女性价值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大,枝子始终没有厘清,因而,无论是果断的出走,还是急切的回归,她都始终挣扎在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双重要求中,无法确认女性自身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其次,枝子将家和自身归属感加以模糊对应。对女性而言,家庭和厨房一样是把双刃剑,既是安度生命的地方,又是消磨灵性和才情的场所。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男人和女人都深受家庭的制约,“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4]不同的是,男人们从修身齐家做起,以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获取自我价值和归属感;女人的一生则很难离开家庭,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观念,明确规定女性不能独立生存,要始终生活在男性家庭成员的监督或保护之下;“安”字的构成,即意味着女性只有在“家”中才是安全的。因而,家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为女性提供了生命活动的安全空间,更在于规约了女性获取自身归属感的领域,因为除了家,女性对此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家成为女性获取自身归属感的唯一选择。传统观念中,女人最好的归宿是找个好男人,组成幸福家庭,安静地活到终生;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认为女人的归宿是家,而不是自我能力的发挥。这是男权文化对女性归属感的设定。
小说中,枝子对于家的认识、定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起初的家,对枝子来说是一个禁锢生命的牢笼,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2]她需要一个释放生命的舞台,而这个舞台绝不可能是家,于是她毅然闯入社会,带着满腔的激情在充满竞争的商界开创出一片天地,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枝子本可以继续把事业做大,然而事业的成功,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应有的归属感,反而使她倍感疲惫,“她真的是不想再在外面应酬做事,整天神经紧绷,跟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虚与委蛇。不知为什么,她有些厌倦人。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龌龊的、猥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整天地与人打交道也快把她的神经折磨垮。”[2]在与男性的不断拼杀中,枝子一面积极应战,一面品味自身归属感匮乏的虚弱,心灵的疲惫使她迫切需要休息,和外面的喧嚣、算计相比,家显得尤其安宁而沉静,“家里的饭桌上没有算计,没有强颜欢笑,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更没有讨厌的卡拉OK在耳边上聒噪,将人的胃口和视听都野蛮地割据强奸。”[2]她“一心一意想要躲回温室里,想要回她当初毅然决然抛弃割舍在身后的家。”[2]在现有的情况下,家又成了枝子唯一可以信赖托付的地方,只有家才能给人以安全感;至于事业成功到什么程度,这只是释放人的生命能量,远不能带给人归属感。女性对于自身归属感的寻求再次落入到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枝子的渴望回归家庭也再一次印证了女性逃离传统伦理规范的艰难。
枝子对厨房和女性价值、家和女性归属感之间的含混认识并非其个人的认知局限,而是时代观念在个体身上的具体表现,即使是市场经济下的今天,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都表现出相当的成就,人们依然认为操持家务是女性的义务,厨房才最能体现女性的价值所在,家才是女人的归属,究其实质,这是男权中心文化观念在当代社会的一种回响;因而,她也就不可能凭借回归厨房、回归家而寻找到自身价值和归属。但对枝子而言,这种回归乃是一种奋力的自救行为,只不过这种自救是他求的、赖他的,无法独立完成,必须有所依凭,即一个她中意的男人乐于和她结婚并相爱相守,而这又不取决于她自身的素质和努力,是她所不能把握掌控的,因而她的自我拯救是无力的,很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二、他救的无望: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
与子君不同,枝子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显赫的主导性话语只能是市场”[5]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男尊女卑性别观念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也唤醒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将人们裹挟进功利主义的浪潮之中,强化了人们在求学、就业、择偶等方面的功利性考虑。已然不惑的枝子,为了自救而回归家庭,想和意中人走进婚姻殿堂,然而现实功利的男性则更多地想获取男女交往过程中的好处,而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羁绊,不愿承担任何责任,哪怕是和富婆的婚姻,这种功利性的考虑使枝子的他救处于无望状态。
首先,功利算计对男女行为选择的影响。如果说依仗体力的农业社会催生出了男性的中心地位观念,那么在重视智力、交际、流通的城市社会,女性的生理弱势得以被淡化,城市为女性的自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社会,作为历史存在(同样也是现实存在)的父权统治常将妇女行为规范于一定空间范围内(这种规范往往是理论上的)。而充当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交中心的城镇,历来被视为妇女活动的‘真空地带’。相应的,一旦属于妇女的‘性别空间’出现扩张趋势,其征兆往往首先出现在城市空间中”[6]市场经济时代的城市是智者、能者施展能力才华的乐园,走出家庭的枝子经过一番闯荡后,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为商界新秀。经济资本雄厚的枝子,不仅资助画家松泽举办了个人画展,而且全力包装他,使松泽短时期内就大获成功且声名远扬。经济资本的参与,使枝子和松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男女两性关系,更带有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意味,功利性构成了两人行为选择的根本动机。
小说没有营构曲折的情节,只细腻地描绘了枝子与松泽情爱追逐过程中的微妙心理及最终结局。作为投资人,枝子想在松泽的生日用精湛的厨艺表达自己的心意,并借用浪漫的情调引发他的激情,最终使两人走进婚姻,为此,枝子可谓费尽心机。然而,松泽之所以留在家里和枝子一起共进晚餐来为自己庆生,并非男女两性情感的自然吸引,而是出于功利性的考虑。“与待在家里传统的吃生日饭相比,当然卡拉OK包间或派队沙龙里搂搂抱抱的扭捏抚摸更能激发创造力。但若从长远的角度看,比起跟那些小女孩崇拜者玩玩自拍,不如跟女老板处理好关系对他将来的用途更大一些。男人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从最实利的目的想。所以他决定还是死心塌地,留在家里与女老板亲近感情。”[2]可见,松泽留在家里的行为动机是为了自己今后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什么两情相悦。“所以他只是听之任之,一边散漫无际地调着情,一边还要暂时做出温文尔雅。”[2]在松泽眼中,再温婉可人的枝子,仍旧是女老板而不是女人。因而他在与枝子独处时,边试探边调整自己的行为,“主要是男主人还没有拿捏得准女老板的意图……不知道她想要他做什么,要他做到什么程度。他还时时没有忘记她是投资人。”[2]可见,枝子和松泽之间全然没有言行上的默契、情感上的交流和心灵上的共鸣,有的只是一厢情愿和相互试探。
对于在商界拼杀多年的枝子来说,功利性无疑是其行为选择的动机所在。她赞助松泽的绘画,是看上他画风里的野气和灵性,她一头扎进松泽的厨房更带有着极强的目的性。“女人枝子正处心积虑地,在用她的厨房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真爱。”[2]为此,她不惜低三下四地挺进松泽的厨房,向他献艺。枝子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她试图用一桌精心烹制的美食来诱惑松泽的性和爱。“脸上修饰完毕,枝子又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套真丝晚装,换下了一进门来时穿的果绿色白领丽人套服。……这些都是为今晚的爱情特地准备的。”[2]等到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她不假思索,一口贪婪地吸住了他的舌头。男人立刻就被火辣辣地舔了进去,任凭怎样也抽脱不出来。”[2]松泽这才恍然意识到“她为他所做的一切,她的所有厨房语言,好像都在向他示意:她愿意做他这个厨房的女主人,她是做他这个房间女主人的最好人选……”[2]松泽终于明白了枝子的真正意图,她处心积虑想要的并不是一时的情欲满足,而是一种长久的被承认也被保护的夫妻关系。
然而婚姻责任是松泽所极力逃避的。因为松泽所想要的只不过是与女老板亲近感情,好让自己的事业顺风顺水。他根本不想给自己找个负担,更不愿有任何形式的羁绊。家庭责任也好,社会义务也罢,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他根本不想在事业最火爆的时候,娶个老婆在家里守着。如果说枝子抱着某种目的走进松泽的厨房,那么松泽的功利主义更赤裸裸,为了利用女老板,他一方面呼应着枝子的情感信号,以免她难堪,另一方面又不著痕迹地恰到火候地终止这种情感游戏,彻底断了枝子的念头。功利算计使松泽不愿意给予枝子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无论是感情还是家庭,从而注定了枝子想从松泽身上寻找失去的一切只能成为一个妄想。纵使枝子想回归家庭,也没有合适的接纳她的人,她试图向松泽寻求救助的努力被功利化的现实击得粉碎,他救是无望的。
枝子的如意算盘是诱惑松泽和自己结婚,松泽的目的则是利用女老板并逃避责任,两人功利打算的错位,注定了这场男女情爱关系的惨淡前景,因而也就注定了枝子试图对外寻求他救以自我实现的失败结局。枝子借结婚回归家庭获取归属感的愿望就此落空。
其次,消费意识对人们性爱观的冲击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如社会统一性的瓦解,个人情感欲望的合理化以及消费意识的蔓延等,“人们丧失了一体化社会提供的那种狭隘但安全的精神家园,而处于焦虑与不安之中。”[7]尤其是消费意识已日渐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甚至连性、爱、情都难以获取免疫力,人们的性爱观也受其冲击而分化。
“在传统的男性文化中,女人处于服从男性、追随男性和为男性奉献爱情的从属角色。”[8]所以在传统社会,男人的性爱欲望被当作合理的要求得以满足,“食色,性也”的男性话语意味是其明证;而女性正常的性爱需求则被压抑在见不得光的阴暗角落,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长久以来,女人对自己合理的生理欲求不敢表达,一旦提及就陷入不道德的境地。因而,女性总是极力躲闪着身体需要,然而越是压抑,内心的欲求也就越强烈。已届中年的枝子,纵然已是事业风生水起的女强人,但依然有着普通女性的生理需要,她渴望性爱和男人的呵护,“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伸着,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2]这些纯生理特征的描写,反映出枝子作为女人内心对男性身体的期待。为此,她主动走进松泽的厨房,试图想通过美味的饭菜来换取男人的柔情蜜意。枝子所精心准备的一切,无非是想找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一个可以停靠的家。她以为只要真诚地把自己的性爱交付给他,就可以得到她想要的婚姻。而松泽想要的却只是激情和快乐,而不是婚姻和责任,他一点都不想对别人负责。白玩可以,动真格的却不行。“若说假意嘛,他可是随便乱施得多了,还挺自在安全、挺幸福的;若论真情的话,他画家松泽除了对自己、对他的名和利以外,就再也没对谁真情过。他不怕玩,他就怕认真。”[2]对松泽来说,一夜情可以激发他的艺术创作灵感,他的性是自由的,不牵扯到爱和责任。然对枝子来说,性和爱是交缠共生的,她愿意把自己献给松泽,也就是说她爱他;当然,之后的松泽也应该承担起男人的责任,给她一个安稳的家。这就是枝子的逻辑,也是她的性爱观,这种性爱观注重性的社会属性,具有社会规范性和规定性,正如黑格尔所说:“两性的自然关系通过它们的合理性而获得了理智和伦理的意义”。[9]枝子与松泽对性爱行为的不同期待,无疑显示了消费意识对人们生活态度、行为取向的影响分化,松泽对“一夜情”的热衷并非偶然。
以往性爱观强调两性性行为的社会性以及双方的责任义务,尤其是女性的忠贞和专一;然而社会已悄然改变,人们已跨入一个对消费狂热崇拜的时代,各式各样的物品、服务还有感情等,不管是有形的物质还是无形的观念都被人们快速地消费着,性爱也随之成为一种可供消费的快餐服务,重享乐轻责任的“一夜情”现象的出现,就是消费意识扩大势力范围的明证。枝子最后的被拒,确证了女性想通过一夜的性爱来获取牢固婚姻的想法已成为天方夜谭。
总之,不管是依靠自己来自我拯救,还是伸手寻求他救,枝子都失败了,她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换来一包可笑的厨房垃圾。既让人悲愤难平又令人深思:如果女性不能确立起自己的价值追求,寻找到自我生命的真正归属,就只能始终挣扎在男权文化的性别规范中,枝子对厨房、家表现出的过分的美化渴求,就体现了男权文化观念在当代社会的深层制约,因而无论是出走还是回归,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枝子内心那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感;在市场经济下的消费主义时代,到底怎样建构女性自身价值是直到目前仍未解决的难题。从子君的出走悲剧到枝子的回归失败,既表明中国女性的性别平等追求并没有超越历史而成为无根之物,又显示了男权文化的强固,“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10]性别观念的变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女性对性别平等、自身价值的寻求可谓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杨宜音,等.性别认同与建构的心理空间:性别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互联网[C]∥孟宪范.转型期的中国妇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徐坤.厨房[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3]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399.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12.
[5]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72.
[6]巴巴拉·阿内尔.政治学与女性主义[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17.
[7]任现品.价值寻求与感性生命的错位:对市场经济下中国小说创作路向的反思[J].烟台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48.
[8]陈顺鑫.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82.
[10]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5.
(责任编辑:黄仕军)
Inability of Self-Help and the Hopelessness of Being Saved——On Zhizi’s Regression Failure in Kitchen written by Xukun
REN Xianpin JIANG Xiao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As an echo of the answer of “What is going on after Nala left” in Regret to the Past, Kitchen shows the situation that women with economic independence, were eager to return to families, but failed.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the concept of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the market economy.Impacted by the concept of patriarchal culture, Zhizi confused the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and the pursuit of Self-value, which made useless and powerless her self-saved attempt to return to family.Moreover, as a result of the strike of the market economy, Zhizi and Songze have the opposite demands: one desires to return to family and the other is eager to escap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made hopeless Zhizi's self-help.All in all, both the inability of Self-help and the hopelessness of being saved lead to the failure of the Zhizi's return to family.
Key Words:Kitchen; Self-Help; being-saved; Patriarchal Culture; Market Economy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任现品(1970—),女,山东单县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6)03-009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