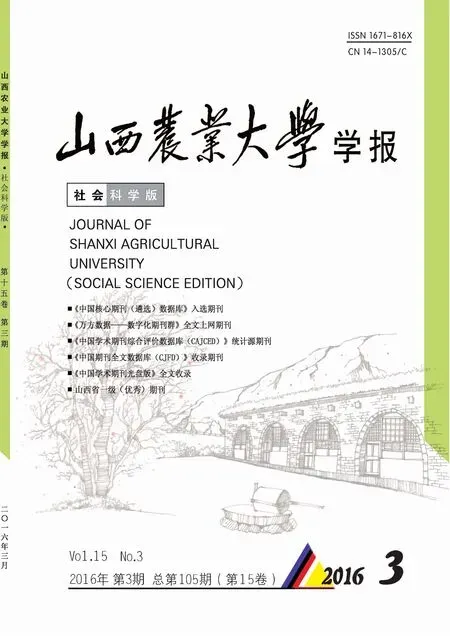青春文学和青少年亚文化空间研究概述
严晓驰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
青春文学和青少年亚文化空间研究概述
严晓驰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
摘要:在中国青春文学的研究中,文化维度的意义超越了文学维度的意义。青春文学在国外一直被纳入亚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范畴中,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空间这一理论来找到突破口,从而了解到青春文学文本是如何逐步建构起独特的意识形态空间,实现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父辈文化、媒介文化等的抗衡。
关键词:青春文学;亚文化;空间
作为一个盛行的文学现象,中国青春文学研究在最初时遭遇了评论界“失语”的尴尬状态。事实上,在“80后”文学现象出现之初,将其推到了风头浪尖的主要是媒体炒作,如魔铁公司总裁沈浩波当时让春树穿着红肚兜签售新书曾引发一片舆论哗然,除了白桦等一批先行的批评者,主流评论圈尚处于暂时失语的状态。“80后”文学被认为在主流文坛之外。这也就造成了之后青春文学与主流文学之争。由于媒体的过分介入,“80后”作家及其作品一度成为“明星化”的标签,这使得之后的青春文学研究产生了狭隘化的趋势,很多学者甚至只将目光锁定在“80后”一代的创作上,当然也促使“80后”作家与市场的关系更为紧密。
之后,青春文学开始泛滥化,各类“销售神话”相继出现。被媒体所捧红的青春文学作家们开始了集体性的“叛逃”,他们纷纷对商业文化和主流文化发起了挑战,这直接引发了主流文学圈对于文学写作的“规范”讨论。而媒体对“80后”、“90后”群体本身以及相关文学本身制造了混淆,在一些关于青少年负面新闻的影响下,青春文学和青少年终于被冠以各类“标签”:叛逆、道德丧失、孤独、虚幻等。
目前,国内对于青春文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将青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研究,另一类主要通过文化的角度来切入。
一、文学维度
(一)历时性的纵向研究
在对青春文学进行文学性的分析研究中,还可以细化为两类:首先是对青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历时性的纵向研究,探讨青春文学的概念、起源、流变、未来走向。
白烨、江冰等人是较早一批对青春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学者。他们将青春文学主要集中在“80后”文学中来考察,细致梳理了其产生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并从思想内容与创作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分析,对“80后”文学的研究做出了较大的突破。白烨有“青春文学教父”之称,曾供职于布老虎丛书编辑部,先后经历了对美女作家和青春文学作家作品的出版策划。同时,他也是最早走进“80后”作家群的评论者之一,早在2004年6月,他就与张萍在《南方文坛》发表了《崛起之后——关于“80后”的答问》一文,同年,他还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发表了《不可阻挡的崛起——文坛“80后”答问录》,将“80后”一代视为文坛的新生力量。在2005年1月,他先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中国图书评论》发表了《走进“80”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80后”:徘徊在市场与文学、追捧与冷落之间》二文,白烨发表了多篇对“80后”研究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并且积极致力于为青春文学作品作序推荐,可以说,他是文学界最早关注“80后”并对其基本持积极态度的学者。而2006年,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80后”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却直接引发了文学界著名的“韩白之争”,韩寒针对此文发布博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
白烨等人为之后的评论家提供了线索,另一批评论家也相继开始关注,如曹文轩《他们的意味—“80后”写作与时代》(《中关村》,2005(1))、《我看“80后”少年写作——“80后”诞生于幸福时代》(《中国图书评论》,2005(1)),此外曹文轩还为郭敬明小说《幻城》以及韩寒小说《三重门》作序,在序言中,他亲昵地称呼郭敬明为“小人儿”,还认为《三重门》有着极大的可能性。
贺绍俊在2005年的《文艺研究》上发表了《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现象》一文,在其中他提到了“80后”作家明星化的现象,同时认为文坛对此的表现不够积极。到了2010年,他对青春文学的关注热诚仍未消退,在《以青春文学为“常项”——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视角》一文中扩大了青春文学的概念,将50年代初的一些小说也归入其中。
这批最早的评论者倾向于对某个或某类青春文学类型进行归类性的讨论。评论者徐妍被认为是学界最早通读通评当代青春文学的学院派批评家,她首次从文学史的维度来分析“80后”的作品,带动了许多评论者对于“80后”文学断层和代际写作等方面的思考。较早如丁元骐在2004年发表的《“80后”创作的三波浪潮》一文中就提到了“80后”创作在文坛中的承接作用,帅泽兵和邵宁宁还考察了80后文学这一概念的缘起于流变,之后张颐武在2009年发表的《当下文学的转变与精神发展以“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崛起为中心》以及王纯菲在2010年发表的《“80后”:入史的青春文学现象》等都详细讨论了“80后”一代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学者邵燕君另辟蹊径,主要针对女性创作群体研究,对张悦然、笛安、安妮宝贝等女性青春文学作家进行个案分析研究。评论者李敬泽和谢有顺更是为单调的青春文学增加了两抹重重的色彩:青春文学诗歌批评,底层文学批评。刘广涛则在集大成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二十世纪中国青春文学史研究:百年文学青春主题的文化阐释》(山东:齐鲁书社,2007),对青春文学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和总结。
(二)文本细读
其次是对青春文学进行文本本体的分析,探究其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特征以及相关的主题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展开,如刘广涛在2005年发表的《世纪末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的主题研究》中就侧重于研究“病态青春”的文本,,陶东风2008年发表的《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 后写作”举要》一文中更是关注到了之前为主流文坛所忽视的玄幻及盗墓文学。
就文本分析的领域中,青春文学文本也有积极的价值因素,如评论者们认为青春文学作为一种切身的当下写作,很好地抒发了青少年的成长苦闷和心理忧虑,反映了当下青少年的生存状态。同时,青春文学的走红也间接激发了阅读作为一种时尚行为的兴盛,为青少年进入文学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如李蕾的《80后文学的审美价值》以及潘进听的《青春文学的读阅价值》等充分肯定了青春文学对于青少年阅读的价值。而从消极层面来看,“80后”写作群体并未获得主流文坛的正式认可,无论是从媒体的极度包装和宣传,还是2007年作协所谓的“破格录取”青春文学作家进入作协,主流话语圈对于这个新生的文学写作群体还保持着怀疑,因而关于青春文学作家是否被“招安”问题也被激烈地引发开来。青春文学作家群自身文学素养的不足和当下消费文化催生下浮躁心态的流行,都使得青春文学文本本身遭受着重大质疑。徐妍的《青春文学的情感资源:在经验与才情之外》、张柠的《“80后”写作——偶像与实力之争》等都为此表示了忧虑。
另外,对于主题和现象的分类研究中,评论者们对青春文学文本做了细致化的分类研究,比如青春文学的场景基本集中在家庭、校园、青少年特殊的社会聚集地(如酒吧、步行街、公交车站、主题公园、舞厅等)中;题材基本集中在成长现象,叛逆现象,自恋现象,小资情调,流浪主题(实际上可以跟成长结合起来),忧伤心理等,传统的亲情、友情、爱情三类题材依旧贯穿其中,只不过以更为个性化的手法呈现出来;人物类型处理上按照人物年龄主要划分为青少年和成年人两代,从青少年人物中又可粗略划分为“听话派”和“叛逆派”两类;而文本的基调多为恶搞戏谑和极度忧伤两个维度等,如杨剑龙等的《青春与自恋—关于80后作家的讨论》以及吴专的《“80后”写作的孤独意识探析》等。这类对文本的近乎“解剖”式的研究,主要将青春文学视为一种类型化的文学来讨论。
二、文化维度
青春文学在文化维度上的意义大于文学维度的意义,因其不光带来了文化冲击,更是积极带动了青少年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链的发展。
(一)青春文学与媒体文化
文化维度研究的第一层面是将青春文学的产生与市场相联系,讨论其出版流程及与媒体的密切联系。如江冰于2005年在《文艺评论》上多次发表关于“80后”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等文章,考察了“80后”文学命名的误读以及与网络、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关联,并进而对“偶像派”和“实力派”的写作进行了评论,可谓是“80后”文学的积极关注者。而张柠、刘广涛等后继研究者也纷纷将青春文学纳入到市场化的场景中,这也是青春文学遭受诟病最多的部分。因为青春文学先天不足的文学性和深刻的社会性内涵,使得那些对于青春文学的审美和阅读价值的过分强调显得力不从心,只能沦于流俗的“喝彩声”。另一方面,市场出于行销宣传的目的而对青春文学的刻意“力捧”又难逃评论家们的“法眼”,而一些最初怀有善意的评论家如白烨等也被主流评论家进一步视为市场操作下的作秀者。在两下不利的局面下,青春文学必然失去了主流评论界的青睐。因而,从《青春文学“大暴动”》(陈益民)、谈到《当文学青年遭遇市场——青春文学产业化、娱乐化现象探析》(崔秀霞)、再到《青春文学中的媚俗文化》(魏萌)、《青春文学缘何盛行不衰》,还有一些评论,诸如《“80后”:写作因何成为时尚》(路文彬,《中关村》,2005(1))、《新的文学法则的生成——青春文学杂志书的运行态势与作家形象建构》(岳雯,《南方文坛》,2011(4)),《青春文学图书市场分析》、《青春文学的配方》(《中国图书商报》)等。面对青春文学的当下困境,评论者们几乎集体将矛头都对准了市场以及市场早就的青春文学作家们的急功近利心态。
过度抬高媒体与消费文化在青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会忽视对青春文学自身的创造性和反叛性,在媒介文化和消费文化合力操盘的情况下,青春文学也表现和重构了自己的意义空间。媒介文化和消费文化并不是谋杀文学的工具,相反还可以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为文学和文化注入生长的资本。
(二)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
文化维度研究的另一层面是将青春文学同青少年亚文化相结合。至于两者结合的缘由,陈殿林在《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机制研究》中解答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青少年亚文化不同于英国伯明翰学派所研究的那样,英国的青少年亚文化有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并且形成了独立的具体的亚文化群体,真正承担起了与主流文化进行对抗的角色,而我国的青少年亚文化每一形成具体的群体,“更多的以文本形式存在。”[1]中国青春文学整体离批判性的反文化还有相当距离,也没有滑入过度颓废、放纵的负文化范围。因此可视作一种亚文化。
关于青春文学在亚文化背景下的分析,研究者的关注点多集中在青春文学的代际书写中,即分析青春文学与父辈文化之间的关联。如田涯文化工作室在2006年主编出版的《80后心灵史》一书,通过与青春文学作家春树、小饭、蒋峰等人的访谈以及作家自述的方式介绍了80后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再如郭艳的《代际与断裂——亚文化视域中的“80后”青春文学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8))则从亚文化的角度切入,认为“80后”代际写作深陷在自我情境中,《当文化成为一种姿态》在分析青春文学的世代特征时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杨庆祥作为一个80后的代表也于2015年出版了随笔集《80后,怎么办》,当中以随笔以及访谈的方式细致论述了80后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并收集了近年来有关80后一代人的文学评论。
学者焦守红将青春文学纳入到生态场中研究中,其著作《当代青春文学生态研究》(湖南:湖南师大出版社,2008)被认为是当代第一部青春文学研究专著,由中国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杨匡汉先生作序。曾经的“80后”作家群已大部分步入而立之年,因而在2008年对青春文学做一个回顾性的研究是有其意义的。作者认为,“生态逆补”是自然界生态平衡和人类文化生活调节的重要手段。而当代青春文学则因“以病为美”、“以悲为美”的倾向陷入“恶补”的泥淖。
不管是从生态场域的角度还是从亚文化的视阈中,就目前国内的研究而言,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视察青春文学的研究尚停留在伯明翰学派“风格”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是对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出现表现得过于恐慌以至于忽视了传媒和消费文化在提供亚文化资本的支持和积极推动方面。此外,国内的研究未能将青少年亚文化放在广阔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结合的背景下来研究和定位。很多对青春文学的研究擅长罗列各类亚文化特征,如叛逆、虚幻和自恋等。这种倾向于把亚文化视为几个具体的风格标签的做法,会导致青春文学的概念化和单纯化,缺乏对全球化时代亚文化碎片化和流动性的理解。我们需要把亚文化放置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具体分析,深入探讨青春文学写作是如何产生所谓的“叛逆”、“虚幻”、“忧伤”、“自虐”等标志性现象,并通过制造这类现象来构建起一个专属于青少年的文化和文学“空间”,以此来对传媒和主流文化进行抗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学界主要将青春文学作为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这两个方面来研究,前者倾向于问题分析的研究策略,在突显市场和媒体的操控力时忽视了文学作为作者内心的表达所具有的主动性。而后者则陷入在“风格”理论的泥淖中,在缺乏对全球化时代背景和中国本土化民族特色这两者的了解上,把青春文学肢解成一个亚文化风格下的具体标签。同时,国内对于青少年亚文化所秉持的态度多建立在道德批判上。而从最早研究亚文化理论的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开始,亚文化被西方理论家视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而不针对其有别于主流道德文化的“越轨”行为。甚至可以说,对于主流和社会的反叛,本身就是亚文化得以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从青春文学本身如何具体构建起自己的亚文化领域来做具体的细究,于是,我们需要把“空间”的概念引入其中。
三、亚文化研究和“空间”概念的由来
中国的青春文学以其对主流文坛反叛的姿态而兴起,因而我们需要纳入亚文化视域的讨论,而亚文化青年群体的形成即在于其建立其了专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于亚文化的研究最早来源于西方,主要经历了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和后亚文化研究三个阶段。
(一)芝加哥学派
亚文化研究第一阶段主要在20世纪20—60年代,当中的代表性学派是美国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特点即在于读亚文化进行了学科化的研究。1915年,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在《城市》一文中就开始注意现代城市社会中各类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之后从1921年到1931年,他鼓励学生们用“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来考察“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他们发现传统社会结构和道德秩序正在逐渐解体,由此导致大量越轨亚文化行为和群体产生。
1947年,米尔顿·戈登(Milton M.Gordon)成为第一位考察sub-culture一词意义发展的社会学家。他在该年发表了《亚文化概念及其应用》(The Concept of Sub-culture and Its Application)一文,提出纽约1944年出版的《社会学词典》(Dictionary of Socialogy)当中就已收录了一个同“亚文化”意义相似的词:“culture-sub-area”,以此来指代“一个更大的文化地域中的一个次等部分或者亚分支”[2],这个词强调了在地理学意义上的毗连。戈登还发现,阿诺德·格林(Arnold W.Green)在1946年在谈及焦虑症时偶然使用过“严密组织化的亚文化”(highly organized subculture)的说法。
1955年,艾伯特·科恩(Albert K.Cohen)系统深入探讨了越轨青少年亚文化现象,这位美国的社会学家在其《越轨男孩:帮伙文化》(Delinquency Boys: the Culture of Gang)一书中融入了“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理论,他将青少年亚文化乃至青少年的犯罪文化都视为是其对于主流社会的“反叛性回应”[3],而在这些文化群体中的成员则被统称为“越轨男孩”。
1957年,默顿(Merton)将“手段与目标”的概念引入一种解释模式当中,试图将越轨行为解释为那些在社会上缺乏既定“手段”的团体用以获取物质和文化收益的一套解决方法。……越轨亚文化群体只有在他们制造越轨手段以获得大多数人通常追求的社会目标的时候,才呈现出越轨特征。马札和塞克斯(Matza and Sykes,1961)认为亚文化群体虽然在提供各种反传统的(non-conformist)追求愉悦和兴奋的途径方面显得有些偏离正统,但并不会对主流社会构成同等的挑战和破坏。
1963年,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在《局外人》(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中提出了“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并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这为后来的英国学者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提供了启发,斯坦利·科恩在之后研究英国主流传媒对两类青年亚文化反叛群体(摩登族和摇滚乐迷)的“妖魔化”描写,并于1972年出版了《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一书。
1970年,约翰·欧文(John Irwin)对亚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补充,他结合了美国多元文化的具体语境,认为这一概念不仅仅指代某个具体的社团,也代表着某种生活方式和行为体系,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社交空间。
芝加哥学派主要倾向于“问题解决”理论,认为亚文化是青少年对于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也由此获得了一系列关于“越轨亚文化”和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成果。该学派主要提倡“民族志”和“参与考察”的研究方法,成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方法。伯明翰学派的威利斯、克拉克与赫伯迪格等学者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威利斯更是以此创作出了亚文化经典《学会劳动》。
(二)伯明翰学派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早期是亚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研究的重心从早期的美国芝加哥学派转移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成立者理查德·霍加特自此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化研究事业(Cultural Studies),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伯明翰学派。早期代表著作有理查德·霍加特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的用途》,威廉斯在1958年和1961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1961),还有汤普逊在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在伯明翰学派产生之前,英国的青年研究对社区和区域性研究保持着强烈关注。梅斯(Mays)致力于利物浦青少年犯罪的研究,认为当地男青年接受了越轨的模式并将其付诸实施。帕特里克(Patrick)关注对20世纪6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帮派的研究。科恩关注对“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社区”的研究。
随后,亚文化研究的重心从对区域和社区的强调转向对阶级的宏观透视。伯明翰学派把阶级理论引入到青年亚文化中,并开始重视青年亚文化实践中的“仪式抵抗”意义,这可以从1976年出版的《仪式抵抗》中体现出来。伯明翰学派认为工人阶级青年日益增长的消费力,尽管会将他们塑造成消费者的形象,但却根本无法从实质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境遇。
到1970年代中期,伯明翰学派的学者开始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资源。逐渐将青年亚文化视为一套构成青年小众群体特定生活方式的符号系统——风格,还提醒其警惕被主流强势群体和商业文化所“收编”,代表作为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1979年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该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等代表学者认为“青年文化最能够反映社会变化的本质特征。”[4]
此外,伯明翰学派还做了一系列个案研究,讨论了嬉皮士、摩登族、无赖青年、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涂鸦等亚文化,如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在1973年发表《足球流氓和光头仔》(Football Hooliganism and the Skinheads)一文来研究足球流氓与光头文化,托尼·杰斐逊(Jefferson)在《无赖青年:一种政治复兴》(Teddy Boys)中对泰迪男孩风格的研究,南茜·麦克唐纳(Nancy Macdonald)的《涂鸦的风格》等。伯明翰学派同时认为,青年亚文化的出现是一种想象性解决。因为“青年亚文化群体都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战和颠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拥有的文化“霸权”。他们甚至认为,青年亚文化用“象征性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生活方式。
伯明翰学派主要从“风格”入手,进行符号的意义解读,从而探寻到亚文化的风格关键,并且讨论了区域和阶级在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青年亚文化的“想象性解决”现象。
(三)后亚文化时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进入了“后亚文化”时代。马格莱顿(Muggleton,2000)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描述为“亚文化破碎和增生的时代,充斥着大量旧时尚的复兴、混杂和转换,各式各样的风格并存于某个时代的关节点上”[5]。多元文化的并存使得人们正处于“风格超市”中,因而对于风格的单一化描述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这标志着后亚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的风格刚好与中国青春文学的兴起时间相吻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青春文学所受到的影响。
后亚文化时代开始关注女孩在青年亚文化群体中的存在和作用,认为很多对亚文化的讨论中都将女孩当作了边缘人甚至圈外人。有趣的是,提出批评者正是伯明翰中心自己培养的女研究生们,当中为代表的McRobbie和Garber对“女流行音乐迷”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这种文化“可以看做是对那些控制女孩生活的有选择性的、专制结构的有目的的对抗(reaction against)”[6]。春树在《北京娃娃》以及《长达半天的欢乐》等作品中就细致描述了所谓的朋克青年群体以及自己作为一个乐迷和女性朋克爱好者在此中所遭遇的歧视。
其次,消费并不等同于抵抗,许多青年人很有可能是为了“娱乐”而扮演各种“亚文化”角色,之前的伯明翰学派过分强调了这一点以致于影响中国的学者忽视了中国青春文学与媒体的友好联系。迈尔斯(Miles)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青年消费者在他们所消费的商品当中所获得的各种实际的意义。”[7]钱伯斯(Chambers)也提到“经过选择的消费对象提供了一种可以突破乏味的常规生活围墙、进入带有想象状态的鲜亮环境的可能性。”[8]最终问题在于协调青春期和亚文化的关系。大多数工人阶级青少年参与团体、交换身份、扮演休闲角色的目的都是为了娱乐;他们在其他方面——性别、职业和家庭——的差别要比他们在风格之间的区别显著得多。青少年很多时候是为了娱乐而扮演各类亚文化角色的并且,亚文化群体成员并不是绝对排外的,且并不是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阶级之上。科恩(Cohen)十分同意这一点,他对想象性的解决方法提出了质疑,转而认为亚文化是对更具个人主义的色彩的身份表达的寻求。正如班尼特(Bennett)所发现的那样,亚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9]的术语,青年人的一切社会生活都被囊括其中。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是,中国的“80后”乃至“90后”作家群都已充分的姿态与市场拥抱及合作。认识到媒体在亚文化和亚文化身份方面的创造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就提出了“亚文化资本”(subculture capital)概念。在她看来,一旦某些元素得以流行或被青少年们推崇而成为一种“亚文化资本”时,就会催生出相关的文化产业,桑顿举的例子是关于“颓废”和“玩酷”这两大标识性的元素。因而所谓的“亚文化”很可能丧失自己本有的抵抗主流文化的先锋立场,转而沦为商业文化中的“表演”元素,同时也让一批消费者建立起群体归属感。
其三,后亚文化时代还注意到青年亚文化韵流动性和变异性,青年亚文化会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出现一些本地化的变种。正如沃特斯(Waters)所指出的,“在亚文化研究中地理特征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10],因此他认为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需要关注区域性的亚文化群体。皮尔金顿(Pilkington)接着阐明到,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中,“没有搞颠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运动的社会基础”[11]。刘易斯则(Lewis)认为音乐和建立在风格之上的青年团体更应该被理解为“趣味文化群落(taste cultures)”[12]。这一点正逐步为中国的研究者们所重视,即认识到不同区域的亚文化群体并不相同,而反映到文本上也发生了龃龉。
第四,我们关于“青年”的定义需要拓展,只把青年看做一个年龄范畴(16~21岁)是较为狭隘的,这种做法认识不到可以把青年转变为意识形态范畴、精神状态而不是生活特定阶段的其他流行文化资源,因而无法解释成年人对于“年轻态”的保持和纪念。
不管是早期芝加哥学派对于越轨文化的关注,还是伯明翰学派对于区域和阶级的划分,或者后亚文化时代对于场景、新部族等范畴的诠释,青少年亚文化最突出的一点——自我空间和领域的构建——一直都在讨论之中。
因而,当亚文化理论被引入到中国青春文学的分析中,我们更需要从“空间”为切入口来考虑这种文学乃至文化现象的亚文化特质和相对于主流文化的特殊价值。由于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群更多的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所以我们有理由将外部“空间”的概念引入到文本内部“空间”中来进行讨论。
四、传统空间理论综述
(一)空间概念
“空间”概念最早扩散在地理学、哲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中,而对于空间的文学研究是被忽视的,仅仅被视为是承载文学的一个器皿,但是对于空间的思考和构建却一直存在。最早的对于“空间”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建构的三等级的“理想国”(城邦空间)和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永恒实体”世界的想象。
不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空间作为一个主体的研究一直未能得到重视,正如菲利普·韦格纳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认为的那样,“被看成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其本身和内部都了无趣味,里面上演着历史与人类情欲的真实戏剧”[13]。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空间理论的边缘化地位得到很大改善。尤其是在70年代,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系统地阐释空间的辩证逻辑关系。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提出了三元辩证法,将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联系在一起讨论,他在其中“强调了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14]。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与资本运行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性,由此,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进入了空间领域,由此诞生了空间政治。
大卫·哈维着重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我们探究问题的方法,他在《空间之时.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中提出,“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15]这些时空的概念被用来组织物质时间,以此来契合物质再生产的目的。
福柯从知识和权力的角度来探讨空间,他在1966年《词与物》一书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揭示了有关异位的关系性和异质性的空间。
1945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于1945 年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中首次系统地在叙事学领域创建了小说空间形式的理论,这就是“空间化叙事”。约翰·伯杰认为我们还应考虑地理学方面的问题,同时,“空间看来远比时间更能对我们隐藏各种经验导致的后果。”[14]叙事学理论由此也进入了对小说空间的论述。
20世纪90年代后期,跨学科的空间转向与都市经验研究的蓬勃兴起几乎是同时的。爱德华·索亚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还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构想,他从“游记”的性质出发,试图寻找重构列斐伏尔思想的途径。在索亚那里,第三空间是建立在由日常生活和体验所代表的第一空间以及由意识形态所象征的第二空间的基础之上的,是多种元素杂糅的空间。
在福柯、齐美尔、列斐福尔的努力下,“空间”跻身于当代理论界重要主题之列,并构成了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空间转向。空间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社会学与地理学两个方向,前者以布尔迪厄等学者为代表,后者以克朗等文化地理学家为代表。
(二)亚文化视域中的“空间”概念
如上所言,空间理论的社会学代表主要以布尔迪厄、吉登斯等为主,他们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研究空间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布尔迪厄试图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与二分法,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场域”(又译为“场”(field))概念。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16]这些处于不同位置的资本或权利关系在场域中互相抗衡。
在布尔迪厄眼中,场域是个永恒斗争的场所,且具有相对自主性。场域很好地体现了各类不同力量之间的张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之后的研究者们便将“场域”的概念引入到对亚文化的研究中,用以作为体现宰制性文化与青少年亚文化博弈的场所来分析。
随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84年又率先推出了布尔迪厄的《区分: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又译为《区隔Distinctions》),探究了所谓的文化资本,即通过早就社会地位的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它是区隔体系中的关键物,在该体系中,文化等级相当于社会等级,人们的趣味是阶级的首要标记。布尔迪厄把资本分为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是可以转换的。这以想法被再度引用到亚文化研究中,萨拉·桑顿借此提出了亚文化资本的概念,拓展了媒介文化与亚文化关系的研究。
然而,“场域”所涉及的“反文化”的气息太过浓厚,而亚文化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概念。同时,“区隔”这一概念所带来的阶级意识并不适用于在中国当下环境中的亚文化分析。因而用“空间”来代替“区隔”显得更为和谐,可以更好地阐释青春文学这一文本的亚文化性。
由于亚文化自身所有的“抵抗性”和“边缘性”,使得从事该文化的青少年群体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与主流文化相区别的特质。首先,青春文学文本在整体上就是一个涵盖了青少年书写自我和阅读自我的亚文化的虚拟“空间”。其次,文本内部从文学地理学上的空间构建走到了意识形态上的空间构建,可逐步揭示出青春文学是如何通过文本的形式来搭建自己的亚文化平台。同时,作为叙事学层面的“空间叙事”和“空间形式”等也会被考虑其中。
当下中国青春文学中呈现出来的亚文化空间风格是多元化的,当中有两个主题特别引人注目:即荒芜的个人精神空间与狂欢化的集体群落,此外还包括一个理想型的“空间”构建:即“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对青少年而言,参与一些有象征性的空间和场景,往往是构成参与者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对青春文学的研究当中,关于其“都市化”以及对“都市化”的偏离倾向也是重点讨论之一,这里所涉及的“都市化”实质上就是青春文学作家刻意制造的“疏离”现象,亦是“空间”的一个变体。
将空间理论应用到对青春文学的研究中,宏观上可以更好地考察文学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从文学细部来看,又可以更为深刻地了解到作品内部的精神建构,以便清晰地把握住青春文学文本是如何逐步建构起独特的意识形态空间,揭示出青春文学的本质,揭示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父辈文化、媒介文化等的区别与联系、抗衡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殿林.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机制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43.
[2]Ken Gelder and Sarah Thornton. The Subcultures 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7:41-43.
[3][英]班尼特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9.
[4]Stuart Hall(ed.), Tony Jefferson(ed.).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M].London: Hutchinson,1976:27.
[5] Muggleton, D. Inside Subculture: The Postmodern Meaning of Style[M]. Oxford: Berg,2000:47.
[6] McRobbie, A. and Garber, J. Girls and Subcultures: An Exploration[C]//S. Hall and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1976:220.
[7] Miles,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 Identities and Consumer Culture[J]. Youth and Policy,1995:35.
[8] Chambers, I. Urban Rhymes: Pop Musica and Popular Culture[M]. London: Macmillan,1985:17.
[9] Bennett, A. Subcultures or Neo-Tribe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 Style and Musical Taste[J]. Sociology,1999(33):599.
[10] Waters,C. Badges of Half-Formed, Inarticulate Radicalism: A Critique of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Working Class Youth Culture[J].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1981(19):32.
[11] Pilkington. H. Russia's Youth and Its Culture: A Nation's Constructors and Constructed[M]. London: Routledge, 1994:228.
[12] J. Lull (ed.). Popular Music and Communication[M]. London: Sage,1992:141.
[13][法]热拉尔·热奈特等.载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7.
[14][美]爱德华·索亚.陆扬译.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86,252.
[15]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M].台北:明文书局,2002:50.
[16]李艳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研究综述[J].决策与信息,2008(6):137.
(编辑:武云侠)
Overview in youth literature and youth subcultures space studies
Yan Xiaoch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In the study of Chinese youth litera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dimensions is beyond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dimensions. Youth literature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realm of subculture and even counter-cul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refore, with spatial theories, we can find the breakthrough to grasp how youth literature texts construct unique ideology space and how they compet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fathers' cultures and media cultures in their localization process.
Key words:Youth Literature; Subculture; Space
作者简介:严晓驰(1989-),女(汉),浙江诸暨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7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6)03-02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