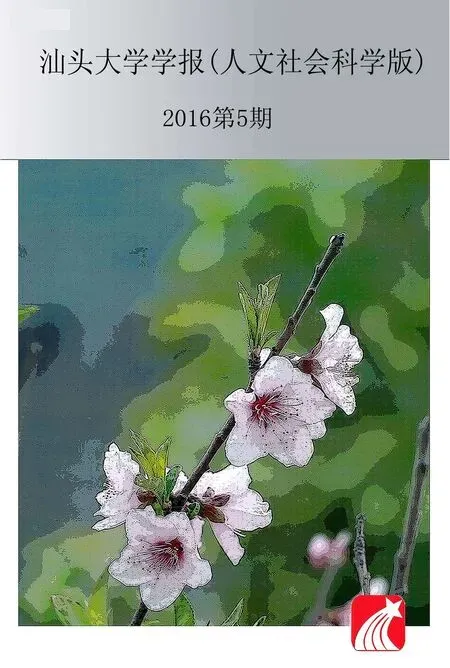论三国魏文帝时期“怨毒杀人减死”的刑法精神
陈可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论三国魏文帝时期“怨毒杀人减死”的刑法精神
陈可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三国魏文帝时期颁布的“怨毒杀人减死”法令,沈家本先生的《历代刑法考》从该法令的起源“刘朱案”讲起,分析了“怨毒杀人”的基本概念以及对遭受苦毒者杀死施加苦毒者的情况。“怨毒杀人减死之令”,可谓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创举,体现了三国魏时期立法者对于刑法的谦抑、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初步探究,“怨毒杀人减死”本身体现的刑法精神对我国现行法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怨毒杀人减死;《历代刑法考》;刑法精神;罪刑相适应;主观恶性;被害人过错
怨毒杀人减死,起源于三国魏文帝曹丕所颁布的“怨毒杀人减死之令”这项法令,发布这项法令的缘由是“刘朱案”,在魏文帝时期,有一位叫刘朱的妇人,趁其子不在对其儿媳妇进行恶毒非人的折磨,并多次用鞭子对她们进行殴打,导致了其子先后娶的三个媳妇都选择了自杀。对于这样的恶果,在上报魏文帝后,刘朱却未被判处死刑,而是改为判处输作刑,也即“论朱减死输作尚方”。判处其到尚方这个地方执行输作刑[1]20“减死一等”,在三国魏时是死刑的次一级刑罚。“刘朱案”中,官府认为三个儿媳并非刘朱亲手杀害,但是她们的死亡均是为刘朱所逼,因此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罚到监狱尚方监做苦力。①参见“势分三足鼎——三国往事闲弹”,载http://book.mihua.net/txt/3/3419/3419_20.html。为了确立今后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罚原则,“怨毒杀人减死之令”也由此而颁布。在封建社会,皇帝颁布的“令”即相当于法律,作为法律形式之一,其效力与“律”相当,甚至高于“律”,其对律具有补充和修改作用,正所谓“令必行,禁必止”。[1]27-28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先生《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二”一章里对于“怨毒杀人减死”有较多的描述和深究。本文探讨三国魏文帝时“怨毒杀人减死”法令的原理及其对我国现行法制的启示。
一、“怨毒杀人减死”的基本特征
(一)“怨毒杀人减死”之原意
对于“怨毒”一词,字典上可解释为怨恨、仇恨或悲痛②参见百度百科“怨毒”词条,载http://baike.baidu.com/link?url=1RSRVmw6Nhg6CWQ4At04SxDllBiVompV31BJ9irY3NdrEwfv Kota2Ido_hxILkxw1sUeIKHfDkz4UvJiNEpCtK。,而在“怨毒杀人”一词中,因为是刘朱对其儿媳施加的残酷的殴打和虐待行为,也即施加了“苦毒”,所谓“苦毒”可理解为通过狠毒的手段使人感到痛苦,因此“怨毒”应当理解为凶残、暴戾、苦毒。这里的“怨毒”除了指施加苦毒者行为的凶残,也指其性格的暴烈、凶险。同时也可理解为因遭受他人施加的苦毒而感到怨恨、仇恨。如《通考》所载:“故不胜其怨愤起而杀之。”[2]218
(二)杀人之含义
在“怨毒杀人减死”一词中,“杀人”应当有两层含义,即“直接亲手杀人”和“间接杀人”,即指造成受害人死亡结果与行为的直接因果关系与间接因果关系。
1.过失致人死亡。对他人施加苦毒,加以虐待、毒打,在虐待过程中导致被施苦毒者死亡的,应当是属于现代刑法中的过失致人死亡行为,即施加苦毒者主观心态上并不存在杀死被施苦毒者的故意。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对过失犯罪有明确规定,《周礼·秋官·司刺》中,西周立法者提出的“三宥”,所谓“宥”,解释为“宽也”,即从宽处理[3]。另外《尚书·舜典》有“眚灾肆赦”,将过失称为“眚”;而《尚书·康诰》中的“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及厥辜,时乃不可杀。”,明确提出了过失犯罪再大也不可杀的过失从轻的处罚原则。[3]223
2.致使他人自杀。对他人进行虐待和毒打,导致被虐待者不堪忍受凌辱而自杀身亡,施加苦毒者间接造成了被施加苦毒者的死亡。以当代刑法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死亡结果与施加苦毒者行为不具有必然联系。死亡结果的出现只是对“怨毒杀人”行为量刑时考虑的一个情节。[4]
如上文所言,“减死”意味着死罪可免,也就是虽然刘朱间接造成了三人的自杀身亡,但是毕竟不是其亲手杀害了三人,并且三个受害人的死亡系由于长期遭受刘朱的折磨而不堪忍受导致自杀,与那些直接强迫、逼迫受害人自杀的行为存在差异,因此可予以减轻处罚,即对行为人刘朱免于死刑。
(三)“怨毒杀人”之另一释义
对于怨毒杀人案件,沈家本先生在《历代刑法考》中,还提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情况,也就是当“怨毒”被解释为“因被施加苦毒而感到怨恨、仇恨”时,还可能是受苦毒者不堪忍受虐待而杀死施加苦毒者的情况,沈家本先生提到《通考》的记载:“按所谓怨毒杀人者,盖行凶之人遭被杀之人苦毒,故不胜其怨愤起而杀之。”《通考》之记载未免显得有些狭窄,因为其对怨毒杀人的范围只限于受苦毒者不堪忍受虐待而杀死施苦毒者的行为。这便与魏文帝颁布“怨毒杀人减死之令”所要规制的“怨毒杀人”行为不相同。所以,《通考》也才会提出在学界存在“今刘朱之事,史不言子妇有悖逆其姑之迹,则非怨毒杀人也。要之姑挝其妇,妇因挝而自杀非手杀之,则可以免死,但以为怨毒则史文不明,未见其可坐以此律耳”[5]的争议。
虽然魏文帝颁布“怨毒杀人减死之令”,旨在对类似“刘朱案”的案件做出一个处断原则,但同时笔者认为,如果是出现刘朱的三子妇不堪忍受虐待,并出于义愤而将刘朱杀死的话,同样可以适用这一处断原则,此时“减死”的对象则是刘朱的子妇而非刘朱。因为对于逼死三子妇的刘朱尚能够免予死刑,而对于因不堪受辱而愤起杀死施苦毒者的受害者却仍然处以死刑,造成了同种行为两个不同结果,最终对于施加苦毒者减死一等,处以“减死输作尚方”刑①不同学者对于输作刑有不同的理解。张晋藩教授主编书籍观点认为:输作,即司寇作,二岁刑,即到边远地方戍边服劳役;范忠信、陈景良教授主编书籍观点认为:输作有时候是罚作复作的统称,男为罚作,女为复作,戍边一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此种输作刑为髡刑,五岁刑,因为五岁刑乃徒刑最重者,常用于减死一等的替代刑。,对于受苦毒者则仍旧处以极刑,这是与社会公平原则相违背的。沈家本先生在“怨毒杀人减死”处的按语中也提到:“窃疑刘朱施苦毒而子妇自杀,得以减死,故受苦毒而怨愤杀人者亦得减死论,事实相因,故著于此,非谓刘朱之事为怨毒杀人也。”由此可见,沈家本先生也认为,被施加苦毒者不堪忍受虐待,愤而杀死施加苦毒者,同样属于法令中所提及的“怨毒杀人”,同样适用该法令。
二、“怨毒杀人减死”体现的刑法精神及原理
(一)谦抑
可以说像刘朱案这样的案子,就算是放到主张刑罚轻缓化和刑法谦抑性的今天,都可能出现一片“喊杀声”,因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严重,引起的民愤大,甚至也可能出现民意与舆论的导向最终影响法院的审判的现象,而这些现象都是对刑法谦抑精神的公然违背。刑法谦抑是指刑法需要具有谦虚、退让的本质,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进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以便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即有效预防和抑制犯罪。对于可用刑法或可用其他法律手段进行规制的行为,应当尽量不用刑法而用其他法律手段予以规制,根据刑法可轻判可重判的犯罪行为,应当尽量予以轻判。这也是一种经济量刑的体现,因为刑罚的谦抑可以节省更多的司法成本,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采用刑罚制裁犯罪,一旦适用刑罚偏重,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尤其是死刑,一旦错杀了一人,即便进行纠错,也不可能再挽回人的生命。当今中国司法实践主张“少杀、慎杀”,以及将死刑复核裁量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都体现了应当谨慎适用死刑。对于“怨毒杀人减死之令”,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三国魏文帝时期,便能对此有所关注,并形成此制度,实属难能可贵。
(二)罪刑相适应
罪刑相适应是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称罪刑均衡原则,是指犯罪行为人所犯罪行与其应受的刑罚相适应,量刑既不会显得畸轻也不会畸重。而中国古代法典早在西周时期便有“另类”“罪刑相适应”的倾向,如西周时期就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周礼》中的“以八辟丽邦法”反映了身份对于刑罚的影响[6];集中国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则通过“十恶”、“八议”等制度充分体现身份对于科刑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对于罪刑相适应,多体现为行为人身份与刑罚的关系。而在“怨毒杀人减死之令”中,体现的罪刑相适应倾向却是与现代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相类似的。“刘朱案”中,施加苦毒者刘朱被判处“减死输作尚方”的输作刑,相比其他故意杀人的行为人,施加苦毒者并非亲手实施了杀人行为,因此虽然刘朱之行为也间接造成其子妇的死亡,但其子妇终究不是其亲手杀死的,其社会危害性相比故意杀人行为要低,而故意杀人行为通常都是判处死刑。因此对于“怨毒杀人”行为,比照更严重的故意杀人行为,在死刑之下量刑,这是做到了罪刑相适应。
(三)对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关注
相对于“刘朱案”中行为人刘朱虐待子妇从而逼迫子妇自杀的“怨毒杀人”情节,前文所提及的“怨毒杀人”的另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古代律令对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关注,即被施加苦毒者不堪忍受虐待折磨而杀害施加苦毒者。对于这类犯罪行为,如果将它与普通故意杀人行为等同,则是不公正的。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再次进行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而这类案件的行为人通常都是主观恶性较低,对于杀人行为并无预谋而是临时起意,并且杀人行为事出有因,不属于累犯、惯犯,因此犯罪行为人的再次犯罪可能性很小,人身危险性也必然较低。因此对于这类“怨毒杀人”的犯罪行为人,不应当判处与普通故意杀人行为人相当的刑罚。这一类犯罪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小,因此改造难度也相应的较小,“减死一等”减为输作刑,对于犯罪行为人日后的改造也有很大的帮助。而类似“刘朱案”的这种“怨毒杀人”的行为,同样是属于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不应当与故意杀人行为的刑罚相当。“减死一等输作尚方”的量刑结果同样是考虑到其人身危险性并且有利于其改造的结果。
(四)对“被害人过错”的关注
在沈家本先生对“怨毒杀人减死”的另一释义中,可以看到,“怨毒杀人减死”包含有对“被害人过错”的关注,可谓是“被害人过错”这一现代刑法概念的萌芽。被害人过错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被害人权利运动”,作为一个从西方学界传入的概念,在当代中国受到学者重视与研究的时间则是在21世纪初。被害人过错强调对被害人权利的关注,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法律制度中的积极地位,使刑事案件被害人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第三者成为享有实在具体的程序法和实体法权利的当事人,打破了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二元刑事法律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三元刑事法律关系。“怨毒杀人减死”体现了古代立法者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对被害人本身具有过错的情节的关注,诚然,这种关注并不成熟,其仅仅局限在故意杀人罪这一罪名,且并未有深入的探究,然而,“怨毒杀人减死之令”作为对被害人过错有所关注的一个制度,可谓是对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初探。
三、“怨毒杀人减死”对我国现行法制之启示
(一)“怨毒杀人减死”与虐待罪的关联
“苛政猛于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无一不为这条定律所左右,历代王朝亡于苛政者也为数不少,如秦朝、隋朝等,因此,许多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注重对于刑罚严厉程度进行控制,施用轻刑。魏文帝曹丕颁布“怨毒杀人减死之令”便是如此,改变了自秦代以来的苛政和重刑制度。然而这项制度在三国魏之后的历朝历代立法中却几乎不见踪影。其后还有一起类似刘朱案的案件,也即在唐朝京兆府审理的一桩婆婆鞭打子妇案件中,该案因唐朝大臣、京兆尹柳公绰提出了“尊殴卑非斗,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才得以免于死刑,相比魏文帝时期的“怨毒杀人”的适用范围,唐朝时对其进行了严格限制,也就是仅限于尊殴卑致死这种情况。[2]218而唐之后的各个朝代立法直至现代的立法中,便极少见到“怨毒杀人减死”这一制度的踪迹了。
站在我国现行刑法角度看,“怨毒杀人”行为应与《刑法》第260条规定的“虐待罪”存在关联。“怨毒”行为表现为对被害人的长期虐待、殴打行为,刑法上的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给治病或者强迫作过度劳动等方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与古代“施加苦毒者”的行为相似。虐待罪在现行刑法中是亲告罪,属于不告不理的案件。虐待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有时候比较模糊,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某一行为是构成虐待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时,一般从主观故意上区分二者的界限,虐待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对被害人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在“怨毒杀人”中,通常行为人是对被害人进行折磨和虐待,没有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此外,虐待罪虽然是亲告罪,但并非绝对,亦存在例外情况,《刑法》规定:“犯本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不适用告诉才处理的规定。”所谓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是指由于被害人经常受虐待逐渐造成身体严重损伤或导致死亡,或者由于被害人不堪忍受虐待而自杀造成死亡或重伤。[7]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虐待罪的规定包括了类似古代“刘朱案”的情形,这种“怨毒杀人”情形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可认定为虐待罪,量刑较轻,最高刑为有期徒刑7年。笔者认为,虐待罪的最高刑之所以不会上升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因为虐待罪被告人与受害人同为近亲属关系,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犯罪,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故意杀人犯罪,并且虐待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死亡主观上只能是过失,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较低,因此法定最高刑也不宜过高。
(二)被害人过错应当法定化、明确化
“怨毒杀人”行为的另一释义,即行为人不堪忍受折磨而杀死施加苦毒者,这一规定体现了故意杀人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的问题。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情节较轻”的量刑,在实践中经常适用于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陈兴良教授认为,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的责任存在被害人加害在先,引起他人加害以及被害人激化矛盾,引起他人加害这两种情形。上述两种情形,都属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中,被害人的过错是酌定的从轻情节,它在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中具有重要意义[8]。酌定的从轻情节是由人民法院依法律的规定及立法精神,在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在量刑时酌情适用的案情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长期遭受虐待、摧残、折磨,因不堪忍受而动手杀死施加虐待、摧残、折磨行为者的,一般认为是属于情节较轻的情况[9]。这种情况属于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而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被害人长期实施迫害也属于“怨毒”行为,因此被害人对自己的死亡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对这种杀人行为应当减轻处罚。正如刑法期待可能性原理所表述的,根据行为人所处的现实环境,法律不能期待行为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合法行为,长期遭受虐待迫害的行为人实施了杀死虐待者的行为,法律同样应当考虑其所处的环境而对其进行宽大处理。不过,如陈兴良教授所言,被害人过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还不属于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只是属于酌定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也只是笼统的概括,并无具体的规定,对于“怨毒杀人”更是无任何规定。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相比之下,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立法的规定更为完善,如《澳门刑法典》第130条规定了“减轻杀人罪”①《澳门刑法典》第130条减轻杀人罪:如杀人者系受可理解之激动情绪、怜悯、绝望、或重要之社会价值观或道德价值观之动机所支配,而此系明显减轻其罪过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并同时列举了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又如《台湾刑法典》第271-275条亦详细列举规定了故意杀人罪的几种形式,其中第273条“义愤杀人罪”②《台湾刑法典》第273条义愤杀人罪:当场基于义愤而杀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则与“怨毒杀人”中遭受苦毒者因不堪忍受而杀死施加苦毒者的情形是相符的,对这类犯罪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比第271条的“普通杀人罪”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量刑明显减轻了许多。这一点应当值得我国现行刑法借鉴和学习。承前文所言,被害人过错并不局限于故意杀人罪,还应当涉及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对于其他犯罪,如与故意杀人罪同属于《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中的其他暴力犯罪,乃至侵犯财产类犯罪,都可能存在被害人过错的问题。从司法实践中观之,曾有检察官对浙江湖州市2005年的665件刑事案件进行调查,所涉及到的34个罪名的案件中,有11个罪名都涉及到被害人过错问题。而被害人过错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在判决书中被引用也已成常态化。可以看出刑事被害人过错问题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而不是孤立的存在。[10]
日本学者大谷实将被害人的概念界定为“生命、身体等个人法益受到犯罪危害的被害人”。起源于西方国家“被害人权利运动”的刑事被害人过错在20世纪末逐渐得到学者的重视和研究。进入21世纪后,学者对被害人过错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将被害人过错引入刑法的必要性层面,而是对被害人过错如何影响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性依据及被害人过错成立的具体条件等进行基础性与规范性层面的研究。虽然学界对于被害人过错的概念以及过错的界定还存在分歧,存在“广义说”与“狭义说”以及“主观过错说”与“客观过错说”之争③学界持“广义说”者观点认为:被害人过错是被害人实施非法行为对被告人产生突然的、强大的精神刺激,使其不能自我控制,在激愤的作用下对被害人实施犯罪;持“狭义说”者认为:被害人过错是致使犯罪行为发生的被害人自身存在的过失和错误;持“主观过错说”者认为:过错本质是一种应受谴责的主观心理状态;持“客观过错说”者认为:过错是一种行为而非主观心态。,但是学界仍然普遍认可被害人行为与刑事犯罪之间应存在关联性,并且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被害人过错是与加害行为相互作用的道德上或法律上应受到刑法意义上的否定性评价的行为”的观点。我国现行《刑法》对被害人过错没有明文规定,只有相类似的规定,如《刑法》第5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虽然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能够为被害人过错情节适用提供依据,但仅有这些规定明显不足。原因在于:第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被害人过错问题的案件,被法官判决最终认定或在量刑时考虑的还是占少数部分。绝大部分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案件,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并没有追究被害人的过错责任,没有因此而从轻处罚犯罪人。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过错各地的做法都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恶性暴力案件,不少地方法院实际很少考虑这一情节。第二,关于被害人过错不论是被告人还是法官都没有统一的概念与标准。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找的案例为例,不同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害人过错理由或大或小,最为离谱的例子是有一个案件中被告人提出的理由是被害人在十几年前抢过其两块钱;而在几个相似的故意伤害案件中,存在同样的被害人过错事实即被告人妻子与他人存有不正当关系,导致被告人报复其妻情夫,但不同法官对此的认定却不同,有法官认为这种行为是重大过错,有法官则认为这种行为是一般过错。不同程度的被害人过错认定导致对被告人最终量刑的差别很大。因此,如若《刑法》没有对被害人过错进行具体的规定,使被害人过错仅仅作为一个酌定从轻情节存在,被害人过错在量刑中的适用将会出现混乱而不规范的局面。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笔者认为,以故意杀人罪为例,可以在《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条规定的表述中增加具体的被害人过错情节,可以将被害人过错从酌定情节上升为法定情节。以义愤杀人为代表的“怨毒杀人”行为在现今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对于这样的案例,充分考虑被害人存在的过错与危害结果的关联性,因为被害人实施的毒打、折磨行为,危害性较大,超出了行为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所以在量刑中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法律的正义和社会的伦理德尚。如果判刑过重,有违民意,容易脱离群众,引起骚乱,有违刑法的立法宗旨。①《浅谈义愤杀人》,载http://china.findlaw.cn/bianhu/gezuibianhu/zuiming/guyishangren/41379_2.html。同时,也有违“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将“怨毒杀人”等义愤杀人行为作为量刑中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是必要的,而对于可能存在被害人过错的其他类型犯罪,也应当在《刑法》中明确“情节较轻”的具体情形。在将被害人过错由酌定量刑情节提升为法定情节的同时,还应当明确过错的等级,细化每一具体犯罪中被害人过错对量刑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被害人实施了违背道德的过错行为而导致自我被害的情形,更应当在法条中明确过错的等级和程度,若仅存在轻微、普通的不道德行为如嘲笑等,不应列入被害人过错。
可见,虽然“怨毒杀人减死”仅限于故意杀人或过失杀人行为,但其所体现的在量刑时充分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以及被害人的过错的原理,为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修改所借鉴时,应该涉及到其他罪名,而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刑法》中将被害人过错法定化与明确化是必要的。
三国魏文帝颁布的“怨毒杀人减死之令”,可谓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创举。它形成了对“怨毒杀人”案件的处断原则,并逐步将其制度化,体现了三国魏时期立法者对于刑法的谦抑、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初步探究,以及对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进行初步的关注。虽然在历史上,这一制度的存在并不长久,但是,魏文帝颁布的这一法令推动了后世立法的发展,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乃至对我国现行法制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对“怨毒杀人减死之令”的借鉴,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被害人的过错,同时在《刑法》中将被害人过错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明确化,将因义愤而杀人的故意杀人案件以及其他可能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案件的量刑处理进一步完善,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1]张晋藩,乔韦.中国法制通史:卷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张彬.魏文帝怨毒杀人减死制度初探[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4).
[3]陈兴良.刑法哲学(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223.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6-91.
[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
[6]高绍先.中国刑法史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4-55.
[7]徐松林.刑法学[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474.
[8]陈兴良.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问题研究——从被害与加害的关系切入[J].当代法学,2004(2).
[9]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39-640.
[10]周晓杨.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之实证考察[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9).
[11]范忠信,陈景良.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汪小珍)
DF092.361
A
1001-4225(2016)05-0074-06
2015-10-14
陈可(1991-),男,广东揭阳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