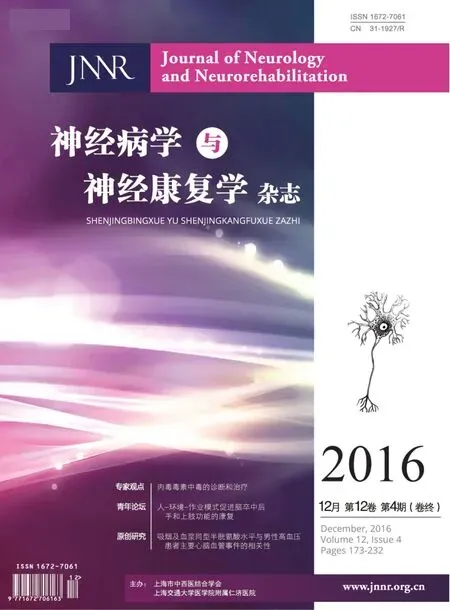高血压性脑出血后二次脑损伤的发病机制及中西医防治进展
孙传河,廖伟龙,高鹏琳,姜文斐,潘卫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脑病科,上海 201203
高血压性脑出血后二次脑损伤的发病机制及中西医防治进展
孙传河,廖伟龙,高鹏琳,姜文斐,潘卫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脑病科,上海 201203
高血压性脑出血是神经科急危重症,具有高致残率及病死率,当其发生二次脑损伤后,后果更加严重,死亡率显著升高。本文对高血压性脑出血后二次脑损伤的发病机制进行全面探讨,并从西医学和中医学的不同角度,对高血压性脑出血后二次脑损伤的定义、病因和发病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对西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性脑出血后二次脑损伤的策略进行综述。
颅内出血, 高血压性;二次脑损伤;发病机制;中西医结合疗法;大黄
二次脑损伤(secondary brain insult,SBI)是指在原发脑损伤[1]基础上并发继发性脑损伤;SBI可明显加重原发脑损伤和脑水肿,延长病理过程[2]。由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或是在疾病的自然进程中发生的SBI,被称为高血压性脑出血(hypertensive intracranial hemorrhage,HICH)后SBI,可导致病情发生迅速恶化并引发猝死。目前,西医对于HICH后SBI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而含有大黄的中药方剂则对其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3]。本文从西医学和中医学角度分别对HICH后SBI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探讨了基于上述理论的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HICH后SBI的现状,以期提升临床医生对HICH后SBI的认识,并为中西医结合治疗HICH后SBI提供参考。
1 HICH后SBI的诊断标准[4-5]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3分的HICH患者病情稳定时间>3 d时,如果符合如下8项中的4项就要考虑HICH后SBI的诊断:(1)NIHSS评分≥4分;(2)头颅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omputerized tomography,CT)检查证实脑血肿体积增大>30%;(3)体温≥39.0 ℃的时间>2 h;(4)收缩压/舒张压≤90/60 mmHg或单纯收缩压<90 mmHg持续>2 h;(5)血氧分压下降≥10 mmHg;(6)空腹血糖水平升高>3 mmol/L;(7)出现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失衡;(8)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ICP)>2.9 kPa或脑灌注压(cerebral perfusion pressure,CPP)<9.3 kPa。其中,NIHSS评分≥4分以及头颅CT检查证实血肿体积增大>30%是必备条件。
2 HICH后引起SBI的可能机制
2.1 HICH后的脑水肿及脑血肿体积增大加重病情
脑出血发生后数小时,血肿周围的脑组织就开始出现水肿,一般于3~7 d达到高峰[6]。血肿占位效应是导致脑水肿的最主要因素,占位效应可直接引起ICP升高,使血肿周围发生广泛的缺血和缺氧,继而生成氧自由基,并迅速释放兴奋性氨基酸递质,使缺血组织中血管的通透性增加,最终形成脑水肿。
此外,血浆蛋白、凝血酶和血红蛋白也均参与了脑水肿的形成。血浆蛋白渗出可使脑内局部渗透压升高,持续的渗透作用可导致脑水肿。血红蛋白诱发脑水肿的机制涉及血红蛋白分解产物血红素和铁离子的细胞毒作用以及血红蛋白自身的强神经毒性,可导致迟发性脑水肿。
脑血肿体积增大一般是指在患者的症状进行性加重时,其头颅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证实脑血肿体积较之前增大>30%[7]。脑血肿体积增大被普遍认为是由活动性出血所致,常见的相关因素包括出血部位、血肿形态、收缩压升高以及凝血功能异常等[8]。收缩压升高、出血时间延长和出血量增加均可使ICP升高,引发机体自动调节血压以升高收缩压,最终形成再出血的恶性循环。临床数据表明,丘脑部位的再出血发生率较高,其中不规则血肿较类圆形血肿更易发生再出血,从而扩大血肿范围,加重脑水肿。
2.2 HICH后的发热导致进一步的脑损害
HICH后引起发热的机制十分复杂,主要是由于脑出血后的占位效应,尤其是脑疝形成,压迫了丘脑下部的散热中枢而抑制了中枢散热功能,继而引起发热或加重发热[9];此外,HICH后发热也与局部脑组织坏死、红细胞破裂后被吸收以及其他组织和器官的继发感染有关。王子峰等[10]认为,当脑干发生出血时,由于阻断了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的调节功能而引起发热;此外,当脑干网状结构受损时,也会影响到局部血管的舒缩功能而导致体温升高。高热时,人体耗氧量增加,导致酸性物质的产生也增加,继而加重脑细胞的酸中毒,引起脑细胞水肿,引发脑组织代谢紊乱;当各种离子进入神经元细胞内,尤其是钙离子的内流,可导致线粒体中出现钙离子沉积,继而引起神经元死亡,最终导致或加重SBI[11]。GLOBUS等[12]研究发现,体温异常升高时产生的大量氧自由基也可诱发后期神经元死亡。动物实验亦发现,体温升高可直接加重乳酸堆积而引发神经元死亡[13]。
2.3 HICH后的低血压进一步加重原发性脑损伤
脑干功能受损和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是导致HICH早期发生低血压的主要原因[14]。低血压可直接降低有效的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和CPP,从而进一步加重缺血和缺氧,引起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匮乏以及细胞膜泵功能衰竭,最终加速神经细胞死亡。此外,低血压所致缺血引起的脑组织水肿也会影响动脉周边区域[15]。费舟等[16]发现,弥漫性脑损伤合并低血压时,血栓素A2(thromboxane A2,TXA2)增多可引起血管痉挛、血小板聚集以及血栓形成,加重原发脑损害周边脑组织和细胞的进一步受损。
2.4 HICH后的低氧血症进一步加重缺氧性脑损害
有学者认为,导致低氧血症的因素在病程的不同阶段亦有所不同,早期由交感神经系统过度兴奋、血儿茶酚胺类增多以及肺功能障碍所致,后期则是与呼吸道分泌物增加、排痰功能下降以及并发感染导致肺通气和气体交换功能减弱,继而引起低氧血症有关[14]。HICH时,颅内延髓化学感受器与延髓反射中枢以及脑桥上部的呼吸调整中枢均会因为受到出血部位和血肿大小的影响而引起低氧血症。此外,脑组织对缺氧的耐受能力很差,低氧血症时易形成脑的代谢性酸中毒,使脑血管通透性增加,继而加重脑水肿。HELLEWELL等[15]发现,弥漫性轴索损伤合并低氧血症后,轴索损伤区域出现大量巨噬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聚集,由此认为低氧血症可能通过刺激炎性反应而损伤神经元。朱坤灿等[17]认为,低氧血症时谷氨酸大量蓄积,其兴奋性毒性可加快神经元的坏死和凋亡。此外,低氧血症可以通过兴奋主动脉和颈动脉的化学感受器引起过度通气而导致碱血症,继而加重脑组织的缺氧,引发进一步的损害[18]。
2.5 HICH后高血糖促进细胞凋亡并加重脑水肿
HICH后高血糖由应激反应所致。张光明等[19]认为应激性高血糖主要由如下原因所致:(1)脑血肿和局部水肿的占位效应通过刺激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引起交感-肾上腺系统功能亢进,继而增加升血糖激素的释放;(2)甘露醇、降压药物和激素的不合理使用,引起胰岛素分泌减少和胰岛素敏感性降低;(3)末梢组织和器官出现胰岛素抵抗;(4)脑干的糖调节中枢受损。应激反应引起的高血糖可使乳酸生成增加,不仅可以直接损伤脑组织,还可促进CO2生成;高浓度的CO2可直接扩张血管,使CBF出现异常增加,升高ICP,最终导致脑损伤[20]。有研究者发现,高血糖时血浆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等炎性因子的水平较高,推测高血糖可能通过炎性因子介导细胞凋亡;此外,高血糖还可促进氧自由基生成以及诱导缓激肽生成,从而加重脑水肿。
2.6 HICH后的电解质紊乱通过破坏血脑屏障而加重脑水肿
HICH后发生高钠血症主要与丘脑和下丘脑功能异常有关:(1)当丘脑出血时,下丘脑分泌抗利尿激素减少,可导致中枢性尿崩症[21];(2)丘脑出血可通过刺激交感神经皮层下中枢,产生异常的交感神经兴奋,继而导致Na+重吸收增加;(3)下丘脑-垂体系统受损可影响下丘脑-垂体-盐皮质激素(醛固酮)轴,引起渗透压感受器或渴中枢功能障碍,导致渗透压感受器阈值上升、渴感反射调节机制丧失以及机体排钠减少,最终引起高钠血症。
HICH后发生低钠血症的原因主要与钾摄入不足、利尿剂的不合理使用以及脑损伤后引起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有关。HICH后出现低钾血症的主要原因包括:(1)钾摄入不足,大多由患者进食不足或补钾不足所致;(2)代谢性碱中毒,即肾小管H+—Na+交换减少导致K+—Na+交换增强而致肾排钾增加,并促使细胞外K+转移至细胞内;(3)过度使用利尿剂后,一方面通过抑制Na+和Cl-的重吸收导致远曲小管Na+增加,而Na+—K+交换加强可进一步引起失钾,另一方面由于血容量不足而刺激醛固酮的分泌,继而影响电解质平衡;(4)过度使用胰岛素后,通过增强Na+-K+-ATP酶的活性,可促使K+转入骨骼细胞和肝细胞内,继而使细胞外液中的K+减少,导致低钾血症。各种电解质紊乱既可使脑细胞膜受损,造成ATP酶活性和磷脂代谢的障碍,最终引起神经细胞的变性和坏死;还可损害血脑屏障,使血浆蛋白和电解质逸出至血管外,增加细胞外渗透压,从而加重脑水肿。
2.7 HICH后的酸碱失衡引起酸/碱中毒,继而引发脑细胞死亡
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和代谢性碱中毒是HICH后最常见的酸碱失衡类型[22]。引起呼吸性碱中毒的原因包括:(1)严重的慢性低氧血症;(2)IPP升高以及过度兴奋呼吸中枢导致过度通气;(3)高热、感染和疼痛等因素导致呼吸频率增加;(4)各种原因引起的焦虑、紧张和强迫呼吸等;(5)人工辅助呼吸使用不当,如呼吸频率过快或潮气量过大。引起呼吸性酸中毒的原因包括:(1)脑出血后的占位效应使呼吸中枢受到抑制,引起CO2潴留;(2)颅内病灶影响脑干的呼吸中枢,继而并发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3)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引起代谢性酸中毒的原因包括:(1)应激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增加、低氧血症、继发癫痫、继发感染、高热和休克等因素均可导致乳酸堆积;(2)进食过少或无法进食以及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在遭受应急时更易引发酮症酸中毒;(3)使用利尿剂、缺血和缺氧等均可导致肾功能障碍而使酸性物质排出减少;(4)输入高能营养液如阳离子酸或不含HCO3
-的0.9% NaCl溶液,均可引起高氯性代谢性酸中毒。引起代谢性碱中毒的原因包括:(1)长期大量使用利尿剂或糖皮质激素;(2)钾摄入不足;(3)过量使用碱性药物引发高碳酸血症后的碱中毒。酸碱失衡引起的脑组织和细胞的病理变化或者使病情加重的机制均较为复杂,往往不是直接发生,但却常常引起全身各脏器的损害,最终加重脑出血所致的损伤,继而诱发或直接加重HICH后SBI。
3 HICH后SBI的中医病机
HICH或HICH后SBI多伴有反应迟钝、嗜睡、失语、精神行为异常甚至癫痫等脑功能受损的症状,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中医学理论认为,脑出血或脑出血后SBI属于“中风”“中脏腑”范畴,其病机涉及多种理论。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内风”学说。大量的临床观察性研究发现,便秘或腑气不通证候可以发生在脑出血急性期,并且可以持续数周以上。在气虚体质的人群中,以血瘀和痰浊为诱因而发生出血性卒中时,由于气虚不能摄血以及血液运行无力而致出血与瘀血并行;气虚可致水湿运行失常,淤而化痰,继而与瘀血相夹杂,痰瘀互结,痹阻脉络,引起气血逆乱,上犯于脑或流窜于经络,渗溢于脉外则为脑出血[23]。出血性卒中大多发生于中老年人,这类患者大多患有肝肾亏虚,每因情志不遂或受到饮食不节等不良因素的刺激,以致“形气绝而血菀于上”“血之于气并走于上”,进而发作为脑出血,血溢脉外而成离经瘀血。临床发现,发生脑出血后SBI时,主要表现为中脏腑,患者除有昏迷和半身不遂等症状以外,往往还有气粗、口臭、便秘、躁扰不宁、舌质红、舌苔厚燥或腻以及脉弦滑数等证候。大多数学者认为,脑出血急性期时,相当一部分患者属于痰热内闭心窍及风火上扰清窍证型[24]。
4 HICH后SBI的防治进展
4.1 HICH后SBI的西医防治进展
目前,对于HICH后SBI的防治措施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在临床实践中,通常以治疗原发病为主,而对SBI仅进行对症处理,所以往往会再次引发脑损伤。因此,必须在现有防治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更加有效的防治方案。
4.1.1 HICH后发热的防治
在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5]中,虽未提出具体的治疗措施,但一些研究发现尽早进行亚低温治疗可以在有效减轻HICH后脑水肿、降低IPP的基础上,预防高热和呼吸循环障碍。
4.1.2 HICH后低血压的防治
HICH后低血压防治的重点在于选择合适的降压时机、合理使用降压药物以及对血压执行严密的连续监测。在选择降压药物时,应首选起效快、半衰期短的一线静脉用制剂,并且确保能够有效地监测血压;同时,慎用口服或含服的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对于已发生的低血压或血压相对较低的情况,应及时进行补液、输血和抗休克治疗,并针对病因和症状给予针对性的有效处理。
4.1.3 HICH后低氧血症的防治
对于急性期患者,应保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除口腔和鼻腔内的异物,同时监测血气分析。一旦发现通气功能欠佳或出现低氧血症,应及时进行气管插管和氧疗,必要时行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并使用有效的抗生素。国内有学者报道,在HICH后尽早进行高压氧治疗,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治低氧血症,还可以使患者在治愈率、预后、康复结局和生活质量等各方面均获益[26]。
4.1.4 HICH后高血糖的调控
胰岛素是控制HICH后高血糖(血糖水平>10 mmol/L)的首选用药;其次是要加强血糖监测以及限制含糖液体的静脉输注。然而,由于脑干出血导致血糖调节中枢受损引起的高血糖可以长期存在,因此可能同时引起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失衡。
4.1.5 HICH后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失衡的防治
对于HICH后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失衡的防治,脑血管病相关指南尚未明确提出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在临床实践中主要根据症状和体征以及实验室指标制定对症治疗及病因预防措施。此外,HICH后电解质紊乱引起的症状十分复杂,易与HICH引起的神经症状相混淆,因此易被忽视,而导致高病死率,所以一旦发现电解质紊乱应及时予以纠正。防治酸碱失衡的重点在于及时治疗原发病以及保护好在维持酸碱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肺功能。
4.2 HICH后SBI的中医药防治进展
中医药防治HICH恶化或HICH后SBI显示出较好的疗效。JIANG等[3]发现,口服脑血疏口服液(大黄蛰虫丸+补阳还五汤)可以显著减少HICH后SBI发病率,并且减轻HICH患者神经功能的缺损。廖莎等[27]采用大承气汤加味中药防治HICH患者的急性期发热,结果发现中药组的急性期发热和神经功能缺损均较西药组显著减少。有学者发现,含有大黄的中药联合亚低温疗法可以明显改善HICH患者的临床症状,并降低死亡率[28]。一些研究发现,单用大黄这一味中药即可减轻脑出血大鼠的脑水肿并抑制伊文思蓝透过血脑屏障,提示大黄可有效减轻脑水肿和保护血脑屏障。现代研究发现,大黄中含有葱醒类衍生物揉质、游离酸和钙等物质,对于外出血和内出血均具有良好的止血作用,可以缩短凝血时间。大黄还有助于促进神志苏醒,加速神经功能的恢复。许多研究证实,对于脑出血,大黄除了具有止血作用以外,还能促进脱水,从而减轻脑水肿[29]。因此,使用含有大黄的中药制剂或是单用大黄即可有效地防治HICH后SBI。
4.3 HICH后SBI的中西医结合防治进展
综上所述,HICH后高热、低血压、低氧血症、高血糖、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的最终结果是使ICP升高、CPP持续下降,导致脑灌注不足。如果病理因素持续存在,就会发生全脑性的缺血缺氧,最终引起ATP匮乏,导致细胞膜功能衰竭而致细胞死亡。随着对HICH后SBI发病机制的日益明确,HICH后SBI的防治水平必将得以提高。目前,西医在防治HICH后SBI方面尚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中医药防治可能成为重要的突破点。含有大黄的中药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可使HICH后SBI得到有效的控制。王明哲等[30]在患者发生HICH后立即给予含大黄成分的脑血疏口服液治疗、脑血疏口服液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或是西医常规治疗,结果发现脑血疏口服液联合西医常规治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有效防治HICH后SBI,促进神经修复,降低脑出血致死率和致残率,其机制可能与减轻脑水肿的占位效应、促进血肿吸收、减少毒性刺激和抑制炎性因子有关,最终减少SBI的发生,且不良反应较少。此外,药理学实验[24]也证实,大黄可以加速脑出血大鼠的血肿吸收、减轻ICP、改善脑组织血供以及氧分压等。随着康复医学的兴起,早期进行康复干预、实施个体化的康复计划以及康复科医师与神经科医师之间协同合作,不仅能够保障卒中单元的有效实施[31],也给HICH后SBI的治疗带来了希望。最后,由于改变环境可使神经功能得以恢复,例如通过加强肢体活动和增加学习经历等来丰富患者的环境,不仅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还可以促进神经重塑[32],这也为HICH后SBI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方向。
[1]MlLLER J D, SWEET R C, NARAYAN R,et al. Early insults to the injury brain[J].JAMA, 1978, 240(5):439-442.
[2]谢道珍, 顼宝玉, 孙 怡, 等. 脑血疏口服液治疗出血性中风的临床研究[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07, 5(8):690-691.
[3]JlANG H, QlN Y, LlU T,et al. Nao-Xue-Shu oral liquid protects and improves secondary brain insults of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J].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6:9121843.
[4]胡福广. 重型颅脑损伤合并二次脑损伤的临床研究[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2003, 29(4):299-300.
[5]刘兴波, 衣服新, 罗俊生, 等. 二次脑创伤临床诊断指标的初步探讨[J]. 辽宁医学院学报, 2002, 23(3):1-3.
[6]陈 娟, 赵爱英. 脑出血后迟发性脑水肿与甘露醇治疗的临床观察[J].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2009, 6(1):39-41.
[7]王罗军, 林达伟. 高血压性脑出血早期血肿扩大的相关因素分析[J].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2006, 3(3):129-130.
[8]林 智, 潘瑞福. 高血压性脑出血CT影像学与预后相关性研究[J].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2009, 6(2):95-99.
[9]李培珍. 高血压并脑出血急性期体温与预后分析[J]. 右江医学, 2008, 36(1):76-77.
[10]王子峰, 赵玉环, 毕双梅. 脑卒中急性期体温与预后关系214例分析[J].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01, 14(2):122-124.
[11]潘 辉, 隋冰冰, 董长峰. 亚低温对重型颅脑损伤后高颅压及凝血异常影响的临床研究[J]. 中国综合临床, 2003, 19(4):340-341.
[12]GLOBUS M Y, BUSTO R, LlN B,et al. Detection of free radical activity during transient global ischemia and recirculation: effects of intraischemic brain temperature modulation[J].J Neurochem, 1995, 65(3):1250-1256.
[13]GlNSBERG M D, BUSTO R. Combating hyperthermia in acute stroke: a significant clinical concern[J].Stroke, 1998, 29(2):529-534.
[14]刘范君, 徐海金, 肖晓莉. 二次脑损伤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预后的影响[J]. 临床军医杂志, 2009, 37(6):1102-1103.
[15]HELLEWELL S C, YAN E B, BYE N,et al. Posttraumatic hypoxia exacerbates tissue damage analysis of anonal injury and glial responses[J].J Neurotrauma, 2010, 27(11):1997-2010.
[16]费 舟, 章 翔, 易声禹. 大鼠弥漫性脑损伤合并二次脑创伤时脑血栓素A2及前列环素的变化[J]. 中华创伤杂志, 1997, 13(2):105-106.
[17]朱坤灿, 王洪财, 马延斌. 创伤性脑损伤合并低氧血症性二次脑损伤的研究进展[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2013, 8(1):66-70.
[18]李旭丰, 费英芝. 急性脑卒中144例动脉血气分析[J]. 承德医学院学报, 1990, 7(4):227-230.
[19]张光明, 黄荣华. 胰岛素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后应激性高血糖[J]. 现代医药卫生, 2009, 25(3):350-351.
[20]费舟, 晁晓东. 加强二次脑损伤因素的循证医学研究[J]. 解放军医学杂志, 2012, 37(2):90-93.
[21]张建军, 顾水均, 朱镇宇, 等. 重症脑损伤急性期患者钠代谢失衡特点与其预后关系[J].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1999, 11(3):158-160.
[22]陈玉熹. 脑卒中病人血气变化的探讨[J]. 河南诊断与治疗杂志, 2002, 16(1):10-11.
[23]龚 立, 王静予, 孔令军, 等. 祛瘀化痰通腑法治疗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的临床观察[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29(4):24-26.
[24]唐宇平, 蔡定芳, 刘 军, 等. 大黄改善急性脑出血大鼠血脑屏障损伤的水通道蛋白-4机理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6, 26(2):152-156.
[25]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014)[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5, 48(6):435-444.
[26]岳喜进. 高压氧治疗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脑氧代谢的影响[J].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4, 17(19):113-114.
[27]廖 莎, 彭德辉. 大承气汤加味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急性期发热30例临床观察[J]. 中国医疗前沿, 2011, 6(14):26-28.
[28]尹晟. 羚羊角口服液联合亚低温疗法治疗急性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疗效观察[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8.
[29]孔令越, 陈汝兴. 生大黄治疗脑出血疗效观察[J]. 中国中医急症, 2005, 14(7):601-602.
[30]王明哲, 张 亮, 姜文斐, 等. 益气化瘀豁痰法防治高血压脑出血后二次脑出血的临床疗效及机制研究[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 11(11):129-132.
[31]李 梅, 王慧萍, 陈玉芳, 等. 早期康复治疗对急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2011, 8(1):4-6.
[32]季 力, 崔 晓. 丰富环境对脑神经可塑性的影响[J].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2013, 10(2):99-101.
Advances in pathogenesis of secondary brain insults after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N Chuanhe, LIAO Weilong, GAO Penglin, JIANG Wenfei, PAN Weidong
Department of Encephalopathy, Shuguang Hospital Aff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The hypertensive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HICH) is a critical neurological condition which has a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hen HICH is complicated by secondary brain insults, it will lead to more severe outcomes and a high mortality. This paper aims to completely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secondary brain insults after HICH according to diferent views from Western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volved in definition,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Western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for secondary brain insults after HICH are also summarized.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hypertensive; Secondary brain insult; Pathogenesis; TCM WM therapy;Rheum officinaleTo cite: SUN C H, LlAO W L, GAO P L,et al. Advances in pathogenesis of secondary brain insults after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Neurol and Neurorehabil, 2016, 12(4):215-220.
PAN Weidong
10.12022/jnnr.2016-0052
潘卫东
E-MAILpanwd@medmail.com.cn
孙传河,廖伟龙,高鹏琳,等. 高血压性脑出血后二次脑损伤的发病机制及中西医防治进展 [J].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2016, 12(4):215-220.
E-MAIL ADDRESSpanwd@medmail.com.cn
CONFLlCT OF lNTEREST: The authors have no conficts of interest to disclose. Received Aug. 16, 2016;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Sept. 20, 2016
Copyright © 2016 byJournal of Neurology and Neurorehabili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