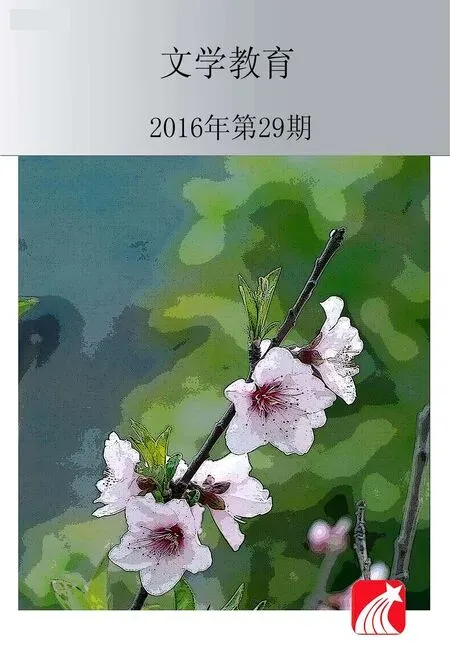红尘梵音的守望
——读邓诗鸿《一滴水也会疼痛》及《青藏诗篇》
陈亚奇
红尘梵音的守望
——读邓诗鸿《一滴水也会疼痛》及《青藏诗篇》
陈亚奇
诗人可以爱任何人,意为诗人要有博爱悲悯的心去感触世界,他的诗才能在别的心灵那里引起共鸣。邓诗鸿便是这样一位诗人:他的诗歌不仅博爱,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离散之苦在其中。诗人用一颗敏感的心行走红尘感触种种的物象,并用这些物象描绘出对于灵魂归属的渴望和向往,进而营造起自我的诗歌世界。
邓诗鸿 诗歌 一滴水 疼痛 故乡
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探索一直都是文学作品中不断呈现的主题。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以女娲补天剩余的一块通灵石头入世为人,阅尽人世繁华,洞观人生百态。邓诗鸿则是行走在红尘中的“一滴水”来观感世界,并用种种物象来描述和构筑人世的百态人生。他笔下的诗人也不再是像诗仙李白白衣着身,金樽在手,洒脱的让众人钦羡;更不再是苏仙苏轼蓑衣挡雨,行走天涯,辉煌的让后世仰望千年。
在他笔下,诗人是一滴行走在异乡的水,一滴曾在天堂伴随上帝左右的水,带着“世界上若有一个人受苦,全人类就要一起哀痛。”的信仰,作为使者被上帝派往人间去替他经历人世,尝尽苦难。因为他远离故乡,所以“按捺不住的乡思和离愁,在滚动,在聚集”在微茫的震颤中终成裂岸惊涛!由此故乡变成了诗人内心无法跨越的海洋.以诗歌为梵音表述自我对于灵魂故乡的守望和皈依。
一.红尘故乡
1.行走在红尘中的一滴水
诗人在他的《写在前面的一点感想》中如是说:在情感剥离,思想抽空,灵魂缺席的大面积覆盖诗坛的语词丛林中:面对挣扎着的芸芸众生,这是否意味着需要诗人们的二度觉醒,诗人们必须将痛感还给语言,而使诗歌面对生命与万物不再麻木……”作为一名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的值岗中总不免对汇聚到此、并匆匆而过的人、物细细观察:神色恍惚的下岗老司机,闯红灯的民工和母亲,被急促的喇叭声驱赶的持杖老人,暴雨中孤独的人力车夫,抛锚的长途汽车,破旧的三轮车,以及拥抱着相互取暖的废弃轮胎,和被车辆碾压朝行人四散飞溅的一洼水。他们都是行走在红尘中的卑微的灵魂,有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拼凑成这个城市完整的模样。于是诗人忍不住发出感叹:
“这破碎的瓷,玻璃的残骸
谁能窥视你心中的疼痛与圣洁
风在吹,缝在梦境中翻动着乡情
一滴水在风雨中疾行
它追逐着流水、波涛和飞雪
却让疼痛,静静的覆盖一生
一滴疼痛的水
在异乡,最终成为坚冰”
一滴水,行走在人世红尘,他眼中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被庞大的社会机器操控的卑微灵魂,他们之所以在路上行色匆匆,是出于对家的渴望和故乡的怀想。由此在诗人笔下多次以“异乡人”自居:“一个异乡人,独自行走在喜马拉雅”(《内心的喜马拉雅》),“如果一篇雪花,在视野中转身离去/它会不会影响,珠穆朗玛/在一个异乡人心中的高度……”(《一个人的珠穆朗玛》);“这一粒粒霞光,雀跃着,伸出温暖的双手/让一个遥远的异乡人,羞愧万分”(《我突然深深地爱着两种事物》)。在诗人笔下,每一个人都有“异乡人”是与“本土人”的双重身份,之所以成为“异乡人”是出于对“故乡”的逃离。
2.“异乡人”的疼痛
对于故乡逃离,却并非是出于自愿。“清晨,村庄在露水里轻轻摇晃/绕过梦中的流水、小桥、和炊烟”村庄的美丽“婉约、纤细,猝不及防……”(《露水里的村庄》)然而回首前尘,是什么打破了村庄自然的宁静和安详?又是什么逼迫得我们的民众在自己的故土上背井离乡?近代以来,我们的祖国在血泪中跌入低谷,战争和外敌的入侵残暴的摧残蹂躏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我们在深重的苦难中逃离家园,背井离乡,寻求富足强国之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物质的洪流已不可抵挡之势闯入中国。我们自己的文明在战火的废墟之上开出不伦不类的物质文明之果。文化被称为是“形而上的怪兽”唯恐被人谈起,诗人更是像文化乞丐般步履维艰。
“长风中,谁在翻捡着现代文明盛产的垃圾/像一滴泪,掀开它永不愈合的伤痛/某年某月某日的午后遇见她/一滴灰尘咬咬牙,紧跟着一群苍蝇/落在她花白的头顶——多么于心不忍/阳光照亮了她的疲惫、困顿、局促/和无所适从……”(《风中的母亲》)“母亲”的困顿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些行走在他乡的“异乡人”的悲哀和无法诉说的苦痛呢?“我熟悉这漫漫的晨曦,和曦光中/弥散的宿命,通向虚空的天幕/分开善恶的小径,骤然逼近的苍凉/和支离破碎的月色,一点点释放出/摇摇爇短的炊烟,随风纷溅的泥浆,/和弯腰汲水的粗布衣裳……”(《晨曦》)我们熟悉的故乡已然变了模样,在现代物质文明的挤压下大肆荒芜……然而,当“补丁、布衣、绑腿……”等我被物质文明淹没并抛弃的名词一次次的出现在诗人的诗篇,我猝然发现,在这个物质洪流奔腾而下的时代,诗人那一滴水的疼痛是这红尘中天籁梵音的守望,给众多疲累焦灼的灵魂故乡般的柔软和依靠。
二.红尘梵音
1.诗歌的故乡
说到诗歌就必然会提到唐诗,那是我们中华文化光辉璀璨的见证和结晶,诗歌便是从哪里出发走向世界,那便是诗歌和诗人魂牵梦绕的故土乡音。那曾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健朗和洒脱,也曾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肃穆萧杀。但无论怎样都挡不住后世的仰望和欣赏。唐诗宋词里的诗歌世界也渐渐了成为了诗人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那种深沉得向往也已经随着血脉涌进灵魂深处,在夜色深沉得寂静里随风潜入梦。
“我们在思想的纵深处
吟诗作赋 擎盅劝酒
毫不保留的相互倾诉
它们同我 难舍难分
独自去唐诗中散步
这个习惯由来已久”(《在唐诗中散步》P132)
在诗歌的故乡与三两个好友把盏弄影、谈笑风生是何其惬意、何其欢畅!似乎人生一世就只如光阴一瞬。行走在唐诗的诗情画意之间,就好比跟仙风道骨悲天悯人的诗人们进行思维纵深处灵魂的对话。甚至是随手拈来的一些蛙鸣也会在顷刻间化为最动人的诗句,敲打着诗人孤寂清瘦的身影,惹出一汪一汪的乡愁出来。然而故乡在现实中是触不可及的幻影,梦里的美好和温暖只能加深现实中的伤痛。
2.呓语的乡愁
“在回忆中爱是一种甜蜜的痛,犹如一只小花虫
对画册里所有芬芳的开端
都只能在想象中结束”(《娓娓而来的空酒杯……》P134)
那种山河仍在,故乡难回的惆怅压抑在心中穿越岁月的河流和距离的阻隔,在现代和那个在与祖国隔离的海岛上苦吟着“乡愁”翘首盼望祖国的诗人引起共鸣。无论是穿越时光的河流还是跨越距离的阻隔,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诗人在致余光中的诗行中说道:乡愁是一直疲惫的蝴蝶。“邮戳风尘仆仆,蝶驮着沉重的情绪/怆然间/累倒在我的桌面”“蝶疲惫了,在残雾茫茫的秋之湄/一种沉重的情绪,已踮起脚尖/在每一棵树梢/高高地眺望”(《乡愁是一只疲惫的蝶——致余光中》)
在《一颗白菜行走在返乡的路上》中,诗人以一颗白菜隐喻奔波在回乡路上的“异乡人”,并以讲故事的手法猜测一颗行走在返乡路上的白菜的前世今生:“他是不是在前往超市的途中/开了小差;抑或,是从商业的缝隙中逃了出来……”“喧嚣散尽,浮华散尽……一条郁结愁肠的小路,让一颗返乡的白菜于万木霜天中,怯生生地探出头来你看他受惊的双眸,慌乱地打探着突然变得陌生的世界……”(《尾随着一棵返乡的白菜》)逃离并非是逃避,而是听到了故乡母亲的召唤和执着的盼望与等待,因为等待,母亲依然在村口站成了树的姿态。“风中树一样召唤的母亲啊/除了你,谁能将他们聚拢在月下/返回家乡?”(《尾随着一棵返乡的白菜》)
游走在城市的文明中,血液里是喷薄欲出的乡愁。在这个急速运转的时代,似乎连停下脚喘息的机会都成为了奢望。在人潮汹涌的现代都市,尘世喧嚣,物欲横流;每个人为了更好的物质享受而逃离灵魂的故乡,辗转奔波,风霜扑面,任久不打扫心房灰尘垒垒,蒙尘的心灵也日益灰暗麻木,甚至最终成为坚冰。《沉默的大多数》中对于赣江,沙仙村,草帽的书写,再现诗人梦中回不去的故乡的渴望和疼痛的怀想。诗歌里浓重的乡愁才能唤起早已遗忘的乡音,给疲累的灵魂带来梵音般的洗礼和灵魂的震颤。
三.红尘中的守望
1.重提乡音
“夕阳下,谁在翻晒着灵魂深处的补丁?”(《高台民居》)是那个静坐的人。“静坐的人,在疯狂的钢筋水泥中/躲进了更为幽暗的内心/他触摸到灵魂的坚硬/和冰冷”。伫立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便是繁华中静坐的人,因为静,他看到了:“猥琐、怯弱、甚至有点脏”的“屋檐下的农民工”,他们被暴雨驱赶,“带着伤口、疾病和血泪,在闪,在躲,在远离……”然而更深的伤痛确是来自于他们用汗水和辛劳供养的城市人中眼中的警惕和鄙视,“加深了城市的鄙视和遗弃”。(《屋檐下的农民工》)他看到了:一些可遇而不可求的坏天气,让“一位身材娇小的外来女工/哦不,一部奔跑的马达/一台轰鸣的机器……”停止了转动和轰鸣,在一场雨后的“疲惫和累,倦怠和困顿”。(《一些可遇不可求的坏天气》)他看到了:满脸油污、满身汗水的擦皮鞋的人,为了生活在城市中走街串巷,“那双干瘪、锈蚀而青筋突暴的双手”也许“昨天还在张网、锄草、捞粪或者插秧”,今天便出现在城市的街巷为小姐、老爷、公子们服务。(《擦皮鞋的人》)还有“目光浑浊,表情阴郁而愁苦”的摆地摊的人,“简单、粗鄙的生活”。(《摆地摊的人》)以及“那些拉煤球、摆地摊、擦皮鞋的人/那些农民、渣滓、苦力和贩夫走卒/他们起早摸黑,风餐露宿,咬紧牙关/或者打掉牙往肚里咽,他们连脸上的血和泥/都来不及擦拭,目光在风中无力地翻卷”。(《心灵史》)
诗人眼中的世界是定格在十字街头的画面,每一张为了生活所奔波的“异乡人”的脸,在繁华且冷落的都市里沦陷。这些卑微且坚韧的灵魂默默的挣扎在社会的底层,泥浆满身、风沙扑面。而那个伫立在十字街头的“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我也将消失,多年以后
当我一次次写到:我们这些卑微的灵魂
写下挥汗如雨的动向,和他们大痛如玉的乡情
写到汗水,就仿佛拨动了天上的大琴”(《我们卑微的灵魂》)
面对逃离故乡,奔赴城市,在都市底层劳动的群体,诗人总是以一颗赤子之心与他们站在一起,每一滴疼痛的水汇聚在一起,荡起了诗人心中的涟漪,而涟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我们的这些卑微的灵魂”。在黑夜发出的惆怅而又苦痛的叹息,便汇成了无需沟通的乡音,乡音汇聚成“令人心颤的一条河流,令人心颤的流水,波涛和涟漪,以及尾随其后的形而上的光阴,惊醒了生命中的沧海,照亮了千年无语的水伤,多少年来,一直在我的心头澎湃”《河流》。
2.执着的守望
一滴水,行走在人世红尘。他的指尖触摸到的生命的苦痛和煎熬,是诗人从基督的情怀出发对世人的悲悯。诗人眼中的世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作为“一滴疼痛的水”虽然不能改变世人的处境,却可以通过诗歌唤醒他们在物质世界渐进迷失的灵魂。诗人就好比“花生,红薯,秧苗”在物质文明的都市默默生存,“在城市文明的边沿/渺小/卑微/伸手可及”默默地坚守,执着的守望。诗人说:“多年以来,我试图沾着自己的鲜血和骨髓,通过诗歌介入与世界和心灵的本体对话。”把诗歌当成心灵与心灵沟通的桥梁,用语言的诉说来描述生命的苦难和碎片在灵魂中刹那间的呈现。在诗歌以故乡为主题唤醒“我”和我眼中的“他们”最后成为“我们”,就像一滴滴水汇聚一起成为涟漪,流水,波涛和翻涌的沧海。所以诗歌是心中翻涌的一滴水既有着沧海蝴蝶般落寞的苍凉与绝美,也有着裂岸惊天的豪迈与雄壮,更有在落叶缤纷的小路上,渺茫的生命顿悟。(《我踏上了落叶缤纷的小路》)以一滴水的形态行走红尘,诗人试图把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变成诗歌得以呈现。但是“我并不赞成诗歌作品以承担为己任,也不主张极端的自恋式的个人主义的诗歌写作。”诗人认为诗歌应该是可以通过物象所表述的灵魂的独白,而这独白便可称之为“乡音”。所以他多次在诗文中提到“碎片”、“补丁”“布衣”,因为在诗人看来“一枚补丁,它的出现带来一次/灵魂的颤栗/与远征”,布衣,对于你,眼中总是/饱含着血泪与饥馑。”似乎,一滴水的疼痛从“碎片”破碎的凄美中呈现,灵魂的触动和觉醒从“布衣”、“补丁”这些具有丰盈的精神内涵的贫瘠中迸发。对于故乡的渴望也由此从卑微的灵魂呐喊中去呈现。
邓诗鸿认为“诗歌,承担了一切痛苦,一切激情和忧伤。”诗歌“有一种扎根生存状态、呈现悲悯本性的道德力量,它拔出了深深扎进我们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在这个浮华的物化时代,邓诗鸿的诗歌带着这样一种悲悯的情怀,用语言编制一座城堡,带给读者一个可以信赖的、宗教般的心灵故乡。对于诗歌的追求,正如诗人所说:“开拓更开阔的意象,抓住生命中更长久的、尖锐的痛感,让读者有铁丝穿过心脏的痛和乌云压过头顶的重,让读者有豁然开朗的陌生感,有深深哭泣的愿望和长久沉默的震撼。”从邓诗鸿诗集中饱满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对于灵魂故乡的探求和渴望,给我们行走在红尘,风霜扑面的我们一个梵音的守望。
[1]邓诗鸿《一滴水也会疼痛》,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版
[2]邓诗鸿《青藏诗篇》,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版
(作者介绍:陈亚奇,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