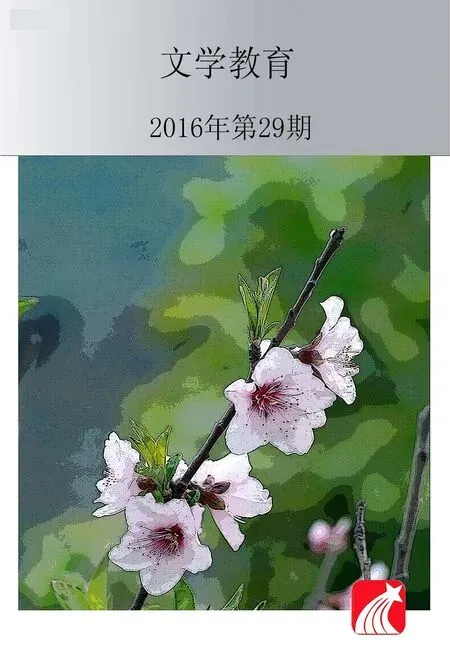穆时英小说感觉化的故事建构
毕金林
穆时英小说感觉化的故事建构
毕金林
穆时英开启了真正的现代中国都市小说。在上海这个带有近代工业文明和殖民性特征的畸形环境中,以感觉作为创作的基点与核心,靠直觉来把握社会人生,创造出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异样的艺术世界,为都市叙事引入了一种新的叙述意识。
穆时英 小说 感觉化 故事建构
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的中坚,穆时英的小说吸纳借鉴欧美和日本的现代小说的新元素,将都市故事内化为直觉的呈现和感受的外化,“将五官的感觉,练得及其细腻,及其灵敏,对于色、声、香、味、触等感觉虽极细微均能感受。再以典丽的字法、新鲜的言语、复杂变化的文句,以立体的方式表现之”[1],为现代都市小说提供了新颖的艺术空间,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独特的审美领域。
一.故事序列的感性化
故事序列是由故事节点和表达节点之间关系意义的组成的网链,表征了叙述人对故事流程的掌控。穆时英从对叙事对象内视角的情绪出发,表述作家或人物的感知的流转。在感性化的主导意识推逐下,故事的节律或快或慢、时空的转换或逆或顺、结构浅层深层的跳跃、意识的现实或梦幻中交织互证,“轻迹凌乱,浮影交横”,(鲍照《舞鹤赋》)“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眼花缭乱的场面,以显示人物半疯狂的精神状态……”[2]传达出作品的深刻内涵。
《上海的狐步舞》采用“平行对称式结构”的横向组合的形态,围绕着文本这“舞池”,以影视蒙太奇手法转换时空,把上海-沪西-林肯路空间的转换作为叙事的轴线,对小厅、街角、赌场、旅馆作为时间序列的节点进行拼接组合,使场景频繁置换,阐释开篇的“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采用作品内部结构的两个向度:一个是历时性,一个是共时性的话语系统,五个人物的五个个案互不牵连,但又有相同的时间节点和空间一致性的夜总会作为话语诉求的深层结构的相关性。五个故事各个要素与故事之外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叠合关系。表达对都市生活的一种背离、逆袭的故事建构。在有限篇幅内拓展了小说艺术表现力,包容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与心理空间,形成故事场面的无穷张力。《街景》将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和故事内容中具体呈现的时间瞬间相交织,把繁华的上海都市一角的街景作为老乞丐活动的具体时空,描述他的痛苦的现实和悲惨的结局。用“也是那么个晴朗的,浮着轻快的秋意的下午”,借助于感觉与联想,插入过去的时空系统叙述过去的经历。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频繁的切换中,打乱事件的发展顺序,造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效应,以此映衬现代都市的畸形繁荣和老乞丐的痛楚的人生遭际。《空闲少佐》以日本军官空闲少佐与中国少女黎姑娘恋情为中心,用空闲少佐的对家乡、妻子、儿子的话语与形貌的闪现和忏悔、自责、自杀作为故事的序列节点完成对故事的构建。此外《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五月》都是以心理活动构建故事,以灵动的画面组接塑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
二.场景设置的梦魇化
场景赋予作品以意义,通过人物行为和环境的组合显现生动的具体的艺术形象,产生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穆时英一方面尽情享受着现代都市优越的物质生活,一方面也经受着现代都市文化的精神异化,其主体人格也处于裂变之中[3]。因此,对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以及都市人的刺激与诱惑,不再诉诸外在的客观描摹而直接诉诸心理感觉,打破设置在作家和创作对象之间的界限,使主观与客体、人与物交互错叠在一起。以“感觉”表现人的精神状态:焦虑浮躁、虚无神秘、幻灭悲观的情绪色调和迷离错乱、荒诞猥琐、邪恶丑陋的主观感受,以此拒斥外部世界,表达弱者群体的一种精神呐喊,构成了反传统的感觉主义和印象主义小说形态。场景的设置呈现出不同形式的梦魇化的特征:幻觉、错觉,变形和变态。
《上海狐步舞》中穆时英用林肯路、铁道交通门、别墅式的小洋房、跑马厅、舞厅、电车、华东饭店、小胡同、浦江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用联想、想象、幻觉和潜意识作为人物思想延伸的触角,构筑了一个声色迷离的审美意境:关于腿的联想、关于跑马厅的幻觉“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的神经。”关于鞋跟的幻境、华东饭店眼睛所及的叠化,二楼、三楼和四楼一例是“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这些时空场景以没有任何因果联系的生活片断,交叉错综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个非理性的颠倒错乱的表象世界,凸现出大上海的飘忽和轻浮,疯狂和糜乱,真实地暴露了半殖民地都市社会不合理的病态现实,成了主题意义。《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以“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作为总的时间节点,先分别呈现金业交易所、校园、霞飞路、书房、市政府五个地点的五个人的故事。接下去是把场景设置在没有理性、法官也想犯罪、上帝进地狱的星期六晚上的夜总会。使用了四个人物视角,展现人物间的情绪流动与情感纠葛,体现人物不同的“错乱”特征,“卖报的小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天空中有酒、灯和高跟鞋”,在繁华喧闹、色彩斑斓的大都市才会有这种超乎常态的感觉。让人真切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繁华与紧张跃动的气氛,“什么是你!什么是我!我是什么!你是什么!”于是我们的眼睛所觉察到的种种物象特征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构成,而是作为有生命感受的意向、欲望、理解、期待。《公墓》是一个有丁香般淡紫色的故事。《Pierro》房屋内一切都是黑色的调子,经常造成一些触目惊心的视觉效给人以神秘的印象,烘托出主人翁当时迷乱病态的心理。
三.叙述语言的感官化
小说的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穆时英个性化的感官叙述使得文本的语义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他将人物的视、听、嗅、味和触觉感知,通过直觉的交流沟通和多向度的关联,创造了多维的语言言说。以奇特而陌生的语言组合起来,反映直觉的神经波动。在知觉化的语流中,建立了文学语言与时尚上海之间的新的关联通道,“作者以及作品中人物的主观感觉往往与叙事相融合,感觉成为叙事中心,客观现实延伸至主观世界中,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刺激,由是引起新文学叙事方式的深刻变动,创造出一种新的表现手法——感觉化的叙事方式……”[4]
在穆时英的笔下,物化与人化的都市景观比比皆是。公墓》写郊外的每一朵小野花“含着笑。田野是广阔的,路是长的,空气是静的,广告牌上的绅士是不会说话,只会微笑”,秋天是有重量的,“太阳从白窗纱里透过来,抚摸着紫丁香的花朵,夜风是冷的,夜是默静而温柔的”,苍郁的灌木在矮篱里边往外伸着胳臂,风吕草在脚下怨恨着,“火车在铁路上往那边儿驶去,嚷着,吐着气,喘着,一脸的汗”,都市的景观获得了自主的生命力,感受着情感、意愿。交际花的恋人就像雀巢牌朱古力糖,成为治愈消化不良症的“辛辣的刺激物”,烟卷成为孤独男子的恋人。在物与人的双向互渗中,流露出对于物质世界的偏爱对人的世界的厌弃。《CRAVEN“A”》中听感知Craven“A”清脆的带着橙子香的声音是“啧啧啧啧啧”,进入读者视野的是字体由小到大排列,传达出袁律师感觉中由小到大的声浪。《PIERRT》中,用一种“黑”的颜色的视觉显示,形塑潘鹤龄心理上一种透不过气来的忧郁、压迫、孤独和辽远的愁思、枯死的寂寞:在黑暗里边,黑的笔、墨水壶、书、石膏像、壁纸、画、毡帽、床、花瓶、橱、沙发,连同黑色的钟的走声、黑色的古龙香水的香味、黑色的烟卷上的烟、黑色的空气和窗外那个黑色的夜空。《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描写上海租界繁华区的夜景,写街上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色情的眼,饕餮的蝇眼、乐天的醉眼、欺诈的俗眼、亲昵的荡眼、伪善的法眼、奸滑的三角眼、朦胧的睡眼……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边展开了都市的风土画。用鲜明的黑白二色构筑夜总会中失意人内心那种挣扎、困厄、孤独和无助的二难选择和畸形都市的物质文明和广告文明对人的压迫和异化:先重叠三个“白的台布”,然后以“白的台布”为中心,上面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旁边坐着“黑头发,白脸,黑眼珠子,白领子,黑领结,白的浆褶衬衫,黑外褂,白背心,黑裤子”穿晚礼服的男子;后边站着“白衣服,黑帽子,白裤子上一条黑镶边”侍者。
穆时英用极富想象力的色彩构建了一个缤纷的视觉盛宴,将都市和都市人生幻化为色彩的审美元素。色彩表征了都市的欲望,《白金的女体塑像》中女客暗绿的旗袍、红腮帮、红嘴唇、紫眼皮、黑宝石的长耳坠子和戒指,目眩了谢医师的心境,颠覆了他的世俗人生;色彩也隐喻了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都市风貌,《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一个患有女性嫌恶症的男子难以把持抵御蓉子那一朵紫色的吻,最终逃脱不了被消遣的命运。《黑牡丹》中,旋转在舞池中的黑牡丹“在蓝的灯下,那双纤细的黑缎高跟鞋,跟着音符飘动着,那么梦幻地,象是天边的一道彩虹下边飞着的乌鸦似的……她嘴唇上的胭脂透过衬衫直印到我的皮肤里……我的心脏也该给染红了”。都市的异化风貌征服了畸形的都市生存常态,在色彩的世界里,“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挡。”
四.结语
作为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家,穆时英开掘了都市生活的现代性艺术领域,用他独特的艺术才华表述了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既是对现实的一种挣扎与无奈,更是对现代的一种反思对传统的一种打捞。特殊的历史时空造就了穆时英的鬼才风格和众说贬抑,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毕竟有过作为,如李欧梵教授的意为:穆时英与刘呐鸥、施蛰存等是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功不可没。
[1]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M].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3.P94
[2][严家炎.《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P144
[3]王嘉良.《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 P457
[4]方长安.《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感觉化叙事方式》[J],《晋阳学刊》.2004.4
(作者介绍:毕金林,南阳理工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对其附逆之事的再思考
——从《文学界》追悼特辑到夭折的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