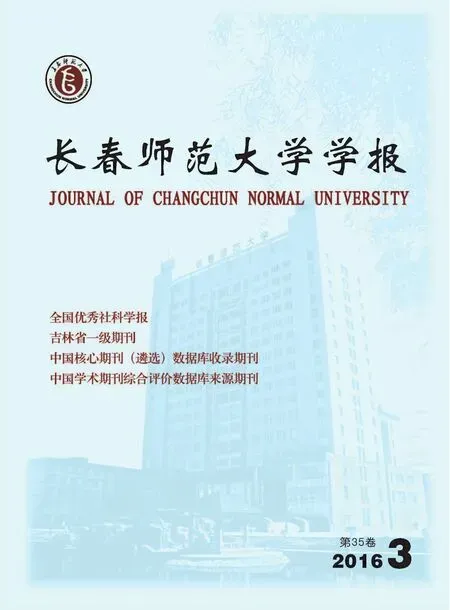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咖啡馆与约翰·德莱顿的文学公共活动
霍盛亚
(1.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089;2.中央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1)
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咖啡馆与约翰·德莱顿的文学公共活动
霍盛亚1,2
(1.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089;2.中央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哈贝马斯在研究资本阶级公共领域时提出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概念,并指出这一领域的出现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英国文学家通过在咖啡馆中进行的文学公共活动介入他们所关注的公共问题,德莱顿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位。以他为首的一批英国作家通过在维尔咖啡馆中对文学话题的讨论和辩论,训练了资产阶级使用文学实施的“辩论机制”“理性交往”以及“公共舆论”,从而间接促进英国文学公共领域迅速走向顶峰并继而向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转型。
[关键词]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维尔咖啡馆;约翰·德莱顿
“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ische ffenlichkeit)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研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35。但是欧洲诸国的文学公共领域诞生自不同的文化机构(cultural institutions)中: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发轫于1680—1780年间的咖啡馆中,法国和德国的文学公共领域则出现在文学沙龙中。但不管在欧洲的哪个国家,这些文化机构都具有一个共性,即“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1]37。在17—18世纪英国的数千所咖啡馆中,维尔咖啡馆(Will’s Coffeehouse)因为以德莱顿(John Dryden)为首的一众文学家在其中的文学公共活动而享誉欧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成熟和发展。
一、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兴起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将文学公共领域描述为:“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公开批判基本还集中在自己内部——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1]34。基于哈氏的描述,陶东风教授曾将文学公共领域定义为“一定数量的文学公众参与的、集体性的文学—文化活动领域,参与者本着理性平等、自主独立之精神,就文学以及其他相关的政治文化问题进行积极的商谈、对话和沟通”[2]。这一概念抓住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复杂性,也起到了规范这一术语的作用,因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个术语的翻译和理解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文学公共领域”一词在思想层面上应被译为“文学公共性”(literary publicity或literary publicness);在社会层面把握“文学公共领域”时,这一术语则应被理解为“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而呈现文学公共性的具体物理空间应被称为“文学公共空间”(literary public space)。
“文学公共领域”一词由哈贝马斯最早提出。哈氏从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论那里获得灵感,首先研究了古典公私领域关系。他认为基于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城邦体系,自由民之间“公共领域”(koine)和“私人领域(idia)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生老病死都存在于“私人领域”中,而“公共领域是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因而和必然王国、瞬间世界形成鲜明对比”[1]3。到了欧洲的中世纪,由于封建制度的特殊性,公私界限消失,因此“从社会学来看,也就是说,作为制度范畴,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1]6。哈贝马斯将这一时期的公共领域命名为“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和主权国家的形成、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传统的贵族政治衰落了,代表型公共领域开始土崩瓦解。
伴随着商品和信息交换的发展,国家和社会最终在18世纪的欧洲各国分离,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也旋即分离。前者以宫廷为代表,后者则由游离于统治阶层的第三等级组成,且后者中的个人与个人集合形成了一个与国家权力领域谋求“对话”的领域。这种对话的沟通模式是从宫廷中游离出来的边缘贵族将宫廷中的社交方式带到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判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1]34。这种对话方式训练了资产阶级的辩论技巧,奠定了公共交往的模式和公共舆论的技巧。而这些对话方式首先是在文学领域得以演练,哈贝马斯因此将其称之为“文学公共领域”——一个“不仅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更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向‘市民公共领域’过渡的一个中介”[3]。文学公共领域的诞生伴随着一系列新的文化机构的产生,比如咖啡馆和沙龙等。通过在这些场所中不断演练文学批评的技能,“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1]37。
在这个中间阶层中,实施文学批评的主体是开始走向职业化的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逐渐摆脱封建的“文学资助人”,在开始职业化的书商的帮助下,借助咖啡馆、沙龙、戏院等机构,讨论文学相关话题。在这些文化机构中,不论是文学家还是读者都接受了批判技巧的训练。这样一个具有批判性和自律性的读者群的形成对于欧洲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哈贝马斯曾说:“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纸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1]55。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与讨论,培养了更多具备资产阶级公共交往能力和公开批判技巧的社会公众,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更强的批判意识和参与公共讨论的意识。
按照哈贝马斯的研究,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发轫于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直到“长期反对派”发表三部讽刺作品以及1726年柏林布鲁克的《匠人》(Craftsman)杂志的出版开始向政治公共领域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印刷技术的提高、1710年英国首部《版权法》的颁布、文学赞助人的式微、职业出版商的崛起等都为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兴起和成熟提供了必要条件;咖啡馆在英国的流行则为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场域,它们成为英国文学家与国家权力领域进行“对话”的具体场所。具备了“公共性”的文学家通过在咖啡馆中对文学话题的讨论和批判为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立法”,这为后来英国政治公共领域的发展树立了范本。可以说没有英国咖啡馆就没有英国文学公共领域,也就没有英国民主政治的出现。
二、“便士大学”与英国讽刺文学作品的发展
1665年,署名为“眼见耳听者”(by an Eye and Ear Witness)的诗人写过这样几行诗:
咖啡与共和
起首皆相同,
共同促革新,
赋民释与宁[4]68。
虽寥寥数句,却写出了英国咖啡馆对英国政治、历史及文化的巨大影响。咖啡如同中国的茶叶一样,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它与茶叶和可乐并称世界三大饮料。咖啡的出现改变了欧洲人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英国人不再清晨起床便开始饮酒,而改喝咖啡,由整日酩酊大醉过渡到了更文明的、基于理性对话的、新型的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对欧洲的影响非常深远,一位法国哲学家不无夸张地说:“咖啡的出现,带给了欧洲人自使用火以来最伟大的文明”[5]。
咖啡最早出现在埃塞俄比亚,1615年到伊斯坦布尔寻求东方特色商品的威尼斯商人将之带回欧洲。1650年,一名叫雅克布的犹太人在英国剑桥经营了“英国甚至是在整个基督教国家的第一家咖啡屋”[6]xiv。剑桥的这家咖啡馆既满足了学者和才子们对东方的猎奇心理,又提供不至于像鸦片那样容易成瘾的咖啡。咖啡馆很快开始向英国主要城市进军,两年后伦敦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根据1663年的一个统计,当时伦敦仅有82家咖啡馆,而到了18世纪初伦敦的咖啡馆就已多达551家之多。大量咖啡馆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英国人的文化生活,还改变了英国人的文学创作习惯和政治生活,因此有学者认为咖啡馆是英国“公共舆论”“市民社会”和“民主文化”的策源地[4]。英国日记作家佩皮斯从1660年1月到1669年5月3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99次访问咖啡馆时的见闻,足见咖啡馆对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1950年,德裔美国社会学家施拜耳(Hans Speier)在其《公共舆论的发展史》一文中指出,18世纪是现代“公共舆论”理念形成的关键历史时期。他认为在英国和法国,阅读群体的增加与新型社会机构(new social institutions)如英国咖啡馆与法国沙龙的涌现对于欧洲公共舆论意识的形成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中产阶级(在咖啡馆中)接受了教育”[7]376,因为在咖啡馆中“新闻汇集、散播,政治辩论和文学批评大受欢迎”[7]376。同为德国人的哈贝马斯于1962年与施拜耳遥相呼应,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文学和艺术催生了批判性辩论(critical debate),也催生了文学公共领域,其中英国咖啡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哈贝马斯曾总结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要素和它的运作机制:第一,一个阅读公众的形成,即“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层构成,他们的阅读范围已超出了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1]3;第二,一旦足够多的阅读公众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1]3;第三,有了阅读的公众和交往的空间,就需要一定的规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以文学家为代表)从游离贵族那里习得的平等交往原则、自由讨论方式和依照多数决策等原则得以贯彻实施,而这些要素的形成都发生在一个物理空间——咖啡馆中。
在咖啡馆这个文化机制中,一套隐形的“规章”通过不断的文学辩论和讨论形成:第一,一种并非建立在“级差”基础上的社会交往模式的形成,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1]41,但咖啡馆并非公众讨论产生的充要条件,因为“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虽然尚未真正出现,但已在酝酿之中”[1]41;第二,公众在文学公共领域中讨论的议题不受限制,因为“(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不再继续是教会或宫廷公共领域代表功能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它们失去了其神圣性,它们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变得世俗化了。私人把作品当作商品来理解,这样就使作品世俗化了”[1]41;第三,这个文学公共领域具有普遍开放性,也就是说,“公众根本不会处于封闭状态”[1]42,“因为,他们一直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处于一个由所有私人组成的更大的群体之中”[1],而且在这个空间中讨论的话题可以使“所有人必须都能加入到讨论行列”[1]42中来。
咖啡馆中英国文学家的公共活动直接促进了复辟以降散文与诗歌中“粗俗讽刺作品”(vulgar satire)的发展,这一文类主要包括拙劣模仿作品(low travesties)、滑稽讽刺作品小册子(chapbook burlesques)、历史笑话集(jest-book histories)以及抨击性民谣(broadside ballads)等,它们大多是对控诉书(complaint)、请愿书(petition)、游记(travel journal)、新闻报道( news report)等严肃文体的粗俗戏仿。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创造性和艺术性很强的讽刺作品的出现,比如修地布拉斯体(Hudibrastic)就是从17世纪英国作家塞谬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为嘲讽清教徒而创的一首题为《修地布拉斯》的讽刺诗而来。还有一些嘲讽式控诉书(mock-complaint)在当时的咖啡馆中很受读者追捧。这些控诉书通常借轻浮的女仆、啤酒屋女老板或女商贩之口,用粗鄙的言辞向法官陈情。此类作品多为文人所作,代替普通大众控诉时弊,在咖啡馆中非常流行,读者也都是咖啡馆中的普通大众。
英国咖啡馆还复兴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类——人物或性格特写(The Character)。这种文类由古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所创,常用来刻画一类具有典型特征的人。这些文章篇幅短小,却诙谐辛辣,因此常被用作犀利的武器来攻击持不同意见者。由于篇幅短小、易于出版,这些文章也因此在咖啡馆中广为流传。第一篇对咖啡馆的特写创作于1661年,题为《咖啡和咖啡屋特写》(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s),生动地记录了早期咖啡馆中的公共活动。此文至今仅剩三个善本,留存在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图书馆(the Worcester College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th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和苏黎世约翰纳雅科布斯博物馆(the Johann Jacobs Museum, Zurich)中,十分珍贵。
英国咖啡馆文化史研究专家伊利斯(Ellis)说咖啡馆“把来自社会各界的人首次团结在了一个民主的集会中,使得人们暂时搁置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陋习。通过这样的集会,人们可以感知到共同的危机”[6]xv,不仅如此,咖啡馆还是市民阶层交流政治观点、讨论文学、科学等议题的重要场所,它在英国人信息传播和知识习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人戏称咖啡馆为“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因为在这里不管是谁,只需要花费几个便士就能获得一杯咖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与众人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可以说,在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英国散文的发展、现代意义报纸的出现,乃至“英国民族礼节、风度和礼仪的核心价值观念”[6]316的形成都与咖啡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英国复辟到安妮女王治下期间,众多的咖啡馆中,维尔咖啡馆(Will’s Coffehouse)因为德莱顿等文学“才子”的公共活动而备受当时英国人的瞩目。
三、维尔咖啡馆中的文学公共活动
英国罗素大街上星罗棋布的咖啡馆对英国文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弥尔顿(Milton)、马维尔(Marvell)、佩皮斯(Pepys)和哈林顿(Harrington)在洛塔(Rota)咖啡俱乐馆经常聚会,启发了哈林顿《大洋国》的创作;艾迪生(Addison)和斯蒂尔(Steele)在布顿(Button)咖啡馆开始了他们的报纸写作与发行,推动了英国报刊业的飞速发展;以约翰·德莱顿为首的文学“才子们”(wits)则喜欢在这条大街上最早开张也最富盛名的维尔咖啡馆中聚会。这家咖啡馆在复辟时开门迎客,此后的30多年中一直备受当时文学家们的青睐,也成为很多年轻诗人和作家成名的摇篮。德莱顿在维尔咖啡馆中对文学相关话题的讨论为日后文学鉴赏和批评设立了标准,18世纪的很多作家都效仿他到咖啡馆中寻找创作灵感和喜欢自己作品的读者。
德莱顿是维尔咖啡馆的上宾,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这家咖啡馆中,这里设有他的专座。“德莱顿习惯坐在一楼,他冬天的专座设在壁炉旁,而在天气好的时候他更喜欢坐在阳台的角落里,在那里他可以远眺街景,他把这两个座位叫做‘冬座’和‘夏座’”[4]xi。他的到来使得“当时人们以能亲耳聆听他谈论诗文为殊荣”[6]67。德莱顿在咖啡馆的文学讨论和争辩中充当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年轻作家都希望进入维尔咖啡馆的文学圈子中,而获准加入该圈子的标志就是德莱顿从自己烟盒中拿出一支鼻烟让新人品尝。康格里夫(Congreve)、威彻利(Wycherley)以及艾迪生(Addison)等一大批作家都曾在这里受到过德莱顿的提点,并因此走向成功。
德莱顿喜欢在维尔咖啡馆中写作,也喜欢加入这里的文学讨论。维尔咖啡馆里到处都是已刊登或等待刊登作品的手稿,从诗歌到讽刺文章应有尽有。诗人罗伯特·于连(Robert Julian)专门负责从中挑选供他们讨论的素材,斯威夫特在其《谈话的诀窍》(Hints to an Essay on Conversation)中戏谑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文学辩论的情形:
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糟糕的对话正是在维尔咖啡馆里,在那里“才子们”(就像人们所说的)正式聚会,他们五六个人聚在一起,在如此严肃的氛围里,拿他们之前写的几处剧本,序言或者一些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彼此娱乐,好像他们所做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事业,或者他们是“王国宿命”决策者[6]65。
当时的英国咖啡馆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现象:诗人们通常会在公共场所大声朗诵他们创作的作品或者大声议论发表在报纸上的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咖啡馆中的文学讨论并非如哈贝马斯理想化的那样自由与开放,当时主要的几家咖啡店通常由一个中心人物来主导,他们对各种争论进行“仲裁”,这便招致另外一些文学家的不满。斯威夫特就曾在一首诗中嘲讽德莱顿:
他给出决断性的判断,
对四下围坐着的“才子们”,
递上来的“神谕”。
他为城市发展指明方向,
指点江山[8]。
从这首诗歌不难看出,英国咖啡馆中文学公共领域所依托的平等对话的机制被类似德莱顿这样的“主持人”左右,使得文学公共领域的平等对话原则很难得以真正实现。
另外,英国重要报纸《闲谈者》(Tatlar)第一期的头版中曾这样写道:“如果想看勇敢的、快活的、娱乐的报道,就请去怀特巧克力屋,如果要读诗歌,请去维尔咖啡馆,如果要学习,请到‘希腊’咖啡馆,如果是要获取国内外新闻,就请去圣詹姆斯咖啡馆”。通过这段记录,我们不难发现英国咖啡馆已经开始按照不同群体的需要划分了类别,也就是说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某种“排异机制”,这种机制将无产者和女性排除在外,为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埋下了自我解构的因子。哈贝马斯在其“文学公共领域理论”建构中无视这一问题,从而为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等学者所诟病。这种排异机制在文学公共讨论的实践过程中有时会表现得非常激烈,甚至会出现言语乃至身体上的伤害。艾利斯研究称:
他们用这种文体(讽刺文章)取笑对方,他们尤其喜欢取笑初来乍到的人(尤其是来自乡下的人,因为他们通常不那么老于世故)[6]66。
1687年,德莱顿曾发表过一首名为《马鹿与黑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的诗,为自己改信天主教辩解。这首诗马上就招致普莱尔(Prior)和蒙塔古(Montagu)的辛辣讽刺,他们改写了德莱顿的诗歌,并把题目改为《马鹿与黑豹,变身为乡下老鼠与城市老鼠的故事》(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transcended, to the Story of the Country Mouse and the City Mouse),将德莱顿诗中象征基督的鹿和代表教会的黑豹改写成了一只乡下老鼠和一只城里老鼠。乡下老鼠天真无邪、涉世未深,想要参观有着“才子咖啡馆”美誉的维尔咖啡馆:
我久仰才子咖啡馆,
‘斑点’兽说你定要去瞧瞧,在那里
牧师们呷着咖啡、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品着诗人的仙茶;
这里穷人得自由,富人着华服;
这一切让大官丧气,让测试难熬[6]66。
然而,当他们看到维尔咖啡馆的时候,却发现德莱顿高高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他是神圣才子诗坛的判官,
他端坐在自己荣耀的阴影之中。
仿佛月亮女神接收到光芒,
她将周遭照亮;
也照亮了他,在远处闪闪发光,
他向这颗星借了光芒
高乃依和拉宾所制定的条条框框
被身后的涂鸦者奉为金科玉律。
他把这些借来的真理再次分发,
你将因阴谋分裂受到惩罚
若你胆敢质疑他,或只信自己的判断[6]66。
城市老鼠讽刺德莱顿充当本市诗歌创作的评判者,认为德莱顿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理仅仅是被动地臣服于以高乃依和拉宾为代表的法国诗歌的主张。诗歌作者将这个例子同德莱顿宣誓效忠天主教和独裁政治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嘲讽德莱顿的目的。德莱顿确实因为这首诗歌而受到了伤害,他曾在咖啡馆中和才子们聚会时说自己的讽刺诗歌在发表的时候总是署名的,而攻击他的人不敢这样做。
1679年,德莱顿更因为一首题为《讽刺》的诗招致了身体上的伤害,坊间到处流传说这首诗是德莱顿为讥讽国王和他情妇之间的丑闻而作。一天晚上,当德莱顿从维尔咖啡馆出来回家的路上,这位作家被三个男人截住痛揍一顿,暴徒的指使者很有可能是国王情妇之一的朴茨茅斯公爵夫人路易斯。一首诗歌不仅引发了语言暴力的出现,甚至引发了对文学家本身的身体暴力,而暴力的出现正是文学公共领域的大敌,这是哈贝马斯在建构理想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所未察的情况。
德莱顿死后十年,维尔咖啡馆依然是才子们进行文学创作和讨论的中心,直到1712年它的地位受到新开张的巴顿咖啡馆的挑战。此时咖啡馆中的文学讨论越来越多地掺杂了政治话题,文学公共领域开始逐步向政治公共领域过渡。但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知识分子在咖啡馆里建立起的社交模式已经深入人心,在咖啡馆里辩论和社交、读报纸、看杂志、关心公共事务的习惯都被保留了下来。咖啡馆吸引了众多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到来,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分享创作经验和阅读的快乐体验,从而直接参与建构了英国文学公共领域。但从对维尔咖啡馆的研究不难看出,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并非如哈贝马斯所建构的那样理想,它通过一系列“排异机制”将女性和平民隔绝在外。另外,语言和暴力的存在也威胁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这都是哈贝马斯“文学公共领域”中所忽略的。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陶东风.阿伦特式的公共领域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启示[J].四川大学学报,2010(1):31.
[3]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18-9.
[4]Ellis, M. Eighteenth-Century Coffee-House Culture[M].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5]郑万春.咖啡的历史[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4.
[6]Ellis, A.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M].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6.
[7]Speier, H.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0: 55(4): 376,376.
[8] Pat Rogers ed.Complete Poems[M].London:Penguin,1983:539.
British Literary Public Sphere, Coffeehouses and the Literary Public Activities of John Dryden
HUO Sheng-ya1,2
(1.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2.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Haberm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his study of bourgeoisie public sphere,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end of 17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18th century Britain. British writers got involved in the public issues in the coffeehouses through their literary public activities, among whom John Dryden was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Headed by him, writers in Will’s Coffeehouse discussed and debated literary topics so that the “debating mechamism”, “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were practiced and reinforced by uprising bourgeois,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erary public sphere to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Key words:British Literary Public Sphere; Will’s Coffeehouse; John Dryden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3-0138-06
[作者简介]霍盛亚(1981- ),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研究(1640—1726)”(14CWW012);中财121人才工程青年博士发展基金项目“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研究(1640—1726)”(QBJ1425);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基础学科科研扶持计划支持项目(021650315005)。
[收稿日期]201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