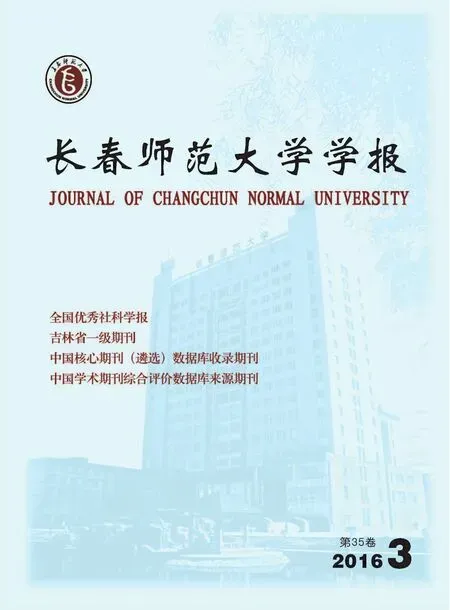生产、销售假药罪罚金刑数额的应然走向
高广龙,刘晓莉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生产、销售假药罪罚金刑数额的应然走向
高广龙,刘晓莉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从生产、销售假药罪罚金刑的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趋势是加重对其处罚。我国现行立法对该罪采用的是无限额罚金刑模式,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缺点较为明显,且在数额上无法与行政罚款相衔接。因此,该罪的罚金刑应当设定下限数额,以适应立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其缺陷。
[关键词]制售假药罪;无限额罚金刑;下限数额
继《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假药罪(以下简称“制售假药罪”)罚金刑改为无限额罚金刑之后,《刑法修正案(九)》又增加了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我国《刑法》的立法趋势除减少死刑适用罪名一大亮点之外,也有降低入罪门槛、加大惩罚力度之趋势,颇具“死刑慎用,生刑更重”的意味。本文便是在认可该种立法趋势的前提下进行讨论,建议对制售假药罪的罚金刑进行完善,增设该罪罚金刑的下限数额,在弱化无限额罚金刑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同时,也在数额方面使该罪的罚金刑与行政罚款更好地衔接。笔者认为此建议并不违背“宽严相济”的政策,因为“宽严相济”要求的是“该宽则宽,应严必严”,加大对该罪的打击力度也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制售假药罪罚金刑的立法沿革
(一)1979年《刑法》中罚金刑的性质分析
我国刑事立法对药品相关犯罪一直保持罚金刑的规定。1979年《刑法》(以下简称“旧《刑法》”)之前的《刑法草案》中对药品犯罪就有相应规定,例如1957年《刑法草案(初稿)》(第22稿)、1963年《刑法草案(修正稿)》(第33稿)、1979年《刑法草案(法治委会修正第二稿)》中均有相关规定[1]。1979年旧《刑法》正式通过,其第164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制造、贩卖假药危害人民健康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大部分学者认为此中罚金刑是无限额罚金刑,但是笔者不敢苟同。无限额罚金刑与限额罚金刑应当是相对概念,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由法律明文规定数额或者范围,那么其基础就应该是罪刑法定原则。据此,笔者将无限额罚金刑理解为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呼应的一种刑罚方式。然而罪刑法定原则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我国受到注意,因此旧《刑法》中的罚金刑是否属无限额还在立法者的认知范围之外,将此种情况下规定的罚金刑理解为无限额罚金刑略为不妥。
(二)1997年《刑法》关于制售假药罪罚金刑的规定
在1997年《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制订过程中,市场经济日益发展,货币在生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学界一致认为扩大罚金刑适用率是世界立法潮流(但近年来有学者以详实的数据表明大多数国家罚金刑的适用率都在下降[2]),新《刑法》将适用罚金刑的罪名由原来的20余个增至130余个,以期发挥罚金刑的优势。新《刑法》第141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新《刑法》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影响,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中均将罚金刑规定为倍比制,并以销售金额作为倍比基础。在当时看来,这种改变无论从立法技术还是立法精神上无疑都是一大进步。
(三)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制售假药罪罚金刑的修改
随着经济发展,市场逐渐多元化、复杂化,制售假药行为日益猖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生产假药案。以2008年为例,全年查处药品案件共273265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223件[3]。药品违法犯罪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在此背景下,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将141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该条修改了制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将其从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无疑降低了入罪门槛。在罚金刑方面,将原来的倍比制罚金刑改为无限额罚金刑,并取消了罚金的上限和下限,但从立法精神上不难看出立法者有加大处罚力度的趋势,即其目的应为突破罚金刑的上限以发挥更大的惩戒作用。
二、制售假药罪罚金刑立法研究现状
(一)制售假药罪罚金刑立法现状的优势
首先,从无限额罚金刑固有的优势来看,其有利于保证刑法的稳定性与严肃性。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限额罚金刑和倍比罚金刑经常表现出原有规定数额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4]。无限额罚金刑也符合我国《刑法》总则中应根据犯罪情节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给量刑留出一定的灵活空间。同时,无限额罚金刑的这种空间无意之中也避免了与《药品管理法》中违法生产、销售假药的货值金额不协调的问题,使药品违法犯罪的罚款和罚金的衔接问题在数额方面的矛盾有所弱化。
其次,加大对药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药品犯罪行为愈发严重,加之其侵害客体为复杂客体——国家药品管理制度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权,使得药品犯罪的危害结果不容忽视,加大对药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成为肃清市场经济秩序与维护民生发展的需要。
最后,无限额罚金刑可以其强大的威慑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效果。相对于倍比制和限额制罚金刑而言,无限额罚金刑在数额上的不可预测性会使预备犯罪的行为人加大对犯罪成本的估计。当意识到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的时候,大多数行为人会选择放弃犯罪行为,这样便实现了无限额罚金刑的一般预防的目的。同时,对已经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进行更加严厉的处罚(超出限额罚金刑或倍比罚金刑的最高限度)会使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刑罚所带来的痛苦,并且这种惩罚会剥夺犯罪人再犯的能力。从理论上讲,惩罚力度与再犯可能性成反比例关系,现行立法加大对药品犯罪在罚金方面的打击力度是可以降低再犯率的,因此能体现出无限额罚金刑的特殊预防目的。
(二)制售假药罪罚金刑立法现状的弊端
第一,无限额罚金刑最为人所诟病的弊端是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无限额罚金刑以其无法预测的特点发挥了其一般预防的功能,但这一特点实属“双刃剑”。没有具体数额的规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不利于人权保障,同时会导致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甚至导致权力滥用。
第二,制售假药罪罚金刑突破上限的同时也打破了下限,有违加大处罚力度的立法趋势。继《刑法修正案(八)》将制售假药罪罚金刑改为无限额罚金刑之后,《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扩大了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如第120条、280条等都增设了无限额罚金刑,可见立法精神在于加大对这些犯罪的惩罚力度、收获更好的刑罚效果。但是,一旦修改为无限额罚金刑,罚金的下限就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所规定的1000元来判处,那么像制售假药罪这类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就很可能出现刑罚畸轻的现象,同时易导致罚金数额额低于罚款数额,凸显行政处罚与刑罚难以衔接的问题。
三、制售假药罪罚金刑数额的应然走向
上文简述了制售假药罪无限额罚金刑的利弊,笔者更倾向支持对制售假药罪加大惩罚力度的立场。反对者普遍认为我国刑法立法趋势应跟随世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并且全世界只有包括我国在内的个别国家还保留无限额罚金刑。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应适应经济基础而存在。刑法和刑罚手段作为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角色,应当符合本国犯罪情况,不能盲从世界潮流,也不宜盲目推崇他国立法。在笔者看来,这些形式化的理由不应该成为反对无限额罚金刑的理由。我们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罚金刑模式,发挥无限额罚金刑威慑力较大的优势,同时弱化无限额罚金刑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的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罚金与行政罚款在数额上难以衔接的问题。基于此,笔者提出“单边无上限罚金刑”这一称谓,即只有下限而无上限的罚金刑,并且将生产、销售假药罪罚金刑的下限分情况进行规定:(1)未经罚款处罚的,处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罚金;(2)已经罚款处罚的,处罚款金额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罚金。
(一)单边无上限罚金刑的合理性
首先,单边无上限罚金刑的更大惩罚力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立法的主要目的[5]。在笔者看来,预防犯罪是惩罚犯罪的必然目的,惩罚犯罪的手段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法律是调控社会关系的规则,应当由社会需求引领立法趋势。2012年的“毒胶囊事件”使药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之大、社会影响之恶劣,举国震动。药品犯罪层出不穷,危害也越来越大,应当引起人们对其控制手段的反思。从数据上看,2008年与2009年我国查处的药品安全案件分别为273265件和196910件,而《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的2013年和2014年,我国查处的药品案件分别为147322件和103318件[6]。可见,《刑法》加大对药品犯罪的惩罚力度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笔者提议在此基础上设立单边无上限罚金刑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
其次,单边无上限罚金刑可以最大程度地打击行为人的侥幸心理,发挥刑罚的威慑和预防作用。从犯罪学角度来讲,行为人进行犯罪行为前会有一个利弊博弈的过程,即在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人更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犯罪行为的实施是一种理智决策的过程”的观点,认为行为人经过考虑,选择可能付出的成本尤其是受到刑罚处罚的风险最小,但能获得最高收益的犯罪行为加以实施[7]。简单讲,就是行为人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其能够从犯罪行为中获益。在笔者看来,这种侥幸心理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希望逃过刑罚制裁;二是即使受到刑罚制裁,也希望制裁较轻。单边无上限罚金刑恰恰没有留给行为人第二种侥幸心理存在的空间。行为人一旦落网,等待他的必然是严厉的刑罚制裁。这就使得其在考虑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会增加对犯罪成本的估计。过高的犯罪成本会使其对犯罪行为望而却步,打消其犯罪意图,从而实现刑罚的威慑和预防作用。
最后,单边无上限罚金刑有利于弱化无限额罚金刑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缺点。无限额罚金刑最为诟病的缺点就是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大部分学者认为无限额罚金刑在应然层面会走向衰亡。笔者认可这种应然的理论观点。但从实际情况出发,无限额罚金刑在我国仍具有必要存在的空间。我们应该立足现实,将其逐步完善,慎用“一刀切”观点。单边无上限罚金刑在立法层面赋予无限额罚金刑一个下限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法定化,虽然其存在形式化之嫌,但是其所确定的下限数额切实地限制了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不能判处过低数额的罚金的自由裁量的权利。
(二)单边无上限罚金刑的下限数额规定的必要性
为制售假药罪罚金刑提出单边无上限罚金刑称谓并为其寻找一个下限数额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制售假药罪的惩罚力度,其二是在数额方面促进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两法衔接问题从2001年7月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颁布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之前,理论界已经对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问题进行相关探讨并得出主流结论: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上的程度不一致,因此对其进行不同性质的处罚,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量较小,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即可;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量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与违法行为存在质的差异,因此需要惩罚力度更大的刑罚对其进行规制。由此得出的当然论断是:刑罚的力度应该大于行政处罚。
《药品管理法》第73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药品管理法》中罚款数额的确定采取的是倍比制模式,并以制售假药的货值金额作为倍比基础。我国现行《刑法》对制售假药罪罚金刑的描述仅限于“并处罚金”,其下限数额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所规定的1000元来确定。如此低的罚金下限完全比不上动辄几万元的罚款数额,由此便会出现刑罚远低于行政处罚的尴尬局面。笔者所提出的假想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并针对案件处理的实际状况作分别处理:对未经罚款的案件处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罚金,这样就可体现出刑罚相对于行政处罚更具有严厉性;针对已经罚款的案件处罚款金额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的罚金,该数额的确定依旧可以体现出行政处罚与刑罚力度上的递增,同时也体现罚款与罚金在数额上的衔接。
(三)单边无上限罚金刑的下限数额规定的可行性
笔者将单边无上限罚金刑的下限数额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设定:一是未经罚款处罚的,处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二是已经罚款处罚的,处罚款金额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的罚金。
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药品管理法》中所规定的药品违法责任中没有对罚款数额进行规定,现行《药品管理法》中“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表述可追溯至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的现行《药品管理法》。其中对于罚款数额的规定已达十多年之久,行政机关对于执行该规定数额的罚款可以说已经具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刑法》所规定的倍比基础是“销售金额”,但是这一表述在实际认定中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也与《药品管理法》中的货值金额不相衔接。因此,笔者建议将未经罚款处罚的案件罚金的下限设定为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的二倍,一方面可以与《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相衔接,另一方面也便于司法机关在实际认定罚金下限时加以操作。
而对另外一种情况,笔者并没有将行政罚款的数额作为罚金的下限数额,而是作了部分提高,百分之一百五十的罚款数额也就是罚款数额的1.5倍。笔者基于刑罚中应折抵同质行政处罚的规定,对此数额进行了设定。《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这一规定的存在使得法院对罚金部分作出的宣告刑与执行刑产生差异。例如,某法院判决:被告人宋某某犯生产假药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中五千元已处罚款折抵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缴纳”[8]。从其形式不难看出,宣告的罚金数额包含了行政罚款的数额。试想若不明确将罚金的数额规定在行政罚款数额之上的话,就会出现法院判决罚金数额之后,经折抵罚款,就再无可供执行的罚金刑,这样就会削弱罚金刑应有的作用,也无法体现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
如上规定单边无上限罚金刑的下限数额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有案不移”的困境。众所周知,导致“有案不移”现象的最大因素在于部门利益。行政机关所处罚款的多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工作人员的待遇。因此,很多行政机关都会积极进行行政处罚以获取罚款,获取罚款之后只将少部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同时,行为人也会考虑将自己置于何种境地之下会比较“划算”。笔者对已经罚款处罚和未经罚款处罚分情况设定数额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这个原因。举例说明:某人进行了制售假药的行为,假设其货值金额为100万元,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其应接受的罚款处罚在200万至500万元,起点为200万元。一旦行政机关对其处罚之后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那么其还会被判处罚款数额1.5倍以上的罚金,即最低300万元,经折抵,执行数额最低也是300万元;若其未经行政机关处罚,直接接受司法机关处罚,那么按照其货值金额的二倍计算,其应缴纳罚金数额为200万元以上,起点为200万元。可见,两种情况的起算点是不一致的。行为人经过理性分析,就可能选择“成本较低”的方案,即一旦案发,立即主动向司法机关投案。
四、结语
药品犯罪日益猖獗,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就我国国情来看,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会好于其他手段所获得的效果。就当下及未来几年看,降低入罪门槛、加大惩罚力度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立法趋势。笔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上拙见,部分观点仍需通过实践来检验其合理性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38.
[2]熊谋林.我国罚金刑司法再认识——基于跨国比较的追踪研究(1945-2011)[J].清华法学,2013(5):101-104.
[3]赵秉志.《刑法修正案(八)》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99.
[4]刘晓莉.无限额罚金刑的司法适用及其未来展望——以生产、销售假药罪为视角[J].当代法学,2013(5):81.
[5]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5.
[6]2013/2014年度食品药品监督统计年报[EB/OL].(2014-12-23)/(2015-07-24)[2015-12-08].http://app1.sfda.gov.cn/WS01/CL0108/.
[7]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8](2015)东刑初字第00085号判决书[EB/OL].(2015-01-30)[2015-12-08].http://www.itslaw.com/detail judgementId=f745d8de-d10e-4fa2-879c-10f1ce571767&area=1&index=5&sortType=1&count=5&conditions=searchWord%2B(2015)东刑初字第00085号%2B1%2B(2015)东刑初字第00085号.
Trends in the Fine of Production and Sale of Fake Medicines Crime
GAO Guang-long,LIU Xiao-l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angchun Jilin 130117, China)
Abstract:From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fine of production and sale of fake medicines crime, the legislative trend is increasing the fine amount. The legislation adopts for the unlimited fine penalty mode, but the mode conflicts with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and it can not link up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fines in amount. Thus the fine penalty should be set a lower limit amount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legislation and weak the defects.
Key words:Production and Sale of Fake Medicines Crime; unlimited fine penalty; the lower limit amount
[中图分类号]D9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3-0044-05
[作者简介]高广龙(1991-),男,硕士研究生,从事刑法学研究;刘晓莉(1963-),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刑法学、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2013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对策研究”(CLS2013C80)。
[收稿日期]201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