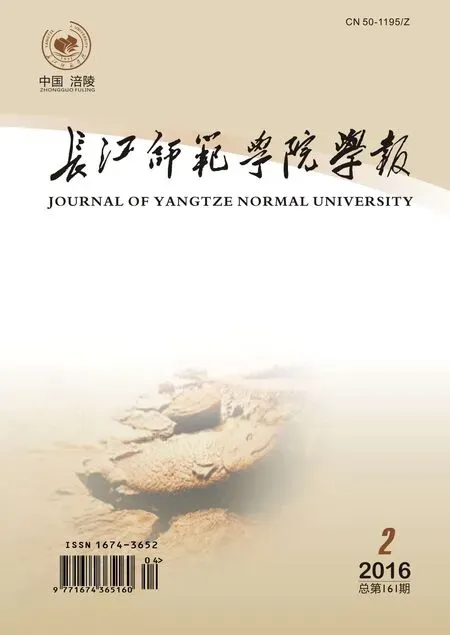试论三峡地区的 “毁器”葬俗
封世雄(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历史研究
试论三峡地区的 “毁器”葬俗
封世雄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葬俗所反映的丧葬观念与人们当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是不同地区的先民在相似生产力水平下的共同选择。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毁器”葬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并且在空间分布上十分广泛,且这种葬俗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国周边后进民族的墓葬中也常有出现。在三峡地区,“毁器”葬俗主要源自新石器时期以来该地区的传承,它与当地人们的生产水平和社会思想意识相对应,并具有自己的特点,并非中原或其他地区传播而来。
[关键词]三峡地区;毁器葬;源流
一、序言
丧葬习俗是世界民族文化中最复杂、最具神秘意识的习俗文化。丧葬礼仪是丧葬习俗的体现,关乎人的生死大事。自人类产生鬼神崇拜以来,丧葬礼仪就越来越复杂化,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在历代典籍中谈论丧礼的著作颇多。《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1]远古时期的人们虽未形成系统的丧葬礼仪,但他们在逝者的尸体上盖以树枝的行为,当属于丧葬礼仪的萌发。在 《礼记·曲礼》中我们会看到 “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等记载以及 “卒哭”等字眼,这表明丧葬礼仪已经形成[2]。
对于中国古代的 “毁器”葬俗,学者们早已注意到,并对此展开过讨论,“从考古发掘看,其发端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到了商周时期,尤其是在中原地区的一些墓葬中较为多见。”[3]由于考古资料和地域范围的局限,人们对 “毁器”葬俗的认识莫衷一是。“毁器”葬俗,有学者又称之为 “碎物祭”[4]或 “碎物葬”[5]。其中,张英说:“‘毁器’习俗,是早期人类产生原始宗教祖先崇拜后,受 ‘万物有灵,灵魂不死’观念驱使,祭祀或葬死者时,人为地将部分盛装酒食器皿,或其它 (他)诸如生活、生产用具、兵器等随葬品,毁之于棺内外的一种行为。”[6]这个概括比较贴切。由于三峡地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始于三峡工程开工之后,因此对该地区 “毁器”葬俗的研究在学界不多,然而伴随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多,对三峡地区的 “毁器”葬俗价值的探讨便越来越引人注目。
二、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研究的回顾
从目前来看,对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有所涉及的文章有:黄凤春的 《毁器与折兵——楚国丧葬礼俗的考古学观察与释疑》一文,梳理并谈到了东周时期楚地一些 “毁器”与 “毁兵”的考古资料,以及对“毁器”葬俗的看法。他说:“所谓的毁器,不仅是指在入葬前有意识将葬器毁坏,还包括一些将本来是一件器物上的附件,如器物的耳、环和链等有意拆下,或者干脆去掉某件器物的附件,形成一件不甚完整的器物,或者使用铸废的器物入葬。”[3]朱世学的 《巴楚墓葬中 “毁兵”现象的考察及相关认识》一文,梳理并谈到了东周时期巴、楚地区一些 “毁兵”葬俗的考古资料,以及他对 “毁兵”葬俗形成的看法[7]。邱诗萤的 《长江中游史前毁器葬》一文,认为长江中游 “毁器”葬出现于8 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并且延续于长江中游诸史前文化中,下迄盘龙城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一脉相承的葬俗[8]。
实际上,“毁器”葬俗相当复杂和不易把握。究其原因,第一,我们常常很难辨别这些器物的破碎是否是因为发掘的缘故或故意为之,并且在考古发掘报告中予以关注和描述的甚少;我们在整理出土器物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器物缺失的部分进行修复,这就使 “毁器”这一特殊葬俗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第二,有关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的历史记载不多,并且古人出于对墓葬保密的需要,故史书中关于“毁器”葬的记载几乎未见,这就使学者们缺少可供研究的相关史料。因此,无论是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还是史籍记载的葬俗资料,都给 “毁器”葬俗问题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时至今日,当我们对 “毁器”葬俗现象的意义有了足够的认识后,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将其区别对待,并将之记录于发掘报告中,进而通过对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现象的深入研究,探索三峡地区先民的思想文化状况。但是,我们也看到,对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的探讨还不系统、明确,很多考古发掘资料还需辨别,这就需要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三峡 “毁器”葬俗研究这种历史现象上。
三、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原因的探讨
自新石器时代起,三峡及其周边地区就有若干 “毁器”葬俗的考古实例。在大溪文化中,巫山大溪遗址有部分墓葬的随葬陶器 “少量是打碎后再随葬的”[9]。三斗坪遗址大溪文化遗存中M1至M8“基本上未出完整的随葬器物”[10]。雕龙碑遗址油子岭文化遗存M19的墓主 “左肩部发现一件残石璜”[11]。在屈家岭文化中,屈家岭遗址第三期遗存M1“器物大多残破”;M12墓葬随葬品 “分为实用大型陶器和小型冥器两类,实用大型陶器均破碎无一完整,似为埋葬时有意识地打破而放入。”[12]屈家岭文化螺狮山遗址的墓葬随葬器物出现器足遭到毁坏的情况,“随葬器皿中的圈足和三足有的是有意打掉的”“器足和圈足,有的有意识打掉。”[13]其中,3号墓中的陶豆M3:2“圈足中部以下残缺”;2号墓中的陶罐 “圈足大部残缺”[14]。雕龙碑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存M14墓主为儿童,“头部盖一件残陶罐”;W31“随葬残陶弹丸1件”;W32随葬 “残陶环1件”;W39“随葬残陶纺轮1件”;W52在作为葬具的 “两罐的下腹部之上分别放置有故意打碎的属于同一器物 (可能为盆)的几块彩陶残片”[12]。怀化高坎垄遗址屈家岭文化第二类墓葬 “随葬器物布满墓底或置于墓底一侧,大多残破,但可复原,从清理现场观察,同一个个体的大件陶器,往往散布在不同的位置上,甚至分别在墓底一侧的南端。由此推之,这些大件陶器是有意打破后埋入墓内的。”其中,M24墓有 “四件石器是在下葬前有意打破而后埋入墓内的”[15]。石家河文化枣林岗遗址瓮棺葬中的玉石器 “出土时大多己破碎,有的似为下葬时人为破碎。”[16]邓家湾遗址M27“墓底南端还有残甑片,北端有缸片”;M19随葬器物中有 “残陶器1件”[17][8]。大量材料表明,三峡地区的 “毁器”葬由来已久,足与黄河流域的 “毁器”葬相提并论。
黄卫东将中国各地的史前毁器葬分为 “打碎器物为死者陪葬”“打碎器物以装殓死者”“打碎器物以祭奠死者”3种,然后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蕴。他认为古人的碎物葬是用碎物显示生与死的不同,表明古人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即生人与死人的用具应有所区别。古人在万物有灵的信仰驱使下,为了死者能够在冥界享用这些器物,便将器物毁坏,使这些器物的灵魂跟随死者进入冥界。历史上,“史前碎物葬兴盛期以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两地出现最多”[5]。基于这种观点,作为兴盛地之一的长江三峡地区,“毁器”葬俗形成的脉络与发展无疑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
一些学者在探讨 “毁兵”葬俗的流行族属时,根据周墓中的大量考古资料,认为是 “周人固有的葬俗”[19]。那么,东周时期三峡地区巴、楚墓葬中也大量见到 “毁兵”葬俗是不是受周人的影响呢?黄凤春持不确定的态度[3],而朱世学认为是受到了战国以来社会风气的影响[7]。我们不能肯定 “毁兵”这一“毁器”葬俗的表现形式是否是周人传播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巴、楚墓葬中的这些 “毁器”葬俗材料的发现,可以证明三峡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周人多有交流,这为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来探讨 “毁器”葬俗的发展脉络将大有帮助。
对于墓葬中的 “毁兵”现象,民间盛传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墓主厌战、仇家复仇等。学术界也有多种不同的推测或解释。其一是认为 “毁兵”葬俗与方相氏驱鬼有关,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传统的观点;其二是认为毁坏兵器是显示成功和富有;其三是认为 “毁兵”葬俗可能与某种宗教仪式有关;其四是认为 “毁兵”葬俗与武王克商后的 “堰五兵”有关;其五是认为 “毁兵”葬俗是周朝 “示民疑也”与 “尊礼尚施”思想观念的反映;其六是认为 “毁兵”葬俗是 “鬼器”观念的体现;其七是认为 “毁兵”葬俗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风气即厚葬引起盗墓之风有关系[7]。诸如此类的各种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缺乏充分的依据。学界仅从 “毁兵”思路进行解读,而未将 “毁兵”这一独特现象与 “毁器”葬俗的普遍现象相联系。因此,我们认为,作为丧葬行为的表现形式,“毁兵”当属 “毁器”的一种,站在 “毁器”葬的高度,上述推论往往难以使人信服。
三峡地区的古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由于认识上有所局限,出于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出现了以 “毁器”为形式的葬俗。这是原始思维的一种表现,器物被人们认为是有生命的,它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也就是损毁来同死者一同达到死亡。
四、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源流的认识
“毁器”葬俗在三峡地区的源流,应是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在这一地区的传承。春秋、战国时期的“毁兵”现象是作为 “毁器”葬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存在的。在历史时期,三峡地区仍然存在除 “毁兵”之外的其他 “毁器”葬俗的表现形式,当然这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的证明和学界研究人员的注意。三峡地区的 “毁器”葬俗是否和三峡地区原始宗教或者巫文化有关?古人受到 “万物有灵,灵魂不死”观念的驱使,“毁器”葬俗作为一种仪式在原始时期到历史时期的长河中或许表达的观念意识有所差异和变化,但作为一种习俗,它至少保留了毁坏器物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一直得到了延续。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时期,相对于进入文明大门的中原民族,周边的后进民族更容易形成或保留这种葬俗。
在北方地区,张英在 《从考古学看我国东北古代民族 “毁器”习俗》一文中介绍了从商周至隋唐时期我国东北古代民族 “毁器”葬俗的一些简要的概况,指出在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丧葬中普遍地流行“毁器”葬俗。他说:“我国东北古代民族的 ‘毁器’习俗,经世代相传,至辽金时期,或许进入了高峰,在宗教兴起过程中,统治阶级将这种原始信仰流传下来的行为,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丧礼中,即史载契丹、女真人崇尚的 ‘抛盏礼’。”[6]其实,“‘抛盏’就是 ‘毁器’,就是把墓内外的随葬品毁坏、打碎,使它们不完整,这种观念与行为表现了契丹族、女真族的生命与死亡观念。这种观念与行为不只契丹族,其他古族也有保留和遗存。”[20]如金成淑的 《慕容鲜卑随葬习俗考》[21]、孙危的 《鲜卑毁器葬俗研究》[22]、毛远广的 《鲜卑史及其考古学文化相关问题研究》[23]都介绍了鲜卑民族的 “毁器”葬俗情况,并且指出“毁器”葬俗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主动行为,增强了鲜卑民族的自我认同。张军的 《契丹覆面、毁器、焚物葬俗小议》[20]谈到了契丹民族的 “毁器”葬俗情况,并从文化史观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葬俗与萨满文化的关系;马利清的 《匈奴墓葬出土铜镜及毁镜习俗源流考》[24]谈到了匈奴、鲜卑民族的 “毁镜”葬俗情况,并且探究了 “毁镜”习俗源流的几种可能。渤海地区古代民族也有 “毁器”葬俗。根据考古材料,“作为渤海丧葬习俗重要特点之一的 ‘毁器’,其毁损的对象并不限于陶器。”[25]“毁器”葬俗在朝阳发现的北魏墓葬中是比较常见的,从 “出土的陶器看,完整的少,多数口沿残或微残,还有的在器底或近底腹壁上钻有穿孔”“而且在三型墓葬随葬品中还出现了器表留有烟炱的陶罐、裂痕边布满锯孔的陶罐等实用器。这种明器与实用器共出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经济的不发达。”[26]
在南方地区,如整个桂东北地区的东汉石室墓中普遍存在 “毁器”葬俗,“墓室内的随葬陶器大多破碎,同一器物的碎片多分散于墓室不同的角落,有些陶器的碎片并不全,可能下葬时仅以部分陶片随葬”,这类葬俗还 “见于川西高原理县等地汉墓中”[27]。在广西武鸣先秦墓葬中,用碎物随葬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常见的有将完整的陶器打碎,然后用部份残片随葬,另外还有将铜器、玉器、石器打碎随葬。陶器残片多见钵类,将一件完整的钵碎成数块,或埋于填土中,或埋墓底,有部份残片可能是丢弃墓外。总之在墓中发现的碎陶片,都无法拼合为完整器物。”[28]四川理县佳山东汉时期氐族15座石棺以及1座祭祀坑都有将器物事先打碎埋入的情况,“随葬器物中,有的器物事先有意打烂成数块置入墓中或部分随葬入墓中……有的还将打烂后的器物之一部随意丢于墓坑坑沿上。”[29]
以上材料虽为不完全统计,但说明,历史时期我国的周边后进民族仍然存在 “毁器”葬俗,并且“毁器”葬俗的表现形式不仅有毁陶器,还有毁石器、毁玉器、毁铜镜、毁金属牌饰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毁器”葬俗在他们的社会中形成或者继承,必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由此观之,“毁器”葬俗的表现形式,不管在我国的北方地区还是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其产生大体原为各地区处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人们出于对灵魂观念抽象的具象表现。这是一种自发的选择。
五、结语
“毁器”葬俗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葬俗,它流布的地域广阔,不限于中国而且具有世界性;流布的时间久远,不限于史前而且历史时期乃至今日都存在。由于古人在认识上有所局限,出于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出现了以 “毁器”为形式的葬俗。虽然 “毁器”葬俗的表现形式不一,即这种葬俗在各地区所毁的器物不一样,但其重要表现的共通点都是以毁掉器物来贡享或陪葬先人。所毁的器物种类是青铜兵器也好,陶罐、玉石也罢,这应当与该地区的人们所掌握的优势资源有关,或者是用这些器物以表明死者的身份。因此,“毁器”葬俗作为一种人的观念的产物,表现了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对生命与死亡的认识与信仰,这必定是与人们所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考古资料表明,世界初期文化时代的许多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毁器”葬俗,而这种初期文化时代下的人们就处于差不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就是说,这种葬俗所反映的丧葬观念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关,是一种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共同选择。综上所述,对三峡地区的 “毁器”葬俗可得出如下之结论:
第一,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的源流应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该地区的传承,它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主要是受到当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
第二,三峡地区 “毁器”葬俗及其内容可能与中原地区出现相似性,主要是因为先民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基于其上的思想意识大致相同的缘故。
第三,不排除三峡地区与中原等地区在 “毁器”葬俗及内容上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因为该地区在古代社会的战争与交流均十分频繁。
第四,“毁兵”葬俗现象应该属于 “毁器”葬俗的范畴,同样体现出三峡先民对 “器”与死者、生者于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周易[M].四库全书本.
[2]礼记[M].四库全书本.
[3]黄凤春.毁器与折兵——楚国丧葬礼俗的考古学观察与释疑[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2(0):339-345.
[4]何崝.商代卜辞中所见之碎物祭[J].中国文化,1995(1):74-84.
[5]黄卫东.史前碎物葬[J].中原文物,2003(2):24-29.
[6]张英.从考古学看我国东北古代民族“毁器”习俗[J].北方文物,1990(3):21-27.
[7]朱世学.巴楚墓葬中“毁兵”现象的考察及相关认识[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2):30-35.
[8][18]邱诗萤.长江中游史前毁器葬[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7-21.
[9]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J].考古学报,1981(4):462.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1986年三峡坝区三斗坪遗址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99(4):4.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73、208-216.
[12]屈家岭考古发掘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J].考古学报,1992(1):78-79.
[13]湖北省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狮山遗址墓葬[J].考古学报,1987(3):354-356.
[14]张云鹏.湖北黄冈螺狮山遗址的探掘[J].考古,1962(7):344.
[15]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怀化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3(2):301-328.
[16]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荆江大堤荆州马山段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5.
[1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46.
[19]张明东.略论商周墓葬的毁兵葬俗[J].中国历史文物,2005(4):72-79.
[20]张军.契丹覆面、毁器、焚物葬俗小议[J].北方文物,2005(4):40-43.
[21]金成淑.慕容鲜卑随葬习俗考[J].人文杂志,2005(3):126-132.
[22]孙危.鲜卑“毁器”葬俗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2009(0):139-147.
[23]毛远广.鲜卑史及其考古学文化相关问题研究[J].大众文艺,2015(1):269-272.
[24]马利清.匈奴墓葬出土铜镜及毁镜习俗源流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76-82.
[25]彭善国.谈渤海葬俗中的“毁器”——读《宁安虹鳟鱼场:1992-1995年度渤海墓地发掘报告》札记[J].北方文物,2014(1):35-37.
[26]蔡强,寇玉峰.辽宁朝阳北魏墓[J].边疆考古研究,2006(00):327-338.
[27]黎文宗.桂东北地区石室墓的发现与研究[J].四川文物,2013(5):64-70.
[28]郑超雄.武鸣先秦墓葬反映的骆越宗教意识[J].广西民族研究,1994(1):38-44.
[29]徐学书,等.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J].南方民族考古,1987(0):211-237.
[30]张碧波.关于毁尸葬、毁器葬、焚物葬的文化思考[J].中原文物,2005(2):36-40.
[31]郜向平.商墓中的毁器习俗与明器化现象[J].考古与文物,2010(1):42-49.
[32]翟胜利.商代毁物葬俗试探[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3):123-132.
[33]井中伟.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学观察[J].考古与文物,2006(4):47-59.
[责任编辑:丹兴]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6)02-0067-05
[收稿日期]2015-10-28
[作者简介]封世雄,男,重庆璧山人。主要从事区域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
———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