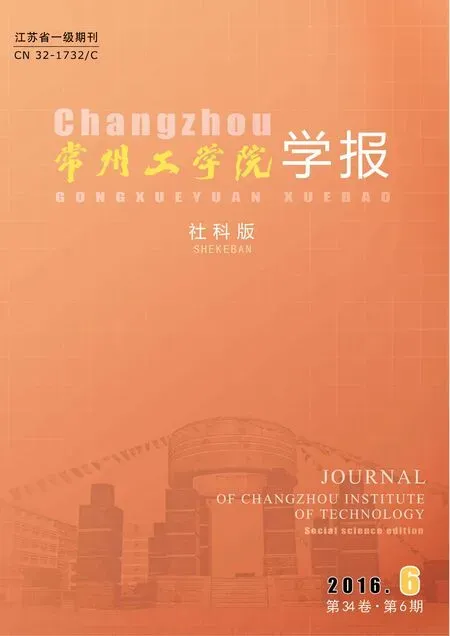加拿大华人真正的关切之声
——采访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得主余兆昌
赵庆庆
(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江苏南京210046)
加拿大华人真正的关切之声
——采访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得主余兆昌
赵庆庆
(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江苏南京210046)
余兆昌(Paul Yee, 1956— ),加拿大知名的华裔英语作家、史学家,是继诗人弗雷德·华(Fred Wah)1985年荣膺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并多次摘取北美其他文学奖项,为加拿大华人英语文学发展和多元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著述丰富,出版了近30部多文类英语作品,包括小说《学飞》《三叔的诅咒》《挣脱》《君子》,剧本《金山惊魂》,短篇小说集《亡者的金子》,儿童故事集《天空斗士,教我飞翔》《金山传说》,绘本《玫瑰在新雪上歌唱》《鬼魂火车》《竹》,以及里程碑式的史学著作《咸水埠:温哥华华人图史》和《唐人街》等。在其众多著作中,《三叔的诅咒》已被中译出版。文章就跨文化成长和批评、写作和身份、边缘和主流、加拿大华人文学现状和未来等问题对作家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在2015年9月于多伦多市作家的寓所进行。
加拿大华人文学;余兆昌;跨文化成长;边缘身份
一、“中国对我来说还很遥远。”
赵:约一个世纪前,加拿大传教士把加拿大文学带到了中国,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有加拿大文学选集出版。您可能是首位有作品见诸中国的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家,1994年,您的短篇小说《草原孀妇》被收进《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读》,在华出版。2013年,您的英语小说《三叔的诅咒》和故事书《鬼魂火车》的中文版在华问世,和郑蔼玲(Denise Chong)、李群英(SKY Lee)、方曼俏(Judy Fong Bates)的获奖书作,同被列入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经典丛书。中国有关您的研究日趋增多。对此,您有何感受?
余:这当然是好事,但我得说这并非我开始写作的初衷。我用心向加拿大人和北美人讲述加拿大华人的故事,中国仍然太遥远了。
我1976年去过中国,那时我二十岁出头,看到了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发生了巨变。由于在加拿大长大,我那时无法理解中国。我用英语写作,写给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看。我惊喜自己的书传到了中国,但我不会因之而改变,不会觉得自己要为中国写作。尽管我对中国好奇,但它对我来说还很遥远。鉴于我的经历,我怀疑自己对中国读者讲述,他们是否会信以为真。中国会把我当作外国人,中国人读我的书,会发现书中有中国元素,但还会觉得我是个西人,以西人身份写作,位于西人的立场。
我高兴这儿的华人移民能读到我的书。他们渴望多了解加拿大,多了解此地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不会讲中文或普通话的加拿大华人。今天的中国移民,和早年来自华南的移民的后代,存在着新的鸿沟。
赵:您有机会回到中国家乡看看吗?
余:1976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去了老家在的村子。我什么人也不认识,也没亲戚住那儿。那个村子在广东省开平县的冲间,乘汽车到那儿后,有同志带我去见村里的长者。我问:“您认识我父亲吗?”我报了父亲的名字,他说不认识。我又说了我哥哥的名字。他说:“啊,我认识你哥!”他带我去看村里我父亲住过的房子。我拍了几张照片就离开了,因为我谁都不认识。1976年,我还去了香港拜访外公,他说我有个嫂嫂住在香港。很多年前,父亲在中国时有个儿子,这个儿子结婚留在了中国。我父母去世后,联系就中断了。我从不知道嫂嫂住在香港,有家有口。但她知道我,只是从未联系。她知道我母亲,讲了她的不少事,让我喜出望外。她嫁到我家后,就和我母亲、兄弟住在村里。
赵:您见过自己的父母吗?
余:从没见过,也不了解。但我嫂嫂了解,她比我大好多。
赵:您有几个兄弟姐妹?
余:父亲的第一位妻子生了儿子,夭折后,就收养了一个男孩。他后来的妻子就是我提到的这位嫂嫂。父亲在发妻去世后再婚,第二位妻子就是我母亲。她在中国没有生育前,收养了一个男孩。当时,父亲已经去了加拿大,她留在村里。因此,我父亲在我哥和我出生前,有两个养子。
赵:这么说,总共有两个收养的儿子和两个亲生的儿子。
余:很长时间,我对此一无所知,没人告诉过我。我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我还有一个哥哥。我只认识母亲的养子,在上个世纪50年代,她把他带到了加拿大。父亲和他第一个妻子的养子则留在了中国,他超龄了,加拿大的移民法只允许21岁以下的孩子入境。
1976年后,我和嫂嫂只是偶尔寄寄圣诞卡,因为实在彼此不了解。1988年我搬到多伦多,感到很孤独,就打电话给香港的嫂嫂,说很想和她一起去村里。她说:“好的,来吧!”那年秋天,她领我去了村子。带了好多东西,她要送给村民。
她用我的护照买了冰箱,因为当时要有华侨护照才能把电器带进中国。我不清楚嫂嫂为什么要帮村里人。那里没有我们的亲戚,但她对他们有感情,困难时期常从香港带这带那回去,待人很体贴,晓得他们的日子不好过。村里人打心底喜欢她,她带我回村时到处受欢迎。我们拜谒了祖父母的墓。刚好有人家举办婚礼,我便参加了婚宴。我对村子有好感,也好奇。
赵:村里人把你当成陌生人或另类吗?
余:没有。那里人都知道华侨。有的华侨回村了,有的没有。我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离开了。村里人对我不那么亲热,是因为我家不在那里。嫂嫂一直保护我,不让人问我要钱或求我帮忙到加拿大。我在那里十分安全,但不梦想回去。我不属于那里。
赵:你在加拿大长大,在此生活了几十年,用英语写作。作为加拿大华人移民的第二代,自然会更多认同加拿大,而非父母的中国。回村两次后,您有没有再到中国?
余:10年前,去长春参加过朋友的婚礼,到了上海和北京观光。那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旅。
赵:2014年,您和加拿大四位主要的华裔英语作家——郑蔼玲、李群英、方曼俏和朱蔼信(Jim Wong-Chu)——受邀来华参加译书的宣传旅行,您为什么没来呢?
余:当时我在写小说《君子》(TheSuperiorMan),得集中精力。
二、“强烈的正义感”
赵:您由姨母丽莲抚养长大,从她那里和图书馆阅读中,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您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余:我还从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黑白电影中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些电影总有道德内涵,关乎责任感和做事正当。
赵:是功夫片吗?
余:不,多数是戏剧片,讲家族纠纷,或是少妇被冤行为不端,被逐出家门,投进监狱,没人甚至她丈夫都不相信她无辜。但最后,冤情昭雪。中国文化中的善必胜给了我力量。记得一句格言,用广东话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是学者认为中国文明幸存久远的一个原因,不同社会阶层互有责任和义务,力求公道,才能和平共处,维持良好关系。
中国故事带有强烈的正义感,错必纠,冤必伸。我为孩子们写的书也显示了匡扶正义,这种非常简单的故事类型,部分就来源于我看的中国旧影片。
赵:诚然,您一遍遍向孩子讲述了公平正义。获得首届露丝·施瓦兹儿童文学奖的《玫瑰在新雪上歌唱》(RosesSingonNewSnow)就沿用了这种故事套路。梅琳是烹调高手,做工勤奋,而她父亲和兄弟却对官员谎称美食是他们做的。官员令其再做,他们却找尽借口也做不出,只好请出梅琳。最终她得到了奖赏。您荣获总督奖的绘本《鬼魂火车》(GhostTrain)也有类似的公义主题。聪艺的父亲和数千中国苦力为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而丧生,既没得到补偿,也没得到安葬。聪艺通过她的画讲述了他们的悲剧,使他们的功劳得到了历史的认可。
余:公义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加拿大同样重要。过去,华人备受白人和种族主义歧视,加拿大华人怀疑他们能否在该国找到公义。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华人被接纳为平等公民,向华人强征的人头税也退还了。因此,能看出社会在进步,加拿大社会从极端种族主义发展到非常包容,是好事。
赵: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负面的?
余:女性待遇太差了。我朋友没上成大学就是因为她父亲说:“我儿子都去上了,没有理由再让女儿去上。”
中国还特别讲究等级,父为子纲,不容纳个人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或家族是全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中心,这就意味着优先照顾自己人。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政局动荡,外忧内患,社会秩序紊乱,南方的中国人出洋谋生。移民多半很穷,地位低下,因此自私吝啬。我家也属于加拿大华人家庭,贫困,以自我为中心。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乐善好施和对艺术、慈善的支持。华人社团渐渐有钱后,情况开始好转。
赵:您怎么看这几十年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余:在新闻曝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受到的报道最多。人们认为,来自中国的富有移民和金钱导致房地产上涨,住户买不起房子,这种现象在温哥华尤为严重。阔气的中国人一来就买豪车豪宅,引发了众愤。一些人还讲,有钱的中国移民到了加拿大后还享受加拿大的救济,因为他们不报收入,故意做出需要政府资助的样子。还有报道说中国移民弄虚作假拿驾照。
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来自想和中国做生意的加拿大利益集团,他们认为中国包含了巨大商机。有些卖房子的加拿大人就受惠于上涨的房地产。
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也有大量从伊朗和俄罗斯流入的国际资金。由于华人的体貌易辨,就被当成了炒高房价的罪魁祸首。政府没有统计房地产买主的国籍,因此无法对这个问题的程度给出精确说法。不过,温哥华的房子买不起,的确已成事实,围绕外国资金和房价攀升的争论依然激烈。
赵:中国移民是否也导致了多伦多的房价上升?
余:我不知道。也有很多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富有移民来到多伦多,但注入多伦多的中国资金却没有受到同样多的苛责。不太清楚原因,可能和温哥华有更多东亚人有关。我觉得多伦多的人口构成比温哥华的多元,比如有举足轻重的非裔加拿大社团。另外,两个城市的地理也不同:温哥华周围是高山和大洋,而多伦多可以朝三个方向扩展。
三、“获总督奖让我有勇气辞职,我知道要对待自己认真点。”
赵:我总好奇作家怎么写成和出版第一部作品。您的处女作《天空斗士,教我飞翔》(TeachMetoFly,Skyfighter!),由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家李群英配画,1983年由詹姆斯·罗里姆公司出版。您还记得是什么激发您写第一本书?您为什么说自己是“误打误撞”成为作家?
余:我开始写作纯属“误打误撞”,是别人让我写书的。当时,我在温哥华唐人街做义工,出版商找来,说:“我们在做一个系列,写加拿大各城市的儿童,温哥华的这本书想以唐人街为背景,要找唐人街的作家写这些故事。”
他们问我想不想写,我熟悉唐人街,儿童书浅显直接,能有多难?我去了图书馆,读了些儿童书,写了九个故事的提纲,出版商选了四个。
赵:花了您多长时间?
余:九个故事的提纲,大概花了两三个月,编辑却花了约两年时间。
赵:自那以后,您出版了近30本书,包括儿童书、青少年书、短篇小说、成人类的非虚构书,还有首部成人小说——今年出的《君子》。写作显然成为您的习惯和激情所系。您获得了众多奖项,《咸水埠》(SaltwaterCity)1989年获温哥华城市书奖,《鬼魂火车》1996年获最令人渴慕的总督奖,《亡者的金子》(DeadMan′sGold)2003年获纽约公共图书馆最佳青少年图书奖,等等。是什么让您保持了30多年旺盛的创作力?
余:我相信,加拿大的书籍肯定会继续反映该国的多元族裔。出版人经常让我写,知道我写加拿大华人题材。比如,这套加拿大华裔女孩淑丽的书,出版人说:“我想为这个阅读层次、这种读者出本书,你能写吗?”或者,出版人会让我写本烹调书。我自己并没有计划写那些书。但是,大概从1998年起,我就一直努力写成人小说。
赵:从您全职写作起,差不多20年了。
余:您下个问题可能是:我为什么要写成人书?一个原因是:儿童作家不被器重。人们会说:“不对!不是这样!为孩子写作很难的。”但是,我体会过,自己不被视作严肃的作家。
赵:难道安徒生、J·K·罗琳也不是?
余:她因为非常成功才受人重视。从1998年至今,我花了17年才出版了一本成人小说,此前,我做过种种尝试,全都失败了,我想自己该放弃了,太难了,写不了。但总不甘心,我确实想创作一部成人小说,必须证明自己能行。
赵:这是您第一次找出版人,而不是他们找上门了吧?
余:是的。被拒的滋味不好受。我把书稿寄给出版社,他们说:“不行,我们出不了。”重写后,送到另一家出版社。还算幸运,因为我在加拿大西海岸有加拿大华裔作家的名声。我还得给出版社提供营销策略,说明这本书怎样卖得好。第一次,我必须做这样的事。
赵:继弗雷德·华1985年获总督奖后,您是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加拿大华裔作家。您当时什么感受?能否描绘一下颁奖典礼?
余:获得这项荣誉,对我意义重大,让我有勇气辞职,知道应该对待自己认真点。颁奖典礼在蒙特利尔,往年轮流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这两大城市举行。现在,我想是在首都渥太华。典礼包括宴会、新闻报道、与总督见面、演说。获奖者在颁奖前就会接到通知。那年我正在温哥华参加作家节,接到来电说:“你得保密到颁奖的时候。”
赵:您是否完全没料到自己会获奖?
余:没有,因为绘本一般不会得文学奖,文学奖通常给小说,小说文字多,有更多故事和人物发展空间。我希望配画的哈维·陈也能获奖,可惜没有。我有一分钟致答谢词。那时,奖金是5 000加元,现在增了。作家和艺术家在加拿大挣钱不多,能有所得就心存感激了。
赵:吉勒(Giller)文学奖有多少奖金?
余:是加拿大文学奖中最高的了。
赵: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家林浩聪得过,我把他的书译成了中文。过几天我们会做访谈。
余:他人很好,就住在附近,在公园的另一侧。
赵:您在文学和历史写作上都有建树。在文学领域,您通过故事鲜活地呈现历史。历史方面,你为建构完整的加拿大华人史和加拿大史做出了贡献。能否请您谈谈自己在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上均获成功的关键?
余:我曾受邀指导写作工作坊,帮助他人写作,我都没答应。我会写不会教。写《君子》时的突破源于写《金山惊魂》(JadeintheCoal)剧本时,我和一位戏剧家合作。她总问这个问题,“你人物的旅程是怎样的?他/她现在到了旅程的哪一段?”现在,我就会反复想,甚至想次要人物的旅程,然后所有碎片就归拢了。“旅程”就是我的核心考虑。
写作过程中,我思绪纷纷,写出提纲,去掉好多想法,让想象和潜意识运转,同时也意识到要用平易的语言。写小说时,我对汉语的熟悉便利了我组织对话。在我所有非虚构类的书籍中,出版社加入了大量图片,为行文增添了人情味。
赵:别忘了,您的史学背景也起了作用。
余:不错,为写书我做了大量的研究,读了非常多的资料,写时只用上一丁点。但我不介意,我喜欢历史和研究。
赵:您一天一般怎么度过?
余:全天写,从早写到晚,一周写七天。小狗巴克斯特还活着时,我起床后遛狗,回家吃早饭后就写作。下午遛狗后,接着写。天天如此。我非常专心,因为我害怕,明年我就60岁了,我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比我年轻的人会突发心脏病,我也会随时死去。我现在写另一部成人历史小说,关于19世纪60年代的淘金华工,已经写了两章。
赵:这本小说什么题目?
余:目前还没有。出版社通常起书名。我起的书名只有几个被采纳,《君子》是其中之一。
四、“移民故事强化了加拿大人的身份意识。”
赵:您说,“我关心华人。我书中的一些人物就源于我自己的家庭或社团。”他们读了您的书后有何反馈?
余:加拿大华人都很给力,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家,如崔维新、郑蔼玲和方曼俏,都受到了加拿大华人的好评,尤其是在加国生活了几代的华人。我们发现,人们对加拿大华人的历史兴致勃勃,许多人想寻找并写下自己的家史。
家人以我是作家为荣,每当有新书出版,都会兴高采烈,但我的书不会成为家庭热点。家人也知道作家挣钱不多,为我担心。总的说来,家里有其他事比我写作更重要,我不过是餐桌上的一张面孔,没什么特别。
赵:2006年10月19日,您作为特邀嘉宾在多伦多公立图书馆作了题为《成为作家》(BecomingaWriter)的演讲,讲稿后被收进海伦·E·斯达布斯纪念讲座集出版。您希望听众“在今晚离开讲座时,不仅对我略增了解,也会更好理解华人——这个在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我肯定他们会的。事实上,您的作品不仅增进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社会和个体的了解,也增加了他们对加拿大这个由200多个族裔组成的国家的了解。我想知道非华裔读者对您书的评价。
余:他们兴趣盎然,读我书的非华裔加拿大人对多元性和不同族裔的移民十分好奇。他们想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在移民过程中的演变。中国人来加拿大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好坏两方面都写了,移民的变化是加拿大经验的组成部分。移民怎么放弃了过去的做法和传统?移民第一代和后几代间的矛盾也是共同话题。老一代从中国来,出生在加拿大的则想做加拿大人,夹在中加之间,他们大多倾向加拿大。加拿大人很受用,觉得“我们的国家真好啊!新来者喜欢我们的价值,要和我们一样。这在文学上就形成了一种自我肯定的主题,而移民故事强化了加拿大人的身份意识”。
成为主流意味着英语流利。像崔维新、郑蔼玲和方曼俏这样的作家说,“我不会讲汉语,也读不懂”。加拿大人就说,“太遗憾了,失去了你的母语”。事实如此。主流社会也就知道了这些移民的后代全都成了加拿大人。
赵:《成为作家》清晰而生动地描述了您的成长和写作生涯,和加拿大华人的历史息息相关,将大大裨益中国读者了解您、加拿大华人及其创作。我可以将您的讲稿译成中文并在杂志上出版吗?
余:当然可以!
五、“我们感觉是局外人,受排斥,因此眼光不同,更加敏锐,能看到不公平。”
赵:您是经历过种族歧视年代的加拿大华人,可能有些不愉快的回忆,也对过去白人和中国移民间的冲突着墨不少。我明白您并不自怜或视自己为受害者,但您可否分享您亲身感受过的歧视和被边缘化?
余:许多作家都是边缘人,身处劣势观看社会,是局外人往里望。我就是这样。我是华人,成长时不属于主流社会而渴望加入。尽管我没有遭过种族歧视,但我知道局外人的滋味,因为我是同性恋。在现在的加拿大,种族主义者不受欢迎,歧视同性恋者却声称宗教信仰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在加拿大,身为华人没什么要紧,身为同性恋却备受争议。有同性恋、双性恋和异装倾向(LGBT)的年轻人自杀率高,有些家庭不能接受同性恋家人,多伦多天主教学校不允许成立彩虹组织帮助LGBT青少年。这都在告诉我,社会对不同的性取向还有成见。
赵:但是,您有没有看到支持同性恋权益的进展?同性婚姻在加拿大、美国等20来个国家已经合法化。
余:不错,争取同性恋权益是取得了进步,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同性恋受到的阻力更为强大。种族主义者让人不耻,而一些人对被称作反同性恋则不以为然,他们说:“圣经上说同性恋有罪,我理所当然反对。”美国反对同性婚姻的势力还很大,尽管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有些州长仍然排斥同性婚姻。作家则退一退,在局外写作评判。一些优秀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如崔维新,就是同性恋。我们感觉是局外人,受到排斥,因此眼光不同,更加敏锐,能看到不公平。我们都深受过伤害,想诉诸作品中。
赵:尽管被边缘化,您仍然觉得不隐瞒真我更好一些。
余:在中国和美国,同性恋生活得不容易。加拿大是我的福地。
赵:您在作品中多次描写了跨族裔的交流和友谊,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比如,在小说《淑琳和蒂亚戈》(Shu-LinandDiego)里,华裔女孩淑琳和同学蒂亚戈在邻居辛普森先生住院时,一起照顾他的狗巴克斯特。在《淑琳和塔玛哈》(Shu-LinandTamara)中,这个华裔女孩和贫穷的非华裔新生塔玛哈成为朋友。在小说《学飞》(LearningtoFly)中,您描写了单亲家庭的华人少年杰新,他妈妈对原住民男孩持有偏见,但他却是他们的朋友。这些情节是否源于您与非华裔交往的正面经历?在加拿大这样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您如何定义自己?
余:我觉得,我不是白人,因而永远不会感觉是百分之百的加拿大人。作为加拿大华人,我们在历史上曾是不被信任、地位低下的少数族裔,回顾这段历史,同时关注其他遭受不公正者,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今天的加拿大,我们认为原住民的所作所为特别不光彩,把他们挤迫到居留区和社会边缘,无视他们,假装他们不存在。联合国就批评过我们的做法。比如,在加拿大多数地区,白人移民和原住民签约获得土地。而卑诗省①省政府从未和原住民签约,就霸占了他们的土地。不公平在于:卑诗省除了从未签约,还从不承认原住民的权利或付给他们土地使用费。简直令人发指!现在,卑诗省在自然资源开发上论战激烈,原住民尽力保护土地免于油气开发。我在唐人街长大的那年头,连华人都歧视原住民,叫他们酒鬼,没文化。现在,我欣见温哥华的很多华人在帮助原住民处理事件,为他们辩护。我们和原住民间存在着历史纽带,都有对公正的共同寻求。华人曾为人头税讨要说法,土著人民则想为更大的事件讨个公道。
赵:加拿大华裔用英语、汉语乃至法语写作。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品已跻身主流,我在Chapters和Indigo大书店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您、郑蔼玲、崔维新、李群英、方曼俏等作家的书,但很难找到加拿大华人汉语文学的英译本。您对他们的文学活动和作品有何了解?
余:了解甚少。我有他们的短篇小说,多数是结集出版的,像《叛逆玫瑰》。我试着读,读得很慢,汉语文学作品太难了。还有,甚至在加拿大中文书店都难找到他们的书。我进去问:“有没有加拿大中文作家出的书?”店员摇头。
六、“《君子》是我的第一本成人小说,披露了中国人的丑陋面。”
赵:《君子》是您首部为成人写的小说。背景是在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筑路华工杨和沿着铁道跋涉,要把他和土著妇女生的混血儿子还给他母亲,途中卷入了筑路华人和土著间的争斗,但他决意不管多大困难,都要成名赚钱。弗雷德·华、郑蔼玲等知名作家和朱迪·杨教授都对该小说予以了衷心的佳评,我也得知它扣人心弦,细节生动感人,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再现了筑路华工,以及华人和土著这两个当时被轻视族裔之间的关系。就像您的其他文学创作,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您能介绍一下在加拿大不同城市《君子》新书发布的情况吗?
余:大部分新书发布由不同城市的地方组织承办。在温哥华市,卑诗省加拿大华人历史协会赞助我在温哥华公立图书馆演讲,我用英语和广东话发言。在维多利亚市,唐人街的母狮俱乐部请我帮助他们筹款,我在宴会上发言。在纳奈莫市,我在温哥华岛大学演讲。在温尼伯市和首都渥太华,我在当地作家节上发言,读书中的选段,这是作家节的部分活动。
赵:您将选读《君子》吗?
余:对,但我不是“读”。我站起来,凭记忆“讲”书里的故事。我不想让书把自己和听众隔开,而想看看他们对我讲述的反应。这年头,出版人都说作者必须和读者互动。因此“讲”故事,而非“读”故事,是我接触听众的途径之一。这也是许多文化中的口述传统,起先是大声讲故事,而不是写。就我而言,这比读故事丰富多了,还要把故事表演出来。
赵:在多伦多书店的发布会情形如何?
余:在多伦多,发布会是朋友安排的。在市中心湾街的一家书店,邀请了朋友和同道,提供葡萄酒和奶酪,还帮书店卖出了很多书。这是一家独立书店,我很想帮助它不要倒闭,这样的书店现在寥寥无几了。
赵:您网站上《君子》的宣传片制作精良,不纯粹是商业性的,有历史感,并且是把书作为严肃认真的艺术品来介绍的。
余:很高兴您能看到。这也是促销手段之一吧。
赵:您为什么最想把《君子》译成中文?
余:这是我的第一本成人小说。它披露了华人的丑陋面,主人公有时令人嫌恶,易怒,对同胞恶语相向。加拿大华人文学的许多作品都害怕写华人的负面,我们小说中没什么坏人,我们想被看作勤劳的,善解人意的。其实,任何团体都有好人坏人。
赵:以前,华人受歧视,加拿大华裔作家就总想展示正面形象。现在,华人已被主流吸纳,是逐渐描绘其全真形象的时候了。
余:如您所言,这得力于华人被接纳的历史进步。
七、“我对华人社团仍有深情……我们这代作家非常严肃,因为继承了充斥歧视和苦难的黑暗历史。”
赵:您在2006年演讲《成为作家》中回答为什么写作,列举了三个原因:1.“从未知走向已知”;2.“让加拿大华人在书中看到自己”;3.“回报让我变得完整的华人社团”。如今,10年过去了。您对写作初衷有什么新认识吗?
余:我仍抱守着这样的写作初衷,尽管我写了10年,希望是越写越好。写《金山惊魂》剧本,我得用中文思考。戏是中英双语的,演员来自广州,讲粤语和普通话。我很高兴在剧本里用了大量的口头粤语。写小说《君子》,我对粤语口语研究更多。我长于英语写作,但我觉得要掌握更多的中文。我现在懂得的能用于写作的中文,肯定比10年前多了。我写作中有个矛盾:我用英语写早年移民的经历,而他们讲的是另一种语言,中文。该怎么写?淘金客和铁路华工的历史是关于讲中文的中国人,我却用英文描写他们。我觉得我用英语只能写出他们的部分真相,还不知道能否行,语言太有玄机了。你或许觉得华人在加拿大的经历应该用中文写,转念又想,“英语读者怎么办?”我写的是英语,却要使它像中文。2006年,我还没想到把中文糅入作品,现在,中文突然走进了我的生活。
赵:您怎样定义自己的写作?
余:我喜欢写有关华人的作品,要让其他华人读者觉得真实,不管这些读者是加拿大华人还是中国人。我希望他们觉得我笔下的华人或加拿大华人真实得就像他们的同胞。我不知道能否成功,这涉及跨两种语言和文化写作,而二者都随时间起了变化。但是,这对我写作至关重要。
赵:您怎样看待加拿大华人写作的未来?
余:未来在年轻的一代身上,他们写当下世界,技术、全球化、建立人际关系的各种方式等。我觉得,年轻一代比年长的作家笑得更多,我们这代作家非常严肃,因为继承了充斥歧视和苦难的黑暗历史。我们必须给它以光荣和尊敬。年轻一代更加放松和开放,他们也关心社会,看到各种不公。我乐读他们的作品,最爱读的有多丽塔·刘的短篇小说集《寸草谢日》、凯文·郑的《美和怜悯》,以及乔恩·陈·辛普森的《中国星》。他们出色展示了加拿大华人的不同风貌。
注释:
①卑诗省,即早年华人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Columbia)的称呼。据加拿大统计局(www.statcan.gc.ca)数据,该省历史上为加拿大华人最多的省份,现次于安大略省,居第二,有华人约50万。全加拿大华人约150万。
责任编辑:庄亚华
10.3969/j.issn.1673-0887.2016.06.004
2016-07-17
赵庆庆(1971— ),女,副教授。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041);2014—2015年度中加学者交换项目
I206
B
1673-0887(2016)06-0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