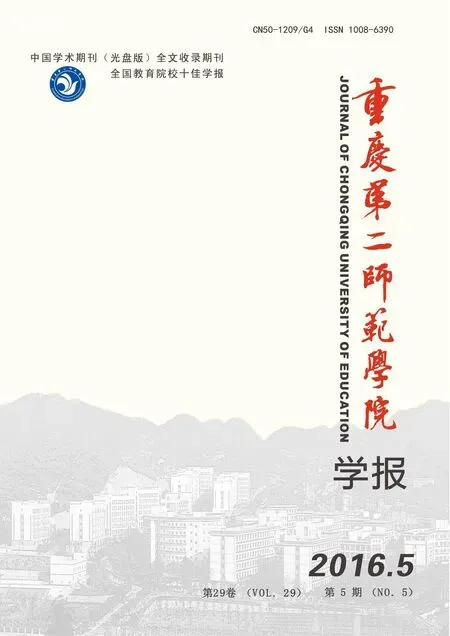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境界”说
高 崎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境界”说
高崎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关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标举的是“境界”还是“意境”,历来争议很大。实际上,“境界”比“意境”更能体现《人间词话》的诗学思想。“境界”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融入了西方美学思想,中西融为一炉且自出新意,最终成为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
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意境
一、“境界”与“意境”的源流
“境界”一词,最早是分开使用的,许慎《说文解字》中谓“境,疆也”、“界,境也”,此处境、界均有疆界之意。而“境”“界”合用,最早见于《列子》:“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此“境界”乃指疆土范围。
汉代以来,随着佛学的传入,“境界”开始出现在佛学著作中。如《杂譬喻经》有云:“神是威灵,振动境界。”《华严梵行品》亦云:“了知境界,如幻如梦。”这里,境界不是指具体的事物,而是含有佛学幽深玄妙的意味。
最迟到隋唐之时,“境界”开始出现在诗文中。如白居易的《偶题阁下厅》中就有“平生闲境界,尽在五言中”,李颀《长寿寺粲公院新甃井》中亦有“境界因心净,泉源见底寒”,此时的“境界”仍没有脱离佛学的意味。到了宋代,“境界”开始运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如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云:“横浦张子韶《心传录》曰:‘读子美“野色更无山隔断,山光直与水相通”,已而叹曰:‘子美此诗,非特为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彻处,往往境界皆如此也。’”这里的“境界”显然不再局限于佛学樊篱,而是表达一种意境或格调。到了明代陆时雍的《诗境·总论》:“张正见《赋得秋河曙耿耿》:‘天路横秋水,星河转夜流’,唐人无此境界。”“境界”含义又延伸了,指在对景物的整体观照中得出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清代以后,以“境界”品评诗词者不胜枚举,其意义也更加宽泛,分化更加细致,渗透在诗、词等多种文学体裁中。如清代金圣叹在《第六才子书》卷七中说:“‘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是清净身’,悟时便有如此境界;‘风弄竹声金珮响,月移花影玉人来’,迷时便有如此境界。”近代以来,“境界”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仍很普遍,如梁启超在其诗文中多次谈到境界,其《新大陆游记》就曾提到:“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鹦鹉名士占尽矣。”同时代的况周颐则在词学领域中标举“境界”说,其《蕙风词话》云:“涩之中有味、有韵、有境界,虽至涩之调,有真气贯注其间,其至者可使疏宕,次亦不失凝重,难与貌涩者道耳。”
由此可见,“境界”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其从一个客观意义上的疆界范围,过渡到佛经中玄虚的义理,随后渗入文学艺术领域,经过历代文人的发挥和渲染,最终形成一个意象饱满的美学范畴。
反观“意境”一词,原本也是分开使用的。《说文解字》云“意者,志也”,指人内心的思想。至于合用,始见于唐代王昌龄的《诗格》:“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艳秀者,神之于心,处心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精。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物境”指经过诗人头脑加工过的客观景物;“情境”指个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体验;“意境”指诗人在对外界客观事物的观照中,不受外界事物和个人情感所左右,产生的一种动人心魄的审美效应。宋代诗僧普闻的《诗论》说:“天下之诗,莫出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易琢,意句难制。境句人皆得之,独意不得其妙者,盖不知其旨也。”在普闻看来,意句比境句更为难得。清代宋徵璧在《抱真堂诗话》中说:“何李论诗以意境合为合,意境离为离,各有是非。”指出“意”与“境”可分可合。实际上,“境”即物境,是经过诗人审美观照的外界客观事物;“意”即情境,指由外在的客观事物所触发的内心情感体验。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境界”出现的年代更为久远,大致从客观的疆界,过渡到主观的佛教用语,再演变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本身有主客体统一的性质。而“意境”出现较晚,且直接见于文学艺术领域。从表面上看,“境界”与“意境”的意义相差不大,以致经常被混用,倘若仔细辨别,便会发现“境界”比“意境”的含义更深远一些。“境界”指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整体的美学价值和风貌,既有客观景象的描述,又有主观想象的参悟,以及“意境”所没有涉及的其他的审美领域。而“意境”则虽有“意”“境”之分,但“境”显然经过个人情感的皴染,带有感情色彩。所以说,“意境”总归偏向于主观情思的抒发。因此,“境界”比之“意境”,渊源更为久远,含义更为丰富,两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微妙的相承关系。
二、《人间词话》标举的是“境界”还是“意境”
在《人间词话》中,“境界”“意境”都出现过,可王国维标举的究竟是“境界”还是“意境”呢?对此,有人持“境界”说,有人持“意境”说,还有人把“意境”与“境界”混为一谈。针对这些见解,笔者认为王国维标举的是“境界”说,理由如下:
其一,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与“意境”出现的频率来看。以王国维亲自辑选并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词话为例,“境界”出现十三次,“意境”仅出现一次。尽管仅从使用频率上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但至少约略知道王国维对其重视的程度。
其二,从《人间词话》的内容来看。第一则即开宗明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第九则又说:“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在参照前人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印证并确立自己的“境界”说。此外,《人间词话删稿》亦有:“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王国维显然对“境界”说已经了然于心,甚至颇为自鸣得意。纵观整部《人间词话》,王国维正是以“境界”说为前提展开其对于词的分析的。
其三,从《人间词话》的发表年代看。早在《人间词话》发表(1908年底至1909年初陆续在《国粹学报》连载)之前,王国维已开始致力于词的创作,分别于1906年刊成六十一阕《人间词甲稿》,于1907年刊成四十三阕《人间词乙稿》,其中在署名为樊志厚、实乃其自撰的《人间词乙成稿序》[1]8中提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不仅如此,序中凡“意境”者比比皆是,而“境界”却只字未提。并且,王国维此前发表的几乎所有相关的文字记录,均没有出现“境界”一词。据此,有人认为《人间词话》标举的应该是“意境”,“境界”是从属于“意境”的。乍一看,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观其1907年所写的《三十自序》(二)中说:“知其可信而不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2]7可以想见,王国维之所以填词,是为摆脱哲学上的痛苦和烦闷,是寻求精神慰藉或者解脱,期间应该没有既定的理论指导,也就是说,王国维在写作人间词的时候,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境界”说,但正是填词的创作实践,为他的“境界”说奠定了基础。况且《人间词乙稿》的最终写成,是在1907年底,而《人间词话》开始刊出,是在1908年底,期间相隔近一年之久,这个阶段也是其逐渐由“意境”向“境界”说过渡的阶段,以王国维的才学和颖悟,完全有能力建立一种新的理论。
《人间词话》完成后,王国维的兴趣又转向了戏曲的搜集和整理。1908年至1913年间,王国维写成《宋元戏曲史》一书。其中在评价元杂剧时,王国维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3]86此处王国维提到了“意境”。由“意境”转向“境界”,再回到“意境”,中间几度转变,有人据此认为王国维本人并未真正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意境”与“境界”差别不大,并提出了“境界”与“意境”同一说。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其一,王国维在写作人间词时,正如其在《人间词乙稿序》中所说,他之所以提出“意境”,是因为他这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境界”说。
其二,《人间词乙稿》完成后,王国维开始酝酿“境界”说,直到《人间词话》六十四则刊出之前,“境界”已成胸中丘壑。与人间词写作时间大致相同的《文学小言》第五则“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段……”,而到了《人间词话》第二十六则改成“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由“阶段”改为“境界”,显然是经过一番酝酿的。
其三,王国维既已形成“境界”说,为何后来在写作《宋元戏曲史》时,又尽弃前说呢?这看似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还是有迹可寻的。一是《人间词话》的对象针对词,而《宋元戏曲史》则是针对戏曲,体裁不同,其理念也不尽相同,不足为怪。二是在《人间词话》创作前后,王国维正沉迷于西方文化,“境界”说除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外,无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人间词话》六十四则在1909年初相继发表,《宋元戏曲史》则定稿于1913年,中间相隔四五年之久,此时王国维随同罗振玉到日本已一年了,不知是对西学已经厌倦,还是受到罗氏的影响,王国维与西方思想决裂,一头扎进了乾嘉派的考古之中。这个时候,是用曾经沾染西学色彩的“境界”,还是用中国传统的“意境”,不言自明,自然选择“意境”了。
综上所述,王国维之所以在《人间词话》中标举“境界”说,是因为:“境界”可追溯到汉代之前,“意境”直到唐代才开始出现,“境界”比“意境”似乎更有来历;“境界”从客观意义上的疆域,成为宗教中的术语,再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术语,经历了历史的演变,而“意境”则直接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故“境界”比“意境”所指似乎更为宽泛;“境界”指文艺作品呈现的一种整体的美学风貌,既可以是一种意境,又可以是一种风格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境”是从属于“境界”的;“境界”除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打上了异域文化的烙印,其内在具有一定的体系和逻辑,有别于“意境”式的感悟。
三、《人间词话》“境界”的含义
《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既汲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借鉴了西方文化的某些特质,并加以融会贯通,在一种中西合璧的形式下绽放出新的光芒。
关于“境界”的含义,研究者多所论述,其中亦不乏新颖独特之见。其一,把“境界”等同于“意境”。如吴奔星认为:“境界既非单纯写景,还包括人的内心世界,实际就是通常所说的意境。”[4]24祖保泉认为:“王国维笔下的‘境界’或‘意境’,是一个概念。”[5]其二,把“境界”看作“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感人的感情”以及“气氛”的意义[6]211-214。其三,从佛学中寻找根据,如叶嘉莹从佛学“六根”“六识”“六境”上阐释“境界”,认为境界是以感觉经验之特质为主的:“《人间词话》中所标举的‘境界’,其含义应该是说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7]193其四,把“境界”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景”或“写景”。如徐复观认为:“他(王国维)之所谓‘境界’或‘境’,实即传统上之所谓‘景’或谓‘写景’。”[8]52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哲学和美学意义上指出“境界”说的唯心论实质,或是与我国传统诗话“兴趣”“神韵”等概念相比较做出新的解释。尽管众说纷纭,但这些研究者大都承认“境界”是景物与情感、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艺术形象。下面笔者分别从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两个角度来阐明个人的看法:
1.从承续传统来看,“境界”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一脉相传,这在《人间词话》中已成既定的事实。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第六则)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删稿》第十则)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境界”应该包括景物与感情两个元素,但必须有“真”字贯注其间,才称之为“有境界”。在《人间词话删稿》中,又对此加以深化,强调景与情是融为一体的,即使看似单纯的景物描写,也隐含着情感,“情”占第一位。其实,景和情的关系,前人已有所论及。如清代王夫之所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9]72,91由此可见,王国维的“境界”说正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学说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词有“隔”与“不隔”之别:
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人间词话》第三十六则)
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人间词话》第三十九则)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人间词话》第四十则)
王国维所谓“不隔”,就是如实地描绘自然,抒写胸臆,“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情感与景物浑然一体。其在《宋元戏曲史》中亦有言:“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不隔”一词,据杨牧所言,是王国维在读戴震论说《易经》中的一篇文章中注意到的,并把那段引文抄录了下来。[10]可见,王国维确实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经过了思想的沉淀,逐步构建起“境界”这一理论体系的。
2.从借鉴西方来看,“境界”说受到了包括康德、叔本华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我们也能在《人间词话》及王国维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证据。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第二则)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人间词话》第六则)
它们之间的大体关系:造境——理想派——合乎自然——理想家,写境——写实派——邻于理想——写实家。
“造境”一词,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郑谷《峨眉山》诗有“造境知僧熟,归林认鹤难”一句,“写境”也与我国传统诗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而“理想”与“写实”则是西方的美学术语。“造境”,以抒发情感为主,倾向于理想,大致相当于西方的浪漫主义;“写境”,以描摹现实为主,倾向于写实,大致相当于西方的现实主义。但写实并非机械地照搬照抄,也要加入个人的情感体验;而理想也并非完全出自主观,同样也要从现实寻求素材。乍一看,“造境”与“写境”好像和“理想”与“写实”存在着等同关系,但如果详加辨别,则大有来历可寻,这在王国维其他一些文论中也能看出端倪。如《红楼梦评论》有云:“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11]4
不难看出,自然界之物直接或间接与我们存在着利害关系,一旦写之于文学及艺术中,必须超脱现实利害及时空限制关系,达到一种“理想”境地,故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此本于康德、叔本华的超功利主义的美学思想;可贵的是,王国维并不拘泥于他们的唯心主义,而是肯定了客观现实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强调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因此,“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难以作截然不同的划分,故“写实家亦理想家”,而“理想家亦写实家也”。王国维慧眼识金,发现中西美学理论微妙的不同,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显示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学的理解。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人间词话》第三则)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知;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人间词话》第四则)
它们之间的大致关系: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由动之静时得之——宏壮,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唯于静中得知——优美。
“有我之境”,以王国维的理解,诗人在对客观景物观照时,挟带着个人的情感,而在情感的渲染下,客观景物也不免带有诗人情感化的色彩,即宋代郭熙所言“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12]26。“无我之境”,是说诗人在与客观景物的对峙中,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此时诗人心灵澄澈,万物与我归一,即李白在《敬亭山》诗中所谓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乍一看,“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似乎是王国维的独创,其实是以西方的理论与我国传统的诗话融合的结果。
“优美”与“宏壮”,本于康德“优美”与“崇高”,到了叔本华那里,又进行了引申和发挥,这可以从王国维的一些论著中找到踪迹。如《红楼梦评论》:“而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则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感情曰壮美之情。”[11]5又如《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及汗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至古今学者对优美及宏壮之解释,各由其哲学系统之差别而各不同。要而言之,则前者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后者则由一对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13]126
“优美”是指诗人在进行审美观照时,以一种超功利的心灵,与外在的客观事物达成的一种默契、和谐的状态。而“壮美”(与宏壮同义)则指外在的事物超越了个人的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导致个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从而反观外物,使自己的心灵达到与外在事物同样的高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与外物有着某种功利主义的色彩,是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下进行的。王国维把“无我之境”与“优美”等同,把“有我之境”与“壮美”等同,那么两者之间各有何相似之处呢?王国维指出,“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知”,而“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可见,在“无我之境”与“优美”中,诗人与外物之间自始至终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而在“有我之境”与“壮美”中,在开始的时候,外物超出人的智力范围,大不利于人,存在严重的利害冲突,两者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因此是“动”的,而一旦人的智力超脱意志的束缚,从而上升到与外物同样的高度,再一次重新回到了平衡状态,利害关系也就逐渐退缩、消失,又恢复到了以前的静寂之中。由“动”到“静”,正是指出了“壮美”的不断演变的轨迹。由此可见,王国维对于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深解个中三昧,不仅如此,他还把它应用到了我国的文学批评中,可谓是有功于后人者。
综上所述,“境界”就是诗人在对外界的客观景物的直观中,外物与情感达到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契合状态,是一种不夹杂功利主义的纯粹的审美过程,是一种透过外物的羁绊又不为其阻滞的一种纯净、自然的审美愉悦的过程,是一种摒弃人世间的樊笼而直探宇宙本源和人生真谛的精神追求。
四、结语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自1908年刊行以来,迄今已百年之久,其影响力不减当年。盖其语言之优美,文辞之精练,读之但觉清新雅致,而无繁芜枯燥之累;且融入西学新观念、新术语,不乏新颖独到之见;注重逻辑,有别于历代之诗话、词话;可谓秉承我国诗学之传统,又兼顾西方之新学,遂开一代之新风,形成独特意义的美学范畴。后人对于“境界”说的评论,可谓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褒者称其融贯中西,开创我国文学批评之新领域;贬者指其偏于印象,逻辑不严密。这些批评意见,大都执其一端,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倘若联系当时社会之背景,王氏以开阔之眼界,敏锐之头脑,进取之精神,标榜西学,开中西文化比较之先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壮举。而其《人间词话》就是中西文化相互结合的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1]赵万里.民国王静安先生国维年谱[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2]王国维.王国维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吴奔星.文学风格流派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5]祖保泉.关于王国维三题[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1).
[6]姚柯夫.《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G].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7]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8]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9]王夫之.薑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杨牧.王国维及其《红楼梦评论》[J].文学评论,1976(3).
[1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郭熙.林泉高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13]方麟.王国维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于湘]
2016-06-01
高崎(1977— ),男,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I206.5
A
1008-6390(2016)05-0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