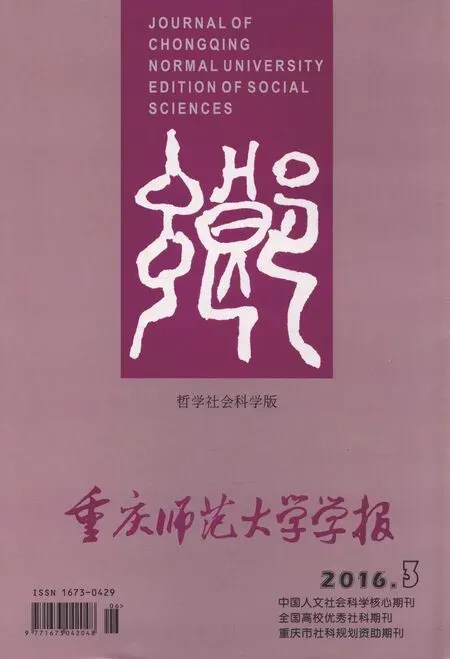陪都重庆与现代青年的战时培养
郝 明 工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陪都重庆与现代青年的战时培养
郝明工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47)
摘要:抗战时期,随着中国大学从东部迁往西部,陪都重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心,加快了现代青年的培养与中国大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陪都重庆;现代青年;战时培养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面临着形形色色的政治暴力,乃至战争阴云的不断威胁,成为文化转型政治化的负面构成。在这里,尽管可以对任何战争进行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是,通常能够形成人类社会共识的,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主要是针对侵略战争而言的。因此,无论是中国抗日战争,还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因为同属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也就必定是正义的,凡是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必定是非正义的,胜利最终属于正义的反侵略的中国与世界各国这一方。
尽管战争给遭受侵略的中国及世界各国带来民族劫难,但是,国家与民族在承受战争种种危机的同时,也迎来种种生机——固有的本土文化秩序在战争进程之中一边被破坏,一边又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秩序的战时重建,文化发展的战时轨迹就是以现代青年的培养促成现代国家的建立。抗战时期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高等教育体系正是在重建之中成为现代青年的战时摇篮,所谓抗战时期大后方以大学为主体的文化四坝——沙坪坝、夏坝、白沙坝、华西坝——前三坝都先后归属于重庆的行政区划。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全国包括国立、省立、私立在内的专科以上的高等学校108所,“大都集中在都市及沿海省份,例如上海就有25校,北平14校,河北省8校,广东省7校”。自从1937年7月7 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到1938年8月,短短的一年间,“在108校中,有25校事实上不得不因战争而暂行停顿,继续维持者尚有83校”,“其中37校被迫迁移于后方”。与此同时,抗战全面爆发前高校教师、职工、学生三者的人数分别为7560人、4290人,41900余人;抗战全面爆发后,教职工的总人数在一年间,起码减少了五分之一,学生则更是缩减了一半以上;而“我国高等教育机关之损失,就其可知者,已达3360余万元之巨”,“关于中国各方面所搜集之材料”,“均为极足珍贵之物,今后亦无重行收集之可能,故不能徒以金钱数字为之表现”。总而言之,高等学校“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之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1]中国246、247近代229、226,这就无可辩驳地证实,在这一中华文化浩劫之中,损失最大者在事实上就是作为现代青年主体之一的大学生群体的迅速流失,从而直接威胁到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死存亡,更是动摇着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根基。
这是因为,无论是校园,还是教室,都可以在短短时间内恢复,而大学生从在校到毕业的人数恢复则需要长达数年的培养周期,更不用说,在战火纷飞之中失去学习机会,甚至失去生命的众多莘莘学子。 所以,为了保护建设现代国家的青年栋梁,更为了保存中华文化的青春血脉,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不得不开始由东向西的迁徙。这首先是中华民族为了持久抗战而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在抗战时局的急剧变动之中,尽可能地保护战火摧残之中的各类高等学校,为其发展保留一线生机;其次是中华民族为了抗战到底而进行的政略大调整,在战时体制的不断改进之中,尽可能地重建硕果仅存的各类高等学校,为其发展提供现实契机;最后是中华民族为了文化复兴而进行的现代大转型,在抗战建国的意识引导之中,尽可能地布局举国一体的各类高等学校,为其发展促成良机。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只有通过各类高等学校不断地进行由东向西的战时转移,才有可能促使中国大学在战争阴霾的重重危机之中,开辟出一条走向抗战胜利的生机盎然的发展之路来。
中国大学在抗战时期是如何走出这样的生路来的呢?这取决与战争态势的风云变幻。最先遭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地区,被迫率先向大后方的中国西部撤离。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最近的平津地区,诸多高校随即遭到了日军的暴力摧残 ——在北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的校园纷纷被日军抢占为兵营、伤兵医院,北京大学的红楼甚至成为日本宪兵队的驻地,而其地下室则成为关押抗日人士的地牢,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教具被日军破坏与焚毁;[1]在天津,南开大学更是遭到了日军的大肆蹂躏。据中央通讯社报道,从1937年7月29日至30日,“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与此同时,7月29日, “日炮队亦自海光寺向南大射击,其中四弹,落该院图书馆后刻已起火”,7月30日,“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最终导致整个校园成为一片废墟。[2]
正是在日本侵略者残暴扩张战争阴影的紧逼之中,平津两地的诸多高校在有关当局的安排下陆续开始撤离。在这一撤离过程之中,平津两地的高校分为两个方向随着战局的进展而逐渐转移:一个转移方向是长沙,然后转向昆明;另一个转移方向是西安,然后转向汉中。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即在南京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常务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委员。随后,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商借100万元作为开办费,先借得25万元。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长沙举行第一次会议;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全校共有教师148人,学生1459人。[3]2901937年底,随着上海、南京的相继沦陷,长沙临时大学奉命迁往昆明。1938年5月4日,长沙临时大学在昆明正式开学 ,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为常务委员。9月10日,在西安举行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1月15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课,全校共有教师159人,学生1553人。[4]由于日机连续轰炸西安,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迁往陕西城固,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令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5]5
在这里,可以看到的就是,从临时大学到国立联合大学,由东向西的高校转移,不再仅仅是应对战局激变的临时措施,而更应该是政府主导之下的高等教育与文化建设的西部扩张,承载着培养一代现代青年的中国使命。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同样是由东向西的高校转移,出现了区域差异——与平津地区将私立高等学校纳入国立高等学校体系进行战略大转移不同的是,在上海地区的私立高等学校则是以政府倡导的方式展开。
二
1938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在上海发动沪淞战役,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同大学、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组建临时联合大学西迁。可是因为经费原因,只有复旦大学与大夏大学分别组成临时联合大学第一部与第二部,联大第一部以复旦大学为主体,迁往江西庐山;联大第二部以大夏大学为主体,迁往贵州贵阳。1937年12月初,联大第一部师生500余人再度随校西迁,拟与联大第二部在贵阳合校,但是,最终乘轮船至宜昌候船半月后,分为三批陆续出发,于12月底到达重庆聚齐,遂以复旦大学名义在重庆复校。
复旦大学在重庆复校时,办学经费十分困难,不仅学生因战乱无法及时缴纳学费,而且政府补贴的每月1.5万元也只能到账70%。尽管如此,仍然能克服经费困难,在恢复了原有的4个学院16个学系之外,还适应战时需要,先后增设了史地、数理、统计、园艺、农艺等专业。[6]258-259显而易见的是,复旦大学之所以最终选择重庆作为复校之地,主要是因为无论是从办学资源来看,还是从办学环境来看,至少这两方面都是适应了私立大学的基本需求的。这也是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在西迁过程中,对于办学之地的最终选择权存在着明显不同的一个客观原因。
相对于平津地区和上海地区的高校西迁,中央大学在西迁重庆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明显特征,其正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幽默之语:“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7]事实上,这幽默之语内蕴的意思就是——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的暴虐战火摧残到鸡犬不留的地步,成为当时中国东部大学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鲜明缩影;而中央大学在西迁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却能够减少到最小,连鸡犬等实验动物也全部运抵重庆,成为中国东部高校西迁最为成功的一个典范。这是为什么呢:从客观原因来看,不仅在国民政府的主持下,能够随同国民政府及相关行政、教育、科研等机构一起西迁重庆,得到统筹安排;而且还获得西迁途中从安全到交通的种种保障,尤其是能够利用西部后方支援东部前线的大量返程交通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从主观原因来看,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早在1937年春,就预见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一方面要求将用于学校扩建的木料制成550个大木箱,在木箱外钉上铁皮使其更为牢固,以备长途搬运物资之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罗家伦随即向总裁蒋中正建议,将东南沿海的几所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西迁重庆,蒋中正接受了这一建议,要求教育部指令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立即迁往重庆。8月13日沪淞战役爆发以后,正值暑假师生离校 ,罗家伦立即发出函电,催促师生立即返校,准备西迁重庆。与此同时,所有的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也开始装进早已做好的大木箱,时刻等待起运。
8月下旬,罗家伦在教授会上正式提出迁校重庆的方案,强调迁往重庆的理由有三:首先,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其次,迁校的新校址应以水路运输能够直达为宜;最后,重庆地处军事要地,再加上地形复杂,有利于防空。因此,迁校重庆的方案得到教授会的一致通过,会后罗家伦再向蒋中正提出迁校重庆的请求,再次得到了允准。与此同时,四川省刘湘主席率大批川军请缨抗敌,其中一路主力乘坐民生公司提供的轮船,由重庆经武汉赶赴沪淞战场,罗家伦请求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将返回重庆的运兵轮船,提供给中央大学装运早已装箱的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卢作孚不仅同意无偿提供轮船,而且派员工打通舱房,以便装运大件设备。到10月中旬,中央大学师生及图书仪器已经陆续抵达重庆,而位于嘉陵江畔的沙坪坝松林坡新校舍也同时建成。12月1日,中央大学正式开课,在校学生共1072人。[8]
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时本来打算放弃的农学院牧场的大批良种牲畜,历经辗转一年以后,在1938年11月抵达重庆。罗家伦是这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的——“在第二年的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很像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只见赶牛的人“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拥抱”。[9]于是乎,便成就了“鸡犬不留”却一个都不能少的幽默意味。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推进东部、中部各个高等学校的西迁。随着中央大学迁入沙坪坝,复旦大学迁入夏坝,大批外地高等学校纷纷迁往重庆的沙坪坝、夏坝、白沙坝——在整个抗战八年期间,先后迁来重庆的外地高校,总数就达到39所,不仅大大地改变了中国西部的高等教育面貌,更是扭转了重庆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现状,从战前仅存的省立重庆大学、省立四川教育学院、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这3所高校,进入迅速扩张的战时发展。随着1940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坝成立,整个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新建的高校多达12所。[10]101-113这也就是说,抗战时期的重庆高等学校,在8年之内,从抗战爆发前的3所。剧增到抗战胜利时的54所。这不仅为战后重庆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为战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合理布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这一点,正如蒋中正在抗战胜利以后举行的教育复员会议上所说:“今后国家建设,西北和西南极为重要,在这广大地区,教育文化必须发展提高。至少须有三四个极充实的大学,且必需尽量充实。除确有历史关系应迁回者外,我们必须注意西部的文化建设。战时已建设之文化基础,不能因战胜复员一概带走,而使此重要地区复归于荒凉寂漠。”[11]103这一高等教育战时发展,无疑是有助于现代中国的战时建设,同时也有利于现代青年的战时培养。面对这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战时转轨,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也就必然会凸显出来:战时中国大学应该怎样办?
有人就主张:“在抗战期间,大学教育应以修业两年为一阶段,使各大学学生轮流上课,及轮流在前线或后方服务,满一年或两年后再返回院校完成毕业。各大学教授亦应分别规定留校任教及调在政府服务两部分。”[12]这就是要求进行大学教育必须直接服务于抗战的战时转轨,从而促成论战。于是,有人就针锋相对地指出:“一个大学生去当兵,其效果尚不及一个兵;反之,在科学上求出路,其效果有胜于十万兵的时候”,再加上“无作战经验,冒失的跑上前线,岂但送死而已,还妨碍整个军事”, 其结论就是——“若学生都参战,教育本身动摇”。[13]学界人士之间发生的这场论战,实际上是由政界人士引发并平息的,因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进行战时体制的政略大调整的一个缩影。
这一论战的发生,其实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引起的。1938年3月上任伊始,就发表《告全国学生书》,称“今诸生所应力行之义务实为修学,此为诸生所宜身体力行之第一义”,“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14]刚好一年以后,促成这一论战趋向平息的则是——1939年3月3 日,蒋中正在重庆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表的训词,他一再强调:“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规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思,认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来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又说,‘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如不是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淘汰灭亡’。我们若是明瞭了这一个意义,就不会有所谓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的论争。因为我们过去不能把平时当作战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生的。”[11]
这就表明,从20世纪初进入中国文化的现代大转型以来,一直面临着侵略战争的威胁,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才将这一威胁具体而直接地展现出来。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平时和战时并没有区分的必要,两者始终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只不过,是从没有硝烟转向硝烟弥漫的战争状态而已,诚所谓“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更为重要是,无论是现代国家的建立,还是现代青年的培养,都需要随时保持一种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战斗姿态,才有可能走向现代生活中的个人自觉。当然,战时教育既然是平时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延续,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教育体制调整以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
三
早在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一方面要求“对现行学制大体应该维持现状”,因此,不仅教学课程不能变,而且教学秩序也不能变,以保障教学效率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更是提出“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急需”,“对于吾国文化固有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15]最终促进学术水准的不断提高。这就表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战时调整导向,就是在学制稳固的基础之上,不断充实学术含金量,。
因此,有必要加强扶持大学研究院所与研究生培养的力度。1939年,教育部从“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这一基本点出发,“对国立各大学原设有研究院所者,除令充实外,近并令人才设备较优各校,增设研究所,由部酌给各校补助费用,统令于本年度开始招收新生。为奖励研究所学生起见,每学部并由部给予研究生生活费五名,每名每年四百元。各学部之其他研究生,并令各校自行筹给津贴”。于是乎,当年在中央大学等8个国立大学所招收的研究生之中,就有160人得到由教育部给予的“研究生生活费”。[16]这就证实了中国高等教育在抗战时期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从而提升办学层次与研究水准。
国立中央大学迁入重庆沙坪坝之后,不仅办学实力继续提高,而且办学规模更是不断扩大。到抗战胜利之时,不仅保持了7个学院44个学系的固有院系设置,连续8年均招收新生,从1941年起,每年招收新生1000余人,在校学生最多时高达4000以上;而教师队伍更是颇为庞大——总计教授364人,副教授63人,讲师85人,助教204人,生师比达到7比1。[17]由此可见,真正是做到了以一流的师资来培养一流的学生。与此同时,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在抗战时期能够持续发展,将部分省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1941年1月,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此后全校由过去的4个学院16个学系增加到5个学院18个学系,以及银行、统计、茶叶、垦殖等4个专修科,扩大了办学规模及办学实力。[6]2601942年2月,省立重庆大学改为国立重庆大学,此后全校由过去3个学院12个学系增加到6个学院20个学系,同样也扩大了办学规模及办学实力。[18]上述大学的战时发展,无疑从一个侧面上显现出抗战时期的众多重庆高等学校,已经向着大学培养现代青年的战时摇篮发展。
更为重要的,抗战时期的重庆高等教育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中是否真正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呢?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全国高等学校分为17个学业竞试区——重庆区、成都区、乐山区、昆明区、贵阳区、桂林区、辰溪区、长汀区、坪石区、城固区、龙泉区、泰和区、镇平区、兰州区、蓝田区、武功区、恩施区。[10]100在这里,所谓的“全国”是指与沦陷区相对的抗战区,包括大后方的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以及前线的各个战区,而重庆被列为首位,并非是偶然的,不仅是因为大后方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而且更是因为高等学校云集抗战时期的重庆。根据相关统计,到抗战胜利之时,包括国立、省市立、私立这三类高等学校在内,“全国”高等学校共计141所,[11]1406较之战前的108所,增加了30.5%;而重庆区则高达54所,较之战前的3所,增长了18倍。因此,抗战时期的重庆不仅成为大后方的高等教育中心,而且成为整个抗战区的高等教育核心,昭示着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代方向,从而为现代青年的战时培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大学摇篮。
[参考文献]
[1] 顾毓绣.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J].时事月报,19卷5期,1938年10月.
[2] 《申报》1937—07—31.
[3]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西安临时大学概况[J].教育杂志,第28卷第3号,1938年3月10日.
[5] 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M].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6] 邓登云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 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学校.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8] 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J].教育杂志,第31卷第7号,1941年7月10日.
[9] 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M]//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 北京:国史馆,1989.
[10] 李定开.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11]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2] 李蒸.抗战期间大学教育之方式[J].教育杂志,第28卷第9号,1938年9月10日.
[13] 吴景宏.战时高等教育问题论战总检讨[J].教育杂志,第30卷第1号,1940年1月10日.
[14] 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J].教育通讯,创刊号,1938年3月28日.
[15] 教育通讯[J]第4期,1938年4月16日.
[16] 国立各大学扩充研究院所[J].教育杂志,第29卷第12号,1939年12月10日.
[17] 郑体思,陆云荪.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 贵阳:贵州文史书店,1994.
[18] 伍子云.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大学[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 贵阳:贵州文史书店,1994.
[责任编辑:朱丕智]
Provisional Chongqing and Fostering Modern Youth in Wartime
Hao Minggong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After Chinese universities moving to western from eastern, Provisional Chongqing had become the center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fostering of modern youth and the developing of Chinese university had been accelerated.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lso had been promoted.
Keywords:provisional Chongqing; modern youth; fostering in wartime
收稿日期:2016-03-22
作者简介:郝明工(1950—),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6)03—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