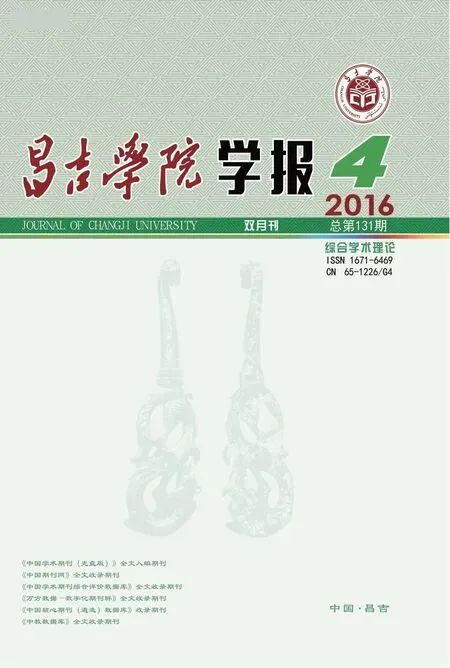《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中的喀什噶尔形象及其书写策略
迪丽热巴·阿吉艾克拜尔
(新疆大学中文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中的喀什噶尔形象及其书写策略
迪丽热巴·阿吉艾克拜尔
(新疆大学中文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神秘诱人的喀什噶尔,在外国人眼里是难以理解又难以抵达的异域城邦,凯瑟琳以“他者”目光,用奇幻的文字为我们再现了西方人眼中的喀什噶尔形象,为我们了解喀什噶尔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别样视角。本文借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分析相关理论,以马噶特尼夫人凯瑟琳的《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为文本细读对象,重点探讨外国人对于喀什噶尔的文化想象及其书写策略,尝试通过这座边陲小镇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再现,展示喀什噶尔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凯瑟琳·马噶特尼;喀什噶尔;形象学;维吾尔族妇女;跨文化书写
在亚洲之腹,在中国最边远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偏僻、富有民族风情的城市——喀什(喀什噶尔)。长久以来,在很多外国人乃至内地人眼里,新疆的喀什噶尔神秘奇幻,是探险者和旅行家无限向往的“异域之邦”。喀什噶尔地理位置独特,是丝绸古道上的重镇,北有天山山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则是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西域探险、考古史上,喀什噶尔闻名遐迩,各类珍稀史料文献都详细记载了该地区的风土人情,成为当下重建丝绸之路、沟通中西文化的一扇窗口。众所周知,西方殖民者早在19世纪就开始觊觎喀什噶尔,凭借“探险”、“旅行”等种种幌子,频繁穿行在南疆各地,为殖民者的扩张野心充当文化“前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国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德国人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帝国的探险家们在他们有关西域探险、旅行的记述里,都曾回忆起他们在秦尼巴克(china park)①受到的热情款待,以及与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外交官马噶特尼的交往[1]。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噶特尼夫人凯瑟琳的《外交官夫人回忆录》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我们尝试重返历史“现场”,管窥当时喀什噶尔日常风貌,探析欧美人对于这一独特地域的文化想象,提供了颇为理想的文本。本文借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分析相关理论,以《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为文本细读对象,重点探讨外国人对于喀什噶尔的文化想象及其书写策略。
一、夹缝中寻求的艰难认同
《外交官夫人回忆录》所叙述的见闻经历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英俄在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角逐”[2]。喀什噶尔是不列颠帝国最前沿的一个阵地,不列颠帝国为了在亚洲取得政治、经济上的主导权,与俄国进行了一场殊死竞争,正是这场“大角逐”使得英国政府在喀什噶尔建立了总领事馆。喀什噶尔地处偏远,封闭孤立,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说并不引人注目,但在那个或可称之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冷战”[3]的特殊历史情境下,喀什噶尔的地缘政治位置极其重要,是西方帝国列强搜集情报、争夺地盘的核心场域。
乔治·马噶特尼(George Macartney),一个温文尔雅、清新俊逸的混血青年,漂洋过海来到喀什噶尔,24岁的他,或许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命中注定,竟在这个“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度过了28年,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1912年,马噶特尼成为总领事,公开任务是照管在喀什噶尔和新疆其他地方的英籍印度属民,这些人均为当地的商人或放债者,非公开的任务则是监视俄国人在喀什噶尔的相关活动。马噶特尼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父亲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苏格兰人;母亲是中国人,出身于名门望族,这样的背景让他精通汉语(汉语名字“马继业”),深谙汉族人民的生活礼节,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这些优势也帮助他能够和喀什噶尔的道台及其他高官显贵建立起友好关系。有意味的是,马噶特尼非常讳言自己的家世,尤其对母亲避而不谈。米斯(Jean⁃nette Mirsky)②曾这样写道:“他出生于一种最可悲的婚姻,即一位苏格兰父亲和一位中国上流社会的女子,因太平天国的动乱而生活在一起,这种家庭背景导致马噶特尼早年经历十分独特。直到10岁,他都生活在南京的一个中国式家庭里,后来因他父亲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被中国任命为驻英国公使馆的秘书兼翻译,才跟随父亲来到伦敦。都市生活流光溢彩,繁华而浮躁,马噶特尼的母亲逐渐被遗忘,在他12岁那年死去。马格里童年好友詹姆斯博兰(James Bol⁃am)的家,成了马噶特尼在英国度过寂寞假期的‘家庭'”[4]。鲍尔杰在书中写到,“涉及到其家庭关系,马噶特尼的父亲马格里总是颇有保留,即便是对他最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不过我想,他的妻子(他们的婚姻完全依照中国礼俗举行)是一位太平军首脑或官员的女儿,他们是在苏州被占领时相遇。围城期间,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因马格里的救助她才幸免于难。”此后,他还提到:“毫无疑问,这位夫人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社会等级,马格里跟她的结合提升了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5]而这位母亲没有在任何官方记录中留下名字,仿若一颗暗淡的流星,转瞬间就消失在茫茫夜空中。
如果是今天,这种跨国跨民族的通婚已经稀松平常,甚至是很多家庭皆大欢喜的事情。但在当时,中西之间的交往甚少,中西文化之间存在许多明显的隔阂和偏见。出身于上流阶级的英国人很容易把“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优越感,转化为种族优越感,坚信英国人有统治有色人种的神圣权力”[6]。对满清来说,虽然经常败于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但天朝上国内心深处的那种文化优越感却是根深蒂固的。可想而知,马继业终其一生讳言母亲,讳言童年,也从不跟他的子女谈及他们的奶奶,甚至接受了“十诫”之外的第11条戒律:“你不得娶外族女子为妻。”[7]这种独特的童年经历或可作为一种间接证据,表明马继业在南京度过的童年给他留下了心理创伤,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对于跨国、跨族际文化的思考认知。
乔治·马噶特尼成为总领事,是英国势力在新疆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以罕见的忠诚和才华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多年来,他独揽狂澜,成功抵消了俄国对喀什噶尔这个战略要地的政治影响,他不仅受到中国人及其治理下的穆斯林们的爱戴,而且也得到了彼时英俄大角逐中敌对方沙俄的尊重。尽管马噶特尼有着中国血统,但他始终是站在英帝国的立场上窥视着喀什噶尔,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诠释着喀什噶尔28年来的巨变。这种“他者观照”揭示出了马噶特尼与异域空间建构起的诸多关联,相对于即喀什噶尔,他既是开创者、文化传播者、守护者,也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二、他者视域下的“喀什噶尔”形象
马噶特尼与凯瑟琳·波尔兰德从小青梅竹马,1898年他从喀什噶尔回到英国,与凯瑟琳结了婚,这位在英国土生土长的、远嫁异域的“小家碧玉”竟成了英国领事馆17年间生活的见证人,她用细腻、温馨的笔调,书写了别样视角下的喀什噶尔——《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在这本书中,凯瑟琳用雄健有力的笔调描写了旅途的艰辛,她将这称之为“一次了不起的探险旅程”[8]。这样一个腼腆,传统的英国女孩,要经历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过欧洲、俄国,渡过里海、骑马翻越天山山脉,最终到达喀什噶尔。
她把这些艰难险阻看作是对她性情意志的考验,并在书中写到:“如果一对夫妇在这样一段旅途中能经受住考验,而且不争吵,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相敬如初,患难与共。”[9]这次旅程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说是漫长人生历程中的一次冒险,是凯瑟琳平静如水、毫无涟漪生活中的调味剂。前往喀什噶尔的路是艰辛的,但路途中的感动是温暖的,一路上他们受到了很多人的热情款待和倾力相助。迎接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终于,他们到达了“秦尼巴克”。经过跋涉千山万水的艰难旅程后,她开始参观这个异域之“家”的每一个角落,从卧室窗外望去的白雪皑皑的群山,到房子下面马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再到路边长满了的瓜秧、苜蓿、水稻的农田,还有供水的克孜尔河。秦尼巴克中最令她心旷神怡的就是花园了,她写到:“我们的花园很大,很漂亮,这里各种水果争奇斗艳,后来,我丈夫又在本地的果树上嫁接了英国的苹果、梨、梅子、青李、樱桃等。看着这一切,我想世界上很难再有其他地方像喀什噶尔一样,适合任何水果生长。”这些看似陌生而又充满新鲜色彩的景象,渐渐在占据凯瑟琳的心。渐渐地,她把那个她丈夫和亨德里克斯神父蜗居的极其简陋的住处改造成了一个温馨的家。
凯瑟琳用一个独特的视角书写了自己初到喀什噶尔的印象,这也是跨文化视域下再现他者文化的典范例证。诺莎代尔(Nohsha Dye)说:“我们赋予事物以我们身上发生的变化。这个国家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时对我产生的不同印象使我总结出我们的关系依靠我们胜过依靠事物,正如我们描写多少画面是这里或那里的事实,必须懂得一位游记作者怎样受到感动。”[10]或许作为一个外乡人,他在一个国度的所见所闻,永远不可能是当地人希望他看到、听到的那样。凯瑟琳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充满奇异色彩的城市,她的双目所及,更多的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美好而又有缺陷的喀什噶尔。
在本书第八章,凯瑟琳深情回忆起她在喀什噶尔度过第一个春天的情形。她写到:“在喀什噶尔度过的第一个春天,对我来说可真是个意外。远处的果园里,传来一阵阵低沉嗡嗡声,我来到果园想探个究竟,不料惊奇地看到那里已变成了一座仙境,鲜花怒放,花团锦簇,那低沉的嗡嗡声就是数不清的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采蜜时发出的。”此后,“每年春天,我们都聆听第一场青蛙音乐会,从来没有错过它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因为青蛙音乐会告诉我们,那单调乏味的漫长冬天终于过去了。”[11]这是一个外国人眼中喀什噶尔的春天,优美的景象,沁人心脾。在游记作品中,作者往往都会扮演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想象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象的投射物,凯瑟琳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她引导着读者走出国门,在阅读空间中去游历异域。
在景物描写之外,作者更关注于人物且更留心她的邻人和过客。在秦尼巴克附近有个汉族人的公墓——“义园”,由一个面容枯槁的老人管理,有位当地的老妪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天,汉族老人死了,而那形销骨立的老妪枯坐在他们房门前面,不吃不喝,不哭不闹,一动不动地坐着。又过了两天,凯瑟琳已经忘记了这个老年失伴的妇女,但她的孩子们玩耍回来后告诉她,那个老妪还是以原来的姿势坐在城外的垃圾堆上,已经冻僵了,但好像还活着。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而且下着雪,没人能在室外过四个小时还活得下来。凯瑟琳和丈夫提着马灯找到了那个老妪。她已经完全冻僵了,仅靠身下那些马、驴、骆驼的粪便提供的一点点微热才没被冻死。凯瑟琳后来才知道,老妪因点火烧着了那个看墓老人的棺材,受到了老人同乡的惩罚,被赶了出来。在领事馆的拘禁室里老妪活了过来,浑身烧的一塌糊涂。这个女人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而这个过程对凯瑟琳而言只是圣诞的一个善举。这一个细节的描写,就像回到了世纪初的古城,亲身感受到了一些人在封建伦理和宗教观念的重负下喘息的苦难和毫无指望的日子。这个小故事,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凯瑟琳亲身经历的氛围。
她对异国情调深情且细致地描写,为读者绘制了一个富有异域情调的他者形象。凯瑟琳在制作“异国形象”时,并不是复制了真实的喀什噶尔,她筛选了这个异域之邦若干鲜明的特征,结合个体的记忆与想象,最终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但我们都知道,从世纪初开始就有一种反面地嘲弄中国人形象,有的作品甚至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中国人的蔑视之情,至少也是嘲笑的态度。而19世纪在欧洲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多体现在外形特征的描写上,凯瑟琳也不例外,她在回忆喀什噶尔的最初岁月时写到:“杨协台的女儿是位只有15岁的小姑娘,看上去病的很厉害,我丈夫问杨大人,他的姑娘得了什么病,他回答说,由于她的脚缠得太晚,脚上的骨头都已长结实了,所以就有了病。有位英国医生给这位大人讲,如果不给这位小姐松开缠脚的那些东西,不让她到户外活动活动,姑娘就会染上肺结核。缠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缠脚,就没有人愿意娶他的女儿做妻子,因为脚太大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等于给姑娘判了死刑。”[12]这样的行为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强迫妇女缠脚不仅违背自然,而且是十分丑恶、残忍,使脚变成了“真正的蹄子”、“畸形的残肢”。[13]在许多游记和有关中国的小说中,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似乎总是存在冲突。随着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中国越来越成为唾手可得的猎物。大部分描写中国的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前蒙受屈辱的形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化”书写,将东方建构为一个神秘蛮荒的他者,不惜笔触大肆渲染某些落后的习俗。
此外,凯瑟琳也对这座位居丝绸古道上的东方小城展开美化和想象,它不再是脏兮兮的赤裸裸形象,而是温文尔雅的,具有气宇轩昂的正气之风。她用西方人的视角书写东方人的生活,将这一形象情感化,展现了独特的风韵。她还写到了第一次在喀什噶尔回城步行穿过街区时令她难忘的经历:“当我们走近离秦尼巴克最近的一座城门时,路中间有一大滩水,我正准备跳过去,突然,一个面容枯搞的汉族老汉走了过来。他背上背着一个筐,他弯下腰,把筐子扣在水洼中,然后殷勤地把手伸给我,扶着我踩在筐子越过水洼,走到了干地面上。他考虑的如此周到,而且这一切都做得极有风度,真使我感动不已,更使我感动的是,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他做这件事不要感谢,也不要报酬。”老人简单的一个举动,却体现出了他的无畏与高尚。不无症候性的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从一个麻木、冷漠、自私并且毫无慈悲的恶人,逐渐转变为一个“文明”的象征,表现出了典型“圣母”形象的外化。
三、凯瑟琳笔下的维吾尔族妇女
落后且封闭的喀什噶尔,在凯瑟琳的笔下正面增值,她对异国的描述,更多隶属于一种“幻想”而非她看到的形象本身,并表现出了一种“狂热”的情感。凯瑟琳心中有一个关于东方的想象,一方面,喀什噶尔这个异域之邦在她的笔下光彩照人,每一个人物、景象都变得过于美好,令读者向往。另一方面,则对中国人形象,对周遭的环境过于丑化,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太脏,没有礼节。反应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像大多数的西方人一样,遥远的东方古国一直都是完美和神秘的。在这些来自欧美世界,来自帝国的游历者眼中,那种无形的“西方优于东方”的文化等级意识始终沉积在他们的意识深处。
凯瑟琳对喀什噶尔人的外貌描写也入木三分,她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颇似欧洲人的长相与身材,对喀什葛尔男人们的穿衣打扮更是做了详尽的素描。喀什噶尔男人的必需品是帽子和腰带,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个男人的象征,妇女的衣服内衣与长裤多数是五颜六色的,她们出门时,会穿上长及脚踝的大衣,有些妇女总会把头巾盖得严严实实,她们羞涩于丈夫外的男人看到她们容颜,认为这是对她们丈夫的不忠。作者回忆起刚到喀什噶尔,这里的封闭导致几乎见不到外国货,而在不久之后,这座城市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一队队商人从俄国和印度运来了日用品、家具及衣料。有钱人家开始修建具有欧洲风格的房子。不过无论喀什噶尔有多大的变化,令作者流连忘返的,还是那些最古老的记忆,因为它们具有东方式的美好。
凯瑟琳很快发现了维吾尔族人能歌善舞,“有时候,我到当地妇女家参加她们的节日招待活动,看看歌舞。在这种场合,这种招待活动总使我非常着迷。”[14]在充满异域的国度里,她感到新鲜不已,比如她这样描写喀什噶尔妇女出席歌舞活动时的装束,“喀什噶尔的女士们艳妆浓抹,她们的眉毛涂得漆黑,而且眉毛之间在鼻子上端用一条长长的黑线相连。她们的小手纤细,保养得很好,指甲涂成了深红色,一串一串的珠子和银链绕着脖子,在长长的辫子末端也缀有珠子和银链,她们一移步,这些珠子和银链碰撞着,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她们的黑发涂上发胶和亮油,闪闪发光。”[15]喀什噶尔妇女无时无刻影响着凯瑟琳。维吾尔族妇女的长相、习俗、装扮对于凯瑟琳来说是新鲜的,且与英国的女子有着鲜明对比。作者塑造出了具有异国情调差异的“幻想”,或以边缘性“差异”来对他者形象的承认。在本书第十章凯瑟琳写到:一家人准备去避暑,但在旅途中遇到了倾盆大雨,浑身湿透,寒意砭骨,他们不得不投宿在一个狭隘的牛毛小店里。这时一位维吾尔族妇女端来了热茶,“端上来的这杯茶,在其他地方我们绝不会喝,但现在却是那样令人高兴,因为端来茶的人真诚友好,笑容满面。”没有什么能比发自内心的善意与微笑更能温暖困境中人的心吧。
凯瑟琳从文明的都市来到一个近乎完全封闭的“蒸笼”,她将这个异国形象这些特殊的凝结物建构成了社会集体想象物,如此勾勒出来的集体想象物显然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维吾尔族女子成婚普遍都很早,满9周岁到14周岁为成婚最佳年龄,维吾尔族有个传说:“用皮帽子轻打女子,若她不摔倒,就可以嫁人了。”[16]传说形象地写出了女子已长大成人,是时候成婚了。成婚后的维吾尔族妇女对丈夫是忠贞无比的。结婚后对于梳的辫子也是有讲究的,婚前可以编好几个,成婚后则只能编两个辫子。凯瑟琳在赞美维吾尔族妇女美丽动人、光彩夺人的同时,也写出了她们身上有虱子,导致她从不敢用维吾尔族妇女做佣人等。就像在前文中提到的,一方面是她对喀什噶尔妇女的完美想象;另一方面是她终究无法完全过滤自我文化的优越感,对喀什噶尔形象进行丑化。
凯瑟琳将喀什噶尔人的生活描写的活色生香。他们总是对邪恶的眼睛十分惧怕,特别是涉及到儿童时更是如此。她写到:“有一天,我们想为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小孩拍张照,正要举起照相机拍照时,她的母亲突然冲过来,一把就把孩子抢走了,并且说,照相机的那只邪恶的“眼睛”如果看了她的孩子,孩子就会死掉。”他们认为只是注意这些漂亮的小孩子,也会使安拉把孩子带走。而这种做法与思想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她还描写到:“刚到喀什噶尔那一阵,因为长途跋涉,有很多衣物得找人洗。于是我丈夫就让手下的人专找一个妇女来洗这些东西。他出去立刻带来了一个妇女。我看到她的身子那么重,吃了一惊。她把所有要洗的东西拢在一起,捆成了一大捆,背着就回去了,这更使我感到不可思议。第二天,一个小男孩跑来对我讲,他妈妈感到很不好意思,衣服没洗完,因为当天夜里生了一个孩子,并说她第二天会把洗净的衣物送来。果然,第二天她带来了衣物和一个小婴儿!此后,每个星期她都会来后院为我们洗衣服。”凯瑟琳从这件小事写出了维吾尔族妇女的勤劳与朴实。这种异国文化在凯瑟琳的笔下正面增值,一个是洋溢着优雅风韵、充满安逸与享乐的文明都市;一个是饱受艰苦封建落后的“宅笼”。凯瑟琳描述的异国形象,故而是一种文化事实,也是文化的集体形象,一个社会正是通过集体想象物来反思与想象的。她意识到了家乡文化中缺乏的东西(勤劳与朴实),从自己的所见所感超值评价一种异国文化(维吾尔族妇女)。因为在她眼中,喀什噶尔妇女恰恰拥有这些价值。喀什噶尔一带有许多圣人墓,女人们在想要孩子或丈夫时,亦或是有了什么麻烦事儿和难处时,常会去墓前恸哭一场,向圣人祈祷万事皆顺。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圣人安娜·比比,她的维吾尔语名字是:“Buwi maryam”,传说她为女性作出过很多贡献,也做过接生娘。凯瑟琳在异国的舞台上扮演了自我经历的主人,言说着她所“穿越”的空间并将之转化为一个“景观”。
在《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中,凯瑟琳的书写透露出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当时的喀什噶尔也是处于男尊女卑的形势,一夫多妻制广为盛行,从凯瑟琳的笔迹中不难看出她对喀什噶尔妇女的同情与怜悯。这也让她的书多了几分颇为触动人心的地方。在理智的文字中是对喀什噶尔女性乃至所有人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感谢,也正是这种细小之处的感动更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虽然理想化,却也同样美丽动人的“秦尼巴克”。
四、帝国衰落下的“文化乡愁”
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不仅是英国进一步加强对新疆渗透的表现,而且也是英俄在新疆展开争夺的产物。领事馆的建立意味着英国有了与俄国在新疆进行扩张、维护英国利益的最重要的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据点。从领事馆建立到1948年领事馆撤销的几十年中,英国通过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积极推行对新疆的渗透扩张政策,干涉新疆内政,挑拨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统属关系,是20世纪前期新疆局势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19世纪世界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英帝国迫使南亚古国印度成为殖民地,并且开始对中国实施侵略。与此同时,另一个处于扩张时期的欧亚强国——俄罗斯帝国占据了中亚西突厥斯坦,并进一步南下。本土原本与中国相隔数万里的英国和俄国,都成了在衰退时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无时不在刺探由绿洲、大漠和群山组成的中国新疆的一举一动。1915年4月,马噶特尼收到了英属印度政府的通知,通知说珀西·赛克斯爵士已经动身来喀什噶尔替换他。凯瑟琳在书中结尾写到:“虽然可以回到英国了,又要见到故乡了,但此时此刻我心里沉甸甸的,真不是个滋味。”[17]自此之后,热爱生活的凯瑟琳和她的一家人再也没能回来。英国的势力再也没能在这一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一战的爆发拖累了不列颠的脚步,深陷欧战泥潭的世界霸主无暇顾及远东的局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英帝国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海外扩张。战争的巨大开销使得英国无法继续承担维系一个帝国所需要的庞大财政支出。英国有数百万人死亡,无数资产被毁,其结果是债台高筑、资本市场的混乱以及在海外殖民地英国籍官员人数的缺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在新老殖民地高涨,而帝国的参战以及非白人士兵在战争中所感受到的种族歧视,都更加助长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日不落帝国”再也不复当年之勇,回顾英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历程,不难看出,英国从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而这种文明一直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争相效仿。曾经在喀什噶尔一度盛行的英国文化,也终究像凯瑟琳笔下的“秦尼巴克”一样消逝在苍茫的历史尘烟中,成为人们心中美好的想象。1898年到1913年,凯瑟琳对这段时期的回忆,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喀什噶尔,“秦尼巴克”焕然一新。喀什噶尔的俄国人也多了几倍,凯瑟琳与俄国人的交往也频繁起来,这个原本封闭的城市有了新的生机。哈雷彗星的出现让凯瑟琳永生难忘,她写到:“那一年在英格兰,人们看到了哈雷彗星,但是,与在喀什噶尔看到的哈雷彗星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18]
喀什噶尔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维吾尔族文化也绵延了一千多年,原本狭窄的街道、坑洼的路面,草席做顶棚的巴扎、成群的乞丐、患病者的凄惨,矮小的毛草屋。而如今,道路宽敞了,路面铺面了,巴扎也迎来了一个个新的店铺,喀什噶尔也有了新的名字“喀什”,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爱好者,今天到喀什旅游的观光者,看到的是一个既有浓郁民族特色文化,又兼有现代文明的城市,这个城市在保持着传统本色的同时仍在与时俱进,散发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两者相互包容,相得益彰。正是因为喀什噶尔的神秘、异域才使得现在的喀什灿烂夺目。
喀什噶尔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它深奥难懂,又朴素无华;它冷峻刻板,又海纳百川。周涛先生在散文《喀什是梦》里这样写道:“你可以一眼望穿乌鲁木齐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双迷蒙的眼睛。”沉甸甸的历史像五谷陈酿,现代与过去的包容像百宝箱。在喀什噶尔,时间被冷冻了起来,岁月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再是只能催白鬓发、添置皱纹,而是为人们提供了尝试过中世纪的生活和追溯历史往事的机会。《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为我们呈现了古老而又纯土的民族风情,让我们领略了凯瑟琳的勇敢无畏,最后,在书中第十一章她以日记的形式写了返回英国度假的过程,读者有种亲临此地的感受。这种描写方式更能贴近生活,让读者深陷其中。
五、结语
人们来来去去,靠他们的语言与文字,或是浓缩,或是冲淡;或是盲人摸象,或是各取所需;或是抽象概括,或是演绎铺陈,把“喀什噶尔印象”介绍给每一个关心它的人,而留给自己心中的则是足以伴随终生的记忆。凯瑟琳·马噶特尼与喀什噶尔谈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恋爱”,字里行间渗透着她对喀什噶尔的深厚情结,让读者感受到了她亲身经历的氛围。凯瑟琳笔下的喀什噶尔,对于我们穿越历史的烟尘,重新认知喀什噶尔的过往岁月,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凯瑟琳的日记书写,呈现了一个“他者”眼中的东方城邦,其中看似矛盾的书写策略,从深层次上揭示了英帝国持续衰落的“文化乡愁”。从这一意义上说,凯瑟琳的《外交官夫人回忆录》堪称一个“跨文化书写”的典型案例。
注释:
①秦尼巴克即中国式花园,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
②斯坦因的传记作者。
[1][4][5][6][7]贺卫方.马继业的身世[J].万象,2012,(12):15-27.
[2][3][8][9][11][12][14][15][17][18]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回忆录[M].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1,2,2,3,119,43-44,122,122,212,207.
[10][1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阿不都热合满·艾白.维吾尔民间文学大典(第十卷)[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I106
A
1671-6469(2016)-04-0067-07
2016-01-31
迪丽热巴·阿吉艾克拜尔(1991-),女,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中文系硕士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