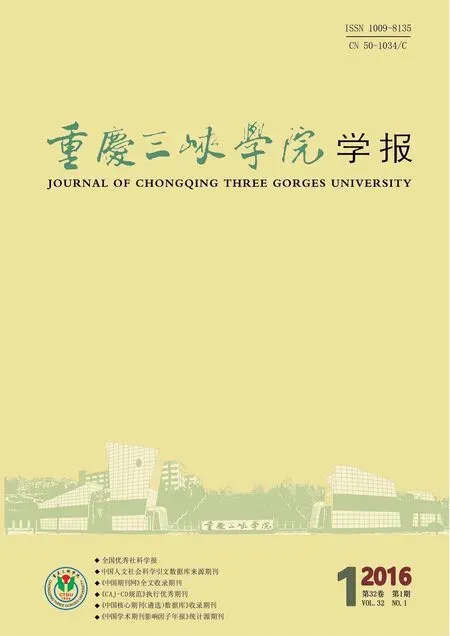近现代之交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黄念然
近现代之交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黄念然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与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逐渐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报纸、期刊杂志、文学社团是中国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三大关键要素。中国近现代传媒中所存在的特定的文化公共领域与批评空间带有明显的批判封建专制、启蒙民众的时代特点。新式传媒和新式社团的出现,为公众参与文化再生产和社会整合提供了公共舆论空间,也为文学批评空间的开创提供了契机,这种批评空间的开创突出表现在文学民主性的发扬、批评民主性的建设以及制度化文学批评生产场域与生产机制的逐步形成等方面,它不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将文学批评变成各种社会综合力量参与竞技的场所。
近现代之交;文学;公共领域;文学批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由于开启民智的社会需要,报刊、出版、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逐步走到了文化与思想传播的前台,它在冲击与解构旧有传播体制的同时,也日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交往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为公众批判和自由发表言论提供了一定的“公共舆论”空间。虽然近代中国有着不同于近代西方的特殊的社会背景,无法完全套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模子,而且,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中,市民社会的形态并不占主导地位,因而形成“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尚不完全具备,但是,上述传媒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而且使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思想从生产、流通、消费诸方面发生了质的变革,特别是文化生产者身份的普泛化,文化产品生产的机器复制性,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群体的大众化等等,改变了旧有的“君权神授”的一言堂,给文化大众的沟通与交流置入了“公共合理讨论”与“平等对话”的全新理念。在中国近现代传媒中所存在的特定的文化公共领域与批评空间带有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公共领域”的特点,这是一种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封建专制、启蒙民众的公共舆论空间,带有明显的中国特点。现代传媒使文化不再是封建士大夫特权阶层的专利品,变成了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它还成为酝酿社会变革、文学发展的策源地,加速了文学艺术的平民化过程和现代转型
一、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在现代传媒影响下,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有三大要素至关重要,一是报纸,二是期刊杂志,三是文学社团。
报纸对现代公共领域形成的巨大作用早为那些“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所注意。比如,王韬曾评述泰西日报说:“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1]171这表明,泰西报纸贴近底层群众、议论政治得失、客观公正的特点就已被王韬所注意。戊戌变法前后,办报已成为富国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的礼部尚书孙家鼐于1896年在《官书局开设缘由》中提到,泰西各国育人与富国之道,无非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随后孙家鼐在《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摺》中奏请“开除禁忌,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论”。光绪皇帝对之批示曰:“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应亟为倡办。”“各报体例,自应以指陈利害、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2]54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应“设报达聪”,他说:“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弊之方,莫良于是(指广开报馆)。”[3]150对于近代以来办报之盛,秦理斋在《中国报纸进化小史》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庚子以还,官厅压力稍弛,新创者渐众,旧有诸报,亦渐由国人购回自办……泊乎宣统,内地府县,并有地方报纸之刊……武汉首义,全国响应……一时民气发扬,政党各派,竞言办报……不仅通商大埠,报馆林立,即内地小邑,亦各有地方报纸一二种,统计全国新闻纸类,不下1 140余种。至于行销之广,告白之盛,实所罕观。”[4]24报纸之功用在于“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灼然无或壅蔽贯,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5]179报纸能“去塞求通”,有益国事,必须加以保护,故而,梁启超援引西人报纸为例说,“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报章,如蚁附膻。阅报章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6]66柳亚子甚至认为报纸这种“批判的武器”较之于“武器的批判”更为有力,他说:“波尔克谓报馆为第四种族。拿破仑曰:‘有一反对之报章,胜于十万毛瑟枪。’此皆言论家所援以自豪之语也。”[7]报纸还能成为女性革命的重要工具,秋瑾在其创办的《中国女报》发刊词中就曾赞扬报纸为“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8]80对于报馆的作用,梁启超曾一度以满怀激情的语言写下了这样的赞词:“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9]476值得注意的是张季鸾曾把报纸的兴盛与时代的过渡性特征联系起来思考,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概括道:“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后而大兴,至庚子后而极盛。”[10]30应当说,这种看法对于了解中国文艺的过渡性特征和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机理非常有帮助。
在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近现代转型过程中,白话报的出现、兴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白话报刊,或文白并用,或开辟白话专栏,有的甚至完全以浅近的俚语白话为表达工具,把发行对象定位于下层民众。比如,1876年3月30日增出的《民报》二日刊,其发刊词中称:“本报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每句人名地名,尽行标明,庶几稍识字者,便于解释。”林白水办《中国白话报》,其对象就是“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11]这些白话报纸在文体的通俗化、口语化变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在教育层面上弥补了正规学堂教育的不足,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后来,陈独秀曾说:“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12]19据学者陈万雄统计,“清末最后约十年时间,出现过约140份白话报和杂志。”[13]134白话报的盛行对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由于白话代替文言已成不可扭转之势,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也最终不得不颁布命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用白话。
借用报纸来表达文学观念或传播西方现代文学思想,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文化或文学常态。在这些报纸中,我们能看到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批判。比如,蒋观云在《中国之演剧界》一文中就批判了传统戏曲观念中的对“悲剧意识”的忽视,认为“国剧刷新,非今日剧界所当从事哉!”[14]50可以说,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改良和文学批评的进一步现代化而言,白话报纸的作用更是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等人通过《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新报》、《蒙学报》等改良运动舆论阵地,不仅清算了旧文学的语言魔障,否定了旧文学的价值,还以报纸为文学探索、文体改革的阵地,尝试用新文体创作“新派诗”,进行了中国文学变革的探索。比如,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1898年于日本横滨创办),就专门辟有诗栏,不断刊登既有新名词又有流俗语入诗的“新体诗”。《新民丛报》半月刊(共出一百期),除继续辟有“诗界潮音集”专栏,发表了五十多个作者的五百余首诗篇外,在第二号还特辟“棒喝集”专栏,发表了四首德日爱国歌曲的译词,直接向中国输入外国诗歌的营养。从第四号起,又辟有“饮冰室诗话”专栏,连续发表梁启超鼓吹诗界革命的主张。“饮冰室诗话”专栏的创办,对当时的“诗界革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它从理论上积极地推进了诗界革命,其“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创作主张也成为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既有公开的发表阵地,又有明确的创作纲领的诗歌革命形式,较之中国古代的种种文学革新运动,辐射范围更大,影响面更广,产生的作用也更大,它已不再是封建士大夫文人圈子里的文学“内部事务”,波及到广大下层民众,对于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与批评空间的拓展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另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就是期刊杂志的兴起。这些期刊杂志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与传播媒介对文化与学术研究的普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出现与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留学生。其中,又以留日学生创办期刊杂志最为热心。这可以从清末民初中国赴日留学生的逐年增加以及留日学生创办的许多杂志中窥见端倪。学者李喜所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赴日留学大致情形是:1896年13人;1898年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608人;1903年1 300人;1904年2 400人;1905年8 000人;1906年12 000人;1907年10 000人;1909年3 000人;1912年1 400人。这期间,留日学生创办了许多杂志,如《开智录》、《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新小说》、《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说》、《女子魂》、《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云南》、《音乐小杂志》、《法政杂志》等等[15]168-170。
文学性期刊或杂志的出现与兴盛行也与这种时代性的办刊潮流密切相关。阿英编辑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曾介绍了近代主要的文学期刊24种,在这24种文学期刊中,有号称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的《新小说》(1902年)、《绣像小说》(1903年)、《月月小说》(1906年)和《小说林》(1907年),也有《小说世界》(1907年)、《竞立社小说月报》(1907年)、《新小说丛》(1907年)、《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等不为现代人所熟悉的小说杂志。《申报》馆所办的主要刊物《瀛寰琐记》(1872年11月11日创办于上海,系综合性文艺月刊,为最早的文学期刊)、《四溟琐记》(1875年)和《寰宇琐记》(1876年)亦在《述略》的介绍之中。此外,还有韩子云私人创办的以刊登个人创作为目的的近代最早的小说刊物《海上奇书》(1892年)。实际上,阿英的《述略》也只是粗略的统计,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期刊杂志兴盛的情形。据祝均宙、黄培玮辑录的《中国近代文学报刊概览》,近代有文艺杂志133种。这些文学期刊杂志从种类上讲,最多的是小说。据徐念慈《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载,仅1907年,沪上15家书局、报馆出版的各类小说就达121种[16]265-275。
近代以来的中国期刊杂志与报纸一样,在对象上首先定位于普通读者。如中国近代最早问世的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编者就希望自己的报纸能够使“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17]。其次把开化民智、改良社会作为办刊的基本宗旨。如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刊登《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宣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18]5又如,《新小说》正式问世前曾在《新民丛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宣传性启事,其办刊条例第一条就说:“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19]31
近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小说、戏曲刊物的“缘起”或“发刊词”如《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小说林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等等,其实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多与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现代性转型问题相关的成份。大致看来,这些“缘起”、“宗旨”或“发刊词”大多显示出这样的基本内容:一、以小说、戏曲为改良社会的文化利器,忧患意识流于笔端,常常提出明确的改良主张或“主义”。二、在中西方比较视域中进行文学比较研究,显示了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单向参照的文学研究或批评视野。三、痛陈传统小说、戏曲之弊端,批判姿态明显。四、对新式文体持欢迎和鼓励态度。五、宣言常是意气相投的同仁取得的共识。六、促成公共论坛形成的意向十分明显。七、常常将办刊对象定位于普通读者或下层民众。
“五四”运动以来,文学期刊或杂志的创办更为兴盛。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1935年8月)导言中说,五四时期是青年团体和文艺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仅1922年到1925年3年时间,就有不下100种文学团体和刊物成立出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种杂志更是层出不穷。1933年到1934年甚至被称作“杂志年”。仅1933年的上海而言,就出版了至少二百种杂志。1934年,仅“文艺定期刊几乎平均每月有两种新的出世”。1934年“自正月起,定期刊物愈出愈多。专售定期刊物的书店中国杂志公司也应运而生”。据统计,当时“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十出版在上海。”[20]
在文学期刊或杂志之外,涉及到文学批评研究的还有学术性刊物,这一点常常为研究者们所忽视。实际上,这些学术性刊物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体而言,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刊物中对现代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专门性学术期刊和综合性学术期刊两大类。专门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时效性强、辐射面广,既为学者们提供了及时发表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也提供了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辩论的园地。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和学术传播方式,也适应了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些期刊、杂志往往开设学术界消息、书报介绍和新书评论专栏,或者转载、译载、摘述有价值的、重要的学术研究论著,及时反映当前学术研究动态(如《燕京学报》曾介绍过学术论著、引得、杂志总计有三百余种,第30期以后,更开设“书评”栏目,共发表书评80多篇)。《国粹学报》、《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专门性学术刊物不仅起到了学术讨论的公共论坛作用,还常常将一些重要的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通过这些刊物迅速、集中而详尽地反映出来,这是旧式学术研究的传播途径如师徒问答录等所不可比拟的。这些专门性学术期刊往往都与高等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曾被称作“四大学术刊物”的《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前三者均属高校学报。《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和《清华学报》等则都曾得到政府或学校的资助,不仅在学术界有着稳定而巨大的影响,扶植和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学术人才,还以其自成一体的学术风格和办刊风格,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构成了一种现代学术研究的承传关系。在专门性学术期刊之外,许多综合性期刊杂志如《东方杂志》、《学衡》等,以及一些报纸的副刊或学术专栏如《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副刊等,也不断发表各种学术论文,开设各种专栏(如《学衡》杂志就设有“述学”、“文苑”、“杂缀”、“书评”等栏目),介绍与学术研究相关的信息,与专门性学术期刊形成呼应之势。清末民初一些以整理国故为主的学术刊物如《国粹学报》、《国学季刊》等,都是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往往还有明确的编刊宗旨或原则,撰稿成员中既有国学大师,也有新派学人;学术成果上既有以考辨见长的专题研究,也有以义理阐发为主的宏观通论。例如,在《国粹学报》撰稿人员中,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黄侃等人既是知名的国学大师,也是公认的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大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于1923年1月编辑创刊的《国学季刊》,前后共出七卷二十七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陈受颐等人都是其中重要的成员。这些人都曾对古代文学批评十分关注。胡、钱二人反桐城派、反“文以载道”的基本立场自不待言,作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写过《中国文学史》,研究过孔子的文艺思想,颇让人刮目相看。陈受颐的《文学评论发端》(载《南风》1卷2期,1910年4月)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二十世纪最早的一篇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专文。《国学季刊》采取从左向右横排的版式和新式标点,在文字上不拘文言、白话(实际上以白话为主),并附以英文目录或所发文章的目录索引等,都是新式学术传播的做法。《国学季刊》在“编辑略例”中称其“主旨在于发表国内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结果”,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与以相当之地位[21]”,这种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以中外文化比较为其研究视域的办刊宗旨或方针,显然对拓展中国文学批评的眼界很有作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1927年6月创刊)还规定:“内容除本院教师之著作外,凡学生之研究成绩,经教授会同审查,认为有价值者,及课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载。”[22]324这种扶持学界新秀的做法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显然也有良好的作用。
一些以介绍与研究现代新思潮或西方文学批评新理论为主的刊物如《学衡》、《新潮》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生产基地。《学衡》杂志在办刊宗旨上特别提出“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可以说对国学研究有着极明确的主张和要求。从它所编辑的79期文章看,其中一个重要的专题就是融合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以及专门的“国学”中经、史、子、集的批评研究。陈寅恪、王国维、汤用彤、刘永济等人都是重要的撰稿成员。另一个重要刊物《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各问题为职司,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作为办刊宗旨[23]94。在它的一些重要成员中,顾颉刚和俞平伯都曾对传统《诗经》学提出过批判;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是学界共认的杰构;康白情对意境理论作过新的阐发;作为文学革命家的周作人曾结合“言志”与“缘情”两大古代文学主流探讨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郭绍虞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据笔者手录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资料目录索引》(未刊稿),解放前刊载文学批评学术论文的主要报纸有《晨报副刊》、《申报》、《晨报》、《中央日报》、《国闻周报》、《大公报》、《庸报》、《天津益世报》等。主要大学学术刊物有《清华学报》、《北京大学月刊》、《复旦学报》、《南开周刊》、《厦大周刊》、《燕大月刊》、《燕大旬刊》、《武大文哲季刊》、《燕京学报》、《中山文化季刊》、《国立四川大学季刊》、《中山大学半月刊》、《师大国学丛刊》、《安徽大学季刊》、《中山学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光华大学半月刊》、《国立中央大学月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河南大学校刊》等。其它的还有《新时代月刊》、《东方杂志》、《文史丛刊》、《艺文杂志》、《文学年报》、《国文月刊》、《国学月刊》、《文艺复兴》、《国学丛刊》、《文艺与生活》、《协大艺文》、《中国学报》、《睿湖期刊》、《国故》、《中国学报》、《真知学报》、《国学》、《青年界》、《华国月刊》、《国粹学报》、《西北论衡》、《中国文学》、《中外评论》、《文学杂志》、《学风》、《文学集刊》、《文化先锋》、《学衡》、《人间世》、《新苗》、《文学》、《学林》、《文学季刊》、《新潮》、《矛盾》等,这些刊物在发掘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内在体系与特征方面贡献良多,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实现现代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还出现了一些纯文学(或文学学术)刊物,如《小说月报》、《戏剧杂志》、《剧学月刊》、《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这些刊物在刊发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兼及文学批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榆生于1933年初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词学的学术刊物《词学季刊》。它自1934年4月起出版,至1936年9月30日3卷3号停刊,共出11期。《词学季刊》在其创刊号的《编辑凡例》中曾开宗明义地宣布了如下两条原则:一、此刊专门发表词学研究成果,不涉及其他;二、此刊登载之文学,无论文言白话,但取其对词学确有研究者。这种办刊原则不仅突出了该刊的专业性质,凸显了极强的文体意识,也体现出办刊者兼纳旧学与新知的勇气和宽广胸怀,对现代词学批评的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卢前、詹安泰等现代词学大家的词学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的形成,都与《词学季刊》有着密切的联系。
应当说,传统文学封闭形态的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的崩解,中西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的形成,新观念、新思潮、新风格的涌现等等,都同近现代以来期刊杂志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的两次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如果没有这些期刊杂志的巨大的影响,是很难实现的。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24]28可见,办学会,办社团,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达到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是当时社团出现的最重要的时代原因之一。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成立的重要学会有62个,发起者基本上都是新式士大夫[25]199-206。学者桑兵的研究表明,晚清和近代以来中国的各种社团组织的繁荣兴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仅就清季十年而言,商会已达900多个;到1909年,各地由于教育救国思想的兴起,共成立教育会723个,并且仍在加速发展;农学会1911年至少有19个总会,276处分会。[26]274
中国古代文人学士本有结社之风,但古代文人结社多以诗文唱和为主,结社的目的也常常是为了逃避政治(晚明以来,复社、东林党等社团始有一定政治倾向,则与民族主义倾向有密切关系),况且,由于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因而,结社往往有名而无实。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组织的社团,往往也带有古代文人社团的性质,大多不以正式的团体名义出现,通常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体。譬如,南社包天笑就说:“这个南社的组织,既无社址,也没有社长,每逢开会,不过聚几个文艺同志聚餐会谈而已。”[27]352从结社方式看,南社确实继承了中国文人结社的传统,传统的修楔、酬唱、花酒、雅集、诗词曲赋等形式仍然保留在南社中。1916年,刘翰怡在上海建立的淞社,也常常是“迭为主客”,“论文”而已。不过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救国图存的理念逐渐成为结社的核心宗旨。社团的性质不断改变,社团成员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如南社后来就有不少人步入政界。社团主办之刊物也成为社团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社团组织生活也开始常规化。比如1921年秋在上海成立的亚洲学术研究会,发行有《亚洲学术杂志》(原定月刊,实为季刊),并计划每月开讲书会两三次,理事汪钟霖、邓彦远,孙德谦为杂志编辑人,任稿会员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该会宗旨愤心时流,攻斥骛新者不遗余力,欲借此拯救世道人心[28]。社团的倾向性、斗争性也开始明显。观念之争往往导致社团成员之间的不和或裂痕。如南社掌门人柳亚子论诗宗法三唐,矛头直指“同光体”,当朱玺声称“反对同光体者,是执蝘蜒以嘲龟龙也”时,柳亚子马上在《民国日报》及《南社丛刻》上刊登了驱逐朱玺出社的启事。个中原因,柳亚子承认他反对宋诗是有政治背景的,而他本人对宋诗并无仇怨。1923年8月,王秉恩、陈三立、辜鸿铭、王国维、罗振玉等20人联名发起成立东方学会,计划设立董事会和理事会,由柯劭忞任董事长,尉礼贤和今西龙为董事,拟定简章10条,宣称:“中国有数千年的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欧美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认识到在强权和枪杆之外还有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纷纷注重研究东方文化。本会以研究中华文物制度为己任,研究古代经籍和历史的关系,以图洞悉国家和社会治乱之根源。”[28]从其宣言中可以明显看到救国与挽救传统文化的目的。
五四以来,社团的发展达到高潮。据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1935年8月)导言中的介绍,仅1922年到1925年3年时间,就有不下100种文学团体和刊物成立出版。这一时期的社团还出现报刊、大学与社团、学会紧密结合的趋势。朱光潜曾说:“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29]郭沫若等人在筹组创造社过程中还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切。”
相对于近代社团而言,现代文学社团往往文学观念更加明晰,文学倾向性更强,主张更明确。比如《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30]这个宣言就明确将文艺看作是为人生的艺术。又如,弥洒社的《弥洒》1923年第2期出版的扉页上,加上这样的一条标语:不批评,不讨论,无目的,无艺术观,只发表顺着灵感的创作。后来,胡山源回顾这条弥洒标语时说:“我决不反对别人的批评与讨论,目的或艺术观,但我自己,只认定创作就是,我们的月刊,只发表创作就是。我想,分工合作本来是现代的科学精神,谁喜欢什么,长于什么,就可以从事什么,何必强不知以为知,学趋时增,舍己从人呢?”[31]这些社团更注意培养文学新人。如鲁迅所支持的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等社团即是很好的例证。在鲁迅培养帮助下出现过一些作家,如高长虹、台静农、李霁野等,他们多写反映农村现实的“乡土小说”,并译介许多俄国文学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这些社团接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影响的痕迹也更明显。如浅草社以《浅草》季刊为阵地,沉钟社以《沉钟》半月刊为阵地,大量介绍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而新月社则受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影响较深,他们当中的主要成员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都是当时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现代社团之间的论争较之近代社团的论争更为激烈。比如,太阳社和创造社在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并且对鲁迅以及语丝派所代表的五四文坛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而引起了革命文学的论争。郭沫若在描述这种转变时说:“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国,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战线。”
二、文学批评空间的开创与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近代以来,新式传媒和新式社团的出现,为公众参与文化再生产和社会整合提供了一个公共舆论空间,普通大众得以深入其中,参与自由讨论,干预、监督、批判、推进并改变着社会变革的走向,在批判封建专制、启蒙民众、酝酿社会变革诸方面发挥更大的力量,同时,它们也成为文学变革和文学秩序重建的策源地,使文学活动的现代化与人们社交方式的现代化逐渐同步。就其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而言,其作用突出表现在:
其一,文学民主性的发扬和批评民主性的建设。新式传媒和新式社团往往采用民主的原则与程序,强调平等,多以选举方式产生组织领导和职员,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表决,因而对文学民主性的发扬和批评民主性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的编者就表示:稿件底取舍,纯准于稿件本身,决不因作者底关系而有所变异。19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则于每周星期三给陌生作者的作品留出版面,编者宣称:“纵有文艺先辈的好文章,也不使这天受侵犯。”类似这样的办刊思想与原则甚至持续到四十年代中后期。例如,《十二月》第二期所登的《稿约》中说:“一、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来稿,凡是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只要是和我们的方向相同,是真实的内容,我们都愿尽力采用。二、一切抒发个人感情的,或暖昧不明的文章,不管它的艺术价值多高,我们一概拒用。三、我们主张大刀阔斧的文学,极力反对中庸派的虚伪声调,后者请免寄。”[33]“饮河诗社”也是一例。1947年初重庆《世界日报》副刊版《饮河》第一期《开场白》中就曾明确主张:“我们愿意作诗人的写手,凡能收到并世诗人篇什,皆乐为刊载,绝无汉、魏、唐、宋之见,亦无名位崇卑之见,更无亲疏识与不识之见。”批评民主性的建设从《小说月报》关于“读后感”栏目的争论与设置也可见一斑。《小说月报》“创作批评”栏目从13卷8号开创起到13卷12号共刊登11篇批评文章。“读后感’,一栏从14卷3号至14卷12号,除了9号太戈尔号外,共登载批评45篇。郑振铎于14卷3号开辟“读后感”栏目时,曾认为“读后感”是“批评创作最经济的方法”,当时,有人对郑振铎说:“去岁的‘创作批评’很有些有价值的成绩,现在虽然这一栏目取消,但是希望有这样的作品贡献给读者们;至少每号要有二三篇才好。因为,中国文学界批评的空气太干燥了。‘读后感’虽然是‘批评创作的最经济的办法’,但究不赶创作批评的文字有系统些,况且凭一时的感想,也未必就算是忠诚正直的批评。”[34]后来,严敦易又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读后感’的办法,似有可议,一件批评文字,要能把作品全分析、了解;去讲领略的情绪,和感触;在短短的几百字里,怕不会有如此经济吧!……没有系统又不见得能指导作家,(而且全是讲作品好的多,这样有何用处)。”[35]“创作批评”较之“读后感”的经验性描述更具体系性、更透彻,鉴于读者的正确意见,郑振铎表示赞同,并于第15卷起取消了“读后感”一栏。
其二,制度化文学批评生产场域与生产机制的逐步形成。与传统文学批评的个人化或私人化特征相比,近现代的文学批评活动更具有制度化生产的特征,它们往往是在某些具有制度性保障的话语生产场域中完成的,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带些鲜明现代性特点的生产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现代文学批评公共论坛的逐步形成。比如,梁启超主持的《小说丛话》的“笔谈”就是典型的一例。这组笔谈第一次利用报刊这种现代传媒,集合了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集中地讨论有关小说的各种话题,笔谈者立场和观点各异,相互辩论,互有交锋,在小说理论探讨方面形成了完全有别于古代评点的理论探讨的新形式和新格局。其参与者大都采用笔名形式,如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曼殊(梁启勋)、平子(狄葆贤)、研人(吴研人)、知新主人(周桂笙)、蜕庵(麦孟华)、瑟斋(麦仲华)等等,这与古代评点以真名示人、看重作者权益颇不相同。其次,延续时间长达数年。再次,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思路各异。既有基于文本细读与阅读体验的理论总结,也有跨文化视域的中西比较,既有基于历史脉络的梳理,也有纯粹原理性的阐发。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类似“文化沙龙”性质的笔谈,是以一种平等、理性的探讨方式出现的。作为“主持人”或“发起人”的饮冰并不以权威压人,参与者自由发言,各种争论也尽量记录在案。可以说,过去那种视小说为小道,重把玩、少驳诘的研究方式,已逐渐变成了在公共领域公开进行的自由讨论,原先局限于传统士大夫小圈子之间的私下活动,已开始通过诉诸公共舆论而扩大了文学批评的空间。《申报》中的“自由谈话会”这样的专栏在近现代以来的报刊、杂志中也是极为典型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空间开创的例证。“五四”以后,一些专业文学性刊物在拓展文学批评空间方面开始有了十分自觉的意识。如《小说月报》不仅开设了“创作批评”这类具有专业性很强需要专业批评家参与撰稿的栏目,还开设了能适应普通读者的“读后感”专栏,把编辑者、作家、读者之间的互动看作是拓展文学批评空间的重要方式,十分重视批评与创作的“共生”、“共赢”。二、新的能促进文学批评空间得以开创的批评文体得到重视。比如对话体。如果说梁启超主持的《小说丛话》的“笔谈”初具对话研究的基本的模式的话,那么到“五四”以后,对话体成了开创文学批评空间的重要方式。比如在《创造季刊》中,对话体和诗这两种文体形式尤其受到批评家的青睐。其中刊出的《批评之拥护》一文甚至全篇采用主客对话、一问一答的形式。三、理论话语的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创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空间。这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撰与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特别推出《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并聘请当时著名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作序,选辑近200篇理论文章,不仅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新文学理论的建设过程,也为理论或论争这些理论话语在文学系统中争得了合法的席位,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理论的研究空间。类似《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的“自然主义的论战”专栏这样的设置,自“五四”以后,更是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学批评已不再是纯粹个人的意识观念的表意实践,而是社会综合力量参与竞技的场所。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其教科书或讲义的编写、报刊杂志与学术刊物等传播媒介的出现,评论机制的独立化等这类具有现代性质因素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活动的空间,使旧有的那种侧重于个人之间的偶然性交流或彼此的欣赏与品玩的文学批评活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公开性和广泛代表性,文学批评的社会性的增强、批评活动的空间与组织形式的变化,使文学批评活动日益成为一种“公共事件”而不是“个人事件”,文学批评在研究方式、交流方式、传播方式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知识活动领域。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空间的拓展,使文学批评活动在生产、消费、组织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方面,共同形成了现代批评家难以逾越的话语生产场域。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新的生产场域的形成和变迁,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知识、结构、欲望与权力之间的多重矛盾与纠葛也给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活动注入更为复杂的因素。
[1]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M]//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2002.
[2] 孙家鼐.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摺[M]//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3]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M]//沈茂骏.康南海政史文选.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4] 秦理斋.中国报纸进化小史[M]//《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上海书店,1987.
[5]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本)[M].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6]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N].原载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1册//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 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J].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号),1904-09.
[8] 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M]//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原载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100期//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二卷.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 张季鸾.季鸾文存:第一册[M].天津:大公报馆,1944.
[11] 林白水.中国白话报发刊词[J].中国白话报,1903(1),1903-12.
[12] 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N].原载《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03-31//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3]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1997.
[14] 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N].新民丛报,1904(17).转引自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15]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6] 东海觉我(徐念慈).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M]//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17] 米怜(William Milne).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J].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第1卷第1号,1815-08.
[18]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M]//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19]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M]//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0] 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102-108.
[21] 《国学季刊》“编辑略例”[J].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01.
[22]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3]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原载《新潮》2卷1期,1919-10-30.转引自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
[24] 梁启超.论学会[M].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5] 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26]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M].北京:三联书店,1995.
[27] 包天笑.集会结社[M]//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28] 桑兵.民国学界老辈学人的学术传承[J].历史研究,2005(6).
[29] 朱光潜.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者徐先生(作于1936年1月7日)[M].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30] 文学研究会宣言[J].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01.
[31] 胡山源.从《弥洒》说起[J].红茶,第2期,1938-07.
[32] 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J].文艺讲座,第1册,1930-04-10.
[33] 十二月文艺社.稿约[J].十二月,第2期,1946-03-17.
[34] 吴守中.通信[J].小说月报,1923,14(10).
(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Public Domai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Literary Criticism at the Turn of Modern-contemporary Age
HUANG Nianran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Wubei 430079)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public domain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Newspapers, journals and literary societies constitute the public domain of China’s literature. The cultural public domain and criticism space in the media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ges were characterized with whipping the feudal tyranny and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media and new societies provided the space of public opinion for people’s participation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provided opportunity for cre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gave full play to the promotion of literary democracy, the construction of criticism democracy and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rule-based production sites fo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echanism. It gave impetu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ducive to the change of literary criticism to the competition site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Modern-contemporary Age; literature; public domain; literary criticism; modernization
I0
A
1009-8135(2016)01-0055-09
2015-11-28
黄念然(1967-),男,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艺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项目编号:08JA7510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