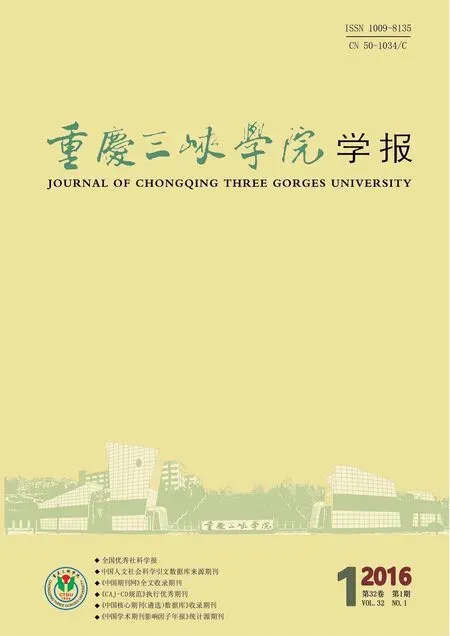苗族“椎牛祀”的文化特征
熊晓辉
苗族“椎牛祀”的文化特征
熊晓辉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苗族“椎牛祀”的文化特征是由苗族传统文化的特性来决定的,在苗族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椎牛祀”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苗族“椎牛祀”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苗族“椎牛祀”是苗族人崇鬼祭天的体现、苗族“椎牛祀”是苗族人跨越文明的体现、苗族“椎牛祀”是苗族人传播傩文化的体现、苗族“椎牛祀”是苗族人娱神娱人的体现等几个方面,它反映了苗族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而且具有原始宗教和民俗传统为中心的社会准则。
苗族;祭祀;原始宗教;椎牛;文化特征
苗族由于分布地域广阔,各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其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在湘西苗族聚居区,人们通过“椎牛”的形式来祭祀鬼神。椎牛的目的一般为的是解除重病,有时也为了求子。在当地,如果有人得了重病,都必须占卜,若被认为是鬼祟作怪所致,就得请巫师(“巴岱”)许下椎牛大愿。许愿以后,如果病人转危为安,或求子得子,就需准备椎牛还愿。“椎牛祀”多选在秋天以后举行,其主要程序包括许愿、买牛、开门、敬家先、享客、摆古、赎名赎利、喂水牛、椎牛、散客等,要举行四天四夜。
当前,许多古老的祭祀仪式在中国已经消失殆尽,而苗族“椎牛祭祀”仍然在偏远的山寨存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奇迹。“椎牛祭祀”也是苗族歌舞艺术形成的重要载体,苗歌演唱几乎贯穿了仪式的全过程。在夜以继日的祭祀活动中,“巴岱”扮演了沟通人神的特殊角色,且歌且舞且吟,祭祀场面显得十分神秘而又活跃。有学者研究证明,“椎牛祭祀”以及后来形成的“椎猪祭祀”为后来苗族傩戏的形成提供了戏剧的时空构建、演出规范、音乐素材和内容题材[1]288。
其实,“椎牛祭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炎黄时代就已经开始实行椎牛之风,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人们看到只有牛的血才是数量最多并且最容易获得的血源,所以用牛作祭品,以血祭祀大地的仪式是上古社会丰产仪式中的一种普遍形式。随着农耕文明的进化和耕种劳作的实施,耕牛成了人们生产劳动的必备物,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和保护。在苗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环境恶劣,外来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阻碍,使得“椎牛祭祀”这一古老仪式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发展,并成为苗族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传统。
苗族人崇鬼信巫,能歌善舞,巫舞祭祀的历史尤为悠久,两千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其《礼魂》中曾写道:“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猖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鼓。”[2]2这即是对当时苗族人在祭祀时击鼓唱歌情景的真实写照。苗族“椎牛祀”是苗族民俗习惯、宗教艺术、生产生活,以及祀神与娱人浑然一体的产物。苗族《古老话》、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优美的歌舞使其古老神秘的宗教仪式变动生动、活泼而离奇。研究发现,苗族许多有关文学、艺术、哲学等,往往同巫术宗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苗族巫鬼文化的独特特征。
一、“椎牛祀”是苗族人崇鬼祭天文化的体现
苗族人信鬼好巫,有其源远的历史。早在远古时期,苗族人就相信万物都有灵魂。苗族人对自己的祖先十分崇敬,认为祖先“虽死犹生”,会永远与自己同住,所以在苗族社会中盛行祖先崇拜与崇鬼祭天。根据苗族地区许多地方志记载,苗族人每逢节日必杀牛祭祖祭天,这种祭祀活动至今仍然盛行于许多苗族地区。《汉书·地理志》曾记载:“楚人信巫好鬼,重淫词”。楚人信鬼,其实是有史可证的,而且楚巫文化源远流长。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古代三苗巫文化、楚巫文化、苗族的巫教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并一致认为楚人主要是“九黎三苗”[3]77的后裔。许多地方志都记载了“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在狩猎时期,牛是苗族人重要的衣食来源,常常被赋予男人的形,而受人尊敬。苗族“椎牛祀”,有歌有舞,“巴岱”以鼓为号令,手脚随着鼓点的节拍舞动,这也许跟苗族人崇鬼祀天的文化有关。在汉代,就有史料记载苗族地区人们“信巫鬼、重淫”。[3]70清代《永绥县志》(卷六苗峒)记载:“苗俗又有所谓跳鼓脏者,乃合寨之公祀,每户杀牛一只,蒸米饼一石。届期男女早集,多者千余,少亦数百,赴同寨之家,每户各食饭一箸,牛肉一片,糟酒随饮于敞处。将四根高一丈五尺的木柱埋于地中,横木板用草铺垫,陈设米饼牛肉,上履以屋,以祭众神。苗巫擎雨伞,衣长衣,手摇铜铃招请诸神。另一人击竹筒,一木空中,二面蒙生牛皮,一人衣彩衣服挝之,其余男子各服伶人五色衣,或披红毡,以马尾置乌纱冠首。苗妇亦盛。男外旋,女内旋,皆举手顿足,其身摇动,舞袖相连,左顾右盼,不徐不疾,亦觉可观。而芦笙之音与歌声相应,悠扬高下,并堪入耳,谓之跳鼓脏。”[4]27笔者还调查到,现居住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花垣县雅酉乡境内的苗族和凤凰腊尔山苗族,都有遵守“岁首”(苗族人一般以六岁为一“岁首”)和“牛酒祭天”的习俗。笔者认为,苗族这种“岁首”祭祀习俗属于苗族古老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习俗并不代表着它就是苗族原始习俗,它其实就是苗族古老文化与苗族巫鬼文化的相互融合。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人们非常注重天人关系,无论苗族、汉族、土家族等,他们都主张天人合一,这是先民们对大自然的一种理解、崇敬及价值取向。
古代苗族社会,人们的生产能力和认识能力极其低下,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自然现象等不能科学地认识,为了求得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们不得不崇拜自然、崇拜天神。从苗族“椎牛祀”的歌词中,可以看出苗族人遵循天道,是为了感恩天地为人类提供的丰富物质资料,并希望灾祸消灭,六畜兴旺。如苗族“椎牛巫辞”中《祭天歌》唱道[5]370:
这个天神敬得好,怎得天天都晴朗;
同一天空普遍罩,同一日头普遍热;
清晨一直到黄昏,午时躲阴凉处歇;
水中青蛙呱呱叫,天然虫蚁齐露头;
高山大岭小山冈,全都长草绿油油;
好天我们要播种,种下三草就开口;
求天放晴已得到,上天恩情记心头。
从苗族人祭祀歌词和宗教信仰上观察,苗族原始宗教与巫鬼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苗族人祭祀,无论是从表层形态,还是深层内涵,都表明出民族性、系统性和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以及悠久的渊源。苗族人有浓郁的巫鬼风俗,他们崇信神巫尤甚于古,平时婚丧建造都取决于巫师之言,就是每当有人疾病损伤,不以药治,而卜之于巫师。在腊尔山苗族地区,苗族崇拜的鬼神有很多种类,人们常常称有“三十六神、七十二鬼”。巫鬼在苗族地区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苗族人有共同的祭祀对象和神袛体系,有固定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祭祀社群,有特定的巫术、神祠,有专门主持祭祀仪式的“巴岱”,而且苗族传统祭祀占卜与楚巫占卜非常相似。我们把苗族“椎牛巫辞”中《祭天歌》与《楚辞》中的《九歌》相比,有许多类似之处。如《九歌》中的一十一篇,除了《国殇》、《礼魂》以外,其余九篇都是以祭祀神灵为主的神歌,被后来研究者称为“神曲”。李廷贵、张山等所著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指出,“苗族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膜拜偶像,有的以日为神,有的以山为神,有的以河为神。像‘山鬼’、‘云神’、‘河神’之类的词汇,在苗族的巫词祷语中便屡见不鲜。就是《九歌》作品中,不少格调与现今苗族的民歌特别是巫歌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山鬼》与苗族巫歌《榜祸歌》,苗族《烧汤捞油巫词》与《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等某些字段,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两者均雷同或近似。”[1]188又如苗族长篇史诗《古老话》里的《天地形成》,它既叙述了神造天地、人类繁衍、万物生长的基本过程,又描述了洪水滔天、魔鬼入侵、民族迁移、部族战争等神话。在苗族的《古老话》中,苗族人记叙了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形成的情况。苗族人认为,在远太古代以前,整个宇宙都是紫气,之后紫气又慢慢地透出五色云光,由五色云光分出十二种乃至三十七种光色,又由这多种光色变化成以灰色为主的浓气,灰色之气通过漫长时间不断加浓加固,凝固成地球,最后形成天体。与其他民族的创世史诗相比,苗族原始先民对天地形成的看法也体现了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展示了一个自然生成的“原生宇宙”。在这自然生成的“原生宇宙”中,不仅天地有别,而且同时还有天神、人和动植物的存在。所有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自然本身就包罗万象。结合苗族人原始先民的生命意识和“万物有灵”观来说,人类是有生命的自然实体,天地也是生命的自然实体,在整个大自然中是同时存在、天生一体的。苗族人把“天地形成”又叫“开天辟地”,这段《古老话》在椎牛祭祀、接亲摆酒等场合讲述,起到纪念祖先、歌颂祖德、传教后人的作用,同时又是一种陪客的方式。
苗族“椎牛祀”是苗族人祭祀祖先、崇鬼拜天的原始宗教仪式,从祭祀仪式内容上看,它脱离不了与神灵崇拜、遵循巫鬼、民俗生活、民族战争的关系,在“椎牛祀”中,常常也会看到一些宗教祭祀动作,如“敬家先”、“送黄牯”、“跳鼓舞”、“椎牛”、“送客”,等等,在这类“巴岱”祭祀仪式中,苗族人非常崇尚人性美,在仪式中无不使这种人性美展现出来。远古时期,牛是人们常用的祭祀牺牲品,用牛作牺牲以及以牛血祭祀大地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祭祀仪式,因此,苗族人为了让大地丰产而获得再生的力量,先民们就用鲜活的牛血来祭祀大地之神。据《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献集成》记载:“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由于人对自己生命的体验,人们都相信血不仅是维持生命、增强力量所必需的自然流体,而且还是生命的精华,是灵魂的居所和载体。血有灵性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即便在离开动物或人体之后这种生命力还继续存在,因此,它被看做是复活的再生、传宗接代的力量所在”。[6]290可以看出,苗族巴岱“椎牛祀”仪式就是苗族人的一种精神安慰,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苗族宗教祭祀,作为苗族社会文化的一种现象,对苗族人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艺术思维等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苗族巴岱“椎牛祀”仪式属于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宗教现象,也是苗族社会独有的一种意思形态,它包括复杂的宗教心理,多元的哲学思维以及多样的崇拜仪式等。
二、“椎牛祀”是苗族人跨越文明的体现
史料记载,人类在杀牛祭祀之前,用于供奉神灵的牺牲并不是牛、羊、猪一类的动物,而是人类自己。作为牺牲的人,首先是部落酋长、儿童、美女和罪人。中国古代有关美女祭神的记载比比皆是,如罗琨在《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中曾记述:“酒河五十牛,氏我女?”大约到了商代才开始由人祭过渡到牛祭。古代苗族先民曾把雷神想象成女性,祭雷神用雌猪,不用公猪,而且要一妇女坐在木椅子上,双脚分开踩着一张犁口的两头,象征性地代表雷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类慢慢地以动物代替人作为祭祀的牺牲,这些动物曾有牛、羊、猪、猴、狗等。从苗族“椎牛祀”产生时间来看,可能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因为在苗族“椎牛祀”仪式活动中能扑捉到许多原始社会苗族人留下的文化痕迹,比如“椎牛祀”仪式中跳鼓的隆重场景,那是苗族先民集体宗教活动的再现;苗族人对舅方的至上尊崇,体现了“母权制”在苗族人心灵上留下的印记;就“椎牛”仪式而言,人们见到椎牛后血淋淋的场面都习以为常,还不时地传来热烈欢呼声,这其实就是古代崇尚“血祭”的遗风。苗族“椎牛祀”仪式在苗族社会内部形成以后,并世代传承,历世不衰。据湘鄂渝黔毗邻地区的一些地方志记载,在新中国成立前期,居住在湘鄂渝黔毗邻地区的苗族几乎都有“椎牛祀”的习俗。苗族崇尚“椎牛”习俗,苗族人的宗教又称“鬼教”,因为苗族人以“信鬼”、“祭鬼”为主要内容。在所以这些祭鬼活动中,椎牛是苗族宗教中最重要的一种,即是特祭又是常祭。清嘉庆之前,椎牛是最能代表苗族核心价值的宗教活动。
苗族“椎牛祀”主要是通过椎牛请求祖先和神灵保佑子孙安宁,并且传达祖先的希望。“椎牛”,苗语称“弄业”,就是苗族人“吃牛”的意思。苗族“椎牛祭祀”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祭祀重要的对象就是苗族自己的先祖们。苗族先民在“椎牛祭祀”中常常运用鼓声渲染气氛。仪式场地内鼓声阵阵,围观的群众呼声震天,只见银光闪闪的长矛不断刺进牛的左前腿部位,直刺得水牛鲜血直流,最后倒在血泊之中。当晚举行“独乐”(“跳鼓脏”)活动,男女青年跳鼓喝彩,通宵达旦。《永绥厅志》记载,湘西苗族地区流行一种“跳鼓脏”,是一种祭祀乐舞。合寨共祭,数年间行之,亥、子两月,择日举行。每户杀牛一只,蒸米饼一石。届时,男女早集,多者千余,少亦数百,祭众神。“椎牛祭祀”、“跳鼓脏”是苗族人祭祀远古祖先的一种仪式,传说是母系氏族酋长奶夔、父初期酋长玛苟为祭祀发明饲牛和创始农耕的祖先柳斗、柳庆(一说是祭神农氏、祝融)的一种祭祀祖先的活动。“椎牛祀”仪式的内容和表演形式十分古朴,并保留了许多的远古遗存信息,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苗族历史文化的表征。人们通过仪式与表演来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历史,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解放以前,苗族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对封闭,对外交流很少。由于政治、环境等因素,像“椎牛祀”这样的活动只是在苗族人的内部交流,基本上限定在族群内部的小社会结构中。苗族“椎牛祀”仪式是苗族人祭祀活动中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这种祭祀仪式承载了苗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信息和内容,人们可以利用祭祀仪式的形式在社会活动中进行交往,以增进彼此间感情与思想的联系。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苗族“椎牛”祭祀确实是跨越文明的一步。
但是,苗族“椎牛祀”祭祀仪式耗资非常巨大,尤其在活动中需要宰杀大量耕牛,对农业生产以及生产力的破坏极大。根据文献记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清政府下令“禁苗人椎牛祭鬼、放蛊、赌博、渎伦诸习”。[7]严禁椎牛之令颁布后,苗族地区每年可以“全活耕牛数万头”,从生产上来说,这确实是一笔非常巨大的生产资本。19世纪上半期,苗族社区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的稳定,可见严禁椎牛政策也确实产生了一定实效。新中国建立后,苗族地区的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椎牛祀”祭祀仪式习俗逐渐被苗族人摒弃。但是,不能否认,苗族“椎牛祀”祭祀仪式中蕴藏的丰富民族文化遗产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三、“椎牛祀”是苗族人传播传统文化的体现
从苗族“椎牛祀”祭祀形式上观察,苗族“椎牛祀”仪式的表演形式非常丰富,其中有两种普遍存在的仪式最具代表性,一是模仿式祭祀仪式,二是悼念性祭祀仪式。
模拟式仪式一般以牛、蝴蝶等动物、昆虫作为祭祀图腾,在力求这种祭祀图腾的物种大量繁殖时,做出模仿它们的许多动作,由此达到无比兴奋的状态。例如湘西腊尔山地区苗族人在“椎牛祀”中穿插着打猴儿鼓的场面。
在完成各个模块的FPGA硬件实现后,先要通过Modelsim进行功能仿真,然后进行板级测试,验证模块功能是否正确。整套系统软硬件测试平台如图10所示。
悼念性祭祀仪式是以悼念神话中的图腾祖先为目的,由苗族巫师“巴岱”诵经、表演,将苗族神话传说中各种人物信息传递给观众,其中“椎牛祀”仪式里常常提到苗族人自己的价值观、生死观、伦理观,等等,这种仪式直接给人一种安慰感和娱乐性。
但是,无论是纪念性仪式还是模拟式仪式,都强调了苗族人的原始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调整了人们道德观念,它们都是苗族人传播传统文化的体现。从椎牛的目的来看,苗族“椎牛祀”又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庆祝性椎牛,这类活动是为了庆祝一年的丰收,并祈祷来年分调雨顺,人们于每年农历十月举行椎牛祭祀活动;二是还愿性椎牛,人们遇到疾病或中年无子,往往幻想通过祭鬼祛病或求子,如卜得病为牛鬼作祟或牛鬼在南天门阻止女阎王送子,都必须请“巴岱”来家里烧黄蜡,打锣鼓,许椎牛大愿;第三种是公祭椎牛,与第一类祭祀情况有些类似,但第一种类型的椎牛限牛一头或两头,每年都要举行,而公祭则数年举行一次;第四种是盟约椎牛,也就是为了达到整合社区内的力量以实现复仇或应对仇杀而采取椎牛活动。一般来说,椎牛活动时间比较长,参加人数多,影响很大。特别对年轻人来说,椎牛场所也是他们谈情说爱的地方,椎牛在民族价值认同、民族内部团结等方面起到了调节和关键性的作用。
据《永绥厅志》(清同治版)记载,苗族人古时椎牛多是“合寨之公祀”,数年间举行一次,名曰“跳鼓脏”。届时每户杀牛一头,男女集于郊外,“多者千余,少亦数百”,以牛祭诸神及祖先。祭必“男子各服伶人五色衣,或披红颤,以马尾置乌纱冠首。苗妇亦盛,男外旋,女内旋,皆举手顿足,其身摇动,舞袖相连,左右顾盼,不徐不疾,亦觉可观”。至清中叶后,椎牛逐渐被单家独户的行为方式所取代。
苗歌演唱几乎贯穿了椎牛祭祀的全过程。苗歌分为高腔、平腔两大调式,而平腔又有20多种腔调。鼓舞在祭祀活动中得到空前发展,逐渐成为一项引人注目的舞蹈艺术。鼓舞分男女,男鼓舞有鸡公啄米、阵鼓催兵、犁地耕田、农夫插秧、收获打谷、大鹏展翅、猴儿戏物、九龙下海等;女鼓舞有美女梳头、包头洗面、巧妇织锦、绣花挑花、辄麻纺麻、左右插花、团圆鼓舞等。“巴岱”就是通过“椎牛祀”来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因为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往往只能利用“椎牛祀”这样大型活动来全面传授苗族传统文化。一般情况下,苗族“巴岱”通晓苗族历史,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对苗族传统文化传播起着积极作用。
“椎牛祀”中,苗族人讲的《古老话》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苗族史诗,它其实就是“巴岱”吟诵的巫词,长约万行,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词句优美,并包含了苗族创世神话、民族迁移、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生产劳动、伦理道德、音乐舞蹈、宗教文化等内容,按《古老话》中讲述的内容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鬼神的崇拜,还有一类是对苗族历史变迁与发展的叙述,它是研究苗族社会历史、文化艺术、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和民俗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
四、“椎牛祀”是苗族人娱神娱人的体现
“椎牛祀”有歌有舞,特别注重与苗族民间情歌的结合。椎牛仪式由始至终都穿插着情歌演唱与对唱,娱乐性强。清代严如煜在《苗防备览》中曾记载湘西苗族“椎牛祀”时娱神娱人的情景:“男左女右旋绕而歌,举手顿足,疾徐应节。”又据张子伟主编的《中国傩》一书记载:“苗族举行椎牛仪式的先晚,主家的客人娘舅、妻舅、姑妈、姨妈、姐妹诸家,也就是抬腿的亲戚。都要选择最漂亮的、未结婚的、擅长唱歌的青年男女,少则四队,多则十几对,来主东家对歌,主东家也要早早训练一二十对男女歌手,与诸亲歌手对唱。对歌时可以动手动脚,行动比较自由,打打闹闹,通宵达旦,十分热闹。”[8]304同时,我们发现在《凤凰县志》里也记载了苗族“椎牛”的娱乐现象,据《凤凰县志》记载:“歌已,男女杂坐,欢呼牛饮(割牛肉烧吃),醉饱戏谑,无所不至。”[9]57在椎牛仪式中,青年男女对歌于野外,这就是苗族人典型的以歌娱神而又自娱的形式。苗族“椎牛祀”不仅仅是苗族“巴岱”的单独表演,而且更多的苗族群众都参与活动之中,只要是前往做客的苗族人都穿着盛装艳服。地方文献记载,“椎牛”祭祀时,苗巫(巴岱)撑雨伞,衣长衣,手摇铜铃,招请诸神。另一人击竹筒,一木中空,二面蒙生皮,一人衣彩服挝之。其余男子各服伶人五色衣,或披红毡,以马尾置乌纱冠首,苗妇亦盛装,跳舞娱神。”[10]118既然苗族“椎牛祀”的主要活动是以舞降神,巫俗以此为盛,那么苗族人必定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苗族地区也必定是歌舞之乡。举行“椎牛祀”,在一片歌乐鼓舞声中,人神杂糅,娱神娱人,重情重义之色彩甚为浓重。
在苗族地区,人们祭祀祭神,娱神娱人,主要是为了禳灾祈福。苗族人长期居住在高山密林之中,山高水险,交通十分闭塞,生活环境恶劣,加之其认识能力有限,很难对自然界和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各种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并且往往误认为自己能唤起和创造这些自然物,于是就萌发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苗族人认为,自己的命运自己难以自主,从来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把握自身的命运,只能相信人生的无常归于天命,所以,神在这里被普遍地信仰着。苗族人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场面极为隆重、庄严,如若身临其境,或会产生祖先的魂魄就要从阴间返回,人、神和自然万物彼此会融为一体的感觉。苗族人有祭祀神灵的习俗,不仅表现在一些重大节日活动中,也渗透到苗族人的生活习俗上。比如苗族人家有人生小孩,待孩子生下来后,家长担心其长不到成人,便会在本村选择一颗老树,在树枝上系一块红布,树前摆一盘“刀头”肉,再点上几柱香,祭拜老树为干妈,孩子便可以平安长大。有时遇上疑难是非,当事人也常砍鸡头,饮血酒,发血誓,以明心迹,这些都深刻地表现了苗族人禳灾避祸的迫切愿望。苗族人在椎牛祭祀时,杀牛敬神、娱神,同时也为了娱人。由于受到“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苗族人心目中的许多神灵,实际上就是神话时期的神灵,而苗族“巴岱”则是人与神沟通的使者。人们在“椎牛祀”祭祀仪式中祈神、施法、娱神、敬神,都要通过“巴岱”去执行,于是“巴岱”就成了神的代表,由他执行的巫术便获得了神秘的原始宗教色彩。苗族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娱神娱人,人神同乐,追求生命存在的现实满足。从苗族“椎牛祀”还傩愿中还可看出一个人神杂糅、娱神娱人的动人场面,而娱神实则是为娱人,从这个角度看,苗族人十分懂得生活,也懂得该如何愉快和幸福地生活。苗族宗教祭祀仪式不仅作为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活动形式,而且也作为他们的社会文化活动形式,集中体现了人们的宗教观、生命观、艺术观、娱乐观、审美观,并通过祭祀仪式满足人们的艺术和娱乐需求,从而使“椎牛”仪式发挥出宗教和娱乐作用。
[1] 胡萍,蔡清万.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献集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 熊晓辉.湘西音乐丛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3] 汉书·地理志[M].清光绪刻本.
[4] 永绥县志[M].清宣统本.
[5] 张子伟,石寿贵.湘西苗族古老歌话[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 李廷贵,张山.苗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7] 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征服下[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8] 张子伟.中国傩[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9] 凤凰县志[M].清光绪本.
[10] 熊晓辉.湘鄂渝黔边区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态与特色[J].黄河之声,2007(9).
(责任编辑:于开红)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illing-Bull Sacrifices in Miao Minority
XIONG Xiaohui
(Art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Miao “Killing-Bull Sacrific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Miao culture, “Killing-Bull Sacrifices” shows a strong nature of inheritance in that it is the occasion when the Miao people worship gods and heaven, the reflection of civilizing, the spreading of Nuo Culture and the occasion when humans and gods have a carnival time. It is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natural condition and the social-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it common rules concerning the primitive and folk tradition are observed.
Miao; sacrifice; primitive religion; Killing-Bul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892.2
A
1009-8135(2016)01-0028-06
2015-11-15
熊晓辉(1967-),男,湖南凤凰人,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民族音乐与舞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苗族巴岱信仰的历史与现状”(编号:11BZJ029);2014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辰河高腔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编号:14ZDB0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