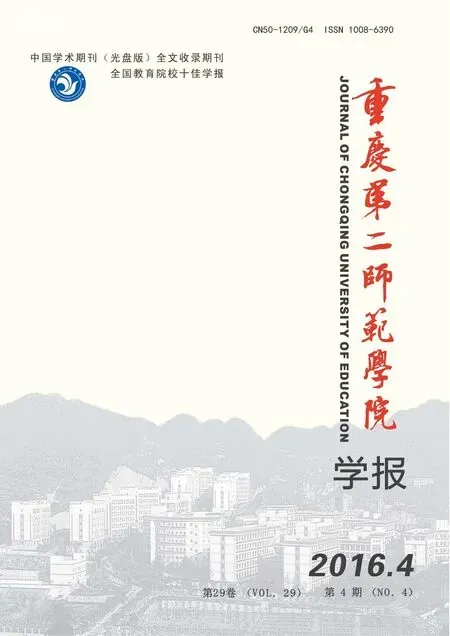英雄主义的回归与变异——从近百年中国文学看《三体》
高 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英雄主义的回归与变异
——从近百年中国文学看《三体》
高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英雄是文学作品的主要书写对象,《三体》塑造了一群与众不同的英雄形象——冷酷的英雄。不同的时代,英雄主义在文学中必然呈现独异的色彩。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英雄主义大致经历了文化启蒙的个性英雄主义、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高度理想化的“扁平”英雄主义、充满反思性和悲怆感的英雄主义以及“反英雄化”、“祛英雄化”的演进过程。只有将《三体》置于近百年中国文学英雄叙事的衍变中,才能对其英雄主义的特质以及艺术价值做出更切实的分析。
百年中国文学;《三体》;英雄主义;回归;变异
自刘慈欣的《三体》获得素有“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后,一时间,评者如潮,洛阳纸贵。《三体》给疲软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无限惊喜,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人对于文学走出国门,为世界所肯定的殷殷期盼,也在文学想象、人物塑造、思想技巧层面上带给了读者久违的震撼,那种冷酷的英雄主义便是其中之一。“英雄豪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之高是无与伦比的。”[1]从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和中国的远古神话、古典诗歌起,均是如此。然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不同的时代,英雄主义在文学中必然呈现独异的色彩。具体到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英雄主义大致经历了五四文学中的文化启蒙的个性英雄主义、革命文学中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中高度理想化了的“扁平”英雄主义、新时期文学充满反思性和悲怆感的英雄主义以及后新时期的“反英雄化”、“祛英雄化”的演进过程。因此,只有把《三体》置于近百年中国文学英雄叙事的衍变中,才能对其英雄主义的特质以及艺术价值做出更切实的分析。
一、百年中国文学英雄叙事的衍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世纪后半期,一方面西方列强大举入侵,另一方面,中华传统封建文化的软弱性和黑暗性越发显露无遗。尤其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人们纷纷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曾经的辉煌和雄强再也难觅踪影,一次次的战败和列强的凌辱让整个社会弥漫着失落、愤激、沮丧甚至绝望的情绪。为了挽回民族尊严,“复我华夏之汉唐”的雄强梦想,人们期待英雄横空出世。“谁救了我们,谁就是一个英雄;在政治行动的紧急关头,人们总是期望有人来挽救他们。每逢社会上和政治上出现尖锐危机,必须有所行动,而且必须赶快行动的时候,对英雄的兴趣自然更加强烈了。”[2]19世纪后半期中国对英雄的呼唤正是如此迫切,而且人们呼唤的主要是“政治英雄”,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不息乃至英勇献身的英雄。此类英雄呼唤是为了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不是人的独立。“实际上,他们也不可能把‘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凌驾于‘挽救国难’之上。”[3]
从洋务运动的提倡到戊戌变法的失败,从甲午海战的全军覆没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在体验了器物层、制度层、文化层的不足之后,五四时期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以‘启蒙’为指归的‘现代化诉求’上”[4],有识之士看到了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才是社会改造的根本任务和目的。于是,知识分子们纷纷通过文学来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呐喊”出“反传统”、“反礼教”的时代最强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五四文学涌现了一种文化启蒙的英雄主义。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祈望的“精神界之战士”实际上就是在呼唤文化启蒙英雄,他列举的代表此类“精神界之战士”的“摩罗诗人”都“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中国只有“群体的英雄”,少有“个人的英雄”,中国人大都消沉委顿,中国多的是迂腐的、故步自封的、追求名利的人。因此,鲁迅才会翘首以盼在中国能有“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以“援吾人出于荒寒者”[5]。
鲁迅所阐发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英雄理念在五四文学中得到了再好不过的落实,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既“表现在创作主体上”,也“升华为审美范畴作用于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3]前者指不论是文学革命的发起者胡适、陈独秀,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鲁迅,还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骨干,都可视为现代文化启蒙英雄。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那种冲决罗网、勇敢豪迈的英雄气魄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后者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涌现的一批闪光的文化启蒙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包括郭沫若诗篇中开辟洪荒、昂扬乐观的大我形象;鲁迅作品中洞悉传统文明凝固性、封建文化落后性起而反叛传统的先觉者;甚至在沈从文笔下也不乏对雄强、血性的讴歌,比如《虎雏》中不被城里人规训的虎雏,《龙朱》里高贵、热情、勇敢的白耳族王子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里信守诺言、诚诚恳恳,心爱之人自杀身亡后自己也尾随而去的豹子等。
英雄人物塑造的高潮始于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作品。这时,“对社会发展起规范作用的意识形态从多元并存变为一元独立,这就使转折期文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深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预。”[6]意识形态给文学设定了一系列“疆域”和“方向”,一切写作都被限定在特殊“疆域”里,不能越雷池一步,值得肯定和推广的便是符合所给定“方向”的创作。英雄主义文学同样如此,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甚至成了本时期文学的唯一受到鼓励的“方向”。
终于,英雄主义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此时,“三突出”的原则被规定为塑造人物形象的强制标准,由此产生了一大批“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其中,又以“革命样板戏”和浩然的小说为典型代表。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既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又具有纯粹的高尚的个人品格,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英雄形象。这样的英雄叙事彻底瓦解了现实中的英雄真相,使得英雄叙事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
另外,十七年时期英雄叙事的流行除了以上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与整个社会的强烈需求和作家本人的自觉意识有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重获新生,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人们打心眼里觉得幸福和感激。战争结束后,又面临着发展经济,提升生活水平的艰难任务。这就使得人们常常回首曾经的壮烈岁月和英雄们无私奉献、勇敢无畏的人格风采,既是缅怀也是一种激励。再者,市民社会本来就有强烈的任侠尚武、崇拜英雄情结,更何况是对于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战斗英雄,民众自然更加尊崇和喜爱。作为人民一分子的作家自然也不例外,这就使得作家们有着强烈的愿望用笔记录下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自然而然地,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要求被作家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不但不会犹疑,相反带着极大的热情投身写作之中,有时还会因为所写英雄人物不够完善而愧悔和自责。总而言之,十七年时期文学的英雄叙事样态可以说是政治命令、社会需求和作家自愿三者联动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反思极“左”政治思潮成了文学的主要内容,对理想主义“英雄神话”的全面解构应运而生。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直到后新时期名目繁多的文学样式中,英雄主义日渐凋零,各种“反英雄”、“祛英雄”的写作甚嚣尘上。
新写实作家们嘲弄英雄、拒绝崇高、推崇自然主义的创作风格,在日常性和世俗化的“烦恼人生”面前,“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普遍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厌弃,对激情和浪漫生活的拒绝,而无可奈何地认同于“一地鸡毛”似的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新写实小说摒除了任何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热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成为小说人物的主要信念。而刘震云、苏童、叶兆言等人的新历史小说则强调历史的“偶然性”、“破碎性”和“不确定性”。这些作家往往乐于以个人生活的卑微记忆,来解构“大历史观”下的“英雄神话”。而个人的记忆又是五光十色的、不可靠的,由此也就导致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历史的“文本化”——所谓历史,变成了每个个体心目中自由书写的文本。在新历史小说世界里,欲望强盛,暴力涌动,个体生存才是当务之急,才是最迫切的事,国家大义和民族尊严只能“靠边站”。革命英雄主义的人生观被新历史主义小说敲打得七零八碎。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市场化的消费型社会,文学艺术的后新时期到来了。后新时期文艺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作家和市场经济、文学和大众文化合谋。这是一个典型的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作“文化工业”的时代,“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祛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7]文学艺术也被整合进“文化工业”中,不再给“无意识崇拜留出任何地盘”,悲剧消失了,“虚假的个性”开始流行,文学艺术已经不再是纯精神产品,不再产生“轰动效应”,它更多的时候被普通读者和市场需求牵着鼻子走。正是在这样一个英雄渐行渐远的当口,我们遇见了《三体》,迎来了英雄主义的回归和变异。
二、“吃人”的冷酷英雄
刘慈欣和江晓原曾经做过一次有趣的对谈,谈话中刘慈欣假设有一天人类将面临巨大的灾难,这时是否可以在人们头脑里植入某种芯片,以便统一思想,更有效地对抗灾难,刘慈欣认为这是可行和必要的。继而刘慈欣指着为他们谈话做记录的女士问道:“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8]对此,刘慈欣同样作了肯定的回答。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极具启示性的设想和发问。《三体》中的英雄都面临着类似的终极抉择:《三体Ⅰ:地球往事》中从文革大创伤走过来的叶文洁对人类失望透顶,发现“人类文明已经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了”,可是该不该向外星文明发送信号,请求他们的力量来介入?《三体Ⅱ:黑暗森林》中的罗辑在太阳周围布下足以发布三体星系坐标的大量核弹,如果向太空发送咒语,引爆核弹,地球和三体都将毁灭,罗辑想以此为筹码阻止三体人的入侵,问题是这样道德吗?章北海为了保存人类文明,选择“背叛”,以至于要牺牲无辜的战友,怎么评价?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程心两次面对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选择,要么选择牺牲一部分人来挽救地球,要么选择所有人和地球同归于尽,选择哪些人去死,自己究竟应不应该导致“死亡面前的不平等”?
刘慈欣经常让笔下的人物置身于这类非此即彼、极其残酷的选择之中,是即使灭亡也不失去人性,还是为了生存而选择“兽性”?吃,还是不吃?这是一个相当折磨人的问题。
之所以这般残忍,是因为“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往小处说,这是科幻迷们很感兴趣的问题;往大处说,它可能关乎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9]。在刘慈欣的想象中,整个宇宙都遵循两条“宇宙社会学”的公理:“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10]由此衍生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前者指永远无法确定两个宇宙文明之间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宇宙文明处于无限延伸的猜疑链;后者指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技术爆炸,从而赶超原先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给对方带去威胁,这样又反过来强化了宇宙文明的“猜疑链”。于是,整个宇宙为了生存实际上便成了一种“黑暗森林”的状态:“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10]447
这样的“宇宙不是童话”,人类的历史尽管比较幸运,“文明出现以来,人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未面对过来自人类之外的能在短时间内灭绝全种族的灾难”[12]。但是,这并不等于人类能一直免遭这样的灭顶之灾,没人敢担保人类社会肯定会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于是,当地球面临外星文明的全面入侵时,为保卫我们的文明,必须得吃掉一些人才能挽救地球,“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是否还要继续嘲笑英雄主义呢?那时高喊人性和人权能救人类吗?”[11]于是,“吃”人的冷酷英雄便诞生了。
这群英雄和传统的慷慨激昂、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有别,他们少了一些高亢和热血,多了一些冷静和残忍。他们是不可以用道德的准则去评判的,“比较理智和公平的做法,是将英雄主义与道义区分开来,只将它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品质,一种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12]严锋称其为“超英雄”,他们的抉择关乎的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地球,而是整个宇宙。这是科幻文学,以至主流文学难得一见的人物形象,刘慈欣给了我们和文学一个机会,让我们和文学的目光再次宽阔起来。
三、自由伦理叙事下的圆形英雄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认为:“一个圆形人物务必给人以新奇感,必须令人信服。如果没有新奇感,便是扁平人物,如果缺乏说服力,他只能是伪装的圆形人物。”[13]以圆扁而论,十七年时期文学中的类型化人物是扁形的,只被“单向度”的社会赋予了“单向度”的思想。
反观《三体》,其中的英雄人物个性鲜明,复杂多样。叶文洁看透了人世险恶和人类文明的无望后,向三体发出求救信号,组织地球叛军,与整个人类为敌,似乎冰冷、残酷到了极点。但是从叶文洁在大兴安岭农家度过的半年时间来看,她的本质是善良的、温柔的,她与村民互敬互爱,相处得其乐融融,一切都是浓烈和温热的,但一切又都那么简单和平实,叶文洁本人也觉得“这段日子不像是属于自己的,仿佛是某片从别的人生中飘落的片段,像一片羽毛般飞入自己的生活”[14]221。当三体文明开始侵入地球,叶文洁也被逮捕,最后她来到“红岸遗址”缅怀此生。叶文洁置身于荒芜的峰顶,这个因对人类绝望而引入外来力量挽救地球的冷酷英雄,把目光集中到山下那个自己唯一有过美好记忆的小村庄。在“人类的落日”临近之时,我们发现只有叶文洁孤傲而圣洁,只有她有资格沐浴在“人类落日”的余晖中。
而罗辑本来只是一个浪荡的大学教授,他从叶文洁那儿了解到了宇宙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并提出科研选题申请。他原本只想哗众取宠,却引来了ETO的暗杀,阴差阳错地被选为“面壁者”,被寄予拯救世界的厚望。成为面壁者的罗辑并没有想拯救世界,而是利用面壁者的特权享受生活,还动用国际力量在现实世界中为他找到梦中情人。行星防御理事会的要挟以及萨伊的坦白使罗辑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开始思考这个宇宙,并建立了宇宙社会学,成为自己的破壁者,并最终延长了人类文明。
罗辑似乎有点像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中常见的那类成长型英雄,由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名英雄。但两类英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左翼或者抗战文学作品中的英雄的成长主要是指人物的精神逐渐走向纯洁,并且这个过程还被设定为是在党的引领下实现的(这些作品中党往往被具象化为长辈或者其他的革命者)。而罗辑尽管最后变得冷酷、理智、坚强,却并没有成为行星防御理事会的附庸,也没有舍弃自己的个性。他虽然接受了“面壁者”的身份,担负起了拯救人类的重任,但他一直清楚人类必败的命运,对于政治家借“民主”和“全人类”为口实,实则暗行不轨,他也心知肚明并敢于当面批评。“做一个普通人”一直都是罗辑的真实想法。罗辑后来以地球和三体同归于尽的结果要挟三体世界,而被人们看作魔鬼,但从他和史强的兄弟情深以及对于妻子庄颜的爱上,又展现了罗辑人性中的亮色。罗辑整个“成长”过程也并非是跟随某种思想亦步亦趋的结果,相反他始终和那些颐指气使的政治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程心是另一种英雄形象。在她身上更多地保留了东方女性的古典美以及母性的博爱之心,也正是因为她给人的美好形象,被选为接替罗辑的第二任执剑人。但正是由于心里的善意,程心在三体世界开始对地球进行进攻时没有按下威胁开关,该举动断绝了人类“生”的希望,直接导致澳大利亚大移民和地球治安军与反抗组织的产生。后来,她又说服维德放弃对太阳系联邦的抵抗,第二次断绝人类生的希望。叶文洁、章北海、罗辑甚至维德等人至少延续了人类文明或者提供了人类延续、改良的希望,而程心却两次亲手葬送了拯救人类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程心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罪人。但是,在人类灭亡的紧要关头,程心依然葆有坚定的善意和爱,这实则是另外一种英雄品质。正像刘慈欣借云天明之口说的那样:“人类世界选择了你,就是选择了用爱来对待生命和一切,尽管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实现了那个世界的愿望,实现了那里的价值观,你实现了她们的选择,你真的没有错。”[15]不管怎样,“爱是没有错的”,爱是伟大的。
总而言之,《三体》中的英雄人物不是像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那样被意识形态所规约、所扭曲,而是充满了人的丰富的个性,既有坚定的信念和超乎常人的胆识,也是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有自己的爱恨情仇,其思想性格中既有集体主义观念也有个性主义意识。
刘小枫认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是两种现代叙事伦理。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淹没了个人命运的独特性、丰富性,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与想象”,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它不受“历史圣哲设定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规约,而是由一个个具体偶在个体的生命事件构成的。[16]以此观之,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压抑下片面化发展,而《三体》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却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英雄主义色彩。
四、英雄受尽冷遇
叶文洁从人类的疯狂年代走来,目睹了亲人之间的背叛、师生之间的戕害和人性的极端黑暗,她对人类之恶进行理性思考后,陷入了恐惧的深渊:“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外来的力量。”[14]70于是,她“狠心”地向三体文明发出了求救信号:“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14]205
在某种意义上,这跟五四时期洞察到中国文明的落后性而求诸西方文明的文化启蒙英雄是相似的。他们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负面性”,并且“对于人类的负面,普通人并没有高级知识阶层那样全面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受现代科学和哲学影响较少,对自己所属物种本能的认同感仍占强势地位,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背叛,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知识精英们则不同,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早已站在人类之外思考问题了。”[14]205这指的是像叶文洁一样的人类“叛徒”。五四的文化启蒙英雄们与之相比,不过是站在民族之外来思考问题,然后对民族的负面有着“全面深刻的认识”,并将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背叛。
两者的“背叛”对象不同,但他们的立足点是一致的,即都是出于不满足和失望而“反叛”各自的对象,以求改造各自所“反叛”的对象。鲁迅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17]叶文洁仰望夜空感到“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里的偶然,宇宙是个空荡荡的大宫殿,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14]240。对于鲁迅而言,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传统文明不过是奴役的手段罢了,而对于叶文洁来说,人类的自大和盲目乐观不过是一种无知,如果站在宇宙的高度观察人类,我们只会茫然和战战兢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不抱希望……并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希望才赐予了我们”。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免遭“单向度”思维的同化。[18]
然而这类英雄最终却受尽冷遇。比如罗辑,“他在公众眼中的形象由一个救世主渐渐变成普通人,然后变成大骗子”。虽然还保留着“面壁者”的身份,但“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了”[10]455。最后,居民们甚至以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为由,“将罗辑驱逐出小区”[10]456。当他把执剑人的掌控权交给程心时,“人类不感谢罗辑”,反而指控他“犯有世界灭绝罪”,打算逮捕他。这样的例子《三体》里可谓多矣,除罗辑之外三个“面壁者”均不得好报,还有章北海、维德等也都有相似的遭遇。他们为了延续或者拯救地球文明,迫不得已成为选择“兽性”的冷酷英雄,然而,人类要么不理解他们,要么以“民主”和“道德”的名义审判他们,要么仅仅把他们当作工具,等到没有价值时,便一脚踢开。这和五四时期,特别是鲁迅笔下启蒙英雄的遭遇何其相似。
《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是典型的“旧轨道破坏者”,他发现了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吃人”的历史,他起而“诅咒吃人的人”,要“劝转吃人的人”[19];他窥见了人们内心的残酷,并和“心怀叵测”的父亲、哥哥、医生作对。《药》里的夏瑜则是勇于献身的启蒙英雄。他怀揣“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之理想,义无反顾投身拯救民族的启蒙革命之中,即便身陷囹圄,“还要劝牢头造反”,终至被杀头。然而,狂人却被人们视为“疯子”,在所谓“正常人”的谩骂、囚禁中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替大众谋求解放和正途的夏瑜在人们看来却是“发了疯了”,他流的血被愚昧的人们拿去治病。文化启蒙英雄,要么最后妥协了,要么到死也不被群众理解。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们都曾立志要战斗一番,可到头来一个像蚊子一样“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20],一个“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21]。鲁迅后来在《故事新编》里也塑造了悲剧性的启蒙英雄,比如女娲、后羿、眉间尺、墨子等,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从致力于启蒙大众、解救大众到被大众嫌弃的过程,英雄们的初衷和他们付出的辛劳与他们最终享受的待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就赋予了此类英雄人物深沉的悲凉感。
泰勒脑海中不时回想着一位即将出击的神风队员写给母亲的遗书上的一句话:“妈妈,我将变成一只萤火虫。”卡莱尔也将英雄比作萤火虫:“里希特尔说:苏门塔腊岛有一种‘发光的金龟子’,即大萤火虫,人们用叉子把它们串起来,用作夜间行路的照明。有身份的人很喜欢借这种令人愉快的光亮旅游。伟大的荣誉应归于这些萤火虫。但是——!——”[22]是啊,但是……人类只记住了这些先驱者作为“萤火虫”的实际作用,却忘记了自己对他们的误解与亏欠。《三体》中的英雄们就是现实世界中那些勇敢献身却不被理解者们的最好注解。
五、重拾丢失的英雄行囊
如前所述,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和后新时期名目繁多的文学样式中,英雄主义日渐凋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裹挟下,更多的文学是不痛不痒的、软性的轻松的文学,它们使人“作一刻的沉醉,然后随手一丢,便完全抛入遗忘里”[23]。文学作品犹如罐头吃完便丢掉一样,向读者提供的是一种消遣。虽然在军旅文学和史铁生等少数作家笔下还能见到英雄主义的苦苦支撑,但对于更多作家来说,不是对于英雄主义“避之唯恐不及”,转而关注庸俗人生的点点滴滴,就是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为英雄的标签,大玩特玩所谓“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醉心于表现世俗情怀和世俗欲望。
刘慈欣无疑对这种凡人大行其道的“非英雄化”写作现象感触颇深,所以他才会说:“现代主流文学进入了嘲弄英雄的时代,正如那句当代名言:‘太阳是一泡屎,月亮是一张擦屁股纸。’”[11]就是在这样一个英雄凋零,文学叙事变得越来越琐碎化、日常化、戏谑化的时代,刘慈欣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群久违了的英雄形象。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时代,不再需要英雄。《三体》里的政治家和民众们也是以所谓“民主”为理由歪曲、诬陷英雄的。悉尼·胡克认为,民主与英雄的主要矛盾是民主社会不能确保委派出去的权力是否会被英雄滥用。胡克主要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强调“道义所在应该是加强斗争”[2]169。胡克的意思绝不是让人们打压英雄,或者对英雄心怀畏惧,而是说要避免英雄发展为极权主义,民众应该随时保持理智。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英雄的向往已归寥落,拒绝崇高,逃避英雄成为整个社会的流行趋势。在文学作品里,虽然作家们手中玩弄着各式各样时新的技巧,乍一看,五光十色;但据此写出的人物却都一个个意气萧索,文学的精神天空灰蒙蒙的,细究之下,囧相毕露。
英雄绝非偶像,佩服与崇拜有别。英雄是指“伟大人格”,确切地说,“是永恒价值的代表者或实现者”。佩服是“佩服一个人唯一无二的特长……同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不发生密切关系”,而崇拜“乃是崇拜别人和自己所共同有的……真正的崇拜,就是自己的精神与崇拜对象的精神相交契”。如此,民主与英雄崇拜非但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因为,英雄崇拜让人们互相钦敬,互相尊重,这样会对社会的民主产生良性影响,但如果我们“都自己以为自己是英雄,不崇拜任何别的英雄,那么民主绝对不能推行”[24]。我们可以补充贺麟的观点说,假如每一个人,都视英雄若妖魔,不尊重和理解任何英雄,那么即便社会变得民主了也无非是“花手巾盖灯笼——表面好看里头空”。
我们不能为了保存对英雄的信仰和敬意而阻止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步伐,但公民意识的普遍崛起,非理性、享乐主义的风行,又毕竟让人怅然若失。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逆流而上”,重新捡拾起被人们遗弃的英雄主义行囊,就显得弥足珍贵。
六、结语
通过与近百年中国文学的三个主要阶段所展示出来的英雄形象——五四文学的文化启蒙英雄,十七年及“文革”文学的无产阶级“扁平”英雄以及后新时期文学的“反英雄”、“祛英雄”——的比照中,我们发现《三体》中的英雄主义和五四的启蒙英雄相比,站在整个宇宙的高度思考和行事,但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先觉者的大无畏精神和超前的眼光,并且他们的价值都没有被群众所认识和传承,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英雄和民众之间的隔阂,这使得这两类英雄身上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性;与十七年时期文学的无产阶级“扁平”英雄的“单向度”、“一体化”、“概念化”、“漫画化”有别,《三体》中的英雄主义可以说是“多向度”的、“丰富”的和“圆形”的;而相较于后新时期整个文学的“反英雄”、“祛英雄”潮流来说,刘慈欣的《三体》更显珍贵,因为他逆流而上,重拾被我们丢弃的英雄行囊,在英雄消失的地方,凭一己之力,让英雄重新崛起。总之,《三体》中的英雄主义是久违的英雄的回归,同时,和百年中国文学的英雄叙事相比,它也有所变异。刘慈欣不同意赋予科幻文学某种使命。“他‘就是想讲个好故事’,既不是要针砭时事,也没想过要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可不论自觉与否,他的《三体》确实做了很多主流文学该做、想做而没有做或做不到的事。“科幻是种类型文学,科幻这种类型文学能讲出其他类型文学讲不出的故事”[25],刘慈欣如是说。刘慈欣在《三体》中对英雄主义“瞥上”的这一眼,就足以让我们感动。
[1]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1.
[2]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M].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7.169.
[3]朱德发,等.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93.
[4]刘忠.英雄·白痴·土匪——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之二[J].文艺评论,2002(4):23-31.
[5]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2.
[6]朱德发.晚清至“五四”:新文学“英雄理念”的嬗变与钩沉[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26(4):1-7.
[7]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1-122.
[8]王艳.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刘慈欣VS江晓原[J].新发现,2007(11):84-91.
[9]刘慈欣.三体Ⅰ:“地球往事”三部曲之一·后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00.
[10]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41.
[11]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J].科普研究,2011,6(3):64-69.
[12]严锋.创世与灭寂[J].南方文坛,2011(5):73-77.
[13]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68.
[14]刘慈欣.三体Ⅰ:“地球往事”三部曲之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221.
[15]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485-486.
[1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7.
[17]鲁迅.灯下漫笔[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8.
[18]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03.
[19]鲁迅.呐喊[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0.
[20]鲁迅.彷徨[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
[21]鲁迅.孤独者[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3.
[22]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M].周祖达,张自谋,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19.
[23]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M]∥叶维廉文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200.
[24]贺麟.文化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6-77.
[25]刘慈欣:让我们仰望星空吧[N].南方人物周刊,2011-05-09.
[责任编辑于湘]
2015-12-14
高强(1994- ),男,重庆彭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I206.7
A
1008-6390(2016)04-00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