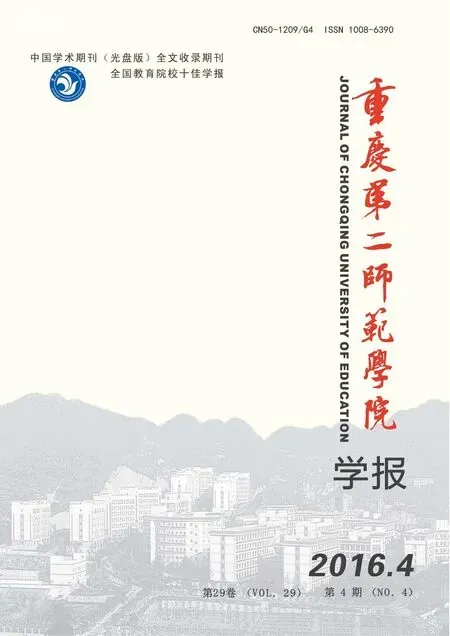高尔斯华绥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
高壮丽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高尔斯华绥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
高壮丽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传入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译介及研究深受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梳理其在国内的译介及研究状况,探讨影响译介的成因、译介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以及推动翻译作品接受与影响的因素。
高尔斯华绥;译介;研究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是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17部长篇小说,27个剧本,以及12本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书信集,并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高氏的译介及研究曾盛极一时,其戏剧《银匣》《争斗》《法网》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高尔斯华绥与萧伯纳、康拉德、威尔斯同时代,然而相比于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热烈而持久的关注来说,高氏可谓“怀才不遇”。对高尔斯华绥的研究存在许多问题,对其作品的关注和分析不够全面,至今都没有一部评论专著。高尔斯华绥对现实主义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梳理其在国内的译介及研究状况,探讨影响译介的成因、译介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以及推动翻译作品接受与影响的因素,以引起学术界对高尔斯华绥的进一步关注。
一、高尔斯华绥在中国的译介史
翻译是了解一个外国作家的第一步,而要有更深入的了解就必须熟知其译介史。高尔斯华绥在中国的译介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到1966年,1978年至今。1966年到1978年,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导致高尔斯华绥的译介出现了空白,故此段时间不计。
(一)“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成立
我国的现代文学翻译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涌现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文学社团组织。爱国文人们既积极地进行文学创作又热衷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进新思想,创造新文学。正如郑振铎在《文学丛谈》 里所说的:“想在新中国创造新文学……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国,取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学始可以有发达的希望。我们从事新文学者实不可放弃了这介绍的任务。”[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文学经典被引入国门。陈大悲是我国翻译高尔斯华绥作品的先驱。他于1920年3月翻译了高尔斯华绥(时译高斯倭绥)的《银盒》(TheSilverBox),并连载于1920年《戏剧》第一卷第一期、第三期和第五期。由此可见,高尔斯华绥是以戏剧家的身份传入我国的。1923年8月和9月,《晨报副刊》连载陈大悲译的《忠友》(Loyalties)和《有家室的人》(AFamilyMan)。1922年,邓演存翻译《长子》(TheElderSon)并刊登在文学研究会编印的《文学研究丛书》上。1925年,顾仲彝改译《相鼠有皮》(TheSkinGame)。1926年到1927年,郭沫若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先后翻译了《争斗》(Strife)、《银匣》(TheSliverBox)、《法网》(Justice)三部戏剧。之后,谢焕邦重译《争斗》。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席涤尘与赵宋庆合译的《鸽和轻梦》(ThePigeon,TheLittleDream)。1930年,朱复翻译《群众》(TheMob);1933年,蒋东岑重译《群众》。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向培良译的《逃亡》(TheEscape)。194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方安、史国纲译的《正义》。以上简略所列的都是读者熟知的作品,还有许多其他译本,不一一赘述。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高尔斯华绥的戏剧译本在中国有22种,涉及12个剧本。
高尔斯华绥小说的翻译几乎是与戏剧翻译同步的。早在1923年,《东方杂志》便刊登了子贻译的《质地》(Quality),之后又陆续刊登了《迂士录》(TheManWhoKeptHisFarm,傅东华译),《小人物》(TheLittleMan,万曼译)等短篇小说。1932年,高尔斯华绥凭小说TheManofProperty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国内对其作品的翻译更加热衷了。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光健选译的《置产人》(TheManofProperty)(第一部曲)。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实味的全译本《资产家》(TheProperty)。1948年,骆驼书店出版了罗稷南的全译本《有产者》(TheManofProperty)。这一时期,在翻译高氏代表作的同时,其短篇小说及散文的翻译也在持续不断进行着。
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高氏作品在中国大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呼吁通过改革来改变社会现状,他是受压迫者的“代言人”,这与当时的中国国情不谋而合,因此,广受文人志士的推崇。
(二)1949年到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国文学翻译步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文艺界遵循党的方针,积极发扬“五四”新文化传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期间,对高尔斯华绥作品的译介也更加准确全面了。1951年3月,三联书店再版了罗稷南的《有产者》。周煦良全译了《福尔塞世家》(TheForsyteSaga)的三部曲。1958年6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有产业的人》;1961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骑虎》(InChancery);1963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三部《出租》(ToLet)。沈长钺翻译了《高尔斯华绥短篇小说集》,其中收集了《品质》《勇气》《良心》等短篇小说,并于1957年6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岛国的法利赛人》(TheIslandPharisees)是高尔斯华绥于1904年发表的一部重要作品,正是这部作品引起了英国文学界对他的关注。余牧、诸葛霖合译了该书,并于1959年12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徐燕谋注释翻译的《斗争》。汪倜然翻译了高氏第二个三部曲《现代喜剧》(AModernComedy)的前两部,1958年6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白猿》(TheWhiteMonkey);1961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银匙》(TheSilverSpoon)。而高尔斯华绥的第三个三部曲《尾声》(TheEnd)中只有第二部《开花的原野》(FloweringWilderness)译成了中文,译者为李葆真,1958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
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国内对高尔斯华绥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小说上,而对戏剧的翻译只有徐燕谋所注释的《斗争》。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当时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学界仍然发扬“五四”传统,不断翻译外国作品,引进新的思想,但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扩大,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被定义为鼓吹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的“大毒草”。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禁戏,甚至连《雷雨》《日出》等剧也被认为是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2]在这种情况下,高尔斯华绥的戏剧自然成为了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潘绍中在对剧本《最前的与最后的》(TheFirstandLast)进行现实主义分析的过程中指出,高尔斯华绥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是服务于他所企图“改良”和维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应该让学生认清这一外语学习材料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毒素。[3]在当时,这篇文章几乎可以说是宣告了与高尔斯华绥的彻底决裂,因此,对高氏戏剧翻译数量少也就不难想象了。
(三)1978年至今
1976年10月以后,许多出版社又陆续恢复出版外国文学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千零一夜》《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希腊神话和传说》等几部与意识形态相去较远的作品,从而再次开创了外国文学翻译的新局面。[4]此时外国文学的新译作很少,出版社“无米下锅”,大多都是再版以前的译作,对于高氏的作品也不例外。1978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周煦良译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接下来的几年内,余杰重译了《岛国的法尔赛人》,并于1983年9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友爱》(Fraternity)是高尔斯华绥早期的优秀作品之一,曹庸翻译了该作品,并于1985年6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冠商译的《白猿》,之后一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汪倜然译的《白猿》。由此可见,我国译界从荒芜状态重新走向“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根据孙致礼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一书中的统计[5],1978年至2008年,我国共翻译了23部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其中小说、散文居多,而戏剧只有裘因译的《银烟盒案件》以及张文郁与周锡山重译的《最前的与最后的》。2009年至今,翻译出版较多的是高尔斯华绥的散文与短篇小说。2015年7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婷婷和曹丽合译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系:福尔赛世家(全三册)》。
虽然1978年至今,我国政治思想自由,翻译文学迅速发展,但与其他同时期知名作家(如萧伯纳、康拉德,美国的德莱赛、杰克·伦敦等)相比,高尔斯华绥的作品所受的关注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他的戏剧,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高尔斯华绥的研究状况
高尔斯华绥既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鉴于以上对其译介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国内对高氏作品的研究。
(一)戏剧研究
“五四”时期,高氏剧作一经引入中国便引起了阵阵热潮,为中国戏剧创作带来了积极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高氏剧作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作者和部分剧情的介绍上,[2]研究成果多体现在译者为原作所写的序或前言里。戏剧家陈大悲、郭沫若、向培良、曹禺等均就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发表过各自的看法。在《银匣》的序言中,陈大悲不仅详细介绍并分析了该剧剧情及人物特点,而且还就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普遍问题做出了回答,推动了中国戏剧的进一步发展。在《争斗》的序言中,郭沫若指出,高尔斯华绥是一个写实的剧作家,他在剧作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自然地凸显了社会矛盾,如实地反映了弱者在社会中受压迫的困境,希望由此能给“一般的人类指出一条改造社会的路径”。[6]向培良为《逃亡》所作的序言里详细评价了高氏剧作,并认为《逃亡》打破了传统的三幕或四幕剧的分幕法,除序幕外共有九个场面,这是“技巧上的一大改革”,使结构更加自由而真实。[7]此外,这一时期的杂志如《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也刊登了不少学者对高氏剧作的研究成果。1924年,余上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读高斯倭绥的〈公道〉》,借戏剧中的“公道”抨击了当时黑暗腐朽的法律制度,并评价该剧人物“平庸”、故事“平庸”、取材“平庸”,但平庸的现实却给人强烈的震撼,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现实。[8]张嘉铸的《货真价实的高斯倭绥》全面分析了高氏剧作的特点,在他的剧作中“没有一点伤情分子,也不用许多的动作,冲动刺激,普通的跌宕,或者那种well-made戏剧的种种巧计……亦不用诙谐的对语,长篇的讲演……他的戏剧有一种极妙的抑制同描写周到的洁白”,“在舞台的灯影底下加添了许多可爱的和我们一样的人”。[9]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成果是傅东华写的《戏剧庸言》,其中记录了高尔斯华绥的戏剧观及创作观,为中国戏剧发展做出了贡献。
20世纪40年代,国内对高尔斯华绥剧作的研究主要沿袭前人的步伐,没有太大创新性突破。建国后,随着国内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高尔斯华绥因其在作品中展现出的阶级倾向,招致了较多批判,对其戏剧的研究也大多是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如潘绍中的《剧本〈最前的和最后的〉的现实主义意义及其思想局限》,对高氏剧作研究影响巨大。1978年以后,虽然国内兴起了各种文艺思潮,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文献资料显示,高氏剧作研究仍然是被忽略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国内剧作家及评论家忙于吸收荒诞派、复调理论、残酷戏剧等欧美新型戏剧理论,希望以此来弥补舞台空白,从而冷落了对高氏戏剧的进一步研究。1986年,周锡山的《高尔斯华绥和他的〈最前的和最后的〉》详细分析并评述了《最前的和最后的》一剧,并对高尔斯华绥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与萧伯纳一起,为英国剧坛继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二次具有世界意义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0]秦文的《疏离·客观·公正》不仅深入分析了高尔斯华绥独特的戏剧创作手法,而且还指出高氏为社会问题剧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11]这些分析改变了以往从阶级意识形态角度分析高氏剧作的路径,转而开始关注其中的具体元素,并对剧作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虽然这些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但学术界对高氏作品的研究依然寥寥。
综上所述,高氏剧作的研究与翻译一样,在民国时期达到了巅峰,此后一直呈下滑趋势,而且对其剧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银匣》《公道》《斗争》《最前的和最后的》等几部熟知的剧作上,对其他剧作的关注度不够。此外,从新角度、利用现代文学理论探索高氏剧作新意方面也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二)小说研究
早期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在中国是受人反对的,其原因有二:第一,他把文学当成了宣传自己道德观念的工具,作品充满讽刺色彩;第二,他的叙事不够刚强与决断,对社会的批判总是被他的悲悯与同情所掩护。但是刘奇峰于1929年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一文中对高氏小说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他的描写尤为精美”,“关于家庭制度及社会秩序,高尔斯华绥有深刻的观察与研究……那些家庭经他一描写,就如有血有肉的人物所代表的家庭”[12]。这一论断扭转了以往遭受反对的局面,引起了高氏小说研究的浪潮。1932年,高尔斯华绥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小说月报》《大夏期刊》《新中华》等杂志又陆续刊登了《高尔斯华绥自述创作过程》《高尔斯华绥评传》《高尔斯华绥遗稿》等有关高氏研究的文章。1936年,刘荣恩根据H.V.Marrot所写的TheLifeandLettersofJohnGalsworthy写下了《高尔斯华绥书信传记》一文,从不同侧面剖析了高尔斯华绥的文学观及创作观,为高氏小说及戏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内高氏小说的研究也渐渐走向低谷。20世纪80年代,“书荒”之后国门再次打开,文艺界迫切吸收西方新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同时对高氏小说的研究也开始扭转视角,就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探究。1986年,邵旭东在《在传统与现代派之间——论高尔斯华绥小说创作的革新意义》一文中重新审视了高氏的文学地位,认为虽然高尔斯华绥反对现代派,认为现代派是“不认识亲生父亲”的文学传统,但在他的创作中依然借鉴了现代派的技巧和手法,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做出了革新,使现实主义文学过渡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段。[13]同年,石璞在《论〈福尔赛世家〉》一文中从修辞及人物特点等方面细致地剖析了该部巨作的艺术特色,并给出了客观中肯的评价。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尔斯华绥又继续遭到了文学评论家们的忽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逐渐自由化、开放化,国内西方文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阐释和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关高尔斯华绥的研究也就成为凤毛麟角。
三、问题与反思
回顾近百年来高尔斯华绥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总体来看,对高氏作品的研究视线过于集中,关注《福尔赛世家》《银匣》《斗争》《法网》《最前的与最后的》较多,而对其他优秀作品如《岛国的法尔赛人》等关注不够。其次,对高氏作品研究的角度陈旧。尽管20世纪文艺思潮多元化,但对高氏作品的研究还是习惯性地从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析。再次,受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民国以后,高氏作品研究一直遭受冷遇,即使是现在,有关高尔斯华绥的研究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评论一个作家及作品要看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14]处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变迁期,高尔斯华绥不仅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对中国戏剧、小说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高尔斯华绥的文学艺术不是对后世毫无影响的,他的描写既不矫揉造作,也没有使用夸张性语言,却塑造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同时代的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密友阿诺德·本纳特(Arnold Bennett)曾盛赞《福尔赛世家》,认为“福尔赛太普遍了,我们都是福尔赛”[15]。毫无疑问,这说明了高尔斯华绥是真正的一流作家。他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道德精神及人文主义关怀对当下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还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因此,对高尔斯华绥进行深度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郑振铎.文学丛谈[J].小说月报,1921(12).
[2]黄晶.高尔斯华绥戏剧中国百年传播之考察与分析[J].学术探索,2014(11):103-108.
[3]潘绍中.剧本《最前的与最后的》的现实主义意义及其思想局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64(2):50-53.
[4]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5]孙致礼.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6]高尔斯华绥.争斗[M].郭沫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7]高尔斯华绥.逃亡[M].向培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8]余上沅.读高斯倭绥的“公道”[J].晨报副刊,1923(5):2-3.
[9]张嘉铸.货真价实的高斯倭绥[J].晨报副刊(剧刊),1926(6):14-15.
[10]周锡山.高尔斯华绥和他的《最前的和最后的》[J].名作欣赏,1986(1):89-90.
[11]秦文.疏离·客观·公正——高尔斯华绥戏剧创作探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111-114.
[12]刘奇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J].晨钟汇刊,1929(224):1.
[13]邵旭东.在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论高尔斯华绥小说创作的革新意义[J].外国文学研究,1986(2):80-86.
[14]毛敏诸.论高尔斯华绥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J].外国语,1987(2):34-37.
[15]Gindin.J.J.JohnGalsworthy’sLifeandArt:AnAlien’sFortress[M].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87.
[责任编辑亦筱]
2016-03-07
高壮丽(1989- ),女,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
H315.9
A
1008-6390(2016)04-007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