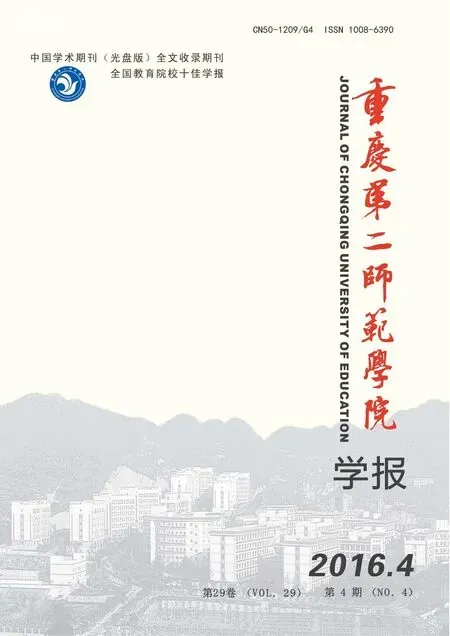孟子人性论的四个维度
任鹏程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孟子人性论的四个维度
任鹏程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人性论是孟子哲学的理论基石。孟子所见,人性生而有之,“性”不仅仅指涉“欲性”,“四端之心”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四端之心人人皆有,与生俱来,亦是善性之原,扩而充之,即为仁义礼智。人人皆有善端,君王亦是如此。孟子不辞劳苦宣扬其说,最终目的即是凭借君王之心推广王道政治,实现解救民众于水火的夙愿。换言之,仁政即是孟子性说的最终理论目的和现实归宿。
孟子;欲性;四端;扩充;仁政
人性问题的探讨可谓是中国哲学领域亘古长青的话题。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1] 2而在儒家哲学之中,孟子人性论则一直是历代大儒品读不厌的重要内容,其思想被后人简单概括为“性善论”。诚如《孟子·滕文公上》开篇即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千百年来,“性善论”一直受到儒家学者的推崇和厚爱。对此,现代学者又有“人性向善”[2]4、“性可善”[3]96之说,并有学者从多维度对“性善论”作出解读。[4]16-25然而,我们发现,以往学者的论说多源发于“人之异于禽兽者”这个角度。本文则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试图从欲性、四端、扩充、仁政这四个方面对孟子人性论进行探讨和诠释,进而揭示孟子性论与其整个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关联。
一、性即生之初
“性”字,许慎《说文》曰:“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5]217在古人看来,“性”字从“心”,心之本义乃是指心脏,即血肉之心。诚如中医文献《黄帝内经·素问》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可见,古人认为,心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黄帝内经·宣明五气》云:“心主脉。”众所周知,“脉”即血液流动的通道,中医采用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切”就是号脉,脉搏的跳动是生命的象征。我们通过把脉感知血液是否流动从而断定人之生死存亡。性从心,心主生,故,性即生。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早期古人对于“性”问题的探讨,是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贤哲认为,我们生活的场所都被视为一个有生命的世界。诚如《周易系辞·下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万物繁育被先哲们视为宇宙的基本特征,“生”是万物存在的本原依据,或者说是存在的事实基础。故,告子曰“生之谓性”,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董仲舒曰“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王充曰“性,生而然者也”,《白虎通·情性》曰“性者,生也”,韩愈《原性》曰“性也者,与生俱生也”。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学者们对于何为“性”,或者说,对“性”的基本意义已有共识,即“性”只是相对于“生”而言,它是生而有之,自然禀赋,绝非外来者,亦非后天学习所获得。故,现代学者梁涛对此说:“即生言性乃是古人论性的一大传统。”[6]155
孟子论性亦不排斥这一立场和观点。他说:“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上》)他认为肢体和容貌是天生就有,此即“天性”。这种言论显然是从先天性的角度对何为人性发表见解。孟子又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自从人出生以后,嘴巴就会喜欢美味的食物,耳朵就会喜欢美妙的声音,鼻子就会喜欢芬芳的香味,身体就会喜欢舒适的环境,人之感官的这些喜好都属于天生固有,与生俱来,不能改变。或者说,生理感官欲望是人出生后本来的面貌,人生之初的原始状态。故,徐复观曾有“性之原义,应指人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而言,犹如今日所说之‘本能’”[1]6的论断。
观览《孟子》文本,孟子并不排斥人类的感官之欲,相反,他认同人们有普遍的、共同的物质生理欲望。例如他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认为针对常人而言,丰厚的物质条件才是为善的基础和前提。并且,他认为人有好利之心,其言曰:“欲贵者,人心之所同也。”(《孟子·告子上》)显然,在孟子看来,普通人的生理欲望等都是生来就有的,并非外来,不可除去。故,他倡导“寡欲”而非“绝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 尽心下》)进而言之,孟子并没有明确地反对把欲望之性视为人之属性和特征。所以,我们说孟子之“性”并未完全脱离“性”是人生之初的自然倾向这一层内涵。然而,问题在于,虽然欲望之性是人生而有之,如果以此规定人性,就会出现牛马之性与人性相互混同的局面,也就是说人即禽兽豺狼。
对此,先秦学者告子和孟子之间曾有过“人禽之辨”的争论:“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此段文献告诉我们:孟子虽然并不明确否定“生之谓性”的命题,但是简单地把食色之欲视为人性的做法,无异于是“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孟子·告子上》)这种局面又是他所不愿看到的。故,他试图在“即生言性”的基础上找寻人和动物相区别的东西,或者说,从规定性或主宰性的角度探求人性的基本内涵。[7]108-115
二、性即生之质
如前文所言,先秦之际以“生之自然者”为“性”成为思想家们的共识。“生之谓性”又称之为自然人性论,自然之资即指感官欲望或本能。但孟子的贡献在于试图从质的角度为人性寻找一种普遍性依据,这也是孟子对儒家哲学的创新和转换。西方哲学对概念的定义的基本模式即“种加属差”。例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首先肯定人是动物的一种,在此基础上又把理性视为人之独有,并以此区别人兽。理性不仅是人作为动物概念的属差,而且是人的本质特征,故而西方哲学历来都把人之实践看作理性指导下的行为。
黑格尔说:“某物之所以是某物是由于其质,且失去了其质,某物就不成其为某物。”[8]313“质”即事物的本质属性,或曰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孟子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非兽,肯定有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或属性。或者说,他之所以不太欣赏“生之谓性”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这种看法仅仅指出某物之所有,而非某物之所是。它充其量表现了同一‘类’(genus)中各物之所‘同’,而非各物之所‘异’。为了界定一物,必须知其本质,亦即‘类’加上‘种差’(difference of species)”[9]55。进而言之,“生之谓性”并不能凸显人兽之异、人之高贵、人之尊爵,孟子论性并不仅仅指涉人生之初的自然倾向,他还试图为“人性”这一概念作出自己的创造性注解,即人性所涵括的是一种人之为人的规定,或曰人性是人的主宰,存之是人,舍之非人。故,现代学者沈顺福说:“从孟子开始,性便有了性质的属性。”[7]108-115
孟子有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孟子的论证,四端之心的由来就像人之四肢的长出,自然而然,天生如此,绝非外来,故仁义礼智等非由外铄,皆由四端长出。四端之心就是仁义礼智之本,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者。存之即人,舍之即兽。故,朱熹注曰:“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进而言之,孟子创造性地把“四端之心”融入人生之初的本来面貌,认为“四端之心”是人之初生之时的自然状态,即人性。四端之心,操之在己,无此四端,非人也,换言之,孟子认为,“四端”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者或曰主宰。
人性的基本内容即“四端”,善性品德皆由其生出,故,“四端之心”又可称之为构成人性的材料、材质。材料即“才”,“才”字,《说文》曰:“艸木之初也。”[5]15其本意为草木之初,草木的最初状态就是嫩芽,它是构成草木生命的发端或曰起点。对人而言,“四端之心”是做人为善的基础和依据,诚如程伊川所言:“才是一个为善之资,譬如作一器械,须是有器械材料,方可为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孟子向来以“性善之说”而闻名,“性”之所以为善正因为其构成材料(四端之质)或起点是好的。“言才则性见,言性则才见。”[10]39才、性不可分离,四端之心即性之本原,故,性无不善。所以二程对此说:“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以此逻辑推论,情即性的展开,由性而生的情亦无不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孟子·告子上》)故,东汉学者赵岐对此注曰:“性与情相为表里。性善胜情,情则从之。”孟子又云:“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故,才,或者说性,不仅是人生存的起点,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且也是人类美好品德的基础和根本。“为恶作乱”乃是陷溺其心,或者说,是“固有之材”丧失其养的缘故。①
总而言之,孟子之性即人之本质。构成人性的基本材料(“才”)即四端之心。性的展开即情,从本原上而言,性善则情无不善。性、情、才与四端之心名称虽殊,然而意义相近,用法相同,都旨在描绘人性之初的本来面貌,并从人自身存在的道德价值角度来说明人类作为一个生命体存活的本质意义之所在。
三、性贵在操行
孟子认为,人人皆有善性之端,故而曰:人性本善。就成圣的基础而言,人人皆可以成就其善性,皆可为尧舜。德性养成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故而他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的功夫,认为人之善性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犹如孔子所说的“操则存,舍则亡”。在肯定人人皆有先天善性四端的前提下,孟子更加强调后天扩充对成人的价值与意义。按照孟子的逻辑,养其善端,顺其自性便可达到圣人的境界,即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人人皆有成善的基础和条件,但不等同于人人皆可成善。同时,孟子也从来没有断言“四端”都能够发展成为“四德”。相反,他多次提醒人们,要精心呵护这些娇嫩的萌芽,使之茁壮成长,而不能掉以轻心,致其枯萎殆尽。他曾以“荑稗与五谷”两种作物喻之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善端”只是人性的材料或曰起点,后天的精心照料和涵养才是成就人性的关键所在。让我们试看孟子的另一段话语:“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人性之善,人格之美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涵养之路,绝非一朝一夕之力可为之。完善人性,从而完美人生,万万不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孟子·告子上》)人性之端只有在道德修养发挥适当的状况下方能发展为人性之善,如果人性向善之路被阻滞或闭塞,那么人性最终是无法至于善的。
究其原由,乃是因为在德性养成过程中极易出现“失其本心”或者说是“陷溺其心”的状况,孟子称之为“放心”。而从其“小体”是“放其本心”的缘由,“小体”即是人的耳目等感官之欲,亦可以引申为外界的诱惑。人心易受外界干扰和诱惑,不义之举由此产生。孟子批评了这种行为:“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孟子·告子上》)他进而倡导“寡欲”以“求放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寡欲的实质在于杜绝人为和主观刻意,使人之言行皆顺由本性。人之本性体现在天生之心或曰原初之心,即四端之心。四端之心要时常操练、践行。否则,道德的沦丧、争夺与混乱的局面就会随之而来。
孟子进而认为,尧舜等先贤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将人之“几希”保存下来,听到善言,见到善行,便自然而然地去做。“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这是德性修养的最高水准,亦是人性圆满的彰显。视听言动的产生皆源于人的本真情感的流露,毫无功利目的,这无须学习就能习得,不用思考就能产生,犹如孟子所称的良知、良能。孟子又言:“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朱熹注曰:“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人之趋善,就像水流向低处流,野兽向旷野奔跑,皆是其本性使然。与此逻辑相同,人民向往仁德,也是其本性所决定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人之向善行善是自然而然的行为,绝非思虑或刻意为之,更要杜绝勉强、做作。人与生俱来赋有善的“四端”,顺着或依从别于禽兽的“善端”自然而行,方能成德成圣。
孟子认为,人与圣人皆是同类,圣人并非常人遥不可及,“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尧舜是做人之典范,“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故而道德涵养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言行举止皆效法尧舜,“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此即言,成人之道要杜绝思维逻辑、勉强行事等刻意行径。善性之端我本固有,德性成就是人人能为、人人可为的。做人只要任其天然,扩而充之即可。总而言之,率性自然即孟子信奉的做人信条。故,二程曰:“无我,则圣人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
四、仁政即性的归宿
孟子认为,人性即人之“善端”。扩充善端,顺其本性,养成善性即人之生存的意义。
然而,尽管孟子不辞劳苦地对人们进行说教,仍然有一部分人不仅不能养成善端,而且还为恶作乱,扰乱社会的安稳。因而,王道政治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家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谋求全民的福祉,而全民的真正福祉即人人的向善本性可以得以充分实现。政治的一切措施莫不着眼于此,必须使人的形体生命不虞匮乏,而专务于道德修为。”[9]146孟子倡导道德教育,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怀和儒者积极入世的传统精神。他主张依靠君王的仁义之心,教导民众,改善风气,以此成就良好的社会秩序。总而言之,仁政即孟子性论的最终理论目的和现实归宿。
孟子认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者或规定性。换言之,人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在人群之中具有普遍的相似性。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所以对于君王而言,亦存有此善性之质或四端之心,四端之心为仁义礼智之原,或曰人性之本,符合仁义礼智等善行皆系由心所生。孟子云:“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君子言行高尚、举止文明正是由于他们的内心充盈着人性之善端的缘故,内心美好的人性毫无遮拦地体现在言行举止上。以此逻辑推论,属于人的君王亦是如此。针对齐宣王“以羊易牛”而祭祀的行为,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齐宣王正是因为存有恻隐之心的缘故,看到将要用来祭祀的牛不停地打哆嗦,故而心生怜悯之情,才会产生有“以羊易牛”之举。这与“孺子将入于井而救之”的原因同出一源,此类行为之所以呈现完全源于毫无功利目的、本真的心理情感流露,亦即人之善性之使然。
此等善心或曰本性也是推行仁政的基础,故而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君王将此等不忍人之心推之于天下,即可实现王道政治,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那么,如何教导民众使之向善呢?
首先,孟子强调,为政者自身要有仁爱之心,仁而得民。《孟子·离娄上》云:“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王先要端正其心,摒弃杂念和私欲,这是国治邦定的起点和基础。诚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君王的行为会对臣子和民众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君王如果践行良知,操守本心,涵养善端,以身作则,化育人民,如此,民亦从之。久之,淳朴的社会风气才会形成。反之,君王如果肆意横行,贪得无厌,鱼肉人民,长此以往则会出现暴乱和争夺等不良局面。在孟子心中,尧舜正是施政和做人的典范,为政者要以尧舜等圣贤为楷模,应事接物无不以心灵内在仁义处之。久之,自然形之于外,犹如江河之决堤,气质会有所变化。如此,民众定会从善如流。
其次,孟子主张推行富民保民经济思想。针对当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民众·梁惠王上》)的社会局面,孟子认为,作为国君,必须使老百姓有耕地、住宅等恒产,安居乐业,尽力农桑,丰衣足食,养生送终,死而无憾。具体的措施是:“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孟子并非一味地否定人的欲性,对于民众或常人而言,欲望的满足是其为善的前提条件。同时,孟子指出,保民富民应该“勿夺民时”和“不违农时”。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君王采取了富民方案,实行了王道之策,如此就可以安定天下。所以他多次声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最终,他得出结论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再次,孟子倡导君王应该设置教育机构,化育民众。孟子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所以他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教育民众的目的就在于明人伦,即让民众知晓人类生活的基本伦理关系。这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常人容易受到感官欲望的诱惑和干扰,日日伐之“善端”而不知养,易而蒙蔽心灵,结果沦为禽兽豺狼。先贤圣人设置教育机构的目的就是让人类知晓其自身本来就有善性的种子,不必外求。常人之“学”依孟子所言就是求其放心而已矣。人人都具备善性的萌芽和内在的知识(良知、良能),学习无非就是提摄本心,时时刻刻践行之。针对现实利益与仁义之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的局面,孟子开出的药方是:“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即是说,彻底放弃现实利益,率性而为,任由先天仁义之端的呈现。
五、结语
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向来以性善论而闻名于世。首先,孟子并未否认“欲性”是人的基本属性和特征,欲性等生理特征自然禀赋,它是人出生后本然之状态,不可除去。故,“孟子亦不否定人们的生理物质欲望为人性的内涵。”[3]79其次,孟子对传统“生之谓性”的自然人性论观点进行了再造和转化,试图从质(或特殊性)的角度和层面对人性做规定,提出“四端”说。四端之心生而有之,不仅是人性的基本内容,而且是人性的决定者。再次,孟子论性贵在扩而充之,涵养本原或曰人心。故,做人的关键在于顺由本性,杜绝人为、刻意、思虑、狡诈等。②久之,善端必然长出仁义礼智等善性品德。
然而,孟子之时,礼乐崩坏,战火纷飞,民众疾苦,诚如《孟子正义卷一·孟子题辞》曰:“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有感于此,孟子倡导“四端之心”人人皆有之说,拯救时弊,论证君王亦有善性之心,君王之心推而广之,启迪民心,使之富有,化育民众,使之向善则成了其不辞劳苦宣扬自家之言的心灵支撑。故我们说,孟子性说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试图为理想王道政治的实现找寻合法的理论依据。
总而言之,孟子人性论的四个维度层层递进,它们共同构成了孟子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性善之说不仅促进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信任,而且使人看到自身伦理价值和实现完美道德的希望。这也是千百年来儒者孜孜不倦地把孟子性说奉为圭臬的秘密所在。
注释:
①《朱子语类·性理一·人物之性气质之性》曰:“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初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
②《朱子语类·学六·持守》曰:“今说性善。一日之间,动多少思虑,萌多少计较,如何得善!”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2]傅佩荣.解读孟子[M].上海:三联书店,2007.
[3]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赵法生.孟子性善论的多维解读[J].孔子研究,2007(6):16-25.
[5]许慎.说文解字[M].徐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63.
[6]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沈顺福.试论中国早期儒家的人性内涵——兼评“性朴论”[J].社会科学,2015(8):108-115.
[8]黑格尔.小逻辑[M].黄昀,常培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傅佩荣.儒家哲学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何文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1.
[责任编辑文川]
2016-03-0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儒家哲学基本问题研究及其现代意义”(15CWHJ15)
任鹏程(1990- ),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家哲学。
B222.5
A
1008-6390(2016)04-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