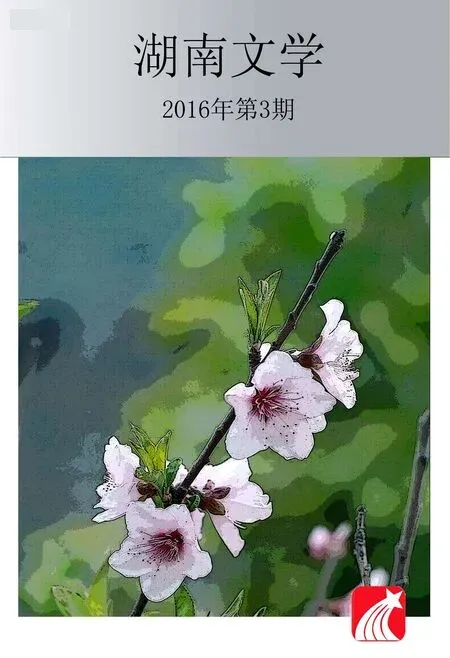岁月深处的家园记忆
→宋世兵
岁月深处的家园记忆
→宋世兵
一
从迁陵西行四十余里,拐弯处,荡漾着一派爽爽朗朗的田园春色,弥漫着丝丝缕缕鸟语花香的气息,勾留了旅人的匆匆行色。
一方约三百多亩的台地沿河铺陈舒展,春意盎然。脊背般的山峦眠在春困里,任由台地依偎绾眷,袅袅炊烟腾起的地方,一幢幢吊脚楼稀疏地贴近山脚,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台地与河风亲吻处,下切成一条宽约百余丈的河流,土家人唤之白河,亘古流淌,在村庄与台地的上空演绎着唇齿相依的千古恋情。
村庄、台地和白河,三者不可或缺,相互依存,氤氲为押马坪动人心弦的生命、亲情和爱情的底色。如果以白河为纵坐标,以村庄为横坐标,勾勒人生轨迹,从纵横交错处的那一个细微的圆点出发,以脚步丈量生命的历程,是起点,也是终点。
白河向右,我向左,从村庄出发,肉体与精神的生命经过放逐,最终皈依故园。
仰望过梅里雪山,越过云贵高原,穿过三江平原;行走沅江,停靠洞庭湖,拥抱大海。高山平原,江河湖海,似乎都不曾妥贴地安放我弱小的身躯与灵魂。行走之间,曾不止一次地发问: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白河去而来,我追随着白河永不停歇的脚步去而来;
台地去而来,我循着播种与收获的号子声去而来;
村庄去而来,我沿着炊烟升腾飘逝的方向去而来;
白河左岸——我的故乡,我的家园,游子依依不舍的眷恋。
我从白河的涛声中走来,向白河深邃的目光里走去。
白河消逝的尽头,隐隐约约浮现祖辈跋涉的背影。传说中的祖辈从遥远的江西一路向西,或迫于重重厄运,或迫于连绵的战火,或迫于突兀的灾害,水迢迢,山重重,路遥遥,披荆斩棘,历尽千难万险,在一个名叫沅陵的地方作短暂停留。这里的青山绿水给疲乏身体补充了新的能量,壮起远行的行色。一部分人留恋这好山好水,停止了跋涉的脚步,余下的再次抖擞精神,沿沅水继续逆流而上,途中拐入白河,至江口,又一次寻着清水江逆行,本想在普溪作长久的打算,一百年或至永远。我的曾祖父莫名地又一次驾一条船顺清水江而下,至江口拐进白河逆流西行,约三十余里,在猫滩下的一个渡口,就此扎根,做起了野渡里第一个摆渡人,战激流、搏风浪,斗漩涡,将生命放逐于风口浪尖上,在白河左岸押马坪与右岸官山之间架起了一条情感永续、生命轮回的绿色通道。
关于野渡和祖辈的记忆,在我幼小心灵的深处,只残存那么一星半点。每逢年节,无论天晴下雨,摆渡人背起背篓,像一条爬虫,蠕动在通向四邻八寨的山路,在小路的尽头一栋栋吊脚楼前,奉上吉言,赔着笑脸,向每一个主人打躬作揖,一升谷,一箪包谷,一两个高粱或玉米或糯米粑粑,一瓢残羹冷炙,摆渡人艰辛的生活和卑微的生命,曾无数次撞击我幼小的灵魂。摆渡人是白河上漂荡的浮萍、无根的水草。然而河流无私地给予了卑贱生命绵绵不绝的营养。
白河时而暴戾咆哮,时而温情脉脉;时而波涛汹涌,时而深沉涵养;时而排山倒海,时而低吟浅唱。在左右两岸人眼底,白河是一条孕育生机与生命的河流,一直都是子子孙孙顶礼膜拜的神明,供在毕兹卡的神龛。
六岁时,我第一次见识了河流的不怒而威,“欺山莫欺水,欺水要见鬼”的乡间谚语,在我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春夏涨水季节,五六个同伴目睹了县游泳队员矫健的身姿,像鱼儿一样在河边一条长约一千米的沟槽中自由滑跃。待他们完成训练走后,同伴们模仿队员的姿势先后扑入水面,我隔房的兄长仓促入水,被水呛住,挣扎了几下,便沉入水底,不再出来,伙伴们惊慌失措。村里千百年流传下来规矩,但凡意外死亡,一律视为伥死鬼,禁葬高山,只能埋在河边,让河水千万次荡涤洗刷污秽的灵魂,以这种诡异的方式,救赎生命以全新的姿态转世轮回。
这时节,是白河左岸男人的最忙碌的时候。伐倒在深山老林中的柏木、枞木、杉木已风干,正好乘这季节顺溪流放出山,捆绑在一起,扎成木排。还有囤积一个冬天的桐油,一些知名不知名的山货,装上船,吆喝放排佬为伴,一起下迁陵、王村、浦市、沅陵、洞庭湖、汉口,满世界地推销白河两岸的风物去了。二十岁之前,我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便是古丈罗依溪,去看铁路桥和火车,就是这时节随驾船的父亲去的。山外世界留给我的最初影像,除了铁路桥,还是铁路桥,除了火车,还是火车,其他新鲜事物,脑海里几近苍白。
白河里,沉淀着祖辈,父辈和我辈诸多的痛苦与欢乐,就像一条脐带,一头拴住我的心脏,另一头扎根于村庄下的那一方台地地脉,今生今世永远也挣不开,脱不掉了。白河就是贴在我身上的一块胎记,无论我离开多远多久,河流的喜怒哀乐,始终如影随形,相伴一生。
汛期里,小溪涨水,大河满,正是练胆的最佳时节。桃花汛里,大河的鱼儿白天拼命地向小溪里游窜,深夜回游大河,在溪水涨落之间,瞅准时机,选准落差大的地点,搬开河道中间石头,呈倒喇叭状围堰,掏沙堵住石头中的间隙,喇叭口铺一块光滑的石块,石块下安好牢筛,用马鞭子树枝盖住,等到半夜过后,一个人胆战心惊地摸到围壕边,惊奇地清点渔获,那种在惊悸之中收获快乐的经历,经久耐人回味。秋季里大河涨水,说涨就涨,来势汹汹,飞流直下,瞬间淹没了田地,冲刷一切敢于阻挡河水的事物。来不及转移的木料、猪、牛、羊等等,被河水猝然冲下,顺流漂浮。见状,家里穷得揭不起锅盖的同伴,开始打赌,比谁抓得木料、牲口多,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扎入飞流的洪水中,向漂浮的猎物游去,顺着水流将它们一一拖回岸边,脸上洋溢着与河流斗智斗勇的得意的神色,博得大人们的夸奖。偶尔也有那么一两次失手,不仅没抓得,反而被河水吞噬了年轻的生命,留给亲人们的是呼天抢地的疼痛和哀伤。河边的人家,每家每户都备有用油桐树杈围成一个圆圈、上穿渔网编织成漏斗状的捞兜,每当涨大水,大人或小孩拿起捞兜往河边赶,顺着飞流的河水朝下捞起,时常不落空,兜里跳跃着飞坨、鲶夫子、鲫鱼、鲤鱼等等,收获着只有汛期里才有的欢乐与满足。
白河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天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无论怎样待她,她即使发怒的时候,也在向人们奉献着信心、财富和快乐,传递着宽容、谦爱和幸福。
祖辈的脚步从未离开过白河,我辈的脚步虽离白河渐行渐远,目光始终沉醉在白河的涛声里。关于白河,村里人一直做着一个高峡平湖的梦。缘起于本村的一个在中南水利勘测设计院工作的王姓子孙,曾多次往来碗米坡下实地考察,昙花一现。时过境迁,上个世纪行将谢幕时,传来喜讯——碗米坡电站开工建设。消息就像春天的布谷鸟,扑棱地展开翅膀,飞到白河两岸的土家山寨,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白河从此变了模样,坝上碧波荡漾,高峡平湖,鱼翔浅底;坝下水流潺潺,气若游丝,鱼群销声匿迹。就像川剧变脸,时而容光焕发,争奇斗艳,生机勃勃,时而面如菜色,气息奄奄,萎靡不振。白河在物欲的横流中彻底失去了本色,以另一抹星星点点的亮色舔啜着皲裂的伤口。白河上巍然耸立的那一堵芳华,时常挂在人们的嘴角,贴上人们的笑脸,成为小城人引以为豪的时尚模特,露点流行为普遍的审美怪癖,我不知道怎样面对这场盛宴,应该欢呼?还是反思?人类总喜欢操纵自然的命运,殊不知河流适时地掌控着人类的命运。
我从村庄的炊烟中走来,向村庄的心脏里走去。
打那一腔激越的号角声给村庄的天空撕开一个豁亮的口子,我的父辈挽起湿漉漉的裤角上岸了,从渡口到村头的百余级青石台阶,纵是很短,我的祖辈足足走了两个多世纪。至今,我的父辈仍然保持着打赤脚的习惯,即使穿上鞋,也时常忘记套袜,白河烙上的印记太沉太深了,几辈子都无法抹去。挽起裤角上岸,打起赤脚下田,开始换一种姿势,变一种活法,沾一沾村庄的烟火气息。
码头那条青石长阶径直通向村庄的腹地,村头沿河壁立着一堵高约二十丈的陡坎,村庄的历史层层叠加,累积成水波纹的厚土。曾经有一群手拿洛阳铲的考古学者,沿河而来,目光投向这里,企图寻找一把解开白河、押马坪和台地的生命密码的钥匙,复活河流的记忆,还原村庄的过去,寻觅土家先人的踪迹。一件件青灰色铄石刮削器、砍砸器和石斧,静静地躺在厚厚的黄土中,重见天日,考古学者如获至宝,结论为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一方小小的台地之下竟隐藏上万年的岁月之谜,让我对白河、村庄和台地肃然起敬。
村庄的历史一旦被激活,记忆之河便敞开闸门汤汤而来,浩浩奔流。伐木围巢,一栋、两栋、三栋……吊脚楼依山而立,一字儿排开,齐刷刷地面向白河,像一群神情俨然的士兵向崇敬的将军行注目礼。那条老街扁担似的延伸,一头挑起白河岸边的冷月,一头连着村庄的心房。
码头之上那一幢风雨飘摇的老屋,父辈分得一间,岸上生活开始有了生机。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正值童年,岁月早已风干了孩提时代的泪痕。父亲从县简师毕业后,在本村的小学里任教,一个月的薪俸是一只老母鸡价值,家里还有三只嗷嗷待哺的小鸡。父亲辗转难眠,艰难地作出人生重大抉择,放下教鞭,舍弃了那只老母鸡,选择了三只小鸡,回到家里,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父亲弱小的身躯内竟隐藏着巨大的能量,挖蕨根、挖葛根,不输村里膀大腰圆的好汉。母亲把蕨根、葛根捣碎,砸成浆,过滤风干成淀粉,尽管缺油少盐,我、大哥和三弟却吃得津津有味,苦日子不若,苦中有甜,让我们对大自然的赠予,有着天然的亲近与神秘。
父亲的能干在生产队里是出了名的,大队看中了这点,让父亲挑起了生产队队长的担子。为使乡亲们的日子好过点,父亲决定造一般货船,下迁陵、沅陵、洞庭,做起了外销木材、山货生意。每一次外出后,是长久的等待和煎熬,我的母亲、奶奶和全村人牵挂着他们的安危,生意的好坏,关系着全村年底的分红多寡和日子的荣枯。算计着每一次外出归期,我时常站在码头上眺望,企盼一粒糖果、一串灯盏窝带给我的那份喜悦。奶奶去世那年月,父亲正在远行,不得音讯,未能见上奶奶最后一面,好心的大伯大婶,赶来帮忙料理完后事,这是隐匿在父亲心头久久难以释怀的伤痛,一直不愿提及。
父亲为人忠诚、本分、厚朴、包容,在村里有口皆碑。村里凡有红白喜事、大屋小事,父亲都愿意帮忙,从不计较报酬,从不声张,低调行事,举止谦恭。祖上本是一个外来户,没有任何可以炫耀和挥霍的资本,这决定了父亲的性格和行为习惯。有一次,父亲外出帮一户王姓人家做事,夜幕时分,我去接父亲,主人留父亲吃晚饭,恰好赶上,主人的儿子在饭桌下使坏,一个劲儿地拧我手上皮肉,钻心地痛,望着父亲那茫然的目光,我只得隐忍。因为有这样一次被人轻视甚至蔑视的经历,打那时起,我起誓,一定要走出村庄,走出这个伤心之地,干出个宋姓子孙的样子,回击那些蔑视的神情和目光。
包产到户后,村里开始改变模样。人们就像挣脱了缰绳的马在村庄的天地间任意驰骋,各自编织着未来的生计与活路。父亲瞅准时机,承包了生产队里的锯木器具,揽起各家各户锯木料的活儿,早出晚归,足迹遍布了方圆百余里的村村寨寨。那一截截滚圆的树干,在柴油机和锯片嘶鸣的混响中,变成了房屋的椽皮、壁板、枋子和姑娘出嫁的嫁妆,装点着村庄的日子与生活,父亲也收获了浸透心血与汗水的花花绿绿的钞票,给我们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及时的营养。我、大哥和三弟像五月的庄稼步入了春播、秋收的季节。平时,我们把上学读书看成一件极其神圣的本分,勤奋用功,很少让父母操心。大哥远涉葫芦二中高中毕业,高考上了中专线,复读两年上大专线,未被录取,后经父亲艰难求证,大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母始终向我和三弟隐瞒了大哥的病情,直到大哥在一家工厂办公室主任位置上干得正欢的时候,病情复发,生命猝然休止,正在昂洞中学教书的我和正在保靖民中读高三的三弟,才得知这一晴天霹雳。大哥的离世,让三弟的高考一败涂地,而我读完了大哥遗下的一大厢书籍,视若珍宝。在埋藏大哥的那天,我将他十分珍爱的一本泰戈尔诗集放置在棺木的顶端一眼能瞧见的地方,陪伴他的灵魂远涉,心中默念他十分喜爱的于右任的一首诗:“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任思绪横飞,眼泪横流。押马坪宋氏三兄弟读书是出了名的,常常被四邻八寨当作教育子女读书成才的口头教材。自从我考上大学以后,全村陆续出了十多个大中专生,成为各家各户憧憬美好未来的希望。
沿着码头拾级而上,青石铺就的老街蛇行游走,宽约两丈,两旁的吊脚楼和商铺临街而立,黄壁黑瓦。每月逢二、五、八,正是小街最为热闹的日子,沿河上下四邻八寨的村民和商贾自码头鱼贯而入,吆喝声、买卖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华的景象。小街的繁华与落寞随岁月的荣枯周而复始,默默地见证着村庄的沧海桑田、小街的起起落落,村庄命运的起起落落、村里人前途的起起落落。碗米坡电站开工建设后,一条条宽阔的水泥大道从村中穿越而过,村庄的容颜随着一栋两栋三栋小洋楼点点滴滴地改变,村庄笑貌面向公路集体向后转,村庄的声音时常被往来穿梭的汽笛打断,村庄的岁月亦如白河的流水,潮涨潮落,时断时续。
我的村庄和忙碌在村庄的乡亲,无论贫富贵贱,白河一视同仁地给了鲜活的记忆,爱并痛着,痛亦快乐着。当我离开村庄,一次次远行,才发现始终活在村庄的背影里,村庄早已为灵魂贴上了标签般的印记,如影随形,无法割裂。
我从台地茂盛的庄稼中走来,向台地层层叠叠的褶皱里走去。
岁月去而来,脊背般的山峦与流纱样的河流在这里婉转缠绵,耳鬓厮磨,相亲相爱,诞下爱的结晶,经时光磨洗,锃亮如昨,丰盈肥美,亦如大地母亲的双峰,无论高傲,还是低垂,让每一个子孙垂涎不已,恋恋不舍。
台地不仅生长庄稼,生长五谷杂粮,还生长生命、爱情和亲情。台地上的子孙原本就是台地喂养出来的一束束金黄金黄的稻谷、一枝枝红得发紫的高粱、一株株吐穗扬花的苞米、一藤藤葫芦似的落花生、一串串鲜红鲜红的辣椒,合着春夏秋冬四季的轻盈节拍,在村庄的时空里,交替展示无与伦比的神奇与壮美。
爽爽朗朗的台地,从村庄的腹地生发,呈伞面状散开,弧面白河蜿蜒流淌,自山脚向上延展抬升的是一绺绺梯土,朝河流铺陈的是一片片鱼鳞状波光潋滟的水田,庄稼在季节里生长、拔节、吐穗、扬花,直到累累硕果挂满枝头。
在麦苗泛青、吐穗扬花、油菜花含苞待放的时节,冷冷清清的月光下,台地成为儿时伙伴游戏的青纱帐,捉迷藏的游戏一幕幕在这里上演,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插秧前后,台地一派忙碌的景象,大人们吆喝一头大水牛,扛上犁铧,翻耕肥沃的田地,一片片泥土在吆喝声中瓦片状翻卷,一字儿排开,整齐壮观。接着用耙密密匝匝地往复梳理,瓦泥渐渐光滑如溜,状如竹簟。我时常跟在牛屁股后,瞅着翻卷的泥土中的泥鳅与黄鳝的身影,迅捷下手,总能捕捉到一篓的美味佳肴,沾沾自喜。春夏之交,正值庄稼地里包谷苗、黄豆苗拔节疯长时节,太阳在头顶毒辣辣地照着,弯腰置身禾中锄草,长时间劳作,汗水湿透了衣背。累得要命的是秋收,跟着父母背着打谷机去稻田里打谷子,金黄色的稻谷在烈日中迎风摇曳,美丽动人,弯下身子手拿镰刀割水稻,整齐地摆成脚肚子大小的堆堆,割完后递给父亲,父亲把打谷机踩得呼啦啦地响,一束束稻谷被铁磙子打落在谷仓,堆满后装进麻布口袋,然后又接着打,往往要三五天才能打完,打完后一袋袋往家里背,倒在晒谷坪里晒干,装进粮仓,人早已累得气喘吁吁,累并快乐着。我的儿子辈早已远离稼穑,没有尝试过劳作的艰辛,童年沉迷于网络虚拟的世界,做着与我和我的父辈、祖辈截然不同的梦,我想过各种办法让他们远离网络和游戏,皆是徒劳。在这个钢筋水泥建构的城市森林里,除了上网玩游戏,他们别无选择,我非常恼火,他们的童年已经快要完结,不知道未来又是什么样子。
老街像从村里那些能工巧匠弹指间崩出的波状墨线,线头弹了一个粮店,一所卫生院和一个油房,缀落在我家房前屋左屋右,线中系着一个气派的商店,线尾挂着一所片完小,让我见识了与村庄和台地不一样的世界,感受了别样的世道人心。
寒冬腊月,闲置了大半年的油房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油房上空冒着一串串油烟,响起嘭——嘭——的油锤撞击声。生产队将从山里采摘的油桐籽、茶籽、油茶籽、花生运进油房,烘干、碾碎、榨油。因为饥饿,对于榨花生特别关注,时常乘着夜月,偷偷地爬到火炕边偷花生,偶尔也被看守炕的人逮住,一顿训斥。花生炕好后,村里的伙伴争先恐后地钻进炕底热烘烘的大坑里,捡拾炕上散落的花生,衣裤口袋里塞得满满的,往往被弄得灰头土脸,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傻笑。
粮店是备战荒年的产物,高高的灰白围墙上用红漆写着“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的标语,这里是四邻八寨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天天有人进进出出。当那一船船统销粮从迁陵码头运输到这里,每一个麻袋足足有一百五十斤重,消息传到村里,年轻后生和中年汉子迅速背上背笼往河码头赶,背起粮包往店里送,每包赚取五分钱的血汗钱。因为离粮店近,每次运来统销粮,店里工作人员首先告诉我父亲,父亲从不缺席,粮包数量从不输年轻后生。有一年,大哥莫名其妙地生了一场大病,村卫生院的赤脚医生治疗不好,家里急得团团转,店里好心的大伯大婶让我父亲加工了一万斤稻谷,赚得几十块钱加工费,大哥才被送往县医院救治脱险。我外出读书时,不用背粮,靠转粮食指标到学校,学校再到当地粮店结算,免除了背粮长途跋涉的辛劳,得益于建在家门口的那个粮店。如今,白河的繁华落尽,粮店留给台地一片荒芜的废墟,留给我们难以割舍的情怀。
寨子中央的那个聚焦目光的商店,货物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奢望。只有到了年节,母亲总会给我几分钱,我一溜烟工夫跑到商店花掉了。偶尔还会带我到商店购几尺赊销布,做一身新衣裳。商店对我来说是莫可名状的诱惑,即使心里痒痒的,也不敢靠近,站在远远的地方,眼睛干巴巴地瞅着,情形实在可怜。
村尾的那所片完小是我童年时期逗留最久的地方。学校靠山面河而建,呈汉语拼音字母“F”状,上下两级,合抱柱头架构的教室每间宽约二十米,深约十五米,黄色的板壁,黑色的瓦,大致有十多间,有的被隔成教师的宿舍。上一级是操场,下一级是运动场,场边是一壁陡坎,密密地生长着苦楝树和柳树,阴翕蔽日。学校规模最大的时候,与中心完小旗鼓相当,非常的热闹。我因为淘气,留了一年学,再又赶上五年学制改为六年学制,多读了一年,在这里,我度过了七年光阴。毕业时,教我语文的宋姓老师带我下城参加保靖民中招生考试,结果差几分失望而归,分数上了县办保靖五中录取线,十四岁才得以迈进中学大门,三年过后考入了心仪的保靖民中读高中,又三年入吉首读大学,换了一种活法,离开了这一方台地,闯世界去了。
白河,台地,村庄——构成押马坪永不消失的风景,贴在我的面庞,嵌入我的胸膛,植入我的记忆,装进空空的行囊。
每一次告别白河,江河湖海的目光总是被她牵引;
每一次挥别台地,高山平原的地脉总是随她律动;
每一次离别村庄,高栋大厦的怀抱总是被她仰望;
白河左岸——我的故乡,我的精神家园,从此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