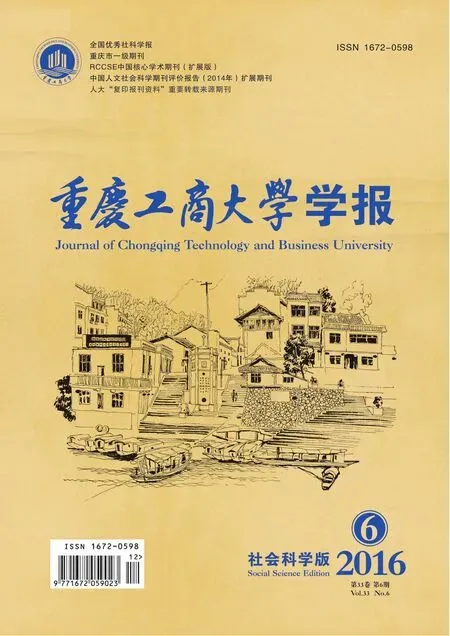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
陈用芳
(福建商学院 思政部,福建福州 350012)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
陈用芳
(福建商学院 思政部,福建福州 350012)
如何实现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是近代中国人艰辛探索的问题。毛泽东继续这种探索,他既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又充分肯定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他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践中,坚持现代化追求的社会理想目标。他不仅把共产主义视为理想,而且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改造现实的运动。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现代化带来了一些挫折,但其中包含的批判超越精神、人民主体观念和道德建设思想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代化;社会主义;理想主义;毛泽东;人民主体;再认识
现代化是在科技发展推动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导致的开放化、启蒙思想形成的理性化过程中形成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毛泽东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其中既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有一些实践上的失误。认真分析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现代社会的悖论与近代中国人对它的求解
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的附录中针对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提出了一个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命题。他认为这一命题起源于卢梭。卢梭作为影响深远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呼唤自由平等,主张建立理性王国的同时,又发现了科技进步和理性主义的“社会工程——技术”取向必然对社会道德造成破坏,他对此表示了种种担忧。他把希望寄托于出于公心的“大立法者”。但这样又会造成“领袖决定论”,导致个人专断,人民的自由权利也必然不复存在。
资本主义发展证明了“卢梭命题”的深刻性。虽然也有人提出要倡导人文主义和新的宗教精神,但工具理性却长驱急进,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道德的江河日下。19世纪初,站在道德理想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从理想主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设计未来社会。但史华慈说:“作为伦理剧的历史如何与作为技术经济发展和社会理性化的历史结合起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卢梭和圣西门并未握手言和。”[1]219实际上,技术进步导致的现代化与道德理想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悖论性命题。
马克思不是单纯从道德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依此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从经济的角度论述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并在其中论述资本主义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把社会主义看成从人的“异化”向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的历史过程。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包含了丰富的现代化思想,但他并没有提出现代化的概念。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下,传统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也开始了变革传统社会,建立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追求。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如同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把未来社会描绘成一个“理性王国”,而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根据新的时代特点重新阐释传统的大同理想,并以此为根据追求现代化的目标。
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提出了发展交通通信、实行新闻自由、推行民主政治、兴办现代学校以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同时他也敏锐地发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它虽然使“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治更有精密”[2]281;但是他又揭露西方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劳苦大众的苦难,并预言将发生“铁血之祸”,根据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把世界大同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并依此规划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启超曾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3]750
孙中山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不同,但他也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提出现代化任务的。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他不仅制订了气势恢宏的实业计划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而且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为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握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4]84为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他明确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4]802
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目标和道路选择,其中体现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与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的关系。“卢梭命题”在中国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这其中,“社会工程取向”主要表现在经济变革的现代化追求上,而道德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为理想主义。如何在这二者之间保持一种相对平衡,成为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选择中的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当然,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他们毕竟历史性地提出了这一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康有为大同思想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评价中,不少学者往往以“空想主义”“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为资本主义披上美丽外衣”对其进行理论定性。这就掩盖了其中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追求精神,以及大同思想和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深刻社会意义。其实,理想主义是社会变革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人们往往就失去了对现实的判断能力,也无法点燃心中之火,形成一种历史使命感,进而寻求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以历史主动性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或许可以认为这种理想主义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是美国学者赫茨勒不仅把乌托邦思想家称为“真正社会巨匠”,而且认为他们是“新思想的源泉,正如许多重要作家所证实的那样,可能也是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哲学以及以之作为基础的有关运动之奠基人。”[5]286应当说,大同思想和民生主义为中国现代化选择了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
二、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及其对大同思想和民生主义的超越
现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主题。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有远大的抱负,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为己任,投入革命洪流中。他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重大问题,从实践上把现实与理想联系起来,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进行分析,进而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任务,同时也提出了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坚信革命的正当性并对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心。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6]102正是因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所以也就形成了顽强的革命意志,宽广的革命情怀,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走向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国家富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
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毛泽东高度重视孙中山的思想遗产。他不仅称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而且还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7]111他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这个革命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与三民主义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他又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三民主义才能实现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他还说:“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付诸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的行动。”[8]184
在谈到中国未来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不能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而是要建立在工业化之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9]186
毛泽东在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现代化扫清政治障碍,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同时,更重视理想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他的理想主义不是空洞的,而是与革命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要求革命队伍有严明的纪律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道德要求。他还重视以道德理想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特别是中国的基本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也就更要把无产阶级思想灌输到农民中去。
史华慈说:“对毛泽东而言,无产阶级意味着自我批评的美德,一切服从集体需要的献身精神,毫不松懈的努力,对敌人的无比仇恨,铁一般的纪律等等。……尽管毛泽东强调群众是智慧和美德的基础,然而无产阶级的观念作为一种理想,仍然需要群众去努力实践。”[10]136他还认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不是从抽象的公理中推演出来的,而是有强烈的民众取向及对群众智慧和美德的歌颂。中国传统文化给毛泽东的思想造成了深刻影响,“他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式的。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兴趣甚于对西方思想的兴趣,以至他用更高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包容它们。”[10]133毛泽东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普罗米修斯式的激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前夕,毛泽东说:“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1]1360
从根本上讲,不论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最终目标上同共产主义都不矛盾,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与共产党人有共同之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超越他们,就在于他不仅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把它视为一种指导思想,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还把共产主义看成一种运动,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造就出一代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毛泽东理想主义在其中的意义
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已经有了大约占国民经济10%的现代型工业经济,但是还有占90%左右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新中国的成立就“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11]1320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领导人民进行“一化三改”,而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初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的情况下,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其目的是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在社会组织形式上通过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重视生产力发展,但又有唯意志论的倾向,这就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并由此助长了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潮,违背了他曾经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理想主义,理论界多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或民粹主义。这个问题只有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认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他又把未来才能实现的理想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去推行,从而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但我们必须看到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中国的现代化确立了明确的理想主义维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现实主义要求人们从实际出发,把握客观规律;理想主义则要求人们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并在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中不断寻求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按照理想复制现实必然造成种种困境,失去了理想又会在认同现实中无所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创造性发挥中追求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毛泽东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恶果,他不愿中国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因而也就以理想社会判断现实,希望中国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共产主义。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从肯定的意义上把毛泽东的社会理想称为“乌托邦”,并认为其中包含的批判超越精神,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保持生命力所不可缺少的因素。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由于缺乏那种乌托邦精神而渐渐变成一种使自己适应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12]25他同时还指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使人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从而在道德上支持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勤劳、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的形成和发挥。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对未来的意义上讲,“他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都起着一种使人们行动起来,改造世界并改造他们自身的作用。”[12]192应当说,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其次,它体现着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毛泽东历来视群众为真正的英雄,他不仅坚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而且担心中国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道路,必然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人民群众走向苦难的深渊。这就使他相信群众中有一种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张通过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现代化建设。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光环下的民粹主义,其实,这种判断也是值得商榷的。民粹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群众理想化,并强调群众的意见永远高于精英的见解。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虽然他多次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领导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但这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主张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在一起。
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在一种视“人民”为有组织的整体并赞美他们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中表现出来的。他说:“毛泽东总是认为,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指导。毛泽东总是表示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智慧,这却是列宁既不具有也不曾表示过的。毛泽东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实际革命效力的评价,是与民粹主义对群众基本革命创造力的信任和设法把一切都‘归入’群众之中的冲动结合在一起的。”[12]97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和群众观念结合起来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在实践中仍然在求解“卢梭命题”,并认为“道德理想”比“社会工程——技术”取向在其中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
再次,它是对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毛泽东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希望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当他看到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并认为这种现代化也必然造成社会腐败丛生时,他就忽视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并在中国展开了共产主义的实践。他相信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力量,可以形成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共产主义很快就能实现。这样,他就把人的主观意志和道德精神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了,但德国学者鲍吾刚称之为“伟大的悲剧”,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对毛泽东这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既要看到它给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又要看到它给人们提供了哪些启示。他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也重视发展生产力,但他相信精神的力量和良好的道德会使科学技术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坚信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他不是单纯强调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而是主张在共产主义目标下寻求它们的意义,并认为物质的丰富并不一定能保证共产大同社会的到来,只有在良好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准则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他把人们的价值观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应当说,毛泽东在物质与精神、生产力发展与道德追求关系的认识上更重视后者,从而也就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形成了误区。
研究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成功和失误,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人们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地坚持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了“告别乌托邦”,进而否定理想主义在现代化中的意义。这样,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代化的现实主义维度形成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工具理性主义通行了起来,理想主义则走向了衰落。我们不能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对立起来,既不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实行共产主义,也不能在现代化中丢掉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要不断寻求二者统一起来的实践途径。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实主义往往使人目光短浅,人与人的关系冷漠无情,降低人的品质。而理想主义使人变得目标远大,追求高尚,并从精神上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并在理想的阳光照耀下发现现实中的黑暗角落,在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中探索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有永恒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M].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3]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4]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 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2] 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校:杨 睿)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Idealism of MAO Zedong
CHEN Yong-fang
(IdeologicalandPoliticalDepartment,FujianBusinessUniversity,FujianFuzhou350012,China)
How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ism is a challenge of hard explo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MAO continued the exploration, and he both highly thought of Sun Yatsen’s livelihood and fully affirmed the cosmopolitism of Kang Youwei. Therefore, he applied Marxism to the practice of China and adhered to the modern social idealistic goal. Not only did he consider communism as the ideality, but put it as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realistic movement. Althoug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eople’s commune movement had caused a number of setbacks to the modernization, his critical surpassing spirit, the concept of the people’s main idea and the moral construction thought are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modernization; socialism; idealism; Mao Zedong;main body of people; recognition
10.3969/j.issn.1672- 0598.2016.06.002
2016-05-20
福建商学院校级科研立项课题“‘大众文化’批判与理想主义建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SZKQ201401)
陈用芳(1964—),女,福建南平人;福建商学院思政部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A84
A
1672- 0598(2016)06- 0008- 05